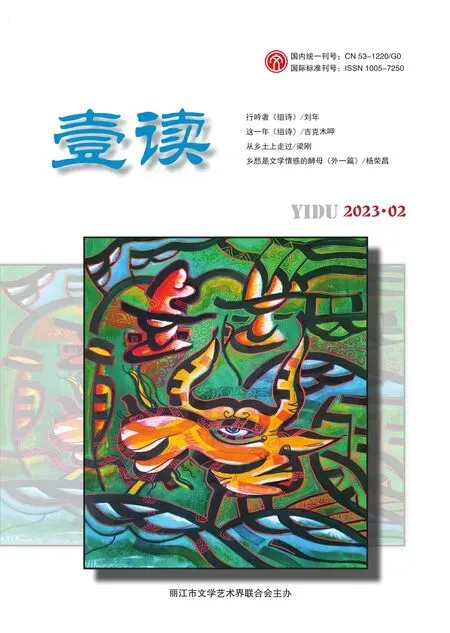从乡土上走过
◆梁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
每年清明节期间,我们村的人都会集中到一个地方——县城西面的龙潭坡山上,给去世的先人上坟。
墓地是多年前老村长为村人置下的,占地十几亩,几十年下来,坟茔从当初的零星几座,现在已是星罗棋布。不少死者还是我和村人一起,把他或她,从晃桥河边那个小村,用结实的黄栗木杠子,抬到这里入土为安的。外村人到这里,都夸赞这里的风水好:山上长满云南松、黄栗树和一些土著灌木,站在这里,还能把整个城区望得一清二楚。
村人去给亲人上坟时,按照习俗,要在周围的每个坟头插一炷香,算是打个招呼,就像活着时见面递支烟或送上一个笑容。人到中年以后,在坟头点燃香插好时,我会在坟头小坐一下,这一来激活了童年一些似已沉淀的记忆,空间的距离不在了,时间的距离也被抽空了,甚至于感到我就站在他们中间。想起我尊敬的作家苇岸写过的一段话:“在造物的序列中,对于最底层和最弱小的‘承受者’,主不仅保持它们数量上的优势,也赋予了它们高于其他造物的生命力。草是这样,还有蚁,麻雀,我们人类中的农民也是其中之一。”我有了为他们写一本书的心思。现在,还是让我先写下其中几个人生平的片段吧。
“聪慧能干从不弃 慈爱如母感天地”。这是伍菊花大婶的墓碑碑文,字不成体,但对这个一生劳碌的女人,碑文的意思是贴切的。当我俯下身仔细打量墓碑,内心里却充满了仰视之情。
在我的记忆里,伍菊花大婶年轻时大眼小嘴,满头黑发,家里家外的活计都拿得起放得下。十五岁那年,她被我们村长着一张红扑扑大脸的男人朱家汉,用一匹又瘦又小的小毛驴娶到我们村。她嫁了一个好人家,虽然贫穷,但公婆和男人都待她好,不让她干重活,不让她冷着饿着。在她三十岁那年,已经生下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就在给老三过完满月的第四天,男人却死了。她守孝三年满后,白春联才换上红春联,不少人都上门来劝她改嫁,被她婉拒了。但一有什么伤心事,她就带上她的三个儿女,去亡人的坟头大哭一场,回来后继续过日子。
这期间,尽管她的三个儿女吃糠咽菜,她却不让他们受一点委屈。她无师自通做得一手好饭菜,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请她主厨。记得她的手指细长,饱满的指甲用金凤花给浸得深红。在晃桥河一带的村落,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一些金凤花。金凤花开如火的时节,每天临睡前,大姑娘小媳妇们便会把多汁的金凤花捣烂,用布条包在手指甲上,次日一早,她们便会有一双指甲红红的手了,用水也洗不掉。肉煮熟,她会趁人不注意,咬一大口含在嘴中,悄悄走出来,吐给等在外面的她的几个儿女。就是在我们孩子的眼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但村里没有人说闲话。
日子到了腊月,做豆腐的日子到了。菊花大婶做得一手好豆腐。她做的豆腐又白又嫩,家家请她去帮忙。我家就请她做过豆腐。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出锅,压水……每一道工序,都一个人,就像在表演,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那时她好像不到四十岁,大眼小嘴,满头黑发,腰身丰润轻灵。夏天,在河里洗过澡后,她一张圆圆的脸上会泛起淡淡的红晕,随手将乌黑的长发用手帕扎在脑后,这时的她,年轻清爽得像个大姑娘。这年腊月的一天傍晚,大儿子相中的姑娘和媒人突然上他们家。她惊喜万分,她向正帮着做豆腐的人家讨了一大块,用个大碗端着回家。路上,一不小心,一跤摔倒,额头血流如注,她忙不得抹一把,奔向摔得粉碎的豆腐和碗,一点点用手指捏起没有被路上灰土染脏的豆腐。我和村里几个背书包的小伙伴站在一旁,一瞬间,我看到“辛酸”一词在世间的形象翻译。
土地下放后,她在自己家开了个豆腐坊,儿女们为她打下手。豆腐坊生意异常红火,她家很快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家。但她的儿子嗜赌如命,常有人三天两头堵在她的豆腐坊前向她讨赌债,这时,她会将自己那颗骄傲和破碎的心深藏起来,面无表情地将当天收的钱交给人家。好在她的豆腐照样好销,除了送到刚刚在县城兴起的超市,村人是主顾,每天一早,妇女老幼就会端着碗,两角三角钱买一碗刚出锅的豆腐脑喝。男人们呢,会揣上酒,割两块豆腐打成片,拌上辣椒酱油,摆在她家豆腐坊闲下来的案板上下酒,一消磨就是几小时。傍晚,女人们又会上她家,买臭豆腐回去炖吃。
这年,她请村里的木匠在二楼上用坚实的椿木打了一个带梯子的、足有半间屋子那么大、两米深的柜子,用来储放黄豆。木柜子下面留个可开可关的口子,只要轻轻一拉开闸门,黄豆便像金水般奔涌下来,下面盛豆的竹箩满了,轻轻一关,要多省事有多省事。有一次我跟着扛豆包的男人上了梯子,张望过那个木仓。大豆从麻袋口倾斜而出,发出“哗哗”的笑声,落在仓库里的同类身上,还要滚动一番,才慢慢落实。楼上有一种非现实的色彩,光线半明半暗,像凌晨或薄暮,但豆子们闪着黄澄澄的光芒。
大约在七年前冬季的一天,她忽然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家人到处寻找无果。几天后,家人隐隐闻到非同一般的臭味,最后确定臭味是从大椿木柜子里散发出来的。打开闸门,黄豆飞速下流,淌满了一地。不一会,只见她露出身子来,一双长年累月被水泡得变形的双手高举着趴在柜子一角,一张脸金黄如纸——揉皱的黄纸,满嘴塞满黄豆。据公安人员现场侦察后推测,她一定是去察看豆子时不小心一脚踏空掉下去,陷在黄豆里出不来给闷死的。
豆子也能淹死人的事,比鸟的翅膀还快,在晃桥河一带的村庄传得沸沸扬扬,外村很多人成群结队,跑到她的豆腐作坊看稀奇。她死时,还有一个月就满六十八岁。为她办丧事时,赌徒儿子拿不出一分钱,最后还是村长出面,派人将那些埋死她的黄豆偷偷运到远处卖了,总算替她购置了一口还算像样的棺材,让她入土为安。
前些天,读到作家刘亮程的散文《寒风吹彻》,我忽然想起了伍大婶:“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做豆腐是很磨人的营生,儿孙们吃不了这份苦,没有人肯接她的班。她的坟头还没长草,她家的豆腐坊就倒闭了。
“挥毫落风雨 铺纸生云烟”,这是画匠宋传书老人的墓碑碑文。关于他,早年我用稚嫩而真切的手笔写过一首题为《乡村画匠》的小诗,抄录于下:
门、框、窗,家具,甚至棺材
都是他的画布
在我们晃桥河两岸的村寨
活跃着一个姓宋的画匠
作业时习惯将笔尖含在嘴里濡湿
他走村串寨,爬高上低
嘴巴总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看他风风火火的架势
似乎把整个田野搬到他的画布上
也不在话下
见鸡画鸡见狗画狗见猫画猫
但画得最多的
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龙啊凤
是人们没有见过的神啊仙
他画的花你能闻到它的香
他画的火你能感到它的热
他画的桥你能在上面走
他画的河有鱼儿在游
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厉害的画匠
可有一天他遗憾地告诉我
他总是画不准姑娘们
脸上的那抹羞涩
他是在八十二岁那年走的
乡亲们将他埋葬在村后的龙潭山坡上
人们用黄栗树做了一只如椽大笔
立在他的坟头
我在山上放牧,常常看到有鸟
落在笔尖上
像是一团颜料,等待他运笔挥洒
黄栗树长得慢,但真的耐得住风雨的侵蚀。我们把它插在这里十几年了,它仍然像铮铮铁骨一样立着。
我第一次抬棺到这儿,是在十七岁那年。那天,我抬的位置是棺头一侧,村里最漂亮的少女小水仙往我口袋里放米粒,又在我的上衣纽扣上缠上红线。她咬线头时,我闻到了从她黑发上散发的油菜花的那种芳香,我感到心跳加快了,但接下来她一一为抬棺的男人放米、缠线,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有领头的说声“起棺”,鞭炮响起,锣鼓喧天,脚杆粗的木杠就上了我们的肩。被缚了脚、拴在棺面上的公鸡这时惊慌失措地连声大叫。一路经过三五回绕棺仪式后,棺材被抬到了龙潭坡山上的坟地,一阵鞭炮声响过,男人们七手八脚把棺材轻轻放下挖好的墓穴,又七手八脚挥锹把土填进去,很快,山上多起一个馒头样的土包。从外村请来的看风水的术士——一个我看不出年纪的老人,用树皮般粗糙的老手,解开缚在鸡脚上的麻线,把放生的公鸡往坟边不远的林子一抛,看着公鸡闪身进了树林,他像完成一项重要得不得了的使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随后,他面无表情地对大家说:“这个人,当年出生后还是我给他取的名字。现在想想就像是昨天的事。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人生啊,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不再说笑。那一刻,木讷如我的人,也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生死啊,原来离得这样近。下山,一到村头,一堆柏枝正燃烧着。柏枝是刚砍下的,用松毛给引燃,白烟升腾,散发着清香,男人们先后跨上去,闭着眼睛,让烟熏火燎。新鲜柏枝生出的烟雾,据说能把抬棺者身上的晦气除掉。直到烟雾散开,人们才走开。这时,有人说话了:“人死一阵烟,说没就没了。”
“英年早逝痛不已 清风明月永思念”。这是马家龙墓上的碑文。但坟里面没有埋着马家龙的真身,而是一个衣冠冢。
马家龙五岁才会走路,七岁才会讲话,且口齿不清,整天拖着长长的鼻涕,村里五六岁的孩子也常常欺负他,他只有哭的份。村里大人小孩都喊他“傻瓜”。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且生性木讷,常受人欺负,因而,同病相怜,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一起:一起玩耍,割草,捉鸟,偷食邻居家的石榴、桃子。他父亲当时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公社配了一杆步枪给他。马家龙常趁他父亲不注意,把枪从家里偷出来,我们一起在玉米地或其他背人的地方舞弄。
我们村前有条小河叫“晃桥河”。河里常年清流滔滔,鱼虾多得数不清。一天,我和他一起花了大半天工夫拦截了一个河湾,用盆舀干水,看到河湾里有一条差不多有三公斤重的大鱼,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高兴得在泥水里打滚。就在我们正在想办法捕捉这条大鱼时,我们生产大队书记的儿子江东来了,光着的上身全是疙瘩肉。他跳进河湾,三下两下一手提一边鱼腮,上岸就走。我去他手里抢鱼抢不过,回头喊马家龙帮忙,才发现他不见了。我暗骂,这个胆小鬼,以后就是叫我亲爹也不跟他玩了。
江东双手提着鱼,大步走在河堤上,我束手无策,哭哭啼啼地跟在他身后。就在我们转过一个河湾时,大步流星的江东突然止步了,我抬头一看,马家龙手端步枪迎面拦住江东,枪口直指江东厚实的前胸。我看到,马家龙的眼睛成了红色的,面目狰狞,嘴里咕哝着什么。我从没有看到马家龙这样可怕的样子。江东面如土色,把鱼往河岸边的麦田里一丢,悻悻地走了。我破涕为笑,上前紧紧搂住马家龙的脖子。
土地承包到户后,马家龙埋头在田地里干一些粗活,父母甚至还从外村为他娶回一个媳妇。几年后,那女人丢下丈夫和刚会说话的儿子,跟一个男人一走了之。多年艰苦的劳作使马家龙体壮如牛,常年都亮着一颗光头,满面风霜。为省钱,头都是他老母亲动手给他剃的。土地被城市建设征用后,因身无一技之长,他只能和村里一些老人一样,常年一手提着一把火钳,一手提着一只化肥袋,每天在县城走街串巷捡垃圾过活。
平常一日两餐,马家龙总是放下饭碗就出门捡垃圾,晚上十时左右就回家,从没让家人操过心。但五年前的一天,马家龙吃过饭出门到凌晨三点钟也没回家,家人将整个城都找遍了,但一直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以为要么被人骗去黑砖窑,要么被人杀了卖肝卖肾。两年前,父母便找出他的衣物,用一个木箱装了,用拖拉机拉到这里埋葬了。
我二十岁那年,村头九十六岁高龄的刘姓老人去世,装棺时,我去帮忙。我和几个男人七手八脚把身体已经僵硬如一根坑木的老人抬进棺材,往脸上盖麻纸,往嘴里塞糖果铜元。一旁,刘家请来的风水先生一边敲着小小铜钹,一边摇头晃脑地诵经。由于他声音含混,他念的很多经文,我只大致听懂了一两句:“九十六年头插地,这回日日面朝天!”我问为何让死者在棺材里仰面躺着,侧睡不是更舒坦?风水先生头一昂,低吼道:“连那么小的鸟都知道向天飞,连刚学打鸣的小公鸡都知道要抬头望着太阳叫,你做人会不懂?”他的话让我听得一头雾水,但不禁手搭凉棚一抬头,望见的则是刘家用报纸裱过的竹篱笆顶棚。从此,我爱有意无意地打量天空,它要么平淡,要么灿烂,要么素净。但慢慢地,望天望久了,我感到了一种敬畏。时间的深长,天的高远,那蕴含其间的深意,又岂是匆匆一瞥能够体会的呢。我越发感到自己小如一粒草籽或一只蚂蚁,随日月穿梭,屋檐飘雨,小径风霜,云飞雪落,春发秋衰,自生自灭。凝视天空,我想起了俄罗斯乡村诗人叶赛宁的不朽诗句:“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生前劬劳传佳话 逝后劭德播美名”。是郭子元墓上的碑文。他的坟包上面长着一大丛白花草,是去年的老草,风吹日晒,都变白了,像他当年粗硬的白发。花开花落,太阳照常升起,新绿在当年的衰草上散溢。
土地承包到户的大潮席卷全国农村时,晃桥河一带的农村,还迟迟没有动静。就在那段日子,地主成分的郭老三把村里的水牛放丢了一头。
记得郭老三中等个子,长得相当结实,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气血旺盛,布满了红得发亮的疙瘩。那时,一年四季,村巷道的卫生都由地主富农义务打扫。冬天铲雪,他们会在腰上紧紧地系一根草绳,不让身上一丝热气散失。这时,见到出身好的人走来,不管男女老少,他们会赶紧住手,拖着扫帚弯着腰,一脸谦恭地靠边站了让路。还有的地主时刻满脸堆着笑,作着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向什么人都陪着小心,甚至见了一条狗走来,也会停手让它或慢或快地走过,再继续干活。而郭老三,就是寒冬也赤裸着上身,裤管挽到膝盖以上,露出强健的脊背和腿肚。这个长着山羊胡子的壮汉打扫村街时面无表情,有人无人都像羊一样点着头,手中的大竹扫帚却惊天动地。
大队派文书召集了各村七八十个民兵,把老郭平常放牧的龙潭坡山和晃桥河两岸十里大大小小的村寨拉网式地搜寻了个遍,无果。村长严令老郭:“给你一个星期去找牛,牛在你在,牛不在你不在!”
老郭却神色如常,也许在他的意识里,牛还活在人世间。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把家里仅有的五元钱揣了,像走亲戚似的,体体面面地出门找牛。五元钱的用场他想好了,牛肯定被一户好心肠的人家收留了并精心喂养,找到后他有义务赔偿人家的工时草料费。
鬼使神差,三天里,老郭穿着崭新解放牌鞋子的脚竟然将他带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的热闹小镇,这里早已听不到晃桥河的水声。小镇一角,肉汤飘来迷魂般的香气。三天来水米未进的老郭却一点也不感到饿,他的心里整整装着一头牛,直到坐在一家苍蝇狂舞的牛肉铺里,忽然感到心空了。那一刻他决意:切半公斤牛肉,打半公斤酒。吃完,他就往村子的方向走,跳晃桥河。自己浪里白条的水性在河里不好死,他早已想出了法子,在河边割几根手指粗的青藤,把一条石头绑在身上,打十几个死结,找个河潭跳下去,一了百了。一锤定音。主意打定,他放开肚皮,海吃海喝,与其他食客谈笑风生。酒干肉净,他内急去后院解决,惨淡的马灯灯光映照下,他看到了他的牛,从一面墙壁伸出它的头角。醉眼迷蒙,他不放心,出手去摸,果然,牛还在,只剩下了一个头,挂在了墙壁上。他的酒意一下烟消云散,客气地与店主结账,走人,直奔公社派出所。
那年月的派出所破案具有惊人的效率。顺藤摸瓜找到嫌疑人,三拳两脚,贼人招供,从重从快,获刑四年,外加扒掉贼人家三间新房,将大小梁柱拆下赔我们生产队。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牛头就挂在大队队部支书身后的土墙壁上,牛头上两只角粗壮,黑得发亮,但由于当初处理不当,双眼紧闭。七老八十的支书坐在那里办公,一天上级领导来检查,看不惯老支书这种作派,老支书讪讪地解释说自己挂牛头,是激励自己一辈子像老牛一样勤勉。领导笑了,说,哪有闭着眼还能勤勉的领导。领导一走,支书就唤人叫老郭把牛头扛回去。牛头被老郭放在晃桥河里泡了两天,用柴火烧黄,下锅用猛火煮了一天,竟剥下一脸盆皮肉。老郭全家大小无不欢天喜地。村长和村里的其他头面人物也分享了这顿牛头大餐。第二天一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同班同学,老郭的小女儿小杏,还不时用她红润的舌头,舔舐她的那双小手。
除非是夭折的人,七老八十的人走了,人们总是把白事当喜事办的。送葬那天,村里比过大年还热闹,亲朋好友一大堆,都来为死者送终,人们吹吹打打,唱唱跳跳,簇拥着棺材一步步向后山走去。当天,除了死者亲人一身白孝、哭哭啼啼,其他的人就像相约着赶集一样有说有笑。也有的老人对生死相当达观。这年晚秋,村里一位老人无疾而终。老人的“后家”(娘家)请了三支细乐队,下葬那天从早闹到晚。我们村七十几户人家三百多人,那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没有去掰玉米,大人小孩全来看热闹。满山坡都是人,都穿得红红绿绿的。我也站在人群中观望着。八十六岁的老人陆氏拄着拐杖站在山坡上,对身边的儿子白忠说:“快两年了,村里都没有人办红白喜事,人都快闷死啦。等过几年我死了,你要是也像这样唱唱跳跳送我走,让村里人高兴高兴,我也就不枉来人世间一趟了。”说完,她叹了一口长气。白忠不高兴地说:“妈,你活得好好的会说这样的话?我少了你吃还是穿?”陆氏嘴一歪:“只有长生不老的天,没有长生不老的人。”那时,村里很少有人外出谋生,抬棺的常常是嘴上刚长毛的小伙子。
倒是今天的抬棺人,说不定隔天就和村里的姑娘们,组成了娶亲的队伍。他们穿着簇新的衣服,抬着新娘的陪嫁品,一路打打闹闹,有的男女就在路上生了情。大年一过,媒人一走动,两人就结下了良缘,往往当年冬,就成了让村里小伙子和姑娘们羡慕的新娘新郎。
“一趄风烛红霞敛 万古仪形碧草埋”。这是村里刘凤冠教师墓上的碑文。
和那个时代很多同龄人一样,青春十八,我们连恋爱都忙不得谈,日日夜夜让人沉迷的,是诗。
当我的第一首小诗被我工整地抄录在小楷本上,我跑到村头的晃桥河,爬上一棵最高的清香树,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大声朗读。邻家正在割麦的少女银瑞,拎着镰刀,从篾帽下抬起头来,手搭凉棚。在她不远处,正在犁秧田准备撒谷种的赵康德老爹,喝住了他的牛,抬起头来,手搭凉棚……那一刻,流水,花木,飞禽走兽,连同整个世界,静下来,倾听我变声期的嗓音:啊,我爱你,被阳光点燃的金银花!啊,我爱你,炊烟袅袅燕影翩翩的家!啊,我爱你,磨坊里的石磨吱吱呀呀……
听说我会写诗,几天后,家住村头的刘老师来了,给我送来一本信笺。我用半个月时间,在这本在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漂亮的信笺上,写满了诗。
我鼓足勇气,把那沓写满诗的信笺送到他家,请他指正。一个星期后,他的小儿子送还我的诗稿。他只改了几个别字,同时附诗一首《日子》,批字要我“指正”:
要比别人种田
不要比别人过年
再好的年
三天五天就过完
新衣裳会旧
力气用不完
做人啊,一世到老
要死的时候,揣几颗种子在身上
当土埋葬了你的身体
说不定有一颗
会生根发芽
看到的人都会说
那就是你的今生
此前我从未读过这样的“诗”,像老农在说话,但有的话他们又不会这样说,这如同当年钱忠老人被雷打死时他写的悼词一样让人感到新奇。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一知半解,后来冲动地跑到他家当面向他请教:“我以为文章中只能像报刊上发表的那样,什么‘玫瑰’、‘夜莺’、‘心跳’、‘月亮’、‘麦子’、‘水’……”
他微微一笑,说:“写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写你心里想写的东西。”
日子是平淡的,生活是多彩的。他的话震动着我的心扉。这也是我写作最初得到的启蒙。杂花生树,流年风雨。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我提着一只笔不知深浅到城市以文谋生,一想起他的诗,更感到其珍贵:世故油滑的人写不出这样的诗,缺少乡村阅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平白晓畅,水落石出,有一种与岁月相对应的丰饶沧桑之美。
我们村的张寡妇早年在放夜水时嘀咕:“哪棵树不落叶?哪个人不变土?”但更多的人说:“老牛老马难过冬。”
冬天,是老人归土最多的时候。有的老人头晚还和刚生娃娃的儿媳分享了一碗糖水鸡蛋,天亮,人们还没有走到晒太阳的地方,就听到从老人家里传来嚎啕。老人们听着,不再言语,呆若木鸡,孩子们也一脸严肃,不再笑闹。村子一静下来,哭嚎声就显得更大更响了,哭声像一条河长得不能再长,又像是冰雹合着雨水,席卷整个村庄让人心凉。而这时,会有邻居家婴儿催奶吃的啼哭声不管不顾地响起,直到奶头塞进他或她的小嘴,啼哭声才止住。常常,出殡时撒在地上的纸钱还没有被风吹散,就有坐月子的女人把表示添丁的鸡蛋壳倒在街道上让人踩,踩的人越多,表明新生儿得到的祝福越多。村人往往今天吃白事饭,但转天,人们就穿得光光鲜鲜到晒场上喝喜酒了。孩子满月或嫁娶喜宴,老人们都端坐上桌,他们一个个神态自若,有说有笑,手里端着酒,脸上没有一点前几天兔死狐悲的阴影。死者入土为安后,三天两天,村子里一如既往,人们感到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就像你从河里舀了一瓢水,或倒进去一瓢水。每天天一亮,老人孩子又散落在村街上晒太阳。
“近时疑水近 高处见天阔”。这是“老伙子”胡中明的碑文。
下霜的清晨,是“老伙子”最忙碌也最快乐的时候。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要经过晃桥河。常常见到他用青筋毕露的手捧着草滩上的霜粉,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来回奔走。
听大人们说,“老伙子”十岁还数不清自己有几个手指,但在他十八岁那年,一个下霜的早上,他曾在河边拦住村里最漂亮的女子豆花,说,“豆花,嫁给我吧。”一个为麦苗放水的村人目击了那个场面。那个早晨,像往常一样,豆花带着毛巾、香皂到河边洗脸,冰冷的河水使豆花满脸潮红。面对傻不拉几的“老伙子”,豆花指着河滩上衰草上的霜随口说了一句:“你用它堆成一个人,我就嫁给你。”他重重地点头,马上动手干。一个长冬很快过去了,“老伙子”没有堆成一个霜人。
在村人的眼里,“老伙子”是一个奇人。他个头不高,大眼小嘴,两弯淡淡的眉毛下,是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常年只穿一条看不出颜色的裤头,一身的疙瘩肉,从他身边走过,一大股水草味,像你割草时看到一只青蛙,嗅到它的气息。
据村里的老人说,他妈胡王氏怀着他时,吃错了药,使他一生下来就长着胡子,人们都叫他“老伙子”。
豆花出嫁的前夕,我跟母亲到豆花家贺喜,去贺喜的亲朋有的带着脸盆,有的带着暖瓶,有的带来镜框,有的带来一块花布,总之,都没有人空着手来的。“老伙子”来了,一张脸笑意晏晏,他的礼物是一条一米多长、手腕粗的白花蛇,蛇身软软的挂在他黑亮的脖子上,像是一个裁缝把皮尺挂在胸前。大家对此一点也不以为奇。“老伙子”可是捉蛇的能手,在小阳春到第一场清霜降临这段日子,人们时常能看到他像拿着一根绳子一样摆弄着蛇,只是这根绳子不时变换着颜色,有时是黑的,有时是白的,有时是绿的,有时是灰的,晃桥河谷有哪些种类的蛇,都会不时在他手中出现。
有一次,在晃桥边纳凉的老人们看到他从草丛中捉到一条蛇,那是一条胳膊粗的大黑蛇,他十指紧紧掐住它的七寸,蛇用长长的身子绳子似地紧勒着他的脖子,勒得他满脸血红,红红的舌头伸出嘴唇,眼珠似要跳出眼眶。老人们都叫他快放开。他看样子想放,正在犹豫间大蛇挣脱了他的手指,张开碗口般的大嘴对着他的胸脯咬了一口。“老伙子”大怒,出手如电又抓住了蛇,也张开嘴向着大蛇的咽喉狠狠地回敬一口,不一会,蛇与他都浑身是血,他摔倒在地。后来,还是李氏大着胆子上前,操起手中的拐杖,用拐杖尖一下接一下地直戳蛇的腹部,终使蛇散了架,慢慢松开了他。村里几个小伙子把“老伙子”扛回他家。“老伙子”昏睡了三天,人们都以为他不行了,第四天一早,出工的钟声响过,他又准时出现在大青树下。村里的男人们对他很好,常常叫他去捉蛇来下酒。
那晚,在豆花家,见人们都注视着他,老伙子很得意,提着蛇尾,在豆花家的场院抡开了,送礼的女人们见状连忙闪开。豆花的妈也吓了一跳,正要呵斥,却见豆花的爹从屋里走出来挥手让他停下,向他丢去一支烟,老伙子轻松地把烟接在手中。豆花的爹说:“明天豆花要结婚,蛇煮鸡不就是龙配凤,一道好菜。”“老伙子”高兴得哈哈大笑,跳起好高,眯缝的眼睛露出激动的光。他把蛇随便放在就近一个女人手上。女人的惊叫声,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有人逗他:“豆花就要嫁人了,你不难过?”
他愣了一下,泪流满面:“怪我没有本事,堆不出霜人。”
热闹的场面一下静了下来。
豆花远嫁他乡,可他一直不曾停止这种努力。每个霜晨,“老伙子”差不多是在堆霜人的劳作中度过的,一双手被霜冻得硬如柴块。一天,我掬了捧霜走向他拢起的小小的霜堆。“老伙子”不领情,把我捧去的霜掀到白雾升腾的小河……
一个早晨,霜把晃桥河两岸都下白了,在河边干活的村人看到,在“老伙子”时常劳作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盘腿坐着的霜人。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他把自己埋进了霜堆。人们七手八脚扒开霜,他早已断气了,眼睛却大睁着。
这一年,“老伙子”刚过了三十岁的生日。
埋葬在这里的上百的亡人中,据我所知,只有我的岳父李汝生是自己为自己挑选的坟地。站在他的坟头,整个县城近在眼前,生活在山下的我有时一抬头,似乎会与他的眼神相碰。2012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走了。当晚我正准备赶往昆明参加由《滇池》文学月刊社举办的“滇池之友”笔会的报到。我向主办的老师请了假,次日把岳父送上山,含着眼泪写下一首诗《在乡土上走过》:
春发,夏长,秋收
我知道冬是收藏的季节
果然,这年冬天,它收贮了我的岳父
一枚在世上飘零了73 个春秋的叶子
像活着一样,连死,也没有惊动任何人
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凌晨
在前几年他还在耕种、如今沦为城中村的
一间简陋的小平房里
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断然与人世诀别
你的长子抱扶着你
像你当年抱着他一样
我的连襟为你剃头
一刀一刀,一连用坏了五块刀片
你的头发,像你的命一样硬
为你净身时,我不惊叹你
双手老茧,两腿青筋
挺拔的脊梁,似乎从没有负过重荷
我感叹你爱干净,一盆热水
用过后,还清澈如初
年过七旬的人,天天用冷水洗澡
这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为你穿上一件又一件衣裤
你受过尘世太多的寒
这回要到传说中的阴间
我们希望你不再打寒颤
都说同在一片蓝天下
但你历经的风雨太过酷虐,7 岁成孤儿
蒲公英还有一把小伞你没有
为人放牛赶马,忍饥挨饿,
九死一生,把自己养大
十几岁,各种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
再后来,盖房,娶妻,生有三男二女
晃桥河畔,一个叫新瓦房的小村,
多了一个家
夫妻都是苦命人,日子风雨飘摇,
但炊烟不断
我是在你最好的时候跟你成为一家人的
你的长女18 岁时,是一朵村花
你一言九鼎,从众多的求亲者中
挑选了身为村办煤窑工的我
认亲那天,我带着煤窑赐的一脸苍白
两眼乌青,像根坑木一样站在你面前
叫了你一声“爹”,胆战心惊
你半天才应声
多年后,我们喝酒时,你告诉我
你看中我的,是我经年在井下
没有旷过一天工,为人实诚
肯吃苦的人看着就顺眼
当然,男人天生的苦命嘛……你总结
你是窑工、篾匠、石匠、泥水匠、厨师
马车夫、手扶拖拉机驾驶员
是用一双大手为人舒筋活血的好手
祖传的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的一切礼仪
了然于心,施行自如。还粗通风水
隐忍,本分,不彰人短,不炫己长
用一生实践居身务期俭朴
教子要有义方的古训
黎明即起,和大地一起醒来
熟悉土地、节气,像土地、节气一样熟悉你
管理庄稼,像整饬一支军队
做一根锄把,如打造一根法杖
相信别人,像相信自己
60 岁那年,一次暴雨前我们抢收
你捆了一挑稻谷,
我和连襟先后上前都担不起
你上前弯腰,两根扁担叠加上肩
起身,三个动作
两座小山,就在田埂上像两团云朵飘动
一天,你赶牛来为我家耕田
我牵着牛一走神,犁沟偏了
你一鞭子,抽打在牯牛背上
疼在我的心里。村里大人小孩,见了你
都按辈分亲热地跟你打招呼
靠血汗打拼出来的身份
总是像土地一样可靠……
失去土地,苒苒物华休
你不再耕云播雨,一天天,
像日头坠向西天。越走越远
此前,你没有误过一年的
种种收收,收收种种
不管飞霜满树,还是田园丰饶
我接受了你的一份遗产
是你的女儿,我的妻子打给你的一件毛衣
上面有汗水的气息,五谷六畜的气息
泥土的气息,草木的气息和
生命的气息。我穿着它,跑到别人的田野
听到风送来,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而你分明刚刚从乡土上大步走过
埋葬在龙潭坡坟墓里的人,曾是我的乡亲,亲人。现在他们已经成泥成土。但不管怎样,他们曾在晃桥河畔的大地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