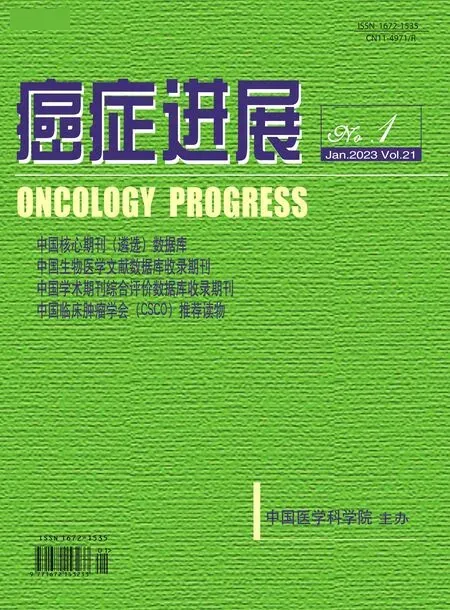绒毛蛋白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赵伟天,王万祥,杨帆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呼和浩特 010050
细胞骨架结构是真核细胞中一种复杂的蛋白质网架结构,主要由肌动蛋白、微管蛋白、细胞角蛋白及肌丝蛋白来维持功能[1],从而影响细胞分裂、分化、迁移及凋亡等多种生理活动[2-3],近年来,与其生物学相关的研究报道也越来越多。肌动蛋白结合蛋白(actin-binding protein,ABP)是细胞骨架结构中一种重要蛋白,如绒毛蛋白(villin)可通过调控肌动蛋白细丝的聚合和降解(解聚)来影响肌动蛋白的动力学[4],对正常细胞运动及肿瘤细胞侵袭、转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多项研究证实,villin在多种肿瘤的诊疗过程中有重要价值。本文对villin在肿瘤诊疗过程中的应用价值进行综述。
1 villin的来源与功能
villin存在于人类第2号染色体q35~36区,由25 000个碱基组成,是以单体形式出现的酸性多肽,分子量为95 kD[5]。villin是上皮细胞特异性Ca2+调节的一种常见的肌动蛋白修饰蛋白[6],其在肌动蛋白成核、肌动蛋白细丝组装、肌动蛋白封顶和切断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种覆盖肌动蛋白、切割肌动蛋白、核化肌动蛋白和捆绑肌动蛋白的蛋白质[7]。villin可以通过肌动蛋白的动力变化调节细胞的存活和迁移,在炎症和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正常上皮至肿瘤的转化过程中异常表达。胃肠道、肾脏和泌尿生殖系统上皮细胞被证实存在大量的villin,其在调节细胞形态和细胞特异性上皮抗凋亡方面有一定作用[8]。villin中一个小的羧基末端结构域称为头端,具有结合放线丝的能力,它的氨基末端核心保留了受钙离子调控的肌动蛋白切断、封顶和成核功能[9]。此外,villin核心部位还保留了几个配体结合位点,相关位点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也受其调节,包括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phosphatidylinositol 4,5-bisphosphate,PIP2)结合位点、溶血磷脂酸(lysophosphatidic acid,LPA)结合位点、酪氨酸磷酸化位点[10-12]。
磷脂酰肌醇(phosphatidylinositol,PI)是一种含肌醇的甘油磷脂[13],其通过与多种不同的蛋白质进行相互作用来参与肌动蛋白动力学、信号转导、细胞内转运、膜动力学及细胞-基质黏附等多种细胞功能[14]。PIP2的主要功能是使具有抑制肌动蛋白聚合能力的相关ABP失活。villin中已有3个PIP2结合位点,分别为PB1、PB2和PB5[15],PIP2与villin的结合使PB1、PB2结构域功能丧失,抑制了villin的肌动蛋白封顶和切断活性,提高了villin所结合的肌动蛋白丝的黏度,促进了肌动蛋白丝间的结合和交联,增强了外周肌动蛋白结构和细胞骨架结构的稳定[16]。F-肌动蛋白丝在形态上虽没有明显变化,但出现了更多的分支及交联情况,增强了肌动蛋白的聚合能力[10-17],减少了肌动蛋白的断裂,促使外周细胞骨架结构的生长和稳定,促使肌动蛋白束可以更好地支持和稳定质膜的突起和内陷。
LPA是一种小分子生物活性磷脂,正常由活化的血小板、成纤维细胞、间皮细胞和脂肪细胞产生。villin可以激活LPA受体(LPA receptor,LPAR)1~6,并调节各种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如细胞增殖、细胞保护、伤口愈合等,并参与血管稳态、骨骼和基质重塑、淋巴细胞运输和免疫调节等过程[18-19]。LPA需与细胞内的其他因子相互作用才能发挥作用,其可以直接与villin相互作用,表明villin也是潜在的可以调控LPA生物学作用的靶点[20]。LPA可与PIP2竞争相同的villin结合位点,但对肌动蛋白所产生的功能与PIP2不同,LPA也可以与PB1、PB2、PB5位点结合,且亲和力比PIP2更高[11]。villin与LPA结合可以抑制肌动蛋白的成核能力、解聚活性及封顶功能,LPA能作为抑制villin介导的细胞内肌动蛋白动态变化的调节因子。此外,LPA对vil-lin的酪氨酸磷酸化具有促进功能,从而引起villin的构象变化[21]。
磷酸化的villin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改变肌动蛋白的构象,包括降低与F-肌动蛋白结合的亲和力,抑制现有肌动蛋白核的聚合或切断原有的肌动蛋白丝以产生新的肌动蛋白核,从而调节细胞的运动,在细胞迁移中发挥重要作用[22-23]。villin的肌动蛋白核化和肌动蛋白切断能力明显依赖于一个或多个酪氨酸残基的磷酸化,villin氨基末端的某个区域是磷酸化的位置,该区域主要的磷酸化位点Tyr-60、Tyr-81和Tyr-256,在细胞迁移中发挥重要作用[12,24],这些磷酸化位点中的任何一个突变都会抑制villin聚合肌动蛋白丝的能力,此外,Tyr-286位点磷酸化还可促进villin肌动蛋白的解聚[25],使细胞保持较高浓度的未聚合肌动蛋白,肌动蛋白的解聚也可以产生新的用于形成肌动蛋白丝的带刺末端。当villin磷酸化及其肌动蛋白封顶能力激活时,可以帮助封盖带刺末端以保持细丝长度,从而促进具有推进能力的短丝的生成,并有效推动质膜运动,进而影响细胞迁移过程。对villin磷酸化位点的干预,也是一种控制细胞迁移、延缓疾病进展的手段。
2 villin在肿瘤诊疗过程中的应用
细胞迁移中最关键的过程是肌动蛋白的快速聚合和沿细胞运动方向的伪足的形成。肌动蛋白结合蛋白通过促进肌动蛋白细丝的聚合和降解(解聚)来影响肌动蛋白丝的生物动力学,包括创建新的聚合位点、产生分支并使肌动蛋白丝相互交联、稳定肌动蛋白结构、阻断游离末端以及促进球状单体的传递[26-27]。
villin作为一种ABP,可以通过切断肌动蛋白丝产生新的末端和头端,促进肌动蛋白丝之间的交联以延长肌动蛋白丝的长度,覆盖肌动蛋白丝的头端或末端以限制其生长,靶向调节肌动蛋白丝的长度[24-25,28]。villin的酪氨酸磷酸化也增强了肌动蛋白的切断活性,促进新的带刺末端的产生。villin也可以增强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诱导的细胞运动,经EGF处理后,表达villin的细胞比不表达villin的细胞迁移得更快,表明villin可以促进基底细胞和生长因子刺激的细胞迁移。villin参与了致癌过程的初始步骤,其诱导的细胞迁移和侵袭可能在肿瘤细胞扩散中发挥重要作用。下文对villin在结直肠癌、胃癌、肺癌、胰腺癌、肠道转移性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总结。
2.1 结直肠癌
据统计,结直肠癌是除肺癌、乳腺癌外,全球发病率(10.0%)、病死率(9.4%)排名第三的恶性肿瘤[29]。虽然目前的诊疗手段对结直肠腺癌的检出率较高,但对恶性程度较高的结直肠癌的诊断仍相对困难,且针对villin的相关生物学作用在结直肠癌诊疗过程中的应用研究较少。有研究显示,多原发结直肠癌(multiple primary colorectal carcinoma,MPPCC)的发病率为9.4%~27.8%[30],结直肠浸润性微乳头状癌(colorectal 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MPC)在进展过程中有较高的侵袭性及转移风险,肿瘤TNM分期处于晚期较多,预后也较差[31-32]。一项研究纳入222例结直肠腺癌患者,术后病理结果显示,215例患者villin呈阳性表达[33]。另一项检测villin表达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81例结肠癌患者中有77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90例IMPC患者中有88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34]。由此可见,villin是诊断结直肠癌较为敏感的指标,对villin表达与结直肠癌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可能为结直肠癌的诊疗提供新思路。
2.2 胃癌
胃癌目前仍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肿瘤之一,据统计胃癌每年新发病例超过100万例,死亡病例约76.9万例,每13例因肿瘤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例胃癌患者,其发病率在全球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五,病死率排名第四,且男性的发病率是女性的2倍[29]。国外有研究对67例原发性胃癌患者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其中52例患者villin呈阳性表达[33]。国内也有研究指出,villin的表达与胃癌的分化程度相关,60例胃腺癌患者中,中高分化胃腺癌患者的villin阳性表达率最高,低分化胃腺癌患者的villin阳性表达率最低[35]。提示villin是一种很好的肿瘤标志物,有助于预测胃癌患者的分化程度,且细胞异型性增加时,上皮细胞会发生紊乱,维持微丝结构的成分减少,villin的表达强度也随之增加。这为胃癌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根据villin表达评估胃癌分化程度及预后情况,并针对其相应靶点尽早进行治疗提供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手段。
2.3 肺癌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男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女性中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且肺癌的病死率居恶性肿瘤首位[29]。对于原发性肺癌、结直肠腺癌的肺转移以及肺癌的特殊分型肺肠型腺癌(pulmonary enteric adenocarcinoma,PEAC)的临床鉴别相对困难,但villin的使用似乎对鉴别肺癌的原发情况也有意义。一项对50例原发性肺腺癌患者的研究指出,术后病理结果诊断为原发性肺腺癌的50例患者中,29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33],虽然villin诊断原发性肺腺癌的灵敏度不如诊断胃肠道肿瘤高,但另一项针对PEAC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19例患者的病理切片进行villin表达强度分析,结果有17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37],并且该研究推测,针对PEAC患者,villin的阳性表达率高于其他肠道肿瘤标志物[38],其主要原因可能是PEAC的肿瘤细胞中存在大量的微绒毛,而villin主要在上皮细胞的刷状缘微绒毛中表达[39-40]。在诊断PEAC的过程中,villin联合CK7鉴别诊断原发性肺腺癌、结直肠腺癌肺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对原发性肺癌、肠道转移性肺癌及PEAC的鉴别诊断中,应用villin联合相关敏感标志物,无疑可以提高疾病的正确检出率,并通过对villin表达与肿瘤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运用villin的相关生物学作用靶点进行早期干预,也是一种临床诊疗思路。
2.4 胰腺癌
虽然胰腺癌的发病率较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肿瘤低,但其死亡率、5年生存率及预后情况都相对较差,且亚洲地区新发病例占全球胰腺癌新发病例的47.1%[29],对胰腺癌及其分型进行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治疗胰腺癌的重要环节。一项检测40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villin表达情况的研究指出,术后病理结果诊断为胰腺导管腺癌的40例患者中,24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33]。此外,在胰腺癌的癌前病变如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 of the pancreas,IPMN)的临床诊断中也有较高的诊断价值。IPMN是一种胰腺囊性肿瘤,是胰腺癌的癌前病变,有较高的恶性转化的可能。有研究指出,在手术干预的IPMN患者中,有超过50%的病例侵袭程度较高,预后也较差,对于侵袭程度较低或尚未发生侵袭的IPMN患者,全胰腺切除术后患者的长期生存率较高[36],且IPMN进展较为缓慢,这也为胰腺癌的早期干预提供了机会。根据IPMN的分型,肠型IPMN患者的生存率较胃型IPMN低,恶性程度也更高,预后更差[41]。一项分析40例术后诊断为IPMN患者villin表达情况的研究指出,肠型IPMN患者的villin阳性表达率高于胃型IPMN[42]。上述研究表明,在考虑胰腺癌或癌前病变的患者中,villin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目前通过villin的相关靶点对胰腺癌或癌前病变进行早期干预的手段较少,这也为villin与胰腺癌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助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
2.5 肠道转移性癌
肝脏及卵巢是消化系统肿瘤常见的转移部位,villin是肠上皮细胞分化和肠道转移性腺癌的肿瘤标志物,其在肿瘤诊断中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43]。一项对40例原发性肝癌和40例肠道转移性肝癌进行免疫组化检测的研究指出,4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仅5例患者villin呈阳性表达,40例肠道转移性肝癌患者中33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44],这为肝癌的鉴别诊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诊断方法。另一项对45例原发性卵巢癌和15例肠道转移性卵巢癌的患者进行免疫组化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45例原发性卵巢癌患者中,仅4例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15例肠道转移性卵巢癌患者的villin呈阳性表达[45],当肿瘤出现远处转移时,其恶性程度相对较高,肿瘤分期也相对较晚,通常情况下villin的阳性表达率也随之升高。villin的表达情况对消化道肿瘤的远处转移具有评估价值,针对villin的相关作用靶点及早对转移病灶进行干预,可进一步使原发病灶获得允许进行更多治疗手段的条件,甚至使原本不能行手术切除的晚期肿瘤患者经过转化治疗后达到能够行手术切除的水平。虽然目前相关研究较少,但也不乏为一种临床诊疗思路。
3 小结与展望
villin是一种多功能的肌动蛋白调节蛋白,其对评估常见肿瘤如结直肠癌、肺癌、胃癌、胰腺癌及肠道肿瘤转移性癌的检出、预后评估提供了一种评估方法。了解villin与PIP2、LPA结合后所产生的生物效应、villin酪氨酸磷酸化后对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结构的调控,能够进一步对肿瘤患者进行早期的干预和治疗。虽然目前有多种潜在的药物靶点已经可以用来治疗多种疾病,但关于villin的预防及治疗手段十分有限,挖掘villin的治疗靶点、探索肿瘤进展过程中针对villin改善患者预后的干预方式、筛选适用疾病及适用人群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