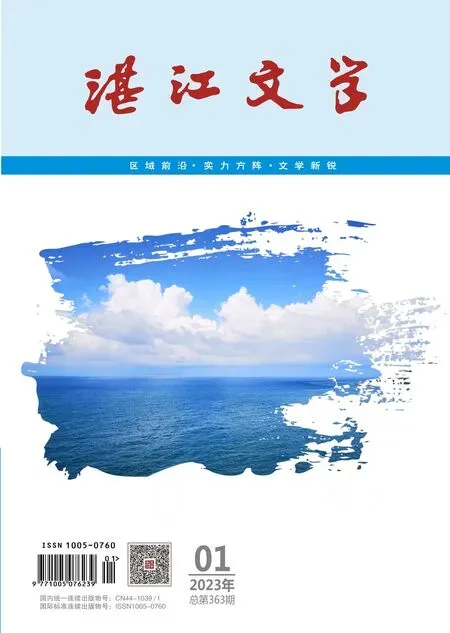遥不可及
◎ 兰喜喜
1
文学打来电话,说寿盛和凤霞想邀我小坐。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使劲在大腿上用铅笔戳了一下,疼痛使我自觉不自觉地爆了粗口。我揉了揉眼睛,摇了摇头,再次证明这是现实而非梦境。并在脑海里快速回忆着寿盛和凤霞的容貌,以及我们在经年岁月里有过交集的点和面。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实在太模糊,脑海里的影像画面时断时续,时续时断,几乎组不成一副完整的画面。
最后,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灰头土脸的少年时光,那些记忆,青涩、单纯、就像安徒生童话故事里的一个场景,一闪即逝。那些岁月里有趣的,难忘的事情一件都想不起来。事实上,那时候,我们虽然同班,但因年龄尚小,对于彼此,都没留下太深的记忆。
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似乎没有理由。
我一遍遍在脑海里回忆着这件事,并沿着福尔摩斯和卫斯理的路径,一一排除了非正常因素的可能性。首先,借钱不可能,我现在很穷,银行存款基本保持四位数。绑架、诈骗、劫色他们都不划算。对于我这样的人,从头到脚,所剩的残值已经不多了。
用句中肯的话总结我的现状,一个底层百姓的灰色人生。在这个人人都寻求联合、随大流的世界上,除了所剩无几且毫无道理的文学理想外,没有别的。这样的人生,着实有点荒诞,像个笑话。
有一年,同学小聚,到场的个个风光无限,穿名牌,开豪车。唯独我灰头土脸,样貌寒酸。席间,几位当年彼此暗恋,但没来得及下手的,在还没结束的宴会上,迫不及待搞起了眉来眼去又不明不暗的小动作。让我想起网络上的一句糙话,“同学聚会,无非三件事。炫富、摆阔、搞破鞋”。这三件事,我哪件都沾不上边,索性就退出了此类活动。
我说,你不是逗我玩吧。
文学说,你个混蛋,还是老吊样,一点没变。
我说,在一个人人都在求新、求变的时代,能保持本色,这是需要毅力的,你得向我学习。
文学说,本来的色性。
我说,《孟子·告子上》里有句话,“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文学说,别逗弯子。
我说,到底什么事情?
文学说,他们有个文化公司,想找你谈点事。
我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况且我连个书生都算不上,找我能谈什么事情?
文学说,你就说你来不来?
我说,就我们四个。
文学说,是的。
我说,来。
随后,我们约了个地方见面。寿盛、凤霞却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朴素、简单,为人谦和,落落大方。我们谈了很多话题,这些年在外南来北往、居无定所的生活,家庭琐事、孩子上学以及少年时代与流氓混混打群架、翻墙逃课、偷盗自行车的事情。感觉很惬意,像是重新回到了二十年前。
我们还谈到电影,关于霍建起、贾樟柯、滕文骥、田壮壮和王家卫。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说想投资电影行业,问我有没有好的思路?
我说,电影首先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其次是一种精神和情怀。当下的很多电影人,过分注重前者,而有意忽略了后者。使电影市场变得混乱不堪。各种潜规则、各种劣质游戏、各种骗局都有。加上电影看起来很美,但真正做起来很难。
寿盛说,我知道难,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越难的事情,做起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难的事情,做起来越有意义。
我说,你这是典型的人已中年,皮糙肉厚,最让人讨厌的是理想不死。
他只顾低头嘿嘿笑。
凤霞说,你在文化行业里多年,应该对电影行业有所了解。
我说,我只是文化行业底层的一个“小单元”,文学期刊的编辑而已。至于电影,真不敢说什么?
凤霞说,至少你看过的电影比我们多。这些年,我们在社会上忙忙碌碌,对这方面确实没有过多的了解。
我说,看电影和做电影是两个概念。就像读书和写作一样,读书你可以没有选择性,投其所好,喜欢就行。写作却完全不一样,你要考虑的综合因素很多。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以及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心理感受都需要考虑。如果要谈电影,我到可以和你们详细聊聊。我虽然算不上电影迷,但看过的电影数量也是足够多。可今天你们要做电影,我真不懂。
寿盛说,你不懂可以,身边有资源。目前影视界和你关系好有潜力的人,你可以推荐几个,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说,电影水太深,溺水不偿命。
寿盛说,我懂,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我说,朋友中可靠、信得过的人有两个,一是东莞的穆肃,二是北京的孙睿。他们在“80后”作家中,文学造诣极高。孙睿著有多部畅销书,《草样年华》系列、《活不明白》《朝三暮四》《我是你儿子》等。这些书写的风趣、幽默,动辄发行过百万,在国内有很高的人气。2007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毕业后,一直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前年,他将《草样年华》改编为电影,现已拍摄结束。我说,目前该影片还未上线,如果你想参与,我可以联系孙睿,看能否有机会参与。
寿盛说,这样最好。
不料,当我拨通孙睿电话后,孙睿说现在不需要资金,一切就绪。制作完后,就着手宣发了。随后,我联系了穆肃。去年我去东莞的时候,穆肃正在拍一部电影。前段时间,刚拍完。和穆肃联系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制作完了,目前不考虑与其他公司合作的事情。最后,他们说,不行就改编,让我操刀。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做什么样的电影?艺术片还是商业片?这是两种路径,弄清楚这点,很重要。
最后,落脚点在宁夏本土作家群体里。宁夏本地作家中,多半都熟悉,做起来阻力相对小些。加上,宁夏本地作家朴实、厚道,不像国内某些作家,唯金钱论。我向他们推荐了石舒清和郭文斌二位先生。
凤霞说,对郭文斌先生很了解,问我能否联系上。
我说,可以。
在宁夏作家中,石舒清和郭文斌是继张贤亮先生之后,才情与气质并重的两位作家。能选择将他们的文学作品搬上荧幕,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后,我给郭文斌先生打了电话,将寿盛和凤霞的想法说了,没想到,郭文斌先生很快就同意了。
事情是联系上了,可心里还是没底。想起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外婆的道歉信》里的一句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想到此处,心里坦然了许多。
2
银川一位谢姓先生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农历》剧本他看了两遍。
电话上,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扬。面对他的赞誉,我多少有点紧张。这些年看了太多的电影,但真正打算做电影,还是头一次。无论从技术、经验以及对剧本本身所赋予的思想性、艺术性都缺乏应有的底气。
说到底,我还是个外行。
但面对谢先生、寿盛、凤霞的一腔热情,我不想让他们丧气。可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真正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仅仅依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电影从来都是喜欢它的年轻人的梦想,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成了它的台前客,有的人成了它的幕后人,有的人一生都是观众。
就《农历》来讲,我找过几个专业人士,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有鼓励的、也有劝阻的、还有质疑的。无论鼓励、劝阻还是质疑,我都十分感激。电影说到底,是投资行为,要遵循它的商业规律。它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酒囊饭袋们的夸夸其谈和无所事事者的高谈阔论,也不是名利场上的“韭菜”,看着长势喜人就可以收割。对我们来说,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是理想的执念,更是每一个参与者与出资人的心血、希望和生活的柴米油盐。
所以,今天做的每个决定都必须进行深思熟虑,把所有的不利、可能导致的失败因素全部放到台面上,来正视,来分析。我有个不正确的观点,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唯有正视失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就《农历》电影来讲,我没想过成功,但一直在做规避失败的事情。
网络上有句话说:“会飞的鸟总会捕捉到什么。”对于电影来说,我还是个未真正学会飞翔的鸟,但我在努力练习飞翔。我时常在想,在真正开始拍摄之前,我要把每一件可能导致失败的事情都要仔细、认真地分析一遍,唯有这样,我才能做到内心平静。倘若做了分析,也启动了规避失败的机制,仍然失败,我想失败也是优雅的。正如惠特曼所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我和谢先生在电话上聊了很久,把剧本的优缺点再次讨论了一翻。谢先生说,你肯花心思去琢磨一件事情,还担心什么?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怕做事的人,就怕花心思去做事情的人,任何事情,只要肯花心思,不成功都难。
我说,我对商业不懂,所尽之力全在文学范围内,文学和商业是两个概念。谢先生说,你只需做好文学范围内的事情,至于商业事情就交给商业,不要想太多。
他越这么说,我越战栗,甚至惊悚。因为电影对我们来说,虽然是个美好的隐喻,但现实对我们来说,有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
3
一拍即合的事情,容易成功,但更容易失败。为了确定一些未尽事宜,约寿生一起小聚。
在家门口的愚人火锅。这家店,我之前和妻、孩子来过一次,感觉很不错。粗线条的中式风格,显得轻松和随意。选择这里,与愚人、逗乐没关系,纯属为了方便。下午,妻打来电话说,晚上不回来了,住父母家,我自然十二分支持。
父母年迈,已过七旬。他们住在良田镇。我平时因要照顾孩子,只有周末才能去看望他们。两年前,因孩子需要人照顾,我和妻多次动员二老,希望能与我们住一起。一来可以帮我们照看孩子,二来照顾起他们也方便。可父母一生都在农村自由广阔的天地里生活,住不惯城市的楼房。他们每次来我这里,都显得匆匆忙忙,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逗留时间也不过一两天。有一年冬天,二老来家里,我多留了两天,一天下午下班回家,发现他们在吵架。母亲说,让昨天回,你就是不走,脚后跟沉的很。父亲说,是你不走,还把责任推我身上。母亲说,我要走,可你不抬脚。
父亲又想怼母亲,见我已站在门口,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如今,两个孩子都上学了,但每天还需要照顾,辅导作业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妻工作特殊,早出晚归,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时间长了,两个孩子也渐渐习惯了由我陪伴。一段时间,宇扬晚上睡觉都不和妻睡。每天晚上,上床之前总要征求我的意见,我睡卧室他就到卧室,我睡书房,孩子就跟到书房。
这些年,生活虽然过的简单、朴素,却也少了许多杂念,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等寿生和凤霞的时间,在网上看见王清宪博士的论文后记,顿时眼泪就下来了。想起十年前,我在西南大学许许多多个日夜,那真是一段痛并快乐的日子。痛是因为贫穷、饥饿、孤独和煎熬,快乐是因为无论生活过的怎样的贫穷、饥饿和孤独,我始终和歌德、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卡夫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鲁迅、梁实秋、沈从文、路遥、史铁生等人类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在一起,与他们保持了最真诚、最执着的交流与对话。
那段时间,生活可用艰苦二字来形容,但它朴素的一面却是我喜欢的,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体验感虽然不具普遍性,但也存在典型性的可能。因为一个真正为内心自由而追逐梦想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多么遥远,是否被实现,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正如那句流传甚广的话:“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我常把个体生命在最鲜艳的时刻,经历的这个过程作为衡量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准。事实上,就我的一生来说,我宁愿生命枯竭于奔跑的路上,绝不允许它坠落于享乐的温床。因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喜欢的风景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努力,才能欣赏的到。
王清宪博士如今当了高官,多数人惊呼于这一点。而我则更看中作为博士的王清宪,或者是作为学者的王清宪。至于他今天能做高官,也并非坏事,希望他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海瑞、林则徐、焦裕禄为榜样,做百姓心中真正的父母官。
我对官阶大小一直形不成明确的概念,到底多大的官才算大官,我实在弄不清楚。王清宪是副省级,算大官吗?从留言区里看,好像是大官。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官阶大小似乎没多少意义。我一生笃定要过普通人的自由生活,做一个不被多少人知道的文学爱好者。忙时劳作,闲时码字,自由自在,平淡一生。这看似不可理喻,实则是我真实的想法。即使这样,我还是想送给王清宪博士一句话,作为官员,“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把人民的事当作全天下最重要的事,无论你将来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会像孔繁森、焦裕禄、雷锋、邱少云一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他能坚守学生时代的理想和信念,这对他来说,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世间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就是在看透了生活黑暗,却依旧热爱生活。”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生活概括的如此清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概括的如此清楚。
4
《农历》电影琢磨了很久,我们一直犹豫不决。建安时期,吴侯孙策去世的时候,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可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张昭和周瑜在哪里?为了抹去蒙在眼睛上的灰尘,我们决定进京与制片方面谈。
早上起来,给寿盛打了电话。再次,确定了见面地点。
寿盛说,他来小区门口接我。十点半了,他还没有来。我再次致电,他说公司的事还没处理完。电话里,他不紧不慢,让我有点琢磨不透。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挂断电话,我一个人在屋里团团转。
今天是周末,妻和两个孩子还在补一周来欠的美容觉。这些年,孩子太小,妻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艰辛与努力。她在这个家里,为人妻是贤惠的,为人母是善良的,作为当家的,亦是称职的。为了能让我安心写作,她承担了家里的一大半的事务。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在我眼里,妻无疑是成功的,遗憾的是,在写作上,我依然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
事实上,我对写作的看法很简单,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终于内心。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写的东西再多,其实都是无效的。文学自有其发展规律,一个时代文学事业繁荣,有时并不和经济发展、社会的开放度、自由度成正比。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20世纪的拉丁美洲,经济落后,文明程度不高,但文学的繁荣程度却很高,出现了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罗贝托·波拉尼奥等文学大师。“五四”时期, 军阀混战,百姓疾苦,救亡图存成了最大的“革命主题”,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依然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蔡元培、严复、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郁达夫、朱自清、黄侃、吴宓、章士钊、辜鸿铭等一批优秀的作家、学者。而今天,你能找到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超豪华阵容吗?
不得不说,如今经济发展了,祖国强大了,而作家这个群体却没有真正做到“励精图治”。
这不,前两年,一个四川籍著名作家,为了一个文学奖项,在网络上谩骂了很长一阵子。这虽然不是大多数作家的惯常表现,但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事实上,在大多数写作者的眼里,名利大于写作,金钱大于文学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难道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最大危机吗?
尽管我也是一个俗人,放下手中的笔,也为养家糊口、财迷油盐和一日三餐而忙碌,但在写作之内,我从不沽名钓誉,也不以“文学的名义”拉帮结派,搞圈子主义。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引以为荣的地方。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里说,“每个人都在愤世嫉俗,每个人又都在同流合污”。
我也想愤世嫉俗,也想同流合污,但实力不允许啊。
这些年,也写了一些东西,发表的很少,出版过几本书,也没引起多少人注意。当然,那些以发表为目的的人,自然对我这类写作者不屑一顾,他们精致的人为,文学作品写出来就是要人看的,不被人阅读的文学,从来都是无用的文学。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原因此处不论。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首先是忠于文学本质的,是纯粹而不含任何目的的写作,是忠于心灵,带着自由的。发表只是整个写作环节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更多的是呈现方式,没错,它只是方式,不是目的。
有天晚上,妻一个人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我本芳华,却无端生出沧桑相,你说我该如何是好?我安慰她说,为人妻,你徐娘未老,为人妇,你风韵犹存,何来沧桑?
妻说,我徐娘半老,风韵不存。 想当年,我也花容月貌,仪态万方、楚楚动人、闭月羞花,你看现在,一朝春尽容颜老,哎……
我说,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风姿卓约的徐娘,虽不至倾国倾城,但也足够花容月貌。你要知足,青春作伴,理解万岁。
妻叹息道,人生苦短,还未认真地年轻,却只能无奈地老去。说着说着,悲从中来,从头到尾把我这些年的种种不堪细数了一遍,痛心疾首地说,此生若不遇上我,说不定现在依然花容月貌,遇上我后,本以为我会为她遮风挡雨,没想到,风雨来临的时候,我却成了躲避风雨的人了。我说,你辉煌的前半生岂止于“伟大”二字说能概括尽的?简直太伟大了,尤其在这个家里,你不觉得吗?
她说,你少来,十年了,没有一天不给我戴高帽子的。我说高帽子总比绿帽子好。她说,她倒希望有顶绿帽子,可就你这样的参差品,恐怕市场销路不好。我说,疫情下的中国,滞销的都是好产品。她用鼻子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恨不得把我生吞了。女人都一样,得意时高歌,失意时埋怨。这是她们的优点,也是她们的缺点。
十二点十分,寿盛打来电话。说到小区门口了,我急忙下楼,匆匆上车,丝毫不敢怠慢。今天去北京,为了《农历》电影合作事宜,路途遥远,心有不安。
出门前,我刻意翻看了日历,用笔圈出一个记号。没想太多,也未见得有什么寓意,只是觉得此刻应该记住什么?至于究竟要记住的是什么?我并不清楚。但有一点,需要在此交代一下,时至今日,我已年近不惑。《论语·为政篇》里有一句话十分准确地概况了我目前的现状,原话是这样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这一句话所阐述的前半部分我已经历,后半部分还未经历。对于未经历的,此生有可能会经历,有可能不会经历。而目前正在经历的,才是真正的“骑虎难下”。孔夫子是大智慧者,四十岁的时候,遇事就不迷惑。而我的四十岁,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时常想,倘若这次失败了,寿盛、凤霞必然会在这件事上跟着失败。每每这时,我就不免紧张了起来。惠特曼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想到这里,我又释然了。
5
车过呼和浩特,我们做了短暂的停留。
七年前,我因工作面试,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在西藏某地工作,因实在忍受不了三婚女领导的变态和生活环境的恶劣,最后选择了离开。离开藏区,我只身闯入蒙地。妻得知我的消息,不远千里从银川赶往内蒙古与我相会。
那时,我们结婚不到半年。
有时想想,牛郎织女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他们生性浪漫,因触怒天帝被惩罚,从此过上了“执手相看泪眼”的生活。我们是一对凡胎,并未触怒过谁,但还是和牛郎织女一样。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苦日子,尤其对于一个想把自己一生托付给一个男人的女人来说,就显得更加苦了。那时,为了改变生活的窘迫现状,我都不惜背水一战了,可生活还是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好在,天不绝人。几经波折,终于走上了生活正轨。
如今,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过的去。在西部边陲的小城,我很享受这种人情简单的朴素生活,也感念于天地恩赐以及亲朋好友的大力相助。
这些年,我写文字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从内心上来讲,并不想与谁为敌,更不想惹谁生气。文学无非争论的是观点,涉及不到深层次问题。但某些人,还是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美好的事情妖魔化。他们执意要这样,也怪不得谁。其实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多余,倒不是因为那把腐朽的骨头,就其炮制的很多所谓的文章来看,完全是毫无意义的。
车子进入呼市,寿盛问我此前来过没?
我说七年前到过一次,有过六小时的短暂停留。
他说他在呼市待过三年。2012年至2014年,他辗转于呼市和包头之间,那时事业在这边。我说很遗憾啊,在你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擦肩而过了。寿盛说起了那些年,在呼市的生活经历,轻描淡写的叙述让我多少有些惋惜。我说,你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正是我人生最窘迫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地区,却未能遇见。
他说,那时候我急需一个助手,但一直没有寻觅到。假如那时候,我们相遇了,你会和我一起干事业吗?我说不会?他问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随性的人,虽然需要生活,但与生活相比,更需要理想和自由。和我在一起,也未见得没有理想,没有自由。我说,你是商人,逐利是你的天性,生活中你更喜欢纠缠于不同的人和事之间,这一切对你来说似乎是常态,但对我来说,未必见得就适合。他说,能挣很多钱呢?我说不知道。
……
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和七年前毫无二致。马路不宽,楼房破旧,远处的大烟囱,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厌其烦地往外吐着白烟。七年前的景象历历在目,尽管那时我和妻只逗留了几个小时,记忆中那天刮了很大的风。呼啸的西北风,把没有叶子的槐角树,吹得吱吱响。我和妻在内蒙古大学校园里,一面想找个地方躲风,一面还想去看风景。
最后,终因胡地风大,不得不取消计划。
今天,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心境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来寻觅美食的,在百度地图的指引下,我们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一家特色美食店,风卷残云一番后,带着几分倦意扬长而去了。离开呼市的时候,我想起了妻,想起那个二十三岁美丽而单纯的女子。
她的一颦一笑,以及她在西北风肆虐的呼市街头,紧紧依偎在我身边的景象。
如今,她已成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男人贤惠善良的妻子。我们生活不算富裕,但足够安逸。这对我们来说,很享受,也很满足。有句话说的好,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我们在一起,生命不寂寞,却也繁华。
6
和制片人、导演见了面。
就电影剧本、演员、拍摄、后期及宣发事宜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总体上,还算满意。特别是导演,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宁夏人,除说话带点北京腔外,看得出来,她身上依旧保留了宁夏人的那种质朴和韧性。
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多为娱乐圈内的事情。
我是一个不太关注娱乐新闻的人,对圈内的人和事了解不多。但对一些大跌眼镜和违背常理的新闻还是会凑凑热闹,比如“艳照门事件”、“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奖”以及毛宁、房祖名、张墨、满文军、陈羽凡等人的失德事件。至于,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私奔,谁和谁牵手,谁和谁亲吻,均不在我关注的范围内。
下午,本想给李云龙打个电话,一起坐坐。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和寿盛、凤霞都是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很难克服。事先没有告知,临时找地方,实在太困难。北京,给我影响,实在太大了。
十年前,我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在穆肃组织的活动现场认识了李云龙。那时,他在东莞图书馆工作,和大多数文艺青年不同的是,他时常穿一件蓝白条纹的T恤,背一个绿色帆布包,包上面有个耀眼的红色五角星。这种包与时尚等元素无关。相反,它是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年代感极强。那时,他写网络小说,在国内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因为共同的爱好,我们自然便成了朋友。
寿盛问我有没有想见的朋友,我想了想,说没有。他问我想去哪里转?我说去北大和清华转转吧。寿盛说,北大和清华,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正好借此机会,感受感受。出门后,我们找了家饭店,简单吃了饭,就驱车前往了。
在中国,每个年轻的学子几乎都有一个北大或清华梦,这个梦或许遥远,可能远到你永远都不能实现;这个梦也可能真实,对与多数中的少数来说,一觉醒来,他从此就成了清华园或未名湖畔的风景了。无论怎样,有梦想总归是好的。很喜欢网络上的一句话:“人生不可无梦,世界上做大事业的人,都是先有梦想来;无梦就无望,无望则无成,生活也就没兴趣”。鲁迅先生也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我年近不惑,还如此喜欢做梦。
那些年,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清华女生不回头,长发飘飘梦中游。北大女生一回头,倾倒整个男生楼。也正因为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想去北大、清华的雄心与壮志。只可惜,智商这东西,是天生的,吃土豆长大的孩子和喝牛奶长大的孩子,在智力上还是有差别的,别不承认,这是真的。就拿我这个从小吃煮土豆、蒸土豆、炒土豆、烤土豆的人,在学习上尽管很努力,最终还是未能与清华或北大建立缘分。今天,只能带着遗憾,以游客的身份,一睹它们的风采。
无奈,疫情期间,社会闲散人员不能进入校园。站在校门口,寿盛和凤霞各种摆拍,看着他们脸上荡漾着的幸福与微笑,心里的遗憾真是无以言表。好在我和妻已有两个子,如若有一天,能将可唯和宇扬送进这里,让他们将来为“祖国或以梦为马”的人做贡献,即便我满脸沧桑、头发花白,拄着拐杖捡破烂,也不枉此生。
我是朴素且简单的人,不想什么高官厚禄,也未想过荣华富贵。只想简简单单,以文为生。最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如下:
今天,站在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门前,第一次体会到了“碌碌无为”这两个字的含义,那种紧张,局促不安以及遗憾感真是不言而喻。真如菲茨杰拉德所说,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爱,但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
既然如此,那就把它放心里,是激励,也是鞭策。
信息发出后,很多朋友点赞问候。东莞文友薛依依发来截图,并附了题为《已经没有时间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诗作,内容如下:
我走在一条极为平常的路上
街道、落叶,一闪而过的汽车,陌生的脸
看起来都很坚定自己的存在是理所当然
似乎,只有我还困惑自己是否属于这条路
我没有陪着一个女孩在石椅上阅读
也没有试着喊停从我身边跑步而过的男孩
又或许有相濡以沫的夫妻,早已从我身边离开
许多事物未曾真正了解,就已选择视而不见
快走到道路的尽头,才发现自己
已经没有时间成为另外一个人
此刻,我尽可能平静地向她诉说着这一切
但我怎能平静地面对自己碎成一地的人生
看到依依的信息,心里很激动。我和依依因文学交流活动认识,所有的对话时常不超过三个小时。这两年里,我们彼此忙于各自的生活,并不经常联系。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她是如此内敛、安静、清新脱俗,灿如春华,皎如秋月。我们不算陌生,但很奇怪,她在我记忆里却一直形不成整体印象。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活在世俗社会中且与我有一面之缘人,她更像是一个活在厚重文学作品或电影里的女子。
总之,她就是这么美好,令人欣喜。
我说感谢你还能记得茫茫人海中这个沧桑、朴素的朋友。你的诗如此美好,让我读出了来自生活以外的诸多复杂性。
依依说,看到你朋友圈的信息,感觉内心是如此相通。随后,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文学的话题,我们向过去一样,谈到了西川、北岛、海子、朱湘和于坚,还谈到了博尔赫斯、阿赫玛托娃、雪莱、爱伦·坡以及共同的诗人朋友丁成。
谈着谈着,不知怎么竟莫名地感伤起来了。很多年了,我都来不及为一件事情感伤。生活使我变得的麻木、自私、多疑甚至冷漠。可今天,我竟然莫名地感伤,不只道原因,事实上,也没有原因。若不是寿盛和凤霞在身边,我真想大哭一场。
为碎了一地的人生和万劫不复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