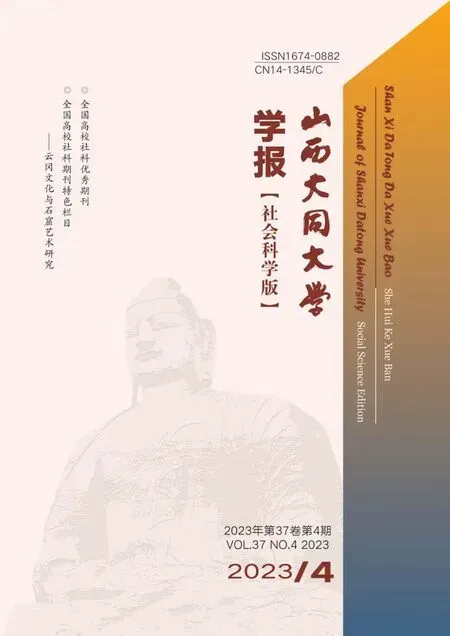严复《英文汉解》中“条顿”考证
甘 霞
(1.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太谷 030801;2.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翻译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的译著不仅影响了同时代及五四前后无数探寻救国救亡道路的有识之士,且在其后漫长时期一直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严复最大的贡献是系统译介西学,后人出版严复全集是纪念严复、发扬严复科学与爱国精神的重要途径。目前已出版的严复全集主要有:王栻先生主编、中华书局1986 年出版的《严复集》(1-5卷);王庆成先生编、台湾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 年出版的《严复合集》(共14种,20册);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严复全集》(10 卷加1 附卷,共11 卷)等。以上全集多收录有严复的《英文汉解》。
一、《英文汉解》及严复其它译著中的“条顿”
(一)《英文汉解》的“条顿Tentonic”《英文汉解》是一篇论述中西文字的演变与区别、英语语法、修辞、英文发音等语言学知识的文章,大约写成于1910-1911 年,分总论、正书两部分,全文1800 余字,手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系残稿。
在《英文汉解》总论中,严复首先讲到汉字与外国文字的区别,“天下文字皆切音,独中国以四象为文字。四象者,象形、象意、象事、象声也。四象为经,而以假借、转注为纬,是谓六书。”[1](P286)严复考据得出“西方诸国文字与竺乾梵字同根同源,分支派别有克罗特Keltic、拉体诺Latina、希腊Hellenic、斯拉方Slavonic、条顿Tentonic 五者。”[1](P286)在严复看来,英语是条顿语的一种,其中伴随其它种文字杂行。
严复此处所提到的“条顿”,在目前的《严复集》(第二册)、[1](P286)《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2](P424)《严复全集》(第7卷)中,[3](P347)均用英文“Tentonic”表示。
(二)严复其它译著中的“条顿”除《英文汉解》以外,在严复其它著作中,“条顿”也经常出现,只是有不同的表述。
在译著《原富》部甲《篇十》的按语中,严复写道:“不惮艰险而乐从军走海上者,欧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图敦、日耳曼之种尤然。”[4](P109)这里的“图敦”,在书中的注释为“Teuton,今译条顿。指日耳曼民族。”[4](P109)
在《原富》部戊《篇二:论国家度支之源》中,严复写道:“其图顿种人及摩洛他官长,则百四十。”其中的“图顿种人”同为“Teuton,条顿,即日耳曼人。”[4](P570)
在《群学肄言》《倡学第二》中,严复写道:“乃至今世史家,如福劳特之欧史,其论条顿、罗马二种人之战也,曰:‘世人当以此为莫之致然,而条顿之胜罗马为侥幸……’”。注释中称“条顿为Teutons”。[5](P24)
在《社会通诠》的《宗法社会》篇中“种人群制分第五”里有“宗法社会,自种人始……条顿种人则谓其本于古史之沃丁。”同样有注释“条顿种人:Teutonic tribes”。[5](P382)
此外,在《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四章《日耳曼王希勒特力之被逐》中的按语中,严复再次写道:“言其大概,欧人之为种三:曰条顿也,曰拉体诺也,曰士拉甫也。”[6](P313)再一次提到“条顿”。
(三)应为“Teutonic”而非“Tentonic”不难发现,在已出版的严复全集、文集中,《英文汉解》中的“条顿”与其它篇目中的“图敦”“图顿”“条顿”所用的英文表述是不一样的。在《英文汉解》中用的“Tentonic”,而其余均用“Teutonic”。
经查,在英汉辞典中,“Teutonic”的解释是:“日耳曼人的,典型德国人风格的;日耳曼语;日耳曼人;指古代西北欧的条顿民族的;条顿语。”[7](P2628)在Merriam Websters Dictionary中,“Teutonic”的 意 思 是:“thought to be typical of German people;relating to Germany, Germans, or the German language:relating to an ancient people who lived in northern Europe。”“Teutonic”首次作为名词出现则是在1612 年,首次作为形容词出现是在1618年,常解释为“Germanic”。[8]
而“Tentonic”在字典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英文汉解》中的“Tentonic”应该是后人在辑录时把其中的字母“u”误看作“n”录入了。①
二、条顿语与现代德语的关系
严复在其译著及按语中多次提到的“条顿”(Teuton),是古日耳曼人中的一个分支,后世常用“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德语“Deutsch”(德意志)、英语“Germanic”(德国的)均来源于“Teutonic”(条顿)。
公元前118年前后,条顿人、安布昂人、辛布里人(Cimbri,属于日耳曼部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三个日耳曼民族沿中欧的易北河(Elbe River)右岸逆流而上,抵达匈牙利平原,并在那里(今贝尔格莱德西郊)建立了首都“条顿堡”(Teutoburgium),逐步与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日耳曼人能征善战,他们受十字军感召,极具宗教使命感,其中又数条顿骑士最为著名。条顿堡森林伏击战后,日耳曼人从罗马帝国手里赢得独立,被南方的古罗马人称为“Teutons”。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由于社会组织形态过于落后,统治者又缺乏政治经验,无雄才大略,小富则安。罗讷河战役后,罗马人得以有了喘息之机。
易北河大约有三分之一流经捷克,三分之二流经德国,因此古代德国人也自称“Teutsche”,他们把条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后来古罗马人又将居住在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和北海之间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地区的条顿人的旁系子孙称为“germen”(日耳曼人)。
德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左右。当时,查理大帝所控制的法兰克王国囊括了今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三大板块,领土相当辽阔。条顿原本是法兰克王国的东半部分,公元843 年,凡尔登条约之后,三分帝国,东法兰克王国(今德国西部)在血统方面主要是条顿人,因此讲条顿语;西法兰克王国(今法国)讲罗曼斯语;意大利王国(今意大利半岛中、北部及东、西法兰克之间狭长的洛林地区)讲威内托方言(即通俗拉丁语)。目前所知有准确记载的最古老的德语和法语文献是公元842 年路易与查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盟誓时,分别使用条顿语(古德语)和罗曼斯语(古法语)宣誓的记录。
现代德语中的“Deutsche”(德意志)是从古日耳曼语“Teutsche”转化而来的。中世纪初期,“Deutsch”(德意志)一词首次在德语中出现。该词的演变历程大致为:theoda(古日耳曼语“部族民”)—thodiscus(古日耳曼语“部族民”)—thiodisk(古日耳曼语“人民”(—teutonicus(条顿人)—teutsch_deutsch(德意志)—Deutscher(德国人)。[9](P23)公元四至八世纪,欧洲民族大迁移(Völkerwanderung)时,日耳曼语发生高地德语音变,从而使德语慢慢从日耳曼语中分化出来。现代英语中“Germanic”(日耳曼)和“Teutonic”(条顿)几乎是同义的。英文“German”(德国人)一词的演变历程大致为:germen(日耳曼语)—germanus(古法语)—Germain(古英语)—German(现代英语)。[10]
三、条顿语与现代英语的关系
严复提到:“民智愈开,引者愈众。故英文一篇,其中字原于拉体诺、希腊者盖太半也,其纯为撒逊盎格鲁者Saxon-Anglo。”[1](P287)英语是一种多中心语言,现代英语是从盎格鲁—萨克逊语中变化继承下来的。大约4000 年前到公元元年左右,英国人一直都使用凯尔特语,也就是说英语起源于凯尔特语。但从公元450年-1100年间的西日尔曼语才真正是英语的起源。在大不列颠岛上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语言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凯尔特语(Celtic)。公元1-5世纪大不列颠岛东南部为罗马帝国所统治,这一时期,拉丁语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凯尔特语的地位下降。公元449年,居住于丹麦与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盎格鲁人(Angles)、萨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这三个日耳曼人部族趁罗马帝国衰落之际,分别占领了日德兰半岛的中部、南部和北部,[11](P5)用日耳曼部族方言同化并取代了当地的凯尔特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盎格鲁—萨克逊语(Anglo-Saxon),即古英语,Englisc。古英语受低地日耳曼语影响很大,比如发音、动词、复合词结构等,但与现代标准德语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公元9世纪,以说北日尔曼语为主的丹麦人大规模侵入英国北部,使大量纳维亚语(以古诺斯语为代表)的词汇融进古英语中。英文大概从诺曼语中吸收了一万多个单词。
大约公元1000 年,整个大不列颠岛被称作“Englaland”。“Englisc”和“Englaland”本是描绘盎格鲁族的词汇,后来逐渐演变为“English”(英格兰人、英语)和“England”(英格兰或英国)。公元1066—1154年,在诺曼底王朝统治期间,英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语言,当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因为上层阶层主要是法国人,没落的英国贵族仍讲古法语方言盎格鲁—诺曼语;教士们用拉丁文阅读圣经、在教堂开展宗教活动;而平民以及农奴等下层社会劳动者则用英语。[12](P139-142)法语在英国的特殊地位一直延续到14世纪。13世纪之后,英格兰王国正式与其他的讲凯尔特语族的王国结成了联合王国式的联盟关系,即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雏形。1337 年,英法百年战争开始。在长达一百多年的争斗中,英语吸收了很多法语词汇,并逐步取代法语,成为当权者的语言。现代英语中约有5万词汇是与法语相近甚或完全相同的。公元1500年左右的元音大推移将中古英语变形为近代英语。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作品将近代英语推向繁荣。18 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殖民地的迅速扩张,英语随着大不列颠对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和殖民走向世界。在19 至20 世纪,英语从各个殖民地吸收了许多新的词汇与表达,加入更多诸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及希腊语的词汇,所以现今的英语已不再是纯种的日耳曼语族,而是同时拥有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及其它语种词汇的多中心语言。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领域的频繁交流,许多国际场合的沟通和文化传播都开始使用英语做为媒介,英语逐渐取代了法语在外交上的地位,成为世界语言。
总的来说,英语变化的轨迹大致为:卢恩语(Futhark)→古英语(即盎格鲁-萨克逊语)(Old English、Anglo-Saxon)→近代英语(English)。
四、《英文汉解》中的语言学知识及思想意蕴
《英文汉解》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文章,严复在其中也不仅仅是为了介绍英语修辞和语法知识,他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传统文化坚守、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高度阐释文字和语言的重要性。
在《英文汉解》的正书中,严复详细介绍了英语的26个字母的大小写及英语发音规律。英语本属日耳曼语族,大约在公元6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语开始借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拼写系统。所谓的“英语字母”其实是古罗马人使用的拼写字母,只是英文字母比旧罗马字母多了一个“W”。英语中的元音、辅音被严复称之为主音、附音,他用中国的“宫、商、角、徵、羽”对比英语中的“a、e、i、o、u”五个元音(我国五声音调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并具体介绍了单元音、双元音、多元音的发音,“合两元为一呼者谓之合音,此外虽合二三元音,而其用与一元等者,此为赘合,名digraph。字母之w与y谓之半元,大抵用之元音之前则同仆音,用之元音之后则成合音。”[1](P288-289)至于辅音,严复指出,其“以必附元音而后可呼而闻也,其用所以变声,或以止气,视居于元音之前后。”[1](P288)严复区分了清辅音与浊辅音的发音的不同,辅音可分舒与促两类,舒者出气,促者闭气,并进一步区分了流音、鼻音、齿音、轻唇、重唇,舌腭、喉音等,[1](P289)着重介绍了英语中的同音异义词和同形异义词与汉语的差别。
严复一直认为,语言的演化同样遵循天演之律,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语言和文字是特定地域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带有先天的民族基因。在《英文汉解》中严复提到,中国的文字只有“虚实”之分,每一个单词的意思及本原流变都甚为繁复,往往初义与引伸义完全不同,虚实转换,动静结合,究竟是何种意思要因事因境而异。西方的字母(Letter)之于文字,“犹化学物质之原行而非其母也。”[1](P287)
西方的语法相对较发达,但是严复认为学习外语不能舍本逐末,一味强调语法。文字和语言的形成、演变并非是在语法律令的框架中生硬组合的,而是人们在特定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中耳熟口从,习以为然,世代传承的结果。语言与文字通谓辞,辞的作用是“达人心意”,“修辞立其诚”。在《与梁启超书》中,严复提到:“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13](P516)言为心声,“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使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14](P151)严复认为,每一个语种都是先有语言而后有语法,并非根据语法排列组织语言。“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跡,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14](P151)“辞必有法而后能达,此天下言语之所同也。”[1](P287)在严复看来,所谓语法,乃“文辞之律令也,其事始于一字。盖察切音之字,其中恒有三者之可言。”[1](P287)严复总结了语法的三大要素:“字之音声”“字之义训与其本原流变”“字之对待所以与句中他字相缀属而成理者”。[1](P287)字母音声拼切之理,即Orthography,正书、正字法;字之门类与其转变之法,即Etymology,字论、词源学;字与字所相为系属之伦脊,而为之著定例,即Syntax,造句、句法规则。严复所编《英文汉诂》是“近代较早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较为系统的汉文版英语语法教科书。”[15]
严复认为,语言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其语义信息尽失。在《英文汉诂·卮言》中,严复写道“南民不可与语冰者,未有其阅历也;生瞽不足以喻日者,无可为比例也。”[14](P154)各个民族或地区的语言各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但这并不代表语言具有排他性,不可相互通约。[16]在严复看来,不同语种之间是可以相互补益的。他一直试图借用英文的语法知识梳理中国语言。严复曾为《〈马氏文通〉要例启蒙》作序,其中便饱含了他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精辟见解。
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习西文则为异族之奴隶”的观点,严复用斯宾诺莎、牛顿、培根等人的真实事迹予以反驳:“二百余年以往,英、荷、法、德之硕师,其著书大抵不用本国之文,而用拉体诺语”,[14](P155)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思想的发挥。在《天演论·自序》中,他借用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话阐释学习外语的重要:“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17](P1319)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是为学之基,外文对于国文具有“相资之益”。“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14](P156)国人通过了解西方文字和文化可以更好地参悟中学的微言大义。一个国家的学术由这个国家特定的文字写成,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学术必须先通其文字,这样才能获取原汁原味的学术精髓。“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14](P153)严复倡导翻译西方思想要直接读西文原著,反对转译经过二手过滤的日本的文献。他曾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提到,相比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和“翻译”,学术之事的“上之上者”是“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13](561)
严复学贯中西,思想深邃,他毕生致力于译介西学、倡导并推动外语学习,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数典忘祖,而是十分推崇传统文化,呼吁保存国文,固守国粹。严复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旁征博引中常现典故,他始终坚信强调本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读经当积极提倡》中提出“群经乃吾国古文,为最正当之文字”,[1](P331)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立国根基、性命根本。严复推崇孔子和六经,呼吁儿童从小读经,耳濡目染,培养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严复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充满深切的民族主义情愫,其译介西学的根本目的是借助西学回照故林,光大国学。严复对语言文字的地域性、民族性的彰显和其对待中学、西学的态度,反映出其在百年未有的时代大变局中,突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中华民族精神的执着和远见,流露出救亡图存的良苦用心。
注释:
①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宪明先生建议作者核实严复《英文汉解》手稿,弄清到底是王栻先生整理时出了错,还是原稿本身是错的。遗憾的是笔者经多方努力未能完成。期待学界前辈和同仁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