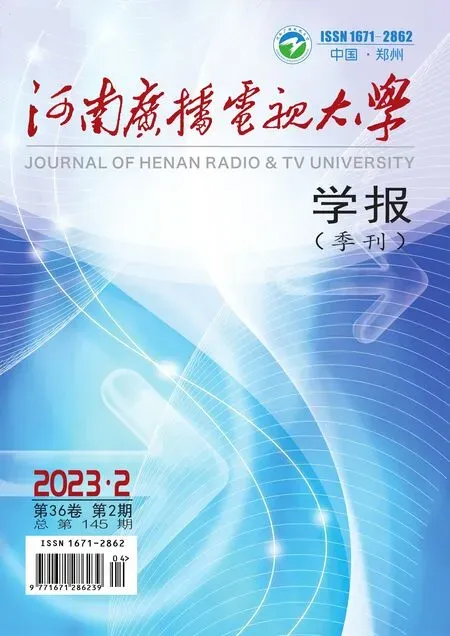西游取经故事的跨文本探究
——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例
梁利玲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文化艺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20世纪初,罗振玉先生于日本游学时发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著作,于是便将其刊印,带回国进行深入研究。这一举措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深切关注。其认为《取经诗话》这一著作的研究可从多方面来进行,比如成书年代、语言技巧、空间布局与宗教文化等。多数学者也对这些因素进行了长时间分析,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学者正视,即《取经诗话》的跨文本研究。《取经诗话》是一部典型的说唱文本,而说唱文本是集合了说部、变文等文本内容的著书体例,从跨文本方面研究这一西游取经故事,能讨论不同文本系统之间的“互文阐释”,对故事背后的文化形态更加熟悉。
一、西游取经故事涉及的主题
(一)宗教主题
《取经诗话》的主要思想倾向于宣扬佛教文化,涉及净土宗、密宗与禅宗的深入教义,可以看出,这些西游故事中带有浓厚的宗教主题思想。从历史层面来看,《取经诗话》是《西游记》成书之前的参考篇目,是唐宋流传的取经故事的全面总结。关于这一话本的宗教倾向,历代学者都持有大体相近的思想观点,即认为全书贯穿了宣传宗教主题的思想,是一部典型的宣传佛法道义的宗教文本。据多方参考资料的对比研究也发现,《取经诗话》中虽然神话传说案例居多,但可看出,每一个故事中都充满了佛教氛围,反映了佛教中多家流派思想。以净土宗为例,早在东晋时期,社会便已经大力倡导弥勒净土思想。释道安派最有慧根的弟子慧远负责传播弥陀净土思想,而慧远受师傅所托,曾在庐山创办了莲社,专门修佛讲佛。净土宗认为,凡夫俗子要想从人世间这一恶俗之处剥离出来,不仅要礼拜参佛,而且要时常定修持法来洗脱身上罪业与烦恼,多捐功德,如此才能得到最好的归宿。这一思想到了唐武宗时期,受到天子的抨击与抵制,净土宗受到重创。与此同时,天台宗、禅宗等别家宗派纷纷崛起,与净土宗分庭抗礼,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取经诗话》中有大量描写佛寺净土的文字,比如在进入钵罗国之后,其中一处写道:“满国瑞气,尽是菩提花;根叶自然,四季皆无……”[1]这一描述与净土佛经中的“无春秋冬夏之分,不寒不热,常和调适”类似。再如,进入天竺国时,写道:“寺内佛具齐全、香烟袅袅,花果重重。”[1]又道:“灵异光明,人所不至,鸟不能飞。”[1]这些描写都将佛天圣境的庄严和神圣表露无遗,其中目之所及的念佛、烧香,是净土宗中典型的修佛场景。可见,《取经诗话》故事中的宗教主题特色十分鲜明。
(二)救赎主题
一直以来,在读者心目中,西游取经故事带有浓厚的救赎主题内容。据可考资料显示,无论是晚唐五代无名氏的《取经诗话》,还是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最后再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大唐法师立志向西取经的故事被逐渐神话和完善。但无论是哪一版本的西游故事,核心主题都是大唐法师师徒相互陪伴、克服困难,最终成功取经回乡。以《取经诗话》为例,这一西游故事中的救赎主题更为明显。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被救赎者、猴行者不断犯错又不断被处罚,进而获得成长等内容。《取经诗话》中救赎主题并未单独刻意体现,而是通过大唐法师与猴行者、深沙神的对话和行为动作描写,以及其他人物的烘托而体现出来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经诗话》中主要有法师、猴行者、深沙神等师徒四人,占据篇幅最多的当数猴行者和深沙神这两个人物形象。比如在《取经诗话》的第二卷开篇,猴行者人物出场之时,便以白衣修士自居,并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猕猴王,愿意保护法师向西取经。法师将其收下之后,虽然猴行者一路上也在降妖除魔,但其不懂“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为人处世之法,因此被法师屡屡训斥。之后猴行者受法师影响,逐渐明白了胸怀天下、济世扶贫的道理,最终得以升仙。《取经诗话》中并未详细介绍猴行者在拜入法师门下之前所犯的大错,只是在途经西王母池时,猴行者自行透露出自己偷食蟠桃被抓获,后被发配花果山紫云洞,而后皈依佛教,最终得以消除业障修成正果的事。而西游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深沙神,是一个妖怪,曾两度要将大唐法师的真身吃掉。当第三次法师经过此地时,深沙神被点化,于是便选择皈依佛门,助法师取经。取经事业完成后,其被天子封为佛殿神将,受世人跪拜。由猴行者和深沙神的经历可总结出,二人都曾犯下弥天大错,但也都在皈依佛教之后潜心改正,这一过程真正体现了西游救赎的主题[2]。
(三)文化主题
王静如先生于1980年首次在《文物》期刊上介绍了关于榆林窟取经壁画中的隐藏内容。据其指出,壁画中描绘的西游取经人物是学界研究取经故事的一个有力佐证。在第二幅猴形神将图研究中,学界将其作为西游取经故事中猴行者人物形象的参考资料,并结合其他壁画内容,发现了取经故事中的师徒并未在《取经诗话》中全部介绍到位这一问题。学者也是基于壁画内容,加之其他文化参考资料的佐证,才证实了这一结论。可见,研究《取经诗话》需要从多重文化角度深入剖析。另外,《取经诗话》中宗教部分的描述中,神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神,一类是社会神。例如,《离骚》中的云中君死后被封为神,后稷教民众种庄稼,死后被封为农神,这一类属于自然神。社会神则是在民间自然形成,由官方加封成神。例如,猴行者被封为大圣、深沙神被封为佛殿神将等,这一类便属于社会神。如此体现出《取经诗话》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见《取经诗话》带有明显的文化主题。
二、西游取经故事中说唱文本的具体体现
(一)记事
《取经诗话》属于典型的说唱文本。在这一文本形式中,记事是主要特性之一。首先,关于其记事表现形式的由来研究,需要从“诗话”这一名称讲起。王国维先生以为,“诗话”二字与唐宋时期的诗话有所不同,诗中有话、话中有诗才是这一体例得名的原因。之后,胡士莹先生也对此观点表示了肯定。其次,从含义上来讲,“诗话”作为文学批评用语,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讲都有记事特征,《取经诗话》这一西游故事又以故事讲述为主,因此此书以“诗话”二字为名十分恰当。例如,在进入沉香国之后,着重讲述了师徒几人的所见所闻,并对周围环境进行了详细描述,最后以一首代言体引诗作整段落的结尾,如此使得沉香国这一故事十分生动且富有画面感,体现了该文本的诗话记事特性。
(二)说部
在文本记事之余,文学批评中的诗话还与说部文体相通,比如孟棨的《本事》、卢环的《抒情》中都有说部文体的体现。至于《取经诗话》的诗话说部文体,有这样的解释:“足考当时诗人之遗闻轶事,体例近于小说。足资昔人诗句考证,何尝不可入子部……无所不包。”[3]从这句话中可知,诗话文体与小说中的说部体例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为“乃留诗曰”之类的引端。这类引端在每一节故事中都存在,比如《取经诗话》中的每一个新故事的开端中都有“途经”“初入”“到”等引端性的词汇,之后又会引入相关诗歌,形成先叙事、后引诗的表现手法,这一形式恰恰与说部著书的常用方式不谋而合。如此便可知,《取经诗话》中的说部文体形式运用较多,贯穿全文[4]。
(三)变文
《取经诗话》中的说唱文体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变文。张锦池先生对《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进行了细致研究,在其研究中提到,该文本中保存完好的15节小标题中,竟有11处带有“处”字,而“处”字是典型的变文格式,由此可见,《取经诗话》中也带有变文文体元素。比如,在“行次至火类坳”“次入一国”“次行又过一新国”等描述中可知师徒几人的途经之地和所遇之事,可见以“次入”“处”等变文文体为转换叙述词,能简洁明了地将西游中的每个故事生动描述出来,由此体现出变文这一叙事手法的功能多样性。同时,程毅中先生在其著作《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中也对《取经诗话》的变文记事体例进行了观点阐述。其认为,《取经诗话》中的变文形式并非变文文体的全部结构,而是自有超越变文之处。就以“处”字为例,该文本中的“处”字不只是引出韵文的意思,作者更是将其放到每一小节的标题中来充当实际的意思表示,并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由此可见,这里的变文文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引文作用,而是成为故事结构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三、西游取经故事中的文本特点
(一)文学性
在《取经诗话》的文本特点研究中发现,其具有鲜明的文学特性,不仅给当时的读者和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而且为后世文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经典素材。文学性强的作品戏剧性都较强,因此,研究《取经诗话》文本的文学特点,可从其戏剧加工手法上来分析。《取经诗话》中对怪、力、乱、神的成分讲解十分之多,同时制造各种悬念,将“神异化”转化为“传奇化”。比如,在法师经过磔迦国时与国王展开的一番僵硬言辞,描写到“动色攘袂”“送师还朝”“呜咽不能复言”等僵持场面,之后法师以绝食相逼,整个过程极具张力和戏剧性,又仿佛合情合理,体现出较强的文学艺术功力。不仅如此,文本中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节,在此便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取经诗话》这一西游取经故事取材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性特点较为鲜明。
(二)生活化
《取经诗话》的文本除了有明显的文学性之外,还带有世俗意蕴明显的生活化描述。据唐代文人笔记了解到,古代文本记述不只有说唱形式一种,还有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体例类型。但在《取经诗话》这一故事中,虽然有戏曲、小说等体例的雏形,但总体结构仍然以说唱形式为主,社会民众都能以说唱的形式将这一故事复述出来,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十分有益。同时在故事讲述中,为迎合中下层民众这一类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取经诗话》从提到钟声梵呗、烟云香雾转而又增加了市井叫卖、山林打猎等故事,由庄严肃穆的参佛生活转移到走街串巷的实景生活,将读者带入烟火气十足的真实情境,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体现出明显的生活化特征。这不仅是古典叙述文学发展变化的主要现象,而且是古典文学与社会生活相衔接的重要体现。
(三)故事性
《取经诗话》的主要文本特点还有明显的故事性。全书共17节内容,每一节内容都各有不同,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观感和想象体验。其中的游民猴行者,主动向法师提议护送其去取经,在取经路上遇到各色妖魔鬼怪,必然需要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打斗,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搞怪有趣之事,可见其带有明显的戏剧性、故事性特征。比如,师徒一行人途经狮子林时,有狮王、麒麟相送;在树人国买菜被化作驴等。这些有趣的故事不仅给漫长的取经之路带来了惊险刺激的感受,而且营造出和谐有趣的氛围,使旅程不至于枯燥无味。同时,尽管西游取经故事已经被翻译成多个版本,也被多次修改完善,但《取经诗话》这一文本在讲述故事时仍具有其独特的虚幻艺术魅力。例如,文本在讲述降妖除魔故事时,折射出风土人情和世间百态,在描述主人公相互救赎的过程时,反映出人性的变化多端。
四、西游取经故事的跨文本意义
(一)以空间结构来言不可说之语
分析《取经诗话》的变文文本可知,该文本的结构设计带有明显的空间叙述性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为文本故事的塑造提供了载体,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空间真实感,容易引起读者共鸣。首先,《取经诗话》故事的场景空间是有先后顺序的。该书作者参考玄奘取经的一路行程,以大唐法师为主人公,构设了大梵天王宫、香林寺、狮子国、树人国、鬼子母国等场景。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写作手法,对路途较艰难的场景进行了详细描写,对其他场景以寥寥几语带过,读者可以从详略分配上体会地理空间的变化。其次,从引文描述中可知,每当师徒一行人途经一处,通常是先以变文词汇转换空间,然后再进行另一场景的描述。空间地点的转换便是情节的转换,对于空间转换,《取经诗话》中并未采用一些明显的转换词汇进行衔接,而是直接以变文形式一概而过,为主角的行为活动阐述节省了大量笔墨[5]。
(二)以神魔传说来构建艺术世界
古代社会中,人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本能的敬畏之心,正是这种敬畏之心,才催生了形式丰富、类型多样的神魔传说故事,而神魔传说故事的存在又为古代文学创作提供了较多素材。比如,《取经诗话》中西王母池、火焰山等地点的选取就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形成的艺术文本素材。神魔传说故事中亦真亦假的空间被作者引入诗话文本中,更好地体现文本的艺术特色。在《取经诗话》中,作者借助多个神魔传说故事讲述了大唐法师取经路途的艰难,描写了师徒情分逐渐深厚的过程,从各个奇幻的故事背后映射现实空间中的世俗文化与生活百态,从艺术的高度给读者的思想观、价值观带来冲击,不仅能让读者了解艺术隐射下现实生活的残酷,而且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坚持内心所想、坚守本心而最终得以修成正果的成就感,珍惜现有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艺术文本中领悟生活哲理。这便是《取经诗话》中大量采用神魔传说故事的创作初衷。但神魔传说构成的诗话文本毕竟是虚幻的,是艺术领域中的表达形式之一。而艺术本身不仅具有生活化特征,而且具有虚构的成分。因此,《取经诗话》以这一方式构建艺术世界是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结合的成果。
(三)以相互救赎来展现人物成长
西游取经故事告诉我们,取经路上的困难并非来自外在客观条件的威胁和影响,而是来自内心世界的“心魔”。心智是否坚定、意志是否强大都是救赎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所谓救赎,必然要与自身的心魔作斗争,战胜心魔便是救赎成功;反之,则无法修成正果。在《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和深沙神同属神怪一物,尚且有不同的心魔欲望;大唐法师属于一介凡夫,必然也会有所求。而有所求便会心生欲望,自然容易被心魔所侵。文中看似是大唐法师在一路教化点拨猴行者和深沙神,实际上猴行者和深沙神一路上的降妖除魔,也在坚定着法师的心智。正是由于师徒之间的相互救赎、相互扶持,才有了最终大道正法得以传承、主人公的愿望都得以实现的结果。如此看来,《取经诗话》中主人公相互救赎的过程也是人物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一主题中深入剖析主人公的相互救赎问题,能深入了解人物性格变化和心智变化,准确把握人物成长的特点[6]。
五、结语
西游取经故事有多个版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一西游故事是早期出现的一种故事文本。从跨文本角度分析这一文本形式,其不仅是虚幻的浪漫主义作品,而且是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其艺术性与现实性兼具、文学性与生活性并存,是少有的隐喻意义大于结构意义的说唱文本体例,具有深远的研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