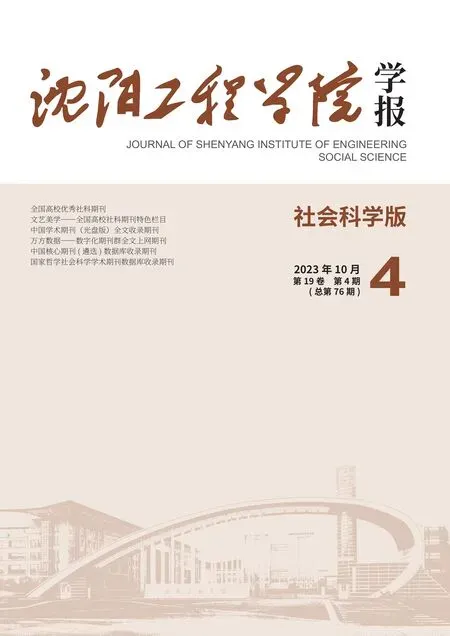充盈的对待与空灵的飘飞
——王静纸上刀绘的生命气韵与审美旨趣
吴玉杰,孙冬迪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一花,一鸟,一世界,一刀见功底。王静在28年间以钢制柔,用尖锐的刀与她自己发明研制的光滑硬挺的刀绘专用纸绘制出二百余幅作品。王静纸上刀绘融合了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用充盈的对待关系显示饱满生动的生命气韵,以神思妙想建构作品的艺术张力,在空灵的飘飞中意象化地表现审美旨趣,展现思想化的力量,个性化风格日趋成熟。
纸上刀绘偶然产生于王静不小心用裁纸刀把卡纸划破,白色线条在红色卡纸上格外醒目,这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她有意识地开始刀绘,把生活中的偶然创化为艺术上的必然。一般人可能在偶然中止于惊奇,而王静却在这一偶然中探秘,成为中国纸上刀绘艺术第一人。这源于她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艺术和生活就这样融为一体。在无数个工作结束后的深夜,王静带着对生活的欢欣愉悦和对艺术的执着热爱投入到创作中,28 年如一日,在空白的纸面上一点点绘制出内心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刀绘由起初的红白两色,发展到如今的斑斓多色,颜色逐渐丰富,层次感不断增强,情思愈加灵动,形式更富意味,完成从技艺到艺境的质的飞跃,展露出磅礴的气势和多彩的才华,成就独一无二的纸上刀绘艺术。正如王向峰教授所说,王静“取得了美术体式的突破,创生了一种介于绘画与雕刻之间的交缘性的美术品种,而且还创造出了一批富有审美意蕴的作品……展现出我们这个有梦时代的丰富景象”[1]。
一、充盈的对待与生命气韵
纸上刀绘中的审美对象,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富有意味的对待关系中存在。充溢丰富的对待关系随处可见。朱熹说:“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因为有对待关系,所以构成一个气韵生动的整体,否则不相干的两物会使刀绘失去凝聚力,而呈现离散性。作为表现主体的动物明确地显现出与或实或虚的对象间的互动关系。有“蜜语花间”中两只鸟的对视,而使互动之生命焕然;有“怜香”中鸟对花的“探视”,而使爱之心迹表露;有“窃喜”中松鼠对果与枝的凝望,而使占有之欲望彰显。“清韵满塘”里四只天鹅的张望与呼唤,动物与对象物相映成趣,如同陆机所说的“应感之会”。《求索》中一只小鸭子竖起上半身想要衔住飞舞的蜜蜂,另一只小鸭子则有自己凝视的标的,动物与对象关系的意趣跃然于纸上。《长歌邀月》中一只孤狼伫立于悬崖上对着月亮嚎叫,叫声在空荡的山谷中回响,孤狼与孤月互为映照,那种彻骨的寂寞与悲凉冲撞着观者之心。《和谐共生曲》中的20 只白鹭于青山绿草之间,虽各有形态,有的高飞,有的驻留,有的远眺,有的俯瞰,有的等待,有的寻找,但细观它们的神态和姿势,各有各的对待标的,因而整个画面生气勃勃。《迎朝红》中一匹草原上的骏马,正迎着初升太阳的方向奔跑,朝阳的光芒即将闪耀,生命与光明形成了表意上的同构,生命迎向光明迈出坚实的脚步。充盈的对待关系中流露出富有节奏感的生命律动。
五代后梁时的山水画家荆浩在《笔记法》中把“气”“韵”放在画的“六要”的前两位,并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这意味着要通过揣度体味获得事物的内在精神实质。既要把握表现对象的真实、生动的外在形象,又要将对象置于自然界的背景中,与周围环境相互关联,有序表现对象与环境之间的纽带,描绘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纵观王静的创作,多以物象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为表现内容,物象与环境构成了相互关系。刀绘存有“召唤结构”,物象不仅仅是在环境当中,更是召唤环境中的对象物与之呼应、交感,从而与环境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犹如刘勰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当物象与环境处于和谐有序的关系中时,便获取了一种对自身尤为重要的稳定性,生命力由此生发,作品便获得了饱满的生命气韵。
刀绘中充盈的对待关系与生命气韵的流动,来自于王静作为创造主体对与其构成对象之间关系的独到把握。刀绘费时,而且没有容错的机会,必须刀刀精准,一次成型。这就要求在刀绘之前必须深思熟虑,刀绘时心、手、刀三位一体,把自己的生命气息通过手和刀传递到对象身上才能使对象“活灵活现”、生机盎然。刀绘之难,一般人难以想象。“一天如果连续不间断地作画8 个小时,那么一幅画作完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由此可见,在铜板纸上作刀画的过程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耗费体力的过程,当然更是一个拷问耐心与毅力的过程。精气神儿、眼神儿,手功、坐功都得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凝结在刀尖下纸板上。用‘千刀万剐’一幅画来形容铜版纸刀画最恰当不过了。丝丝点点间耗去了时光,完成了辛辛苦苦的艺术创作。”[2]王静屏住气息,用刀尖刮去的每一丝,留在铜板上的都是生命的气息。
二、多重的对比与艺术张力
王静将大量的绘画技巧融会贯通,以多重的对比设置,刚柔、明暗、虚实、远近、动静、加减、横竖、轻重等,建构起作品的艺术张力。
以《迎朝红》为例,画面设置了远近关系,马位于近景,地平线处于远景,骏马脚下的草地被精刀细绘,远处的茫茫草原则是虚化的线条,虚实变化扩展了画面的空间感。画面上方天空中的云朵形状柔软松散,下方草原上的骏马肌肉线条强劲有力,刚柔并济,和谐统一。线条的繁简呈现对象的主次,骏马及身下的草地细节甚多,远方的地平线以较粗略的线条表示。线条的疏密表达光线的缠绕,马背线条浓密,有阳光照耀下的光泽感,马腹、马尾等阳光没有照射到的地方线条稀疏,明暗的交汇形成了马的立体感。高光暗影是对不允许出错的纸上刀绘的巨大考验,稍有偏差整个艺术格局瞬间失色。王静以精微之刀炫出不同层次的艺术光影,“明暗塑造法”(伦勃朗)召唤观赏者跟随创造者的情思相机而动。在动感的画面旁边辅以文字题识,卷曲的点线与横平竖直的文字一动一静,又浑然一体。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做减法”,以刀刮去纸面的颜料,不同力道和角度留下不同的痕迹,显现不同的点线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光影格局,最终合为完整的艺术作品,又是“做加法”。观赏过程是动态的,观赏者的目光首先落到骏马这一表现对象,马是背向观赏者的,观赏者的视线随之移动落到远处的地平线上,其反射的光泽将目光引向天空中的朝阳。同时要调动想象力设想马正面的神情,将眼前的实景与脑海中的虚景结合在一起。在远近、虚实、刚柔、繁简、明暗、动静、加减、轻重等诸多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的关系中,王静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众多对比关系,展露出独到的艺术眼光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运用对比,突出对象特点,凸显画面层次,增强艺术张力,和不同的观赏者构成审美对象化关系,使作品的审美意蕴更加丰富,这也是王静刀绘获得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三、空灵的飘飞与趣味美学
王静的作品多使用随心所欲的物语。对象多活动于灵活的空间,处于空灵的飘飞之中,而不胶着于固态的地表,代表了未泯的童心和对生活始终怀有的热情与好奇,这也彰示了她在“好玩儿”“有趣”的“迁想妙得”之下深蕴着的“趣味美学”“游戏精神”与自由理想。
刀绘艺术中有动物憨态可掬,无忧无虑,悠闲自如,或“自娱自乐”,或相望而待;也有凌空振翅,草原疾驰,齐飞、同奔为伴。王静对蜻蜓在半空中翅膀姿态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刀绘,融入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将艺术家的任务阐释为:“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3]这种连续性的恢复首先是艺术品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王静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赋予其令人愉悦的动作和情态,将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联结起来。
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的联结,表现出王静的艺术理想——自由的精神创造和空灵的审美旨趣。卡西尔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Formative)它就不可能表现。”[4]纸上刀绘的艺术构形在空间的设置上别有情致与韵味。王静多以半空或水面为背景,是可以上下位移的更为灵活的空间,蕴含着自由飘飞的意味,显示出空灵的审美旨趣。平静的水面不似土地般坚硬平实,半空中的枝杈作为鸟类的栖息之所同样远离地面,水面和半空可以容纳表现对象上下方向的移动,是更为开阔的自由审美空间。在艺术的世界里,王静选择远离地面所代表的现实场景,以流动的水面和悬浮的半空作为动物活动或植物相伴的场景。当物象与水面或天空发生联系时,会扩容空间的灵动感。王静在飘飞与落地的两极选择进行了意象化的处理。雏鸟作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表现对象,在《新声》《练翅》《初生》《期盼》等作品中,或是努力着初试啼声,或是好奇地观察面前的世界,或是练习着挥动翅膀,待羽翼丰满之际翱翔于蓝天。地面或巢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们终将归属于天空。这些亦真亦幻的人间细节与自由空灵的审美旨趣飘飞在广阔的诗意空间,凸显出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气韵。
王静一面认真观察着日常化的生活细节,一面体味着内在心灵的诉求,不但使她的创作显示出饱满的生命力和空灵的审美倾向,同时也造就了刀绘作品中潜藏着的思想化的力量。刀绘将世界当做风景,表现作为景观呈现的对象与情景,这种情境时刻简单连贯,从中可以参透过去,勾连未来,生成完整的意义。《窃喜》画面中成熟的柿子可推定深秋时节,松鼠的两个爪子合拢捧着一颗松子,眼睛似凝望柿子,面部展露满足的表情和轻松的神态,那高高翘起的尾巴似乎向我们“宣示”着生活的惬意,想必它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冬日做好了储备,可以安然过冬,或者其他什么。从独立的景观中,观赏者可以推想出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从它那里“想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时“窃喜”的意义最终浮现出来。莱辛在《拉奥孔》中认为:“既然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取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5]艺术家要避免激情顶点的顷刻,因为顶点即是止境。王静“节制的激情”在顶点到来之前化入物象与情境之中,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景观,具备某种程度的世界感,尽显静穆的伟大,唤醒观赏者对世界的玩味与爱,“是一种只观察、只欣赏,不批判、不影响的文化意识”[6]。王静的“视角是向下的,但并非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存在于众生之中,满含着悲悯的大德大义注视着‘人世间’的渺渺生灵”[7]。从对象中来,而又不拘泥于对象,从具体对象身上升华的世界感,使王静刀绘艺术的境界不断提升。
富有空灵感与趣味性的刀绘充满着古典情致,也表征着王静的文化情怀。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她说:“希望通过纸上刀绘这一美术新样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用刀和纸这一创新组合绘就万千气象和人生百态。”[8]《十月中国》的红,两只鸟的憨态与意足,既具有古典的韵味,又诠释了新的时代内涵;2022 年,特殊历史节点创作《和谐共生曲》,于绿草青山之间的20 只白鹭,也是融古典与当下性为一体的富有意味的审美再造。
用纸上刀绘符号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王静,始终秉持着一种从容、洒脱、自由的创作姿态,其作品自然地流露出对世界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认同,对生命真谛的体味,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充盈的对待与空灵的飘飞中含蕴着的生命气韵与审美旨趣,使她在艺术殿堂的高阶,下“刀”如有神,状绘世间万象。纸上刀绘的未来,我们更加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