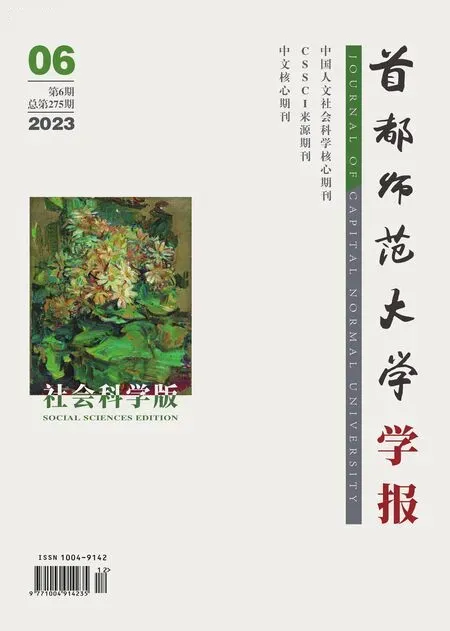情节时间的辩证法:利科论叙事对时间经验的重塑
吴 飞
时间问题无疑是困难却又极具魅力的:时间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测量时间?如何在时间中存在?它们激起了无数哲学家的兴趣,后者则尝试通过物理时间、意识时间、先验时间等众多理论来予以解答。不过某种程度上正如彼得·扬尼希所言,许多涉及时间问题的“反思和回答已然丢失了它们在生活中的位置”,尤其是与语言及行动的关联。①Peter Janich,“Constituting Time through Action and Discourse,”in Jan Christoph Meister,Wilhelm Schernus,eds.,Time:From Concept to Narrative Construct:A Reader,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1,p.29.与这一判断遥相呼应,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试图在传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以叙事理论来提出和解答这种难题。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时间疑难在利科这里主要指时间经验疑难:人们徘徊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之间,被它们撕扯。正如意大利诗人斯帕齐阿妮(M.Spaziani)所写:“记忆是愉快而忧伤的东西……一扇扇窗子朝着未来打开……可这儿的时间充满生机……时间的模糊化作令人头晕目眩的明朗/痛苦如潮水不停地咬啮我。”②斯帕齐阿妮:《现在》,吕同六编:《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利科试图通过叙事理论来解答这种痛苦。在他看来,一方面,经典叙事学几乎没有质疑叙事活动隐含的时间概念,而是不加批判地将叙事时间与线性的流俗时间等同;另一方面,时间理论又常常忽略叙事活动为我们表达时间经验提供了一种优先途径。因此他打算通过“时间与叙事”的命题揭示存在(时间性存在)的疑难如何通过叙事获得解决。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vol.9,1979,p.17.不过利科的叙事概念极为复杂,既涉及指称的真实性问题,也涉及热奈特区分的叙事、故事和叙述等概念,时间命题也因此呈现出不同面相。②在利科的体系中,历史时间、虚构时间、叙事时间、故事时间、叙述时间等都有各自的内涵,甚至部分时间模式在某些层面上还相互排斥,因此不可一概而论。“情节”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因为情节是所有叙事作品的基体和主干,同时利科最初也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理论进入叙事学,并在其“情节摹仿行动”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三重摹仿理论。这样,情节的时间性、情节时间与行动时间的内在关系,就成为通过叙事反思时间经验疑难的本体论基础和首要途径。
一、时间经验疑难与情节时间的提出
利科以叙事理论来解答时间经验疑难的方案实际上源自对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结合,并深刻地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和近代法国语言学的影响。通过“重演”他们并与之对话,利科厘清了语言(叙事)、行动与时间经验的交互关系,为后续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奥古斯丁的探讨为利科提供了时间疑难的底本,同时也暗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对前者来说,时间疑难是多层次的。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本体论困惑:“时间是什么?”在他这里,一方面,根据空间定义时间是无效的。因为尽管人们通常借助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来经验时间,但运动并不是时间,时间不会随着物体的加速、减速或停止而变化。另一方面,实体意义上的时间及其测量同样可疑。因为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现在又不断流逝(如果现在不流逝便不会有时间,而是上帝专有的永恒),看起来“除非因为时间倾向于不存在,否则我们便不能正确地说它存在”;时间测量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了。③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trans.R.S.Pine-Coffin,New York:Penguin Books,1961,p.264.
由于这种态度,有观点主张奥古斯丁实际上承袭了巴门尼德和芝诺等怀疑论者的论调,即倾向于认为时间并不存在,或至少否认其具有真实性。④阿德里安·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胡萌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2-23页。但无论是从神正论还是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时间存在对奥古斯丁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它如何存在、如何起作用以及伦理地位如何。的确,正是语言为奥古斯丁的时间沉思困境提供了最基本的确定性。当陷入本体论困惑时,他注意到时间在话语中是最熟悉和最周知的东西:“当我们自己使用该词(时间)或听到他人使用该词时,我们必定理解其含义”;而且我们能“意识到时间的距离”,能够比较和说出哪段时间长、哪段时间短。⑤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p.264-266.因此正如利科所说:“我们谈论时间,并且是有意义地谈论时间,这支持了关于时间存在的断言。”⑥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vol.1,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7.
那么时间如何存在?奥古斯丁在这里略过语言直接进入意识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对时间的“感觉、比较和测量”实际上正对应着与时间相关的“感官、智力和实际活动”。⑦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9.因此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实际上是意识时间:实存着的并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那些事实的记忆图像”;将来则需根据已存在的“原因或记号”以及“印象”等来“预见”;而现在意味着“直接感知”。这样一来,时间毋宁说是以“记忆”“预期”和“注意”这三种方式存在于心灵中。⑧“存在于……中”为时间提供了一种准空间的存在方式。不过记忆和预期总是发生在现在,因此过去和未来实际上存在于现在,奥古斯丁将它们称为“过去之物的现在、现在之物的现在和未来之物的现在”,也就是所谓的“三重现在”,这是一种更加时间化的存在方式。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269.
但这三者远没有想象的那般和谐。在奥古斯丁这里,它们都是具有“动力学特征”的“意向”(intentio)——该词意指“一种意志活动,其功能是将心灵与世界中的存在者和对象联系起来,从而使人们能感知、记忆和思考”。①Andrea Nightingale,“Augustine on Extending Oneself to God through Intention,”Augustinian Studies,vol.46,no.2,2015,p.185.这种意向是单向的和纯粹的,它使人感知某物、在一定时间内聚焦其上并将其与心灵联系起来。②正是这种性质使奥古斯丁将意向应用到“向上帝延伸”的活动:“心灵通过意志的意向得以延伸,使其仅以纯粹爱的方式与上帝相连。”Andrea Nightingale,“Augustine on Extending Oneself to God through Intention,”p.208.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意向是对所有事物的意向,它无法始终保持对事物的单一意向。现实生活中的时间经验恰恰就摇摆在这三种意向行为之间:人们既要预期未来,又要专注现在,还要回忆过去,但它们却永在流逝,无法把捉;而且它们留下的“印象形象和记号形象”也彼此不同——记忆保存图像,预期则只进行预见或预言。这表明时间经验所在的心灵内部充满了意向的分裂,奥古斯丁称其为“心灵之扩展”(distentio animi)。本·霍兰指出,“distentio”在奥古斯丁那里被经验为“精神与身体、争夺我们的注意力的诸对象、对死亡的惧怕和人类必死性的痛苦事实”等的分割或张力,它意味着一种“膨胀”的痛苦经验。③Ben Holland,Selfand City in the Thought of Saint Augustin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0,p.132.这样,彼此冲突的时间经验就是一种苦难乃至罪愆,它将心灵逼迫到支离破碎的边缘,使人远离上帝宁静平和的时间:永恒。这构成了奥古斯丁乃至其他任何时间理论的基本困境。
利科认为,海德格尔至少在时间经验的分裂问题上与奥古斯丁一致,只不过他是用“操心”的三种时间性“绽出”来代替未来、过去和现在,即将来(coming-towards)、曾在(having-been)和当前化(makingpresent)。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18.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通过“向死而在”强调时间性中未来的首要地位,然后通过“历史性”将重心从未来移往过去,最后返回现在,时间的“扩展”因此才不至于沦为纯粹的分散,这点后文还会再作探讨。在聚焦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的趋同性而非差异性的意义上,利科提出了人类时间经验的三重悖论:
首先,人类时间经验的扩展性与线性时间观的冲突。后者将时间视为由抽象的“现在”均质地、连续地构成的时间“线”,它能定义事件发生的先后以及状态持续的时长;但正如奥古斯丁所示,时间实际上熔铸着人们的记忆、注意和期待,它在“操心”的本体论结构中“连接了认知、实践和情感的成分”,不是纯粹线性的、冷漠的。其次,这种时间经验造成了痛苦,“distentio”在利科看来意味着延展(extension)和分心(distraction):“我们在遗憾、悔恨或怀旧中迷恋过去,在恐惧、欲望、绝望或希望中热情地期待未来,以及怯懦于转瞬即逝的现在;当我们被它们撕扯时,分心就占据了上风”,它不同于纯粹的意向,而且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克服它。最后,“扩展”究竟只是时间意识的某种疾病,还是与“延展”和“意向”有更深层的辩证关系?⑤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18-21.这些疑难和悖论揭示出人类时间经验的模糊性和痛苦性,表征了一种“不和谐”(discordance)状态,它既折磨着奥古斯丁,也成为利科试图解答和超越的难题。
不过利科也在奥古斯丁的讨论中获得了双重支持:其一,语言为抵抗时间的怀疑论提供了有力支撑,它表明时间至少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并能被认识——即便是“记忆、预期和注意”这三种意向也是在语言(诗歌和歌曲)的例子中得到揭示的。⑥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6页。其二,《忏悔录》的整体结构实际上暗示了时间疑难的发展逻辑。利科认为奥古斯丁的沉思是在叙事过程中的沉思,正是各个章节的叙述将充满冲突的时间经验纳入了一个连贯的、逐渐通向高潮的框架,使其能被理解。这表明叙事至少在认识论上扮演了某种关键角色。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利科走向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概念,并与法国语言学进行着有效对话。
一方面,语言与时间在以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为代表的法国语言学界获得了直接的关联。不同于传统时间理论倾向于通过意识、运动等因素来规定和理解时间,也不同于传统语言理论将语言的时间系统视作对现实时间的模拟或再现,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产生了整个时间范畴。在他看来,物理时间和纪年时间“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时间性”,我们无法确定日历上的某个时间点究竟位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实际上所有的时间形式都源于与“现在”的关系,过去是现在“之前”的时间,未来则是“之后”的时间。而这个现在只拥有一种“作为时间指示物的语言学事实”,也就是“被描述的事件与描述它的话语时位的同时发生”。①Emile Benve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Mary 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3,p.227.换言之,正是言说的当下规定了现在时刻。话语陈述据此建立起现在时范畴,后者又产生了整个时间范畴;而主体间的交流进一步将这种私己的时间体验变成公共时间。②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3-163页。这种语言时间观念对利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实际时间与动词时态的循环关系,而这在语言学层面回应了利科叙事学试图打通叙事和现实的一贯目标。
相较之下,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为利科提供了一种更关键的资源,因为情节是一种“和谐”(concordance)的模型,并且该模型并非如后世诗学强调的那般是纯诗学的、封闭的,它与“活的时间经验”相关,③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31.这使其有可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解决奥古斯丁“不和谐”的时间疑难。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核心在于“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④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但应指出的是,这种情节实际上还只限于悲剧情节,为此利科对其作了全面延伸:首先,他将“对行动的摹仿”延伸为对行动的意义结构、符号资源和时间特征的“前理解”,揭示出行动和经验本身就具有“前叙事品质”;其次,将情节延伸到各种叙事体裁,并尤其强调它“将事件组织进一个系统”的“情节化”(emplotment)能力;最后,将摹仿引起的怜悯和恐惧延伸为文本对读者世界的指称和重塑。这样,利科就提出了标志性的“三重摹仿”概念,他“严肃而开玩笑地”称之为“摹仿I、摹仿II和摹仿III”,也就是摹仿活动的三个阶段。⑤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53.时间问题正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线索之一,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表述为“情节时间是对行动时间的摹仿”。其中情节时间是摹仿II的要素,但它同时又关乎对行动时间的前理解和对读者的行动时间的重塑。
行动时间和情节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变得明晰起来,但我们不能对其作过度简化的理解。情节对行动时间的摹仿并不简单地就是使用某些真实的时间标记。真正的问题在于行动时间呈现出奥古斯丁意义上时间的疑难性——我们总是“在时间中”行动,并因此面临各种相互冲突的时间经验。那么情节如何反映并克服这种经验?利科通过挖掘情节时间的内在张力和重释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模型,在行动与情节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关但相离的“平行关系”,使后者得以指称并重塑前者,从而治愈奥古斯丁“心灵之扩展”所带来的痛苦经验;确切地说,它试图通过叙事来“诗意地”解决人在时间层面的生存困境。但在到达这点之前我们必须追问:情节及情节时间本身有何深刻内涵?
二、情节时间的内在张力:时间性与非时间性的辩证法
语言当然与时间有关,我们仅粗略地指出其中三种关联:首先,语言是发生在时间中的话语事件,这种性质为语言带来了现时语境中新的“使用意义值”或者说“信息”,从而确立了语言的实存;⑥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2页。其次,语言具有时间结构,句子的动词时态和各种时间副词都能揭示这一点;最后,语言指称时间,并因此指称人在时间中的存在。由此也可见奥古斯丁以语言来支撑其时间论证并非出于偶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时间”概念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固然拥有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悲剧、小说、历史、自传、谈话等大量叙事资源,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与时间问题相关;但这并不是理解叙事的唯一方式,甚至在某些理解模式中时间还要被排除,比如在科学解释和结构主义那里。那么,叙事时间,尤其是情节时间问题还成立吗?正是在这里,利科试图表明叙事(情节)与时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间接的——尽管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来,情节具有某些逻辑特征,这造成情节的时间性与非时间性的分裂,但正是由于这种分裂,情节时间反而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而积极的理解模式,从而为后面解决时间经验疑难铺平了道路。
首先,关于情节问题。简单来说,情节就是“事件的组织”,只不过利科认为它既具有系统的意义——作为故事线索,更具有行动的意义——能将异质的或相互冲突的事件纳入协调的和可理解的秩序中,拥有“不和谐之和谐”(discordant concordance)或“异质综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的性质。
一方面,“和谐”指情节在形式上拥有“完备性、整体性和适当的长度”等特点,它们突出地强调了情节的逻辑特征。①这三种特征既是对作为摹仿对象的行动的要求,也是对作为摹仿结果的情节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特征在《诗学》的中英译本里都作“严肃”(elevated/serious stature),唯独《时间与叙事》将其引作“完备”(complétude),存疑。其中整体性指情节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从逻辑上看,它们与必然性概念有关:开头不必然上承他事,但必然引起他事发生;结尾必然上承他事,但无他事继其后;中间则介于开头与结尾之间并承上启下。这种逻辑特征也规定了“长度”概念,它要求情节具有足够的规模使事件“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39.另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6页。因此好的情节就意味着其故事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必然律或或然律——具有可能性、可信性、连贯性以及因果性等逻辑特征,并因此能够表现事物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不和谐”指情节违背秩序原则,其中既包括出人意料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包括令人恐惧和怜悯的事件,它们构成情节理解的主要威胁,因为我们很难将其纳入一个必然的、整体的、可理解或可接受的情节脉络。不过在利科看来,这种“不和谐”毋宁说是“不和谐之和谐”:其一,通过“突转”等程序,偶然或出人意料的事件能被整合起来,具有必然性和可理解性;其二,通过这种整合,不和谐的情感冲突反而得到“净化”。不过这种最终的“和谐”并不是说故事必须有圆满的结局,而是说情节在根本上具有“统合”事物的能力,它将“悖论与因果顺序、惊奇与必然的融合带到了它们最大程度的张力”。③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p.43-44.
情节时间在这种规定中是被暗示的——故事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并且围绕它首先产生了两个悖论:
其一,行动时间不仅不被考虑,某种程度上还必须被排除在外。16-17世纪的剧作家提供了反面的例子,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悲剧长度等的讨论提出“三一律”,要求“演出的时间与剧中行动的时间必须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将现实表演时间等同于情节时间,但这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和误读”。④谭君强:《“三一律”的时间整一与戏剧叙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亚里士多德清楚地区分过这两种时间长度:(1)表演时间“是由比赛与观剧的时间而决定的……每出悲剧比赛的时间应以漏壶来限制”;(2)剧中时间则是“由戏剧的性质而决定的……长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许事件相继出现,……就算适当了”。⑤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6页。结合前面的探讨,这意味着作家应该根据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而非时间顺序来安排情节,正如利科所说,情节中两个事件之间的“空洞时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会追问主角在其生命中两个本应隔开的事件之间做了什么”。⑥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p.39-40.叙事作品能够省略无关紧要的时间,现实生活却必须逐日度过它们。这提醒我们叙事时间至少在事件的安排上不同于行动时间。
其二,正是出于时间因素在叙事暴力中的这种被动性,许多叙事理论直接将情节时间简化为空洞的线性时间,甚至将其取消掉。普罗普(V.Propp)就曾认为“功能”是“构成一个故事的基本成分”,但它们的顺序“在极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即便缺少某些功能也“不会改变其余功能的秩序”。⑦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定义与方法》,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增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7页。在利科看来,对情节链的这种切割导致时间片段的孤立,它们因此被视为“外表连贯的不连续实体”。这一过程中只有情节片段的先后关系被考虑在内,时间维度“立即被剥夺了它作为情节的时间构成”。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9.这意味着叙事时间仅被简单地视为承载事件的框架,仅被用来标记事件的先后顺序,它本身的多样性及意义并不受重视;这“为将时间性化约为逻辑性铺平了道路”。在结构主义鼎盛期,这种化约表现为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试图建构缺乏时间性的“叙事模型和代码”,如洛梅尼(Beau de Loménie)提出“无事件的历史”,格雷马斯和巴特也建构过非时间性的叙事模型。因此“时间已经从历史和叙事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②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2.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核心疑难: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结构主义叙事学,情节的时间维度不同程度上被其逻辑维度排除在外(行动也是如此),那么利科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情节时间呢?实际上在利科看来,情节不可能真正地脱离时间,这是其形式特征所规定的基本前提;但情节时间绝非如结构主义叙事学所认为的那般简单,他们忽略了“叙事矩阵的时间复杂性”,也因此忽略了叙事理论为时间经验的现象学所能提供的贡献。③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2.
那么“情节时间”有何复杂性?前面已经指出,情节也意味着情节化,即通过情节使事件组合成故事,实际上正是其中的组合顺序涉及时间问题。这方面的探讨虽然不少,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真正从理论角度研究叙事时间的著作”。④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热奈特就在《叙事话语》中承袭托多洛夫对叙事中“时间畸变”的探讨,详尽剖析了时序、时距和频率等重要问题,揭示出包括时间倒错、倒叙、预叙、停顿、省略、单一/反复、交替等在内的复杂叙事现象。⑤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不同于热奈特的枚举法,利科以演绎方式探究了这种复杂性的一般原理。他认为“通过情节使事件变成故事”恰恰表明故事并非只能根据时间顺序来排列行动或事件,确切地说“情节化行为以可变的比例结合了两种时间维度:一个按时间顺序,另一个则不按”。其中,前者构成叙事的串连(episodic)模式,情节在这种模式中按“物理事件和人类事件共同的不可逆的时间顺序”将事件彼此连接,构成一系列开放的、无止境的事件链,也即线性情节,我们总是可以不断追问“然后呢”,并以“然后、再然后”乃至“如此等等”来回答。后者构成叙事的塑形(configuration)模式,它将连续事件“统合”(grasp together)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从而把情节转化为思想,使其能够被领会。利科为这种统合行为赋予了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和反思性判断的特征——在康德那里,判断旨在“将直观杂多放到概念的规则之下”,而反思性判断更强调为具体事物寻找规律或普遍性。因此在利科看来,塑形模式从根本上具有一种综合(synthetic)功能,它对事件进行反思,以便将其囊括进一个普遍的模型中。⑥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6.关于判断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4页。这种模式在其极端意义上表征了情节非时间性的逻辑特征,即作为纯粹的结构——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表明这种去时间化的模型仍然具有情节因素,因为它涉及准人物、准事件、准情节等准叙事学问题。⑦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224.
这样一来,情节化就处在彻底的时间顺序和彻底的反时间顺序、事件的线性理解和意义理解这两极之间,由此造就了形态多样的情节面貌,并据此成为一种兼顾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的解释学模式。利科意义上的叙事理解实际上就是时间理解与非时间(逻辑)理解的辩证法——这里所谓的“辩证法”脱离了黑格尔所赋予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知识主持着逻辑、精神和自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随着绝对知识理想的崩溃,辩证法随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解释学是后黑格尔哲学时代批判性地继承辩证法精神的关键领域之一,伽达默尔曾明确地提出“辩证法必须在解释学中被恢复”。⑧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利科也是如此,他认为辩证法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生产性的对立(opposition productive),这种对立“以某种方式在现实或经验中激活、促进或者产生新的东西”,系统是这种辩证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或者说“辩证法只可能是事物通过生产性对立而发展的过程”。①Paul Ricoeur,“Le ‘lieu’de la dialectique,”in Charles Perelman,ed.,Dialectics,The Hague:M.Nijhoff,1975,pp.93-95.其适用范围也从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领域缩减到“人类现实”,尤其是欲望、意志等领域。利科的研究始终贯穿着这种辩证法精神。对情节问题而言,时间理解与非时间理解恰恰构成一组生产性对立,它们孕育了超越文本封闭性的力量——阅读活动将是这种力量的延伸和实现,我们稍后会以“重复”-“重塑”的名义回到这点。
概言之,如果说情节化意味着“不和谐之和谐”,那么在时间问题上,情节本身除了具有时间结构和指称时间外,它还游走在不同的时间层次间,旨在建构一个具有必然性和可理解性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意义整体。正如利科所说,情节化在“故事所谓的观点、主题或思想,与直观呈现的环境、人物、插曲和构成结局的命运变迁之间,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可理解性”。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8.这意味着叙事主题不同于逻辑论证,它是将连续的事件统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意义在这里本身蕴含着时间和逻辑、情节和思想的动态关系。这种“对抗与结合”的混合理解模式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未曾留意的,利科的贡献正在于通过揭示情节时间的内在张力提出了叙事作品中时间与意义的辩证法。《俄狄浦斯》等作品的教益恰恰就来自人物的历史行动所造成的伦理悲剧,缺乏这种时间性,它将沦为纯粹的说教。由此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悲剧为何能净化观众,从我们的论题看,即情节时间在何种意义上能指称并重塑时间经验?
三、情节时间对时间经验的重塑
时间经验的疑难性主要在于时间意识内部的分裂:人们被对未来的预期、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当下的专注所撕扯,陷入焦虑乃至绝望之中。尤其是对作为神学家的奥古斯丁来说,这种尘世时间与上帝永在现在、永远宁静的永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不和谐”状态也就愈发令人难以忍受。利科的解决方案是以情节理论所提供的理解模式来再现和治疗这种冲突。在利科的分析中,情节不再具有稳定性,它充斥着各种紊乱的事件和时间形式,而又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具有可理解性的整体中。结构主义叙事学止步于揭示叙事时间的复杂性,利科则将通过情节摹仿行动这一古老命题为这种方法论赋予了目的论意义。
但我们首先面临一个隐藏已久的悖论: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时间根据第二部分所述却不得不被排除在情节时间之外。这作何解释?质言之,这里排除的实际上是物理时间或者说线性时间,真正作为摹仿对象的“行动时间”本质上是奥古斯丁意义上“不和谐”的时间经验——利科借用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将其作了彻底的现象学还原。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于世界中的此在,其存在意义是时间性的。时间性意味着,生存有一被给予的终结,这就是死”。③张立立:《时间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但利科并未完全聚焦于“向死存在”这个问题,他更强调“时间经验的三重结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将通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性尤其是“时间内状态”纳入了讨论。首先,时间性在他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未来的首要性,即直面由承认死亡的中心地位所引起的有限时间结构。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19-20.这种阈限条件“构成了一个预期结构的开端”,使此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回应自己”。⑤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in Niall Keane and Chris Lawn,ed.,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Chichester:Wiley Blackwell,2016,p.107.其次,历史性将重心从未来移往过去。它首先指“我们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成为(becoming)’方式”,即生命的“伸展”(stretch along)、在时间中的生成;接着指此在被抛的境遇:我们“已经被一种基本的历史意义所定向”,这种历史性使我们“所敞开的存在之可能性已然被形塑了”;①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pp.106-107.但此在具有“重复”的能力,这种重复意味着此在能重演过去的主角:“解释他们”,“与他们争辩,回答他们”,②英伍德:《海德格尔》,刘华文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并因此回到“曾在此的此在的种种可能性中去”,从中继承“向之筹划自身的生存上的能在”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6页。,获得身份、潜能和命运。最后,时间内状态(within-time-ness)。利科极力凸显时间内状态的重要性,认为它尚未被敉平为由均质的、连续的现在或瞬间构成的“流俗时间”,它是人类活动的“现在”——我们总是在时间中(in time)行动,总是首先以自然方式而非天文学和物理学等人工措施来估算时间(后者是前者的固化,并促成了线性时间观念)。这种时间概念承载了人的认知、实践、情感、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因此被利科视为行动的最佳表征。
正是这种拓展后的情节结构和时间经验结构,使利科得以通过“情节摹仿行动”在情节时间和行动时间(时间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行关系”,并且试图通过它解释“作为叙事的时间和作为时间的叙事的统一性”。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5.
首先,叙事实际上“将人建立在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时间内状态’的时间化层面,即日常生活的时间”。叙事并不完全按照物理时间讲述故事,它会省略无关紧要的时间,突然插入回忆或预期,加速或减缓事件发展的速度等。这些处理方式不完全是技法问题,在利科看来,叙事时间以“可变的比例”呈现自身实际上是为了讲述“时间内状态作为人类操心的一种真正维度的真相”。故事中的主角们估算时间并利用时间;有时间或没有时间去做某事;失去或赢得时间;被抛入某个环境,而这个环境根据自然措施是一个有“日期”的时间,同时它也是与他人共享和互动的时间。日常生活的时间本身不是均质的、冷漠的,而是有所操心的时间,它承载了人的主观感受并且能被人干预和施加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时间的多样性就揭示了时间性存在的真相。
在结构主义历史理论和文学批评那里,叙事时间被认为是抽象的线性时间序列,他们因此要么将其彻底地还原为非时间性的叙事代码,要么将其附属于科学解释。这恰恰忽视了故事讲述所揭示的时间内状态的“生存论特征”。不过叙事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还立即是一种治疗。正如前面所说,叙事将连续的、偶然的事件统合成“有意义的整体”,为不和谐之物提供了和谐的理解。叙事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乃是一种对生活和主体自身的反思及重建。正如利科在谈到精神分析的叙事方面时所说,患者带来一堆破碎的故事片段,它们“夹杂着患者无法忍受和理解的扭曲及变形”,精神分析师的任务则是“重建一个故事,使之易于理解和可接受”。⑤Paul Ricoeur,Critique and Conviction:Conversations with François Azouvi and Marc de Launay,trans.Kathleen Blam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71.时间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叙事再现并重建了生活。
其次,叙事所做的不仅是将人建立在时间中,它还提供回忆,即将人“从时间内状态带回到历史性”⑥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6.——但利科过于直接地认为这是向历史性的过渡,在我们看来这种回归恰恰首先体现为朝向“未来”或者说“向死而在”的时间性视域;接着我们才以这种时间性眼光来历史性地理解故事,“用未来重新解释、重新阐述这个过去”⑦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p.107.。
叙事提出了“结尾的意义”问题。情节的塑形维度表明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无限延伸的,它必然有其结尾。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利科看来,阅读故事实际上就是“跟进”(follow)故事,也就是“在一种期待的引导下,在意外事件和剧情突变之中向前发展,并最终在故事的结尾中获得实现”。结尾终结了事件的无限绵延,它“赋予故事一个终点”,我们不再面对无止境的事件链条,而总是对结尾有所期待。这种期待再现了海德格尔对“先行到死”的讨论,利科称其为“向终而在”(Being-towards-theend)。结尾不仅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将故事视为一个整体,更要求我们在“为其自身提供承载着自己内在终止之标记的生存论”上来看待这种整体性,①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trans.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vol.3,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64.即在明知有终结的情况下审视故事——它贯穿并重塑了读者的阅读态度,读者不再漫无目的地跟进事件,而是时刻试图“理解连续的情节如何以及为何导向了这种结局”,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7.这恰恰就标志着阅读从时间性转向了历史性,并且伴随它也产生了审慎等伦理态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乌托邦叙事和末日叙事也是这样一种“向终而在”,它们提供了可能的未来图景,而这种图景反过来将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因此叙事实际上在文本内部和外部同时建立起一种来自未来的理解视域。
由此我们转向第三种时间概念,即历史性及重复问题。对众所周知的故事(尤其是个体或民族故事)来说,“重述”(retell)代替了“讲述”(tell),这时理解故事不是为了理解“逆转”或“惊奇”,而是为了理解“开头所暗示的众所周知的结局,以及通向这种结局的众所周知的情节片段”,③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8.这产生了新的时间品质。理解此时意味着“回忆”——对这种“被其结局方式统治的故事”的回忆代替了从过去流向未来的那种不可逆的物理时间顺序:“通过在开头中读出结尾,在结尾中读出开头”,我们学会了“逆向阅读时间本身”。这实际上意味着读者在跟进故事时,通过反思既有情节来理解人物和情节的当下发展。对个人或文化史而言,这意味着读者有意无意地透过历史叙事来理解其身份、潜能和命运。《圣经》、荷马史诗、18世纪的小说、唐诗宋词等,都传递了某种传统,理解它们就是“在真正的历史性,即重复性的层面建立人类的行动”。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8.人们通过重述故事获得了反思和重新出发的契机,文本世界也就实现了与读者世界的交叉。
重复概念极为重要,它通过“重演”此在的曾在或曾在此的此在,使此在以个人命运或集体命运的形式从中继承“最本己的可能性”,以此建构人对自身的理解: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叙事具象化了这种历史性的生存维度,使其不再是抽象的和含混的,利科通过提出三种叙事重复模式清晰地揭示了这点:
1.对起源的重演。这实际上相当接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重复概念,也即回到“初始场景”。童话故事的开篇往往将主人公和读者带回某个梦一般的“原始时空”,那里存在着影响深远的伤痛事件。比如《天鹅的故事》中公主的哥哥们被继母用魔法变成天鹅并飞走了,《小红帽》中女孩进入森林、遭遇野兽。这种对“从前”的回溯打破了线性时间顺序,是对“起源”的重演。但它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具有“浸没在黑暗力量中并被禁锢的特征”。因此这种想象性的重演必须且必然会“被一种断裂的行为所取代”:主人公踏上“探索”的旅程,并最终取得胜利。概言之,这种重演纯粹是以想象方式展开的,它通过回到童年、回到文化的开端来理解个体和集体的命运,但它有可能也是一种“迷失”,因此必须被“探索”的进步时间所取代——这正是利科的弗洛伊德研究隐含的关键论题。
2.“重新发现自己”意义上的重演。《奥德赛》在这里具有典范意义。主人公进行了一次空间旅行,而它又是以“返回原点”的形式结束的。因此这种旅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朝向故乡、朝向自己的旅行。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岛》中所写:“让伊萨卡常在你心中/抵达那里是你此行的目的/……/一路所得已经教你富甲四方。”⑤雷格:《诗歌的秘密花园:20世纪伟大诗人名作细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2页。主人公在旅途中遭受的命运是他必须克服的“启蒙的磨练”,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收获。因此利科指出,每个人都有“迷失自我”的风险,但当走出迷宫、找回家园,他也就成了一个新的存在者,“障碍现在意味着成长”。这种意义上的“重复”就不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一种重新发现和回归自己的“探索”式重复。
3.《忏悔录》自我反思的重演。这种对自身的重复不再以《奥德赛》式的空间旅行为中介,而是直接以一种纯粹的内部反省进行,具有更加本真的时间性意义。通过重演和剖析自己的过往,奥古斯丁创造了一整套叙事形式来讲述“成为他自己的运动”:一次“从外部到内部,从下面到上面”的螺旋运动。这种模式影响深远,卢梭的《忏悔录》讲述了“我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普鲁斯特的《时光重现》讲述了“马塞尔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它们本质上是“将现在与过去、现实与能在等同起来,主角就是(is)他所曾是(was)”。利科称这种反思模式是叙事重演的最高形式,它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命运”——它“在决心中完全恢复了此在因出生而被抛入的继承性能在”。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30-32.
这几种概念实际上是在情节与时间、叙事与经验相统一的意义上谈的。人被理解成一种在时间中延展的历史性存在者,那些过往之事为“主人公”建构起他被抛入其中的境遇,而“重演”正意味着主人公通过回到自己的过去,从中获得同一性、获得最本己的可能性,从而真正地理解自己。叙事在这里通过情节时间的各种模式以及它与行动时间的关系,为反思存在提供了重要契机。正如利科所说,“通过讲故事和写历史,我们为仍然混乱的、模糊的和无声的东西提供了‘形状’”。②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33.个人和共同体的命运由此得到揭示。需要指出的是,利科虽然反复强调历史性与当前的关系,但他显然并不认为过去是无法摆脱的阴影,审视过去毋宁说是为了理解当前的自己,然后更坚决地成为“新的存在者”——这正是“重演”概念的真正含义。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利科的语言和叙事研究的目标正在于揭示主体通过语言超越自身的努力。
总的来说,情节时间与时间经验在流俗意义上的确相互排斥,这正是叙事学和时间理论长久以来隐含的态度。但利科通过利用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资源,重新激活了情节、行动和时间概念本身具有的层级结构和丰富性,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更加动态而辩证的统一性。这样,情节时间就深刻地再现和重塑了鲜活的时间经验:一方面,前者以某种微缩模型的方式具象化了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等论著中将文学看作“实验室”;另一方面,前者直接介入了人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这使得文本世界和读者世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交融。文学不是封闭的,而是拥有重建世界的力量。“扩展”的痛苦因此通过叙事得到揭示和治疗,甚至这种扩展本身也不再是消极的分裂,它以一种生产性的、积极的方式促使此在通过时间来理解和建立其能在。就利科而言,通过“重演”各种理论资源,他为叙事理论赋予了存在论的方向,为时间理论或者说时间性存在问题夯筑了叙事理解的基础,时间与叙事因此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最终指向恢复并且加深“理解自己”的人文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