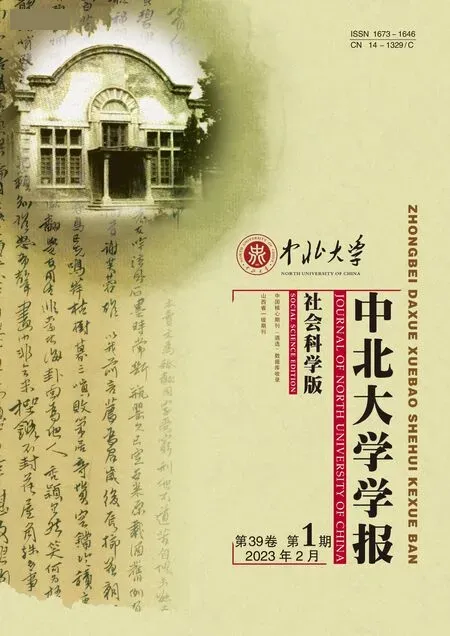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的地域因素及影响*
吴安妮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月泉吟社是宋季元初最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宋末浦江人吴渭(1228年-1290年),入元后不仕,退隐吴溪,延请宋遗民方凤(1241年-1322年)、谢翱(1249年-1295年)、吴思齐(1238年-1301年),创立月泉吟社,相与酬唱品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吴渭“[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其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1]1703。其征诗活动历时3个月:选题-解题-征诗-定期开榜-排名封赏-获奖者回送赏札。征诗期结束,共收到应征诗作2 735首,作者遍布浙、苏、闽、桂、赣各省,后择优选出280首佳品,编成《月泉吟社诗》一卷。
作为宋末元初规模最大的征诗活动,月泉吟社借助发达完善的地方邮驿系统,仿照“锁院取士”的征诗形式,破除了以往诗社地域限制、影响有限的弊端,汇聚了大量的南宋遗民诗人,将诗社活动推向了更加开放的格局。目前,学界对于月泉吟社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多是对月泉吟社的活动形式以及成员构成的研究,且大多数研究局限在遗民的政治性色彩上。然而,作为一个地方性的诗歌集体,月泉吟社孕育于婺州地区深厚的人文传统之中并以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所以,月泉吟社不仅仅是“遗民的”,它更是“地方的”。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分析月泉吟社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从地域文化角度考察此次文学活动蕴含的遗民文化情结及地域影响,以期对月泉吟社有更为清晰透彻的理解。
1 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元初众多诗社之中,月泉吟社以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成为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社之一。这一盛况的形成除了与方风、谢翱等人的声望有关外,也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
1.1 月泉吟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宋元易代,蒙古贵族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统一的大元王朝。在政治上,元朝政府奉行以民族压迫为主要内容、以重兵镇戍为主要手段的高压政策,对于汉人尤其是“南人”多加凌虐与剥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朝政府废除了传统士大夫的晋升之阶——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士人们实现阶级跨越的途径就此中断,他们从原来“四民之首”的座上宾突然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不幸者,社会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破国亡家的悲痛、民族歧视的屈辱、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功业幻梦的破灭,给儒士们带来了无穷的悲哀与积郁。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众多宋遗民离开都城,走向山林村社,希望借助山水田园宣泄内心的愤懑,寻求心灵的慰藉和找寻人生的价值。
如果说蒙元的高压统治以及士人的曲折命运是月泉吟社活动的心理积淀,那么,科举的废除恰好把知识分子从应试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文人们借助诗歌宣泄时代悲愤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怀着不与元廷合作的民族气节,遗民诗人们结社吟咏,寻求患难知己,借诗歌的形式抒发愤懑抑郁之情,企图通过群体的力量对抗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刘辰翁《程楚公诗序》中提到:“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无不为诗矣,所以为诗亦有同者乎?”[2]552在科举废除之后,士人们纷纷投入诗歌创作,借诗歌抒写个人情愫,寻求群体的依靠和精神的慰藉。在集体归属感的驱动下,听闻月泉吟社仿照科举取士之法征诗四方时,遗民们如暗室逢灯,绝渡逢舟,他们积极响应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宣泄内心的愤懑,创造新的精神归宿。
1.2 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的地域文化背景
月泉吟社之前的诗社活动局限于少部分人组成的小圈子之中,脱离现实社会。月泉吟社借征诗活动辐射浙江全省甚至福建、江西等周边省份,汇集了当时江南地区诸多的文人志士,成功破除了以往诗社地域限制、影响有限的弊端,实现了诗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而月泉吟社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婺州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婺州素有“小邹鲁”之美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浙东的这一块土地积淀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宋王朝南渡后,因靠近都城临安,以婺州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在人口、经济、文化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婺州地区更是成为了当时闻名一时的学术重镇。在蒙元进入之后,临安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很多南宋末期活动于此地的文人流落到附近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生活,婺州地区便成为了宋遗民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浦江地处婺州东北部,靠近南宋故都临安,山深谷多,风景秀美,拥有众多自然人文景观,如仙华山、浦阳江、月泉等。据《嘉靖浦江志略》记载,浦江“四围皆山,不通舟楫,商业贸易不发达,百姓勤耕苦读,性情朴茂质实,习俗醇厚”[3]26。浦江境内山峦“自严徽起伏而来,形势斗拔,仙华诸峰如瑞凤、如宝莲、如天马行空”[3]26。宋濂在《题张如心初修谱序后》中也曾盛赞浦江地区以“仙华为屏,大江为带,中横亘数十里,山盘纡周遭若城,洵天地间秀绝之区也”[4]2088。这些自然景观不仅为浦江文人汇聚交游、隐居著书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也为他们诗歌唱和提供了深厚的地域文化素材。
1.3 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的思想文化基础
婺州的秀山丽水不仅造就了当地醇厚的民风民俗,也催生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宋元以来婺州地区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其以忠孝贞洁著者有之,以其政事文学显者有之,层见叠出”[3]26。在宋南渡后,婺州文坛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涌现出了大批的文人名士。这一现象在婺州地方文人的诗文评论中也可见一斑:前有“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1138年-1181年)主张“重道不废文”,其诗歌创作情理交融又圆转流美,承接江西诗派的诗歌传统。后有月泉吟社的主事者方凤(1241年-1322年)开创婺州诗学,其诗学经由弟子吴莱、黄溍、柳贯等人继承并不断发展,再传而到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月泉吟社征诗四方,以杜甫的诗歌创为诗歌典范,力图拯救江湖诗作兴象浅窄、窘于边幅的弊病,为有元一代诗歌之先声。
从人文传统上看,浦江处于婺学为主的理学文化氛围之中。著名理学家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朱子的再传弟子何基、王柏、金履祥均来自于婺州地区。宋代以儒学为立国思想,读书人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抱负,夷夏之辨思想极为深刻。谢翱受聘于吴氏家塾,成立讲经社,与黄景昌等人讲《春秋》、论时事,促成了浦江一带文人的结合,也为浦江士人忠于故宋和坚守节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遗民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归属感更加强烈。在新旧思想文化的冲击之下,南宋遗民忠于故宋、视气节重于生命的精神,为月泉吟社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 月泉吟社征诗活动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月泉吟社此次征诗活动,聚集遗民力量,借诗歌的形式抒发亡国丧家的悲痛之情以及坚守气节、拒绝与元朝政权合作的心志,在团结、激励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保持民族气节方面起了显著作用。此次征诗活动不仅塑造了重视气节的地方文化形象,鼓励了婺州当地的诗歌人才,并且传承了遗民守志不阿的人格精神,对婺州一带的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
坚守气节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道德追求,忠君报国更是不变的价值取向。在浓厚的理学氛围影响下,月泉吟社诗人与当地的秀丽山水一同塑造了浦江重气节、守忠义的文化形象。月泉吟社的三位主事者方凤、谢翱、吴思齐同是入元不仕的故宋遗老。宋濂曾在《吴思齐传》中盛赞吴思齐等人的人格气节:“思齐与方凤、谢翱无月不游,游辄连日夜。或酒酣气郁时,每扶携望天末恸哭,至失声而后返。”[5]在集体归属感的驱动下,遗民诗人们携手纵情山水之间,以高风亮节相互鼓励,以诗文唱和宣泄心中愤懑,在同声相应中获得抗争的力量和精神的慰藉。
谢翱是宋末元初著名的爱国义士,他的文化血性和精神气概也深刻影响了浦江这片土地,为浦江的地方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诗风称:“南宋之末,文体悲弱,独谢翱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6]1413他对朝代更易的残酷现实有着深刻的感受。南宋灭亡后,谢翱曾在浙江、福建一带游历,以诗文会友,相互勉励。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冬,谢翱与吴思齐等人更是登桐庐西台绝顶哭祭文天祥,写下了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谢翱用哭祭的形式,表达了对文天祥的追念和英雄事业未成的遗憾,寄寓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客居浦江时,谢翱曾游览月泉并作《月泉游记》,记中借泉水之消长、月亮之盈亏以及仙华山之永恒不变,曲折地表达出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和忠于旧宋,信守旧志的人生信念。受聘于吴氏家族之后,谢翱以浦江为活动中心,阐释《春秋》大义,为当地士人树立了重气节、守忠义的榜样。在遗民文人的互动往来之中,忠义气节的力量逐渐渗透到浦江文化之中,为当地塑造了重视气节的文化形象。明清之际曾有大量遗民文士前往浦江凭吊谢翱,或以诗远吊谢翱。《光绪浦江县志稿》曾收录邑人朱兴悌的《观月泉书院怀古》一诗,诗云:“离骚读罢问苍旻,曾憇当年汐社人。燕北不归文相国,台西长恸宋遗民。冬青有树埋陵骨,晞发无家剩只身。魂到月泉仍俎豆,不将许剑委沉沦。”[7]
2.2 地方诗歌人才的激励
月泉吟社的三位主事者方凤、谢翱、吴思齐除了以气节不群为世人称颂外,三人均工于诗歌,在诗歌创作上也引领了婺州地区的创作风气。身为南宋遗老,三位诗人心存亡国之痛,意欲隐居山林,其诗多发亡国之痛,音调凄楚,寄慨遥深。黄溍在《翰林待制柳公墓表》曾评论:“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为古文歌诗,皆忧深思远,慷慨激烈,卓然出于流俗,清标雅韵,人所瞻慕。”[8]722在月泉吟社主事者的鼓励和影响下,浦江乃至婺州的地方诗歌人才不断涌现。以浦江月泉吟社为发源地,婺州一带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并于元明之际发展到鼎盛期。
朱琰《金华诗录序》云:“金华称小邹鲁,名贤辈出……至浦阳方韶卿与闽海谢皋羽,括苍吴子善为友,开风雅之宗,由是而黄晋卿、柳道传皆出其门,吴渊颖又其孙女夫,宋潜溪,戴九灵交相倚重,此金华诗学极盛之一会也。” “余谓金华之诗,起于义乌、盛于浦江、振于兰溪、承于东阳,而金华、永康、汤溪、武义应和于其间也。”[9]233清代吴伟业曾说:“浙水东文献,婺称极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华隐者方凤韶卿,与谢翱皋羽、吴思齐子善,賡和于残山剩水间,学者多从指授为文词。”[10]2770清代四库馆臣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着眼,看到了方凤所开之诗学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他们认为:“(吴)莱与黄溍、柳贯并受业于宋方凤,再传为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11]1442正是有如此绵延不断的乡学渊源,婺州文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地发展。
方凤是婺州诗学的开创者。宋濂在《浦阳人物记·方凤传》中称:“凤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发于咏歌,音调凄凉,深于古今之感。”[12]1485方凤曾受聘于吴氏家塾,著书讲学,元代的著名文士黄溍、柳贯、吴莱等皆出其门。其中,黄溍与柳贯二人为同乡挚友,且均以散文著称于世,当时文坛将两人并称为“黄柳”。黄溍与柳贯二人均是博学多通之士,在元代文坛产生重大的影响。黄、柳二人早期诗词创作受方凤影响极深。在目睹了宋元易代的种种残酷现实之后,方凤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避世隐居的倾向。受其影响,黄、柳二人早期的诗歌中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柳贯在“儿辈莫须多识字,只教食力事耕耘”(《元日漫题》)中流露的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与无奈,黄溍在“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风光已杜鹃”(《独立》)中展现的迷茫与伤感,与方凤的诗歌风格可谓一脉相承。
2.3 遗民人格精神的传承
元代婺州文人集团的领袖者黄溍曾在《送吴良贵诗序》中称:“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谊为人所尊师,后进之士争亲炙之。”[13]37在月泉吟社征诗四方的号召下,众多志节之士迅速汇集到婺州一带。吟社诗人的诗歌合集《月泉吟社诗》也与同时代的《谷音》《乐府补题》等共同掀起了遗民文学的创作高潮。月泉吟社也成为后代遗民争相效仿的榜样,缅怀故国、矢志守节成为了遗民诗人们创作的重点。在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气息影响之下,元明易代之际,婺州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联系紧密、阵容庞大的遗民诗人群体。
如果说师承关系是宋遗民与元遗民的传承纽带,那么以婺学为主的理学思想则是遗民传承的精神内核。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论: “婺州作家大多是理学家吕祖谦和朱熹的徒子徒孙,浓厚的理学风气对婺州作家的人格、生活方式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4]191在乡学渊源以及理学意识的牵引下,元明易代之际,婺州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联系紧密、阵容庞大的遗民诗人群体。著名文人戴良(1317年-1383年)正是元遗民中的代表人物。戴良,字叔能,自号九灵山人,婺州浦江人。戴良的一生与谢翱等宋遗民的生命历程几近重合。戴良是金华之学的直系继承人。他早年曾经跟随“浙东三先生”柳贯、黄溍、吴莱学习,继承了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坚守着儒家对于“先王之道”的守成与念念不忘,对忠孝、贞节等问题看得尤为重要。在元朝大厦将倾之时,他忠心耿耿、不曾动摇;在改朝换代之后,隐姓埋名,最后更是以自杀的方式殉元,至死不事二主。除戴良之外,元代婺州还出现了李序、金涓、叶仪等一批遗民文人。这一遗民诗人群体除因亲缘、乡缘、师缘、友缘等因缘而联系外, 其内部也形成了尚气节、重理学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
3 结 语
从“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到“空学成补天才却无度饥寒计”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以及科举入仕道路的中断在士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对南宋遗民而言,尽管田园可以抚慰心理的创伤,但破国亡家的现实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梦魇。没有南宋相对宽松、重视文化技能的社会环境,曾经的江湖诗人回归农耕,走向了山林村社。遗民诗人们在彼此交通声气的过程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遗民们不仅寻到了群体的依靠,而且通过征诗活动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虽然科举的废除阻断了士人的进阶之路,但是遗民们通过诗歌唱和,相互勉励,创造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在吟社征诗四方的号召之下,众多的遗民诗人借春日田园景象宣泄内心的愤懑,寻求精神的家园,在婺州的地方文化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民文人们矢志不渝、守志不阿的人格精神,更是为这片深受理学思想浸染的土地增加了生动的注脚。在他们的带动下,婺州士人掀起了诗文创作的高峰,一代代婺州文人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共同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婺州地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