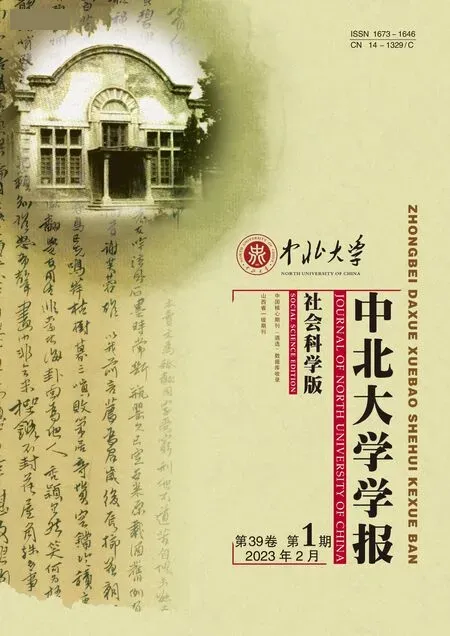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后与教会关系探析
——以拉戴贡德为例*
王秀红
(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太原 030619)
0 引 言
教俗关系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上半期,在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命题提出后,法兰克王国的教俗关系研究迅速升温。二战以后,随着女性研究的崛起,妇女与教会的关系又成为研究的新热点,目前已有不少论述。法兰克王国时期,王后频繁活跃于政治及教会事务,地位非常重要。不过,对于王后的角色和地位等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本文拟以墨洛温王朝拉戴贡德王后和普瓦提埃主教之间的恩怨为主要切入点,分析王后在政治及宗教领域的地位,以深化对这个时期教俗关系的认识。
1 拉戴贡德王后的宗教权威
拉戴贡德的宗教权威首先依赖于她的政治身份。拉戴贡德(Radegund,520年-587年)所处的时代是日耳曼蛮族诸王国建立和发展时期。此时,掠夺土地和财富是王国最直接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王室女性特别是寡居王后或公主常常作为王权合法继承人的中介,成为中世纪早期日耳曼男子合法获得她所在王国王位的一条捷径。拉戴贡德作为图林根公主(1)克洛维的母亲巴西娜曾是图林根王后,后逃至法兰克嫁给了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戚国淦先生指出,有的学者认为拉戴贡德所在的图林根在今天比利时东北一带,并非巴西娜所在的威悉河上游一带的图林根,但其居民可能来自后者。参见[法兰克]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二卷,九,注释一,第66页;十二,注释四,第69页。,成为战争的牺牲品。[1]164也是由于她的图林根公主身份,墨洛温分王国国王克洛塔尔一世(Clothar I,511年-558年为苏瓦松国王,558年-561年为法兰克诸王国唯一的国王)将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兰克。诗人弗图纳图斯称:“她忍受着来自她自己家族的迫害。”[2]71
首先,拉戴贡德经历了图林根王国内部的斗争。她的叔叔赫尔曼弗雷德杀死她的父亲之后,又联合当时法兰克分王国的国王、克洛蒂尔德的继子提奥德里克攻打拉戴贡德的另一位叔叔巴德里克,在其获胜后,没有信守“如果我们能设法杀掉他,我俩就平分他的王国”[1]164的诺言。因此,在531年左右,提奥德里克联合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克洛塔尔一起攻打图林根,并许诺分给他一份战利品。[2]167结果,法兰克人取得了胜利,克洛塔尔回家时“随身带走拉戴贡德作为他的那份战利品”[1]168。此后,拉戴贡德在克洛塔尔的皮卡迪阿瑟斯王室庄园上生活并接受教育,“她经常和别的孩子谈起她的愿望是有生之年成为一名殉教者。”[2]71
拉戴贡德之所以成为战利品被克洛塔尔带回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耳曼传统中认为,女性尤其是王室女性有着一定的预言功能。这一点可以在塔西佗的笔下得到证实,也可以从克洛维的母亲巴西娜的故事中窥见几分。这种预言功能又恰恰是法兰克墨洛温王室用来构建自身政治权威的重要元素。对于当时的罗马公教而言,它也需要与蛮族国王们合作,换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教会在适应日耳曼民族对婚姻和性的看法与做法”[3]161。二是拉戴贡德作为图林根公主,是该王国王权继承的中介。克洛塔尔将她带回自己的王国,是想日后以复仇为借口,合法吞并图林根,这从他后来不断征服并最终在550年杀死她的兄弟可以证实。
其次,拉戴贡德的宗教权威得益于她对宗教的虔诚。这种虔诚迎合了早期的墨洛温王室通过塑造自己的圣徒形象来巩固其统治的需求,从而获得了以国王克洛塔尔为首的法兰克墨洛温世俗王权的大力支持。拉戴贡德的苦难经历使她本能地向宗教虔诚靠拢,以求自保。格雷戈里将拉戴贡德的婶婶——赫尔曼弗雷德的王后阿玛拉贝格描述为“邪恶而又残忍的妇女”[1]164,进一步突出了拉戴贡德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她与她高贵的家人一起生活没多久,胜利的法兰克人野蛮地摧毁了这一地区,她像以色列人一样,动身离开她的家园。”[2]71早年的凄惨经历使得她对人世的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图林根战争更是成为她一生的阴影,这些都为她日后虔心于宗教生活埋下了伏笔。
拉戴贡德在克洛塔尔的王室庄园上生活了十多年,之后,克洛塔尔想娶她为妻,让她去苏瓦松做他的王后。拉戴贡德听说此事后,与几个同伴连夜经过贝拉查(Beralcha)逃出阿瑟斯。这暗示她虔信宗教,一心想做上帝的女仆,而不愿成为俗世国王的新娘。迫于生存,540年左右,拉戴贡德嫁给国王克洛塔尔,成为第二代墨洛温王后中的一员。虽然她答应做他的王后,但她仍虔信宗教,以致克洛塔尔抱怨自己娶的是修女而不是王后。[2]71-72
夜间,当她与她的王子就寝时,她请求起来并离开卧室去厕所。然后她在厕所旁披着一件毛斗篷俯伏在地祈祷,时间很长以致寒冷刺骨,只剩下心是暖的。[2]73
至此,拉戴贡德作为王室权威与宗教结合的桥梁已初现端倪。她出逃后经历了什么,史书无载,只知道她与克洛塔尔国王和解。她到苏瓦松成为他的王后,他对她的宗教虔诚只能抱怨却未能制止。后来,在克洛塔尔国王的安排下,由普瓦提埃教区主教平提乌斯和公爵奥斯特拉皮乌斯迅速完成了普瓦提埃圣十字修女院的修建。[2]89最终,拉戴贡德完成了世俗王后身份向宗教修女身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王和主教起了主要作用。
拉戴贡德依靠她的王后身份获得了宗教权威,这为她的政治权威的获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成就了她“王后-圣徒”的美名。当克洛塔尔在550年杀死拉戴贡德的兄弟时,她出逃并拒绝返回。“她离开这位国王径直去见努瓦永的圣梅达德”[2]75,经过一番斗争之后,这位努瓦永主教接纳她成为一名修女。有了主教的认可,拉戴贡德成功进入了教会的关系网。随后,去图尔的圣马丁墓前朝圣。大约 544年,在平提乌斯任普瓦提埃主教时期,她到达普瓦提埃。587年8月16日,格雷戈里到普瓦提埃出席她的葬礼。
像拉戴贡德这种政治策略指导下的婚姻,夫妻感情并不重要,而且极易被动卷入王国之间的血亲仇杀。在墨洛温时期,法兰克人四处征战、彼此内讧,贵族妇女被俘为人质或作为国王之妻而带来和平,但这种和平往往是短暂的,且大多以悲剧结束。这种由女性嫁接的邦国和平时刻提醒较弱的一方铭记她的母国所遭受的伤害,从而形成宫廷潜在的反对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拉戴贡德利用她自己的公主、王后身份获得了国王和努瓦永主教的支持,从而实现了其宗教身份的转变。她作为王室的宗教代表,在普瓦提埃修女院建立之后,宗教地位才得以巩固。
2 拉戴贡德与普瓦提埃主教的恩怨
拉戴贡德与普瓦提埃主教马罗韦乌斯的矛盾充分体现了当时王室崇拜与地方教会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冲突的导火索是马罗韦乌斯拒绝为拉戴贡德安置圣物,即拜占庭皇帝和皇后赠予拉戴贡德的圣十字残片。该残片可能是在4世纪下半叶耶路撒冷宗主教西里尔赠与君士坦丁的。
首先,冲突的根源要从普瓦提埃所处地理位置的政治归属谈起,或者说普瓦提埃政治归属变化直接导致了拉戴贡德与马罗韦乌斯对该地宗教权力的争夺。拉戴贡德与马罗韦乌斯之前的主教们关系尚且融洽,因为他们没有将她视作一种威胁。随着墨洛温各分王国对普瓦提埃的争夺与统治,拉戴贡德与地方教会的矛盾加剧,恩怨加深。普瓦提埃地处法兰克西南部的阿奎丹地区,归波尔多教省管辖。当时,真正有实权的大主教来自波尔多、科隆和图尔三大地区。
在克洛维之子克洛塔尔一世时期,拉戴贡德离开她的丈夫克洛塔尔,最终选定在普瓦提埃建修女院,当时的普瓦提埃地方主教对此也给予了积极支持。“拉戴贡德拒绝了俗世虚假的甜言蜜语,欣喜地进入了这所修女院。”[2]88-89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称:“在国王克洛塔尔时期,圣拉戴贡德和她的共同体成员都服从于主教们。”[1]530-531根据格雷戈里的记载,第一任主教平提乌斯是由克洛塔尔任命的;克洛塔尔也安排忠诚于他的公爵奥斯特拉皮乌斯作为平提乌斯的继任者。“在克洛塔尔统治期间,公爵奥斯特拉皮乌斯被接纳为教士,后来他被任命为普瓦提埃教区的尚托索管区主教。”[1]214564年,圣平提乌斯死后,由奥斯特拉皮乌斯继任普瓦提埃教区主教一职本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561年,克洛塔尔一世死后,普瓦提埃由他的儿子查理贝特管辖。根据查理贝特的命令,由当时的圣希拉里修道院院长帕森提乌斯继任普瓦提埃主教职位。[1]214-215换言之,由于克洛塔尔的死导致了普瓦提埃管辖权的转移,原定的支持拉戴贡德的主教候选人未能顺利继任。而此时的拉戴贡德已经在普瓦提埃居住了17年,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导致她与圣希拉里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拉戴贡德王后虽然代表王室权威,但是又借助宗教权威实现王室女性的政治参与。她拒绝与国王克洛塔尔复婚,拒绝国王希尔佩里克要求他的女儿巴西娜(希尔佩里克与奥多韦拉所生)还俗的要求。(2)580年左右,巴西娜被安置在普瓦提埃修道院;584年,希尔佩里克打算将她送到西班牙,遭到拉戴贡德的拒绝。她说:“一个已经献身给基督的少女又回到尘世的享乐中去,这是不适宜的。”[2]364-365 这位巴西娜也是后来的普瓦提埃反叛事件的领导者之一。格雷戈里在其作品中只字未提拉戴贡德在世时圣希拉里的修道院长和修士们对她的修女院的态度。安置圣十字残片和为拉戴贡德举行葬礼这两个重大场合,也没有提及圣希拉里的修道院长和任何修士参与。这样一个小小的普瓦提埃城,如果两处圣所没有什么世仇的话,怎么可能互不往来?然而,我们还发现格雷戈里记载了一个片段,那就是拉戴贡德修女院里的女隐士从墙上跳下去,逃到圣希拉里教堂。[1]532
国王查理贝特和他的父亲克洛塔尔一世支持的普瓦提埃主教人选都出自圣希拉里修道院。当我们继续追踪格雷戈里的记载时,发现唯一一次提及的圣希拉里修道院院长是波尔卡里乌斯,他是马罗韦乌斯派去拜见波尔多主教等人的,要求他们在给予修女们教籍以后,准许他前去向她们当面解释。[1]538-539德国学者沙因贝利特认为,波尔卡里乌斯之所以同意充当谈判者,是因为他害怕中断了宗教生活而亵渎教堂。[5]
判决巴西娜等普瓦提埃圣十字修女院修女反叛时,国王希尔德贝特派使臣去见国王贡特拉姆,并提议两个王国的主教们召开宗教会议。希尔德贝特派出的人员有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科隆主教埃布雷吉赛尔、普瓦提埃主教马罗韦乌斯;贡特拉姆派出的是波尔多教省主教贡德吉赛尔。[1]568-570在格雷戈里的墨洛温王朝谱系中,592年,贡特拉姆去世后,勃艮第王国由希尔德贝特接管。也就是说,592年之前,马罗韦乌斯所在的普瓦提埃在世俗上受国王希尔德贝特的管辖,在宗教上属贡特拉姆王国的波尔多主教管辖。当时,墨洛温三个分王国中,希尔佩里克的王后弗雷德贡德和她的儿子克洛塔尔二世处于三方纷争中的劣势,贡特拉姆和希尔德贝特两位国王成为普瓦提埃的主要争夺者。此时的拉戴贡德为了在世俗纷争中确保自己的宗教威望,采用与世隔绝的凯撒利乌斯修道会规。在采用该会规之时,拉戴贡德很可能已经与周围主教们达成协议,如果有修女离开修女院,她们将被永远革除教藉。因为,512年-534年的凯撒利乌斯修女会规中规定:
修女院的许多事情似乎与修道院不同,所以我们从中选出几条,年长者和年幼者应遵照此会规生活,努力在精神上履行她们认为特别适合她们性别的事情。这些规训适应你们的圣灵:
如果一个离开她父母的女孩希望弃绝俗世,进入神圣的羊栏(即修女院),那么,在上帝的帮助下,她可以免受精神迫害(the jaws of spiritual wolves),但至死都不准离开修女院,甚至不能再进入(修女院之外的)教堂,即便她能望见该教堂之门。[4]184
阿尔勒的修女院院长凯撒利亚与拉戴贡德一直有信件往来,她曾经告诫拉戴贡德“不要允许不识字的人进入修女院”[5]39,“如果你希望守卫自己的贞洁就尽量不要暴露在男性面前;如果你摆脱不了男人,你就不能战胜欲望”[6]147。
我们看到即便在拉戴贡德的葬礼上,她的修女院的修女们也只是站在围墙上观望。[2]103在七位主教写给拉戴贡德的书信中指出,一名修女离开修女院犹如“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她将遭受革除教籍的沉重打击。[1]526-529589年,普瓦提埃反叛的修女们去找国王,途中没有一个人供给她们粮食,这些都说明拉戴贡德所建的这所修女院实际上相当于普瓦提埃的一块飞地。王后拉戴贡德试图凭借这块飞地,利用自己的关系对普瓦提埃甚至整个墨洛温王国的信仰产生影响,体现的是一种王者之气。
王后拉戴贡德所建的圣十字修女院在她的各种运作下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地方信徒,对圣希拉里(3)5世纪后期,在普瓦提埃城郊建立了圣希拉里修道院。圣希拉里在出任普瓦提埃主教期间捍卫罗马公教,严厉抨击阿里乌信仰,他死后,普瓦提埃民众为了治病去他的墓地朝圣。当时,圣希拉里崇拜常常与图尔的圣马丁崇拜联系在一起。崇拜的中心地位造成了明显的威胁。普瓦提埃主教也发现这位王后威胁到他的地方利益,动摇了圣希拉里崇拜的中心地位。正如汤普逊所言:“在蛮族时代,农村教会大多落到领主阶层的控制之下。他(领主)的领地有着它的地方教会。这种地方教会,是领主贵族的一个赚钱机关。”[7]123在这种情况下,主教和地方贵族一样成为有钱人,并且一样接受小农所抵押的土地,取消了他们的赎回权。
查理贝特死后,他的兄弟西吉贝特和希尔佩里克展开了对普瓦提埃的争夺。希尔佩里克入侵图尔和普瓦提埃,根据协议这两个地方归属于西吉贝特。[1]241575年,西吉贝特被谋杀,他的遗孀布伦希尔德下嫁给希尔佩里克之子墨洛维,希尔佩里克追击墨洛维时经过普瓦提埃;575年-580年,公爵贡特拉姆•博索将他的女儿们带到普瓦提埃城。当时的普瓦提埃归于西吉贝特之子希尔德贝特,国王希尔佩里克再次攻击普瓦提埃,他的士兵赶跑了国王希尔德贝特,将普瓦提埃伯爵恩诺迪乌斯押解到他的面前。贡特拉姆·博索将他的女儿们留在圣希拉里教堂又回到国王希尔德贝特那里。[1]289希尔佩里克与西吉贝特父子对普瓦提埃管辖权的争夺,迫使拉戴贡德缓和与主教马罗韦乌斯之间的关系。
之后的一些年,拉戴贡德有好几次想获得马罗韦乌斯的帮助,但是一无所获。拉戴贡德和她任命的圣十字修女院院长阿格内斯只好投靠阿尔勒。阿格內斯的任职仪式也是由巴黎主教圣日耳曼努斯主持的。在那里,她们接受了圣凯撒利乌斯和神圣的凯撒利亚会规。她们将自己置于西吉贝特父子的保护之下,因为她们没有引起主教的任何兴趣和支持,虽然他本该成为她们的牧人。因此,这种不和日渐恶化。
587年,拉戴贡德死后,马罗韦乌斯拒绝主持她的葬礼仪式。为此,图尔的格雷戈里远道而来为她举行葬礼。格雷戈里本人在《奇迹集》中关于该次葬礼有详细记载,他表明他最初不愿意介入拉戴贡德的葬礼,但是面对大众的请求他答应了。他在悼词中写道:
神圣的拉戴贡德,我在记载殉教者之书的开头就提到了她,她在完成她俗世的事务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收到她的死讯,我去了她所建立的普瓦提埃修女院。我发现她躺在棺材里,她的圣容如此明亮以致超过百合和玫瑰之美。站在棺材周围的是一大群修女,约有200人,她们因拉戴贡德的布道和养育而皈依这种神圣生活。就社会地位而言,她们不仅出身元老,一些人甚至出身王室;现在她们因循自己虔信的修道会规而繁荣。她们站在那里哭诉着说:神圣的母亲,你怎么抛下我们这些孤儿?你将我们这些弃儿托付给谁?我们已经离开我们的父母、丢弃我们的财产和离开我们的家园执意追随你。[8]90-91
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安魂弥撒后的封墓仪式留给马罗韦乌斯,希望他能出席。但是,马罗韦乌斯始终没有出现。他描述,当葬礼队伍通过时,修女们全挤到城垛和城楼上的窗口观望。葬礼结束后,回到修女院,修女院院长和修女们带格雷戈里参观了拉戴贡德读书和祈祷的地方。修女院院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出示了拉戴贡德曾经跪过的垫子、读过的书和用过的纺车。宝多妮维雅也详细描写了拉戴贡德的入殓仪式,“他们推迟了三天等待这位主教马罗韦乌斯的到来,但是他没有来,前面提及的使徒格雷戈里相信‘伟大的爱使人无畏’,他将她带到圣玛丽的长方形大教堂内,将她安葬于此”[2]103。
拉戴贡德死后,修女院院长阿格內斯再次乞求马罗韦乌将拉戴贡德的修女院置于他的关怀之下。马罗韦乌斯前往国王希尔德贝特二世那里,并获得了一份准予他依例管辖该修女院的证书,其权限类似于他对普瓦提埃教区的其余修道院的管辖权。[2]529-531在处理拉戴贡德和马罗韦乌斯之间的矛盾时,我们看到格雷戈里的普遍原则遭受了挑战。他所强调的教区主教的权威是延续已久的社会秩序准则,充任该职位的全部是男性。按此种社会秩序,即便是拉戴贡德这样的女圣徒也理所当然应该服从于教区主教的管辖。然而,现在拉戴贡德的普瓦提埃圣十字修女院明显是一块飞地。此时,格雷戈里将这种纠纷归结为马罗韦乌斯的傲慢无礼,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现实困境,有效地维护了拉戴贡德的声望。这其实也侧面反映了格雷戈里的个人忠诚倾向,因为拉戴贡德也是他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其次,教会与修道院的管辖归属成为王室与地方教会政治利益冲突的焦点。墨洛温早期,修道院与教会关系尚不明确,因为修道院大多是私人建立的,理论上属于私家财产,管理权属于私人。最初,普瓦提埃主教们也并未将拉戴贡德的到来当作一种威胁,因为之前也有别的王室妇女寡居后隐退至其他城市并成为圣徒崇拜的保护人,对教会的政治权力并没有威胁。然而,拉戴贡德到达普瓦提埃后,他们发现她有着强大的教俗关系网,不仅与巴黎主教日耳曼努斯有密切的来往,还充分利用王室的医疗资源,在她的修女院为人治病,帮助穷人,引来了众多的崇拜者。从589年普瓦提埃圣十字修女院的部分修女对新的修女院院长柳博韦拉的控诉中,我们知道御医雷奥瓦利斯曾作为外科医生与她一起为人治病。[1]570-571也就是说,她在普瓦提埃的各种宗教活动一直受到国王和其他教区(如巴黎、图尔)主教的支持,她在世时制造的各种“奇迹”吸引了大量的信徒,有时甚至可以绕开普瓦提埃主教直接与其他地方主教往来。在一封致拉戴贡德的信中,明显受她请求(包括图尔的尤夫罗尼乌斯和巴黎的日耳曼努斯在内)的七位主教(4)另外五位主教是鲁昂的普雷特克斯塔图斯、南特的费里克斯(Felix)、昂热的多米提亚努斯(Domitianus)、雷恩的维克托里乌斯(Victorius)和勒芒的多姆诺卢斯(Domnolus)。称她为第二位马丁,很显然,这七位主教都无权管理普瓦提埃。为此,普瓦提埃的主教帕森提乌斯感到自己的主权地位受到威胁而很快与拉戴贡德产生冲突,并造就了马罗韦乌斯继任主教的局面。他们对她的宗教活动不再给予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拉戴贡德试图通过自己强大的权力关系网,收集大量圣物来提高圣克罗伊斯修女院的声望,以抗衡圣希拉里作为普瓦提埃崇拜中心的地位。569年,拉戴贡德派遣教士到东方,他们身上带着西吉贝特国王的书信登上旅程,并且带回了一些圣物。在安置这些圣物问题上,拉戴贡德王后和主教马罗韦乌斯发生了分歧。也许是因为拉戴贡德派人出发寻求圣物之前没有预先告知这位教区主教,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寻回的圣物威胁到普瓦提埃圣希拉里的崇拜,而圣希拉里是马罗韦乌斯的先辈。[11]31-36罗维森认为,更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将圣物安置在圣十字修女院,教区居民接近圣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9]193,前面已经讲过拉戴贡德的圣十字修女院不对外开放。因为格雷戈里笔下的马罗韦乌斯是一位了解教区居民需要的主教,他曾请求国王希尔德贝特派人前往制定新税册,解除穷人和病弱者的负担。[1]515-517当国王贡特拉姆的军队到达普瓦提埃时,马罗韦乌斯打破教堂里一盏金制的圣杯,熔铸成钱,赎回了他自己和民众。[1]406-407但笔者认为,马罗韦乌斯拒绝为拉戴贡德主持安置圣十字架残木块的原因主要是她威胁到他在普瓦提埃地区的主教权威,因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这些圣物运到后,这位王后便要求主教马罗韦乌斯以全部应有的尊荣和吟唱圣诗的隆重礼仪来安置它们。他断然拒绝这样做,转而骑马去参观他的一处乡间地产。然后,这位王后再次写信给西吉贝特,恳求他命令他的一位主教按照她的誓愿以全部应有尊荣将这些圣物安置在修女院内。西吉贝特责成图尔主教圣尤夫罗尼乌斯(Eufronius)完成拉戴贡德所要求之事。尤夫罗尼乌斯与他手下的教士来到普瓦提埃。马罗韦乌斯故意离去,但是尤夫罗尼乌斯在圣诗的吟诵声中,在烛光闪烁和香烟氤氲的排场下将该圣物安置在修道院内。[1]530
布雷南认为,马罗韦乌斯拒不主持这次圣物的安置仪式是要保持普瓦提埃城外的圣希拉里长方形大教堂作为崇拜中心。只要他不出席,普瓦提埃城的崇拜中心就不会从圣希拉里转到拉戴贡德的修女院。[10]中世纪史学家范达姆称,拉戴贡德在普瓦提埃的活动是“6世纪中期圣希拉里崇拜和普瓦提埃主教们突然面临的一个新挑战”[11]30。这所新建的修女院过硬的政治后台不仅威胁到圣希拉里的中心地位,而且还影响着教会与王权的合作。
3 结 语
纵观拉戴贡德与马罗韦乌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拉戴贡德作为王后获得了整个高卢教区主教们的广泛支持,但是一直得不到马罗韦乌斯的认可,其中的症结主要是墨洛温三个分王国在普瓦提埃地区的政治利益冲突以及墨洛温王国对地方的治理方式,即国王们不仅安插自己的世俗官员,而且还影响地方主教的选举,导致当地主教缺乏安全感。二是关于拉戴贡德修女院和圣希拉里修道院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回看拉戴贡德和马罗韦乌斯的恩怨时,发现这其实是王室圣徒崇拜和圣希拉里崇拜中心之间在普瓦提埃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是王室与地方的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