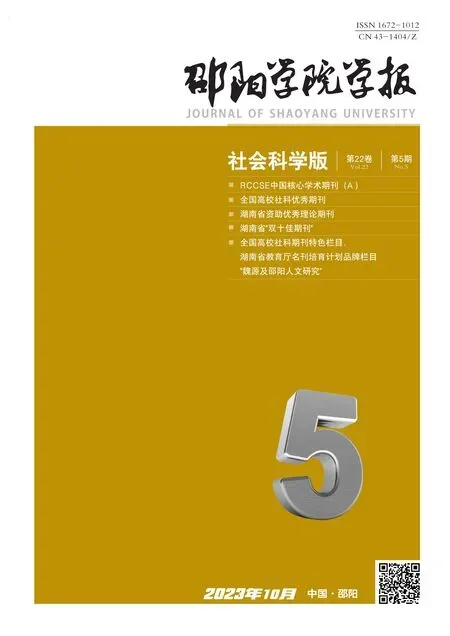儒家身体观与当代文学身体写作的义理边界
陈红玲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儒家身体观内蕴丰富。杨儒宾指出,儒家的身体观包含了意识的身体、形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是意识的主体、形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的综摄,而集中于身体主体之中;当我们一说起儒家意义上的身体,这四种因素就会同时出现,形成有机的共同体[1]9。杨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对儒家身体观的一种综合。其实先秦儒家就已提出了与身体相关的心、性、情、欲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关于身体观的基本结构图式,并为此后儒家身体观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对身体问题的种种探索,可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重要理论思考。20世纪90年代,学界兴起了一股身体写作的热潮,这种热潮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之中。应当看到,在身体写作过程中,作品多有“欲望”或“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书写倾向,而哲学理性并不多见,儒家身体观的相关述说常被置于话题之外。如何将儒家视野中的身体观与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结合起来,体现文学创作的义理边界,并展现儒家身体观的文学意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话题。
一、先秦儒家身体观的结构图式
在儒家视野中,“身”首先作为躯体性存在而受到重视。《周易·系辞下传》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257这里“身”与“物”相应,是名词性称谓,“近身”与“远物”成为伏羲氏探究神明之德、相察万物之情的重要参照,而“身”则成为由近及远考察事物的起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2]284。这是将八卦具体地类比为人身之象,再由身及物,由此及彼地推出事物的形成和发展。
较之《易传》,《论语》中出现“身”的次数明显增加。有学者根据《论语》使用“身”的场合和语境,将之归纳为四种含义:作“身体”解,如“杀身以成仁”;作“行为”“活动”解,如“吾日三省吾身”;作“操守”“自我”解,如“其身正,不令而行”;作“终生”“一生”解,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3]79-84。从物质性角度来指称身的含义,是《论语》对身的基本解释。即便由此生发出来的“行动”“终生”之意,也与物质性的身体密切相关。“身”的概念已内含操守、道德等意涵,使得“身”的多义性有所扩展。“身”的这种含义,与人的社会生活交往的扩展有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自身对自我有道德的期待,也意图从他人那里得到道德的肯定,这种期待或肯定通过主体自我的道德行为而得以实现。从这一角度看,《论语》中的“身”概念,既具有物质性特征,也具有社会和道德的特征。
《孟子》中的“身”,“形躯之身”仍是其基本含义,如“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4]789,但又有所变化。孟子特别重视对“四体”与“心官”的思考。“四体”之说在孟子之前已有之,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5]724之语。到孟子这里,“体”则有“大体”“小体”之分,所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4]792。孟子以为,耳目和心虽都为物质形体的一部分,但“大体”之心以礼义为思,不使耳目为利欲所蔽,故能成就“大人”之位,而“小体”之耳目纵恣情欲,不思礼义而为利欲所蔽,则终为小人。孟子从形躯之身所具的耳、目、心等出发,指出耳目和心在官能上的根本区别,由身之“大体”“小体”推导出人的德性地位上的大人、小人之分,可知孟子思考“身”的重点已逐渐转向对人的道德追求的关注,人之身兼具形躯之体与德性之体的双重含义。孟子进而指出,在形躯之体与德性之体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以德性之体为重,即他所说的“舍生取义”,由此可见孟子论身的深奥。
《荀子》论身和孔孟有诸多相似之处,如细究,孟子之“身”更多强调的是“自己”之意,而荀子更突出“身”的“行动”义[6]。除此,荀子在其身体思想中突出“情”字,并将之和心、性、欲合并阐发。荀子指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7]447表面上看,荀子说的性、情、欲有层次的划分,实际上都是从“欲”的角度进行说教。荀子说:“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7]461表明欲就是性,是“性之所具”,用的是“以欲说性”的手法。徐复观就此点出:“荀子虽然在概念上把性、情、欲三者加以界定,但在事实上,性、情、欲,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而荀子性论的特色,正在于以欲为性。”[8]205荀子主张性恶,克治性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后天的行为实践加以纠偏,而这与身有关。荀子顺此提出“美身”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7]11所谓“美身”,意指学人经过真切的身体修养实践,纠正不合理的欲望,使之归于社会基本道德法则之内,以德润身,以身指行,从而起到身体示范的作用。“美身”效果的实现,表明心对身体有主宰作用,是心对情欲的克制。因此,荀子通过“身—心—性—情—欲”的多层解说,在继承前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身体观作了更多发挥,可视为先秦儒家身体观之集成。
二、儒家身体观的展开
先秦儒家身体观基本结构图式的确立,为后世儒家身体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先秦儒家“身—心—性—情—欲”的结构图式下,后世儒家身体观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即“本—道”之变、性情之论、理欲之辨。
(一)“本—道”之变中的“身”
“修身”之说在《孟子》《大学》《荀子》等儒家经典中早已有之。如《荀子》专门有《修身》篇,中有“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7]17的语句,表明以善作为修身的最高标准,修身的手段重外在的礼法。至朱熹,他在诠释《大学》章句时,给予“修身”另一种解释:“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9]4意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助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展开。如此一来,“修身”就在整个条目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成为内圣外王的关键,“身”实际上也成为有待改造、有待完善的对象。这在他的修身论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10]631朱熹以为,要达到修身的目的,需通过格物穷理的方式才可实现,也就是他所说的“深探其本”。朱熹这种“修身为本”的观点在宋儒中具有典型性。
明儒王艮写有《明哲保身论》[11]29-30。按照他的逻辑,知保身则必爱自身如宝,能爱自身则不敢不爱人、不敬人;因自己能爱人敬人,他人会持同样立场,也会爱我敬我,如此就能做到“吾身保”。用这种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既能保身,也能保家、保国、保天下。王艮认为这就是“仁”,是“万物一体之道”。这种“以身为本”的观点,意味着“身”成为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成为衡量天地万物的标准和依据。更重要的是,王艮将“身”与儒家之道联系起来:“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11]37在他看来,身与道原是一样,没有区别;又因为道善就是性善,而性又为至善,这样身就表现为至善,身从而取得了本体地位。明代另一学者李材也认为“身为本”:“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当先者也。”[12]682把身当成事物的本始,实际上是把“身”当作善的存在。由至善之身出发,人的生活行为也自能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
可以发现,身体观发展到明代,已由宋代的“以身为本”演绎出“以身为道”的路向,由此前的物质意义上的形躯之身演绎为哲学意义上的道德本体之身。这种观点的出现与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有关。这也意味着儒家哲学中的身体观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本体的意义,它实际上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儒家身体观是附着在人性论、天理说、良知观之中,成为解说人性、天理或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潮流而存在。
(二)性情之论中的“身”
与身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性和情。人有性情,始成为人,因而论身就当论性和情。前文提到,荀子大量使用“情”的称谓,将情等同于欲,以此论证“人之性恶”。在此之前的孔子关注的重点在仁,没有将身与性、情合并讨论。孟子以心说性,他所指称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实就是情,性与情在孟子这里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尽管已有性、情之说,但关于性、情的理论说明仍是粗糙模糊的,如此便不能明辨儒家主流所强调的性善与现实人生中的恶的问题。
至韩愈,则将性、情相对而言,提出性、情“三品说”。韩愈认为性与生俱来,情是接于物而生。其中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为善,生来具有仁礼信义智五德;中品五德不完整,性可善可恶;下品五德都缺失,其性为恶。与性三品相应,韩愈认为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人自身能将七情控制适中,为上品之情;表达情感“过”或“不及”,但尚能“合其中”,为中品之情;凡任情而行,不加约束,则是下品之情[13]122。韩愈性、情“三品说”尽管意在排斥老佛之说的影响,但关于性情的关系在他的带动下就显出了另外的含义。从身体观而言,“三品说”体现了个体在传达性情过程中的差异性。换言之,性虽具有普遍性,但落实到个体,情的表现却是不一。李翱就此进一步提出了“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性无不善”,而“情本邪也,妄也”,情对性具有迷惑性,主张灭情复性[14]280-281。韩、李关于性、情有分的论述,是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拓展。置于身体观的意域中,其使人们认识到人作为肉体性存在具有复杂而多元的一面,身体成为研究性情关系的重要载体。当然,通过研究性情,关于身体的认识也逐步丰富,人们开始注重从心灵、精神的角度来看待身体的存在。同时,这种性情观也为宋代“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提出打开了理论窗口。
“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由北宋关学学者张载提出。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15]280-281“形而后”的“形”即形体,也就是身体,人之肉身从天地中来,每个人都是如此。在人的躯体形成之后,现实中的人就有了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之分。按照张载的观点,人先天为善,但人作为肉体性存在,因为气秉的不同,因而有善恶、材质高下的区分。需指出的是,作为万物之气的“气”有清浊、幽明、厚薄、偏正的差异,因此人的身体在由来上尽管都一样,但在现实中却有种种不同人性的出现。因此张载又说:“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11]22人的身体有耳目口鼻之欲,但不应放纵身体之欲。张载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意在解决人性中的善恶问题,对这一问题又是通过对人身之欲的约束来解决的。
张载“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给二程和朱熹很大影响。程颢所说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16]81便是张载之说的继续。特别是朱熹,对张载“气质之性”尤为肯定。因为此前儒家所论人性,都只着眼于仁义礼智之善,故而对世间的善恶、贤愚、人物、人禽之别等人生种种问题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朱熹运用张载所提“气质之性”解释世间现象,也为我们从“气”的角度理解儒家身体观呈现了新视角。
张载和朱熹肯定气质之性,是因为气对人之生成具有原初意义。吕思勉在谈到张载的气论时指出:“其论人,则原与天然界为一物。盖宇宙之间,以物质言,则惟有所谓气,人固此气之所成。以性情言,则气之可得而言者,惟有所谓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而此性即人之性也。故人也者,以物质言,以精神言,皆与自然是一非二也。”[17]70人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性情,又与气的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相匹配。从这个角度而言,张载的气论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生成论的色彩。程朱的气质之性说由张载而来,吕先生的这种说法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程朱之说。因此,在张载、朱熹的身体观中,他们不是单一地谈论人的性、情或气,而是将三者合而言之。因此,儒家身体观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性—气—情”的架构形式,身体自身包含的复杂属性,在这种性情之辨中可以看出其端倪。
(三)理欲之辨中的“身”
在“身—心—性—理—欲”关系结构中,还涉及理欲关系的处理。先秦儒家在性与欲的关系问题上,认为二者并非对立。他们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时,主张控制过多的欲望以伸张人的道德理性。
随着天理观的形成,理欲问题在宋儒这里出现了某种对立。朱熹指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18]167从德性层次看,“天理”就是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需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一谈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便以为是去掉人的一切欲望,其实并非如此。在朱熹的思想构成中,“人欲”并不是指人的一切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去除的是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身体冲动。朱熹所说的“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19]751,以及“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19]771等说法,表明朱熹是正面看待人的正常身体需求的。因此,朱熹的理欲观,既认为“天理人欲常相对”[18]167,也主张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纲”[20]2142,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一分为二”。
尽管朱熹无意将理欲完全对立,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隐含着两者走向对立的可能。王阳明就有“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21]8的质疑和呐喊。在王阳明看来,天理人欲没有主次之分,天理杂以人伪就是人欲,人伪得以消除便是天理,人伪消除之后的主体之身也就具有道德的意义。王阳明“天理人欲不并立”的看法,在晚明学界得到诸多响应。诸如颜钧所言“只从情耳”[12]703,何心隐“君子性而性乎命者,乘乎其欲之御于命也”[22]40,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23]40等观点,实际上已将人的身体欲望等同于道德伦理,这是身体观在晚明的另一种表现。即便如此,以当今视角而论,他们所说的“情”之种种表现,实际上仍是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表现,并没有超越儒家伦理之外。
明清之际至清中后期,在肯定天理的同时,情欲亦取得了与天理同等的地位。如戴震,认为“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24]754,指出了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他甚至还指出任何事物的完成,都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得到适当满足的过程。这就由个体之身扩展到社会之身,从而具有普遍的意义。由此也可进一步看出,人之身具有社会属性,对个体情欲所持的态度立场和处理方式,会产生超出个体之外的社会影响。因而如何对待人之情欲,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性的问题,涉及社会的回响和模仿。
三、儒家身体观对当代文学身体写作义理边界的限定
文学作品在展现人事、社会的过程中,少不了人的活动,当然会涉及人的身体。身体写作最早由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他们的观点是否适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已经在学界和社会引发讨论。从儒家身体观而言,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应当遵循其中设定的、具有正面导向作用的义理边界规定,即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范围内从事写作活动。
(一)当代文学身体写作不能脱离儒家身体观的历史脉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系统性的文学评论著作,它既是对齐梁以前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总结,也是此后从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理论借鉴和评价依据。因此,以它来说明儒家身体观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也就具有典型意义。需指出的是,《文心雕龙》含有以佛道观点来论文体的成分,然其立足点仍是儒家立场,五经是刘勰眼中文章写作的标准,设立《宗经》的主要用意也在这里。
《文心雕龙》剖析文体,常以人体为喻,如《辨骚》篇“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25]47,《附会》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25]650,《序志》篇“轻采毛发,深极骨髓”[25]727等。这也就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身体隐喻”。以身体来隐喻文体,其中当有可通之处,即儒家身体观可与文学写作形成必要关联。徐复观就此指出:“这种由活的人体形相之美而引起文学形相之美的自觉,为了解我国文学批评的一大关键,也为了解中国艺术的一大关键。”[26]27那么,儒家身体观中的身、心、性、情、欲之论是如何在《文心雕龙》中得到落实的呢?《风骨》篇指出:“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25]513“风骨”是对作品外在风貌的一种比喻,这种比喻与“风骨”最初用于对人的外在形体的品评有关。当然,品评人物不仅着意于外在形体面貌,更强调通过形体面貌而体现出来的气度精神,文章之风骨便也含有这种意思。因此,风骨之形体在这里便兼具物质躯壳和精神气度之意。《文心雕龙》也时常以身体之耳目、肌肤、骨髓等构成部位来代指整个身体,以反映身体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论心方面,《文心雕龙》指“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25]725,认为写作文章的主要目的在“树德建言”。这样,心的物质观念被淡化,而其道德文化的一面则被凸显出来,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心敏则理无不达”[25]715。情在文章中亦有其独特作用,刘勰用“情者,文之经”[25]538对之加以概括;而情的发出显然在于身,故刘勰又有“五情发而为辞章”[25]537的话语。当然,在所发情性中,有合乎文则的,也有不合乎人之本性的,不合乎者就是欲,《文心雕龙》就此谈道:“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25]254认为枚乘《七发》是以嗜欲之害来劝诫富家子弟。因此,在情与欲之间,《文心雕龙》强调义对欲的宰制性:“《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25]393刘勰以《丹书》之语警醒为文当以义为先,消泯嗜欲,才能达到崇其德的文学目的。因此,对于文章思想主旨的阐发,《文心雕龙》特别提到:“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25]328儒家之理就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无论何种文体,身体写作要有一个义理核心,这在古代如此,当代身体写作也自如此。
《文心雕龙》关于身、心、性、情、欲的论述在基本理路上与早期先秦儒家身体观有相似之处。它的突出特色在于,将儒家之所谓身体,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解释各种文学现象。这也表明,身体观不仅体现在哲学领域,也可以用于文学阵地。《文心雕龙》的身体隐喻说,也给后世儒家哲学提供了有益思考。如韩愈认为情接于物而生,这种观点就与《文心雕龙》的物感说相吻合;以理御欲、心与理合一的观点在宋以后被广泛提及,除了儒家哲学本身的发展外,也与《文心雕龙》的说法有着一定关联。当代文学开展创作活动和文艺批评,《文心雕龙》是重要参考依据,其所包含的身体隐喻手法,既吸收了先秦儒家身体观的思想成分,对后世儒家身体观的展开也有积极作用,从而融入儒家身体观的历史脉络之中。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应当秉承《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论观点,与儒家身体观的历史脉络相对接,确立时代核心主题,反映大众心声。
(二)当代文学身体写作应在“身—心—性—理—欲”的结构图式中展开
儒家身体观表明,“身—心—性—理—欲”结构图式是各要素之间互为关联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身体的行为实际上受到性理的约束,欲的表现也是在性理约束下的合理结果,不能有逾越于性理之上的行为出现。其中尽管有将理欲等同的观点,但欲的实施仍然在理的范围内。晚明李贽、清中叶戴震等人,将欲的地位极力抬升,戴震还指责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然其基本倾向仍在儒家系统内。只不过随着自我认知的提高,人们认识到身体价值的正当存在,才拔高了人性的正常欲望。这些观点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相一致。也就是说,欲是在心的指引下所表现出来的合乎理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而心就表现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规范。只有在这一伦理的规范之下,身体行为才能做到不逾矩。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在处理儒家身体观中的“身—心—性—理—欲”各思想元素之间的关系时,一方面主张人的合理情欲的正常宣泄,这是人身作为物质性存在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认为情欲的发出当受限于普遍性的社会伦理规范,即受到被主流民众所认可的社会准则的制约。这也应当成为当代身体描述所应遵循的写作之道,即身体写作的义理与道德边界是普遍性的社会伦理准则。当然,传统儒家身体观的提出是基于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要求和思想立场,现代意义上的身体观对之当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就其基本内容而言,身体行为当符合社会整体要求,需在社会规定的性理原则范围内加以展开。因此,当代文学身体写作,既有承继儒家合理身体观的学理责任,也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发文学新主题的创作任务。
与之相应,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也应与“身—心—性—理—欲”结构图式的内在要求相符合。身体写作热潮的兴起,表明学界在写作领域的积极推进,然有许多作品将身体写作简化为对性、欲望的夸张描述,甚至打出“下半身写作”的口号,使得一些作品向低俗化、艳情化方向倾斜。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文学身体学”的写作主张:“在身体的肉体性泛滥的今天,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这一点便显得非常重要……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这就是我所称的文学身体学,也是写作中必须遵循的身体辩证法。”[27]人的正常肉体性情感的表达当然重要,但一味沉溺其中,将庸俗行为高尚化,纯粹自我发泄或毫无文学底线,并误以为这就是文学的全部,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身体写作的艳情化倾向也违背了儒家的身体哲学观。如前述,儒家哲学的身体观没有否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只是反对超出社会伦理规范的泛情滥欲行为。嵇康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但也主张“情不系于所欲”[28]402,表达的都是对身体本真的追求、对人生超越的努力。这种身体行为的出现,其实是魏晋名士释放感情的特有方式,与当时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状态有关。“至情论”在晚明也有表现,尽管如此,性对情的管制作用其实一直存在。这实际上表明儒家道德之性理对身体之情欲的约束仍是古代文学写作的基本倾向。因此,在讨论当前学界身体写作这一思潮时,我们应将其定位于身体伦理学的层次。这既是儒家身体观和文学创作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观点,也是我们开展身体写作所应依循的写作原则。
(三)当代文学身体写作须“身—儒—文”互动形成正面文学效应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身体的书写,在儒学独尊以后明显带有儒家主流思潮痕迹。儒家身体观在当代还有没有文学价值,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儒家身体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身—儒—文”相对应的结构图式,这种结构图式对当代文学创作仍具参考价值。二是对于儒家身体观中不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观点主张,自然也应当予以剔除。如性理的内容在古代有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妻等纲常关系的成分,而在当代,这些性理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表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内容和特征。这也实际上规定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基本方向,身体书写也当在这一范围内。下文以受儒家身体观较深的韩愈和曹雪芹为例,探究儒家身体观对他们的文学作品所发生的影响作用,通过解剖“身—儒—文”的结构图式,来说明在身体写作中应坚持具有正面作用的儒家身体观。
韩愈诗歌中有大量关于身体词汇的运用,涉及身体的多个部位。如《落齿》中有“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13]16之论齿的诗句。韩愈由身体变化联想到人之相同的生命归宿和人生所需的豁达态度,这是由躯体之身上升到对性情之身的理解,是儒家之性理在身体观上的内涵表达形式。儒家重身,是将身置于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而非将身完全等同于其他生命体之身。其他生命体之身,有自然而无社会的成分;人之身则既有自然的一面,更有社会的一面。当然,韩愈在这里引用庄子“木雁”之典故,并不意味着韩愈转向庄子学方向,而是借用庄子之言,由身自然地过渡到心的讨论,表明身体是变化的,而心境则可以追求恒久之洒脱。这种由身而心的论述方式,在孟郊、李贺、卢仝等诗歌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故有学者提出韩愈的这种诗歌写作举动有可能“代表着唐代诗歌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日常生活中身体书写的转型”,并由此启发我们从身体与风格之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韩孟险怪诗派的风格[29]。这种诠释路径为我们站在当代文学角度理解不同类型的文学风格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除了诗歌,韩愈《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等文,既是哲学之论,也是文学之作。“五原”以探求本原为核心,其本原正是儒家之道。韩愈性情“三品说”就是基于这些德性在人之身的有无程度而言。实际上韩愈的“文以载道”,本身也包含了儒家之道中的身体观,故而能从身体实践和社会要求中促进唐宋古文运动的兴起。韩愈的这种文学表达形式,包含身体观、儒式文人和文学创作等多重因素的参与,可以用“身—儒—文”的结构图式加以表示。“身—儒—文”结构图式在韩愈创作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也给后世身体写作带来启发。当代文学创作既要有承于此,又要依据时代所需,对儒家身体观进行转化和发展,写出真正反映当代社会心声的作品。
《红楼梦》中的女性身体书写,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其实曹雪芹通过贾宝玉“正邪两赋”论所体现出来的男性身体书写方式,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在《红楼梦》第二回中,针对贾政、冷子兴对贾宝玉酒色之徒的评价,贾雨村提出了“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30]18之“气论”。在他看来,一个人成为仁者或恶者,关键看其所秉气的不同,贾宝玉就是具有正邪两赋的气质之人。贾雨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曹雪芹的观点,是曹雪芹运用“气”的观点来评价贾宝玉之品性。如前所言,“人秉气而生”是张载以来在人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反映在身体观上,则意味着人为肉身,人是从自然中而来的。但人不能限于自然之身,还有社会成分,有善恶的评价,其评价依据就在于贾雨村认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之“大仁者”的儒家之德,而身体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红楼梦》以贾宝玉为典型的男性身体书写对象,既突出人之由气而来的一面,因而人有情有欲,也强调气质之身在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因而人需要礼乐、伦理与道德。因此,贾宝玉之任情乖张,实际上是人的合理情欲在其身上的种种表现。相对于贾政、冷子兴之“腐儒”,贾宝玉其实是最符合儒家道德期待的人物。贾宝玉最终中举但遁空门,导致其这种命运并非儒家身体观出了问题,而是以贾政为代表的腐儒势力夸大了性理的控制力量,忽略了情欲在这一系统中的合理作用。曹雪芹对贾宝玉及女性人物的身体书写,有强烈的悲情成分,从文学创作而言,也从反面视角以文学的形式告诉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的合理情欲。曹雪芹采用的典型人物的典型身体书写方式,是《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的重要原因。曹雪芹的儒者身份,其运用儒家身体观成就的伟大作品,又可从另一侧面体现“身—儒—文”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不妨从这些经典文献中寻找写作思路,排除低俗成分,给当下中国文坛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儒家身体观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它一开始就与儒家所强调的心、性、情、理、欲等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身体观较为清晰的结构图式。这种结构图式传达的思想主张,就是使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能各顺其则,进而使人伦事务各得其宜,以仁义润身、以身行仁义,将身心安顿于儒家所倡导的性理之中,以此实现“但观吾身,便可见万物”的清明境地。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身—文”之论、性情之辨,还是当下进行的身体写作实践,我们都可从儒家身体观的内容构成和思想态度中寻找到与之相关的伦理依据。儒家视野中的身体观,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儒家哲学和文学的内在关联,确立当代文学身体写作的义理边界,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