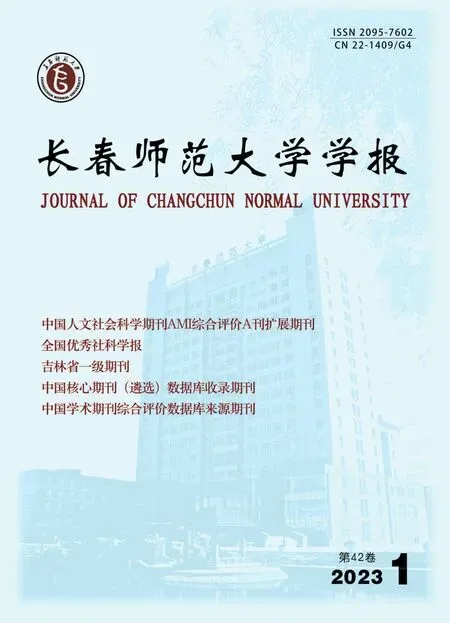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理
——以《卖烟叶》为中心的考察
崔靖晗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赵树理的小说被学界普遍视为“延安文学”和20世纪50年代主流文学的代表作。但据李杨等学者的考辨,“赵树理方向”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间存在裂隙和张力,形成“历史的辩证法”[1]。实际上,赵树理写出《小二黑结婚》等“方向”的代表作时,尚未读过《讲话》。赵树理之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成为主流文学“方向”,是因为陈荒煤等主流批评家看中了他创作的三点价值:首先是“赵树理同志的作品的政治性是很强的”;其次,“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最后,“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这是当时主流文学对作家的要求。实际上,赵树理小说既是主流文学的应时之作,又是试图占据农民精神世界、建立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小说。赵树理小说颇具写实精神,对板话、鼓词等民间文学形式的汲取和创新,客观上使赵树理的小说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具有颠覆性。竹内好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新颖性,在于它跨越了西方中心现代观的“现代文学”和民族本位现代观的“当代文学”或“人民文学”的界限[3]。因此,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二重性,既曾在20世纪40年代被树立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范本,也蕴含颠覆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倾向。
一、《卖烟叶》: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
赵树理的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写于1963年,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既采用了民间文学的“说故事”形式,也以其写实精神成为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卖烟叶》以其独特的构思,书写和分析20世纪50—60年代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写作这一“文学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确立于苏联1934年第一次作家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坚持文艺的真实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具有文学真实性的书写,肯定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思想上教育人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后,成为左翼文学和“十七年”主流文学的创作原则。
“农村题材小说”指20世纪40—70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
“元小说”与叙事学的“元叙述”密切相关。“元叙述”就是“关于叙述的叙述”。帕特里西亚·沃指出:“元小说一词是用来指那些有自我意识的,并系统地关心自身作为一件人造品的身份,以便对小说和现实间关系提出质疑的艺术创作。”[5]“反叙述”指对小说中既有叙述模式的颠覆。
赵树理讨论农村知识青年出路问题的《互作鉴定》《卖烟叶》中,农村知识青年以脱离农村为目的的功利性写作逐渐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这与20世纪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乐观前景相悖。
因此,虽然《卖烟叶》并无戏仿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观意识,但小说的情节与叙事接近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卖烟叶》中,贾鸿年写作主流“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赚钱,因为“缺少生活”被退稿后,“农村题材小说”的神圣性被消解殆尽。正如赵树理在小说“前言”中所言,“故事、小说、评书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我写的故事,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我现在写的时候有叫读者当做‘故事’说的意图,就更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卖烟叶》延续了赵树理小说出于方便农民读者立场对叙述方式的关注,这一叙述特点指向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的反思。因此,《卖烟叶》和赵树理之前的小说一样,因形式的“旧”或“民间”而具有“新颖”性。李国华注意到赵树理小说叙述模式、情节结构由“说理”主导的特征,而“理”指向农民朴素的“老直理”和社会历史“真理”,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存在张力[6]。因此,赵树理的小说有意识地通过叙述方式、情节结构与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区别开来。
《卖烟叶》中,贾鸿年将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视为功利性经济活动,将写小说看作逃避农业生产、脱离农村的手段。以农民和国家的“中间人”自居的农村知识分子赵树理自然对这种现象持批评态度。如作家兼革命者、自愿去农村支教的李老师对贾鸿年的小说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社会生活知识”,“写自己不懂的事谁也写不好”。赵树理有意将“做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和“修改长篇小说”对立起来。贾鸿年的“写作”成为推动“卖烟叶”这一“投机倒把”行为的主要情节。“创作忙”的目的是“智取王兰”,因小说被退稿,贾鸿年编造理由向李老师借钱,从而进城“卖烟叶”赚钱。之前论者对《卖烟叶》的研究多着重于剖析城乡二元关系和农村知识青年出路等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问题,但“写作”这一行为在赵树理农村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赵树理笔下通过“写作”试图脱离农村的农村知识青年是重要的文学史形象系列。这一群体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深造,因为在农业生产劳动中难以实现对自身价值的期许,渴望脱离农村。对这一群体的批判,与赵树理本人的思想与文艺观一脉相承。刘正(《互作鉴定》)、贾鸿年(《卖烟叶》)等农村知识青年的原型之一,是一位想通过成为作家改变命运,给赵树理来信并受到批评的学生夏可为。赵树理在《文艺学习》刊出的给夏可为的回信,引发了读者的争议。读者认为赵树理有违鲁迅帮助文学青年的奉献精神;赵树理指责夏可为不安心学生的职责,不可能写好学校生活[7]。同时,赵树理强调“业余写作”“生活经验”的优势,并把“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把你们社办成一个模范社”作为对女儿的期许[8]。
此处赵树理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为三点:首先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对“劳动”的重视。有论者指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劳动经历了由“翻身”到“翻心”的过程,“真正的出路在于,翻身之后,还要‘翻心’,底层翻身后,如果仍然认同以前的原则,譬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不过是很简单地从受压迫者变成现在的压迫者”[10]。郭文元等学者注意到,《地板》试图通过“劳动”建立给农民带来主体性地位和尊严的乌托邦[11]。其次是将劳动“纯化”为体力劳动,甚至将文学创作、当干部视为“非劳动”;在文学写作中推崇“业余作家”的“生活经验”。再次,是赵树理小说中“地方性”的本体性意义。赵树理对曲艺等民间文学作用的强调,对“写真实农村生活”的推崇,都指向对“地方性”或“农民性”的重视。这一方面与现代乡土小说借“地方性”反映“民族性”或国民性的诗学特征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源于他试图在文学叙述中建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杜赞奇将“地方”视为“民族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中心张力点”,并将用“地方性”指代“民族性”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乡土诗学[12]。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小说”以地方性书写直接代表中国“民族性”的文学叙述方式,与新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存在紧张关系——被殖民国家走向现代化,是否要抛弃“地方性”甚至“民族性”?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解决乡土小说中民族性与西方中心现代观的矛盾,建立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性。赵树理在“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苏联写作品总是外边来一个人,然后生产共产主义思想,好像从外边灌的”,“农村自己不生产共产主义思想”,隐含对源自苏联的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的批评[13]。农村题材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作家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试图书写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土社会这一“地方世界”的改造。赵树理的思想与创作,与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具有潜在的矛盾,因为后者旨在用“共产主义”改造“地方世界”,从而生成新的民族性;赵树理从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出发,试图用“地方性”甚至新的“农民性”代表“民族性”。
因此,赵树理的思想隐含深刻的矛盾——“知识分子”或“民族国家话语”与“农民”的矛盾。他试图站在国家和农民平等地互相“说理”的“中间人”地位。赵树理对“劳动”“业余”“生活经验”“群众”的推崇,背后隐含着他的农民立场。论者将赵树理的小说艺术世界称为“农民说理的世界”,究其根本,赵树理试图用“理”,即真理或乡土伦理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让农民获得主体性地位[14]。因此,赵树理对农村知识青年试图通过“写作”成为职业作家,脱离农民群体和农村建设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赵树理小说中“世界”消失这一叙事特征,意味着农民通过“说理”获得主体地位这一逻辑面临严峻挑战——农村知识青年作为赵树理曾经寄予厚望的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通过写作行为试图脱离农村进城,这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甚至乡土社会和农村前景的质疑。同时,农村题材小说的文体合法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小说中如何处理贾鸿年的身份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赵树理赋予贾鸿年奸商后代而非真正农民的身份和自我认同,从而对他试图通过写小说赚取稿费来结婚、骗取李老师的信任借钱来卖烟叶等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从叙事层面观之,《卖烟叶》旨在探讨农村知识青年作为有知识、有文化并曾被赵树理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农民,如何处理作为农民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农民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赵树理通过自愿下乡工作的革命者兼作家李老师对贾鸿年的批评教育,使贾鸿年幡然悔悟,“要做一个好的劳动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李老师说:“各行各业都一样,抱着个人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名为利,抱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共产主义”。赵树理试图用“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矛盾解释农村知识青年不安心于农业生产劳动、对农民身份失去认同的现象。贾鸿年写的小说歌颂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革命者老队长,赵树理通过这一将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精神作为主题的“书中之书”,客观上将农村题材小说的合法性作为尖锐的文学史问题提出:如果“农村题材小说”的作者怀有“个人主义”思想,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前景和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失去信心,作为文学体裁的“农村题材小说”如何维持生机?
赵树理在《卖烟叶》“前言”指出,这篇小说是对“说故事”的模仿。写作过程中,赵树理有意识调整叙事模式,甚至“去小说化”,从而使《卖烟叶》成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反叙述”。与同样写农村知识青年题材的《互作鉴定》相比,《卖烟叶》更接近民间文学:小标题如“智取王兰”“创作忙”等,接近民间文学的评书体;《卖烟叶》手稿本相比于《互作鉴定》,心理描写、风景描写大幅度减少,但在《卖烟叶》发表版本中增加了心理描写、风景描写。论者认为原因在于农村“讲小说”活动中“故事员”主要是读过现代小说的农村知识青年。“对于处于写作者和听众(预期读者)的中介的农村知青,或许可以视之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将‘道听途说的经验’——此处是通过阅读——‘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同时融合了现代的‘短篇小说’与‘口头叙述传统’”[15]。因此,《卖烟叶》的叙事模式隐含着赵树理对农村知识青年的训诫意图。但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卖烟叶》又推翻了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判断。贾鸿年通过创作“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赚稿费失败而堕落为“投机倒把”者,指向脱离农村过上城市生活的目的,这隐含农村知识青年对农村前景的悲观、对农民身份的不认同。《卖烟叶》的价值悖论与小说的叙事模式悖论息息相关。
赵树理小说对叙述模式的重视,可以视为赵树理小说具有新颖性、甚至在形式上不经意间成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的重要原因。赵树理主观上并无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文体的反思意识,但《卖烟叶》的小说文本通过小说“前言”提到的“说故事”这一民间文艺形式、通过贾鸿年将老队长的一生写成主流“农村题材小说”试图换钱这一事件,形成“中国套盒”式叙述结构。换言之,《卖烟叶》是一个关于农村题材小说这一主流文学写作的“故事”,文本中民间“故事”与主流“小说”的界限不再分明。
二、关于“小说”的小说:《卖烟叶》中的“故事”
《卖烟叶》的叙述层面,“故事”始终占据重要作用。赵树理在《卖烟叶》“前言”中这样解释小说采用“说故事”叙述模式:“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方面,增加了‘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面我还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卖烟叶》通过这一叙述模式,成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或“反叙述”。
《卖烟叶》是一部关于“故事”或“小说”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一向重视“说”与“写”的关系。《李有才板话》中,叙述者关于“诗话”与“板话”、“诗人”与“板人”关系的议论,实际上是赵树理对现代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思考。“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作‘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所以叫作《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小说始终试图突破“说”与“写”、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二元论,并否认前者高于后者的成见。从这个角度看,《卖烟叶》借探讨“小说”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试图创作出一种具有农民主体性的农村题材小说。
《卖烟叶》对农村题材小说形式的探索,也在作为现代文学形式的“小说”与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故事”的关系层面展开。赵树理对“小说”的反思体现在《卖烟叶》的情节中。革命者李老师和甘于“劳动者”位置的女同学王兰欣赏贾鸿年的文学才华。但赵树理极力证明贾鸿年并不具有文学才能,他的文学创作来源于模仿而非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与赵树理注重“生活经验”的文学观相悖。因此,李老师和王兰被贾鸿年蒙蔽,是上了“文学”的当。作家在叙述这一故事过程中,有意采用了“说故事”的民间文学形式,试图用“说”打破“写”的神圣性。《卖烟叶》采用口语化评书体小标题。小标题“创作忙”可以看作对20世纪50年代习惯用语“生产忙”的戏仿,而小标题“智取王兰”又暴露了贾鸿年对女性的不尊重及思想的庸俗陈旧。赵树理在《卖烟叶》中弱化文学创作的精神劳动实质,将写作视为与农业生产劳动同样性质的世俗事务,这与赵树理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赵树理看似将体力劳动神圣化,通过“劳动”建立农民主体的乌托邦,如《三里湾》《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将农村知识青年与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对比,但实质上他旨在探索农村题材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的叙事模式质疑主流的“小说”形式,从而产生独特的现代性。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对“故事”作了如下定义:“故事”主要指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和情节[16]。卢卡奇《小说理论》将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与“现代”进行了密切的联系。卢卡奇认为,“现代”的兴起意味着“心灵的现实占据了重要的作用”[17]。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指出,“现实主义的形式通常表现在内容层面。就这一点而言,现实主义模式与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形成密切相关。”[18]在这个层面上,现实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赵树理小说通过民间文学的“评书体”和“说故事”,以其朴素的写实笔法、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生成了新的文学现代性。
赵树理将小说和“故事”同样视为纯粹的叙述模式。《卖烟叶》似乎有意淡化小说的精神内涵,强调贾鸿年写小说“卖钱”的文学创作动机的功利性。在此,赵树理并非主观上贬低小说的教育意义,而是反思文学叙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正如《卖烟叶》中王兰的好友周天霞所指出,“什么人什么事,在学校里听他说,是看不清的。要到社会中实践,结合了理论才能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考量《卖烟叶》中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卖烟叶》试图通过打破二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反思“小说”,尤其是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革命者兼作家李老师,是参与过革命、教过中小学的赵树理的代言人。李老师和出版社一样,认为贾鸿年的小说“缺少生活体验”,过于模式化。同样,赵树理针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模式化倾向,特别重视作家的“生活经验”,如他对“业余写作”及其业余性的重视,试图回归写实主义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从这个层面看,赵树理《互作鉴定》《卖烟叶》等农村知识青年题材小说,通过“反叙述”质疑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叙事的真实性,用民间文学的写实“故事”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形式,并尝试确立小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互作鉴定》中,农村知识青年刘正向下乡视察的县委书记上“万言书”申冤,将农村社会称为迫害他的“罪恶社会”。小说的构思颇为巧妙,以刘正“文艺腔”的万言书开头。随后在“鉴定”中,刘正文学叙述的真实性被打破——刘正沉迷写诗,幻想通过当上作家脱离农村,耽误了生产劳动。《互作鉴定》通过质疑“文学”的真实性,以民间故事的叙述结构和写实笔法获得了小说文体的现代性。《卖烟叶》更进一步,通过“说故事”这一民间文艺形式质疑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真实性。这体现为《卖烟叶》对贾鸿年功利的创作动机、单薄的生活体验的批判,对贾鸿年小说主人公原形“老队长”婉而微讽的批评。革命者兼农村干部老队长退休后,好大喜功,极力让贾鸿年在小说中吹捧他。因此,“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20世纪60年代主流文学创作方法难以维持生机[20]。
三、结语
《卖烟叶》作为赵树理饱受批判并导致其告别小说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对解释赵树理由“赵树理方向”的中心地位到在农村题材小说潮流中边缘化,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卖烟叶》从农民主体地位出发,通过民间文学的“故事”形式和写实主义笔法,成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通过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真实性,客观上获得了“新颖”的文学现代性。正如竹内好所言,赵树理小说沟通了现代文学(写实主义的乡土小说)和“人民文学”(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等“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