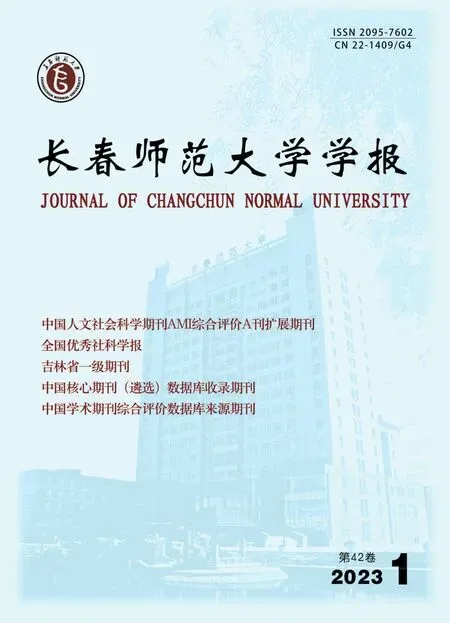近代中医科学化探赜
胡冬敏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现代意义上的中医生成,始于中西医之争[1]。“科学”自清末传入中国医学界,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学人提出“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应运而生[2-3]。中医科学化是中医界为将中医学纳入近代科学体系,构建与西医平等对话的“科学平台”,而主张改造中医学的思潮[4]。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医科学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余新忠[5]以近代天津名医为个案,从生命史学的角度管窥丁国瑞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还原近代名医面对近代医学知识转型过程中的心态、追求和对中西医汇通的认识。皮国立[6]选取唐宗海为个案,探讨早期的中西医论战背景下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他认为唐氏运用西医理论阐释中医以维护和发展中医自主性的方法值得借鉴。郑洪钧[7]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仅简略涉及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尚有商讨空间。雷祥麟[2]首次以英文专著的形式深入探讨近代中医“科学化”争论始末。祖述宪[8]搜集、整合近代学人的中医观资料,集结为专著。相关学者的著述多仅限于粗略勾勒,缺乏深入研究,仍有较大探讨空间。
本文通过梳理近代报刊、日记、书信等文献材料,厘清中西医融合思想的源流与背景,探讨知识学人对近代中医科学化道路的探索,分析知识学人如何通过报刊传播科学知识,呈现民众声音,以期勾勒中医科学化论争的社会场景和文化内涵。
一、冲突与调适:西方医学的冲击
19世纪初,西方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西方医学家,都在思考如何将西学传入中国。张大庆[9]认为,近代西医的本土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后一阶段则以中国政府为主导。西方传教士为扩大西医在华影响,积极倡导西医教育与译介西方书籍。早期医学传教士如伯驾、嘉约翰等人,通过创办医院、诊治病人来传播西学,希冀通过“医务传道”打破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的刻板印象。教会医院通过“医务传道”的方式,利用成功率较高的眼科与外科手术吸引病人,传播医学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招收学徒,以招收信徒。1837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招收中国学生。1839年合信在广州惠爱医院,招收生徒。西方医学著作的编译和出版为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①在此进程中,西医知识在传教士的转译中影响日益扩大,也冲击了传统医学。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医学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洋务派提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欺蒙”的想法。清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地设立新式学堂,教授西学。1865年,北京同文馆增设医科,聘请德贞主讲解剖、生理。1888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医学馆,后更名为海军医学校,这成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
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对西方以“科学”标榜的诊断治疗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将“西医”视为改革的有机整体,讲《身理启蒙》《体性图说》《西医略论》等书列为参考书目。②李鸿章曾在《万国药方》中所做的序中指出:
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遂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③
由此可见,李鸿章十分推崇以“科学”为基础的西医。作为传统体制的守护者,他仍希望中医能吸取西医所长,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与精极微之境”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在晚清士大夫当中,并非仅有李鸿章提倡西医、批评中医。桐城派吴汝纶在《答萧敬甫》中曾批评道:“今西医盛行,理法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绝非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友民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10]此外,吴汝纶在书信当中多次提及中医不可信。④他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脏、寸口脉候视五脏均为妄说,中医不能深明药效。1902年,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曾在同仁会欢迎会上致答辞:
贵国文明之化自医学开始,今亦望中国振兴医学即是起手办法。贵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11]
吴汝纶批驳《难经》《素问》皆为伪书,认为五脏描述皆毫无根据,并将西医比作今文经,将中医比作古文经,将代表古典中医文化的《难经》归为伪书。吴汝纶还认为日本的医学虽从中医习得,但在吸收西方医学精华的基础上取得长足发展,因而中医应该向日本取法,以求精进。
改良派的著名人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中从医理医法、解剖、大脑与心血管系统的功能、治疗和病症分类五方面数列中医不如西医之处。[12]他指出: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抑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13]
罗芙芸在探讨卫生在中国的演变时,曾论及随着武装的帝国主义的到来,中国人开始紧密地围绕着这一词语展开如何实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争论。西医知识入华的进程中,卫生的含义逐渐偏离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涉及国家的权力、进步的科学标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健康观念。[14]晚清的知识学人围绕医学的争论亦是如此。梁启超认为:“故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他还指出,“凡世界文明之极轨唯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15]1897年,刘桢麟在为《知新报》撰写的《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中亦提出,“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16]彼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各种思潮涌现,“医学救国”成为医学界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纲领。
经学大师俞樾最早反思中国传统医学。1876年,他在《春在堂全书》中撰写专篇论及“废医”,分为七篇,即本义篇、原医篇、巫医篇、脉虚篇、证古篇,去疾篇。
第一篇“本义篇”中,俞樾以《周礼·天官》《春秋左传》《史记》为据,言及周和春秋时期,“古者醫卜並重”,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甚至“重卜甚于医”,及至唐,废龟论产生。如此一来,俞樾问道,“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此篇以医和卜作对比,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篇“原医篇”中,俞樾考察神农尝百草说,认为孔子的《书》对于百草描述年代久远,不足为据。《汉志·艺文志》载,“神仙家有神农集子技道二十三卷,而无本草之名。”又引《中经簿》和《七略》以证《中经簿》所言,“子仪本草经一卷”在汉时并不重要。故而,俞樾认为,医道传自古仙圣,世人不查,不可议废。
第三篇《巫医篇》中,俞樾引征《素问》《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关于巫和医的描述,认为巫医同源,“醫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17]750。他指出:周朝建立礼制后,巫医始分。汉巫蛊之祸后,巫之道日益衰落,巫既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医亦可废。
第四篇《脉虚篇》中,俞樾认为医家治病,其要在脉,但脉象不可凭信。郑玄将《周官》中九藏解释为,“胃旁胱大肠小肠”,其中大肠小肠合为一肠,肺心肝脾肾为另外五脏,合为九藏。《素问》中又提出“三部九候论考”[17],将脉分为上中下三部,每部又分为三候,但是俞认为此种说法自相矛盾,即上下三部各分三候,为何中部不称之为手阳明?又《太史公·扁鹊》传记,扁鹊舍弃繁杂的三部古法,将脉分为上下两部,开创中医的寸关尺三脉相诊治法。俞认为此三种记载,自相矛盾处极多。昔日王充作《论衡》以批评儒学的谶纬学说,俞樾先生作脉虚篇以“废医”。
第五篇《药虚篇》中,俞樾引郑玄、贾公彦在《周官》中对“五味五谷五药”的阐释,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上药不足以养性,中药不足,而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17]751俞樾认为,脉诊杂乱,医用药杂乱,医学是虚无的,全然无据可循。
第六篇《证古篇》中,俞樾列举周公代武王戴璧秉圭、孔子重巫不重医、许世子弑君,以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此外,俞樾也表达对药物的看法,认为有无药物,皆可治愈。因而医治病人,患者最后会“轻病以重,重病以死。”[17]752
第七篇《去疾篇》中,俞樾认为,不生病者是因为“善养生者消恶心而长善心”,病家生病是因为“风雨不时,寒暑不节。”因而,唯有“长其善心,消其恶心,使太和之气洋溢于其中,而熏蒸乎四肢颜色悦怿”,方可“坚强寿命。”[17]754-755
综上所述,俞樾从五个方面,阐释其中医观。无论从古典中医学角度看,还是从西医角度看,俞樾此番种种论证,似乎都有违“常识”。俞樾作为一代经学大师,不善医学,为何作《废医论》专篇呢?俞氏在《余曲园书札》中承认,“辱以素问见询,素问乃上古遗书,向曾浏览,惮其艰深,且医药自是专门,素未通晓。”[18]章太炎作为俞樾的学生,曾在《医论》中多次分析其师的文章。章太炎批驳道,“先师俞君侨处苏州,苏州医好以瓜果入药,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长子之丧,发奋作《废医论》。不怪吴医之失,而迁怒于扁鹊、子仪,”他还尖锐地批评道,“亦已过矣”。[19]赵洪钧认为,俞樾创作废医论处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一向轻视医学;二是清末民初医学发展凋敝,庸医横行;三是俞氏妻子儿女早年丧病,激发他对中医的强烈不满。[20]
不同于早期全盘否定中医,俞樾晚年再作《医药说》。他在论述中多次引征《礼记》《曲礼》《说文》《春秋》等,以阐释医不可信,药可信:“余废医之论,本之此也。然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21]。长期以来,学界多将俞樾视为近代“反中医”第一人。为何俞樾一改之前的全盘废医说,转而支持废医存药呢?张田生认为,俞樾所作《废医论》,只因家人遭受病魔蹂躏,对医家发出“学理化”牢骚,此种牢骚在当时实属常见。[22]俞樾从内心中并不完全排斥中医。
俞樾的学生章太炎也主张废除中医五行,但与俞樾不同的是,他主张中医不应将精力浪费在与西医的争辩上,而应谋求自身的发展。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提倡建设医学专门学校,并把中医药排除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表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23]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知识界的中医和西医论争思潮暂趋于平静。
晚清知识学人对西医的认知、探讨与推崇,较其他社会群体更为深刻。他们的思想是社会变革的缩影,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过分崇拜西医、极力贬低中医也造成中医被误读。[24]
二、新旧之争:中医融通西学
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说以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念和辩证法为架构,人体生理功能与病理现象的诠释也皆有赖于此。以“援物类比”将中医和西医加以对比的理论体系也有其弱点,即对人体的构造缺乏精细的认识。此外,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观念使解剖学知识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西医知识入华对中国医学知识产生强烈的冲击,西医的病因、病理学说在解释疾病以及传染病的病因、病理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以病理解剖为基础的“病灶”理论与以微生物和寄生虫为基础的病原生物学思想,是近代诊断技术、外科、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思想核心,也是时人比较中西医学长短的参照系。近代中国西方医学和卫生观念的传播远远超过医界的范围,成为科学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社会观念和制度变革的理论基础。[25]受过西学教育的医者将中医看作不科学的“旧医”,把西方医学视为代表先进和文明的“新医”。如近代医学家丁福保认为,“吾国旧时医籍,大都言阴阳气化,五行五味生克之理,迷乱恍惚,如蜃楼海市,不可测绘,支离轇轕,如鼷鼠入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26]在教科书中,丁福保亦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传统医学的鬼神之说不可信。[27]
激进的医学家认为中医是“旧医”,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其中,言行最为激烈的是余岩。余岩(1897—1954),字云岫,浙江镇海人,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曾任职于公立上海医院。[28]余岩留学日本期间,目睹日本近代医学的兴盛,认为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废止汉方医的结果,主张只有废止中医,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才能得到发展。余岩运用考据法,从批判中医的立场出发,系统地研讨中医经典,于1917年撰写《灵素商兑》,对《内经》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基本理论进行全面的批判。他将当时的西医理论与中医理论进行比照,以西医知识作为衡量正确与否的批准,比照的结果是《内经》“无一字不错”。余岩的观点引发争论。
余岩以西医病因病理学理论为依据,对六气致病的观点作了辨析。他将六七致病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诱因三类,认为:
直接原因致病并不常见,只有在六气之变化极其剧烈为人类所不能抵抗者,始足以使人致病,如严寒时之冻伤、近火者之烧伤以及酷暑时之中暑等。间接原因导致的疾病较多,如夏秋之交,气温高、湿度大,微生物容易生长,饮食诸物,腐败极易,故肠胃诸病,夏秋较多。加之苍蝇蚊蚋,增殖极繁,最易传播病毒、古疟痢等病,亦有夏秋为多….诱因者,疾病种子,幸遇身方强固,难以发展,一旦遭逢他病,则授寇贼以机会,乘时蠢动以成病也。如肺炎之双球菌,健康之肺中,亦尝有之,然不为祸害,一罹感冒,则乘坐人之隙,发为肺炎者,往往而见。痨病之菌,百种已有九十侵居体内,然往往静居蛰处,不见其害,迨一罹他病,如麻疹、如肺炎、如重度之感冒、如伤寒等病之后,往往病趋骤进。[29]
余岩的观点吸收19世纪西方医学的知识,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论证伤寒、疟疾等疾病诱因,但其观点过于偏激,引发医学界强烈震荡。
率先与余岩展开论战的是恽铁樵。恽铁樵,字树玉,江苏武进人,早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曾任《小说月报》主编,因丧子而改学医,而后成为著名的儿科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重要医学家。为批驳余云岫对《内经》的攻击,恽铁樵重新解释古人对生命现象的探究,而不是在医理上进行争论。他和余岩的论战主要收录在《群经见智录》当中。他认为,“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是内经的理论精华之所在,因而人的生命活动与四时密切变化相关,四时是全书的总纲,五行、五脏、六气与四时相配,用以说明四时,“《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30]
1929年2月24日,余岩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废止旧医案,并获得通过,将废中医舆论推向高潮,引起中医药界强烈的震荡。[31]随后,上海特别市医药团体代表会批驳余岩等人的废止中医案:“发挥国粹研究国产,以掩其专销西药之罪名,乃巧立名目,强分新旧,更提倡废止中医,成立议案,以期消减中医中药而达彼等推销西药之奸,谋至天产物叶,置于生命命脉转系他人,丧心病狂莫此为甚!”[32]
1933年杨则民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探讨》一文,认为恽铁樵的论文观点严谨、鲜明,“绝无旗鼓相当之论文出世”[33]。该文认为,中医具有整体观,西医则通过局部来寻找病灶,因而在治疗上“中医为生物学的方法,视身体为整个的而不容分割,故局部病亦视为全身病之局部透现;外医为理化学的方法,视全身病亦欲求的其单一之病原与病灶。”[34]该文于1933年发表之后,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多家刊物纷纷进行转载。
面对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知识体系和疾病理论的冲击,中医学界的少数医学家仍坚持经典,愈来愈多的医学家则开始接受西医的生理学观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西医汇通派。中西医汇通思想对医家唐宗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宗海认为西医与中医互有优劣,主张“损益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然而,唐宗海的基本思想是厚古薄今、重中轻西,因此他很难客观评价中西医的不足。[35]
恽铁樵对两种医学本质的理解较唐宗海更为深刻。他指出:“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在疾病的命名方面,“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因此“今日中西皆立于同等地位”。[36]另一位著名的中西医汇通派医学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列举“衷中参西”医学思想,即以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为本,参考西医知识和药物,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从余岩对中医的强烈批评,到杨则民、恽铁樵等人提出的汇通思想,反映出当时知识学人改进中医的探索。中医界出现的汇通思想,力主中西医的原理是相通的,试图通过西医肯定中医。从整体上看,学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仍存在局限性,如对中医药理论的独特性认识不足。
三、革故鼎新:中医改良道路探索
继中西汇通思想提出之后,知识学人寻求探索一条属于中医发展的道路。中医界提出改良中医、中医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主张。丁福保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他在《国药新声》发刊词中写道:“中西药沟通之呼声逾四十年,吾人主张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亦四十年……然所谓科学化者非仅徒托空言,必求之实际。”[37]显然,他认为中西医沟通的前提是中医求教于西医,而不是一味排斥。事实上,知识学人赞同中医科学化的声音愈发活跃,如陆渊雷、谭次仲、施今墨等人。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知识学人亦卷入这场争论。1934年3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论所谓“国医”》,呼吁在中国医学卫生方面作出改良,并提出以下建议:设训练内地服务医生的学校;建立公共卫生机制体系;训练内地服务之看护,尤其是女子看护;批评近代女子运动多为虚荣运动,振兴女子看护事业方可助力女子运动;政府出资设立医药工厂;政府充分地推广生育节制;政府奖励近代医学。傅斯年尤其强调应该逐步废止中医,但因中国医生人数尚少,可先禁止大埠“国医”,再对正在行医的医生加税,“寓禁于征”以渐次禁止“国医”。在文章的结尾,傅斯年表示“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38]傅斯年的文章引发医学界、知识界的争论。胡适将之转载至其主办的《独立评论》上。留日学生金正愚以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治疗神经衰弱的亲身经历,批驳傅斯年未曾亲身体验过中医治疗而断然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论说。他还对余云岫的废中医论加以批驳,认为余云岫仅仅攻击中医医学理论,而未对药物学理加以深研[39]。民国医师王合三则以《异哉傅孟真之“所谓国医”》为题,从中医起源问题、取消大埠之中医、医药改良问题以及中央医院四个方面驳斥傅斯年,并自认为此番做法乃是从“大处落墨”见报诸端,以尽绵薄之力挽救国家危亡[40]。
8月13日,医生赵寒松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傅斯年的文章,认为傅斯年缺乏医学常识,见解错误,对中西医学不甚了解,而妄加指摘。赵寒松详细阐释中医的五行六气说,并从内外因两方面阐释六气致病理论。他认为中西医对疾病的阐释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认可规范、整治中医和中医市场的主张,否定傅斯年全盘废止中医论,主张用西医的技术发展中医的医药和医学理论。[41]
医学行会亦参与论战。8月18日,《大公报》上刊登天津市中医公会主席陈泽东的文章[42]。稍后,陈泽东又将全文发布于《国医正言》上[43]。该文斥责傅斯年“一味蛮骂胡说而已”,针对傅斯年认为中西医之争可耻一说,认为傅斯年不思如何改进国医,一味强调用西医之法取代国医,实为荒谬 。
傅斯年随后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上下两篇《再论所谓“国医”》,回应赵寒松和陈泽东批驳他“一派胡言”和不懂医学科学。傅斯年认为,所谓国医与近现代科学不相容,是件明显的事实;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傅斯年提问道:国医是否科学?“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字——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傅斯年认为赵寒松为中医改良派,陈泽东则代表儒医的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医最大的缺陷是无病理、缺诊断,无法用近代科学的“微菌”观来解释,中医与中医间的争论是无意义之举动。傅斯年认为中医缺乏科学的医学统计体系来评估最终的治疗结果,无法计算何为“治愈”。傅斯年最后呼吁政府应该承担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责任,认为政府的失职引发“中医西医优劣论。”[44-45]
赵寒松再次连发三文,以驳斥傅斯年。他认为傅斯年的研究态度尚为严谨,但对医学仍然缺乏相关的认知。他认为国医的病理相较于西医更为精准,并用中医义理详细论证伤寒杂病的判断、治疗和诊治。他指出,“西医每将传染病与温热病混杂不分,反诋中医不能治传染病,而不悟已不能治温热病,诚属少见多怪。”[46-48]
研究实验语言学的学者刘学濬向《独立评论》去信,指出:中医的柱石是五行六气阴阳等学说,虽然暂时尚未证明其合理性,如若稍加研究,必定能研究其真理;虽然学者多以为中医诊脉术无科学依据,但是西医亦有切脉术,未见其科学依据。[49]傅斯年随后对刘学濬的疑问给予回复:中医的五行六气阴阳学说是玄学;中医所谓经验良方,仅有经验,未见良方;中医的经验也只是经历,无科学依据。对于刘学濬所提及的中医诊脉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傅斯年认为,“机械测量远比人体更为精密而正确。”[50]
除医学专业人士以外,普通民众也参与到这场争论当中。天津纱厂会计向《独立评论》投稿,强调传统医学的优势:国医理论诚然玄虚,诊治确实有效的;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是《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国医既然有《经验良方》,必然是有效的。针对此三方面,傅斯年一一作出应答,尤其是在回答是否具有发言权的问题时,谈及早年曾学习心理卫生学,但赴德之后,察觉实验科学在具体的实践中更加有效,遂转而学习生理卫生学。[51]
对比19世纪西医形成的科学实证方法,近代知识学人认为中医以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理解疾病,缺少科学性。傅斯年对国医的批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非个例,梁启超、丁文江、鲁迅、郭沫若等知识学人对中医均持否定态度。梁启超也曾否定中医:“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的大本营……”[52]他还比较中西医教育:“西人医学,设为特科,选中学生之高材者学焉。中国医生乃强半以学帖括不成疾者为之,其技之孰良,无待问矣!汉志方伎犹自列为一略,后世废弃,良足叹也!”[53]因而,他建议开设学堂,兴建学会和创办报刊,“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开医会以通海内外之见闻,刊医报纸以甄别法西法之善美,立医学堂设医院以究理济贫”。[54]
相较于早期学理论争,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论争中的多数人对中药科学化的客观事实给予肯定。傅斯年等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学人对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废医存药、废除部分理论,以及保存部分理论。
四、结语
晚清以降,思想界甚至政界对传统中医的怀疑日益剧增。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传统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视为旧传统、旧文化的代表,受到新学知识学人的猛烈抨击。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等无不深恶痛绝医学,鲁迅甚至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普通民众也参与论争当中,显示了20世纪西方医学知识入华后对中医界的冲击。近代知识学人所追求的实现中医“科学化”抑或医学的现代化道路,是一场探索国家现代化的科学救国运动。陈邦贤认为,“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成为科学的医学。”[55]自俞樾到余岩再到傅斯年,对中西医的争论不再仅仅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的争论,而是扩及思想文化的范畴。[56]
在现代西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医学有着独特的发展体系。中医哲学、中医流派与学说体系,自成一体。随着殖民扩张活动而来的西方医学,对中医形成强烈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医学一度将西方医学视为建立现代化的指标。中医的病理解释与疗法受到来自知识精英的质疑、官方的约束以及民众的怀疑。知识学人面对一系列叠变,提出中西医汇通论,发起中医科学化论战,并对中医现代化道路进行思考,反映了知识学人为应对外界变化而作出的种种调适。
[注 释]
①合信翻译的医书包括《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妇婴幼说》等;嘉约翰编译的《西医说略》《割症全书》《化学初阶》《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医名目》等;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傅兰雅与赵元益合译的《全体通考》《西医举隅》《续西医举隅》《英国官药方》等。
②据笔者统计,列为参考书目的西医书有艾约瑟的《身理启蒙》、傅兰雅的《体性图说》、合信的《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嘉约翰的《西药略释》《皮肤新编》《割症全书》以及嘉约翰和林湘东的《花柳指迷》、德贞的《西医举隅》等.
③《万国药方》由美国传教医士洪氏提(S A. Hunter)翻译,李鸿章作序。本书首版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版于1919年,收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本文用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九次版。吴克让在《解放前西药出版简史》指出,中国西医的出版经历了五个阶段:1871—1905年,开始翻译外国药学书籍时期;1905—1932年,编译外国药学书籍时期;1932—1937年,自编药学书籍时期;1937—1949年,战乱时期。洪氏提:《万国药方》(卷一),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
④吴汝纶在《与吴季白》中指出:“不知近日五洲医学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他在《与王小泉》中称:“畏药如闻敬弦,惟坚守勿药,以后复元。”他还在《与廉惠卿》《与贺松坡》《与李亦元》《与儿书》《同仁会欢迎会答辞》等书信、文章中主张中医向西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