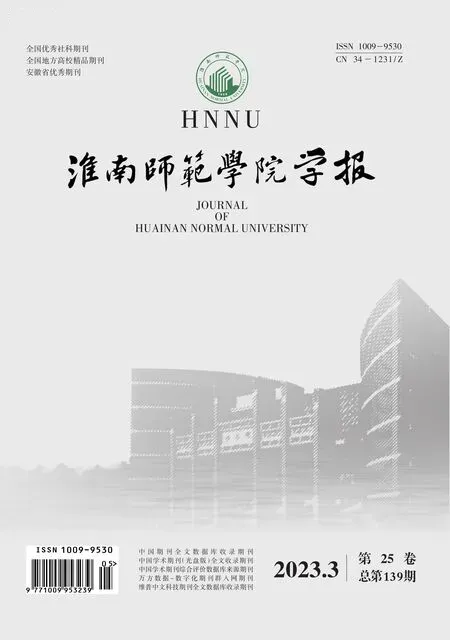唐顺之江北赈灾事宜考察
刘笑天,张艳芳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唐顺之,字应德,别号荆川,常州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顺之精通文史,晓畅军事,曾任兵部主事、职方员外郎、太仆寺少卿、右通政及凤阳巡抚等职。嘉靖中后期,南倭北蒙交至,天灾频仍。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北(明代的江北地区,指南直隶的扬州、淮安、凤阳、庐州、安庆等府州,即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庐、凤、淮、扬四府发生严重旱灾,农亩失收,时唐顺之接替李遂出任凤阳巡抚,不顾劳累,舆疾赴任,对收集赈灾物资以及筹划赈灾措施做出不懈的努力,史称其“捐俸设粥,活民数十万”[1](P1075)。文章基于唐顺之于是时所上奏章及其赈灾时所发牌令,对其赈灾之始末进行梳理。
一、江北灾情及赈灾物资的筹备
(一)江北灾情与赈灾物资的匮乏
江北地区的灾荒源于倭患与旱灾,唐顺之在奏疏中写道:“照得江北地方,今岁既遭重大倭患,复罹异常旱灾,以致远近农亩失收,到处米价腾贵,即今饥窘之民充斥道路,嗷嗷望赈。”[2]在倭患与旱灾的双重打击下江北地区出现大量饥民,唐顺之描述灾荒之地的情形称:
江北今岁灾伤十分重大,各处饥民无虑数万,前在秋末,尚有草子木实可赖充饥,今值隆冬,虽草木亦无可食。强壮者相聚为盗,老弱者则弃卖妻孥。有司无日无盗劫之申,地方无处无离散之苦。沟壑莩尸,遇目成悲,道路啼号,触耳可惨。言及于斯,稍有人心者,鲜不恻怆,况为民上者哉[2]!
可见,江北等地的灾情其时已十分严重。然而江北诸州府仓库的情况却十分窘迫。由于连年倭乱,仓储空虚,无力放粮赈灾,唐顺之在乞留余盐疏中称:“缘自连年倭患以来,窘急搜括,仓库处处空虚,今内帑既不敢望,而仓库之积又极不够赈济,委实难处。”[2]不仅赈灾的粮食无从所出,而且迫在眉睫的春汛防倭军饷也无处筹措。基于这种两难的境地,前任巡抚都御史李遂、巡按御史陈志上奏明廷,乞求发放赈灾物资及蠲免钱粮等项,户部的回复如下:
即今银库十分匮竭……合行各该巡按行令各府州掌印正官,备查在仓预备粮米及府贮无碍官银,侯冬春之时,如果饥馑难存,即行勘实,酌量银米,选委廉能正官分投相兼赈济。如或不敷,多方区处,务使穷户均沾恩惠[2]。
户部以银库匮乏为由,让巡按等大臣利用灾地的“在仓预备粮米及府贮”进行赈灾。但江北诸州府由于连年的倭乱,仓库早已空虚,以江北州府府贮仓库进行赈灾的命令,无异于空文。不过,李、陈二人的上奏仍起到一些效果,明廷蠲免了江北诸州府的部分赋税,唐顺之在凤阳等处灾伤疏中称嘉靖三年(1524)侍郎席书在江淮赈灾时,“税粮不拘起存,尽数蠲免……席书得以大为展布,极贫鬻粥,次贫给予银米,全活者二十余万”[2],而唐顺之面临的情况则是“内帑既不敢望,而起运钱粮又升合分毫不敢乞免”[2],相较于嘉靖三年(1524)席书赈灾时起运和存留的尽数蠲免,此次明廷所谓的蠲免赋税,仅为存留一项而已,至于起运,则分毫未免,这对于江北的灾情而言,实属杯水车薪。
(二)唐顺之对于赈灾物资的筹备
在这种境遇下,唐顺之不得不为赈灾物资另作打算。其筹备赈灾物资的方法主要有乞余盐、乞剩盐、截漕粮和起运粮折银等项。
1.乞余盐与乞剩盐
明代盐政有正盐与余盐之分,正盐又有常股和积存之分,而余盐是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唐顺之在乞余盐疏中道:
至于钱粮,实是窘迫无处。伏望圣恩悯念江淮重地,赈饥饷军皆是紧急要事,敕下户部从长议处,将余盐银十万两特发济急。其七万两补军饷之不足,其三万两以备赈济之用,则沟中之瘠获更生之望,荷戈之士奋敌忾之气,江淮阖镇军民皆歌舞圣德于无穷矣[2]。
唐顺之乞请将余盐银十万两用来济急,其中的七万两用作抗倭军饷,三万两用作赈灾之用。朝廷同意了唐顺之的请求,作出“清理盐课,赈济饥荒,其用兵钱粮,库无积贮,许于盐课内支用”[2]的答复。在此基础上,唐顺之又呈上乞剩盐的奏疏:
该臣查得各场积盐数,多只为正盐余盐正额所拘,称掣不尽,往往雨淋风销任其折耗,又只足为盐徒私贩之资。何无从权议处,每一引除正余盐之外,许带剩盐四十五斤,易米一斗五升,若掣盐二十万引,可得米三万石。稍够备赈,旋即停罢,不复再带[2]。
唐顺之见正盐余盐外所剩之盐通常被浪费,提出以每带四十五斤剩盐换米一斗五升的办法,这样每掣出正余盐二十万引,便能得米三万石。他认为这种方法“既无官给之留难,又无劝借之纷扰,况于国课商利并无亏损”[2],是快捷有效的筹集赈灾粮食之法。
2.截漕粮与起运粮折银
明代发生重大饥荒,截留漕粮进行赈济是常有之事。嘉靖二年(1523),江北灾荒,曾截留漕粮二十万石赈饥。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截留了扬州等府的起运漕粮数万,以赈淮北。唐顺之依据截留漕粮的先例,上疏请求“将起运粮米比照嘉靖二年事例,截留十数万石,委官分投赈济,其亏欠额运之数,于临、德二仓兑支运纳”[2]。他认为如果不能截留这十数万漕米的话,则“不惟饥民无路求活,加以来年春汛,官军一齐上班,米价必大腾贵”[2]。但唐顺之深知明廷财政匮乏,恐怕“十数万石”的请求会遭到拒绝,又提出可行且折中的办法:
然今方在国储缺乏之时,臣亦何敢容易开口。伏乞敕下户部,俯念民艰,从长计议,或照嘉靖三十年、三十六年事例,截留漕粮七八万石,或五六万石……但容臣暂借淮扬漕米五六万石,待臣防过春汛半年之后,收拾余银,多方籴买,还运京仓。此只迟五六万石半年之运,臣必不敢亏误[2]。
唐顺之希望朝廷能至少留下五六万石漕米,以资赈济,并计划于半年之后补还截留的漕米。此外,唐顺之还请求将江北地区需要解纳京师的起运粮折银征收。他上奏说:“乞照折兑事例,江北原额运米三十二万石,近以蒙恩折银十五万石,其余运米或尽与折银,或量折一半九万余石,则银归内帑不失原额,米留地方足支艰窘。”[2]唐顺之认为,将江北受灾地区的起运粮米折银征收,不仅可以使灾区得到急需的粮食,而且不影响明廷的财政收入,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办法。
3.物资筹备结果
唐顺之提出的这些建议,虽然未全部得到朝廷批准,但为江北地区的赈灾筹集了必要的物资,这从唐顺之与一些官员来往的书信中可见端倪,比如他在与胡宗宪的书信中提到:“江北救荒养兵之费,藏于官、藏于民者两无所处,近请余盐得七万,庙堂已为破格过厚。”[3]唐顺之请余盐银十万,明廷给予了七万。为筹备赈灾物资,他还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由于唐顺之晚年出仕与严嵩和徐阶等人的推荐有关,他与这些阁臣往来较密,其与严嵩、严世藩、徐阶等人的书信往来中皆提到江北灾情。其与徐阶的书信中称:“浙中条陈及江北请粮揭帖渎览,幸教诲而扶持之。”[1](P995)筹措物资的想法得到这些权臣的扶持,为此后赈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赈灾措施
唐顺之在江北的赈灾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赈灾组织、粮食的筹集与节约、疾病预防。唐顺之认为:“做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穷饿之甚方肯赴食,若能自营一食者,决不甘此,故荒政非一,首先此焉。”[1](P885)这三部分均围绕同一主题,即以有限之物资拯救尽可能多的灾民。
(一)赈灾组织
赈灾的机构称作“粥厂”,对于粥厂的设立,唐顺之做出规定,粥厂设在寺观、校场、马厂及各宽闲之处,并依据灾区内县的大小不同,所设立的粥厂数目也不尽相同。小县设八个粥厂,中县十二个,大县十六个,而各县不同粥厂又编成天地玄黄等不同名称。唐顺之对每个粥厂每日的用米数量也作出规定,即每厂每日用米两石左右,每锅用米七升五合,一锅可给二十五人,每日赈济两餐,为避免“冷热不等,给散不均”[1](P887)的现象,规定每个粥厂赈济的灾民数量最多不得超过五六百人。
在赈灾人员的配置上,唐顺之规定每县由一名官员负责,该官员可以选用十人共同做事,这些人员负责核实每县应设多少粥厂,以及用多少钱粮。而对于下面粥厂的负责人,则不论僧道,抑或富人长者,均可以充任。除此之外,还设置了监管机构,不仅每日所用粮米及赈济灾民的数量要登记在册,由“在官人”考查,还派遣四府的官员四处巡历,以避免贪官污吏从中克扣赈灾物资,以达到“务查奸弊,以行实惠”[1](P885)的效果,并且承诺将在事后对赈济有方的官员进行旌举。
(二)粮食的筹集与节约
由于赈灾物资的匮乏,唐顺之不得不在赈灾时继续进行粮食的筹措,为此,唐顺之作出以下规定:凡罪犯能出谷百石以上者,准其进行赎罪。唐顺之认为这样可以“失一人之不经,全百人之命”[1](P882),所得大于所失;对于自愿进行施舍的富贵人家,可以一人或两人设立一处施粥厂,并由州县长官上报给唐顺之,在事后进行表彰;对于周围没有受灾或者受灾较轻的州县,如果官员有心赈济境外的灾民,则允许其自行出资设立粥厂,事后亦行表彰。赈灾过程中粮食的筹集可由罪犯入米赎罪,或由受灾较轻的州县自愿设立粥厂,或富贵人家自愿出粮赈灾。
在赈灾粮节约方面,唐顺之认为佃户饥饿的部分原因是由田主所造成的,规定佃户应借用田主的粮食,并在有收之年进行归还,而对于富贵之家的家丁则严格监管,不准其进入粥厂混食。此外,唐顺之对进入粥厂食粥的灾民进行了严格的管控:首先是进入粥厂的灾民要按次序席地而坐,不准移动,这样就避免在同一粥厂对同一灾民重复施粥的现象;其次是严格限制进出粥厂的时间,早餐只有在辰时方可进入,巳时方能离开粥厂,晚餐也有固定的时间。由于进入粥厂的灾民既不能随意移动,也不准提前离开粥厂,而每个粥厂的施粥时间皆相同,这样就避免了饥民在不同粥厂重复食用赈济粮的现象。唐顺之认为这些使灾民受到少许拘束的规定,会大大减少那些能够吃上饭的人来粥厂混食,从而可以将有限的赈济粮节约下来以救济更多的饥民。
(三)疾病预防
对于往时的赈灾,唐顺之认为其缺点在于粥厂聚集在一起,非常容易传染瘟疫,因此,唐顺之将众多粥厂分散在各县不同地方,不仅方便灾民就近就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因人多密集接触而发生大规模的瘟疫。除此之外,唐顺之对于粥厂卫生也做了严格规定,不仅要求粥厂的粮米要淘洗干净,且用清水煮熟,并且每日的赈济粥要由管事者先吃,监管的巡视官也要验吃赈济粥,以检查赈济粥是否干净、煮熟。而对于久饥之人,唐顺之则规定一开始只准给予半碗赈济粥,以免其“乍食乍饱”[1](P888)而死亡。对于已经患有疾病的饥民则进行隔离,死人则责令地方上埋葬,避免瘟疫的发生与传染。
三、赈灾成果及意义
(一)赈灾成果
恰如唐顺之所言:“救灾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赈以粥,正欲死者得不死焉。”[1](P886)相较于嘉靖三年(1524)席书在江淮地区的赈灾,明廷不仅豁免灾地的全部赋税,并且发太仓银二十万,而此次唐顺之赈灾所请得的物资,可以明确的仅余盐银七万及部分漕粮折银征收而已。即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唐顺之的赈灾依然取得了极大成效。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是岁大侵,民无半菽,公(指唐顺之)周旋于师旅饥馑间,旦夕不懈,首捐俸金,次请余盐,请截运米,条画煮粥事甚详,民赖以存活者数百万。”[4](P173)而冯时可则称:“会江北大祲,春汛且至,先生力疾冒冰雪走海壖筹兵事,归则策荒政,留余盐截运米,捐俸设粥,活民数十万。”[1](P1075)可见,唐顺之的赈灾取得极大成效。其成果相较于嘉靖三年(1524)席书赈灾时“活民二十余万”亦不遑多让。在这种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唐顺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不能不归结于其对赈灾措施的缜密筹划及其过人的才能。
(二)赈灾对江北地区的意义
当时唐顺之面临的是旱灾与倭患的双重压力,其赈灾不仅是出于拯救民众的意愿,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防倭的考虑。唐顺之在赈灾开始前就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万一饥民啸聚,本镇西北不免盗起,东南又有倭子,则两头具动,其缓急轻重机宜,虽在临期斟酌应之,然有须当预算者。西北盗起,用何将何兵支当? 倭贼起,全靠何将何兵支当?”[1](P882)为了避免饥民转而为盗,进而影响防倭大计,唐顺之自然不能对灾民视若罔闻,而其乞余盐疏中提出,欲将十万两余盐银中的七万两用作抗倭军的军饷,三万两用来赈灾,足见唐顺之对倭患的重视。
(三)赈灾的现世意义
唐顺之在接任凤阳巡抚之前已经身患重疾,据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记载:“(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升江北都御史,代李公遂。公自浙直以劳故吐血数升,亲友方以得过家从容休卧为公幸,而春汛将至,江北适大饥,公谓吾若不速行,或告休于家,则新旧交代之期缓,交代缓则民之饿死者必众。”[1](P1044)可见,唐顺之并未因自己的病症而推卸责任,他坚持带病上任,且在江北任内“夜治文书,经理戎事,每夜至四鼓尚未就寝,子弟交谏,答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分委贤教职下村镇煮粥食饿者,捐俸禄家财助赈,矻矻不少休。”[1](P1044)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唐顺之没有为自己的身体考虑,为防倭与赈灾做出不懈的努力,终因积劳成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卒于任上。扬州百姓为感谢唐顺之,为其设立专祠,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并于民国十八年(1929)重建。“襄文之没距今三百余年,祠屡废屡修,固由功德及人之深。”[5]其在赈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贤士大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后世景仰。
四、结 语
文章主要从凤阳巡抚唐顺之所上奏疏及所发牌令着手,对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三十九年(1560)其在江北地区的赈灾事宜进行了梳理。唐顺之筹备赈灾物资的方法有乞余盐、乞剩盐、截漕粮和起运粮折银等项,在当朝权贵的支持下,最终为灾区乞得七万余盐银,并且将灾区的部分税粮折银征收,为灾荒赈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在赈灾过程中,唐顺之展现了较为高超的筹划才能,通过赈灾组织、粮食的筹集与节约、疾病预防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赈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