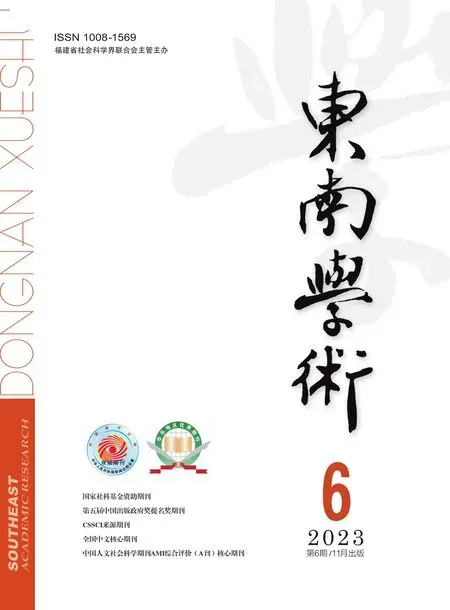哲学论笔化与论笔哲学化
——艰深晦涩,或如何阅读阿多诺
赵 勇
一
凡是读过阿多诺著作文章的人,无论他读的是德语原文、英译文还是汉译文,都会直呼其难——语言难、文笔难、阅读难、翻译难、理解难,吃透更难。 这些难加在一起,自然也就难于上青天了。 最早有此感受的或许是他的社会研究所同事马尔库塞。 一方面,马尔库塞对阿多诺赞不绝口: “我只能称他为天才,因为……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人能象他那样,同时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挥洒自如。 ……而且此公谈锋犀利,出口成章,录下即可付印。”①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周穗明、翁寒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67、77 页。另一方面,在回应 “你刚才说他是天才。 而我却读不懂他的书” (访谈者麦基的说法)时,马尔库塞却 “坦白地说,阿道尔诺(引者注:即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 。②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周穗明、翁寒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67、77 页。从此往后, “读不懂” 或 “不可译” 似乎就成为阅读和翻译阿多诺的一个重要标签。 例如,塞缪尔·韦伯是把阿多诺著作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他先把《棱镜》的 “译者前言” 取名为《译不可译之书》(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亦可意译为《天书的移译》),然后指出: “如果阿多诺是完全可译的,那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正是由于他的不可译性。 从头至尾,塑造阿多诺句子、格言、论笔、著作的东西是那种无解的张力,它源于并见证了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意义之间和谐结合的不可能,……阿多诺的不可译性是他最深刻、最残酷的真理。”③Samuel M.Weber,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Theodor W.Adorno,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81,pp.14-15,11.这很可能是阿多诺 “不可译” 的最早说法,而更有名的说法或许是来自于《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E.B.阿什顿,他在《译者说明》中开宗明义道:
首先我得承认,这本书使我违反了我认为哲学翻译者须遵循的 “头号” 规则:在你自认为弄懂作者的每句话,尤其是每个词的意思之后再去翻译。 我是不知不觉走到这一步的。我曾读过这本书的德文版,虽然读得不太认真,但对它的论题绝非毫无把握。 我清楚地记得它在精美散文(polished prose)中传达的主旨,而且似乎是很容易翻译的。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不仅是因为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大部分哲学词汇都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做主干,而且在英语和德语中也完全相同。 他的句法几乎不需要像康德以来的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弄清理顺;他不像他们那样沉迷于造词;而且他使用的新词也很少借自于英语。
翻译之初,让我不时感到纳闷的是:后面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 而其他读者也说体会相同,可阿多诺在其序言中承诺,起初看起来令人费解之处稍后会得以澄清。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误译其语句。 他的句子很清楚,词汇(也就是他自己的词汇;对于他对别人词汇的讨论则另当别论)也毫不含糊,其英文对应词则毋庸置疑。 我步履维艰,继续前行,完全忽略了我的 “头号” 规则。
但不解之谜却堆积如山。 我发现自己虽然翻译了整个书稿,却没有看出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论据导向结论的。 我准备把此书视为不可译之作——对我来说,至少是如此——这使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位译者的故事:他受托翻译一本书,当他被问及是否有机会读过这本书时,他答曰: “我没读,我译了。”④E.B.Ashton, “Translator’s Note” in Theodor 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4,p.ix.中译文参见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英译者按语》,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 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其一,阿什顿把《否定的辩证法》看成 “精美散文” ,很容易令人想起塞缪尔·韦伯对阿多诺文章的类似说法——哲学散文(philosophical prose),⑤Samuel M.Weber,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Theodor W.Adorno,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81,pp.14-15,11.这很可能是英语世界对其文体属性的最早定位。 其二,阿什顿对阿多诺之难、之困惑、之不可译的坦诚之言,以及 “我没读,我译了” 之类的调侃之词,可谓道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译者的心声,因为笔者在翻译阿多诺时也常常大惑不解: “后面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 而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译事之难超乎想象,甚至连曹卫东都萌生了远离阿多诺的退意。 他说:
由于阿多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一贯主张 “小品文” (Essay)的写作方法,加上许多著作或是断片之作或是未竟之作,使他成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艰涩的一位,给读者、特别是非德语语境的读者带来了重重的阅读障碍。 据说,德国有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可翻译的,一个是本雅明,再一个就是阿多诺。 而阿多诺尤以为甚,他一生坚持用德语写作,即便是流亡美国期间,也断然拒绝用英文写作。 在西方,阿多诺成了不可翻译的代名词。 出于尝试,我和友人曾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辩证法》。 虽然经过认真准备,还得到了许多德国专家的大力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小心加谨慎,然而,译本终究还是留下许多的遗憾,让我切身体会了阿多诺的不可译。 从此,我决计轻易不再去翻译阿多诺。①曹卫东:《人书情未了》,《读书》2005 年第5 期。
曹卫东好像已说到做到,因为虽然阿多诺的译著后来不断问世,随着阿氏著作进入公版期,翻译其书也几成理论界盛事,但我们似乎再也没有见到曹卫东的身影。 然而,他的学生辈的学者却不得不与阿多诺较劲,只是较劲的结果同样是创伤满满,因为阿多诺 “太难” 。 例如,姚云帆就曾说过: “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我基本不愿意阅读阿多诺的著作,因为太难了。 这个难度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还有其语言的艰难。 我的同事、华东师范大学黄金城教授已经苦译阿多诺《审美理论》数年,对他繁难诘屈的德语啧啧抱怨,但‘爱之深,怨之切’,越抱怨越不肯撒手。 我的朋友胡春春博士德语极好,他也认为阿多诺的德语极为晦涩,胡博士约略言道,阿多诺不仅在写作中应用这种艰深准确的风格,而且在公开讲演中也使用这种风格,以至于听众只有在其最后一个动词说出时,才能听懂他的长句。”②姚云帆:《姚云帆读〈新音乐的哲学〉︱辩证的音乐史和新音乐的辩证法》,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 年5 月10 日,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16172。这是笔者看到的年轻一代国内学者关于阿多诺之难的明确说法。 而且笔者可以预言,以后只要依然有愿意与阿多诺较劲者,这种 “读不懂” 和 “不可译” 之难就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但是,为什么就 “读不懂” 和 “不可译” 呢? 阿多诺之难究竟应该从何说起?
二
首先当然是思想之难,但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需要花相当大的篇幅。 为集中论题,本文将主要讨论其文笔/文体/文风之难。 这很可能是让所有阿多诺的读者都大挠其头的最大难点。
如前所述,当韦伯与阿什顿把阿多诺的著作文章看作 “哲学散文” 或 “精美散文” 时,这种定位虽有其道理,但并不十分准确。 其实,早在1931 年阿多诺发表就职演讲时,他就曾树雄心、立壮志,要 “把第一哲学转换成哲学论笔体(philosophischer Essayismus)” 。③Theodor W.Adorno, “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 in GesammelteSchriften: PhilosophischeFrühschriften,Bd.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3,S.343.TheAdornoReader,ed.Brian O’Connor,Oxford and Malden,M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37.于是论笔便成为他后来精心打造的文章体制,论笔体也成为他孜孜以求的文体风格。 但为什么阿多诺要如此行事? 这又需要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的随笔文体首先由蒙田开创,根据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词源学梳理,随笔(un essai)作为一个名词, “原义为实验、试验、检验、试用、考验、分析、尝试等,转义为短评、评论、论文、随笔、漫笔、小品文等” 。 而蒙田把其著作取名为《随笔集》(Essais),则有深意存焉。 接着,随着《随笔集》被翻译出去,在他国开花结果者渐多,于是便有了培根开创的英国随笔传统,也有了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传统。 后来,由于随笔中 “论” 的因素开始增多,其内容尽管严肃甚至可能枯燥, “而其文体则都是灵活雅洁、引人入胜的,毫无高头讲章、正襟危坐的酸腐之气。 18 世纪的思想家狄德罗说:‘我喜欢随笔更甚于论文,在随笔中,作者给我某些几乎是孤立的天才的思想,而在论文中,这些珍贵的萌芽被一大堆老生常谈闷死了。’生动灵活与枯燥烦闷,这是我们在随笔与论文的对比中经常见到的现象” 。 于是斯塔罗宾斯基如此定义随笔: “随笔,既是一种新事物,同时又是一种论文,一种推理,可能是片面的,但是推到了极致,尽管过去它有一种贬义的内涵,例如肤浅、业余等,不过这并不使蒙田感到扫兴。 ……这是一种既谦虚谨慎又雄心勃勃的文学体裁。”①郭宏安著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一书,其中第八章是《让·斯塔罗宾斯基论 “随笔” 》,以上所引便出自该书该章。 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6、288、290 页。
如此看来,试验应该是随笔的基本含义,而灵动则是随笔文体的基本特征。 也正因此,朱光潜认为 “essay” 译作 “小品文” 并不能曲尽其妙, “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试笔’,凡是一时兴到,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叫做‘试笔’。 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 中文的‘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 。②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朱光潜全集》第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428 页。而验之于蒙田之写作,其随笔确实名符其实,因为他是在 “用他的手、用他的感觉来试验‘世界’” 。 而 “‘用手思想’是他的格言,永远要把‘沉思’生活和‘塑造’生活结合起来” 则是其信条。③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292-293、295 页。正是基于这种信条和格言,他才把《随笔集》 “试验” 得活色生香:
《随笔集》凡三卷,107 篇,长短不一,长可十万言,短则千把字。 内容包罗万象,理、事、情俱备,大至社会人生,小则草木鱼虫,远至新大陆,近则小书房,但无处不有 “我” 在;写法上是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但无处不流露出我的 “真性情” 。那是一种真正的谈话,娓娓然,侃侃然,俨然一博览群书又谈锋极健的人与你促膝闲话,作竟日谈,有时话是长了点,扯得远了点,但绝不枯燥,绝不谋财害命般地浪费你的时间。 就是在这种如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蒙田谈自己,谈他人,谈社会,谈历史,谈政治,谈思想,谈宗教,谈教育,谈友谊,谈爱情,谈有关人类的一切,表现出一个关心世事的隐逸之士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忧虑和思考。 所以,让·斯塔罗宾斯基说: “在蒙田的随笔中,内在思考的演练和外在真实的审察是不可分割的。 在接触到重大的道德问题、聆听经典作家的警句、面对现时世界的分裂之后,在试图与人沟通他的思索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与他的书是共存的,他给予他自己一种间接的表现,这只需要补充和丰富: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④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292-293、295 页。
这是郭宏安对《随笔集》的概括。 它既涉及内容,也涉及形式(写法),可谓提纲挈领,全面细致,笔者已无须再画蛇添足。 而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大谈蒙田,是因为只有了解了随笔始祖的文章做法,才能够意识到阿多诺所谈的论笔和他亲自实践的论笔与这一法国传统有何异同。 大体而言,其相同者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如前所述,蒙田的随笔是在做试验,阿多诺对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说过: “Versuch(尝试或论笔)这个词语,其中思想乌托邦的中的之处,关联着它自身的易错性意识与临时性特征。 ……Versuch 并非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是具有一种意欲在暗中摸索的特征。”①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为了强化这一点,傲慢的阿多诺不惜引用其后学马克斯·本泽之言,甚至对其论述视同己出: “论笔把自己与学术论文区分开来。 用论笔体写作者其实是一个进行实验的创作者,他把写作对象颠来倒去,质询它、感受它、测试它、彻底反思它、从不同的角度攻击它,用其心灵之眼搜集他之所见,然后在写作过程创造的条件下,把写作对象让他看到的东西诉诸于笔端。”②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第二,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蒙田所创造的随笔是 “一种既谦虚谨慎又雄心勃勃的文学体裁” 。③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290、285-286 页。阿多诺对此也有同感,因为他引卢卡奇的话说:当蒙田把其作品命名为 “随笔” 时, “这个词易解好懂的谦卑背后是一种高傲的骑士风度” 。④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第三,在蒙田那里, “信马由缰,汪洋恣肆” 是其主打风格,阿多诺也非常欣赏随笔的这种洒脱: “于论笔而言,运气与游戏至关重要。 它并非从亚当与夏娃那里起步,而是始于它想谈论的问题;它在灵光乍现时开始言说,在无话可说时骏马收缰,而并非完全穷尽其所谈主题。 因此,论笔被归类为瞎胡闹。”⑤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第四,斯塔罗宾斯基琢磨了一番蒙田后指出, “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 , “其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 。⑥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290、285-286 页。阿多诺则断言: “论笔在德国遇阻,是因为它唤醒了精神自由。”⑦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而追求精神自由,应该是阿多诺赋予论笔的最重要品质。 以上所及,都意味着阿多诺的论笔与蒙田随笔的法国传统是一奶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姊妹文体。 因此,于阿多诺而言,他之经营论笔绝不是白手起家,因为在他之前已站着无数随笔高手、论笔达人,他们都是阿多诺追模的榜样。
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阿多诺所谓论笔的与众不同之处。 据马克斯·本泽梳理,论笔的德国传统始于莱布尼茨,后途经莱辛、赫尔德、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狄尔泰、尼采,以及西班牙出生的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人发展壮大。⑧Max Bense, “On the Essay and Its Prose” ,trans.Eugene Sampson,in eds.Carl H.Klaus and Ned Stuckey-French,Essayistson theEssay: MontaignetoOurTime,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2,pp.72-73.在德国传统中,阿多诺的论笔观及其论笔实践究竟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但至少,尼采的论说与格言体对阿多诺影响不小。 而在同代人中,与阿多诺私交甚笃的本雅明则无疑让他深受启发,因为在专论本雅明的文章中,阿多诺特别梳理和分析了本雅明的论笔与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之断片形式的内在关联,⑨Theodor W.Adorno, “Introduction to Benjamin’s Schriften” in NotestoLiterature,Volume Two,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222-223.并如此夸赞道: “论笔作为一种形式,在于能够把历史要素、客观精神的显现、‘文化’仿佛看成是自然的。 就此能力而言,本雅明出类拔萃,世人无出其右。”○10Theodor W.Adorno, “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 in Prisms,pp.232-233.于是前有尼采,后有本雅明,他们的论笔理念和为文风格都让阿多诺获益匪浅。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阿多诺的论笔体和论笔观呢?
三
首先,阿多诺变原先的叙论结合为一论到底。 无论是蒙田开创的法国传统还是培根开创的英国传统,叙论结合都是随笔展开的操作手法。 “我属于最不会悲伤的人了,尽管大家众口一词都对这种感情格外垂青,我既不喜欢也不推崇。”①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 卷,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4 页。这是蒙田随笔《论悲伤》的开头句,也是其行文运笔的主打写法:拿 “我” 说事,先 “叙” 我之经验、观察、情感等,然后带出所 “论” 之题、所 “议” 之事,由此展开叙与论的互动和碰撞,直到撞出火花,碰出哲理警句方才罢休。 职是之故,只论不叙应该是早期随笔的一大忌讳。 盖因如此,厨川白村才说: “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 他甚至如此归纳随笔做法: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 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 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采,浓厚地表现出来。 ……有一个学者,所以,评这文体,说,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诗,行以散文的东西。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者,就无聊。 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②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3-114 页。
如此看来,这种随笔是 “有我” 的随笔,是有所叙之 “琐事” 的随笔,是不让人读起来 “头痛” 的随笔,所谓事、情、理缺一不可。 然而随笔发展下来并没有循此规矩,一往无前,而是所 “论” 增多,渐成主流。 斯塔罗宾斯基指出,1688 年,哲学家洛克发表《论人类的理解力》,这个 “‘论’字就是用的essay(随笔)” 一词。 这意味着随笔文体已非蒙田那种 “冲动随意的散文” ,而是要 “谈论一种新的思想” ,对所论问题有独特阐释。 此后伏尔泰发表历史著作《论风俗》(1756),柏格森命名其哲学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 “论” 字用的都是 “essai” 。③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288 页。而到阿多诺发表《论音乐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1938)时,此 “论” 虽然没用 “essay” ,但这是典型的论笔体文章,而全篇那种密集高能的论述既让人胆寒也让人头痛。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在本雅明那里, “论” 还有 “叙” 相伴而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便是这种写法;那么,到阿多诺这里,他已经冗繁削尽留清瘦,把 “论” 提升到几近完美的高度,也推进到相当恐怖的程度。 于是阿氏论笔已入 “无我” 之境(除非像《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这种具有自叙传色彩的论笔,才可以看到第一人称行文),它既不叙事也不抒情,而是专门用来发议论的。 昆德拉说: “小说家有三种基本可能性: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5 页。套用此论,我们也可以说,阿多诺写论笔如同穆齐尔写小说,他绝不会 “讲述” 和 “描写” 事物,而是不但要 “思考” 事物,还要把它 “思考” 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因为他说过: “论笔也悬置了传统的方法概念。 思想的深度取决于它穿透事物的深度,而不在于它把事物还原成别的东西的程度。 ……它在自由选中的对象中与种种事物狭路相逢,又在自由关联中对它们展开思考。”①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正是基于如上原因,笔者才把阿多诺的这一脉随笔称为 “论笔” ,以与蒙田等人的随笔相区分。
其次,阿多诺变原来的随笔文学化为论笔哲学化。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说法,随笔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正规随笔(formal essay) “不大受个人情感影响,作者以权威或至少是博学之士的身份书写,条理清楚、层层深入地阐述论点” ;而在非正规随笔(informal essay)——亦称家常散文(familiar essay)和私人化随笔(personal essay)——中, “作者则用亲近于读者的语调,内容常常涉及生活琐事而非公共事务或专业论题,行文活泼自如,观点直截了当,而且有时也饶有风趣” 。②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7 版)(中英对照)》,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4-165 页。 根据原文有修订。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端于蒙田的随笔虽在欧美文坛迁流曼衍,呈复杂歧异之貌,但大体演变成体式不同的两支: “一支主要由法、德随笔作家所发展,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严肃深刻的议论体的论文、论著,笔者称之论议体随笔;一支主要由英、美随笔作家所承接,记述身边琐事,笔调风趣活泼的絮语体随笔。 这两支都可以在蒙田的《随笔集》中寻觅到自身的艺术质素与审美基因。”③庄萱:《周作人借鉴西方Essai 的考古探源与历史审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 期。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艾氏所说的 “正规随笔” 和 “非正规随笔” ,还是国内学者所区分的 “论议体随笔” 和 “絮语体随笔” ,它们都与蒙田开创的传统有关。 而很显然, “非正规随笔” 或 “絮语体随笔” 更具有文学性,它们就是周作人所说的 “美文” 。④参见周作人:《美文》,张俊才等选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 页。
阿多诺并非不知道随笔文学化的历史沿革和文人传统,因为当他对本雅明的论笔赞赏有加时,他其实是把后者看成一个 “文人” 或 “作家” 的。⑤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而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定位本氏论笔,它虽然也是 “论议体随笔” ,但其中的文学性显然不可低估。 只不过与英美那种风趣幽默相比,本雅明的文学性是诉诸理性也形成理趣的文学性,是借助他所说的 “文学蒙太奇” 制造出一种特殊审美效果的文学性,是像弗·施莱格尔那样定位所谓 “断片” 的那种文学性: “一条断片必须宛如一部小型的艺术作品,同周围的世界完全隔绝,而在自身中尽善尽美,就像一只刺猬一样。”⑥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86 页。 此处采用的译文见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 页。然而,尽管本雅明的论笔体让阿多诺心醉神迷,但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向本雅明看齐,而是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论笔哲学化之路。 对于阿多诺来说,如此行事自然也不难理解。 因为他首先是哲学界人士,而所有的哲学训练必然让他的关注重心首先面向哲学,更何况他在 “新手上路” 时还立下了 “把第一哲学转换成哲学论笔体” 的宏愿。 另一方面,阿多诺毕生致力于打造的是 “非同一性” 哲学,是面向漏过概念之网的事物的哲学,是反抗着短暂性亦即 “瞬息万变和转瞬即逝者不配被哲学谈论” 的哲学。 而既然这种哲学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那么,只有找到与这种哲学内容相关的成龙配套的形式,才能成就其伟业。由于论笔既可以 “无法而法地行进” ,又可以 “通过避免把自己简化为任何一种原理,通过针对整体而去强调部分,通过其碎片化的特征” 而呈现出一种 “非同一性意识” ,⑦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所以,论笔简直就是为阿多诺的 “非同一性” 哲学量身定做的哲学形式。 这样,在阿多诺手中,把论笔哲学化同时把哲学论笔化,也就变得在所难免。
最后,阿多诺变原来随笔的清晰明白为论笔的晦涩含混。 在阿多诺之前,无论是 “正规随笔” 还是 “非正规随笔” ,把它写得清晰明白,恐怕是所有随笔作者自觉的追求。 蒙田说: “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骄傲地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饱满时,它们开始谦虚,垂下麦芒。”①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 卷,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 页。这话说得何其清澈见底。 培根说: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 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②培根:《谈读书》,王佐良译,《王佐良全集》第9 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0 页。这话又说得何其通俗明白。而蒙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告诉读者: “我愿意大家看到的是处于日常自然状态的蒙田,朴实无华,不耍心计。”③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 卷,第38 页。于是郭宏安指出: “蒙田的思想是‘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清晰、透彻,以个人经验为源泉,以古希腊哲学为乳汁,转益多师,不宗一派,表现出摆脱束缚、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自由精神,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萌发作了准备。”④郭宏安:《重建阅读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 页。
由此反观阿多诺,我们或许就会觉得他的论笔体与论笔观是有意要与蒙田开创的随笔传统分庭抗礼:蒙田追求清晰,阿多诺希望晦涩;蒙田旨在通俗浅易,仿佛要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李忱《吊白居易》),阿多诺则志在高深复杂,其文如同李商隐的 “无题” 诗,既让人觉得美轮美奂,又使人感到朦胧难解。 因为后者指出,论笔所要挑战的恰恰是 “清楚明晰的感知和不容置疑的确定性” ,是笛卡尔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和最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仿佛一步一步地)上升到较为复杂的认识。” 论笔与这种规则可谓势不两立: “因为论笔始于最复杂的东西,而并非从最简单和已熟悉的东西开始。” “论笔所要求的在于,人们从一开始就要像事物本身那样去复杂地思考问题” ,从而把 “‘可理解性’(Verständlichkeit/comprehensibility)的陈词滥调” 抛在脑后。⑤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而当阿多诺认为,对于研习哲学者而言,作为形式的论笔才是上佳的入门指南时,斯图亚特·霍尔那个 “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 或许能为他提供一些佐证: “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⑥黄卓越、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90-91 页。这就是说,人只有击退理论才能拥有理论,只有面对烧脑的东西才能够开脑。 因此,阿多诺不让你走很容易的阳关道登堂入室,而是让你过高难度的论笔独木桥一步到位,实际上是在教你取法乎上。
在此语境下,我们便可以对阿多诺使用的 “亚历山大风格” (Alexandrinismus)概念略作分析。 在《论笔即形式》中,阿多诺突然撂出一句让人困惑的句子: “论笔的亚历山大风格所回应的事实是,正是依靠丁香花与夜莺这样的存在——无论在哪里,普遍之网还没有把它们赶尽杀绝——才让我们相信生命依然充满活力。”⑦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那么何谓亚历山大风格? 为什么阿多诺在这里要扯出亚历山大风格? 其实在谈论《浮士德》时,阿多诺就曾把亚历山大风格定义为 “沉浸在传统文本中的阐释” 。⑧Theodor W.Adorno, “On the Final Scene of Faust” in NotestoLiterature,Volume One,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111.如果再联想到他对本雅明的解读,问题似乎已不难理解。因为在阿多诺看来,本雅明的 “‘论笔体’就是要像对待神圣文本那样对待世俗文本” ,而同时,由于他 “坚决保持自己的亚历山大风格,从而激起了所有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 ,①Theodor W.Adorno, “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 in Prisms,pp.233-234.所以在阿多诺这里,亚历山大风格就是一种阐释,尤其是像本雅明对待悲悼剧文本那样的阐释:先是沉潜把玩,然后开掘出某种让人震惊的意义。
然而,在更通常的解释中, “亚历山大风格” 则是指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公元前323—前30)的作家们形成的一种诗风、文风和理论,其特点是高度藻饰、华丽晦涩。 这种风格在挽歌、讽刺短诗、小型史诗、抒情诗等文体中均有体现,甚至冒险进入到了戏剧文体之中。 于是我们不妨大胆猜测,阿多诺启用 “亚历山大风格” 既赋予其新意,也一语双关,是在为一种华丽晦涩的文风委婉辩护,因为本雅明谈及悲悼剧时曾涉及 “亚历山大诗体” 的语言风格,认为它虽 “晦暗费解” ,却 “反而会增强其权威” 。②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55 页。而实际上,本雅明的 “论笔体” (如《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也是晦涩费解的,阿多诺的 “论笔体”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阿多诺拿丁香花与夜莺作比,既是在说这种阐释活力无限,也应该是在说这种文风硕果犹存。 也许,只有如此一石二鸟之后,我们对 “亚历山大风格” 的理解才不至于被阿多诺完全带偏。
四
据说流亡美国后,阿多诺准备在美国某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却被要求写一 “内容提要” 。 阿多诺立刻就炸了,他愤怒地大喊大叫: “我的文章和音乐一样构造精密。 音乐能写提要吗?”③三岛宪一:《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贾倞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92 页。这则逸闻初看仿佛笑话,仔细琢磨却隐含着某种深意:按照学术规范,论文是必须提供摘要也是可以提供摘要的,但论笔能提供摘要吗? 笔者自己的感受或许能说明一二。 译出阿多诺的文章后,笔者准备把它们拿出来发表,刊物编辑却让附上摘要和关键词,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这个摘要,笔者不得不颠来倒去,反复阅读阿多诺文章,最后使出洪荒之力,才勉强形成四五百字交差。 直到那时,笔者才明白了阿多诺怒火冲天的道理。
所以,阿多诺说自己的文章如同音乐,绝非夸张之词,而就是一个基本事实。 实际上,一些阿多诺研究专家也是如此看待阿多诺所经营的论笔的。 布克-穆斯指出: “阿多诺不是在写论笔,他是在谱写(composed)论笔,而且他是一位运用辩证法的大师(virtuoso)。 他的言辞艺术作品通过一系列辩证的反转与倒置表达了一种‘观念’。 那些句子如同音乐主题一般展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螺旋中分裂开来并自行旋转。”④Susan 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 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7,p.101.普拉斯则认为: “阿多诺的文体之所以如此令人望而生畏,是因为他的抽象具有一种作曲和音乐般的品质。 阿多诺在写作《美学理论》时声称,他的写作与荷尔德林晚期的理论文本有着密切联系,他将黑格尔视为否定性生产风格的典范。”⑤Ulrich Plass,LanguageandHistoryinTheodorW.Adorno’sNotestoLiterature,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2007,p.2.为什么说阿多诺在谱写论笔? 为什么说他的抽象如同作曲? 为什么他的句子如同音乐主题一般展开? 所有问题都需要从十二音体系说起。
众所周知,至20 世纪,传统的调性音乐已走到尽头,于是有了勋伯格对调性体系的瓦解和对无调性原则的确立。 “这种情况导致音乐技法上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传统音乐中的那种固有的持续性,动机、主题的展开,完整、延绵的旋律结构,音乐中常规的逻辑发展等等都受到剧烈的冲击和破坏,形成某种强烈的两极对照。 ……音乐语言向两个极端分化:一端是大幅度的心理震荡,另一端则是恐惧造成的呆滞。”①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410 页。有了这一重要过渡之后,勋伯格便确立了自己的十二音技法。 而按照阿多诺的看法, “不应该将十二音技法理解为像印象主义那样的一种‘作曲手法’。 所有将其当作一种作曲手法的尝试都陷入了荒唐的境地。 十二音技法其实更像是对调色板上的色彩进行排布,而不是像画作的绘制。 事实上,只有当十二个音符都已经排列好之后,作曲过程才开始。 所以,十二音技法并没有使作曲变得更简单,而是更难了” 。②特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罗逍然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71-72、73 页。同时,阿多诺认为,在具体的作曲中,勋伯格通常以四种形态来运用音列:基本音列、基本音列的倒影(亦即将音列中的每一个音程替代为相反方向的音程)、逆行(开始于音列的最后一个音,结束于单列的第一个音)、逆行的倒影。 “这四种形态各自都可以进行移调,将半音阶中十二个不同的音当作起始音,这样,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音列就有四十八种不同的形态可供选用。”③特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罗逍然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71-72、73 页。
仔细琢磨,论文写作和论笔写作确实与调性音乐和无调音乐存在着某种对位关系。 论文就像调性音乐一样,需要确立核心观点(相当于音乐主题),需要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相当于展开的旋律结构)。 这个过程需要举例,需要旁证(征引他人说法),也需要起承转合的谋篇布局(如同交响乐中的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 这种写作遵循着线性思维,依据着因果逻辑,讲究 “文章不写一句空” ,亦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而且,为清楚明白计,论文应该像艾柯所说那样,把它 “当作是给全人类看的一本书来写” , “即便论文研究的是未来主义艺术家的风格,你们也不能用未来主义风格写论文” ,因为 “写论文用的语言是元语言,是用来谈论其他语言的一种语言” 。④安伯托·艾可:《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给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建议》,倪安宇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19 年版,第216、220 页。只有如此这般之后,论文才像论文,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
但论笔可以像无调音乐一样,不按常理出牌。 因为论笔写作是 “无法而法” , “论笔内心最深处的形式法则就是离经叛道” 。⑤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那么,阿多诺的论笔体又是如何体现出无调音乐的风格呢?这里不妨举例说明。 在《文化批评与社会》的最后一段,我们看到阿多诺使用了这样一些关键词——物化、超验批判(超验方法)、一体化社会(同一性)、露天监狱、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真理之盐、大众文化、俄国人、奥斯维辛,实际上,这也正是他调色板上准备排布的色彩,是他计划作曲的基本音列。 由于在阿多诺的论笔辞典中,这些语词除 “真理之盐” 之外或是贬义词,或是只能引起人们的负面联想,所以,调色板上的色彩就基本上都是冷色调,基本音列则如同勋伯格《华沙幸存者》那样阴森、恐怖,闻者无不胆寒肝颤。 在具体论述(演奏)的过程中,阿多诺先是从批判 “传统的意识形态超验批判” 开始,引出 “物化” ,然后又把它融入正在变成 “露天监狱” 的 “黑暗的一体化社会” 中,进而提醒人们意识形态已不再是 “虚假意识” ,而就是人们生活中的 “思想体系” 。 于是,文化放弃了自己的 “真理之盐” ,变成了垃圾般的 “大众文化” ,而文化批评则发现自己 “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 。 这里有 “逆行” (物化),也有 “逆行的倒影” ( “一个社会越是总体化,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而精神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 )。 而当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警钟长鸣时,这一突兀之语仿佛天外来客,却成为此段文字(其实也是整篇文章)最刺耳的 “不协和音” 。①Theodor W.Adorn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p.33-34.但也唯其如此,它的冒犯性才无与伦比,其 “影响” 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 而当这些基本音列各司其职、旁逸侧出时,也正应了阿多诺对论笔的期待:在论笔中, “思想并非在单一的方向上踽踽独行;相反,种种契机(die Momente)像在一块地毯中那样经纬交错” 。②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笔即形式》,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
再举一例。 《介入》一文写至中部时,阿多诺忽然拎出 “苦难问题” 说事,于是有了如下论述:
我并不想缓和 “奥斯威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 这一说法,它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的冲动。 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Mortssanssépulture)中,有一个人物曾问过这样的问题: “要是有人打你,打得你都骨折了,这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 同样的问题是,当今的任何艺术是否还有存在的权利;社会本身的退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介入文学概念所代表的精神退化。 但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反驳同样也是正确的——文学必须反抗这种定论,换言之,必须证明它在奥斯威辛之后的继续存在不是向犬儒主义屈服投降。 矛盾的是文学的处境本身,而非人们对它的态度。 大量真实的苦难不允许被遗忘;帕斯卡尔的神学格言 “不应该再睡觉了” (On ne doit plus dormir)必须被世俗化。 不过这种苦难,也就是黑格尔所称的不幸意识(Bewußtsein von Nöten),在禁止艺术存在的同时也要求着艺术的继续存在;实际上也只有在现在的艺术中,苦难才依然能感受到它自己的声音,获得慰藉而没被慰藉直接背叛。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们已经遵循了这一原则。 他们作品中那种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被诋毁为形式主义的种种特征,赋予它们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而这也正是有关受害者的软弱诗歌所缺少的东西。 但是,即便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überlebendevonWarschau)也陷入了这一困境,它以自律的艺术结构去强化他律,直至变成地狱。③特奥多尔·W.阿多诺:《介入》,赵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
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一系列辩证的反转与倒置” ? 阿多诺先是引用《死无葬身之地》中的问题为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一命题辩护,然而当他指出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正确时,他用了 “aber/but” (但是),这是第一次反转。 为了让这一反转理由充分,他甚至搬出了帕斯卡尔和黑格尔的相关说法为其站台。 紧接着,又一个 “aber” (笔者译成 “不过” )不期而至,但这一 “aber” 不像是反转,而更应该是有意模糊反转(此种策略下文详述),以为前面的论述寻找根据。 正当我们为这一反转以及模糊反转拍手称道时, “aber” 又来了,于是阿多诺以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为极端例子,再度反转。 而就在这一翻一滚的螺旋递进中, “苦难问题” 这一 “音乐主题” 则伴随着 “两极并置” (juxtaposing extremes)的言说方式(音乐演进方式)徐徐展开。 在布克-穆斯看来: “‘两极并置’意味着不仅要发现对立面的相似性,还要发现现象中看似无关的元素之间的联系(‘内在逻辑’)。”④Susan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p.100.但笔者以为,发现对立面的合理性进而让并置的双方处于 “二律背反” 的矛盾结构之中,这应该才是阿多诺的主要用意。 比如,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一警句最终被阿多诺解释为一个二律背反命题,①See 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 Conceptand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0-111.便是最典型的一例。
因此,在阿多诺的表述中, “aber” 这一关联词便显得举足轻重,这一点也许他是在学黑格尔。 阿多诺曾经指出: “就像荷尔德林的抽象一样,黑格尔的风格是抽象地流动,呈现出一种音乐的品质,而这正是冷静的浪漫主义者谢林所缺少的。 有时他会在对立的小品词(antithetical particles)如‘aber’(但是)的使用中让人感觉到只是出于单纯连接目的。”②Theodor W.Adorno,Hegel: ThreeStudies,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The MIT Press,1993,pp.122-123.中译文参见阿多诺:《黑格尔三论》,谢永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94 页。而在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段文字,特别是强调了其中的一个 “aber” 之后,阿多诺接着说: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风格与惯常的哲学理解是相悖的,但他的弱点却为另一种理解铺平了道路;阅读黑格尔时,必须随着他一起记录下精神运动的曲线,用思辨之耳参与其思想的表演,就好像那是乐谱一样。”③Theodor W.Adorno,Hegel: Three Studies,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The MIT Press,1993,pp.122-123.中译文参见阿多诺:《黑格尔三论》,谢永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94 页。在这里,阿多诺一方面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看作抽象流动的音乐,只有用思辨之耳参与其中,才能获得某种真谛。 而实际上,把这种说法用到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另一方面,正如普拉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黑格尔使用 “aber” 这种对立的小品词来连接两个思想,那么实际上简单的 “und” 便可胜此任。 而黑格尔之所以如此操作,其实是要替代语言的标准使用和正确用法,强化无处不在的辩证推进的冲动。 “同样,阿多诺自己对连接词的使用也并不总是直截了当,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不乏并列、从属和对立的因素。”④Ulrich Plass,LanguageandHistoryinTheodorW.Adorno’sNotestoLiterature,p.3.这也就是说,在阿多诺那里, “aber” 不仅仅是 “但是” ,它还可能是 “与” “以及” 等。 于是,阿多诺对其思想的辩证推进除了反转、倒置、逆行之外,显然还有两极并置、二律背反乃至隔山打牛、见缝插针等修辞策略,而所有这些,既增加了语言表意的模糊性,也加大了我们理解其文意的难度。
五
理解了阿多诺的论笔具有一种无调音乐的品质,也就理解了其论笔为什么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方面如此与众不同。 若是拿小说作比,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论文如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那么阿多诺的论笔就是《尤利西斯》或《终局》之类的作品,它就是要有意制造阅读障碍,增加理解难度。 我们面对其论笔,必须像他面对贝克特的《终局》一样,排除种种障碍,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去 “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 。⑤Theodor W.Adorno, “Trying to Understand Endgame” in NotestoLiterature,Volume One,p.243.阿多诺是 “通过说出不可言说之事来反驳维特根斯坦”⑥Theodor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p.9.的,我们则需要通过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去接近阿多诺。
不过,如此一来,最后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为什么阿多诺要把他的论笔打造得如此之难呢? 他把思想搞得如此 “不可理解” 究竟意图何在? 这时候,关注一下对他知根知底的同事的说法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马尔库塞谈及阿多诺不好读、读不懂时曾提供过一条后者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 “他认为,一般的语言,一般的文章,甚至包括行文十分老练的文章,无不受到现有体制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无不反映出权力结构对个人的巨大的控制和操纵。为了逆转这个过程,你就必须在语言上也表明你是决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 所以,他就把这种决裂体现在他的句法、语法、词汇甚至标点符号中去了。 至于这样做能否被接受,我不知道。”①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77-78 页。在 “批判理论” 的总体框架下,这样的理由自然是顺理成章:当资本主义进入 “晚期” 之后,通行的语言也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 “全面管理的语言” 。 在此语境中, “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 该领域的语言是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 。 “于是,词变成老生常谈,并作为老生常谈而支配演讲和写作;因此,交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②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第78、80 页。阿多诺反其道而行之,便是在与这种 “全面管理的语言” 公开抗争。
但在笔者看来,阿多诺如此行事,或许在语言层面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众所周知,经过法西斯主义的大面积利用后,德语已被严重污染。 而这种污染也正如克莱普勒所言: “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的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③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8 页。阿多诺非常清楚德语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于是他在1951 年写出一篇英文文章:《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 此文的论述重点虽然不在语言,但他依然把法西斯领袖们归入 “口唇性格类型” (oral character type),认为他们有一种滔滔不绝和愚弄他人的冲动: “他们对拥趸们施加的著名魔咒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口头表达:语言本身缺乏其理性意义,只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那些把个人贬低为群体成员的古老退化。”④Theodor W.Adorno,TheCultureIndustry: SelectedEssaysonMassCulture,London: Routledge,1991,p.148.而在1966 年所作的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的演讲中,阿多诺则干脆列举 “坚强” (Härte)、 “坚忍不拔” (Hart-Sein)、 “办妥” (fertigmachen)等被纳粹挪用的词语,指出其背后所隐含的 “灌输纪律” “忍受痛苦” 和 “人被物化” 的语词污染现象。⑤Theodor W.Adorno, “Education After Auschwitz” in CriticalModels: InterventionsandCatchwords,trans.Henry W.Pickfor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7-199.如果联想到早在1944 年,阿多诺就谈论过大屠杀之后 “文化重建” 的艰难困顿,⑥TheodorAdorno,MinimaMoralia:ReflectionsfromDamagedLife,trans.E.F.N.Jephcott,LondonandNewYork:Verso,1991,p.55.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语言上的 “逆转” 其实便是身体力行,进行着一种 “文化重建” 的努力。 这种努力是否成功自然还可以讨论,但至少阿多诺已付诸了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阿多诺的另一位同事洛文塔尔的说法。 后者在把阿多诺形容成思想、语言层面的 “拦路虎” (skandalon)之后,语重心长地写道:
的确,阿多诺的文本是非常难读难懂的。 他从未打算让他专业领域和思想阵营的同事或他的所有读者和听众感到轻而易举。 他从不能容忍——这也是阿多诺 “拦路虎” 的另一种变体——他必须说的话应该去适应一种容易消费的模式。 相反,他对自己与其受众提出的要求只是他在生产和公认的、富有成效的想象中追求本真经验这一主题的另一种变体。 他对语言的责任感,他对单向度、无内涵、不含糊的高效语言与简化的衍生思想全方位出现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对它们没有给独特、异质、富有成效的想象和反对的声音留下空间表示出的愤怒反抗,让我想起大约一百七十年前柯勒律治写给骚塞(Robert Southey)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为他的 “晦涩” (obscurity)风格辩护,并将其与 “柔弱无骨的现代盎格鲁-高卢主义风格(Anglo- Gallican style)进行对比,后者不仅能被事先(beforehand)理解,而且摆脱了……所有书本和知识记忆的眼睛,从来不会因为事后的回忆而使心灵受到压抑,而是像普通访客那样,停留片刻,便让房间完全开放,为下一个来访者敞开了大门” 。①Coleridge to Southey,October 20,1809; in CollectedLettersofSamuelTaylorColeridge,ed.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1959),vol.3,p.790.——原注。我不知道阿多诺是否知道这封信,但我敢肯定,如果我告诉他柯勒律治对 “晦涩” 的赞扬是对语言消费主义的机智拒绝,他准会微微一笑,点头称是。②Leo Lowenthal, “Theodor W.Adorno: An Intellectual Memoir” in Martin Jay,ed.,AnUnmasteredPast: The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ofLeoLowentha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99-200.
洛文塔尔说法中的部分意思虽与马尔库塞有所重叠,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借助柯勒律治的思考,把 “晦涩” 看作对语言消费主义的机智拒绝。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太清楚大众文化有着怎样的生产套路和消费模式,也太了解 “标准化” 与 “伪个性化” 如何成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 因此,假如一个人的文章用流行语词堆砌,用通行句法呈现,用人们容易接受的结构谋篇布局,那么它就很容易滑向大众文化的怀抱,成为消费主义催生的思想快餐和学术次品。 于是,如何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分庭抗礼,很可能也成了阿多诺重点考虑的问题。 布克-穆斯指出: “阿多诺的论笔结构是商品结构的对立面。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商品的形式受抽象原则(来自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同一性(所有商品通过货币媒介相互联系)和物化(通过把物体从其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将其视为神秘崇拜的僵化物)所支配。 相比之下,阿多诺的聚阵结构(constellations)是根据差异化、非同一性和能动转换(active transformation)的原则构建起来的。”③Susan 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 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p.98.“聚阵结构” 的另一种译法是国内学界更熟悉的所谓 “星丛” 。 阿多诺非常喜欢来自本雅明的 “星丛” 和 “组合” 或 “排列” (configuration),它们不仅是一种 “突然的甚至偶然的认知形式,强调美学和认识论之间的亲和关系” ,④Ulrich Plass,LanguageandHistoryinTheodorW.Adorno’sNotestoLiterature,p.3.而且可以作用于论笔,成为其谋篇布局的基本形式。这也就是说,论笔除了向无调音乐致敬之外,还在向 “聚阵结构” 的 “排列组合” 取经,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拒绝被轻易消费。 在此意义上,论笔制造出来的 “晦涩” 效果就像什克洛夫斯基的 “奇特化手法” ,是为了使形式变得模糊,进而增加感觉的困难,延长思考的时间,是为了避免理论流畅性(theoretical fluency),⑤黄卓越、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第91 页。使其变得油光水滑。
走笔至此,我们便可以讨论一下阿多诺如此这般的利弊得失了。 而为了使讨论立竿见影,有必要引入阿多诺时常批判的萨特的观点。 当萨特着力打造其 “介入” 主张时,他极力反对的是 “由专家组成的读者群” ,因为这样一来,文学沙龙就 “变得多少有点像头衔、身分相同的人的聚会,人们在沙龙里怀着无限的敬意低声‘谈论文学’” 。⑥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集》第7 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6、289 页。为了把普罗大众变成自己的读者群,他大谈 “通俗化” 的好处,反复强调占领 “大众传播媒介” 的重要性。 于是他反复告诫其同道,一定要放下身段, “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 。⑦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集》第7 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6、289 页。“书中的思想” 是什么样子? 《存在与虚无》大概就是范本。 此书用艰深晦涩占领了思想高地,普罗大众买回它来却读不懂,只好把它当秤砣使,因为这本书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整整一公斤。①参见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57 页。“新的语言” 又是怎样的语言? 应该是清晰明白的语言,降低难度的语言,适合普罗大众阅听的语言,具体地说,就是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体表达《存在与虚无》一书核心思想的语言。 于是在文风、文体和表达问题上,萨特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写作理念落实成了一种实际的行动。
与萨特相比,阿多诺的做法恰好相反。 阿多诺结束流亡直至去世期间(1950—1969)参与过160 多次广播节目,②Henry W.Pickford, “Preface” in Theodor W.Adorno,CriticalModels: InterventionsandCatchwords,p.viii.虽然这些节目绝大多数是主题演讲,但他丝毫没有降低难度。 这种情况正如普拉斯所言:
阿多诺对一种阐释学态度深表怀疑,这种态度相信文体简洁与明晰的认知力量。难怪他被卷入 “好” 写作与 “坏” 写作的文化大战中,并作为一个自豪的 “坏” 作家公然藐视一切压力,绝不顺从一种容易被消费的风格。 ……每当阿多诺向非学界的一般公众发表演讲时,他都是照本宣科,不留任何自发推断或精简概括的余地。 只有在大学讲课期间,他才完全畅所欲言,经常即兴发挥。 阿多诺怀疑清晰是一种完美的骗局,是一种将自己与现实隔绝的方式。 完全的清晰不仅是简化的,它也等同于一个完全偏执的系统,因为它认为自己处处受到必须被消除的晦涩和含混的威胁。 “一个人不应该让自己被每一步都可以验证的清晰要求所吓倒。” 容易理解的东西在认识论上也是毫无价值的;最有可能的是,想必简单或明确的陈述将仅仅是对已知事物的重复,毫无价值的同义反复。 “只有不需要首先理解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商业发明的、真正被异化的词语,才会让他们感到熟悉。” (MM 101;GS 4:114)这里的直接观点是,日常语言是异化的语言。 而潜台词则是:哲学和诗意的语言回应了这种异化。③Ulrich Plass,LanguageandHistoryinTheodorW.Adorno’sNotestoLiterature,pp.4-5,1.
很显然,面对普罗大众,如果说萨特是致力于通俗易懂和清晰明白,那么阿多诺却在追求艰深晦涩和模棱两可。 对于前者来说,其损失必然是思想的简化,甚至使思想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对于后者而言,这样做尽管保持了思想的整全和尊严,但思想往往只能成为孤芳自赏之物,成为仅仅在少数专家学者之间秘密旅行的密码式话语,成为阿多诺所说的 “漂流瓶” ,却无法延伸到广大受众那里。 阿多诺曾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表达讥之为 “本真性的黑话” ,但他本人的表达与思想又何尝不是 “辩证法黑话” 的 “审美上演”④马蒂亚斯·本泽尔:《阿多诺的社会学》,孙斌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213 页。 译文略有改动。呢? 假如阿多诺心性散淡,觉得思想与学问就是 “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那么无论它如何高深、晦涩和小众,都问题不大。 但问题是,阿多诺素有悬壶济世之心,启蒙大众之愿。 而一旦要与大众打交道,萨特的选择很可能依然有效,因为假如不去简化思想,软化表达,大众就会被吓得逃之夭夭,致使启蒙话语全部扑空。 因此,简化与软化虽然让阿多诺看不起,却是为了让思想与表达走向大众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阿多诺论笔呈现出 “既吸引读者又排斥读者”⑤Ulrich Plass,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odor W.Adorno’s Notes to Literature,pp.4-5,1.的二律背反难题时注目停留,反思其得失,才不至于完全拜倒在其艰深晦涩的石榴裙下,一方面读得半懂不懂,另一方面高呼这个感觉好酸爽。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