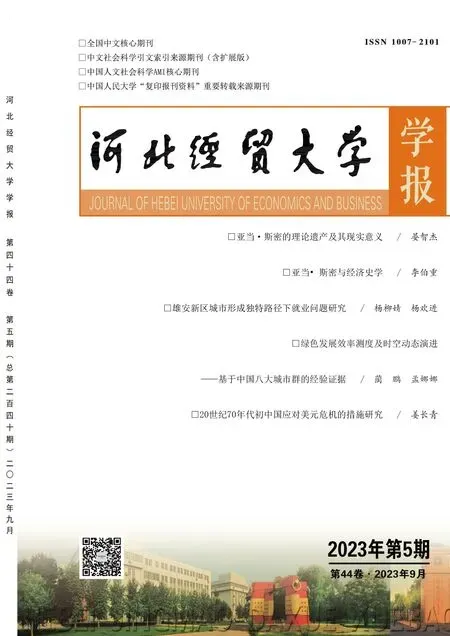亚当·斯密的理论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晏智杰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亚当·斯密(Adam Smith),生于1723年, 14岁入学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学牛津大学,25—26岁任教爱丁堡大学,27—40岁任教格拉斯哥大学,期间(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后陪贝克莱公爵游学法国,回国后历经十年(1766—1776年)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7年任职苏格兰海关专员,1787年秋受聘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病逝于1790年,享年67岁。亚当·斯密逝前销毁了其全部未完成的文稿,这再次彰显了这位思想巨人的科学精神。
一、亚当·斯密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创立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体系
《国富论》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与前人相关学说相比,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在重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之后,亚当·斯密系统阐述了劳动分工论、商品交换价值论、市场供求机制论、收入分配论、资本积累论、国家财政论等,并以极大篇幅批判了重商主义,还对法国重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评论。《国富论》1776年初版,1778年二版,1784年三版,1786年四版,1789年五版,耗费了作者毕生的精力。
亚当·斯密总结了当时先进生产方式(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经验,吸收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提出了以公私利益协调论为支柱的市场经济论,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主要诉求的政策主张。这套理论和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而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内,《国富论》一直被奉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以亚当·斯密学说为旗帜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开拓了看似无限的国内外市场,在这期间虽发生多次周期性危机,但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克服。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终于走到了尽头。1929—1933年,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破产,同时也结束了斯密经济理论的支配地位,显示了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作为一种主流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亚当·斯密学说对重商主义是一种否定。凯恩斯主义又是对亚当·斯密学说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凯恩斯破除了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总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神话,认定不充分就业才是经济生活的常态。由此出发,凯恩斯构建了一整套力图提升社会总需求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尽管如此,凯恩斯所追求的仍然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市场供求均衡论,区别在于凯恩斯所论证的已经超出了所谓微观经济学范畴,他追求的是实现宏观经济的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对亚当·斯密学说核心思想、基本框架的继承和发展。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到此终止,凯恩斯主义因为不能应对新的挑战而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批判,即所谓反凯恩斯革命,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融为一体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和趋势。
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硬核”:一方面,切不可将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定于一尊,事实上它只是近现代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是极其重要的阶段,但它毕竟不是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发生了这些巨大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市场经济学说的核心不仅没有被否定,反而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被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了。我们不能不深刻地理解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硬核”,即关于市场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使公私利益得以协调的制度的观点。至于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形成这一“硬核”,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与人类特有的“交换倾向”密不可分,而这种倾向又同人的本性结合在一起。不难理解,如果一种经济制度能够这样紧密地同人的本性结为一体,其生命力当然也就与人同在了。
我们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前无古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其社会经济制度来说,我们所期待和要求的是什么?笔者以为,仍然离不开构建一个公私利益相协调的机制,而实现这种协调机制的最佳制度则是市场经济制度,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和服务功能。为什么市场经济是实施公私利益协调的机制,其历史及逻辑理由早已包含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论中,其真理性也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经济学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二、亚当·斯密对人类文明的另一重大贡献:《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倡导和遵循怎样的道德规范。面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社会现实,面对各种思想和倾向并存的混乱局面,亚当·斯密以其坚定的立场、敏锐的观察、深邃的思考、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证,摈弃了貌似高尚的单纯利他主义传统说教,鞭挞了极端利己主义歪风,树立了构成其道德情操论基础的“合宜美德论”。
《道德情操论》对各种流行美德论进行了评论。亚当·斯密认为奉行“谨慎”为美德固然没有错,但它很不够。美德不仅在于谨慎小心,还应当包括适宜的进取精神等。他认为“仁慈”固然高尚,但不够全面,也不现实。亚当·斯密说,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他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孟德维尔的“个人劣行即是公共利益”观点,斥之为“放荡不羁的体系”,认为其完全抹去了言行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危害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行径大开方便之门,十分有害。亚当·斯密认为前人提出的合宜美德论是对的,应该推崇那些高尚的、庄重的和令人尊敬的美德,自我控制和自我克制的美德(坚忍不拔,宽宏大量,不为钱财所左右,轻视痛苦、贫穷、流放和死亡等这种肉体上的不幸),但还要肯定和蔼可亲、温和、仁爱。亚当·斯密不赞同斯多葛学派所鼓吹的宿命论,更不愿意肯定该学派所说的心甘情愿去死的说教(上天要你死,你就觉得自己该死,并为此感到幸福)。他认为这是对美德的亵渎。
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自己的合宜美德论。他认为所谓美德,既不应是绝对利他,更不应是极端利己,而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种结合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表现就是“合宜性”。它表现为当事者的感情或感受与旁观者一致;或者指有关各方感情和行为的和谐一致。这个所谓旁观者不仅是指外在的实际存在的旁观者,它还可以指自己心中想象中的旁观者。这种美德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和谐:当事人与旁观者感觉的和谐,个人与集体感觉的和谐,个人情感与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和谐,还有个人自己言论和行为的和谐等。这是亚当·斯密合宜道德观的核心。
关于美德的确立及其内涵。在有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别人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是否一致来判断是否合乎美德,美德就存在于当事人的感情和旁观者的感情和谐一致。它的表现形式是:和蔼可亲和令人尊敬,仁慈和正义;正义比仁慈更重要。在没有旁观者情况下,通过自己心中那个“公正的法官”,即设想中的旁观者的感受来确定自己的言行举止。在这种情况下确立的个人美德,首先是“有良心”,其次是“有责任感”。有良心,表现在“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包括见义勇为和为国捐躯”,还表现在谦虚谨慎和对自己感情的自我控制。有责任感,即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它应当体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等。
为什么合宜美德论是正确的,亚当·斯密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必须适应生长的那种环境。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市场经济本身在亚当·斯密看来就是对公私利益的协调与结合。第二,合乎人的本性,即合理利己和高尚利他的结合。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一个具有完美德性的人。这种原始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在日后生活成长过程中逐渐养成和不断充实提高的。
笔者认为,这种基于人的本性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美德论,首先,既体现了对个人合理要求的尊重,又树立了为国为民的高尚目标,代表着一种既切合实际又保持先进的精神追求,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其次,亚当·斯密将其道德伦理观置于感觉论的基础上,而与强调实践作用的理论相背离。这种倾向在当时就受到理性主义伦理学家托马斯·里德的尖锐批判。最后,如果同欧洲大陆的以宣扬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运动相比,苏格兰伦理学家们学说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我们知道,对经由1688年资产阶级和贵族相妥协的“光荣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亚当·斯密是拥护的。
在笔者看来,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对我们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尽管国情世情大不相同,其内涵也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相互促进;又如,既尊重合理个人利益和诉求,又强调服从集体和国家需要,力求实现两者相结合;再如,既坚决批判极端利己主义歪风,又坚决摈弃脱离实际的空洞的利他主义说教;等等。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立足点应该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其经济学基础应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体现的公私利益协调论。
三、亚当·斯密的人性论值得肯定:兼论“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指,《道德情操论》塑造的是利他主义道德人,而《国富论》塑造的是利己主义经济人。这其实是对斯密思想的误解。的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论述的起点不大相同,前者是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而后者则从商品交易是交换双方追求个人利益入手的。然而,在两书后来的全面论述中,所体现和贯穿的都是其完整的人性论。其核心是说,人的本性既不是单纯利己,也不是完全利他,而是合理利己和高尚利他的结合。
正是这种人性论构成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共同基础,贯穿在其市场经济观和道德情操观之中。如上所说,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就在于它是一种能使公私利益相协调和统一的机制;我们又看到,合宜美德论之所以可取,也在于它符合使个人与他人的感觉(利益)协调统一的要求。换句话说,它们都体现或实现了合理利己与高尚利他相结合的人性。不仅要认同亚当·斯密的人性论,还要认同它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共同基础,才能深刻把握两书的统一性。离开这一点,极易在理论与实践上导致有害的后果。
《国富论》与人性论。进一步说,构成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共同基础的人性论,还体现在他对经济所有权、经济运作方式、收入分配以及道德规范的统一理解之中。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他所揭示的生产、交换和收入分配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他所揭示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而然”的。所谓“自然而然”,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是合乎客观规律,而合乎客观规律必然合乎人性,客观规律性和人性在亚当·斯密学说中高度统一起来了。
亚当·斯密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1]亚当·斯密对资本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更是无以复加。在他看来,除了劳动以外,资本就是增进财富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了,资本数量、投资的顺序、投资的领域等直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财富的数量和水平。唯有土地所有权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是世袭的、垄断的,不是劳动和资本积累的成果,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同样道理,抢夺与偷窃不是人的属性。
《道德情操论》与人性论。亚当·斯密认为,将单纯的赠予奉为圭臬的仁慈,尽管高尚但并不现实;只有等价交换才是自然而然的,合乎人性的;只有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才是自然而然的,合乎人性的;而垄断,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应该尽快予以取消。亚当·斯密赞成北美殖民地独立,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
在道德领域,亚当·斯密还大力倡导自由平等,不承认任何权威,只认同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合宜”才是美德,在这个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同样,面对亚当·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学说,任何行业、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不管出身贵贱,人人平等,都得接受是否是财富创造者的检验,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标准,也是一个道德尺度。
人性论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命题。认同人性的存在,本来不是一件难事。无论就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来说,人都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区别于非人世界的本性或特性。而且,围绕人性善恶等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思想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人性本善论、人性本恶论、人性无善恶论、人性善恶相混论等,不一而足。社会生活的发展既要求在借鉴前人认识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人性的认识,同时也为这种深化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条件。
亚当·斯密思想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而,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思想和主张才真正逐渐被认识和采纳,并结合中国实际发扬光大。在当今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和谐共享的道德规范不动摇,坚持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统一不动摇,也许是我们在纪念亚当·斯密这位伟大思想家诞辰300周年之际,重温其不朽著作,从中应当汲取的最宝贵的思想营养和启示。
——评新译本格拉斯哥版《国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