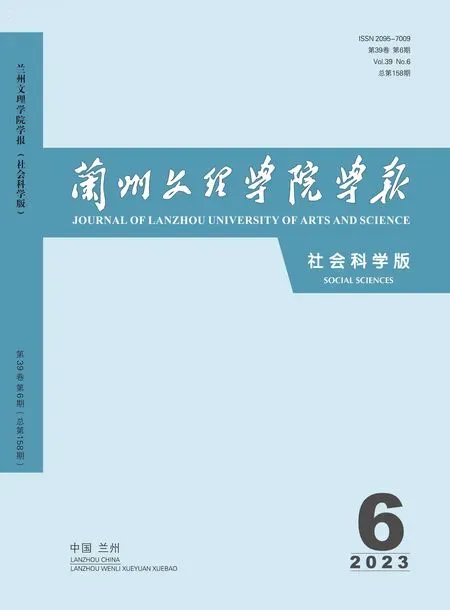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书写
——对肖江虹小说的一种解读
周 仲 谋,格桑拉姆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进入21世纪以来,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变迁的文学作品不少。肖江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作品大多从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视角,通过展示带有原始神秘色彩的地域文化、民俗景观等,折射出时代变革冲击之下、新旧思想碰撞之中的乡村社会现实。肖江虹关注底层人物或留守乡村或漂泊城市的不同命运与心路历程,他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变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迁,有着敏锐、深刻、细腻的把握和呈现。在眷恋、惋惜、希冀和淡淡哀愁的复杂情感中,传达出保留传统文化多样性的诉求,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乡村与底层人物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代性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生活形态的改变越来越明显。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1]现代性带来的变革是如此巨大和剧烈,以至于安东尼·吉登斯用“断裂”(discontinuities)一词来强调“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或那一类)特殊断裂”[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显著加快,“与之相伴的城市化进程也突飞猛进。在中东部地区,不少乡镇和农村都已被纳入了大都市的新版图。虽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中国西部的影响晚于东南部和中原地区,但在愈益发达的现代通讯、传媒、交通等的延伸和触动下,一向闭塞的西部乡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2]一方面,城市日益发达和繁荣,汇聚了大量资金,提供众多就业机会,以较高的收入报酬和物质生活条件吸引着乡村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乡村中的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涌入城市,留守村子的往往是年高力衰的老者和尚未成年的儿童。肖江虹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化进程给中国西部乡村带来的变化,把笔触对准贵州偏远地区的乡村(山村),捕捉时代变迁之下西部乡间底层人物的真实样貌,揭示其生存困境和心灵状态,颇具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肖江虹的小说以细致传神之笔,描写了社会变革中西部乡村面貌的改变。中国传统乡村往往以农耕为主业,“大多的农民聚村而居”[3],人们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村落,守着一方水土,世世代代定居下来。“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3]9传统乡村的人们基本上是“不流动”的,他们安土重迁,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形成了乡土社会的稳定结构和“熟悉”状态。然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大量乡村青壮年离开家乡,外出务工,成为漂泊城市的“流动者”,也造成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肖江虹小说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
《蛊镇》中,王昌林所在的村子,由于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山路走的人少了,两旁的刺蓬往中间长,道路越来越狭窄,渐渐就没路了。村里人太少,隔着峡谷与对面山路上的老迈行人喊几句话,都能让王昌林激动不已。小说这样写道:“那群人缓缓离去,消失在一片云雾中。王昌林伸长脖子,定定地盯着道路的尽头。他的嘴还大大张着,脸色殷红,呼吸粗壮,仿佛新婚之夜。”[4]作者以细腻的神态描写和略带夸张的语气,传神地写出了王昌林与过路行人扯着嗓子交谈后的激动心情,也反衬出平日里王昌林缺乏交谈倾诉的孤独状态。
《当大事》通过描写村中一位谭姓老者去世后留守老人们艰难筹办丧事的过程,反映出乡村被“抽走”青壮劳力后的困窘状态。“几个老者团坐在院子里,个个愁云密布,自顾把旱烟吸得滋滋乱炸。‘和埋条狗差不多了!’”[5]婚丧嫁娶本是乡村的大事,然而由于村中青壮年都外出了,留守的老人们抬不动棺材,也没力气在山上挖墓穴,只好把死者草草地掩埋在房屋旁边,整场葬礼失去了应有的礼仪和庄严。
《悬棺》中,燕子峡和曲家寨的先民们因躲避战乱而迁到此处,在悬崖上放置棺材,头朝着原来故乡的方向,表明不忘来路、终将回归故乡的决心。为了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村民们世世代代练就了攀岩绝技,爬到悬崖绝壁的燕子洞穴中掏取燕粪给庄稼施肥。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主人公“我”自幼跟随父亲练习徒手攀岩的过程:
太阳还没探头,我和来辛苦已经黏附在陡峭的刀壁崖上,如同两只壁虎。
崖下是猫跳河,早不见了秋冬的枯瘦,露出了夏日繁茂雨水后的狂暴狰狞,黄龙似的扭动着粗壮的身子咆哮远去。
我跟在来辛苦身后,浑身上下都是汗水。峡谷里头有雾,一小团一小团,像是母亲纺出的纱线,从我身边无声无息飘过。抽抽鼻子,我闻到了云雾的味道,湿湿的,带点腥味,有点像乡村饭桌上凉拌的鱼腥草[6]。
小说中的这几段语言,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写出了山崖的高、陡、险等特点,以及崖下河流的波涛汹涌、水深浪高,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村民们在艰难环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悬棺成了城里人旅游观光的景点,江流湍急的猫跳峡被打造成奇幻漂流项目,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练就的攀岩绝技,也成了吸引游客眼球的表演。但给燕子峡村民带来最大冲击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走出大山的整体搬迁。费孝通先生指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3]7尽管《悬棺》中的村民们对生活的村庄和脚下的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依赖之情,一直渴望回到原来的故乡,但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潮中,他们接受了再次举村迁移的现实。
作为一位“从小在乡村长大”“在乡村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原始构建”[7]的作家,肖江虹熟悉乡村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对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变迁和情感心理有着深刻幽微的体察。他笔下的青壮年人物,无论外出打工还是留在村里,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蛊镇》中的王四维、《傩面》中的颜素容,都是为了生计,离开村子去了城市。小说深入到乡村青壮年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情感矛盾、爱恨纠葛等抱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蛊镇》中的赵锦绣为照顾孩子细崽和生病的公公,留在了村子,与在城市打工的丈夫王四维两地分居。得知丈夫有了外遇,赵锦绣恼怒、嫉妒,悄悄给丈夫下了“情蛊”。由于长期的性压抑,赵锦绣和留在村里的瘸腿王木匠之间产生了不安分的情感骚动。当王四维的死讯传来,赵锦绣又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内陆河》中,煤厂发生事故,在厂里打工的三十几位青壮年男子全部罹难,留下一群年轻的寡妇,在漫长的岁月里苦苦煎熬。小说女主人公琼花性格沉稳内敛,对亡夫春树有着深厚感情,但在缺乏生机活力的家庭压抑氛围中,赶集成了她唯一的散心渠道。在集上认识了一个“转场汉”后,琼花死水般的心湖重新泛起了涟漪,几经情感挣扎,琼花终于鼓起勇气去追求新的爱情和幸福。肖江虹把青年女性复杂幽微的情感心理刻画得细腻婉曲,含蓄婉转,令人动容。
肖江虹小说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老年人的形象。如《百鸟朝凤》中的焦三爷、《蛊镇》中的王昌林、《傩面》中的秦安顺、《悬棺》中的来高粱等。一方面,小说把乡村老人晚年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真切地传达了出来,从老年人的视角写出了现代化进程带给乡村的变化;另一方面,肖江虹作品中的这些老年人,往往是某种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的习得者和传承者,他们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命运。与老年人相对应的是肖江虹小说中的孩童和少年人形象。如《蛊镇》中的细崽、《悬棺》中的来畏难、《百鸟朝凤》中的游天鸣等。如果说老年人形象代表着对过去、传统的留恋,作者在他们身上唱响的是一曲挽歌的话,那么肖江虹笔下的少年人形象则代表着走向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在他们身上流淌的是一曲希望之歌。
二、现代语境中的地域民俗与民间技艺
有论者指出,“肖江虹的贵州书写主要分为两个系列,即‘底层系列’和‘民俗系列’。”[8]肖江虹在描写现代进程中西部乡村的底层人物命运变迁的同时,还运用大量笔墨,对带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景观进行细腻描摹,呈现了现代语境中地域民俗与民间技艺的真实境遇。
小说《百鸟朝凤》通过讲述无双镇水庄少年游天鸣拜土庄唢呐匠焦师傅为师,学会吹奏《百鸟朝凤》成为新一代班主以及唢呐班最终解散的故事,反映了民间唢呐艺术传承的断裂及其在乡村丧葬风俗中由盛到衰的过程。小说借人物之口,表达了沉痛的惋惜之情:“我知道,唢呐已经彻底离我而去了,这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如此崇高和诗意的东西,如同伤口里奔涌而出的热血,现在,它终于流完了,淌干了。”[9]《蛊镇》中以蛊术为人治病的蛊师王昌林,在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的窘迫情形下,为了能够让蛊术传承下去,不得已为赵锦绣制作“情蛊”,以换取细崽跟随自己学制蛊的机会。但王四维的死亡、细崽的早衰与夭折,不仅让王昌林愿望破灭,也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悬棺》中,随着燕子峡、曲家寨等山村村民们的整体搬迁,原本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悬葬、攀岩等地方民俗文化,也面临即将消失的命运。《傩面》中的傩师秦安顺是傩神面具雕刻技艺及傩戏表演艺术的孤独守护者,同样找不到继承人。当秦安顺这样的老人们渐次离世,傩戏这种民间艺术和相关技艺也将成为绝响。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时代的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1]如果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外延方面的特征,那么,“去传统化”则是其内涵方面的特征,即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肖江虹笔下的唢呐、蛊术、傩戏、悬棺艺术等,既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也是原本渗透在无双镇、蛊镇、燕子峡等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容。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的、熟悉的东西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民俗传统是乡村人的精气神,在长期的发展中,已内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婚丧仪式,并体现出对乡土社会的礼法规约和协调功能,在人们心目当中原本占据重要的位置。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说,“从外表来看,仪式的繁文缛节可能显得毫无意思,其实它们可用一种对人们或许可称作‘微调’的东西的关切加以解释: 不使任何一个生灵、物品或特征遗漏掉,要使它们在某个类别系统中都占有各自的位置。”[10]小说《百鸟朝凤》中,无论是天鸣之父游本盛,还是无双镇各个村子的人们,都对唢呐艺术充满敬意,请唢呐班师傅出席红白事的仪式也颇为庄重,能够吹奏唢呐的民间艺人是受人敬仰的,尤其是吹奏《百鸟朝凤》曲子,更被视为一种荣耀,并且只有德高望重的逝者才配享用此曲。《悬棺》中,燕子峡和曲家寨世世代代的村民为生存苦练徒手攀岩绝技,唯有攀上悬崖掏得燕粪的人,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死后才会以悬葬之礼安置在悬棺之中。他们把提供肥料让庄稼增产的鹰燕看作神鸟,为保护鹰燕,定下了不许掏燕窝不许吃燕肉的规矩。《傩面》里,在秦安顺等众老者心目中,傩戏是与神灵相通的。作为傩师的秦安顺,在雕刻傩戏面具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恍惚大意,生怕刻刀错路面具走样。那些年事已高神志不清的老人们,一戴上傩戏面具,“老眼猛地一睁,刚才还混沌的眼神瞬间清澈透亮”[11],能把整出戏的唱词曲调准确无误地唱出来。上述情节和描写,都传达出民俗传统在乡间原有的尊崇地位。正如有论者所说,民俗传统“和乡村世界的道德法则相互作用,缔结为底层社会共有的秩序规约和文化心理,左右着乡民的行为边界和价值追求”[12]。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加速,不仅改变了乡村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还消解了民俗传统赖以附着的土壤,以及与其相伴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道德准则。肖江虹小说关注的重心,正是社会变迁下民俗传统文化逐渐解体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心理裂变。小说《百鸟朝凤》中,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唢呐的敬意渐渐消失了,迎接唢呐班的礼仪也没有以前庄重了,新的价值观念和娱乐需求,使唢呐艺术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日益减退了。唢呐班的成员纷纷进城讨生活,就连师傅焦三爷也成了纸箱厂的看门人。《蛊镇》中的王昌林以破坏蛊师“规矩”为代价,也没能让手艺传承下去。《悬棺》中来高粱小时候偷偷烧吃殉崖鹰燕的尸体;来向南盗取一百多个燕窝后自断左臂,离开寨子到外面打工,还带走了寨里的壮劳力。《傩面》中的年轻一代对傩戏没了敬畏之心,连刈麦时的丰收戏都不跳了;有人出售傩神面具,将其看作生意;甚至有人把傩戏说成“垂死的玩意”。上述小说中通过前后对比,既深刻地揭示了民俗传统文化的衰落,也写出了世道人心的变化。
三、是挽歌,也是安魂曲,更是希望之歌
值得关注的是创作者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肖江虹的代表性作品《百鸟朝凤》《蛊镇》《傩面》《悬棺》等,基本上都是从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视角,去看待和描述巫蛊、傩戏、悬葬等贵州地域民俗的当代境遇,以及乡土传统文化面临的命运。例如《百鸟朝凤》《悬棺》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的,《蛊镇》《傩面》虽然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作者的心灵、情感与小说主人公是紧贴在一起的,这使得肖江虹的创作明显带有眷恋、惋惜的情感色彩,也暗含着对现代性的思考。不过,肖江虹小说中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从单一到复杂的转变过程。由最初的悲怆、无奈,走向包容、和解、豁达,显得更加丰富、多元、成熟。
在早期创作的几部作品中,肖江虹对地方民俗传统的衰落,持悲观、沮丧、愤慨的态度。《百鸟朝凤》中的游天鸣,被焦三爷选为传承人,学会了吹奏《百鸟朝凤》,可是在葬礼上的关键时刻却吹不出来,把曲谱忘了。在小说情节上,这是故意为之的破绽,因为按照唢呐班惯例,演奏的前一晚都会练习,即便后来唢呐班的成员风流云散,但至少焦三爷会提前跟游天鸣说一声,让他对吹奏《百鸟朝凤》有所准备。小说中,吹不出来的《百鸟朝凤》更像作者的一个隐喻,喻示着民俗传统文化的没落。而结尾处在繁华城市中吹奏《百鸟朝凤》的乞丐,则是传统文化传承者的命运缩影,传达出作者的悲观情绪。《喊魂》中的青年农民蚂蚁在城里被打成痴呆,返乡后家里人以为他丢了魂,按照传统民俗做法为其“喊魂”,却毫无效果。小说对底层人的不幸表达了同情,也暗示出传统民俗文化面对社会变迁、城乡冲突时的无能为力。《蛊镇》中的细崽,脸上的印记与蛊镇地图形状出奇地相似,因此被王昌林选为传承者。细崽的早夭,象征着传统文化、地方民俗、民间技艺的断裂,后继无人,情感基调也是比较悲观的。对民俗传统的失落,作者流露出无限眷恋和不胜惋惜之情,上述作品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恰似一唱三叹的挽歌,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不过,在后续的创作中,作者并没有一味悲观下去,而是开始注重挖掘民俗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力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民间神秘传统固执而又孤独地延续,而日渐荒芜的乡村依然存有希望和温暖,人心中的善意、伦理和信仰构成了乡村结实的内核”[13]。这种变化在《蛊镇》中已显露端倪,王昌林用“幻蛊”让细崽临终前感受到了放风筝的欢乐,他还给自己下了一道“幻蛊”,弥留之际出现幻觉,仿佛又看到了“蛊蹈节”的盛况和成群结对返乡的青年男女,从而在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抚慰和满足。《傩面》中的秦安顺,明知时日无多,仍坚持发挥生命余热,用傩戏为乡间的逝者引路,为生者祈神还愿。面对满口脏话、渎神谩老的叛逆者颜素容,秦安顺以善良和真情待之,为她唱傩解怨延寿,逐渐感化了颜素容因重病失意而扭曲的心灵,一点点修正她失格的言行举止,让她感受到人间真情,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仰。秦安顺自己也通过傩戏,实现了与神灵、祖先、父母的沟通,获得了生命尽头的平静与安详。无论是《傩面》中的秦安顺,还是《蛊镇》中的王昌林,都把民俗传统、民间技艺融入自己的生命,化作血肉和精魂。作品似乎在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作为精神力量顽强地存续着,给人们荒芜困顿的心灵以极大安慰,发挥着类似“安魂曲”的作用。
随着作者思想的成熟,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肖江虹小说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眼光和豁达积极的态度,这使得他的创作显露出包容、和解之意,“似乎人和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完成了某种和解”[14],小说的格局、胸襟、气度也更加开阔。《悬棺》中,来高粱劝解来辛苦和村人们离开,不必守着悬棺,“棺材为啥要悬在崖上,那是祖宗们想回到故土,可他们想回去的那块土地,谁又晓得是不是真的故土”,“祖宗们背井离乡的时候,又能拿祖宗的祖宗咋办?”[6]261《蛊镇》中的王昌林也对细崽说,“哪个都说不清楚到底哪里才是老家,说不定还有老家的老家,老家的老家的老家。”[4]60这既是作者对故乡的态度,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必刻意固守,而应与时俱进,走向新生,在发展中进行传承和创新。当然,作家也写出了乡民们走向新生过程中所伴随的刻骨疼痛,以及对过去的眷恋和不舍。肖江虹的近期作品中都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寓意,例如《傩面》中秦安顺的死亡与他幻想中的出生相互映衬,《蛊镇》中王昌林在临终时看到了传统复兴的图景,《悬棺》中的来高粱从山顶跳崖落进悬棺,以独特方式为整体搬迁的村民们送别,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升华。这种死亡中蕴含着新生的表达,正是肖江虹小说对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变化着的乡村世界的诗意写照。肖江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亦是如此,或许经过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洗礼,地域民俗、民间技艺等传统文化可以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江虹小说奏响的也是希望之歌。
四、结语
肖江虹的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对以往贵州地域书写模式的刷新,而且具有社会时代的现实意义,他关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底层人物命运和传统文化变迁,切中了时代的文化症候。肖江虹努力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意义,既没有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误区,也不是在乡愁情结支配下试图重返过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把传统文化、地方民俗作为思考现代化进程的参照视角,体现出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透露出保留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他试图“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阴翳掉的部分”[15],并尝试把传统文化、地方知识的合理成分化为现代文明的有益补充,思考和探寻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和谐发展之路,这正是肖江虹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
——一个神秘部族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