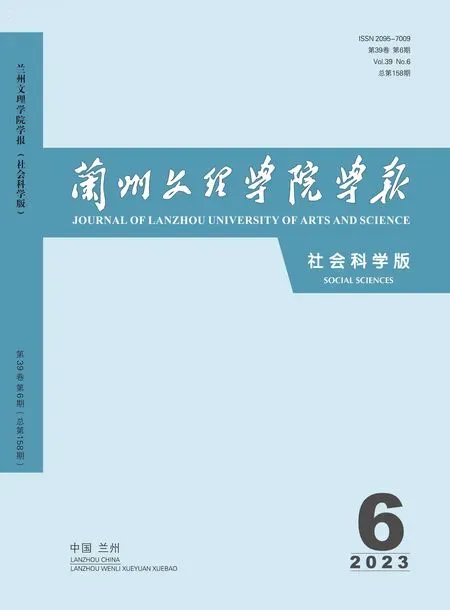晚清民国刊印新技术与《三国演义》两类新印本
许 佳 越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6)
晚清民国是对于四大名著传播影响极为重要的时期,对于《三国演义》,此一时代许多阅读见解都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评价与研究,因而,此时最为通行的刊本自然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晚清民国从西方引进了很多新的印刷技术,如石印、铅印、珂罗版、丝印、照相影印等等,这些技术影响到《三国演义》的刊行,用新技术印刷的《三国演义》刊本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特质,如石印技术以其对书画原笔迹高精度的还原使得它在印刷图像方面具有绝佳优势,从而使《三国演义》刊本中产生了一大批以多图著称的“增像本”;但随着石印本的质量与成本优势很快就由于铅印机械化的日渐成熟而渐渐消失,“新式标点”《三国演义》新需求也使得刊印的重点不再是图像,而是清晰明朗的文字与符号排版,于是这一批以“新式标点”为标签的印本已经不再使用石印,而全部改为了铅印。可以说这两类刊本是《三国演义》在晚清民国刊行中的两股风潮,而在这两股风潮下影响的印本,它们与前代版本之间又具多少联系,我们从它们的身上能看到多少清代毛评本的影子?刊本的内容又有多少是真正属于新的时代,刊印者如何用旧的小说《三国演义》来传递此时新的思想?这又需进一步分析。
一、石印与“绘图增像”
提到晚清绣像本《三国演义》,我们总先想到点石斋1882年石印本《三国志全图演义》,因它是可见最早完全石印的小说[1],许多相关研究都对该本有所提及。点石斋1882年于申报的广告《石印三国演义全图出售》称其以“石印照相法印出”,“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而将其所选为底本的“善本”所原有的图像“仍列卷端”。石印技术通过不同性质的化学药剂使墨迹只在图文处显现,将之印在纸上,配合照相影印,这意味着不需雕版,只要有书画家作好的原图,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印件,其优势除开成本低廉不谈,更能“印名家字画墨迹而不失真”[2],不会像雕版图像那样破坏了软笔的原有质感,从而使书画灵动雅致,就点石斋本《三国演义》绣像来看,流畅的笔锋表现出的人物服装褶皱或花草木石的纹理,均非常自然,且极复杂的线条仍旧清晰可见,这样的印本尤其吸引文人士子与藏书家,甚至到现在,我们在孔夫子旧书网之类的藏书转手网站上能看到的晚清民国《三国演义》,绝大多数仍是石印“增像”本。点石斋的广告中也谈到,当时坊间的《三国演义》“绣像衹有四十叶”,且在点石斋石印《三国演义》之前,当时还是有相当多明清小说在刊印发行的,但并非石印,如,只申报馆铅印出版的明清通俗小说已有十七种之多[3],但铅印技术在印图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很明显,点石斋很好地发挥了石印在印图方面的优势,将图作为了最大的卖点。
点石斋只是这股石印“增像”潮流的开始。紧接着登台的就是同文书局广百宋斋1885年的《增像三国全图演义》,广百宋斋在1886年《申报》登载的广告称:“画成二百四十图,分订每回之前”“卷首又增书中名人画像如汉献帝伏皇后王司徒袁绍徐庶之类为一百四十四幅,每幅俱加题赞”,即广百宋斋又比点石斋多出104幅人物绣像。“增像”竞争就此打响,因为我们在1888年的《申报》看到点石斋《重印三国志演义出售》的广告,写“向有校准精本金评尽列石印,无说今二次付印于逐回绘图前更倩名手增补绣像”,且这一次的价格比初版更低,只售一元八角(初版价格为二元四角)。其后出版的鸿文书局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演义》除每回前情节插图外,有人物绣像144张,数量同广百宋斋;商务印书馆1908年本我们暂不能看到原书全本,但从仅见的几页来看,亦有精美的石印情节插图和人物绣像;天宝书局本《绣像绘图三国志演义》情节插图略少,而仍有人物绣像144张。
这些“增像”本中的图像风格相似,除了较晚出的1923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人物绣像比较独异之外,不同书局出版的图像之间经常是重画复用的。如鸿文书局本和点石斋本的绣像有多张相似;又如天宝书局石印本的人物绣像与1882鸿文书局石印本在顺序上完全一致,在画中人物着装与仪态上高度相似,可以说天宝书局绣像很可能就直接来源于鸿文书局,而在每回前的情节插图上,天宝书局对鸿文书局的插图做了一个节省纸张的巧妙调整,它将左半叶和右半叶相邻的两张情节插图合二为一,并用一种虚化的隔断方式做以区分,举例说明,“说吕布”与“叱丁原”在鸿文本是两张图,其在原著中也是发生于不同地点的两件事,但在天宝本插图中两件事画在同一个图框中,之间只用建筑物与花木隔开,仿佛前厅和后院同时发生的事,而细看之下,其实天宝本合并的两个情节插图,它们各自内部的构图与鸿文本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细节不同。可见当时的石印图像,只要是仿照重画不而是直接照相影印,就不算作侵权。
我们现在可见的以点石斋本为例的绘图增像本,绝大部分为完全的石印本,但是也有一些以铅印法印字,而以石印法印画。与点石斋、《申报》同由英人美查创办的上海图书集成局,就有铅印《第一才子书绘图三国演义》,根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图书集成局创办之初就在创制扁体铅字[2]586,这本《三国演义》的字体也的确是扁体铅字,它可能正是图书集成局的尝试之一。大众书局1933年有王大错考证注评的《考证古本三国演义》,其文字为铅印,图像为石印。另有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本《新式标点三国演义》的《校读后记》中提到的商务铅印本,汪原放以之“铅印本。不知何时印的。坊间通行的本子大都和这个本子一样,对校却都不及这一本”,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此商务本和当时(1922)坊间通行的本子差不多,那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类似的铅印文字的增像本。
在当时所有以增像插图为手段吸引读者的版本中,最具风格特色的是泰东图书局本,名《三国演义:金圣叹原批本》。它的插图风格似乎是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与西式画法的结合,人物像素描画一样具有明暗面,以阴影塑造立体感。其实泰东本图像的本质内容仅仅只是其他绣像本三国的既有构图内容,无论是早出的鸿文书局1986年本还是晚出的商务印书馆1933年本,都出现过与之构图一模一样的插图(图1与图2即为泰东本与鸿文本构图完全一致之一例)——泰东本插图的特殊不在于插图内容,其独异面貌正由它与其他绣像版本采取了不同印刷方式而造成。泰东本刊发同年及之后登载于各大报刊的广告称“铅椠排印,校勘无讹,搜得古画,珂罗版印”①或“大字精校特制铜版美图”②。“铜版”自然不可能是真的铜制版,根据艾俊川《中国印刷史新论》,清代以来标明“铜版”的书都不是真的用铜版印刷的,因为这在成本上行不通,所谓“铜版”只是一种修辞,是“监本”的同义词[4],用以形容一种不可更改的精致。所以泰东本乃是铅印文字、珂罗版印图的一例,其绣像的风格独特,正是珂罗版印刷技术的结果,其网状的背景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珂罗版亦是西人发明的印刷方法,其“利用明胶干燥后形成的细微皱纹进行吸墨和油墨传递的,根据胶膜表面吸光后褶皱硬化的程度不同,吸墨能力有所区别”,从而形成“不同的阶调”[5],因而泰东版绣像才呈现出西式绘画的立体感。泰东本珂罗版绣像数量仅8张,但时人对新式印刷方式的追捧,已经足以让它们成为泰东本的宣传重点。当然,泰东本的珂罗版图像仅是“增像本”的特例,“增像本”主流仍是以石印法印图。

图1 鸿文书局《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插图(1896)(1985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
我们可以说,在“增像本”现象中,是新印刷技术支持了晚清民国《三国演义》刊本多图的新面貌。在此之前,读者对于阅读《三国演义》,未必真有如此高的读图需求,是石印书画的技术便利,使书局与印刷商得以将“读图”有意塑造为良好小说印本的标签,并在广告中大肆宣传。石印“增像本”风潮,是新技术制造新需求的结果。
二、铅印与“新式标点”
不仅是图像与印刷技术,《三国演义》文本本身亦随时代发生着改变,新的刊印需求也同样反过来影响着印刷《三国演义》的技术选择。“新式标点”被提倡,是“白话文运动”的重要一环,《三国演义》作为半文言的通俗古典小说,它既具有语言上的过渡作用,又极受大众欢迎,对它的改造,可以作为辅助民众学习新式标点的阵地之一。于是在绘图增像本《三国演义》风潮过后,又兴起了新式标点《三国演义》风潮。
西方标点符号早在1896年左右,已经由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进行译介,但直到“新文化运动”前后才真正受到重视。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训令,正式批准胡适等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新式标点随即正式实施,而新式标点古典小说很快也被提上日程。胡适几乎是在训令发布后立刻开始了此项工作,《新式标点三国演义》直到1922年才出版,这是有原因的。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的描述,胡适与汪原放等人在协商标点古典小说时,首选是《水浒》《红楼》《西游》和《儒林》[6],所以《三国演义》才拖到1922年。至于同样受人欢迎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不是最被重视的一个批次,这是由于《三国演义》此时处于尴尬地位:其虽然被归在此时推崇的“小说”文体之下,内容上却七实三虚、附会史书,以致于不完全符合白话文运动中对文学的要求,不适于作为古典小说典范。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证明,民国时期的学者在刊行或评论《三国演义》时,多数持有这种观点,我们在此不过多赘述。
1922年,第一本加入新式标点的《三国演义》由汪原放标点、亚东图书馆出版。其版面页码标注方式与现在完全相同,即半叶一个页码。整书并无插图,版面整洁清晰,与字密行多、插图众多的增像本形成鲜明对比。自该刊本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批各书局刊行的新式标点本,如世界书局1924年李菊庐标点本、群学书社1924年许啸天标点本、文明书局1927年大字标点本、1930新文化书社何铭点校新式标点本、1931年大中书局新式标点本、1932年会文堂新记书局新式标点本、1933年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标点本、1937年会文堂新记书局新式标点本等等,另有启智书局标点本在1928至1936年之间逐年都有印本。《三国演义》的刊印显然形成了“新式标点”的热潮。
不同的新式标点本,点读结果并不完全一样。首先,标点的格式不同。例如,亚东本中,专名线与书名号位于文字左侧,而句号、逗号等标点位于右侧,不单独占字位。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描述,1921年他与胡适曾专门探讨过排式,当时有三种排式的设想:
一种是标点符号排在字下,占一个字地位,缺点是遇到行头点不好办;另一种是排在字旁,也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同字旁要排的专名号发生冲突;第三种是标点符号排在文字的一边,专名号排在另一边。……再加上一条:每句空一格[6]76。
亚东本最早用的是第三种排式,后来改用第一种排式。至于其他书局,有些使用的标点排式与亚东本早期排式相同,如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本,也有些则使用了剩下的两种排式设想,如启智书局、新文化书社,就采用了专名号在标点符号同侧的排式,这会导致,凡专名号与标点符号重合处,专名号被省略;而群学书社则采用标点在字下且占位的排式。不仅是符号的位置体现出多样性,使用的符号种类数量也有所不同。例如,世界书局本唯独不用专名号和书名号;再如,启智书局本在1928年的“新式标点本”采用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式标点,它的标点形态类似于新式标点与旧式句读的中间形态,其通篇符号只有尖点顿号“、”与句号“。”,句意已毕用“。”,未毕而需停顿用“、”,但它与旧式句读在排式上有根本的区别——它使句读符号独占一格。可见,在此时各书局的新式标点本《三国演义》之间标点规则并不统一。
其次,断句的方式不同。汪原放本使用句号以及分段的频率较高,而商务本更喜用叹号。如第一回中,“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句前后均在写汉末的种种异象,启智本没有在此分段,而汪原放本分段,“种种不详非止一端”与“帝下诏”之间,汪原放本再次分段,而启智本则没有;第五十一回,“却说孔明欲斩云长”后接“玄德曰”,主语变换,汪原放本在二者之间用句号,而商务本则用逗号;刘备希望诸葛亮对关羽“权记过,容将功赎罪”,句末,商务本用叹号,汪本、启智用句号;周瑜言自己若不能取南郡就任由刘备取,刘备说“都督休悔”句,商务本用叹号,汪本、启智仍用句号。
再次,引号的单、双层优先级不同。民国时期运用新式标点,大多是竖排版的,引号使用的是直角引号,但民国时期的直角引号使用规范并不统一。亚东图书馆本的引号,最外层为双层直角引号,如若一段引语中包含另一段引语,内层就改用单层直角引号,如此运用引号的还有启智书局本、世界书局本、新文化书社本、会文堂新记书局本、文艺出版社本、大达图书供应社本等;而反过来将单层引号放在外,双层引号在内的也是有的,包括大中书局本、春明书店鸿文书局本、群学书社本等。外观完整、用法与今相似的直角引号出现于日本的明治时代,而它的上下两部分,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有人认为,单层直角引号的上半段“「”实际是早在奈良时期就有的符号,名为“庵点”,用来标出唱段的起点;其对应的下半段符号“」”,则出现于江户时代,名为“钩画”,作用是标出对话,这都与现在直角引号的用法不尽相同。如今日本对于直角引号之起源的观点,又以之为过去用于读汉字时分段的符号,因此,有人认为,引号“代表中日交流一直存在,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创造”[7]。据此,或许我们可以猜测,虽然具有直角引号外观的符号一直存在,但最终是西方18世纪已单双兼备的弯引号传入东方,才影响了钩括弧最终功能与意义的形成,所以今天的直角引号才和西方标点符号中的弯引号可以相互对调,且其最终在我国使用方法定型时,二者的区别已仅在于用于横版还是竖版。至于直角引号的单、双优先级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北洋政府所批准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原文,其中只说到“「」”与“『』”“表示引用的话的起结”或“表示特别提出的词句”[8],完全没有提及内外层优先次序问题,甚至在这篇文章自己使用引号的时候,也是时而单层引号优先时而双层引号优先,且对原因全然不做说明;包括胡适1916年刊登于《科学》期刊上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这一著名文章,亦是只说明弯引号的优先级,而未提到直角引号的优先级问题。天津《益世报》曾有公文《采用新式标点,下月一日实行》,此时已经是1933年,而这一公文仍然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我们可以想见,在民国实行新式标点符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单双直角引号的优先度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人们可能都处于按自己习惯来使用的状态,这就是不同书局的新式标点本《三国演义》直角引号单双优先级各自不同的原因。
新式标点本之间点读结果不同,但它们无一不采用铅印技术进行刊印。采用铅印原因,我们可以从新式标点本与石印增像本的广告区别之中找到。新式标点本《三国演义》的广告几乎从不宣传书籍的插图,而更多是围绕《三国演义》作为半文言古典小说,对于民众学习文化知识与写作具有良好帮助,如亚东本广告语称“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③,开明书店洁本小说广告称《三国演义》其为“中等学生国文课外读物的文艺书籍”之一④。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多数标点本此时都与亚东本一样,不再重视图像,绝大部分没有人物绣像或回目插图,即使有,也最多如启智书局本将绘图应用在封面,或如春明书店鸿文书局本那样,仅在目录后有两页绣像,每页挤下四张小图,而每张中同时有几个人物站成一连排,如此小的图幅安排多人,人物细节压缩到最少,实已不再具有多少卖点作用。
此时,《三国演义》印本的生产,重点已经由精绘图像转移到了新式标点之上,一来,没有插图就不需要石印来保留绘画的神韵;二来,“新文化运动”后的标点本《三国演义》与此时许多其他白话小说一样,本身被赋予教育普通民众、传播白话文书写和标点方式的使命,已由面向士人收藏家转变为面向普通民众及学生少年,它将可能作为常印读物,且售价不能过高,因此刊印必须考虑成本。铅印一部小说,各书局只需将已经铸好的铅活字排版,铸好的铅字可以重复利用,此时印刷的机械化已经较为成熟,机械铸字可以方便地将字体放大缩小,“由一种模样制出字体大小之不同之号数”[9],不同的字号不需要分别制作,同一字号之间则整齐划一,尤其是使用了机械排字之后,速度更快,节省人力成本。这些都对于排印图像少,对书法亦无要求,只需要标点符号清晰明朗,而价格须亲民的新式标点本《三国演义》非常适合,所以,此时技术已经成熟的铅字排印,成为标点本《三国演义》印刷的首选方案。
三、两类印本内容差异分析
石印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图像制作的精细程度,带来了更强的读图需求,传播新的文学写作格式与新式标点,则与铅印技术更加适配——新的技术与新的刊行需求伴生,二者相互影响。由此形成的两类新的《三国演义》刊本,它们的差异体现在序跋、评语,以及正文内容上。它们或对前代印行的《三国演义》有所承续,或有着鲜明的本时代标记,分析这些不同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索此时期《三国演义》的出版者受到的底本影响、对文本的态度和对读者的潜在指引。
首先,清代的毛评本问世后,便逐渐成为后续市场的主导版本,晚清民国时期的印本也是如此。在众多石印的“增像本”及其他未采用新式标点的版本中,卷首的序跋主要基于毛本的四个序跋文本:勾吴清溪居士的“重刊序”、金圣叹的“原序”、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与“凡例”。部分版本可能省略了“重刊序”,如点石斋版本。此类版本的目录名通常为“第一才子书目录”,后跟“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等字样。然而,还存在数量较少的版本,只有毛宗岗的“凡例”与“读法”两篇,其目录名为“古本三国演义目录”,目录下亦无“圣叹外书”等字样,包括中原书局《三国演义绣像仿宋本》、启智书局《精印仿宋三国演义》、文昌书局《大字古本三国演义》、锦章书局《大字古本三国演义》等,这几个印本字体、版式、绣像均高度接近。
在当前《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清代“毛本”作为《三国演义》版本的一个重要分支,分支下各版本又仍需细分,许多学者都对此有所说明。如魏安在他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中对毛本进行细分时,除依据版式页面,另一个重要向度就是序与评语的作者,从中划分出了李渔序本与毛宗岗、李笠翁合评本等[10]。对于毛本中出现“金圣叹原序”者,很多学者表示质疑,如陈翔华从所谓的“金序”并不符合金圣叹对《三国演义》的评价等方面入手,以“毛评本《三国志演义》序末所署‘顺治岁次甲申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乃出伪托”,对于原序的作者则提出了“伪金序原来乃出自李渔序”的想法[11];有学者亦提出,金圣叹去世的时间早于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的时间,金圣叹作序更可能是后人附会的[12]。而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金序就是金圣叹本人所作,如:“毛宗岗在毛纶未完成的《三国笺注》评点的基础上,依照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的方法修改评注了《三国》,并请金圣叹为之作序,在后来刊本加上‘圣叹外书’与‘第一才子书’,于是这一版本广为流传。”[13]也有学者认为,金与李共同推举毛评点的《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
我们认为金序乃伪托金圣叹所作的说法相对可信。在陈翔华所举例的清康熙年间醉畊堂《四大奇书第一种》之中,作序者乃为李渔,目录下亦只有“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而不见“圣叹外书”字样,扉页书名则为“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全书不曾有金圣叹作评或作序的痕迹,而将所谓金序与李渔序对比,亦确如陈翔华所言,金序绝大部分字都出于李渔序[11]。因此,醉畊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当是毛氏评本的原刻本”[14]。至于“四大奇书”的说法,其本也来自李渔,金圣叹虽曾有过“六才子书”的说法,但其中并不包括《三国》,而“四大奇书”的说法在李渔之前未有,极可能是李渔混淆了冯梦龙等前人的说法而形成的名词[15]。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大奇书”“古本”这两个词汇的来源是李渔序的毛评本,而“第一才子书”之书名或目录名以及“圣叹外书”则来源于附会的金圣叹序毛评本。我们再回到晚清民国之毛评本刊印,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数量较少的第二类,即书前只有毛宗岗“凡例”和“读法”两种文本的版本,往往书名中亦有“古本”一词,且全书未有金圣叹序,亦不标明“圣叹外书”,这更可能是受了“四大奇书”本的影响。
在图像方面,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增像本”中的人物绣像多数仍可追溯至清代毛本的痕迹,就如点石斋在广告中说的,过去的版本绣像只有40张,这说的正是清代主要毛评本上以昭烈帝刘备为首的40张人物绣像,包括有李渔序的醉畊堂本,以及贯华堂本、启盛堂本等各种“金序本”都是如此。点石斋仅将这40张旧有图像再一次印出,同文书局广百宋斋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汉献帝等一百多人,而晚清绣像本之间又相互承袭图像,所以,在各种晚清版本人物的衣着与神态动作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清代《三国演义》刊本绣像的影子。当然晚清民国《三国演义》也非只有毛本,如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影印过明嘉靖本[16],由于该版本不占主流,加之资料限制,我们此处不作过多阐述。
综上,石印“增像本”在大体上沿袭了清代坊间通行本的序跋、评语、图像。然而,与之相对的“新式标点”本则不同,它们在序跋、目录名称、评语等方面,都与前代《三国演义》有着较大差距。
首先考察序跋。作为新式标点本代表的亚东本,正文前有着名为“原序”的序文,它的实际内容其实是“清溪居士重刊序”,而不是通常毛评本的原序(金圣叹序),这是汪原放在选定底本的时候,看到“咸丰本”,并认为其拥有独异的序文,于是誊录在亚东本的卷首[17],而“金圣叹序”则被替换为胡适的《三国志演义序》和钱玄同的《三国演义序》,毛宗岗的《凡例》仍被保留,后边又添加了《校读后记》和《标点符号说明》。启智书局本只有任松如《三国演义序》;同样,新文化书社本有张恂子《三国演义新序》和李逸侯《三国演义新序》,亦不再用毛评本序跋;群学书社本只有许啸天的《三国志新序》;世界书局李菊庐标点本、会文堂新记书局本和大达图书供应社本只留有毛宗岗“凡例”;大中书局本则没有任何序跋。
其次,目录也有所改变。绝大部分新式标点本目录名不再如过去叫“第一才子书目录”或“古本三国演义目录”等,而是简化为“三国演义目录”或直接叫“目录”。目录中不再如过去那样分卷,只标注回目。偶有分卷者如大达图书供应社本,以30回为一卷,而非按照毛评本的两回为一卷,这只是因为小说较长,全书需要分为四册。
再次是注评,标点本大多已经没有毛氏的评语,包括每回之首的大段评语,以及夹杂于正文之间的小字双行评。至于“圣叹外书”“声山别集”等说明自然也是不再提及。
最后,正文内容在民国时期的某些印本中已有所缩减。如,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本《三国演义》删去了“且说”“却说”之类的套语,开明书店《洁本三国演义》则除此之外还删去部分议论、一些不重要的人物身世说明、神怪、夸张、失实或有违情理的情节等等,最终只剩下六十回,每回也只用四字作为标题,可以说缩减了相当大的体量。另外我们前边已说过,新式标点本的图像也极尽减省,绝大部分标点本甚至没有图像。
从总体上看,新式标点本渐渐摆脱了清代刊本和毛评本的传统影响,古人的序跋选用逐渐减少,更多的是引入当时的学术见解和文学评价。如胡适序讲到了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源流分析,并站在当时新的文学立场,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文学评价;又如汪原放在书前置“标点符号说明”,将《新式标点三国演义》变成了指导民众如何使用新式标点的场所之一;再如许啸天序则直接借刊印《三国演义》抒发对“家奴割据”的旧时代的憎恶。目录的体式也渐渐与“古”背离,越来越简洁,并有了页码的标注,能够让读者更方便地翻找回目,总体而言越来越朝着西方书籍的体式靠拢。正文中的那些评语和小字夹评,也因其不再符合时下的认知与价值观导向而被删除殆尽,甚至连正文内容也要做出符合此一时代文化所需的调整。
新式标点刊本内容面貌的改变反映的正是文化思想导向的改变:清代主流的毛评本《三国演义》作为为帝王正统辩护的文本,到了民国自然有诸多不合宜,刊印者在编选中必然要为读者引导一种“新”的史学眼光,让读者带着审视,而不是纯然欣赏的态度来了解这部小说。
【注释】
① 《申报》1920年3月3日第15版。
② 《新闻报》1920年2月26日第14版。
③ 《申报》1922年7月16日第3版。
④ 《申报》1935年12月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