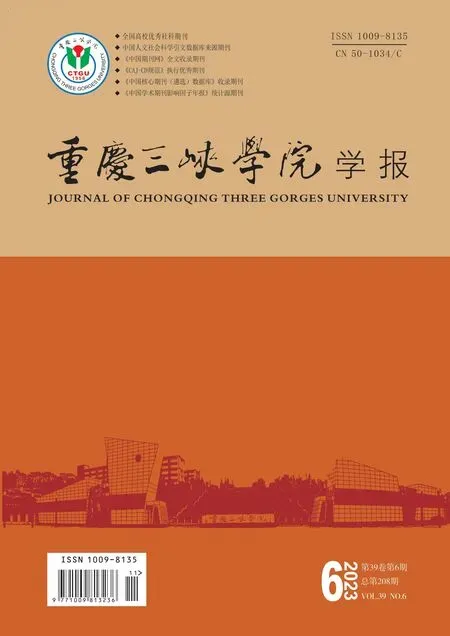《梁书》“诗事”类诗学文献考述
彭沈莉
(成都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中国诗学观念经历了先秦“诗文之学”到汉代“《诗经》之学”再到魏晋以后“诗歌之学”的发展变化过程,魏晋南北朝乃其中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各类文献中有迹可循。《梁书》系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至唐代贞观年间成书,其“诗事”类文献尤为突出。这些关于诗歌事件的历史情境记录,涉及诗歌创作的作者、环境、功能、评价、题材、技巧等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贴近诗歌活动发生的历史场景,理解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学观念,提供了更为细致和丰富的视角。
一、“诗事”之初:“诗”“史”画境
“诗事”,即诗歌之事,从文献角度说,是关于诗歌事件的记载。钟仕伦在《中国诗歌观念与诗学研究范式》中将其列为九种诗学范式之一,主要指有关诗歌的故事和诗人的行历①钟仕伦在《中国诗学观念与诗学研究范式》一文中提出了九种诗学范式,即:“诗本”“诗用”“诗思”“诗式”“诗事”“诗评”“诗史”“诗礼”“诗乐”(参见《文艺理论研究》2015 年第4 期),本文主要以此为依据对《梁书》“诗事”类材料进行考述。。故事,包括掌故、轶事等具体事件;行历,指诗人的生平经历。这类诗学材料在经部、子部等文献中较易区分,但在史部文献里有时难以断定。为说明本文“诗事”所指,须大致辨别“诗”“史”“事”之间的关系。
“诗”与“史”。朱自清称,“诗言志”是我国诗学的开山纲领。闻一多认为,“志”代表了诗歌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的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说文》释“志”,“从心之声”。闻一多将“志”解为从“心”从“止”,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之义,“志”证为“记忆”[1]。文字产生以后,用文字记载,“志”又为“记录”。哪些值得被记忆和记录呢?就传世文献而言,春秋“赋诗言志”,通常都是言国之大事。《左传》昭公十六年:“赋不出郑志。”西晋杜预注:“六诗皆郑风,故曰不出郑志。”[2]“郑风”为“诗”,表达的是郑国的国家意志,是“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3]从先秦文献来看,历史文献《左传》《国语》中与《诗》相关的记录有317 条。西周至春秋中期,《诗》无论是直接记录史实还是作为历史经验而成为社会准则来谏政,无不反映了“以《诗》载史”诗学观,“诗”所指涉之事是为了符合历史事实[4]。“诗”与“史”同源而出,“诗”又与“志”同有“记录”之义,“记录”为“史”。
“史”与“事”。诗既是志,是记录,那么所记录的史,显然是某“事”。《字源》解“史”为会意字,“商代甲骨文作从又持中,又为手之象形,中为猎具,手持猎具会治事。”“史与事、使、吏同源。史用作事,事情。《小屯殷墟文字乙编》:‘辛未卜,贞:有史(事)?甲戌卜,亡史(事)?’”[5]《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段注云:“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事,职也。”[6]“中”训“正”,体现了文字含义的引申,即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观。“事”“史”相通,都有书写、记录的意思,记录事件需秉笔直书。
可见,先秦时期“诗”“史”“事”三者关系甚密。“诗”本身就是“史”,或其所“志”之事指向“史”,为国家政教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7]1038-1039按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与书写文字一定一同出现的唯一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也就是把大量的个人统合进一个政治体系里面,把那些人划分成不同的种姓或阶级[8]。也正因为“诗”“史”“事”源头上的共通性,使得“诗”“史”之间难免陷入后世史学和文学争执的两端。
“诗事”和“诗史”并列,有赖于诗歌观念的自律。一些与诗相关的“事”从“诗史”中分离出来,诗歌之事开始显现出其自身的独特性和自足性。也就是说,当“诗”逐渐从国之大事中疏离出新的空间,“诗事”就会从“诗史”里面旁出一脉,为自己言说。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拔高文事,意味着“文学”之“文”的地位已然大大提高了。其后,汉代受制于经学的“诗”在“诗三百”之外另辟蹊径,发展出“诗缘情”一脉,也就是闻一多先生所谓“诗言志”的第二次引申——诗为“怀抱”。《隋书·经籍志》载:“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7]1089隋志收录以诗歌为名的总集多集中在两晋和南朝,且尤以齐梁为盛。“诗”有别于“经”“史”,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个人表达喷薄而出,“诗”与“史”走上了各自的道路。由此,在诗学研究语境下,“诗事”从“诗”来立意,指向以诗歌为主体的历史事件。
《梁书》言及《诗经》的地方也颇能看出这种诗学观念的变化。其一,《梁书》引《诗经》的文献数量较少,引用之处往往与礼乐政治制度、人物道德品性相关。例如,北魏使者李道固出使南齐,萧琛劝酒,李道固以“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萧琛以《诗》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对之[9]396,此为先秦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余音。其二,《梁书》提及《诗经》之处一般都与人物治学的内容相关。如刘歊“六岁诵《论语》《毛诗》”[9]747,诸葛璩“悦《礼》敦《诗》”[9]744,许懋十四岁受《毛诗》等[9]575。这类人物大多收入《儒林传》《处士传》,皆为儒学传统。由此,除开引《诗》以外,诗文才学意义上的诗歌活动才是《梁书》诗学材料的主体。
二、“诗事”范畴与《梁书》“诗事”概略
通检《四库全书》,“诗事”二字直接出现不多,偶有单独作书名,如辑录于宋代《竹庄诗话》中的《诗事》,其余大多存于“诗纪事”“诗话”或散见于文人杂谈当中。其所录内容大致经历了从追求诗歌史实的考证到追求才学、用典技巧再到记录文人生活趣闻、诗社诗会等情况的变化。综而略之,“诗事”所包含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是直接关于诗歌活动之事,如诗歌酬唱、结社、点评等,其涉及诗歌创作的主体、创作发生的条件、诗歌的传播接受,甚至偶然事件等等。清代阮元《广陵诗事》曰:“其间有因诗以见事者,有因事以记诗者,有事不涉诗而连类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余年来,名卿贤士、嘉言懿行,综而著之;庶几文献可征,不致零落殆尽。”[10]阮元如此辑录,旨在考辨人事,“以诗证史”,若从“诗”着眼,恰好可作为诗学文献视之。
二是诗歌内容所直接指涉之事,如历史事件、传说掌故、诗人轶事等,相当于诗“本事”。本事者,所本之事,即诗歌的原事、旧事,其既是诗歌创作的依据、素材,又能在诗歌文本接受中起到补充、印证、注疏之用。《汉书·艺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11]诗歌所本之事与诗歌所呈现之事有别。本事近于创作题材来源,经过艺术表现之后,成为文学作品,在探讨文学创作内部规律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诗“本事”也关乎诗歌的阐释问题,即突破文辞限制,以“史”为基准来探求诗歌文辞背后的寓意,使诗、诗人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达到整体的和谐,从而确立“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及“诗”“史”互证等诗学研究方法。
三是“诗人之事”,主要指诗人行历或与诗相关的逸闻趣事。诗人行历是对诗人生命历程的概括性叙述,接近于作者研究。诗歌活动是生命个体的艺术创造,诗学研究需考虑诗人所历之事、所处之境。诗人行历由许多大小事件组成,隐含了不同情境之下的心态、视角和经验,能够为探寻诗人的创作动力、目的、技巧、风格等方面提供线索。若《唐诗纪事》计有功之序言“庶读其诗,知其人”,明人孔天胤论观诗须“得事则可以识情”之类[12]。以上三个层面有时候相互重叠,并不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只是在选择文献时,无论长短详略,需完整叙述。
《梁书》诗学材料大略统计有100 余条,其中,“诗事”60 余条,占二分之一以上,且内容多以诗歌活动事件、诗歌本事和诗人行历、轶事为主。南朝刘宋、萧齐统治者重文学,梁武帝是南齐萧子良西府文士,本人文学修养极高,乃继曹魏父子之后创世之君兼擅才学的典范。姚察修《梁书》,本之梁代国史。诗文之盛,乃梁代事实,曾受命编撰过梁朝历史的沈约、周兴嗣、裴子野等亦是诗文创作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又,沈约编撰《宋书》,萧子显撰《齐书》,留下的文学材料自然较为丰富。赵翼曰:“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13]可知,梁代诗文之事应属于必书之美事。例如,《梁书》梁元帝本传言其“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9]135-136。而《南史》则增其“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在幽逼,求酒饮之”等语[14]。
唐初修史,对齐梁文风多有批评,然其诗文之繁盛,确为梁代国史特色。以《梁书》人物传记为例,其官位显要者多以独传入史,如任昉、沈约、江淹、周舍、刘孝绰、陆倕、到洽等;其有文学才能者多以氏族关系合传,如萧子恪兄弟。《梁书•文学传》在总传中占两席,入传26 人,而同时期成书的《陈书》《北齐书》《隋书》的文学传都只有一卷,《周书》则没有以“文学”为名的传记。又据《补梁书艺文志》著录,梁代有别集者多达120 人[15]。《梁书》评述人物行历,长于诗文者皆叙其“擅属文”“工篇什”“有文情”,有著述文集者大多罗列书名和是否传于世等情况。此外,全书不吝添加人物的才学细节,如“(张)率年十二,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诵,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9]475。可以说,《梁书》在收集保存梁代文人诗文活动的记录方面颇为显著。
三、公宴赋诗:梁代诗学的公共空间
宴会赋诗是《梁书》诗学文献中贡献最为显著的一种。此类“诗事”收录了不少与诗歌相关的集会,既有官方性质的,也有私人性质的,从中可以大致窥探彼时文学、诗学共同体的轮廓及性质。
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䜩,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簉中阳,夙忝同闬,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9]397
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9]591
御光华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十二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高祖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9]404
“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9]685这类诗事兼有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性质。
首先,臣子通过诗赋获得奖掖、认同,统治阶层通过诗赋擢升官员,这不妨看作梁代上层公共领域中的某种惯例,带有政治功能。如刘孝绰免职后,萧衍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引与焉。“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9]482沈约、任昉、萧琛、范云乃萧衍在西邸文人集团中的故友,他们围绕在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身边,为谋士,也为文士,文学成果自然丰硕。如《补梁书艺文志》别集类载:沈约注《武帝连珠赋》一卷、《沈约集》百卷、《集略》三十卷、《诗极》一卷;《范云集》十二卷、《任昉集》三十四卷[14]195。陈寅恪概括南朝政治为:“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16]梁建立后,萧氏大兴文教,乃兰陵萧氏向文化高门士族转变的表征之一。萧衍不仅需要过去的西邸同僚担任梁代要职,但也需要新的力量巩固萧梁的政权。所以,萧衍对到溉、到沆(彭城人,宋骠骑将军到彦之后)、刘孝绰(彭城刘氏)等文士的擢赏,本身就潜藏政治用意。同时,萧梁宗室以文事为高,在子弟教育上也有意以文化之。武陵王萧纪颇自骄纵,萧衍命江革匡正之后,萧纪侍宴果然能“言论必以《诗》《书》”,“耽学好文”[9]525,有《武陵王纪集》八卷。宴会赋诗,文辞风雅,是上层文人士大夫交际所需。何敬容就因“独勤庶务”,不合当时宰相“文义自逸”的风气而遭到嘲讽[9]532。诚如有学者所言,萧梁时期,“重大的文学活动、重要的文学主张大都由皇族成员主持或倡导。萧梁文士则多为皇族文学侍从,如沈约、范云、任昉之于萧衍;王筠、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之于萧统;庾肩吾、刘遵、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之于萧纲等”[17]。可知,梁代公宴活动中,诗文写作活动乃当时的社会风尚,同时也扮演了维护君主统治的潜在角色。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自觉于魏晋南北朝,但也不能忽视其政治的他律性质。
其次,宴会赋诗,体现了诗歌的审美娱乐功能。《梁书》中记录的宴会有招募宴、饯别宴、庆功宴、节气节日(三、九日宴)、游乐宴、佛事宴等等,诗歌乃不可缺的助兴雅事。
初,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9]588
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9]512
大同三年,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高祖因赐侃马,令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高祖善之。又制《武宴诗》三十韵以示侃,侃即席应诏,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9]559
总览《梁书》,由帝王亲临的公宴赋诗材料粗略统计有20 余条。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梁代的诗文中,从题目可推知为宴会之作的诗歌数量极为可观。梁代由上导之的诗歌活动构成了梁代史书的叙事特征之一,天子宴幸,群臣赋诗,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诗歌活动的公共空间。
其一,公宴赋诗透露了当时诗歌的生产机制之一,即规定赋诗的题目、范围或韵脚等,群臣当堂竞写。“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9]470-471“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引见。”[9]480“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9]513命题之作,直接影响到诗歌的写作题材。此类诗作大抵围绕宴会场所展开,以咏物诗为盛。其中,咏自然事物者如日、月、雪、风、云、桃、竹、雨、蝉、雁;咏生活事物以及百科学识者如郡县名、姓名、车名、宫殿名、药名、船名等。至于“宫体”以美人为描写对象,乃上层文士宫廷、园林所见所感。公宴赋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提升了诗歌写作的技巧。例如,彭城刘氏诗人的咏物诗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有南朝咏物诗的重要地位,其诗作有意用典,描写细致工巧,艺术性也更为突出[18]。
其二,宴会中的文人构成了梁代诗学阐释、理解和接受的共同体。为了进入这一共同体,甚至武将也不甘落后。胡僧佑“性好读书,不解缉缀,然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僧佑怡然自若,谓己实工,矜伐愈甚”[9]639。被嘉赏的诗作、诗人体现了主流的审美趣味和标准。如柳恽奉和萧衍《登景阳楼》:“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萧衍所美,当时咸共称传[9]331。沈约、范云等文坛前辈的评价又是产生诗文名家的有效机制。王筠以“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被推为“晚来名家”“独步”[9]485。王筠自撰其文,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其诗文名家身份与仕途通达甚为相合。萧子显之子萧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太宗在东宫,早引接之……太宗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9]513
诗可以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方面,在官方历史叙事话语背景下,诗歌创作、交流活动的政治意图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频繁的诗事记录意味着诗歌延续了先秦以来的颂歌功能,并且在君臣乐此不疲的唱和之中,兼具娱乐、学识、诗歌技艺研究等审美功能。宴会诗歌满足宫廷化、贵族化的趣味,缺乏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出于公共空间的诗艺竞技需要,诗歌的自律仍然得以潜在推进。由此,《梁书》载录宴会赋诗的文献,证实了中国古代诗学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即诗歌在上层社会中的交际功能,也展示出诗歌活动悄然生长的情景。
四、诗人之事:诗歌的日常与趣味
《梁书》所录文人交游之诗事材料也值得注意。不单梁武帝萧衍好诗文,萧梁皇子们亦与士大夫结诗文赏爱之交,如以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玄圃之游、以萧纲为中心的宫体诗人群。皇族和上层士人之间的交游难以撇开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而这类诗事相对更贴近文人心性。如刘遵去世后,太子萧纲致信其从兄刘孝仪,赞刘遵“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并谈及汉南会遇之状:“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鹢舟乍动,朱鹭徐鸣。”“酒阑耳热,言志赋诗。”[9]593这里展示的集宴氛围,显然比公宴多了几分真情实感。
文人士大夫往来饯别,多以诗推介、以诗赠别。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梁代诗人文人唱和赠别之作占据了较大比例,是除去拟乐府诗、宫廷侍宴诗和咏物诗之外的主要类型。“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座上宾客,恒有数十。”[9]254刘孝绰为《归沐诗》以赠任昉,昉报章曰:“‘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讬。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其为名流所重如此。”[9]480“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学友会,及是将之县,昉赠诗。”[9]47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任昉诗21 首,其中以“赠”“答”“别”为题目的诗歌就有9 首,可见相关诗事不虚。文人以诗相赠,以诗题壁,或为当时风尚。何思澄“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9]714。又柳恽为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为琅邪王元长嗟赏,因书斋壁[9]331。
同时,文人士大夫之间又以诗嘲讽。江革次子江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词》以刺敬容,为当时所赏”[9]526。“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9]532“点既老,又娶鲁国孔嗣女,嗣亦隐者也。点虽婚,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谕其意也。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尚之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戏也,而融久病之。及点后婚,融始为诗赠点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点亦病之,而无以释也。”[9]733
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集宴、酬唱活动频繁,《梁书》贡献了不少文人雅号。“谢有览举,王有养炬”(谢览、谢举与王筠、王泰)[9]484;“东海三何,子朗最多”(何思澄、何子朗、何逊)[9]714;“杲风韵举动,颇类于融,时称之曰:‘无对日下,惟舅与甥’”(张融与陆杲)[9]398;“充融卷稷,是为四张”(张稷、张充、张融、张卷)[9]270。此外,还有“两到”(到溉、到洽)[9]569、“三笔六诗”(刘孝仪、刘孝威)[9]594、“何刘”(何逊、刘孝绰)等[9]693。
《梁书》所载此类琐事、轶事,意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亲疏褒贬,其中所制诗句,押韵断章,为五言或四言,篇幅形制较为随意,艺术水平参差不齐。然而,这些诗歌事件说明,诗歌韵语技能是文人士大夫的基本素养,是晋升上流社会的重要才能,是社会名流的语言趣味。
五、诗歌之事:鉴赏、技艺与本事
更进一步,《梁书》所载“诗事”,不乏文士之间诗文往来、关涉诗歌内在属性的探讨之事。如:
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直写文词,不加篇题。约谓人云:“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塪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赏。约曰:“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筠又尝为诗呈约,即报书云:“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9]485
这条材料正是“雌霓之诵”的出处,与《宋书》《谢灵运传论》及其《四声韵略》十三卷一致,是南朝诗歌音韵发展的一条例证。沈约“抚掌欣抃”,得知音之喜,溢于言表。“丽则”“声和”“光影”也表明了沈约的诗歌评价标准。对于同为沈约所赏的诗人何逊,范云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9]693又,萧纲与萧绎的书信中批评了“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9]690的时弊,并论及自己的诗学主张,以“英绝”“领袖”来推崇萧绎的诗歌创作。
此外,《梁书》载文人行历也包含了诗歌创作的部分本事。
(王藉)历余姚、钱塘令,并以放免。久之,除轻车湘东王咨议参军,随府会稽。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9]713
此诗流传甚广,《颜氏家训》也有记录,且有北人以为“蝉躁”二句“不成语”之论。会稽自来风景明秀,是衣冠南渡后发现的新世界。《梁书·何胤传》录梁武帝萧衍与何胤书曰:“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9]736王藉游会稽,累月不返,噪静相生,此诗当体悟所得,可看作实录。
又,《梁书》传述豫章王萧综身世遭遇及怨恨所由,叙其诗作,并录文辞:
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大略曰:“听钟鸣,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其《悲落叶》云:“悲落叶,连翩下重迭。落且飞,纵横去不归。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当时见者莫不悲之。[9]824-825
萧综之“不得志”,本传前半段交代:“初,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宠衰怨望,遂陈疑似之说,故综怀之。既长,有才学,善属文。高祖御诸子以礼,朝见不甚数,综恒怨不见知。”[9]823之后,萧综的人生更加曲折荒唐,直到叛梁投魏。此处所引“不得志”部分,只为一二。据研究,此诗应指其入洛而未受礼遇之前的这段时间,更具体一点是孝昌元年的初秋时节[19]。《梁书》所载只记录了他在梁朝的情况,并未涉足在魏的具体事件和心态。从诗的内容看,似乎是对他整个人生遭遇的总结和悲叹。“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2]270蕴藏在心的“志意”,即为诗人之“怀抱”,若还没有表诸为言语文辞,还不是“诗”。“诗事”可以作为创作的部分根由,而诗本身,则可能是对现实的提炼、修辞、含混之后的艺术化呈现。
六朝修史,最喜载文。《梁书》所引诗篇或以诗证史,或以诗补史,一来提供了研究诗人生平和诗歌创作的重要材料,二来又恰好注解了“吟咏性情,流连哀思”之诗学观念。《梁书·羊侃传》附《杨华传》:
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惋焉。[9]556-557
杨华北将归南,胡太后思之作歌之语可算闲笔,颇具小说意味。《梁书》此条于杨华生平交代似无必要,但多了一条诗出哀怨的浪漫诗事。
六、结语
中国史书,自司马迁开纪传体,以人系事,延绵千载。有梁一代,史书所录人物长于诗文者众多,故其所保留诗学文献也较多。诗作为史,作为事,乃人物之记录。编撰者以丰沛之材料显人物之行历、精神,从而连缀历史之画卷。《梁书》史料汇集,关涉“诗事”者可观,且不独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不能不谓梁代诗事确实笃盛。诗歌才学乃彼时士大夫必备素养,具有明显的社交功能,兼具政治色彩和文学色彩。公私宴会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场所之一,乃梁代诗学的公共空间。诗歌除了传达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产生诗歌创作的题材、优秀诗人诗作。文人私下交游记录颇详,好诗、作诗、论诗已成为梁代文士的日常,诗仍然具有记事、议论的功能。至于诗歌的文与质、声律音韵等问题,也在这类诗事之中有所体现。最后,文人历难,感怀自伤,化而为诗。其为文凄怆,“见者莫不悲”乃梁代诗学观之明证。
总之,《梁书》“诗事”本附着于人,士人既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又需要表达主体意识或情志,诗文活动因此具有多重目的和价值。这些诗歌事件在国家叙事之“史”的描述中,逐渐显露出以诗歌为主体的“诗事”之端。基于“诗言志”和“诗”“事”“史”之间的本源联系,《梁书》“诗事”涌现,是“史”之事实,也必然涉及所传人物之“志”。由此,在中国古代诗歌观念变革进程中,《梁书》所录各类“诗事”文献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价值。因为,如果从更长远的维度来看,“因为‘言志’,所以诗以‘纪事’、诗以‘记物’、诗以‘合意’、诗以‘志理’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以诗证史’‘以诗证地’则成了中国诗学的主要任务,从而呈现出有别于西方诗学和当代文学理论的理论形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