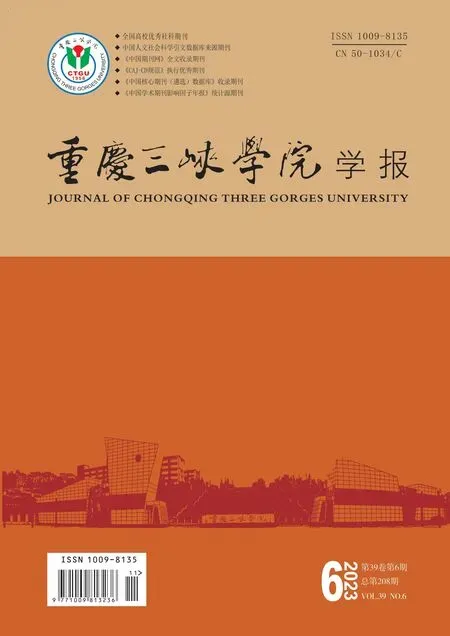元素与时空的文学史书写
——南宋三峡行记文学探赜(上)
王志清 林标洲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作为古代叙事文学的一种体式,行记是文人、官吏、僧侣等主体在行旅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的真实记录。早期行记如先秦《穆天子传》,汉、魏晋时张骞《出关志》、法显《佛国记》等,体例和内容并不完备,与其他地志、史传等材料有很大的混同。魏晋以来,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内容边界的拓展,以及对美学思想的探讨,极大地促进了行记文学的发展,从单纯对异国异地风貌的实录,融入了更多文学创作的自觉,在风物风景的描绘、体式内容的扩展、思想审美的追求上都大大进步。宋代传世行记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十分出彩,相较此前有了更多风物、民情、风俗、历史感慨等人文内容的加入,且在前人歌咏的基础上,营造出浓郁的文化审美价值,“宋人几乎穷尽了这一文体所有的可能性,规定了后世作品的发展方向,塑造了后人对行记的基本认知。在行记体制演变史上,两宋实构成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125。
宋代是文人地位空前的时代,发达的科举文化和浓厚的向学风气,使社会文化水平大幅提升。两宋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对峙,产生了频繁的使节交聘。独特的政治环境,还体现在两宋优待士大夫,文人有一定的豁免权,同时官员的左迁也司空见惯。南宋偏安一隅的国情,使大多数士人的政治、文化生活集中在南方,各种贬谪出行、官员游宦,导致行记创作数量庞大。随着中唐以来的人口南迁,经济中心也南移,南方得到有效开发;面对北人战马集群作战方式,南方细密河网与丘陵峡谷地带也就具有了战略意义,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使南宋官员对行记有所偏好,如北宋张舜民《郴行录》、欧阳修《于役志》等,南宋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骖鸾录》、周必大《南归录》、吕祖谦《入闽录》等,既包括交聘行记,也包括文人出行行记,内容十分丰富。目前学界对行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叙事学层面,从叙事结构与风格切入,探讨行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揭示其文体特点,点明社会与文化、地理与历史施加的效应。这方面颇有见地的文章有李德辉《论宋代行记新特点》[2]、《早期行记的文体生成及多途径发展趋势》[3]、《行记别是一体论》[4]、阮怡《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5]、《宋代域外行记中的奉使交聘文化》[6]等。二是从内容上评析其文学内涵和文化品格,更关注单人作家行记,如《周必大行记研究》[7]、《范成大行记三录研究》[8]等。田峰博士论文《唐宋行记研究》[9]以陆游《入蜀记》为观察点,从文化胜览倾向、旅行体验的书写、诗学和学术品格等方面进行论述。魏秋阳《南宋日记中的旅行书写》[10]与此类似。
三峡位于两宋西南边陲,是出蜀入蜀喉衿。在上述南宋独特政治生态下,三峡一段作为往来的要道,无论从自然景观,抑或士人心态而言,都有独特的地位,在行记与诗文的体现中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南宋这一特殊时代,不仅因其独特的国情,更与南宋行记在内容、风格和体式上的成熟有关。以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二者为主,截取长江三峡这一段相关记载,辅以其人其他诗文,从元素论上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因为元素深入且嵌入于整个时空概念,所以研究元素论视角下文人行记创作需将二者紧密结合,探讨三峡元素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景象呈现,分析历史叙事和地理叙事在三峡行记创作中的独特地位。又宋人行记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如范成大,即有着“成大《石湖诗集》,凡经历之地,山川风土,多记以诗”[11]的评价。诗文别体,互有分工,二者有不同的情感与情绪表达,但在行记中却达到共通的境界,揭示出行记创作从“文叙事、诗抒情”功能到“诗文重情”功能的变化图景,从而在传统叙事学阐述的基础上呈现二者共同塑造的三峡文化空间,更好地推动三峡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汲取内涵。
一、元素论下的三峡景象呈现
元素论是中西方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又极为普遍的构成部分。中国的元素论,包括阴阳、五行、四大或者八卦等等,其中的元素是作为组成部分的一个质料,同时是一个自发的互相生成与克制,并且不断循环转化的系统。这样的一个哲学系统有着很强的同化能力,一个原因便是其不断运动的模式,在一个更大的境域[12]135中成为相互组成与影响的小一级境域。西方的元素论从古希腊的单纯“质料组成说”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认为“元素极少被置于整全境域中,它只是创造所必要的材料而已,它的组合与转换都是受制于机械或有机的物理规律,或者任凭创造者(人或造物神)的意图主宰。作为质料的元素始终没有摆脱被规定者的位置”[12]134。因此,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中,很容易且很习惯从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这是境域与境域之间的一个碰撞与融合。而在西方元素论下进行的思考,则是“将事物置于它所显现于其中的境域里进行观看和理解”[12]133,它需要一个大的境域作为思考的先决条件,去审视在境域的规则控制与驱动下的生成与作用状态。
本文试图从元素论的角度对南宋三峡行记文学进行分析,从传统的中国元素论中挣脱出来,采用另一种境域与元素的作用模式,去探讨创作者选择性地构造与记录三峡地区这一生存空间与诸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企图创新之处。中西方各自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地域性先抛开不谈,因为这正是本文此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而民族性在元素论下能够相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物理规则制约下的境域之中,在人的感受这一来自本身的主观行为上,刨除理解的差异之外都是相同的,即我们的“身体场域”是相同的,也就是施密特所认为的“所有民族的生活世界都包含着同一个原发性的自然境域,这种自然境域的同一性最直观地体现在人的身体性之中”[13]137。与中国佛教“四大皆空”的“四大”地、水、火、风类似,西方的四元素说是土、水、火和气,体现为“寒冷和炎热、干燥和潮湿应该交替进行,相互补足中和,达至平衡”[13]9。这样的直观感受作用于中西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空间中产生了不同的思维理解和不同的思维边界、行为方式,这是其内部性。至于外部性则是不同民族的外貌、气质等等,元素组成的境域因此产生了差别。王凌云在《元素与空间的现象学——政治学考察——以中国先秦思想为例》这篇小札记中选取了土、水、气、天这四种元素进行分析,这四种元素合乎我们的民族性与哲学思辨,因此笔者假前人之功,也以此四种元素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陆游《入蜀记》与范成大《吴船录》是本文的主要文本分析对象,因为二者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三峡这片区域,且各种相关地域文学著作或古代地志、现代地理学著作等对于三峡区域的概念各有分合,为统一理解,故采取一个较为宽松的范围,将二著中湖北路峡州(以三峡入峡口考量)、夔州路所属之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归州(治今湖北省秭归县)、云安军(治今重庆市云阳县)、大宁监(治今重庆市巫溪县)、开州(治今重庆市开州区)、万州(治今重庆市万州区)、梁山军(治今重庆市梁平区)、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涪州(治今重庆市涪陵区)一线作为考量内容,基本囊括了瞿塘峡、巫峡与西陵峡一带。虽划分草草,亦足以察叙大端。“元素—生存空间”之间的体现,将它挪移到陆游与范成大创作的行记中来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其中有许多自然以外的事物呈现。这样的呈现又区别于单纯的自然地理,三峡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民情风物乃至吏治管理都融入了进来。通过此种改变关注单个元素与其他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认知方式,能够在作为文本分析对象的《入蜀记》与《吴船录》之中,更加单纯与独立地分析四种元素组成的三峡境域,在整合于整个南宋更大一级的境域之下,如何将“元素—生存空间”这一关系转移到书面创作中去,并记录其发生的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使在多山多石的西南丘陵峡谷地带,土地农耕仍十分重要。《方舆胜览》描述为“峡土硗确,暖气既达,故民烧地而耕”[14],范成大《劳畲耕》诗并叙也言及“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15]217。即使地力稀薄,农耕技术落后,对于土地的开发耕种也必须进行,这是农耕传统和吏治考核的一环,因此土这一元素在基本的民族心理上,是最基础的元素。我们的民族性立足于土这一元素,在土壤代表的农耕基础上,又因此延伸出了其他的境域——山石、洞穴与亭堂寺庙。试看下列几组材料中的景象元素。
(1)六日……高崖绝壁,崭岩突兀。[16]148
(2)八日……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16]152
(3)十五日……肩舆游玉虚洞……既入,则极大可容数百人,宏敞壮丽,如入大宫殿中。有石成幢盖、幡旗、芝草、竹笋、仙人、龙、虎、鸟兽之属,千状万态,莫不逼真。其绝异者,东石正圆如日,西石半规如月,予平生所见岩窦,无能及者。[16]161
(4)二十六日……关西门正对滟滪堆。堆,碎石积成,出水数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涨时,水又高于堆数十丈。”[16]171
(5)丁巳……峡中两岸,高岩峻壁,斧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滩最号险恶。两山束江骤起,水势不及平,两边高而中洼下,状如茶碾之槽,舟楫易以倾侧,谓之茶槽齐,万万不可行。余来,水势适平,免所谓茶槽者。又水大涨,渰没草木,谓之青草齐,则诸滩之上,水宽少浪,可以犯之而行。[17]卷下218
(6)八十里……虾蟆碚在南壁半山,有石挺出,如大蟆,呿吻向江。泉出蟆背山窦中,漫流背上散下。蟆吻垂颐颔间如水帘以下于江,时水方涨,蟆去江面才丈余,闻水落时,下更有小矶承之。[17]卷下223
(7)八日……系船与诸子及证师登三游洞。[16]152
(8)九日……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绿润,泉泠泠有声,自洞出,垂虾蟆口鼻间,成水帘入江。是日极寒,岩岭有积雪,而洞中温然如春。[16]154
前三组材料描写三峡沿岸及洞穴景观中的奇山怪石,通过“高”“绝”“突兀”等词语白描勾画出山的险峻奇绝。对于“奇怪不可尽状”的山体,陆游一连用九组排比,惊叹之意扑面而来。对于玉虚洞中的怪石,陆游则善用比喻,给予这些不见天日的石头以各种奇特想象,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的奇思妙想结合,塑造了一幕“绝异”的场景。同时这些幢盖幡旗、芝草竹笋、仙人龙虎也与此洞之名“玉虚”相合,因为“玉虚”就是道家三清之一的名称,陆游游览与记录的心情受此影响,在先入为主的观感上,有意识地倾向于名实相符的创作。第四组材料则是描绘江水中碎石堆成的滟滪堆,水升水降,滟滪堆与江水动辄“数十丈”的高差,使人感受到滟滪堆给船家行人带来的危险。第五组材料言“斧凿之痕皴皴然”,借用了大禹开山治水的传说,而后范成大又用精致的“茶碾之槽”比喻黑石滩的险峻,“茶槽齐”“青草齐”这样民风淳朴的称呼,是三峡地区的先民在与险恶自然环境搏斗时乐观精神的体现。范成大在此处施以笔墨,亦有宋时文人喜好煎茶的文化心态在内,与行记内其他各处对泉水论品定级有所呼应。第六组材料描绘虾蟆碚的独特地貌,虾蟆衔江、泉出蟆背,让一路行来见惯了奇险山石的范成大仍眼前一亮。相同的内容,陆游也有所描绘,用“造物之巧,有如此者”[16]154来抒发心中感慨。第七八组材料言洞穴事,与此前玉虚洞相仿。三游洞得名于唐时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之游与北宋三苏之游,前人笔迹今仍有存,即使在陆游看来“阴黑峻险尤可畏”[16]152,但仍然值得一探。虾蟆碚上之洞穴,则纯为自然之巧,“石色绿润,泉泠泠有声”“洞中温暖如春”,在三峡奇险山貌之外,内里却孕育出灵秀洞穴,内外差别极大。关于洞穴寻幽的好感,也多次体现在二人行记之中。此外还有各种亭、台、观、寺,如“静练及洗心二亭”[16]148、“白云亭”[16]166、“四贤阁”[17]卷下216、“烟霏阁”[17]卷下216、“清烈公祠”[17]卷下220、“屈平庙”[17]卷下220、“昭君台”[17]卷下221等,这些都是地方的人文与历史积淀,立足于一地的土壤,最终成为与三峡山川相掩映的存在。在行记中,山川有两种呈现模式,一种是奇险,一种是明丽。前者从上述材料以及传统诗文对于三峡的印象中得以想见,而后者则是隐藏在这种奇险背后,给予亲历者以恍然之感。如“滩际多奇石,五色粲然可爱,抑或有文成物象及符书者”[16]158、“天宇晴霁,四顾无纤翳,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16]168等描述都使人观之可爱,不觉有边瘴之地的恐怖感受。
土作为最基础的元素,从人类生存到生产生活,都立足于其上,是传统农耕文化长久以来的影响。“我们在土地上获得自己的视野,也获得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的跑跳,我们的耕作,婚丧嫁娶甚至是战争等等,绝大多数都立足于坚实的土壤之上。这种来自土壤的安全感让我们发展出了围绕着土壤的政治与伦理,同时制约着其他元素的显现。”[12]143“显现”这个词限制了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凸显了不同元素自身的重要性和相互影响程度。这就是此种元素论视角下的论证过程。土元素在三峡行记中的呈现如上文所述,文人因其个人文化心理与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得文字中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王凌云小札记说道:“水被土包容和束缚……河与井作为源,将人们聚集、连结和固定在周围的土地上。”[12]143这是他在论及先秦儒家思想所作的论说,但在儒家文化成为文化底色的后代,这样的“包容和束缚”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或者说平原地区,体现得更加透彻。在此处强调平原地区,因此就接入了地理这一境域因素的影响,土元素与水元素之间的主导和制约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有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将视野放在三峡地区,从陆游与范成大的著作中,可看见在土元素与水元素的关系不该再依“水被土包容和束缚”来理解,否则容易陷入误区。三峡地区不是传统的农耕农业发达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土水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土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较于传统平原地区,行记中体现出来的三峡地区的土水关系,应该是土被水限制着,是被三峡这一区域的形态划定边界,水元素代表的长江包覆着土元素的同时又连接着外界,即东边南宋国都临安与西边边陲巴蜀的连线。
《入蜀记》与《吴船录》中有许多与水相关的描绘,详下。
(1)登虾蟆碚,《水品》所载第四泉是也。[16]154
(2)微泉泠泠,自岩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尝,当亦佳泉也。[16]159
(3)张又新《水品》亦录此泉。蜀士赴廷对,或挹取以为砚水,过此,则峡中滩尽矣。[17]卷下223
(4)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16]166
(5)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16]171
(6)龙门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锐石,故为峡中最险处,非轻舟无一物,不可上下。[16]159
(7)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涛大汹,濆淖如屋,不可梢船。过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州来合大江。大江怒涨,水色黄浊。黔江乃清泠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17]卷下214
(8)早遣人视瞿唐水齐,仅能没滟滪之顶,盘涡散出其上,谓之滟滪撒发。人云如马尚不可下,况撒发耶!是夜,水忽骤涨,渰及排亭诸簟舍,亟遣人毁拆,终夜有声,及明走视,滟滪则已在五丈水下……十五里,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独滟滪之顶,犹涡纹瀺灂,舟拂其上以过,摇橹者汗手死心,皆面无人色。[17]卷下217
(9)水骤退十许丈,沿岸滩石森然,人鲊瓮石亦尽出。望昨夕系舟排亭,乃在半山间。移舟近东泊。从船迁徙稍缓,为暗石作触,水入船,几破败。[17]卷下221
(10)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17]卷下214
(11)峡江水性大恶,饮辄生瘿,妇人尤多。[17]卷下217
(12)村人来卖茶菜者甚众,其中有妇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颇白皙,语音亦颇正。茶则皆如柴枝草叶,苦不可入口。[16]154
(13)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余犯涨潦时来,水漫羡不复见滩,击楫飞度,人翻以为快。[17]卷下222
(14)然滩上居民,皆利于败舟,贱卖板木,及滞留买卖,必摇沮此役。不则赂石工,以为石不可去。须断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败,皆失于重载。当以大字刻石置驿前,则过者必自惩创。[16]160
前三组描写三峡的好水,陆游与范成大二人皆借张又新《水品》来评断三峡沿途所遇之泉水。这种出自幽洞微泉、细流泠泠的水元素形象,与三峡一段汹涌多变的江水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是行船还是沿岸行走,面对江水的凶险有畏有叹,唯独少了从山间而出的流泉带给人的清秀可爱之感。第四组第五组材料“跳珠溅玉”“平如油盎”的描绘充满情趣,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如陆游《虾蟆碚》诗写道:“啮雪饮冰疑换骨,掬珠弄玉可忘年。”[18]144漂泊宦游之人见此景象,自然生出对明丽清幽之水的怜惜之情。相比于上述的涓涓细流,三峡更常见的是汹涌湍流,江水急,漩涡猛,给行人和船家可怖之感。“不可上下”“波涛大汹,濆淖如屋”“大江怒涨”,这样凶险的词汇,描绘的只是行江日常,人力在天险面前显得尤为渺小。第八组描绘滟滪堆的江水漩涡场景,水涡深旋,水沫喷涌,给予行人和船家“汗手死心”“面无人色”之感受,同时面对忽涨忽退的江水,还要拆毁“排亭诸簟舍”。范成大《刺濆淖》诗还有细腻的场景描绘:“惊呼招竿折,奔救竹笮断。九死船头争,万苦石上牵。旁观兢薄冰,撇过捷飞电。前余叱双来,山险固尝偏。”[15]215行记与诗歌的相互映照,诗文共同描绘,也充分体现了范成大胸中不平激荡之情。第九组描绘的人鲊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鲊瓮”之名本就是船行此处,船中人犹如瓮中之鱼鲊,只能听天由命之意。在人鲊瓮,昨夜停船系舟处,今日一看却是在半山间。江水的涨退,高差对比的猛烈,不仅是亲历者,即使是阅读者亦为之色变胆寒。范成大的“舟师欹倾落胆过,石孽水祸吁难全。山川丘陵皆地险,惟此险绝余难肩”[15]220四句,就在行记之外表达出此时自身的心悸,两相对照,令人称绝。
三峡之水,呈现出柔和秀气与湍急凶猛两种自然地理形态。水不仅形塑了三峡的山川怪石,也塑造了水道航道。陆游与范成大二人的三峡行记中,显现了水土关系,凸显了水对土的限制。除了自然地理形态的呈现,第十组到第十四组材料描绘的是水这一元素对当地人家和过往行船的影响。第十组材料言“水气尤毒”,第十一组材料言“水性大恶”,皆符合古人对于山水险恶的边瘴之地印象,范成大对此也有记录自己的随行婢女因为饮江水而脖颈肿大的事例。第十二组材料描绘了村妇贩茶的场景。远离京都,初来此地的陆游,经历此番奇险山水,又遇贩卖“柴枝草叶”茶水的村妇,水有好水,茶无好茶,且山阴雪来,孤山虎啸,让远放西陲的他心中萧瑟,不由吟咏道:“我行忽至此,临风久呜唈。”[18]145第十三组描述船家盘滩的模样,峡上人家以船以水为生计的民情通过水这一元素呈现,江面上“人翻以为快”的场景活灵活现。第十四组材料则是陆游在新滩面对江底锐石摧毁行船之滩害的感慨。官员有心治理锐石,滩上居民却以贩卖板木给破船从而获利为由进行阻挠。这些都是水元素的另一种呈现形态,水元素塑造三峡的自然地理形态,也塑造了其人文形态。水元素的人文形态其实也表现出一种脱离土地束缚的倾向,但归根结底还是影响并塑造着土元素。
三峡行记中的土水关系,还有另一层连接关系。试看陆游这几首诗:
秭归城畔蹋斜阳,古寺无僧昼闭房。残佩断钗陵谷变,苫茆架竹井闾荒。虎行欲与人争路,猿啸能令客断肠。寂寞倚楼搔短发,剩题新恨付巴娘。(《憩归州光孝寺寺后有冢近岁或发之得宝玉剑佩》)[18]149
一邑无平土,邦人例得穷。凄凉远嫁归,憔悴独醒翁。今古阑干外,悲欢酒盏中。三巴不摇落,搔首对丹枫。(《饮罢寺门独立有感》)[18]149
暂借清溪伴钓翁,沙边微雨湿孤篷。从今诗在巴东县,不属灞桥风雪中。(《巴东遇小雨》)[18]150
瘦尽腰围不为诗,良辰流落自成衰。也知客里偏多感,谁料天涯有许悲。汉塞角残人不寐,渭城歌罢客将离。故应未抵闻猿恨,况是巫山庙里时。(《闻猿》)[18]154
人生未死信难知,憔悴夔州生鬓丝。何日画船摇桂楫,西湖却赋探春诗?(《蹋碛》)[18]162
参差层颠屋,邦人祀公孙。力战死社稷,宜享庙貌尊。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我欲伐巨石,作碑累千言。上陈跃马壮,下斥乘骡昏,虽惭豪伟词,尚慰雄杰魂。君王昔玉食,何至歆鸡豚,愿言采芳兰,舞歌荐清尊。(《入瞿唐登白帝庙》)[18]156
前五首诗是陆游面对三峡景观,触景生情,对于自身明升暗降、远离京华的现状有着诸多苦闷与惆怅。这种情感随着离东面繁荣城市愈远,离贫穷落后西陲愈近而更加强烈。一路过来,各种景观与景点,秭归古城,屈原与昭君,空山虎啸,秋风萧瑟,都给予他凄凉之感。他犹如不胜哀愁的老翁,倚楼栏杆,短发不堪搔挠,旧愁新恨下的古今重叠,犹如屈子放逐、杜甫飘零,前人之感使其倍加心酸。巴东与灞桥、天涯与故里、夔州与西湖,都在陆游的诗中连接了起来。带有隐喻性质的由东至西之旅,陆游通过这条长江水道而来,情感在三峡达到了巅峰。水的流动、水的无形“载不动许多愁”,它将距离隔开,却将情感连接。三峡的无数意象,水、水上之石、石上之猿鸦,都使得无数人在此留下了愁思哀绪,在陆游的行记中,三峡的水元素将这种连接体现了出来。张聪认为“由于在如何获取知识的讨论中所产生的观念变化,结果以前被认为令人生畏的、使人不快的事情,如远行去赴任、求学、赶考等都具有了新的意义:目的地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了”[19]230。这样的评断失之偏颇,赴任有升有降,求学与赶考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来看,漂泊凄凉之感不会因为所谓“远方有山水新奇未见之事物”的获取知识观念发生变化就会改善。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悲的情绪会充斥在从上层到下层的境域转移中。
除此之外,与士人天涯之悲同时并存的是士人的家国之忧,对于家国命运的思考。田峰按照主体与目的的不同,将唐宋行记分为僧人行记、交聘行记、文人行记三大类[9]54。交聘行记有不同于文人行记的特点,即对于夷夏之防与领土意识的强调。这种强调通过交聘行记中“他者”的描绘来呈现,是南宋士人在面对恶劣的外交环境和鲜明清晰的国家残缺、国界收缩后的自发呈现。刘师健认为正是这种政治生态,造就了南宋士人“中国”意识的凸显,对于夷夏之防与领土有缺的焦虑与思考[20]。虽然这是交聘行记中的鲜明特色,但是文人行记寄托的形式与情感在天然上有相通之处,文人行记所记载的游历经历立足于国土,这正是对于国土的一次重新确认,对于国土丢失现状的愤慨和强调,士人官员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由此激发。陆游登白帝庙,有感于公孙述坚守抗战至最后一刻,对于前宋被掳帝王、仓皇南奔的士人、偏安一隅的现状都有着愤慨,说出了“丈夫贵不挠”的宣言,更是希望借此谏言君王,“君王昔玉食,何至歆鸡豚”,不应屈服于北虏铁蹄,而应矢志有为。同样有关于君王的内容,出蜀回乡的范成大则言“天子赐之履,江神敢吾玩?但催叠鼓轰,往助双橹健”[15]215,是在另一种程度上强化南宋政权对东西领土的确认,强化国家政权在土水关系中的上层地位。恰如《诗经》所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1]1141,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水的确起着连接的作用,在陆游、范成大诗文中都有所体现。
土水是二人三峡行记中的主导元素,在三峡和南宋这两处层级较大的境域中,既有着限制因素,也有着连接因素。而天元素在三峡行记中是作为土水的附属元素,不特别突出自身的存在,它的存在是提供一种对比的心态,给行经三峡的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如《入蜀记》:“孤起侵云,名天柱峰。”[16]154“如屏风迭,嵯峨插天。”[16]156“两山对立,修耸摩天,略如庐山。”[16]158“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匹练然。”[16]171此处的天成为山势层叠高耸的参照系,“插天”“摩天”是以观者的视角,脚踏土地或舟船(即江面,视为水元素),仰望高天,天弥远,山弥深弥高。这种参照系是天元素在三峡地区对于行人与船家的一种心理威慑,王凌云在论及儒家思想中的天元素时,认为他们对于天的领会也是以土地主导,以下向上,因此他们敬重所有位于高处的东西,如“天命”“大人”“圣人言”[12]144。这种分析从思想与哲学层面入手,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但是具体到三峡这一区域及其行记而言,天元素成为具体的境域,参与进山水与人的审美心态塑造中。在塑造中,它也会产生自己的独特功用,如《吴船录》的一处描述:
三十五里,至神女庙。庙前滩尤洶怒,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后蔽亏,不能足其数。最东一峰尤奇绝,其顶分两歧,如双玉篸插半霄,最西一峰似之而差小。余峰皆郁嵂非常,但不如两峰之诡特。相传一峰之上,有文曰“巫”,不暇访寻。自县行半里,即入峡。时辰巳间,日未当午,峡间陡暗如昏暮,举头仅有天数尺耳。两壁皆是奇山,其可拟十二峰者甚多。烟云映发,应接不暇,如是者百余里,富哉其观山也。[17]卷下219
这是范成大对于巫山神女峰一带行程的记录,天元素在这里如上文所述的“插半霄”来体现山势高峻。但范成大不止于此,其言“日未当午,峡间陡暗如昏暮,举头仅有天数尺耳”,天在此时被压缩,但是天元素的主导却无限地加强,天带给人的压迫感是通过日光的昏暗来体现的,而这又是土元素主导的山导致的。土元素影响下的天元素在此时凸显,给予人独特的观感,昏暗与压迫感扑面而来,使人心悸。这种因为参照系的变化而导致的感受错位,正如陈与义“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22]的心理体验。而相类似的文句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亦有提及,“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23],也正是通过这种写法,足见三峡诗文历代流传的影响。此段行过,范成大感受是“烟云映发,应接不暇,如是者百余里,富哉其观山也”,同样是天元素在强烈的对比下给予人的审美心态感受,烟云笼罩,与山木山水相映,更显可爱。天元素在与土水关系的配合中,打造出的“畏与喜”使行经于此之人之感受无比深刻。
气元素的呈现形态是风,但在行记叙述层面,非是自然形态的风,而是人文思想领域抽象化过的风。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物民俗,中国教化传统早在《诗经》中就非常成熟,《毛诗大序》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21]16,风针对不同地域反映不同的民情以体现政教观念,这就是气元素在思想领域的呈现。在南宋的三峡行记中,在政教领域之外我们还能看见其他的风元素呈现,具体分为三类:政风、文风与民风。
政风是陆游与范成大行记中关于地方政务的记载与描述,这中间包括行政区划、民族财税、地方建设等内容。如前文所言新滩,官员欲除滩害,地方百姓却以滩害获利,使得政务难以推行,只能刻石以作提示。无独有偶,类似推行政务的记录《吴船录》中也有。麻线堆亦是险滩,但有道人伐木开山,避过险厄处。范成大感慨官司为何不能,自己所任官职号令不达此处,因作《麻线堆》诗给峡州(治今湖北省宜昌市)、归州的四位主要官员以示劝解。除了政务,范成大也记录了少数民族成分:“涪虽不与蕃部杂居,旧亦夷,俗号为四人。四人者,谓华人、巴人及廪君与盘瓠之种也。”[17]卷下214还有地方财税问题:“归故尝隶湖北,近岁以地望形势正在峡中,乃以属夔,是矣。而财赋仍隶湖北,岁输止二万缗,而一州两属,疲于奔命,非是。当别拨此缗补湖北而并以归隶夔,始尽事理。”[17]卷下221以及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州宅有楚塞楼,山谷所名。古语曰:‘荆门虎牙,楚之西塞。’夷陵即其地。自古以为重镇。三国时,又为吴之西陵。陆逊以为夷陵要害,国之关限。今吴、蜀共道此地,但为蕞尔荒垒耳。”[17]卷下223这些都属于为政一方的官员需留意的基本问题,尤其在多民族杂居的西南地区,行记虽然有其文学性,但是其内容也包含实录部分,也能为旁人后人提供情报支持和出游借鉴。
在具有实录性质的政风中还夹杂着一种与之相对的吏隐风气,陆游拜谒寇莱公祠时,对白云亭如此评价:“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止在县廨听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16]166“无如白云者”表达了陆游对此景色的肯定,延伸了对为官的态度。自魏晋以来,山水意识在文人心中觉醒,文人的隐与显、穷与达理念开始频繁出没于他们的作品中。陆游反问,在此处为官,“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一个简单的反问,表明陆游此前因外放西陲郁郁心态的疏解,是三峡土、水、天、气各种元素构成的境域对他的影响。范成大《万州》诗同样表明了此种心态:“营营谋食艰,寂寂怀磗诉。昔闻吏隐名,今识吏隐处。”[15]221
文风是文人之风,体现在二者的行记中十分明显,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在纪实性方面,二人考察地理沿革、旧物源流:
(1)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然地比归州差平。或云,楚始封于此。《山海经》:夏启封孟除于丹阳城;郭璞注云在秭归县南。疑即此也。然《史记》:成王封熊绎于丹阳;裴骃乃云在枝江。未详孰是。[16]162
(2)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缺处铁色光黑如佳漆,字画淳质可爱玩。有石刻鲁直作《盆记》,大略言:建中靖国元气,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摄县事……又有将军墓,东晋人也。一碑在墓后,跌陷入地,碑倾前欲压,字才半存。[16]170
(3)岩壁刻字尤多,坡、谷皆有之。坡书殊不类,非其亲迹。寺屋尤弊坏。昔有刘道者创之,刘死,凿岩壁以藏骨,今有石室处可辨也。[17]卷下217
陆游在第一组中,引经据典,考察旧址,对于书中所记与实际地理难以相符者,陆游并不盲从,妄下己断,“疑”“未详”的字眼体现了其人严谨。第二组中,将具有历史与文物价值的旧铁盆和碑文进行考证,对于外形和铭文都有自己的见解,体现了宋时学者的深厚金石学功底。范成大亦同,面对岩壁刻字也会进行分辨考证,不人云亦云,体现了其学术功底。包括二人在内的许多文人在三峡地区进行考证式的文化活动,使得这种纪实性的文风在行记中凸显出来,彰显行记资料实录的优点。文学性在陆游与范成大身上的体现更是毋庸置疑,陆游记录登秋风亭之场景:“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16]166陆游描写景物清新灵动,写树写水,冷冽不失感情,使人读来津津有味。又有其他三言两语描写间杂于各条行记之中,如“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丽”[16]170“然月明如昼,儿曹与全师皆杖策相从,殊不觉崖谷之险也”[16]161,既写出景色绝佳,又与游人心态相应,字里行间可见喜悦之情。范成大对于归州经历,其写道:“属邑兴山县,王嫱生焉。今有昭君台、香溪,尚存。城南二里有明妃庙。余尝论归为州僻陋,为西蜀之最,而男子有屈、宋,女子有昭君。阀阅如此,政未易忽。”[17]卷下221语言朴实却带有历史跌宕之感,通过凭吊前人,古今感慨从行文中缓缓透出,使人玩味琢磨,印象深刻。
民风是三峡行记中的最基础部分,写一地土水,必有生活在土水之上的人。三峡地区独有的地貌环境,也塑造了不同的风物风俗。如陆游写妇女汲水背水,“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尺,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16]160。对于这样有别于东部州府的场景,陆游用饶有趣味的笔触进行描绘,在诗中也给予笔墨,言“村女卖秋茶,簪花髻鬟匝,襁儿著背上,帖妥若在榻”[18]145;范成大有诗句“瓦屋仄石磴,猿啼闹人语。剔核杏余酸,连枝茶剩苦”[15]221,这些都是三峡地区的风物写照。《吴船录》言归州“满目皆茅茨,惟州宅虽有盖瓦,缘江负山,逼仄无平地”[17]卷下220。《入蜀记》言巫山八月十五月圆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16]168。就连作为水果的杏,当地土人贩卖的时候还要先挖出果核卖作药材,余下杏肉只有酸味。而茶水前文有述,陆游言其柴枝草叶。这些风物风俗的描绘,展现的贫穷又落后恶劣的民风,与江左风俗不同,更遑论范成大所谓“戏题”的《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顷在峤南,其人好食槟榔合蛎灰。扶留藤,一名蒌藤,食之辄昏然,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脓血可厌。今来蜀道,又为食蒜者所熏,戏题》[15]226。二人还写三峡地区“出美梨,大如升”[16]171、有荔枝闻名,曾是杨贵妃上供专用。结合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对于三峡地区的肯定和赞赏,更多来自此地独特的自然地理,以及遗留下来的人文风貌。行记是富于生命力和时代感的个人经历记录,安插于行程叙述间的古诗借之获得精确注脚,回归原始情境和世俗[24]。对于边陲烟瘴之地的轻视与抗拒,在三峡一地真正发展起来之前,一直存在于古代文人的心态之中,这种心态是透过文字笔墨代代相传的,也正是行记与其作者诗文的长久影响,我们在回首这些内容的时候,对此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