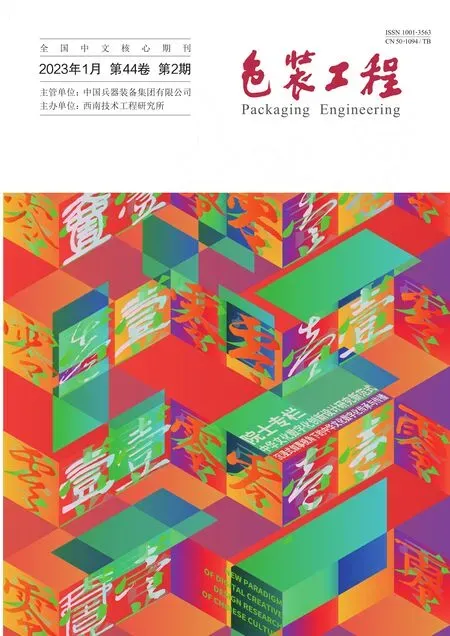威胁诉求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有效与无效
胡垛垛,何吉波,雍琳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兰州 730070)
道路交通事故一直是造成人类死亡和受伤的重大因素之一,也是全世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20 年的全国交通年度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驾驶员数已经超过4 亿。全国交通事故发生数总计244 674 起,造成61 703 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2017 年的报告中强调,道路交通碰撞导致的死亡是发展中国家的十大死亡原因之一。根据WHO 估计,到2020 年,车祸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死因。
为了有效缓解这一状况,世界各国都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展旨在鼓励驾驶员安全驾驶的教育项目和媒体宣传活动,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不良的驾驶行为,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并降低其严重程度。威胁诉求(也称恐惧诉求)就是主要的策略之一,通过向公众展示一些行为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事实,以威胁为基础,引发驾驶员的恐惧与焦虑,促使人们避免或者执行某种特定行为[1]。为此,国外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几十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尽管有证据表明,当威胁诉求与提高效能感相结合时其有效性可能十分显著[2-3],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其他研究显示,它们也可能没有作用,甚至引发负面效果[4-5]。这意味着,威胁诉求的有效性仍是不明确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很难有效地向道路安全从业者提出关于威胁诉求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尽管目前难以给出明确结论,但理解威胁诉求对驾驶安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找出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是明确威胁诉求有效性的关键。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总结目前已有的国内外关于威胁诉求与驾驶的相关文献,并结合相关的理论模型,对威胁诉求与驾驶安全的关系进行讨论分析,试图找出导致威胁诉求有效性不一致的原因,为国内威胁诉求与驾驶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探索视角。
1 相关理论模型
任何行为改变策略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提出的[6],用于解释威胁诉求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有多个[7]。最早提出的是恐惧驱动模型(Fear Drive Model),该模型认为威胁诉求会唤醒个体的恐惧情绪,个体为了维持情绪稳定,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恐惧就成为了促进个体采取行动的驱动力[8]。在此基础上,早期研究提出了恐惧与说服的线性关系,认为恐惧唤醒水平较高更有利于说服[9],但有研究者发现,随着恐惧唤醒水平降低,说服效果更好[10]。为了解释不一致的发现,倒U 型曲线关系被提出,认为恐惧唤醒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此时的说服效果最好,唤醒水平低于或高于临界点,都不利于说服[11]。但这一模型没有得到后续研究的证实。
由于恐惧驱动模型存在弊端,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理论——并行响应模型(Parallel Response Model,PRM),这一模型在情绪的基础上,更强调认知的作用,认为恐惧说服可能存在两种反应模式:一种是恐惧控制,即恐惧唤醒会使个体拒绝信息,产生非适应性行为;另一种是危险控制,即个体会接收威胁信息,并产生适应性行为[12]。这一模型虽然提出了这两种不同的说服路径,但并没有明确这两种路径出现的条件。
Rogers[13]提出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变量:感知威胁(Perceived Threat)和感知效能(Perceived Efficacy),其中,感知威胁涉及个体感知威胁的严重性、易感性以及回报等要素,感知效能则涉及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及反应代价等要素。保护动机则是二者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决策——是否形成保护动机,针对威胁采取保护行为,在评估与实际行为之间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14-15]。保护动机理论认为,对威胁的严重性和易感性的感知、自我效能、反应效能与促进健康行为出现相关联,而回报及反应代价与导致不良行为出现有关[16]。该理论解释了恐惧因素起作用的条件(即感知到高威胁,以及高效能,可以促进受众接受信息),但是没有解释恐惧因素不起作用的原因。
为了更明确地区分恐惧情绪与认知加工,进一步解释威胁诉求成功和失败的原因,Witte[17]在结合PRM 模型和PMT 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拓展平行处理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其核心观点在于,威胁信息引起的恐惧情绪会导致高水平的信息接受,但恐惧情绪并不直接影响威胁诉求信息接受,个体只有在将恐惧情绪唤起之后,对信息进行威胁评估和效能评估,才能引发态度、行为的改变。根据EPPM,个体接收到威胁诉求,会先进行威胁评估,当感知到的威胁水平较低或者与个体无关时,个体会忽略威胁诉求信息。当感知到的威胁水平较高,个体就会进入第二轮的效能评估,即当个体的效能感较高时,会采取控制危险的方法,接收建议措施,即产生适应性行为;相反,当效能感较低时,个体会采取控制恐惧的方法,通过否认、逃避或抵抗来缓解恐惧,产生不适应性行为。
EPPM 模型目前是威胁诉求领域的主流理论。但也有其他研究者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索其他因素的作用,其中研究较多是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该理论认为人类求生的本能会使其产生对死亡的焦虑,个体的死亡意识被激活产生死亡焦虑时,就会采取一系列防御机制来缓解这种焦虑[18],如维护文化世界观、提升或维持自尊、追求亲密关系[19-20]。
2 威胁诉求与驾驶
这些理论模型为威胁诉求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解释的基础,各国都在不断尝试着将威胁诉求这一策略应用到道路安全活动中,以期有效地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率。诸多学者对威胁诉求在驾驶领域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研究结果引发了争议:威胁诉求有效还是无效[3,21]?现有的大量研究为这种两种不同的立场提供了证据。
2.1 威胁诉求有效的证据
威胁诉求有效的证据表明,适度的恐惧唤醒、威胁感(事故的严重性与易感性)和较高的效能感、有效的可执行的建议等,是威胁诉求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大量的元分析通过分析威胁诉求、死亡提醒等相关文献,在整体上检验了这类信息对于公众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22-25]。Witte 等[22]关于威胁诉求对有效公共卫生运动影响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强烈的威胁感和高效能的提醒信息组合,能够使行为改变最大化。为了进一步探讨威胁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有效,Tannenbaum等[23]对248 个独立样本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几乎所有被分析的情况中,威胁诉求都能有效地影响个体的态度、意图和行为,随机效应d=0.29,并且当信息内容的效能感、易感性、严重程度都高、建议行为为一次性,以及女性在目标受众中比例较大时,能够增加威胁诉求的有效性。其他许多相关的元分析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24-25]。另外,一项旨在探讨驾驶员对不同类型道路安全广告有效性的认知的研究表明,以恐惧为核心的诉求比其他类型方法更能吸引个体的注意力[26]。总体而言,基于该领域的元分析提供的证据,研究者认为威胁诉求是有效的。
对此,道路安全相关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道路安全作为公共卫生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威胁诉求在驾驶安全领域中的应用是否如上述研究中一样有效呢?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接连掀起了电视广告运动,试图向公众呈现各种由于饮酒、超速导致的血腥的撞车场景,通过这种威胁诉求的策略来降低超速驾驶和酒后驾驶事故数。Tay[27-28]对澳大利亚维多利达州实施的反酒驾、反超速的执法和广告活动的有效性进行了重新评估,结果表明反酒驾的执法和广告活动都能够有效减少撞车事故数量[29-30]。对此,有研究者提出质疑,由于在同一时期存在加强广告活动与增强执法力度,广告活动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执法水平[31-32],Tay[28]通过在检验执法与广告关系的模型中加入交互项,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广告活动的有效性由执法活动决定。Tay[33]对8 项关于以威胁诉求为内容的广告活动与酒后驾驶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与上述一致的结果,大众媒体活动有效降低了酒驾事故数。即使这些研究不能直接对威胁诉求进行推论,但以威胁诉求为核心的广告与交通事故数的降低确实存在某种关联。为了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Ross Owen 等[34]将元分析所在文章的发表偏倚和异质性纳入考虑范围,最终从67 项相关研究中提取出了119 项结果,加权平均后的效果是道路安全宣传活动使交通事故减少了9%。上述研究并没有像在实验中那样控制额外变量,因此,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其他性质的风险行为上应保持谨慎。之后诸多研究者在实验条件下对此进行探究,Borawska 等[21]在探究公益广告中不同消极情绪强度水平对道路安全宣传活动的影响时发现,高度消极刺激和中度消极刺激都能够减少被试的危险驾驶行为意向。同时,威胁诉求能够降低个体的冲动性决策程度[35]。其他研究尝试着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去解释威胁诉求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结果发现,在呼吁减速的信息中,基于威胁评估的(感知严重性、脆弱性)的信息比基于司法评估的信息更为有效[2,36],个体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及效能感越高,越有助于改变个体的态度与危险意图[37]。此外,Lewis 等[38]从认知和情感成分的角度,证实了反超速广告引起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对接受和拒绝信息都有影响,当被试的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都较高时,他们更可能接收威胁信息,更有效地降低自己的速度。Carey 等[3]也指出,当面对威胁信息时,呈现给个体关于威胁信息的问题,如“采用什么策略避免碰撞?”,同时给予相应的建议,如“不要超速”,有效降低了个体的车速,但个体的愤怒情绪可能会抵消威胁与效能、建议相结合的信息的潜在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可知,恐惧唤醒、威胁感(事故的严重性与易感性)和效能感、可执行的建议等的有效结合,能使威胁诉求的作用最大化,但也要考虑不同的情绪状态对说服效果的影响。
2.2 威胁诉求无效的证据
尽管上述多项研究都表明,威胁诉求是有效的,但是也有研究显示威胁诉求的积极作用并不存在,甚至可能引发负面影响,这可能与恐惧唤醒水平过高或过低、威胁信息的成分组合不当、实验设置的不同等因素有关。
Carey 等[1]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1990 年至2011年进行的关于威胁诉求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的实证研究(K=13,N=3 044)进行了分析,探讨威胁信息对驾驶员的恐惧唤醒、驾驶行为的作用。结果显示,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恐惧唤醒程度显著增加(r=0.64,p<0.01),但实验组的危险驾驶意图与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r=0.02,p=0.38),在模拟驾驶器上的速度也是如此(r=0.08,p=0.26)。Plant 等[39]在给被试呈现描绘撞车的反超速广告后,确实唤起了实验组的消极情绪,但被试的车速并没有显著降低。这说明,威胁诉求确实会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情绪唤醒,但这种恐惧情绪并不会对实际的驾驶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这可能是因为威胁信息与自我无关,那么,当威胁信息与个体本身有关时会不会影响意图与行为?固然,个体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因为不同的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但是这种威胁与个体是否直接相关,严重影响其有效性[40-41],与个体无关的单纯的恐怖情绪可能并不会导致行为的改变。然而,King 等[42]发现,即使操纵了威胁焦点(自我伤害与他人伤害),个体自我报告的酒后驾驶意图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威胁诉求不能有效促进驾驶员行为的转变,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威胁诉求可能会引发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导致更多的危险驾驶意图及行为。万薇洁等[43]以受众的注意力与内隐态度为指标来测量不同效价和不同唤醒度的交通安全广告情感诉求的说服效果,研究发现,高唤醒度的消极情感诉求广告会导致个体对正确驾驶行为的积极内隐态度的降低。Lennon 等[44]在研究年轻司机对于四种分心驾驶行为(包括边开车边发短信)的态度与意图的研究中,让他们观看基于恐惧的阻止分心驾驶的公益广告,报告个体的不安全行为意图,结果显示,年轻司机的分心驾驶行为意图显著增加,其中,与女性相比,男性意图增加更为明显。Carey 等[4]的发现也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接触与驾驶相关的死亡事实比接触中性信息的个体冒险驾驶的意愿更高,即使这种发现只存在于那些认为驾驶相关自尊较高的群体中[45]。Mairean 等[5]的研究扩展了之前的研究结果,发现当评估死亡威胁和驾驶与自尊的关系时,死亡威胁条件下的被试比在控制条件下的被试表现了更高的超速,而且与交通事故相关的死亡威胁条件下的被试的危险驾驶行为意图并没有改变。考虑到意图并不是一个衡量行为的完美标准[7],Ben-Ari 等[46-47]除了考虑态度与意图,同时将驾驶模拟器上的驾驶速度作为因变量,发现在驾驶相关自尊较高的个体中,威胁诉求会导致更快的驾驶速度。
综合以上观点,威胁信息对于改变不良驾驶行为似乎没有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些研究与认为威胁信息有效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呢?其一,该领域大多数研究都基于一个假设,即威胁诉求信息必定成功唤起个体的恐惧情绪,并且是威胁信息引发的唯一情绪[48]。但研究表明,威胁诉求除了引发恐惧情绪以外,还有内疚和懊悔、焦虑[49]。Carey 等[3]将愤怒作为变量引入研究中,发现愤怒可能会对信息的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厌恶情绪的峰值可以预测说服的有效性[50]。其二,在威胁诉求领域,关于恐惧情绪与行为的关系,普遍遵循直接因果模型,即认为恐惧情绪直接引起行为改变。但实际上,恐惧情绪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如自尊[46]。Li 等[49]还提出情绪与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其三,就已有研究而言,驾驶测量的实验部署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影响了实验操作的敏感性,例如操作方式、因变量(自我报告的态度及行为意图、驾驶模拟器、模拟驾驶场景、视频图像)的不同。早期研究者们就曾经对这些因变量的生态效度提出了批评[51],并且结果可能由于社会期望而出现混淆[52]。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构成威胁信息的成分,现有的研究表明,威胁信息中所包含的威胁的严重性(高威胁、低威胁)、可感知性(易感知、不易感知)、效能知觉(高效能、低效能)是影响其有效性的核心因素[2],威胁信息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可能会导致相反的行为反应,但实际上,以往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将这三个因素都纳入考量。
3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现有研究对威胁诉求在驾驶安全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存在的若干局限性。首先,有人提出,威胁诉求与道路安全的大部分研究都依赖被试自我报告的态度及行为意图作为预测行为转变的衡量标准[36],意图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39]。只有极少数文章同时采集了驾驶意图和驾驶模拟器的数据[46-47],却发现在认为驾驶与自尊相关的群体中,驾驶意图与实际的驾驶行为相矛盾,虽然他们报告了较少的鲁莽驾驶意图,但有较高的驾驶速度。因此,单纯测量个体的态度或行为意图,可能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威胁诉求有助于行为的转变。
其次,早期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于反酒驾的威胁诉求信息上[27-28,33,42,53],后续研究者虽然关注到了近几年来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的分心驾驶、超速驾驶等[2-3,36,44]因素,但危险驾驶中涉及的心理社会因素在不同类型的行为中有所不同[54],例如酒驾、超速和紧跟。并且,几乎没有关于疲劳驾驶、愤怒驾驶、强行换道、不按规定让行等风险行为的研究,张圆等[55]以我国广东省交通事故数据为基础,发现由于不按规定让行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所占比例最高。因此,目前的研究尚缺乏对于这些风险行为的探讨。
再次,该领域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效果的即时性,具体来说,就是目前的研究关注的都是短期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威胁诉求持久的作用[3]。Lewis 等[56]在探讨威胁信息的说服力时发现,消极信息的即时效果更好,而积极信息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好,这说明,威胁诉求的效果与时间可能存在联系。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恐惧诱导的情绪体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衰退,但相应的行为转变得到了加强[57]。作者认为这种干预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为人们提供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的机会。
最后,关于威胁诉求的文献大部分研究都是实验室实验(除了少数几个是调查19 世纪末澳大利亚、新西兰广告活动成效的研究)。尽管实验室实验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但其与实际环境确实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为其人为性是众所周知的,这可能导致被试的实验表现与实际表现存在偏差。例如,Hastings 等[58]就提出,这种类型的研究可能会迫使被试关注他们平时不会注意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在现实中的应用性。
4 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也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即威胁诉求起作用的关键在于威胁唤醒、严重性、可感知性、诱导的情绪体验以及有效的可执行的建议与措施。今后研究者们可以尝试从这些方面进行探索:通过综合恐惧唤醒、威胁感、效能感、情绪、有效建议等方面确定道路安全领域中威胁诉求的最佳类型,也可明确威胁信息究竟会引发哪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又会如何影响意图与行为,确定哪种情绪是最有效的;将威胁诉求的方式推广到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上,以确定威胁诉求的效度;克服现有研究即时性的问题,可以试图探索威胁信息对个体产生的即时作用和长久效果。同时,针对以往研究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所存在的弊端,有必要考虑在自然环境中探讨威胁信息对驾驶员的影响,如高速路牌广告、室外LED 广告[2]。当前,我国在威胁诉求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根据我国独特的国情探索中国人的威胁诉求机制,是我国研究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5 结语
威胁诉求的广泛使用表明其在驾驶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目前,研究者们对威胁诉求在驾驶领域的实际应用做出了诸多尝试,探索了许多对威胁诉求起关键作用的调节因子,其是否能够有效减少风险驾驶行为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论,毫无疑问,在短时间内,这个问题可能仍然无法解决。但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推动了驾驶安全研究领域的进步,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