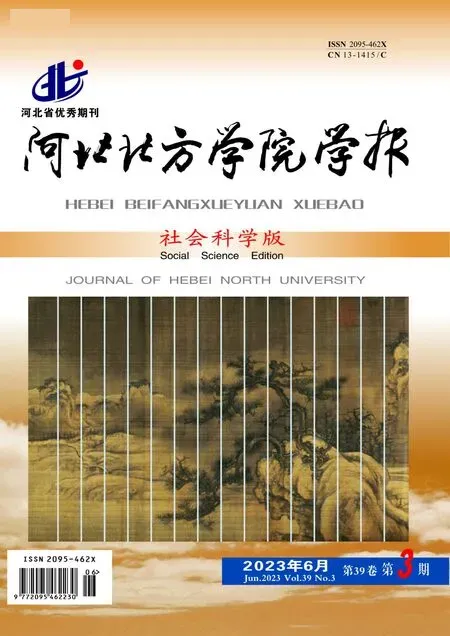浅析中西方戏剧语言及戏剧音乐的特色
詹 元
(沈阳音乐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语言”是戏剧文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构成戏剧文本的基础载体。戏剧语言包含了丰富的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哲理。每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都通过生动而诗性的语言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演变,也凝结着剧作家的思想情感和智慧。音乐同戏剧结合后,可表达各种复杂多变的情感色彩,渲染气氛。音乐与戏剧的交相辉映是听觉与视觉的完美结合,促成了艺术欣赏的极高境界,使观众获得更高的精神享受。戏剧艺术领域不存在永恒的戏剧语言法则,戏剧音乐也始终在向前发展。因此,中国戏剧艺术家应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语言风格和更具审美价值的戏剧音乐[1]。
一、中西方戏剧的起源
处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始戏剧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戏剧是戏剧的源头,这些原始音乐文化的土壤孕育了戏剧艺术。随着古代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原始戏剧开始表现出人们对审美以及对诗性的追求,真正的戏剧也随即进入成熟和繁荣时期。
(一)中国戏剧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的傩戏以及各种民间仪式戏剧和宗教戏剧也有数千年历史。《吕氏春秋·古乐》中就明确记载了一场典型的“杀牛祭”,其中“三人操牛尾”和“八阕”的表演带有简单的情节,可称之为原始戏剧。自两汉至隋唐,民间乐舞百戏也一直活跃在各种勾栏瓦肆中,成为中国戏剧生成的重要文化土壤。中国戏剧的初期,以歌舞为主,角色较少,剧情简单。从元杂剧开始,剧中的人物渐增,具备唱、科、白和完整的剧情。从音乐的表现形式看,中国戏曲音乐有一定的体式,是由唱曲牌的“联曲体”和唱七字句或十字句的“板腔体”以及对两者的综合使用而构成。
在中国古代,由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人们更多地强调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重直观体悟而少抽象思辨,实际上也就是将审美与生活相融为一。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更多地强调个人情怀的抒发,从元、明、清直到近代,以小说和戏曲的兴盛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则从高雅意趣走向世俗生活的真实,市民文艺的发展彰显了其审美文化的意义[2]。
(二)西方戏剧的起源
与中国戏剧相比,古希腊戏剧起步较晚。古希腊戏剧最早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人们在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中吟唱酒神颂,这种祭祀仪式最终发展成为古希腊的戏剧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古希腊戏剧走向繁荣,并在之后的古罗马文化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中世纪,欧洲宗教戏剧蔚然成风,如神秘剧、圣剧和鬼神剧等。同时,欧洲各国的民间戏剧都风行一时,如中世纪英格兰乡村的“假面哑剧”、法国“愚人节”的讽刺笑剧及闹剧等,正是这些中世纪的宗教戏剧和民间戏剧才真正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繁盛提供了重要的土壤[3]。在19世纪之前,欧洲戏剧剧本大多属于“剧诗”,但其他类型的戏剧基本上包含了音乐的成分。如正规的希腊戏剧里都带有合唱团,还有古希腊的羊人剧等也都有音乐融入其中。
在西方的戏剧观念中,戏剧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文人的传统,属于一种典型的诗的形式。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这种净化与陶冶的观念就已经根深蒂固。相对于史诗(叙事诗)与抒情诗而言,戏剧是一种综合了史诗与抒情诗的特殊形态的诗。因此,西方戏剧在本源上仍属于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此外,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就起源于酒神祭祀和丰收庆典,具有明显的大众狂欢和民间节日的色彩。
二、中西方戏剧语言
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都根植于本土文化之中,不管是差异还是相同点,都可以在共存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并推陈出新。
(一)中国戏剧语言
中国的传统戏剧通常称为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中国戏曲语言以唱词为主,又辅以宾白。唱词是有戏剧特性的诗,宾白也是具有戏剧特性的散文。中国戏曲语言的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用案头之词或文学之词以及雅化或俗化,戏曲语言都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例如,明清传奇戏曲的语言风格经历了由俗变雅—由雅趋俗—由俗返雅—变雅为俗的变迁。但对普通听众而言,传奇戏曲的文辞过于艰深、含蓄和曲折,较为不好理解。例如,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等词,普通观众听后就会颇为费解[4]。
中国戏剧语言分为3类,“心口皆深”“词浅意深”和“词浅而意亦浅”。“心口皆深”指作品文辞含义精深;“词浅意深”指作品用语浅近,但含义深远。既不会降低语言的美学意蕴,也不会粗俗和浮泛,“词浅意深”可以将街谈巷议的生活口语甚至俗语加以提炼,从而创造出通俗优美、脍炙人口且生动活泼的文辞;“词浅意浅”指作品用语浅近且含义浅显,美学意蕴也很低。
戏剧语言应该通俗易懂和朗朗上口,不应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去刻意堆砌辞藻。台词语言应精炼,尽可能地去掉无意义且可有可无的部分。中国经典的戏剧作品,其唱词都是戏剧作家经过了反复推敲和千锤百炼,在语言文字的锻造方面更加注重恰当、准确、简洁和精炼,以中国话剧为代表,剧作家们将戏剧语言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老舍的戏剧语言将人物性格刻画得炉火纯青,如在《龙须沟》和《茶馆》等话剧中,对俗白口语的运用恰到好处,语言口语化,充满生气。老舍将性格化、幽默化以及哲理性等特色的语言表现方式有机结合,开创了戏剧语言民族化和口语戏剧化的独特范式,是中国公认的戏剧语言大师[5]。
(二)西方戏剧语言
对西方剧作家而言,戏剧语言造就了戏剧的气质、风格和特色,需要剧作家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如双关语是西方戏剧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它运用语音和语义的联系使词语或句子具有双重含义,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这种修辞手法常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到了20世纪末期,戏剧的文本呈现多元化的形态。与传统的固定文本不同,实验色彩很强烈的反传统固定文本、即兴文本和无言辞戏剧相继出现。诸如荒诞派戏剧、未来主义戏剧以及超现实主义戏剧,其文本语言支离破碎、荒诞不经且毫无逻辑,有的甚至整个剧本只有两三句台词。尽管当代戏剧在实验探索的潮流中弱化了戏剧语言,出现了只有一两句台词的剧本,甚至没有语言的文本,意图创造出另外一套戏剧“语言系统”。然而,这些舞台艺术并非戏剧的主流,语言仍是戏剧传达思想感情的有效手段,是戏剧叙事的基础载体。
(三)中国戏剧中的诗性
诗性可以理解为艺术家与欣赏者共同构筑的一种“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以抒情写意为核心,以创造意境为主旨。具体表现为诗化的语言、诗化的动作、诗化的叙事、诗化的节奏以及诗化的意境等。
在中华文明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产生最早(远古),散文产生较晚(先秦),小说与戏剧产生更晚(宋元以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发展。诗化风格在传唱至今的杂剧、南戏和传奇经典中有所体现,如《西厢记》可以视为元杂剧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不仅题材生动,而且人物刻画细致形象,其曲词尤为优美华丽,富有诗的意境,可以讲每一只曲子都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
放眼中国戏剧舞台,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佳作都与剧作家对台词诗意的精心布置密不可分。以当代剧作家王仁杰创作的剧本《董生与李氏》为例,王仁杰将中国戏曲的诗性精神发挥到极致,如女主人公李氏在一曲《长寡·空闺恨》的哀哀吟唱中姗姗登场:“乍吟白头,何曾到白头!游丝悬君命,冷月照孤舟。虽未效孟姜哭夫,绿珠坠楼,但恐望夫石畔,亦作了怨妇空自守。”观众被王仁杰笔下唱词的诗意、柔婉和真诚所打动,绝不会认为这对旷男怨妇的结合是为人所不齿的逾“礼”之举,这就是剧作家在精心营造的诗意氛围中烘托出的让人回味良久的人物形象[6]。
(四)西方戏剧中的诗性
与中国戏剧相比,西方戏剧的悲剧色彩更浓烈。“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这是《俄狄浦斯王》中歌队长的颂词,这部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之作展示了一篇结构严谨且文辞庄严的悲剧诗篇。希腊的悲剧诗人以原始而又素朴的智慧描绘了高山仰止的神与英雄的事迹,又以诗的形式和语言缔造了古代悲剧的典范,呈现出戏剧诗的文体之美。
西方现代戏剧虽已不强调古代的史诗精神,但依然兼具了史诗的理性庄严和抒情诗的感性深情的品格,承袭了古代戏剧诗的精神内核。虽然西方戏剧语言已不再是诗歌,但仍保留了诗的精神和品格。例如,英国音乐理论家厄内斯特·纽曼评价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的戏剧语言犹如没有乐谱的歌词。梅特林克的《群盲》用象征意义的诗词启示人类树立新的信念、精神和理想以便获得自我拯救;《青鸟》以梦幻的诗歌揭示了幸福的真谛以及爱作为一种信仰的重要性。梅特林克通过诗化的语言创造了诗人马拉美所预言的祭礼性的戏剧。
三、中国戏剧的未来创新之路
中西方戏剧虽然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但语言与音乐的融合却有着相似之处。中西方戏剧语言同戏剧音乐的结合都是在自然形态中产生的艺术样式,且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完善。
戏剧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凝聚了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思想感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戏剧艺术的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现代生活中戏剧的观众群体固化严重,他们对传统戏剧的形式和内容接受和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这就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大力度对现代剧作家的挖掘和培养,使这类作家必须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作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剧目。中国的戏剧应借鉴西方音乐的特色,将这种音乐特色与东方语言完美结合,塑造出富有中国韵味的合理的艺术形象,由此才能受到中国民众的喜爱,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对中西方戏剧语言和戏剧音乐进行探讨,有助于中西方戏剧的借鉴与融合,推动中国戏剧艺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开拓出中国戏剧艺术的新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文化不断交融,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中国戏剧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在全世界展现出自己的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