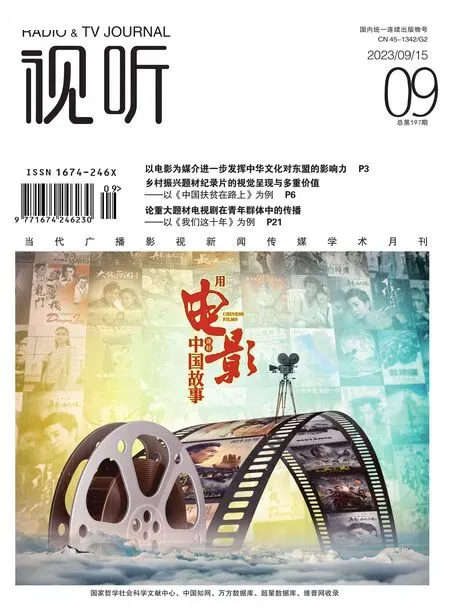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视觉呈现与多重价值
——以《中国扶贫在路上》为例
◎冯笑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描绘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近年来,以乡村振兴为母题展开的艺术创作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文艺光谱中的一抹亮色。人们欣喜地看到,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作为极具艺术魅力与社会价值的影像形式,在新时代的创作需求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产传播态势。此类纪录片娴熟地运用纪实主义的美学手法,捕捉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最为真实可感的社会变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广泛赞誉。其中,由人民日报社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正是典型代表。该片摄制组耗时3 年,行程46000 多公里,采集1300 多个乡村振兴故事,终将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教育振兴等政策方针及数据成果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影像语言并娓娓道来,使观众得以从乡村振兴叙事中感受到潺潺流淌的辛勤奉献与热烈渴望。
一、乡村形象:纵横交错的再现理路
摄影本身具有客观真实的纪实属性,但由此创作出的纪录片却并非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刻,而是体现为一种选择性再现。创作者基于自身对再现对象的理解感知,将其认为“有意味”的影像片段从既有逻辑顺序与叙事语境中抽离并进行二次组合与装配,由此产生的新文本将不可避免地刻上其价值追求与审美旨趣的鲜明烙印。正因如此,探析乡村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景观特征和乡民在媒介再现过程中的形象特点成为研究此类纪录片的首要命题,两者一纵一横构成了乡村振兴的故事脉络。
(一)传承与超越的乡村图景
《中国扶贫在路上》集中再现了我国乡村脱贫前、脱贫中和脱贫后三个阶段的生存图景,详细剖析了跨越式发展背后的深层肌理。对于脱贫前的乡村而言,闭塞与落后是其首要特征。一方面,摄制组大量使用全景镜头将重叠山脉、陡峭乡路、残破村落纳入画面,向观众直观再现了彼时我国落后地区乡村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时常闪现的特写镜头又为此添加了诸多细节真实作为注脚,布满伤痕的双手、满是补丁的衣物、吱呀作响的窗棂等无不令人触目感怀。
对于脱贫中的村庄而言,震荡与觉醒成为纪录片视觉再现的主题。一方面,为了改变闭塞与落后的面貌,强化“村庄单元”及城乡之间的内外关联,交通扶贫成为帮助许多落后乡村摆脱贫困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帮扶与引导下,新思维、新技术和新动力亦纷至沓来,乡民愈发意识到单纯依赖土地产出很难实现脱贫致富,唯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方为有效路径。于是,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了十八洞村盘山而建的乡村公路、乡民创办的苗绣文化产业以及蓬勃发展中的特色旅游事业。在航拍视角下,一条条崭新的通道犹如彩带将城市与乡村紧密联结,曾经的地理枷锁被彻底打破,拔地而起的现代产业建筑也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种种视觉符号都昭示着脱贫致富、全面小康的大门即将訇然洞开。
随着振兴举措的全面铺开,现代化的居住、生产景观成为脱贫后乡村地理空间与生存环境再现的重点,其视觉特征突出表现为传承与发展。传承体现在乡村聚落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与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实现了有机融合。日瓦乡的藏式旅馆、南强村的南洋风建筑、排莫村的传统蜡染工艺等众多具有珍贵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的特色象征符号既是各村落形塑自身“异质性”的主要文化标识,也成为折射各乡村在脱贫攻坚道路上获得跨越式成果的重要视觉表征。发展体现为乡民们因地制宜建立的特色旅游、种植、畜牧等产业正逐步走向成熟并形成合力,由此获得的不仅是摆脱贫困的切实路径,更是迈向美好未来的持续动力。从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到乡村日常的生活劳作景观,现代化的元素不断注入,乡村的价值与意义也随之更迭。它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单位,而是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单位,其宁静质朴的特性、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都将在乡村脱贫与振兴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二)碰撞与变革中的乡民形象
法国乡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提出“农民的终结”一说,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社会的终结,而是从传统小农到农业生产者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扶贫在路上》正是敏锐捕捉到了乡村社会在振兴背景下孕育着的历史性变革,借由对新老两代乡民命运轨迹与心路历程的细致描摹,将其生动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乡民对于土地始终葆有着别样的情愫。老一辈的传统乡民往往将土地视为赖以生存的根基,坚信通过自身辛勤耕种所创造的财富才是最可靠的,所收获的累累硕果也将充分证明自我价值、赢得他人尊重。纪录片中,传统乡民质朴勤恳的形象特征正是通过他们对这方土地的执着坚守而得以直观呈现的。如第二集《扶贫智慧》中所记录的乡民郑志龙,年逾七旬的他是种了一辈子酥梨的老把式,而在因病致贫后更是将酥梨种植视为摆脱困境的“法宝”而愈发精心照料。片中多次记录了以郑志龙为代表的传统乡民在田间劳作的真实场景,这既是对乡民形象客观性的有力佐证,也深刻折射出乡民对脱贫致富的迫切渴望。与传统乡民不同,新生代乡民的恋“土”情结更多指向他们对家乡的眷恋,而非对土地本身的信仰。正如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新生代乡民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当下时兴的概念与技术,逐步摆脱了传统小农意识的束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剥离了农民的身份属性而回归职业属性,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成为现代农业理念与技术的承接者与传播者。例如第三集《志启未来》中的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女孩赵海伶,她选择在大学毕业后回乡建设家乡,在推广新农业技术的同时,又以品牌营销的方式将家乡特产蜂蜜与野生菌由互联网推向全国,带动了当地众多农户增收脱贫,实现了自主创业与脱贫攻坚的深度契合。
二、叙事结构:同条共贯的时空流动
纪录片并非若干片段的简单罗列与集合,行动话语、戏剧冲突等元素遵循着特定的结构逻辑而交织成融洽有序的影像故事,其魅力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和对纷繁素材的选择讲述。《中国扶贫在路上》以乡村振兴为表现对象,从上千件素材中择取21 个典型对象并连缀成篇,形成“在路上”的时空流动特征。
(一)个体影像共筑社会记忆
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扶贫在路上》的创作者并未拘囿于对恢宏历史图景的铺排,而是更多将镜头聚焦于脱贫道路上的微观个体,使宏观抽象的政策数据具象化为鲜活可感的人物故事,从而有效构建起个体叙事与国家形象书写之间的内在联系。片中出现的具体人物、环境等细节的真实不仅构成了整体真实的基础,也“在艺术与观众生活形态之间营造了一种‘同形同构’的逻辑关系”①,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自觉地代入规定情境,架构起相应的话语认同。
《中国扶贫在路上》开篇便以记者王绍据36年前向人民日报投递的一篇反映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贫困状况的报道为由,引出了“中国扶贫第一村”华丽嬗变背后的感人故事。从投稿前的忐忑不安到报道后引发全国反响,从早期的“输血式”救济到后来的“造血式”扶贫,观众透过王绍据的微观视角见证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拉开序幕的历史性时刻,感受到了以赤溪村为代表的乡村聚落在脱贫前后的沧桑巨变,更深刻领会了扶贫工作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与必胜信念。而对于搬迁后就业、邻里乡情等常见顾虑,在片中也是由海国宝以回忆的形式提出,再以其自身生存现状予以回应,一问一答间道出了中国扶贫智慧。此类叙事方式在纪录片后续仍频频出现。更为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未流连于对视觉奇观的塑造,而是将着墨重点置于对乡民们在脱贫致富道路上挥洒汗水的赞扬、对其不断觉醒的脱贫意识的肯定和在成功脱贫后美好生活图景的呈现,从而赋予了纪录片贴近生活的烟火气息与浓厚的乡土人情。
(二)冲突叙事还原跌宕情节
《中国扶贫在路上》中乡村聚落的致贫原因往往大相径庭,其脱贫致富的途径也因人、因地而异。创作者秉持求同存异的叙事理性,深挖差异背后共通的语义句法,以戏剧冲突为交汇点,还原出一幕幕自我救赎与他者相助共同交织的跌宕情节。
在自我救赎的叙事逻辑中,乡民与所处的恶劣环境形成二元对立,这种对立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单向度的矛盾冲突形式,人物形象与环境形态的两极化描写构成了矛盾冲突的性格与存在基础。而“恶劣环境”则既指先天形成的自然环境,如坐落在中缅边陲的云南省沧原县芒摆村,其高海拔地貌使得以陈云为代表的当地乡民终日劳作却难获温饱,也包括后天遭遇的多舛命运,如19 岁因病失明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青年杨跃志。在这样的冲突对立中,乡民们直面苦难、借势脱贫的奋斗事迹成为刻画人物、推动叙事的核心力量。
在他者相助的故事模式里,扶贫者的先进理念与乡民的局限思维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内在的、多向度的矛盾冲突本就不易解决,扶贫者们“外来人”的身份标签也令转变进程更为曲折,但汗水和真情终将换得乡民们的信任与支持。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扶贫干部刘泉善用媒体力量,通过“荣誉校长”模式吸引多方社会资源注入到当地基础教育事业中;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韦店集村第一书记时圣宇用3个月时间跑遍8个自然村落展开实地调研,利用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帮助乡民建立起蔬菜大棚基地、蛋鸭养殖合作社等现代农业设施。正是在乡民们的笑容与赞许中,扶贫干部们实现了从“外来人”到“自己人”的身份转换。
一方面,影片给予了矛盾冲突以充裕的铺展空间,展示了乡村在脱贫前夕积聚的变革伟力与致富之后生活的喜悦场景,因而饱含情感温度与现实锐度。另一方面,创作者通过对人物刻画、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将宏观的时代主题与价值理念巧妙隐匿于客观镜头中,“既有效避免了宏大叙事和人物的概念化,又能通过具象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抽象价值观的导入和弘扬打下坚实基础”②,实现了现实主义题材与纪实主义美学的双峰并秀。
三、多重价值:传递民声的影像信函
作为大众媒介的纪录片因其直观性与普适性的影视语言而具备了跨越地理区域、打破文化区隔的传播优势,所承载的信息理念也得以通过“影像信函”的方式无远弗届地向社会各界传递。《中国扶贫在路上》从人本视角出发,立足时代、扎根基层,真实记录与呈现了我国诸多乡村完成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为这一宏大历史变迁留下了极具社会价值、审美意味与精神感召的影视注脚,具有难能可贵的范本意义。
(一)针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可视呈现
在乡村振兴驶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挑战与难度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对既有脱贫成果和攻坚路径的记录归纳与可视化呈现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现实价值。
一方面,纪录片从物质生活与精神价值两个维度展开了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形象的深度扫描,乡民们生产方式的转变、居住环境的改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思想观念变革、乡土文化传承等多层次信息都被完整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思考当今乡土中国的直观窗口。而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扶贫道路上所遇到的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小农生存伦理抵抗等诸多现实困境,创作者也予以细致归纳,并借乡民或扶贫干部之口讲述其如何逆水行舟,促使外源推动与内源发展相结合,进而实现精准脱贫的路径选择。从纪录片伊始的易地搬迁脱贫、教育精准扶贫到后面的特色产业发展、城镇转移就业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脱贫政策与机制,无不充分证明了我国脱贫攻坚的决心与智慧,突显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创作者借此类脱贫叙事展开以案释政,使观众对党的各项脱贫政策与攻坚理念形成更加直观感性的认知体验,进而唤起其内心的由衷爱戴与拥护。
(二)折射脱贫攻坚进程的人文关怀
福柯曾言“话语即权力”,而以《中国扶贫在路上》为代表的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则将话语权力赋予了每位参与者,镜头流转间展现了乡民们的淳朴勤劳与扶贫者的实干奉献。这种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正是一场创建对话、引发思考、凝聚共识的人文化过程。
创作者对贫困乡民的立体观照和对乡土文化的回溯诠释奠定了影片温暖坚实的人文基调。信息的不对称使久困恶劣环境的乡民们在面对变革时往往感到忧虑与彷徨,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也是普通民众最真实的生存态度。《中国扶贫在路上》既为普通民众情绪的宣泄与释放提供了出口,也以人物命运的起伏为脉络,多维度地呈现了乡民们在变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转变诱因,为“被遗忘的远方”填补了情绪表达的信息鸿沟。片中的乡民们最终克服万难、成功实现脱贫致富,在迎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成为后继者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榜样。乡村作为一个发展空间,支撑着整个乡土文明,其价值与内涵也在纪录片中被着重诠释与书写。一方面,纪录片完整记录了扶贫者与当地乡民们在面对重大时代挑战时如何从新角度探索乡村价值,创造性地将原有劣势和困局转化为推动变革转型的优势与良机,从而实现外源推动与内生发展的融合互动,共同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创作者主动挖掘乡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对各地风俗人情、服饰建筑、传统工艺等元素的呈现,实现对乡村精神文化的塑造与弘扬。侗族的舞蹈、苗族的吊脚楼、布依族的刺绣工艺等各具视觉冲击的文化符号,已然成为我们管窥乡土文明的一面“镜子”。
四、结语
“主流媒体拍摄的脱贫攻坚题材纪录片实质是一种宣传媒介,由此再现出的乡村图景离不开国家话语的影响和对贫困乡民群体及传统乡土文化的解读。”③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通过对两者的细致描摹,勾勒出一幅乡民们与扶贫者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齐心合力、携手同行的美好图景,呈现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时代潮流与进步特征,也为此后同类题材纪录片丰富观照视角、提炼内涵价值开创了可资借鉴的全新范式。
注释:
①冯笑,张郑武文.现实语境下制造题材纪录片的人文叙事与时代价值——以《制造时代》为例[J].电视研究,2019(08):54-56.
②李军辉.《大国工匠》:话语空间与纪实高度[J].中国电视,2018(03):106-109.
③刘娜,陈晓莉.基于再现理论的乡村形象研究——以脱贫攻坚题材纪录片为例[J].当代传播,2019(06):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