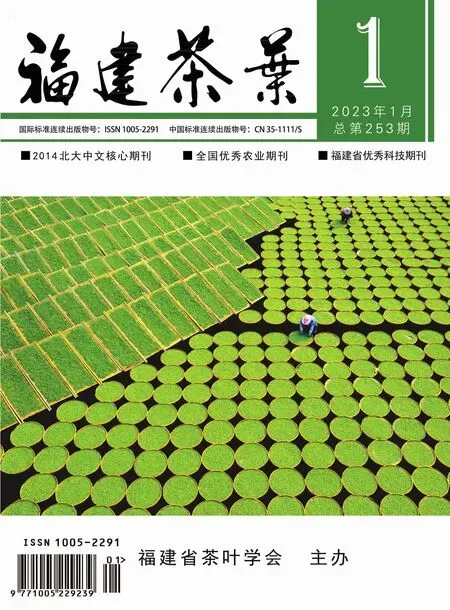从咏茶诗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与审美
张 遥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1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1.1 由京城到市井的饮茶之风
贞观之治后的唐朝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国度,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宽松的社会氛围,昂扬的社会气象,使唐人不仅仅满足于物质追求,更渴望精神的充溢。饮茶之风由此开始盛行,此时饮茶不单单是为了治病,已逐渐上升为一种具有文化意味的喜好。《茶经·六之饮》记载“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1]在唐朝之时,饮茶之风开始普及盛行,西安,洛阳东西两个都城以及湖北、重庆等地更是家家户户饮茶,可见饮茶风气之盛。封演《封氏见闻录》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由此可见唐代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部分,也为我们提供了两项重要的历史事实,一是饮茶习俗是由南方传到北方,茶叶多在江淮一带种植,作为商品贩卖并发展出茶馆,二是饮茶习惯与禅教的兴盛有关,解释了为什么禅教推动了饮茶习惯的发展兴盛。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茶区进一步扩大,也是茶文化发展的必要基础,仅陆羽《茶经》记载就有42州1郡产茶。产茶区域遍及今天的川渝,鄂,皖,赣,湘,桂,粤等14个省区。
1.2 由禁锢到开明的世俗风气
隋唐之际,全面推行科举制为寒士进入统治阶级打开大门,逐渐打破了贵族与寒士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科举制促进文人之间干谒拜会,以文会友,以才显名的社会风气,将诗歌文学创作与个人社会地位紧紧相连。《新唐书》载:“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3]由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几乎脱离了社会劳动,他们的情怀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诗歌无疑是最好的宣泄口。随着陆羽《茶经》的出现引导着茶业进一步发展,言约意丰的深化了饮茶的深层美学和文化层次,使饮茶建立文化体系成了必然。茶渐渐超越提神这样的实际功能,转为寄寓精神之茶,将茶引入了精神领域与审美境界,使得饮茶不仅是生活是仪式,更是一种文学高级意象。饮茶的兴盛也许是一个巧合,但茶诗茶书的崛起离不开大唐士子推动,除了《茶经》,还有《煎茶水记》《补茶事》《茶诀》唐代的茶书编纂,从草创走向理智,从自发走向自觉,开启了随后千年来的宏大规模,成为茶书史上有声有色的序曲。
1.3 儒释道三家的反省梵行
茶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佛家的清寂禅悟,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中庸和谐。在禅宗寺院的修习过程中,静坐的过程十分重要,打坐的时候万虑俱空,才能有一种精神的领悟与超越,这时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茶能提神、健脑、益思,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则更明确指出:“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疾,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陆羽在《茶经》中亦说欲“荡昏寐,饮之以茶”[4]茶能提神又没有任何禁忌这让茶成为修禅悟道的不二选择。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在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发展达到了高潮,由于唐王朝的包容态度对各种宗教文化都采取十分宽容的政策,佛教也积极渗入民间,寺院以茶贡佛,以茶译经,以茶应酬文人,回赠百姓,因而茶叶消费增大,可以说寺院对推动茶的普及发展又立一大功。在禅林僧院之中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安逸,为尘世所累的士人在进入禅境的片刻,感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茶便是帮助他们彻悟的工具。
“道法自然”道家提倡万物皆应效法自然,自然是道家最尊崇的哲学层次,适应自然规律,感受自然给人带来的一切,饮茶是人与自然的直接交流的过程,从茶叶茶汤的变化中,体味真香真味真气,感受宇宙山川大自然的奇妙馈赠,进而领悟自然的真谛,享受人与自然交融的美感。
儒家的中庸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和”是一种自然的平衡,是理性的节制,不是统一是交融,是内外部的稳定有序。茶引文人思,儒士多饮茶,在茶的和谐意境中沟通思想,不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百虑一致”。唐末刘贞亮提倡茶“十德”之说,由此可知茶已纳入君子品行的考察范围,饮茶要求恭敬有礼、仁爱雅致、尘心洗净,这不正合君子之道。可共饮茶之人,必是君子之交。
1.4 由生活渗入诗歌的茶因子
虽不可能像现代一样存在人人平等的观念,但唐代民本思想已经慢慢抬头,艺术创作越来越重视民间力量,并贴近民间生活。时代赋予人们使命,在唐这个强盛的朝代,人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自我看重,自惜其才,这种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让长安的年轻一辈有了紧迫感危机感,必须做出一番事业振兴时代。
中国传统文学最为持久的一个倾向是不看重赞美之词,而看重对作家真实情感的令人信服的再现。[5]“真”的价值在中唐逐渐显现,对文学语言中滥调媚俗有了越来越高的警惕,诗人情不自禁地表达个性,抒发真情,写出的东西只属于自己,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由特性走向个性,源自内心的内在冲动喷薄而出,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家国大事,家国情怀,而是将视角转向日常生活,自然自我,表达真真切切的自我感受,个人反思,茶诗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里以袁高的《茶山诗》为例:
“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诗中嗅不到紫笋茶香,看不到丰盛酒宴,听不到笑语歌声,以茶喻政,茶为表,实则表达作者的真性情,像是蘸着广大茶农的血所写,诗人作为湖州刺史,本想体恤民情,可又不能公然抗旨,只得因循旧制督贡茶,可在茫茫沧海,又有谁能倾听这为民请命的一片丹心。唐人将关注的重点从对上层宏大建树的歌颂转到关注贫民,关注日常生活,由社会转向自我,揭去统治阶级的伪善面纱,看赤裸裸血淋淋的本质,怎能说这不是唐人的进步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对社会本质的清晰认识,不是对当权者权威的质问,此时诗的历史不再仅仅属于诗,变成了“诗歌史”。
“口语化”无拘无束的语言,正好配对肆意纵情的生活,正是因为口语的介入,诗歌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口语化的语言也正是茶诗独特魅力所在,诗中平常自适之味与茶之本味相得益彰,“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韦应物《喜园中荼生》)[6]“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7](郑愚《茶诗》)茶诗的口语化并未让人觉得茶味俗化。正是这样的口语化表达,使得茶更易与人亲近,人易与自然亲近,清淡中见真情,闲适中见清雅。
唐诗传情达意的功夫从从最敏感处的感官入手,不是词藻的堆砌,也不是炫技的功能性手段,是在最平常易感之处找到切入点,突击一下,然后又轻轻一笔撩人心动;不是重赞誉,而是注重作家的真情实感。茶与茶诗的普及,不仅是单纯生活的丰富品,还有其深厚的文化意义和精神美感,让我们思考真善美,也从日常生活中的饮茶告诉我们如何求得真善美。
2 一饮荡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2.1 茶审美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在《茶经》中不仅有“茶之源”“茶之造”“茶之煮”还有“茶之具”“茶之器”“茶之饮”。在唐代文人的引导下茶的饮用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一种境界和精神,与饮茶相关的一切都进入一种审美的范畴。如有吟诵名泉之诗,饮茶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之一就是好茶用好水,对饮茶水质讲究,刘禹锡有“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8]之句;好茶用好具,茶器之诗《贡余秘色茶盏》徐夤的诗可见: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9]
对于饮茶要求逐渐提高,那么对茶与茶饮用的一切关联物都有了更高要求,唐人对茶汤的要求使他们对青瓷更加情有独钟,此诗中的秘色瓷器更是青瓷中的绝品。
煮茶之诗也是表现茶诗审美的整体与统一如:《茶中杂咏·煮茶》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诗人动用所有感官从视觉,听觉,色泽等不同角度对煮茶进行描写,从状的“莲珠”“蟹目”“鱼鳞”表现茶沸腾过程,到沸腾之声“松带雨”至色的“生烟翠”,从煮茶的各个阶段来写茶的状态,将煮茶的过程也纳入审美的过程。
2.2 引君子之爱的茶性无邪
在《茶经》开始“一之源”里就已经提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10]。茶性俭,强调简朴之美,发展出简约哲学,从而把形而下的饮茶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境界。通过饮茶,可以反映个人的人品性格。“五之煮”中“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为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11]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以物喻德”的表述,因而饮茶之人首先有品德上的要求,唐代文人裴汶在其《茶述》中“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过此皆不得。人人服之,永永不厌。”裴汶认为茶的特性在于“性精清”、“味浩洁”,对茶的推崇已经脱俗出普通物质,视同有灵有性的高洁之物,此外,除了茶的最基本自然功效,更注重的是茶对于人思想的触动,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和高洁的品质恰好与文人所追求俭德质朴相契合,这使茶更加成为文人的不二之选。“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来以茶寓意廉洁简朴,现实生活中唐人已经具有了许多超出常规的物质欲望,嗜茶便是其中之一,因茶性甘味苦,嗜茶又与其他欲望相区别,表现出崇俭黜奢的高雅期盼。茶略带苦味,而又有清新之香,香味虽不浓郁却持久悠扬,与君子洁身自好、甘于平淡的人生追求相通。这时的饮茶已经带有了强烈的文化意涵,与清高、文雅、简朴等意识结合起来,进入“清风明月”的境界。
3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3.1 味觉视觉相统一的茶意趣
饮食讲究“色、香、味”三者俱全,饮茶也是如此,是味觉和视觉的相统一,饮茶的视觉美感之一就来自茶具,唐朝饮茶的方法与今天不同,是将茶饼研末,然后蒸煎,但茶末色泽暗红,视觉上不能提供春天山峦青翠的美感,也不能带来心旷神怡的山野联想,那么关键就变成了呈现茶汤的茶碗,陆羽论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12]越瓷它与茶色相近,越瓷青似翠玉苍山,加重了茶的绿色,更加能衬出茶色鲜嫩翠绿,才会有“春水”“绿云”的美感,且合乎味觉与视觉统一的标准。越瓷以釉色见长,瓷面少纹饰,素雅大方,洁白的胎体,外加纯净透明的釉色,呈现出半透明之感,给人如玉般的视觉享受,唐瓷正绵密质朴,细腻光滑,如玉的触觉和视觉享受,其轻盈绵密,色泽绵柔的特点与唐时茶文化正好契合。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13]说的就是越瓷翠绿色与新茶共融产生的轻烟朦胧的视觉享受,茶瓷之美与人心之美相同,在物中呈现士人风度。对茶清香的描写也是唐代茶文学艺术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3.2 茶生活开辟出的私人空间
在中唐以前,写作基本上是公众性的表述,即使是在构筑私人空间亦是如此。那时,一个私人生活的天地,一个在价值取向上可以与个人对公众价值的承诺相分离的空间,尚未建立起来。在中古时期,对于隐逸之乐的吟咏会被解读成批评时政。然而在中唐,一个像白居易这样的作家宣言家居之乐,却不会引发类似的怀疑。[14]写作由大众话语转为私人话语,并得到认可,诗人从对官场的事物不满可退隐家中,掩门闭户,隔断内外两个天地,在封闭的家庭空间之内,努力愉悦自己的“野性”。
白居易的《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新茗分张及病身”,“不及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15]儿时的好友虽已天各一方,但时间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情意,在贫病交加的窘境诗人也能尝到友人相寄的好茶,这种私人化的感情在始终肆意流露,温暖自己也温暖了诗意。私人化的体验与公众形象形成良性互动,以私人化的声音写给大众,在愉悦自己的同时愉悦大众,私人空间创作成为文人安置自我心灵的方式。
4 结语
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萌芽期,在繁盛的唐代提升至情操与精神的高度,使茶的文化功能开始显现,茶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岁月长河中中国茶伴随着中国儒释道的跌宕起伏,从开始兴盛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渐渐把与茶相关的一切都纳入审美范围,唐人因爱茶而以茶入诗,茶不仅成为破睡的工具,更是给陷入泥泞唐代士人一个呼吸的静林,以茶为友,与茶相交体味“茶道”,这些都在唐代茶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杯清茶,一世人生。茶在唐代这个浪漫诗歌王朝的推动下,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解渴的饮品,完成了从制茶、品茶到悟道的提高,从自然物质进入文化领域,成为了一种意象,一种精神,是文人的一种归宿,他们如茶一般不能是尘是土,他们要为世界留下独特的甘,茶诗便是他们种下的种子,让这种精神在华夏大地开花结果,无论出世入世,他们对生命依旧保持着美好的期盼,他们有信心为万世立楷模,不断超越的压力是他们留给后世的礼物,如茶般清风明月的精神是他们对后世的期许。
——基于饮茶习惯双向变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