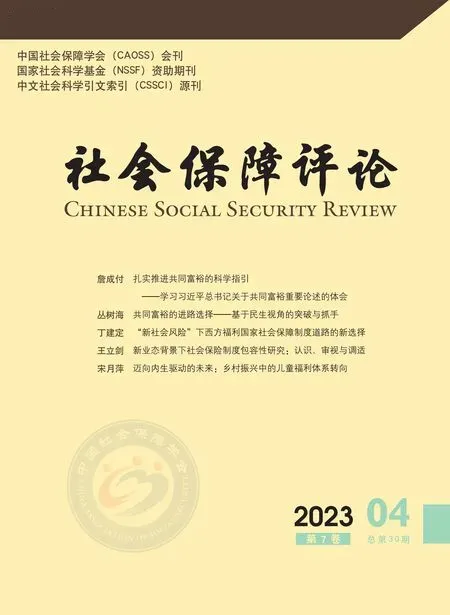迈向内生驱动的未来:乡村振兴中的儿童福利体系转向
宋月萍
一、引言
经过多年耕耘,我国在2020 年底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国“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长期以来,社会政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居民及低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拓展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等路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强调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贫困治理等综合的、多元的扶贫方式促进欠发达地区长远发展。①邓锁、吴玉玲:《社会保护与儿童优先的可持续反贫困路径分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 年第6 期。在“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政策也需全面优化升级以回应新阶段的乡村经济社会形势。
儿童既是贫困地区最脆弱的群体,也是贫困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发展对于整个贫困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儿童福利体系泛指面向儿童的福利供给体系与识别递送机制,不仅涉及如何提升儿童生活水平,更注重为乡村儿童提供更丰富的发展机会,符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是一项积极福利,有助于促进儿童由受助者转化为富有潜力的劳动者、价值创造者,为当地作出积极贡献。在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携手努力之下,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呈现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相对落后。基于儿童发展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①韩华为:《儿童贫困的内涵和形成机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启示》,《社会保障评论》2023 年第2 期。巩固和发展乡村儿童福利体系不仅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举措,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统一,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当前阶段,必须提高对于儿童福利的重视,②姜妙屹:《试论我国家庭政策与儿童政策相结合的儿童优先脱贫行动》,《社会科学辑刊》2019 年第4 期。将儿童福利体系转向作为探讨乡村社会政策体系优化策略的关键。
儿童福利体系转向的本质是要探讨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展演进的不同阶段,如何理解家与国、个体家庭与周边社会在儿童发展中的责任关系,以及重点解决怎样的儿童福利难题。儿童福利体系的运作模式既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彰显了微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的互嵌关系,是乡村振兴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局面的例证。③程福财:《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青年研究》2012 年第1 期。探究乡村振兴中的儿童福利体系转向,关键在于梳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阶段乡村发展战略部署与福利供给基础的演变。
本文试基于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及阶段特征,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儿童福利体系的优化需求与现实基础,进而总结儿童福利体系在乡村振兴阶段的转向策略。
二、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及阶段特征
(一)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
在脱贫攻坚阶段,相关政策设计已多次强调儿童脱贫的重要性,将乡村地区儿童福利建设置于优先位置。2015 年11 月2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从多个方面强调儿童脱贫,在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儿童福利和社区儿童之家等服务设施和队伍建设、未成年人的监护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收入家庭重病重残等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等方面部署工作。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再次在教育脱贫、健康脱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等部分中强调了儿童减贫脱贫的重要性。
在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胜利以前,我国乡村儿童福利体系具有以下特征。在福利对象方面,在扶危济困重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导向下,涉及儿童福利的政策话语更多强调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患病儿童等特殊群体。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乡村儿童福利发展的重点在于扶危解困,在政府主导下调动外部资源促进乡村贫困地区儿童保护,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基本的社会权。在福利措施方面,以社会保护和社会救助为主要手段,重点强化受教育权与生命健康权两项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现出“兜底”的基础建设特点。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农村儿童健康改善和早期教育、学前教育”。对教育权的强调往往凸显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但脱贫攻坚阶段的教育福利的核心并非促进人力资本发展,而是以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为抓手,使乡村低龄儿童进入学校环境,为其提供更丰富的营养福利与卫生安全保障。
伴随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深化,福利资源更加丰富,福利内容逐步拓展,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相较于脱贫攻坚早期的扶危解困,政策服务对象由留守儿童等特殊儿童拓展向更广泛的乡村儿童群体,以底线公平为基准,适度拓展了福利覆盖范围。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明确提出,要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在政策内容上,更加关注福利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发展。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指出,要“加强贫困地区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严厉打击非法侵犯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普通话教育的强调,是儿童福利体系城乡一体化转向与福利体系目标由兜底向发展转变的体现。
在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以后,我国乡村儿童福利体系致力于巩固脱贫攻坚阶段儿童福利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地区儿童长远发展。在福利对象方面,由建档立卡精准支持特困儿童到“适度普惠”,①乔东平、黄冠:《从“适度普惠”到“部分普惠”——后2020 时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策构想》,《社会保障评论》2021 年第3 期。关注更广泛的乡村儿童群体。在福利内容方面,由医疗卫生与营养健康保障等基本权益向发展型福利拓展。以教育政策为例,在脱贫攻坚阶段,重点解决的是上得了、上得起问题,重点完成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历史任务,解决贫困家庭学生辍学问题。而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开展网络远程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出现了教育内容由基础教育向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扩展;教育对象由区域性整体扶持转向区域扶持与对特殊人群的重点资助相结合;教育帮扶的参与主体由单一政府转向与社会力量合作点等多种趋向。②邹培、雷明:《教育帮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
(二)乡村振兴阶段的儿童福利供需特征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脱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儿童福利体系的社会基础有所改变。步入乡村振兴阶段,更需要厘清当前阶段儿童福利体系与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特征之间的张力,辨析现阶段当地儿童福利的供需结构特征,进而明确儿童福利体系的转变方向。
1.乡村振兴地区儿童福利供给基础转变
脱贫攻坚阶段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促使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福利供给基础发生转变,为儿童福利体系优化提供了条件。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巨大奇迹。到2020 年,脱贫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明显改善,儿童福利资源调动与供给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012 年的2.88:1 缩小到2.56:1,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③孙若风等:《乡村振兴蓝皮书: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4 页。乡村振兴地区家庭户收入提升,家庭物质生活环境改善,家庭福利供给潜力提升,使家庭更能成为支撑儿童基本生活需求的坚实后盾。儿童贫困问题有所缓解,儿童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儿童基本权益保障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减。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2013 年到2018 年,中国儿童贫困率从总体上大幅下降,全国处于多维贫困儿童的比例从2013 年的49%下降到2018 年的19%,农村儿童、城市和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率差距进一步缩小。①高琴、王一:《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水平、趋势与模式研究——基于2013—2018 年CHIP 数据的证据》,《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3 期。
乡村振兴阶段的工作重心由提升经济收入水平转向防止规模化返贫,促进脱贫地区持续发展,更加重视社会福利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建设,相关政策导向也由集合外部力量集中解决贫困问题转向促进乡村振兴地区自我驱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政策环境转向,使得乡村振兴地区更需重视发掘在地资源,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依托外部资源介入,以扶危济困为目标的儿童福利体系不再适应当地社会环境,不能有效回应儿童福利发展的需求。但是,当前乡村振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儿童福利供给间的内部循环机制尚未构建完善,由于育儿观念相对落后,儿童福利建设的内驱力及主动性不足,乡村振兴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儿童全面发展的依托,使儿童福利供给基础与儿童福利需求间的张力难以调和。
2.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特征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乡村振兴地区儿童福利,促进脱贫攻坚阶段儿童福利建设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需梳理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的主要特征及当前儿童福利体系无法有效回应的儿童福利困境,由此思考儿童福利体系的必要转向。
基于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的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
儿童群体分化,儿童福利需求更趋差异化、多样化。脱贫攻坚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也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分化,当地家庭间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儿童生存发展的依赖性使其更容易受到家庭以及外部环境风险的影响,家庭类型多样也意味着儿童群体的内部分化,成长于不同家庭环境的儿童的福利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发展型福利需求增加。自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工作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难题,要求我们重视经济与社会剥夺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儿童贫困风险。儿童福利需求的主要内容由获得资源补给,解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争取更丰富的发展权益,呼吁打破城乡儿童福利二元分割的局面。
儿童福利需求识别难度提高,福利脱嵌风险提升。迈入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递送模式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国家层面提供的兜底保障政策逐渐撤出,精准化的儿童福利政策内容更加丰富。精准化的福利递送过程高度依赖于贫困儿童需求识别敏锐度,福利需求发掘精深程度。不同于全面兜底,全面保障的福利递送模式,精准化的福利支持能否触达儿童的关键在于贫困儿童及其所在的家庭能否主动提出需求,主动了解政策,主动接入政策优惠范畴。
福利需求发掘困难,对儿童发展的认知有限影响了需求表达。在脱贫攻坚阶段,儿童福利建设的目标长期局限于保障儿童基本人身权益。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及家庭对于儿童福利的想象仍停留于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家长缺乏育儿知识,众多家庭的育儿观念仍停留于“儿童不挨饿、不挨冻就是尽职尽责”。①李晓红、刘东:《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地区儿童发展观念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堕距明显,各方对于儿童福利诉求认知不足,需求驱动不足也限制了儿童福利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3.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供需体系间的张力与困境
现阶段的儿童福利体系无法有效回应乡村振兴背景下儿童福利需求的结构特征,儿童福利建设的困境表现为以下几点。
福利责任主体及分工转移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家庭尚未成长为独立成熟的福利供给主体,家庭没有承担其应尽的儿童福利供给功能。家庭经济水平提升之后,家庭的福利供给功能实际提升有限,亲子分离及隔代抚养现象广泛存在。不健全的家庭结构,不和睦的家庭关系,不完善的家庭育儿理念使得家庭经济水平改善无法有效转化为家庭福利供给功能的实际提升,儿童福利供给仍高度依赖于政府或社会力量。家庭、政府、社会等福利责任主体间缺少协同合作,政府资源重复投入,影响福利供给效率。
福利供给质量有待提升,行政化色彩较浓,缺乏专业性。乡村振兴地区缺乏专业化的儿童福利供给服务,当地儿童服务人员较少接受系统性培训,专业化社会组织入驻较少。地方性儿童福利政策有限且碎片化严重,②乔东平等:《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新发展与新时代政策思考——基于2010 年以来的政策文献研究》,《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 年第3 期。在儿童福利落地过程中出现执行主体单一化、执行方式线性化、执行人员缺乏意义共识,以及执行资源脱嵌于儿童福利制度环境等问题。③王小兰、宗海静:《“儿童之家”建设的执行差距成因探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当代青年研究》2023 年第2 期。缺乏专职化服务,很多地区仅依靠兼职志愿者提供服务,儿童之家等儿童福利场所缺少全职工作人员。
福利供给模式衔接不完善。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阶段转向之下,普惠型和精准化福利服务衔接不到位,容易造成特困儿童的福利脱嵌问题。“强家庭-弱社会”的儿童权利观以及落后的家庭育儿观念,使得儿童福利需求不能有效向外传递,这既反映了家庭福利功能不完善的不利影响,也显示了乡村振兴地区社会整体儿童发展观念落后,社会文化氛围营造落后于经济建设。因此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必须是立体式、全方位的优化过程,涉及儿童个体及其家庭,也关系到当地的社会建设和文化营造,深嵌于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三、构建内生驱动的乡村儿童福利体系
社会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变化推动了福利体系的阶段转向。④蒙克:《“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5 期。乡村振兴以脱贫攻坚为基础,是更具综合性的发展战略,通过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综合举措与全方位部署,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维护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①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在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体系建设需实现由外部支持促进到内生驱动的转向,这不仅意味着要实现对儿童福利供给模式的纠偏,更需要梳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地区长效发展的家国关系、公私域关系,在为儿童创造良好成长环境的过程中,秉承并贯彻激发乡村振兴地区内生潜力的主旨,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战略主线。在此意义上,儿童福利体系的优化升级内嵌于乡村振兴战略导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促进在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实现乡村振兴地区发展动力由外部助推向内生驱动提供重要依托。构建内生驱动的乡村儿童福利体系,主要涉及以下五条路径。
(一)福利发展模式:由单一到立体
脱贫攻坚阶段的社会福利建设以摆脱贫困为导向,乡村振兴阶段的社会福利建设则具有发展型福利的特征。②蒋国河、刘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经验传承与衔接转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乡村振兴阶段的儿童福利体系在外延与内涵、目标与任务、视角与方法上均应有所转变。为应对多样化的福利风险及差异化的福利诉求,需注重整合碎片化的儿童福利,建设更全面的儿童福利体系。在福利政策设计方面,不能“就儿童谈儿童”,要将儿童置于综合性的社会环境之中,考虑家庭及社会氛围对儿童的影响。儿童福利体系不仅涉及儿童政策,更需要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以社会化、结构性的视角看待儿童发展,以综合性的眼光发掘潜在的儿童成长风险与福利需求,必须注重政策间的协同,将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社会福利纳入共同讨论框架。
在福利范畴方面,需努力构建全方位、全周期满足全体儿童健康成长的福利需求的制度体系。儿童福利不再是局限于民政范畴的民政福利,而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它涵盖生育福利、托育服务、儿童健康保障、儿童教育福利、儿童津贴与社会优待、儿童特别保护等内容。③尹吉东:《从适度普惠走向全面普惠:中国儿童福利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2 期。立体的儿童福利体系应有效落实全体儿童健康成长的全方位、全流程保障。
在福利评价方面,应建立多维的评价机制,不仅考虑到儿童福利的规模与质量,还需着重关注儿童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对体系运行的潜在风险加强识别,提早遏制。重点是对福利筹资和资源调动过程加以反思,对于外部资源驱动的福利内容,尽快探寻乡村振兴地区当地资源驱动的替代路径。
(二)福利供给策略:由资源补缺到机会可及
伴随乡村振兴地区经济水平提升,儿童福利需求由基本生活保障转向更广泛、更充分的发展机会,福利供给的重点已经从增加资源转向能力提升。④Jiachang Gao, et al.,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to Adolescent Poverty in China: Application of a Latent Class Model, "Agriculture, 2022, 12(9).同时,福利供给策略也由物质资源投入与经济支持转向物质、精神与文化领域的多维并举,由机械化的技术治理转向价值治理,更加关注物质福利之外的文化支持和精神教化。
对于儿童而言,非物质层面的福利投资不仅在于心理关怀,更在于在生命早期阶段加强能力建设,实现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可行能力建设。在兜底式物质资源福利基础之上,精准化福利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更在于能否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福利需求。①孙三百、洪俊杰:《城市规模与居民福利——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统计研究》2022 年第7 期。这不仅对基层福利执行主体提出了挑战,也对福利接收主体表达需求、主动接入福利政策网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儿童及其家庭需具备提出福利需求的能力、了解福利供给的能力,甚至应拓展其自下而上需求的以需求驱动福利供给模式优化的能力。而对于地方治理人员来说,需要保障供需衔接,挖掘需求并确保福利供给落地。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注重需求驱动,通过儿童及其家庭提出需求,主动选择提升福利供给的效率,更需要加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出需求的能力建设。重视贫困的分化和意识,以及不同人群获益程度和能力差异,并加强福利政策信息宣传,使儿童及其家庭真正获得接入和选择福利的可行自由。②Alison MacKenzie, et al.,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pproach: A Counter Theory to Human Capital Discourse in Promoting Low SES Students' Agency in Educ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23, 117(1).作为儿童福利体系基层运营的执行主体,地方儿童主任及儿童之家等部门的专职工作人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责任主体:以家庭为中心,提升福利供给能力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家庭作为儿童福利供给主体的作用越发凸显。从英国1601 年颁布《伊利莎白济贫法》至今400 多年里,西方儿童福利的发展经历了“失依儿童救济时期”“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时期”和“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时期”的历史转变。③乔东平、谢倩雯:《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东岳论丛》2014 年第11 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童福利体系也历经由单位为主转向家庭为主,进而演变成家庭为主,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分担过程,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地位越发受到重视。④岳经纶、范昕:《幼有所育:新时代我国儿童政策体制的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4 期。《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分别增设了“儿童与家庭”“妇女与家庭”的章节,家庭不再被概括在社会环境的宏大范围之中,而被赋予独特的政策定位。促进乡村振兴地区福利体系转向内生驱动的重要基础是培育扎根当地的福利供给主体,为此更需强化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功能与地位。
家庭不仅是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更是儿童福利需求识别与需求表达的重要依托。考虑到儿童福利需求的分化及家庭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福利供给模式能够以更灵活的方式回应福利需求。地方政府应以“支持和引导家庭发展”为目标,将“三家建设”等工作与儿童福利工作紧密结合,通过设立及完善专司家庭事务的政府管理机构、启动家庭福利政策法案的立法计划、推行以家庭整体为政策对象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构建以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为中心的福利支持体系。⑤许敏:《家庭变迁与地方性家庭福利政策模式的转变》,《重庆社会科学》2018 年第8 期;张浩淼、朱杰:《“家庭为本”视域下我国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改革与战略》2022 年第4 期。基于家庭为本的导向,发展儿童福利,明确家庭承担的儿童福利责任边界,厘清公私域关系、家国关系。
(四)责任分工:构建专业化、多元化的儿童福利责任网络
在考虑解决困境儿童的现实问题时,如果仅仅是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导向的个体治理,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①张浩淼、朱杰:《“家庭为本”视域下我国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4 期。在发展儿童福利时,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限制,将儿童福利体系完善嵌入地区发展战略,成为社会建设的一环,使儿童福利水平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互促共进。一方面能使儿童群体的福利提升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使地区经济发展红利转变为儿童福利提升的基础,使儿童福利为当地人力资本积蓄助力,另一方面能为儿童福利体系的落地与实践执行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提升儿童福利体系运作的可持续性,需加强基层治理能力与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强基层儿童服务主体建设,通过儿童主任等专职工作人员提供职业化服务,培育和引入专业化社会组织,构建以家庭为中心,以地方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儿童福利责任网络。
(五)福利对象:由兜底保障到实际普惠,坚持特困儿童优先
在脱贫攻坚早期阶段,政策话语中的全面普惠实则是对于儿童基本社会权益的兜底式保障。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后的普惠式儿童福利,才是真正意义上覆盖全体儿童,努力回应儿童不同成长时期不同福利需求的实际普惠的综合福利体系。迈向乡村振兴阶段,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在努力实现由兜底式普惠向实际普惠之转变的同时,仍需贯彻弱势群体优先、特殊困难儿童优先的原则。
为此,我们需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注重儿童主位诉求,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弱势儿童福利需求的识别与挖掘。弱势儿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基层执行主体不仅需设立相应的机制和渠道,让弱势儿童及其家庭能够参与福利政策的规划设计过程,更需通过能力建设以动员其表达需求进而争取政策利好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需要特别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观念水平的分化,弱势儿童往往来自弱势家庭,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家庭的经济状况、教育支持和家庭功能等方面,通过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家庭育儿理念教育以及儿童资产建设干预,帮助其改善家庭整体条件或是提升家庭资源配置效率,努力为弱势儿童争取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平等的发展机会。
四、结论及讨论
基于我国消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以及“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适时转向,既是适应新阶段的乡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必然结果,也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
完善儿童福利体系是向未来的投资,既是对儿童未来的投资,也是对乡村振兴地区可持续前景的投资。对儿童而言,敏锐把握社会福利供给基础与儿童福利需求的演变与二者的张力,适时适度解决迫切的福利困境,关系到儿童的切身权益。对乡村振兴地区而言,内生驱动的儿童福利体系转向,内嵌于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的社会建设工作体系,呼应了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阶段由外力拉动向内生驱动发展的主旨转向。梳理儿童福利体系责任主体与分工,分析儿童福利供给模式演变的过程,也是明晰乡村振兴地区家国关系、社会关系的过程。对于儿童福利责任的梳理,也是对乡村振兴地区未来发展中主体分工及定位的梳理。由此,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将与乡村振兴地区全面发展共进,建设内生驱动的儿童福利体系,将促使乡村社会迈向内生驱动的可持续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