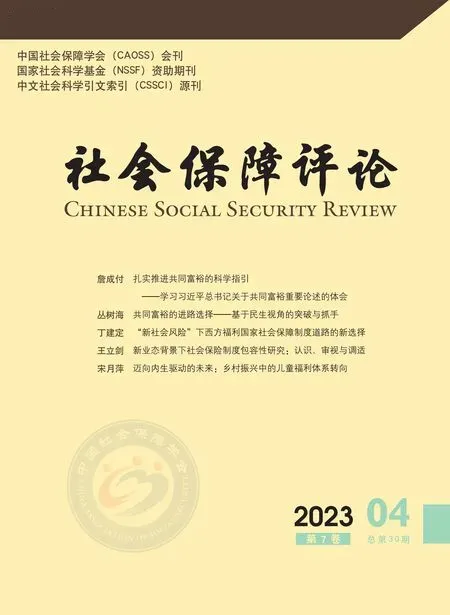多层次医疗保障筹资的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
王增文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结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规定,中国将逐步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和经办管理,并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待遇水平调整机制,实现基金中长期精算平衡;完善医保缴费参保政策,均衡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合理确定政府与个人分担比例;进一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机制,加强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救助等的有效衔接。到2030 年,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成熟定型。为达到这一规划纲要的目标,我们需要审视医疗保障筹资端的基本筹资逻辑。然而,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审视一下中国医疗保障面临的最大行动困境,对助推医疗费用和医保支出持续性上涨这一问题的因素进行溯源。
首先,越来越精准化的治疗技术、治疗手段和器械推动了高科技医疗的迭代发展,使得医疗的成本不断被推高,①封进等:《医疗需求与中国医疗费用增长——基于城乡老年医疗支出差异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3 期;王琬:《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的制度理性与现实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5 期;Keyong Dong,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Evolu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4); Yong-Yi Chen, et al.,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 2016, 3(1);Hua Chen, et al., "Impact of Urban-rural Medical Insurance Integration o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2, 76.其背后除了客观的医疗科技的助推,是否还有与其对冲的医疗成本减缩机制呢?走出生物医学的域界,我们发现,高科技医疗下的生物医学缺乏与心理医学、社会医学、康复医学的融合互动,这使得我们可以思考是否可以干预疾病治疗的过程,用心理、社会和康复的“外驱”机制予以协同治疗,以此来对冲日益高涨的医疗成本呢?其次,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态势使得慢病支出越来越成为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重心,慢病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0%左右。②单大圣:《中国医疗保障决策的地方化特征与改革思路》,《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5 期;彭宅文、丁怡:《风险扩张、财政压力与医疗保障筹资改革:政策变迁及影响因素》,《学术研究》2020 年第4 期。城镇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城镇退休人员不需要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但医疗费用报销依然是从医疗保险基金中支出。由此,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导致基金缴费会逐步降低,而支出水平却持续性的提升,使得“以收定支”的医疗保障基金收不抵支的风险越来越大。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下,医疗保障到底采用“以收定支”的筹资模式还是采用“以支定收”的筹资模式?最后,不断发生的医保欺诈问题使得医疗保障基金的支出越来越偏离医疗保障的保障逻辑和合理性基础,因此,为防止欺诈导致的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是技术问题还是治理决心的问题呢?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凝练出相关的要素体系,诉诸于条件思维,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社会情境,通过比较来进一步厘清中国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驱动逻辑。
中国医疗保障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政策体系基本成型,而从中微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医疗保障政策体系的协同性仍处于较低水平,更为精细和协同性的顶层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虽然《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实行省级统筹,但目前统筹层次仍然参差不齐,绝大多数的基本医疗保险仍然停留在县级统筹层面;③马超等:《医保筹资对医疗服务利用的政策效果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6 年第1 期;彭浩然、岳经纶:《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理论争论、实践进展与未来前景》,《学术月刊》2020 年第6 期;王俊华:《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理论与思路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 年第5 期。与此同时,医疗保障政策横向整合虽然有了较大的推进,如新农合与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进行了整合,但实际上,从非寿险精算的学理视角来看,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逻辑不同,基本医疗保障在一个区域内,不能按照人群、城乡、区域和职业来划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碎片化较为严重,不同的人群间存在较大的支付能力偏差,这需要向医疗保障精算基础的学理溯源,探寻有效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整合路径。二是从医疗保障政策的治理过程来看,管理的低效使得医疗保障在筹资端体现为筹资能力的不足和筹资基数的“弹性”,而筹资费率的“刚性”和筹资基数的“弹性”,使得医疗保障筹资水平仍然处于不确定和不充分的状态。由此来看,单一要素很难去解释和解决中国医疗保障费用持续上涨和医保基金压力持续加大的困境,而需要综合分析环境、法律、政策和管理等来凝练要素。
从学理层面来看,可以通过一条系统逻辑链来展开:“底线-权益-差异”正义价值取向应构成资源配置的基本划分原则,即医疗保障筹资受制于“底线-权益-差异”的原则,底线公平的医疗救助的财政融资的预算原则,医疗保险社会融资的权益性正义原则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融资的个人风险融资原则,以这三种价值取向的筹资原则的有机结合为导向构筑医疗保障筹资治理体系。构筑这一筹资体系需要前置性约束的是支付端的价值性医疗支出,而这一过程又要诉诸于行政对经办、医药服务机构的全过程行政监管的效能,以及经办对医药服务性机构的合约性约束。在医疗保障的筹资、支付和监管的管理闭环下能够有效地实现价值医疗,医疗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健康。所以,从公共卫生系统来看,医疗保障系统需要不断地与公共卫生系统进行协同治理,从治已病向治未病的价值医疗理念演进,从医疗治理向健康治理转型。在此基础上,再去审视“底线-权益-差异”正义价值取向下医疗保障筹资的理论建构及实现路径才会 产生更大的效能性。
二、差异性社会基础下医疗保障筹资机制
(一)医疗保障筹资机制的历史演进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将医疗卫生事业的属性定义为“福利性事业”(如表1 所示),医疗保障通过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方式为全民提供低水平和全覆盖的健康干预,背后的筹资机制体现为公费医疗的财政筹资、劳保医疗的单位筹资及农村合作医疗的集体经济筹资。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产权模式的变迁、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败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大量的体制内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私有经济领域,原有的统一性社会医疗服务体制开始逐步瓦解,筹资机制也不复存在。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医疗保障政策的可持续性,多主体共担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筹资机制开始逐步探索并建立。

表1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保障筹资机制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了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探索,从1987 年起北京、四川等省市的部分行业与市县实施职工大病、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这成为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滥觞。劳动部、财政部和卫生部等8 部门于1988 年开始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小组,探索建立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并尝试试点。1989 年国务院医疗社会保险的试点在湖南株洲、吉林四平、湖北黄石和辽宁丹东相继展开。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并选取了江苏镇江、江西九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为试点,俗称“两江”模式。1996 年4 月,在总结“两江”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56 个城市。随着试点的持续性反馈,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1998 年12 月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职工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2003 年1 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提出建立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农民互助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在医疗保障制度框架上实现了对国民的制度全覆盖。2011 年后,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固在95%以上。此外,对于除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无经济能力参保的贫困群体而言,国家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方面,也逐步做出基本性制度安排,城乡医疗救助分别于2003 年和2005 年在农村与城市进行试点,2008 年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至此,差异性社会基础下中国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和筹资机制基本建立。
纵观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我们发现,2010 年后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医疗救助筹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通过纳入一般财政预算方式予以保障。各级财政按照年度安排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并列入当年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下拨的资金占绝大比重,地方各级财政每年安排的医疗救助资金不能低于一定比例;医疗救助实施过程中的基金缺口由同级财政来弥补。医疗保险筹资方面,职工医保筹资采用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相结合,按照“人头筹资+收入水平比例”筹资方式实施;而居民医疗保险采取的是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按照“人头筹资+固定额度”筹资方式实施。商业医疗保险筹资方面,按照风险程度的完全风险的模式来筹资。对于医疗救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分别按照底线原则和完全风险的差异性原则来筹资,筹资理念和筹资机制相对简单,作为权益性原则筹资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由于在群体间、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差异性,需要进一步透视、厘清和校准其筹集机制的底层逻辑。
(二)在公平性价值取向下探寻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模式与筹资机制
一是财务模式与负担方式:效率性还是公平性。20 世纪80—90 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现收现付还是积累制成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界和实践界“角力”的聚焦点。基金积累的财务模式和多缴多得的负担方式更多地聚焦于缴费端的激励性和待遇端的社会风险性的可保性。1998 年12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通过个人账户的激励性,有效地提升了职工的参保积极性。然而,随着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保障学界的认知和研究的深入,政界和学界逐步意识到个人账户的激励性并不能有效化解疾病社会风险,而且大量的个人账户基金结余成了个体的额外收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常发生。为解决医疗保险基金效能性,个人账户取消的声音不绝于耳。①黄国武:《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发展思辨:基本多层向多元多层转型》,《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4 期;赵绍阳等:《医疗保障水平的福利效果》,《经济研究》2015 年第8 期;刘军强等:《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和田野资料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8 期;顾昕:《公共财政转型与政府卫生筹资责任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2 期;梁春贤:《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政府责任分析》,《管理世界》2011 年第6 期。其中的底层逻辑是医疗保险并不属于寿险,医疗保险本质上属于非寿险,符合非寿险精算原则。由此,个人账户的财务模式和多缴多得的负担方式显然违背了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原则。
二是筹集方式与筹集标准:闭环性还是兜底性。从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出发来审视基本医疗保险的筹集方式可以发现,对于年轻职工或居民而言,即时的满足远远大于延时的满足,因此年轻职工或居民会更加关注当下效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没有强制的环境下,其参保的意愿和积极性显然是弱于中老年群体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急病的风险越来越大,也由此导致其对疾病风险的厌恶性越来越强,自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概率会持续提升。在筹资标准方面,相对定额而言,比率性的筹资标准能够使得费率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筹资规模随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变化而不断变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疾病发生的风险。医疗保险遵循的是非寿险精算原则,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参保群体通过疾病发生的非对称性来对统筹区域内的疾病社会风险进行风险化解,此时,若存在大量参保人群的逆向选择行为,必然会产生疾病风险的不可保性。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必须通过强制性而非自愿性来进行筹资,由此来对冲个体的风险厌恶性导致的医疗保险系统的非闭环性。
(三)通过非寿险精算原则来审视医疗保险费率确定方式:以支定收VS 以收定支
在上面部分,我们讨论了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应以比率筹资的标准来厘定其费率。目前医疗保险的筹资费率确定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收定支”,另一种是“以支定收”。“以收定支”的医疗保险费率确定方式的基本意涵是聚焦于确保医疗保险基金的平衡,而“以支定收”的医疗保险费率确定方式聚焦于参保群体的基本健康权的保障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非寿险精算原则来审视医疗保险费率确定方式,“以支定收”还是“以收定支”更加适合中国现阶段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医疗保险的费率确定方式。由此,除了审视制度端,我们还需要走向管理端来探寻制度本身和制度理性管理机制。从医疗保险基金的制度规定来看,无论是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还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费率确定方式均为“以收定支”的筹集模式。从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原则来看,“以收定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和医疗保险非寿险精算的基本学理基础的。
基于此,“以支定收”在缴费端与支付端两者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要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分清先定报销规则还是缴费比率这一价值优先次序。若医疗保险筹资先定缴费比率,再定报销规则,则为“以收定支”的筹资原则;若先定报销规则,再定缴费比率,则为“以支定收”的筹资原则。医疗保障政策的上层建筑的构筑过程中,需要在经济基础的约束下深刻认识新时代矛盾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学界和政界需要深刻意识到,“以支定收”适合基本医疗保险原则,而“以收定支”适合商业医疗保险原则。
党的二十大指出,“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支撑这种制度上层建筑的价值基础是新时代矛盾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 多年,党和国家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最基本人权来持续性地提升医疗卫生的供给水平和保障效能。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从缴费端来看,截止到2022 年,中国基本医保基金累计结存36156.3 亿元,其中职工医保累计结存29439.7 亿元,居民医保累计结存6716.6 亿元,职工医保累计结存占了全国医保基金累计结存的81%。全国基本医保基金累计结存由2012 年的7644.5 亿元增加到了2021 年的36156.3 亿元,10 年增长了3.7 倍。①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计算而得。大量的医疗保险基金结余,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逐步消耗。《社会保险法》规定退休人员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疾病支出可以从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中列支,而中国的“职退比”②职退比=在职参保人数/退休参保人数,反映多少个缴费的在职职工要养1 个不缴费的退休人员。在持续性地提升,这就意味着医疗保险基金结余在未来30 多年的时间会很快耗尽。从非寿险精算的机理来看,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及统筹层次的提升,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应该逐步坚持“以支定收”的原则。
为何医疗保险基金管理要逐步用“以支定收”的原则代替“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呢?这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以收定支”的原则是基于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原则,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筹资原则,更是一种“可变缴费基数+固定缴费率”的一种医疗保险的支付管理原则;二是由于“以收定支”的原则过于聚焦于支付端,呈现为一种非全过程和缺乏整体性的非系统性筹资原则。由此可见,“以收定支”的筹资形式并非是一种基于非寿险精算原理的筹资原则。中国医疗保障政策经过了30多年的实践探索,通过持续性地建构,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过去一直实施的“以收定支”的筹资方式,需要逐步走向基于科学合理精算原则的“以支定收”模式。从实施条件和实施环境两个基本维度来看,“以收定支”秉承的基本行动理念是计划经济的财政策略,主要是在供给端发力,按照供给水平来厘定需求水平,是一种定额制,缺乏风险理念,由此导致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水平的非充分性;“以支定收”秉承的基本行动理念是科学的非寿险精算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人民健康权的保障成为党和国家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党和国家逐步开始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这时“以收定支”的基本筹资原则就不能很好地关照到保障水平。由此,需要在差异性社会基础下引导“以收定支”的筹资原则逐步向“以支定收”的筹资原则演进。
三、医疗保障筹资的学理基础、理念共识及理论建构
“以支定收”秉承的基本行动理念是科学的非寿险精算原则,其学理基础是医疗保险精算平衡。社会医疗保险精算在公平的价值基础上去化解疾病风险,借助的是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原理,利用保险精算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去化解疾病的社会风险。医疗保障的筹资除了医疗救助诉诸于财政一般预算的筹资基础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大病互助保险以及商业医疗保险都需要清晰地界定好基本的精算基础。
(一)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的学理基础
精算是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基础,若不通过基本的医疗保险的精算学的厘定,医疗保险筹资无法做到科学合理,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无法准确进行,各缴费主体对于医疗保险基金的责任就会模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绩效显然也不会太高。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服务科学化、精细化和有效性的尺度来看,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算是其筹资的基础和依据。医疗保险精算属于非寿险精算,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能够精准掌控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在精算基础上保障参保群体的基本健康权益,并能够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从世界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来看,医疗保险制度实施的早期,医疗费用结算往往采用按项目付费制和按平均费用标准付费等后付制,由此产生了医疗服务诱导需求的现象,使得医疗费用控制困难。随着管理理念演进和信息技术的持续性迭代,后付制逐渐开始被按人头、按病种或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等预付制付费替代,一系列的过程管控对医疗和医药服务费用支出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
政府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组织主体,应同时向参保主体和各缴费主体负责。具体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遵照基本医疗保险非寿险精算法则向不同的参保主体提供适应不同疾病风险概率分布规律的保障;另一方面,向不同缴费主体筹集适宜疾病风险损失额度分布规律的规模保障基金。以此两个标准作为科学的“量器”,筹资的不充分性与过度汲取性都是违反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的科学规律的。由此,基本医疗保险部门要充分运用非寿险精算工具和手段,科学合理地厘定基本医疗保险费率。
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设计涵盖了新制度构建、政策的迭代升级及制度的有效整合等方面。①王增文:《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变化、理念转型及理论概化——范式嵌入与法治保障》,《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5 期;鲁全:《中国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变革研究:府际关系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22 年第2期;管仲军等:《我国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变迁与内在逻辑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7 年第7 期;岳经纶、方珂:《从“社会身份本位”到“人类需要本位”: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式演进》,《学术月刊》2019 年第1 期。然而,无论是制度构建、制度升级还是制度的有效整合,在执行层面都必须有非寿险精算作科学支撑,以保障政策变动的科学性与执行的效能性。探寻其精算的学理基础显得必要且必须,从基本医疗保险费厘定的学理出发,我们能够提炼出相关的非寿险精算的要素集合,涵盖了探寻疾病出险的概率分布规律和疾病出险损失额度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选取合理有效的筹资模式,最后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政策模拟。探寻疾病出险的概率分布规律是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设计的逻辑起点,医疗费用支出往往取决于某类疾病发生概率、疾病严重程度、治疗疾病所实施的方案,以及治疗的医药成本等综合性因素,由此,我们需要精准测度医疗费用发生的风险分布规律。
(二)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的理念共识与理论建构
从医疗保险的筹资学理基础出发,针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地区统筹层次,其筹资的政策制度设计通常需要对统筹区域内的疾病风险谱系与主要疾病类别及与之相对应的医疗成本进行历史谱系、当前结构与未来几年可能性变动态势进行综合研判,得到基本的疾病变化谱,然后运用非寿险精算的工具与数理统计的手段和方法,探寻统筹区域内的疾病风险损失分布函数。针对统筹区域内的疾病分布的费用,可以通过两个随机变量去测度,随机变量一是某一时段统筹区域内目标群体罹患疾病的人次数疾病发生率;随机变量二是罹患疾病群体的次均治疗的费用支出额度。将两者相乘并结合统筹区域内的目标群体数量,由此获得某类别疾病的费用支出的变动逻辑,在此基础上能够精准地厘定每年的保费额度,从而确定保费费率。由此可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模式的确定要以风险理论和损失分布理论为学理基础。
与上述筹资学理相对应的筹资模式也逐渐明朗化,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模式是医疗保险制度及管理的核心内容。世界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并不相同,如德国、日本和韩国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基本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美国采用的是Medicare 和Medicaid 的基金制模式,中国采用的是由两者混合而成的部分积累制筹资模式。从筹资的学理基础来看,基本医疗保险应该属于非寿险精算,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现收现付制基本社会保险筹资模式更符合学理性的筹资基础;美国Medicare 和Medicaid 的基金制模式最后会诉诸于政府的补贴,而补贴的额度取决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程度。可见,从社会保险的基本规律和属性出发,基本医疗保险应采用现收现付制,来保持健康权的获得与基金的短期平衡的双重目标。由此,应该遵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基本筹资原则来确立筹资模式,即以风险损失概率分布为基准,在缴费基数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充分运用非寿险精算手段去测度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费率。
(三)“以支定收”筹资原则的技术性限制和技术可行性
上文中我们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寿险精算的理念共识的演绎,逐步建构起“以支定收”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筹集的学理基础。为何在目前这个阶段,提出这一问题,并要尊重学理基础去构建“以支定收”的筹资模式呢?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一种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除了模式本身的科学性外,还需要有实施的条件以及实施的政策环境。条件和环境这两个维度的约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去构建和实施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维度一是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条件要在符合非寿险精算的基础上,确立相对稳定的筹资基础,在医疗保险支出费用每年动态变动的状况下,动态地调整不同年份的缴费率。维度二是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环境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以收定支”思维模式,社会面很少有“剩余”,而且财政筹资会“顶格”而达到筹资的上限,在这样的语境下,若基本医疗保险采取“以支定收”的筹资模式,一旦出现医疗保险基金的赤字则无法通过更多的财政汲取来予以保证。
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财政及参保群体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由此,从筹资的可及性方面来看,“以支定收”的筹资模式开始逐步变得可能和可行,筹资模式实施的条件基本具备;从实施的环境来看,随着5G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化工具持续性地迭代升级,患者参保、就医的数据在不断地积累,由此而具备了预测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规模和趋势、筹资标准及优化基金管理的条件(DRG/DIP 待遇支付方式),基于统筹地区疾病风险分布预测的“以支定收”筹资模式基础已具备。与此同时,市场化带来了社会面“剩余”不断地增加,由此使得个人支付能力不断提高,正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升着参保群体缴费的弹性空间,这是实施“以支定收”筹资模式的客观条件。从可行性的第二个尺度——主观能动性来看,社会面的不同参保群体已经基本具备一定程度上支付可变筹资水平的能力。
(四)医疗保险筹资制度定型的理念原则与实践路径
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制度要走向定型,需要充分理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结构和基金的管理逻辑。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构建过程是先按照群体和区域分设,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制度开始逐步进行群体整合和区域统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面临两个维度上的调整,分别为整合与统筹。在进行整合与统筹的实践路径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两类人群,即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劳动者通常指的是城镇职工,非劳动者通常指的是城乡居民。从20 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劳动者而言,从2003 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针对的是农村居民,从2007 年开始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针对的是城镇居民。国务院2016 年1 月12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 号),截止到2022 年10 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了全国层面的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2016 年整合以来,筹资机制采用的是财政补助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这其中财政补助占了较大比重,个人缴费占了较小的比重。从补助趋势上来看,按照人均每年增加30 元的标准逐步加大财政补助力度。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缴费标准为320 元,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80 元,财政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1.8 倍以上,①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2022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得。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带有了社会福利的性质。由此,我们不禁会问:对于城镇职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代扣代缴的流量扣除模式是符合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而对于没有工作的城乡居民,国家的财政补助成为医疗保险的主要经费来源。那么,城乡居民一定要通过保险机制来解决筹资问题吗?
如果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来解决,城镇职工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那么,按照非寿险精算的原则理念,显然,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针对风险测度下的保险,因为按照风险保险的基本原理,“以支定收”的筹资模式需要退休人员也要缴费。由此可见,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医保基金的积累额度会逐步减少,甚至会出现赤字。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为下一步制度的再次整合及统筹层次的提升提供条件和基础。
从实践路径来看,若按照社会保险的基本思路去构筑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需要在厘清与把握好基本医疗保险精算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区域统筹下的风险可保性原则进行筹资,形成职工和居民的统一医保基金池,也就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的制度整合,由此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高统筹层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疾病风险的分散,由此达到风险分散的效能性。
四、医疗保障筹资结构治理的前置性约束机制
医疗保障筹资问题是医疗保障制度构建的表征窗口,其内核性问题在于医疗保障筹资宏观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医疗保障筹资结构性治理的前置性约束机制的生成。为了深入分析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放眼审视世界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障宏观治理模式及结构性治理的前置性约束的发生机制,学习其他国家优秀经验,并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以此来重新厘定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发展中的模式定型问题。
(一)医疗保障筹资宏观治理模式的世界性探索
从改革历程和政策定型两个维度看,人类社会对医疗保障的探索模式分为三类:
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医疗保障模式。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特点是制度覆盖面广。英国医疗保障的主体是遵照1946 年出台的《国民健康服务法》来进行筹资的,以国家税收作为主要基金来源而形成国民健康服务筹资体系,通过市场来筹资的商业医疗保险仅仅是一种全风险的筹资模式。由此可见,英国的医疗保障筹资宏观治理模式中,国家承担了绝大比重医疗保障筹资的费用。由于税收成为了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机制,由此体现出了完美的公平性。从财政角度来看,英国国民保健服务所需费用的90%以上由财政税收负担,社会保险总额也会按一定比例汇入其中。①Alessandra Guariglia, Mariacristina Rossi,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and Saving: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4, 23(4).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一般居民,都略去了个人支付能力与缴费之间的清晰对应关系,税收的全民性使得英国公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由此,筹资不涉及医疗服务水平的提供,使得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仅仅依据患者的实际医疗需要展开,而非根据其实际支付能力来提供,因此公平性成为英国国家医疗保障模式的最鲜明的特征。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德国实行强制性全民医疗保险,国家会通过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帮助低收入群体参保。德国全民医保制度总覆盖面达到了98%以上,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和全程覆盖。德国通过医疗保障的法典确立了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保为辅”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实施医疗保障的主体是法定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占较小的比例。德国社会法规定,月收入低于4050 欧元的劳动者须投保法定医疗保险,只有收入在此标准之上的群体,如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可选择加入商业医疗保险体系。由此可见,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基于“双元并立、结构互容”的属性,构筑起具有较高稳定性和相对灵活性的保障体系。德国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筹资机制是由雇主、雇员各承担一定比例的缴费,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由养老金来承担部分医疗保险的缴费。从医疗保险缴费的费率水平来看,缴费水平稳定在平均工资的14%左右,有效地实现了健康群体与病患群体之间、健康高风险者与低风险群体之间、长寿群体与非长寿群体之间、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彼此进行互助共济,通过非寿险精算原则来化解统筹区域内的疾病健康风险,充分体现了社会医疗保险的社会属性、风险保障属性及保障结果的公平属性。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二元有机结合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由社会医疗保险与私人医疗保险构成。在美国医疗是一种产业,看病费用极其昂贵,若无医疗保险,家庭将难以承受巨额医疗费用。美国的医疗保障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面向美国公民与永久性居民来提供两类保障,以及由市场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由此形成医疗保险(Medicare)、政府医疗补助(Medicaid)和私人医疗保险三项制度。
医疗保险(Medicare),是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各州间政策统一,向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能够为老年人提供90%以上的住院治疗医疗费用。美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也延伸至医疗保险领域。尽管医疗保险(Medicare)部分解决了医疗服务公共性和保障性问题,但是从筹资机制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对医疗保险的运作仍然采用市场化的竞争性手段。当然目前美国以自由投保方式为主,但也诉诸于工资税和政府的投入来筹集医疗保险资金。政府医疗补助(Medicaid)是向美国低收入群体提供健康保障,是依赖政府财政为中低收入群体筹资而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医疗保障筹资机制。在联邦政府的上位政策的引导下,各州政府制定适合自身的医疗保险(Medicare)筹资标准、保险程度及保障服务内容。①胡宏伟、王红波:《美国托底性医疗保障:体系阐释、制度评估与经验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5 期;Giulio Nittari, et al., "The Right to Medical Assistance for Seafarers.Ethical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elemedicine to Improve Healthcare on Board Ships," Marine Policy, 2019, 106; Alessandro Manduca-Barone, et al.,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A Review of Canadian Policies and Guideline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5.第三类是私人医疗保险。其作为一种非工资福利,筹资方式是由雇主为雇员支付保险金,也可以自行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多层次的医疗保险的筹资计划满足人群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美国医疗保障筹资模式更加偏重于个人的作用,尽管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相关条例生效后,通过税收来增加医保筹资规模,使中低收入群体也能获得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险,即通过社会团结来抵御疾病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在医疗保障筹资上的个体化取向。但特朗普上台后否定了奥巴马医改方案,美国的医疗保障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个人化筹资模式。
(二)医疗保障筹资结构性治理的前置性约束机制
从人类社会对医疗保障的三类探索模式来看,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医疗保障模式,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亦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二元有机结合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优劣之分,三种模式各有优势,并相对健康运行。不同模式也深耕于其文化基础,如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所以医疗保障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国家性;德国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理论建构能力能够做到医疗保障制度理论逻辑自洽,较好地建成并顺利实施了医疗社会保险,后有日韩追随加入;美国是由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国家,鲜有成为国家追逐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国家-市场”二元有机结合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以上三种筹资模式都形成了各自的基金平衡机制,为何中国的医保基金出现较大的供需压力呢?我们需要首先明确医保基金出现不可持续的关键是前置性问题。这其中分为两种状况:
一是医疗保险的熵增样态。政府通过协同企业和个体以交税(或缴费)的形式形成医保基金的筹资机制,通过筹资模式形成医疗保障基金池的基金专户,由医疗保障机构通过与医疗机构或医药机构的合约签署来实施购买服务,这其中若缺乏行政监管或社会监督会存在医疗机构或医药机构诱导需求的状况,进而产生过度医疗或大尺度开药的诱导需求状况。由此,中国医保实际运行陷入熵增的无序的发展样态。
二是医疗保险的熵减样态。政府通过协同企业和个体以交税(或缴费)的形式形成医保基金的筹资机制,通过筹资模式形成医疗保障基金池的基金专户,由医疗保障机构通过与医疗机构或医药机构的合约签署来实施购买服务,这其中加入了刚性而有效的行政监管或社会监督,使得医疗机构或医药机构诱导需求的状况被持续性关注、监督和惩罚,进而杜绝了过度医疗或大尺度开药等诱导需求的不良行为。医疗保障基金能够被合理有效利用,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世界各国的医保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就是监管的持续性的介入和强化。由此,医保实际运行进入了熵减的有序发展样态。
纵观改革开始到中国十八大之前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我们发现存在的典型问题是医疗保障体制机制的不顺畅,典型特征是医疗保障投入高、效益差,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监督机制的缺乏。①李诗晴、褚福灵:《总额预付制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第4 期;赵绍阳、杨豪:《我国企业社会保险逃费现象的实证检验》,《统计研究》2016 年第1 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监管和其他主体的监督,中国的医疗保障陷入了行政主导下的“床位诱导需求”市场发展理念,②Milton I.Roemer, "Bed Supply and Hospital Utilization: A Natural Experiment," Hospitals, 1961, 35.医疗机构不断地“吸纳”医保基金,而医疗绩效并未同步的显著性提升。③刘子宁等:《医疗保险、健康异质性与精准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金融研究》2019 年第3 期;黄薇:《保险政策与中国式减贫:经验、困局与路径优化》,《管理世界》2019 年第1 期;刘晓婷、黄洪:《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老年群体的健康公平——基于浙江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7 期。实际上,医疗保障制度模式并不分优劣,制度模式往往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等多元要素的叠加,但有一项内容是各个国家均要遵从的基本法则,那就是除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本身,制度运行机制的监督管理过程同样重要,制度模式的运行必须要有全过程监管体系: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医疗保障模式,还是以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亦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二元有机结合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通过国家财政将资金投入到医疗或医药机构,这中间加入了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完成了熵减的干预过程,确保各种医疗保障模式健康运行。
五、医疗保障筹资、整合及统筹的底层逻辑
纵观世界三种典型的医疗保障筹资模式,无论是针对退休人群(65 岁及以上)的美国医疗保险(Medicare),还是退休前后均为财政融资的英国国家医疗保障,亦或是退休前后均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德国医疗保险,其典型的特征是“风险-保险”的紧密耦合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如果风险不能够通过保险的筹资机制来进行化解,则“筹资-支付”必不能达到有效的平衡。遵照这个尺度,本文发现,以上三种筹资模式都能够在“工作-退休”的状态保障有效融资。美国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Medicare)的医疗支付由工作一代予以承担;英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国民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筹资均由国家财政承担;德国完全遵照医疗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退休前后均需要缴费。由此可见,一个健康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底层筹资逻辑是能够充分保障可测度的健康风险,用不同的化解机制予以对冲,其中要基于“风险-保险”的内在闭环性去化解。以此逻辑来审视中国的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我们发现《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退休后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这显然不符合“风险-保险”原理,所以,必须要遵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的底层逻辑,重新审视整个制度的设计,做到保险对风险的有效化解。
基本医疗保险从区域分设、群体分立到走上“整合-统筹”的公平统一的轨道需要理清其中的底层逻辑。医疗保障群体分立最终走向政策的整合路线,通过整合使得制度和水平在群体间的差异逐步缩小直至一体化;而医疗保障区域分设最终走向政策的统筹路线,通过统筹层次的提升,使得医疗保障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收支的规范化管理。由此,医疗保障的改革会呈现出“筹资-整合-统筹”的基本行动逻辑和构筑框架。从基本行动逻辑来看,以筹资为基本逻辑起点,医疗保障政策先整合还是先统筹?或者同步进行?这涉及到医疗保障改革的底层逻辑。当然,中国在这方面通过不断地试点说明了这其中的逻辑先后顺序,其中典型的案例是江苏兴化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政策的全部打通试验,试验进行了两年发现政策不可持续了,政策试验最终宣布失败。政策试验为何失败呢?通过分析“筹资-整合-统筹”的基本行动逻辑和构筑框架来看,大量年轻的城镇职工选择参加居民医疗保险,导致职工医保的筹资和支付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由于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在制度上并没有实现整合,制度的支付仍然是分立的,而在管理上却先行打破两者之间的边界,职工医保中退休人员无需缴纳医保费用,由此职工医保产生了结构性的“挤兑”。这其中的底层逻辑是职工群体的风险没有被职工群体的缴费所化解,城镇职工医保制度与居民医保制度未整合,而管理的改革却走在了前面。如此整合,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职工医保基金被“挤兑”的道德风险便发生了。这也是政策试验失败的底层逻辑。
基于此,我们可以初探医疗保障“筹资-整合-统筹”的底层逻辑:首先,医疗保障政策要逐步定型,其中定型涵盖两个维度上的改革,一是横向整合,二是纵向统筹。在逻辑先后顺序上,应该是先实施政策的整合,使得风险能够在更大群体内得到化解;然后,逐步提升统筹层次,使得风险在更大的区域内得到化解。在此基础上,再走向管理领域,再谈管理效率,逐步将关注点放到较为微观的层面,去审视基金的筹资率和遵缴率等筹资领域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了解底层逻辑的基础上,融合系统性思维去全面审视医疗保障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和系统性管理的改革问题。若缺乏底层逻辑探寻和系统性思维的审视,容易落入群体内部,而局促于医疗保障的群体性内部不停地打转,最终的样态可能是在“以收定支”的筹资模式下,不同群体内部医疗保障基金能够做到相对平衡,但并不能解决健康权的均等性问题。
六、“底线-权益-差异”的多层次医保筹资的实现路径
医疗保障在规模化和整体性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诉诸于DRG 和DIP 支付模式,使得医疗保障支付的效能逐步显现,医疗保障政策正逐步走向定型。然而,在差异性社会情境下,医疗保障在筹资端的“条件-环境”的非一致性使得我们不得不重塑医疗保障筹资的理论逻辑并探寻更加有效的实现路径。医疗保障的筹资必须要夯实学理基础,在稳定的价值取向下,找到其理论建构的社会基础。医疗保障体系的多层次性体现为社会救助系统下的医疗救助体系,维护的是底线健康权;社会保险系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保障的是权责共同体下的权益正当性;商业保险系统下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实现更高健康水平自我保障的正义性。那么,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实施的价值取向是有差别的,如何构建起一条基于“底线-权益-差异”的多层次医保筹资的实现路径呢?
医疗保障筹资体系遵循的是“底线公平+正比公平+效率正义”的多层筹资结构原则,既不能遵循完全风险的市场效率原则,也不能完全采用均等化的风险原则,更不可能倚重于完全公平的社会福利原则。依据“多层筹资结构”原则,中国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元和碎片化的治理格局需要走向“先整合,后统筹”的治理图景,由此形成中国的医疗保障筹资体系,即“财政预算+社会供款+风险筹资”的多元协同供给模式。医疗救助筹资以财政预算为资金来源,体现的是底线公平;医疗保险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多主体供款作为基金来源,体现的是权益公平;商业健康保险体现的是社会差异性原则,诉诸于正比筹资原则的个体完全性风险的筹资模式。保障底线公平,体现权益公平,尊重正比公平,使得医疗保障的筹资体系更多的体现为维护国民健康权益的第一端口。在系统性治理体制与机制下最终探索出一条基于“底线-权益-差异”公平正义的医疗保障筹资的实现路径,使得医疗保障筹资逻辑最终实现从差异性走向共同体。具体来看:
遵循“底线-权益-差异”公平正义的医疗保障筹资的价值取向,在风险建构和逻辑自洽的基础上,按照非寿险精算的基本筹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筹资体系。对于医疗救助筹资遵循的是底线公平的原则,属于财政融资模式,将筹资过程纳入一般财政预算。按照非寿险精算原则,对于权益性正义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要遵循学理上的权责利对应的原则,筹资要走终生缴费路径。医保基金的收支要封闭运行,不能为医疗救助开支留出“口子”,若医疗救助走医保基金报销,需要将财政的缴费划入医保基金池。当然,也不能通过商业保险来为基本医疗保险“打补丁”,要通过“以支定收”的模式来合力筹集医疗保障基金,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不能通过“以收定支”下基本医疗保障筹资的结余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这属于第三层次的医疗保险。各层次能够独立封闭运行,要有各自的功能性边界。
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算基础和筹资逻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是现收现付制,而现收现付制的支付端决定了筹资端,即基本医疗保险应采用“以支定收”的非寿险精算厘定的模式。基于此,退休人员实施的基本医疗费用支出要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来解决,需要相应的筹资保障机制。这其中会有两种机制,一种是通过继续缴费的方式来完成风险的建构;另外一种是通过公共财政来实施老年医疗社会福利,由公共财政为退休人员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当然诉诸于社会福利来解决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问题,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福利治理的规模、税收汲取能力和公共财政水平等因素。针对中国的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本文从保险和福利两个维度提出如下针对退休人员权益的基本医疗保险筹资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社会保险理念思路,新退休人员也要承担起一定个人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责任。一是老人老办法,对于已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属于计划经济遗留的历史性问题,应由企事业单位承担。二是中人中办法,对于政策实施时,尚未退休的职工,由财政与个人共同筹资,可按照其横跨退休人员缴费机制建立之前与之后各自的年限,按比例分段计算。三是新人新办法,对于政策实施后加入的新职工,要终生缴费,退休后以个人筹资为主。这其中,对于领取低保的退休人员,由财政为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对于罹患灾难性疾病等人员,由大病医疗保险来覆盖和保障。第二种路径是社会福利理念思路,继续按照退休人员不缴费的原则,遵循非寿险精算的基本逻辑,将退休人员疾病报销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这就需要国家为退休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由此,对退休群体而言,筹资端以社会福利的形式注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而支付端可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的形式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