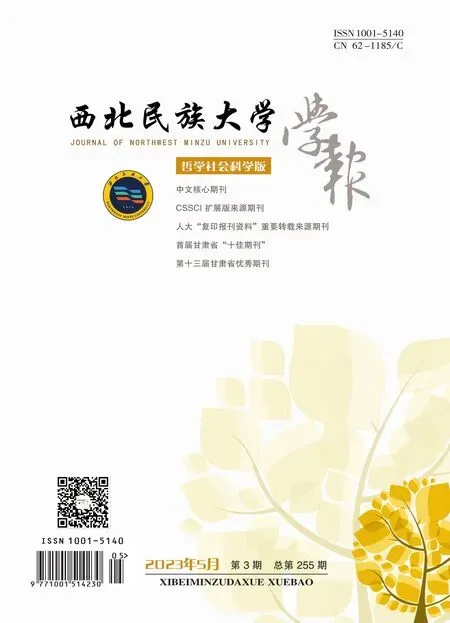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
——论《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写作方式
李韶华,肖锦龙
(1.兰州城市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是波兰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她于2019年10月10日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她的代表作。《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艺术的角度看,则与托卡尔丘克创造性地运用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直接关联。
托卡尔丘克是一位自觉进行小说艺术方式变革的作家,她敏锐地感知到当代人所处的“新现实”的特征:现代生活被瞬间性所主宰,分裂成偶然的碎片,构成一个缤纷的永不枯竭的印象之流[1]。世界瞬息万变,作家要不断更新艺术形式,以适应新的现实。因此,她在《灵性消失的时代需要温柔的力量》中直接发问:“我们该如何构建我们的故事,才能使其撑起世界这伟大的如星丛一般的形式?”[2]文中使用了“星丛”(Constellation,又意为星座、星群)这个术语,并提出了星丛式小说的创作理念。
一、星丛式小说和托卡尔丘克的创作
“星丛”原本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人们划分星空区域和认识星空格局的一种方式。星丛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的网络或空间的集合体。人们用“星丛”这个比喻化的形象来喻指普通人在观看天空中的星座排列时会自认为它们是任意而偶然的,但实际上星辰的位置及活动轨迹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联系[3]。瓦尔特·本雅明首次将“星丛”这个术语引入到其哲学理论中,本雅明从占星术中发现了星丛的多元共处的空间维度特性,以过去与当下的关系及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使用了“星丛”。在思考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时,本雅明认为过去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消失殆尽,而是以零散记忆的形式共存于现在的生活图景中。在这里,他放弃了固有的时间性思维,而是着力于从空间角度来透视这种关系,并指明了其外在形式是零散的,需要再次整合。同理,在探讨人与万物的关系时,本雅明明确使用“星丛”这一概念,认为“星辰间的星丛隐喻着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人与事物之间多维度的相互模仿、呼应、吻合”[4]。他用“星丛”来喻指宇宙万物间的多维度的连接关系。接着,深受本雅明影响的阿多诺继续使用了“星丛”这一隐喻。阿多诺认为,“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像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5]。“星丛意味着一串并列且变化的要素,并不屈服于一个公分母、基本核心或第一原则之下。”[6]阿多诺在这里重申了星丛的互相关联性及异质共存性,并指出了星丛的变化性,进一步明确和拓展了星丛的辩证法内涵特征。后来,阿甘本在研究本雅明的辩证式布局时继续使用了“星丛”这一隐喻,他指出,“要用‘星丛’的方法来界定当代,要把它与‘现在’这个确定的历史事实相结合,从而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凸显出来”[7]。阿甘本既把“星丛”作为方法论来使用,又指出了“星丛”所喻指的各种关系是在运动变化中凸显出来的。以上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是在哲学层面使用“星丛”这一术语,都把星丛作为一个隐喻,用“星丛”来喻指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其内部的运动变化规律及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星丛”及其喻体的特征既是完全不同因素的并列,具有多元混杂性和异质共存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具有彼此关联性和内在统一性。“星丛”这一隐喻及其特征被托卡尔丘克所接受,并被她转化为方法论成为其小说创作的理念来源。
托卡尔丘克认为世界的表象是混乱无序的,是由无数的碎片构成的星丛,但现实又是一个相互连贯、密切相关的影响系统,人、植物、动物和物体都浸入了一个由物理定律支配的单一空间,通过无数种形式相互关联着[2]。托卡尔丘克与本雅明、阿多诺一样,都用“星丛”来喻指世界万物间的看似混乱实则互相关联的关系。不过托卡尔丘克似乎走得更远,她还将星丛的这种内涵特征作为方法论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构思之中。这种新的小说形式既要适应和表现世界的多元复杂性,又要体现其内在的相互关联性。而托卡尔丘克一直致力于做这种关联性研究,并努力寻找使各部分相互联结的方法。她相信作家能用自己善于整合的头脑将散落成碎片的各种现象收集起来,并把它们再次粘合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无疑就是小说的世界。所以她才大胆提出既然世界具有伟大的星丛式形式,那么作家在构筑故事时能否用与之匹配的星丛式小说结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托卡尔丘克也自豪地指出:一个能构建起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的天才作家即将问世,他能讲述完全不同、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故事,也是个能适应一切基本事物的故事[2]。而这个天才作家的新的讲故事方式就是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这就在理论方面理清了星丛式小说的叙事形式,要用无序混乱的外形来匹配世界的多元流动变化,同时,也要有内在的连接点来连贯散乱的碎片化故事,使其呈现出内在的整一性。
在小说创作实践中,托卡尔丘克指出自己是在写作《云游》(2007年)时格外关注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其实在她更早的作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年)中,就已经表现出星丛式叙事结构探索的努力。该小说中有一个名为《星历表》的单元,托卡尔丘克在其中表达了和本雅明从星丛中获得启示的类似的看法,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星历表是完美地标明行星位置的详细表格。数字排列从一到六十,因为人们给了时间那么多的可能性,以便时间能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星历表展现的是一种经过细心斟酌才能构建的空间结构图景,其表现的世界神奇的稳定。这段话暗含了这部小说在结构形式上与星丛式小说结构方面的类似之处,也可以看作是她星丛式小说结构的构思来源。1998年发表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距2019年托卡尔丘克发表《灵性消失的时代需要温柔的力量》相距21年,也可以说,托卡尔丘克是先有创作实践后有理论总结的。关于这一点,《云游》的译者在后记中也提到过:性别界限、国别界限、局限的生活空间、开放的思想历史,种种界限被文字消解,从这个意义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第一部“星群小说”[8]。因此,下文将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作为托卡尔丘克的第一部星丛式小说,对星丛式小说叙事结构的实践方法进行分析。
二、星丛式小说的表层结构
为了展现纷繁复杂的星丛式世界,托卡尔丘克在构筑星丛式小说的结构时,有别于传统小说的严整有序的叙事结构模式,有意将其外在形式打造成如夜空中的星丛那样的凌乱无序,创造了其特殊的结构安排方式。
(一)有意错乱小说的篇章排列顺序,使其失去了文本秩序
一般而言,目录是文章的思维导图,可以直接显示一篇文章的整体结构。民间有“目录不明,终是乱读”的箴言,足可见目录对文章的重要性。因此,传统小说都具有非常严谨的目录,各条目内容编排层层递进,逻辑严密,从目录中我们就可以大致领略作品的整体内容和发展脉络。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却没有目录,由112个单元构成,这些单元也没有标注序号,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的小标题,它们或是由小说中的人物名字或绰号构成,如《玛尔塔》《如此这般》《马雷克·马雷克》《彼得·迪泰尔》《弗兰茨·弗罗斯特》等,或是由动植物的名称构成,如《豌豆》《腔棘鱼》《母鸡,公鸡》《蘑菇》《芦荟》《大黄》等,或是由一些自然现象构成,如《月蚀》《火》《雨》《彗星》《水灾》等,或是由《梦》《网络中的梦》《书信》等名词构成,或是由《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酸奶油焖毒蝇菌的方法》等句子构成,这些单元的内容大多与标题切近,不但能独立成篇,而且随意的穿插放置在整部小说中。整部小说除了叙述库梅尔尼斯的故事时采用了16个连续的小单元以外,其他邻近的单元之间大多没有内容或故事情节连接的承继关系,所以要从标题的内容或排列顺序上几乎很难分辨出整部小说的内在结构,因此,整部小说犹如一个巨大的“迷宫”。
(二)有意安排诸多断裂的时间点,使其缺乏线性连接关系
时间陪伴和作用左右着人的一生,不止是人,世上存在的一切,都受到时间的掌控,都被困在时间的牢笼里。作为时间艺术的传统小说,大多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采用线性连贯的叙述方法,各部分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和因果联系。因此,传统小说中一般都会有比较清晰的时间点设置,写作和阅读时通过梳理这些时间点和因果链,也就可以理清小说的结构框架和情节脉络,让小说自然流畅地连为一体。但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托卡尔丘克在叙述故事时故意切断了时间在确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物理属性,有意模糊其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线索,各种时间标志随处可见但又分不清先后顺序,使小说失去了连贯性。如小说开篇《梦》是以女主人公“我的梦”开始的,没有任何时空历史纬度的介绍。紧接着第二篇是《玛尔塔》,开头第一句是:“第一天一整天我们走遍了自己的土地。……第二天一到傍晚玛尔塔就来了。”[9]3-4第三篇《如此这般》开头是“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如此这般’总是在电视快讯之后迅速就来了”[10]9。这里接连出现了标示时间的关键词“第一天”“第二天”“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表面上看像是连在一起的几天,但实际上这几个时间的间隔跨度很大。“第一天”是女主人公“我”和丈夫“R”三年前初次来到皮耶特诺的那一天,但是确切的“三年前”是哪一年不详,从始至终也没有交代。“第二天”的确切时间也不详,因为女主人公“我”一再强调自己忘记了第一次见到玛尔塔的情景,只能肯定是在早春时节,也就是在早春的某一天见到了邻居玛尔塔,第二天她才来自己家拜访。而“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跟前面两天一点关系也没有,是指邻居马雷克·马雷克葬礼后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大概是在寒冷的一月份。
同时,《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虽多次提到具体年份,但是这些年份出现的顺序却极为混乱。小说中第一次提到时间点是在第34页《阿摩斯》中,提到一个明确的时间为1969年,在这一年的早春时节克雷霞做了一个梦。在第58页《关于皮耶特诺德旅游指南》中第二次提到多个时间点,如在1949年出版的旅游指南中,追溯皮耶特诺最早的时间点是1743年,紧接着列举了皮耶特诺在不同年代的人口情况:1778年人口为57人,1840年为112人,1933年为9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7年为39人。在1840年有21幢房屋,其主人为封戈埃特岑伯爵。但是这些时间点跟小说内部连接的时间没有直接关系。第三次是在小说第245页《未卜先知者》中,外号叫“狮子”的占卜师在1980年冬天开始写一本名叫《末日必将来临》的书,并于1990年自费出版。占卜师预言世界将于1993年11月结束,结果那一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接着在第245页《埃戈·苏姆》中提到时年23岁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埃戈·苏姆在1943年早春时节吃过人肉,后来他辗转来到新鲁达当了历史老师,到了1950年害怕自己会变成狼。《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第281页《屋顶》中写封戈埃特岑教授(1862—1945)时最后一次提及时间,封戈埃特岑教授也是全文众多人物中唯一一个有确切生卒年的人物。从以上几处明确的时间点标示来看,《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部小说中涉及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1743年到1993年,虽然这些时间有交叉点,但总体看来这些时间点只与主人公的生平经历有关,而与整部小说的内在结构没有关系。
因而,星丛式小说看起来时间点多,但都是不确切的时间点,只是一个个时间的断片,与整部小说的叙述线索无关,根本没有办法从叙事时间角度来梳理结构框架,把握文本的构思意图。而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也多次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对时间的态度,即时间禁锢了我们,既没有瞬间,也没有千年。所以她在作品中一再提及时间但又让它们失去其物理联系,意在超越时间对我们的束缚和制约,打破传统小说惯有的线性结构模式,同时在小说结构的构建方面有所创新和拓展。
(三)有意淡化和紊乱故事情节,使小说呈现出情节的无序性和多元混杂性
传统小说的核心使命是讲述精彩曲折的故事,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的结构布局大多坚持以情节为中心,讲求有头有身有尾,注重故事情节的设置,且追求一波三折的效果。以沃尔夫、乔伊斯等人引领的现代主义小说虽极力倡导淡化情节,但实际上只是对传统小说追求的“情节曲折”不满,其总体故事架构还是传统小说的模式。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却全然不同,整部小说没有设置统一的故事情节,也没想塑造人物形象。小说虽然也有贯穿始终的两个主人公“我”和“玛尔塔”,但没有围绕这两位主人公展开故事构造,“我”和玛尔塔从开篇到结尾只是生活在皮耶特诺农村地区的两个默默无闻的妇女,女主人公“我”除了喜欢收集别人的梦以外,生活循规蹈矩,毫无波澜,没有故事性。玛尔塔则略显怪异,她长年昼伏夜出且会在冬天冬眠,她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皮耶特诺,她没有刺激的冒险经历,也没有与他人发生情感纠葛,更没有改变其奇怪的生活习性。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既不明晰,也没有变化。此外,小说也写了其他几个人物的生活,但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占全篇的篇幅极有限,如人物马雷克·马雷克的故事,小说叙述他从出生到上吊自杀死亡的一生仅占用了一个单元的篇幅。还有劳伦霞、埃戈·苏姆、弗兰茨·弗罗斯特等人物的故事都是以各自的同名标题为纽带组合成篇,在全篇的分量有限。整部小说中只有长着胡子的圣女库梅尔尼斯的故事是相对完整的,但也只是占用了112个单元里的16个单元,且散乱穿插在前后各不相关的单元之间,各部分之间支离破碎,紊乱无序,需要读者重新整合发现,才能辨析其故事全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呈现出这样多人物、多情节的散乱模样,其极力淡化情节的做法,消解了传统小说对故事情节的偏爱。
(四)有意设置了多维视点,以展示流动变化的世界
星丛式小说为了展现复杂多变的主客观世界,选择了多维的视点。托卡尔丘克“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我能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多少种世界,我就能生活在多少种世界里。”[10]334《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正是以多维变化的观察视点来展现新鲁达这一地域万物的生存状态的。
1.采用了多方位的观察角度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对新鲁达长达千年的历史变迁的叙述主要通过对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流变及万物的生息繁衍的变化来展现。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既大体相似又变化多端。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一再提及女主人公、玛尔塔、阿格涅什卡等人物观察皮耶特诺的角度,他们从空间方位的上下左右看,从事物的内部观看,又从时间视点的白天和夜晚看,在每一种观察视点中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或是以人类的视点在谷地上方观看村庄的一切生物,或是以蘑菇的视点从下方观看人类的活动,或是从人的嘴巴进入身体内部以便观察人的内部构造,或是从时间链上的白天和夜晚的角度,既叙述普通人看到的白天的风景和白天的房子,又叙述玛尔塔看到的夜晚的风景和夜晚的房子,她看到了成千上万人的梦。这样,将小说中各种各样的观察角度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展现出万物各自的位置及运行特征。
2.采用了比较的观察方法
星丛式小说具有变化流动性,而事物的变化生成性是在同类事物的比较基础上生成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广泛使用了比较观察的方法,通过同一人物错时观察同一对象的方式来展现其流动变化性。如德国人彼得·迪泰尔自年轻时就离开故土,一别就是40年,晚年的他不辞辛劳,不惜跨越整个欧洲返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弗罗茨瓦夫(德语名称,波兰接管后改为“新鲁达”)。彼得想再次看看自己的村庄,但昔日的村庄已缩为一个“骨架”了。过去与现在并存于同一幅画面中,眼前的图景和记忆中的图景重叠交叉,似是而非,变化流离,让他目不暇接,最终因太过激动而死在了边界。又如另一人物帕斯哈里斯也不止一次眺望自己的村庄,可他看到的村庄和他童年记住的村庄也不一样。同时,小说还通过同一物体在不同时段的状态来表现世界的流动变化性。如题为《小汽车日》中,女主人公和丈夫R在森林里发现了一辆隐匿在云杉枝丫里的“奇迹牌”小汽车,而在相隔几百页的《府第》中,才揭开了这辆小汽车的谜底,原来这辆小汽车是很多年前封戈埃特岑伯爵被迫离开自己的府第时从药店老板那里用红宝石戒指抵押来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还是崭新的白色小汽车,现在已经变成了蘑菇和爬山虎的栖居地。小说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托卡尔丘克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世界看似不变实则千变万化的特征。
3.采用了多个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托卡尔丘克不但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统揽全篇,同时她还使用了多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这些以第一人称“我”发声的讲述者并不是同一个主人公。小说中女主人公就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姿态出现的,她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贯穿小说首尾的结构性人物。但除了这个女主人公外,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还通过互文的手法,进入其他人物如帕斯哈里斯、库梅尔尼斯的意识里,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出来发声。如在叙述《圣女传》的篇章中,加入了类似前言和后记两个部分,而所用的叙述视角就是其帕斯哈里斯的第一人称视角。让帕斯哈里斯自己出来说话,表明他在写作《圣女传》时的动机及其惶恐不安的心态。这与五篇《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中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形成互补。而在《库梅尔尼斯Hilaria的幻景》中,也直接以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库梅尔尼斯的梦境及感悟,谈她自己对基督的认知,又与帕斯哈里斯通过阅读她的心声来虚拟库梅尔尼斯的生平事迹形成互补。同时,还用“梦”和“网络中的梦”为标题,以“我梦见……”“我来到了……”等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写不知名的、网络上的众多人的梦。如上在同一部小说中托卡尔丘克运用多个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尝试很成功,因为这样可以进入每个角色的内在视野,让其发出不同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声音,呈现出多声部的特点。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碎片、每一个声音都能被记载,被重视,让每一个碎片都闪耀自己的光芒,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当然,通过这种手法,还可以让小说的叙述视野更宽更远,表现的生活面也就更丰富多彩。
4.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跨越物种,让万物众生都出来说话
受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中心论成为普遍常识,那句被奉为至理名言的“认识你自己,方能认识世界”的话语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指导下,人类自认为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成为一切地球资源和生命的主宰者,忽视甚至无视其他生物的存在及意义。但随着解构论的开放、多元的认识论框架的建立,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人类行为既有一致性和交叉性,也有差异性,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更需要多元多维的角度。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只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人与自然万物同生共长,密不可分,开始重新审视主体、客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动态性关系,并尝试以平等的眼光对待其他生物。托卡尔丘克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得让书中所有出现的生物和物体穿透我,包括所有属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一切,以及所有鲜活着但并未赋予生命的一切”[2]。因此,在星丛式小说中,她以最严肃的态度审视所有的生物,将它们和人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和谐共处。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托卡尔丘克推人及物,让她笔下的豌豆、腔棘鱼、蘑菇、火、白蜥蜴等生物都有了生命,也都在作品中唱响自己的生命交响曲。在小说中,托卡尔丘克会以温情的笔墨叙述鼻涕虫一家的故事。鼻涕虫一家的房子坐落在新鲁达方向约两公里的地方,这是一所位置奇特的房子。溪流从两边冲刷它,舔着它湿淋淋的墙壁。它们家有棕色头发的大个子父亲、矮个子母亲和一双儿女。晚上它们摸黑无言地坐在桌边。夜间大个子父亲会悄悄溜到路上,然后来到人类的住所探险。
托卡尔丘克也会以温柔的笔触描写水和池塘,自然界的水会发出“呐喊”般的哗哗作响的声音,池塘在雨后竟然“溜”掉了。她还会以人格化的方式书写名叫“弗拉蒙利纳”的蘑菇的所见所闻:它是一种冬天生长在枯死树木上的蘑菇,由于生活在自己的蘑菇家族整体死亡的时期,所以它看到的是别的蘑菇的残骸——盖了一层白雪的微绒牛肝菌由于腿已经腐烂而摇摇晃晃,磷皮牛肝菌也已东倒西歪,多孔菌由于潮湿而倒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托卡尔丘克成功地跨越了物种界限,展现了万物共生的生命状态。
总之,托卡尔丘克就是通过上述四种方法,使《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外形犹如无数碎片的随意粘贴,构成了星丛式小说的外在结构。因为,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人学,是人类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以文本的方式的一种表现。
星丛式小说诞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之前遥不可及的事物随时都能展现在眼前,神秘感和距离的消失让人类轻而易举地就能认识世界,了解各类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世界呈现出万花筒般的丰富多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认识到了世界的多样复杂性和多元变化性。而作为世界表现物的小说,也要顺应这种时代突变,以更加丰富多元的方式来建构小说,星丛式小说正是这一新的时代话语的产物。
三、星丛式小说的深层结构
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否则就无法连成一体。星丛式小说也不例外,它的外形虽然混乱无序,但其内里却有其特殊的严整性。托卡尔丘克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最后一篇和第一篇中有意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构思意图。在最后一篇《从天空预测》中,人物R喜欢观察天空的色彩,于是在阳台上架起三角架,将镜头瞄准天空,每天都拍一张照片,从春天一直拍摄到秋天。最后他会把所有的照片堆放在一起,像做拼图游戏一样随意拼接,用照片拼凑出一个天空。这时候就会知道天空究竟是个什么样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摄像头固定的拍摄位置,就如同展现舞台活动的布景,而从春天一直拍摄到秋天再拼凑天空的做法,意指对观察对象不是采用单一固定的角度,而是流动变化,不断生成的角度。而在第一篇《梦》中,开篇第一句话是:“我梦见我是纯粹的看。我站在固定的谷地上方……从那里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切。”[9]1这样,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说要用摄像头拍摄天空每日云彩的变化,开篇则像照相机一样的固定在谷地上方“纯粹的看”,首尾呼应。同时,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还借人物帕斯哈里斯的口吻表达了类似的意图:“他认定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使所有可能的时间、所有的地点和景物并存于一幅画中。”[9]165这种构思意图和前文提出的星丛式小说结构的探索思路和实现可能性恰好一致。在写作实践中,星丛式小说的内在整一性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的。
(一)星丛式小说设置了集中的活动布景
众所周知,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在传统小说中,环境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舞台,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对环境设置最为重视,提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写作要求。但传统小说重视环境描写是为了塑造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是在内容层面的辅助性要求,属于从属地位。而托卡尔丘克的星丛式小说也特别重视对空间环境的构筑,并赋予它中流砥柱的作用,让环境成为全文谋篇布局的核心枢纽。作为一种多元异质共存的小说,星丛式小说必须拥有异质共处的同一场景空间,否则整部小说就真的成了一盘散沙。托卡尔丘克曾明确表达过对小说结构空间化追求的理念:空间里存在着各种看不见的形状、式样,各种基本秩序和规律性[2],这就显示出结构化的“星丛”是一种并置的、共存的网络,类似于天空中万千星球的排列次序,它们同处一片天空却又各自独立运行,泾渭分明。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就以新鲁达这一地理空间为活动布景,让人、鬼、神、动物、植物、物体等万千景象共存于同一空间。小说中,作为承载万物共生空间的新鲁达是一座历经沧桑的城市,它的名字随着统治者的不同几经变更。在《新鲁达》这一单元里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是一座多梦的城市,是一座市区和郊区难分的城市,是一座放任时间自流的城市,是一座没有任何新东西的城市。这个几乎被放置在结尾的单元,其实恰恰是整部小说内容的总结,也是小说安排星丛式叙事结构框架的蓝本。整部小说中多元复杂的众生像就是在此空间范围内展开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城市,新鲁达经历了多个国家的统治。因而,这个城市有德文名字、波兰文名字、捷克文名字,也是德国人的故乡、是捷克人的故乡、是波兰人的故乡。人是有经历和故事的,因此托卡尔丘克写了在这里生活过的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的故事。小说围绕这座小城,书写这里的缔造者刀具匠人的故事,中世纪骑士时代库梅尔尼斯的故事、帕斯哈里斯的故事,封建社会时期封戈埃特岑伯爵家族的故事,以及像克雷霞、马雷克、迪泰尔等现代人的故事。在同一片红色的土地上,人类世代繁衍生息,就像封戈埃特岑家族一样,以相似的面孔和相似的生活方式,错时生活在自己的府第里。各时期的不同人物就像电影画面式的流动,出场片刻,转瞬即逝,只留下一个个片断。
总之,托卡尔丘克以极大的热情抒写了新鲁达及周边村落皮耶特诺的人、黑森林、谷地、溪流、蘑菇以及芦荟,大家都前赴后继,生生不息,一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
(二)星丛式小说设置了功能性的核心人物
星丛式小说具有内在关联性,万物共生互连,因而小说需要这种功能性的连接点。《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玛尔塔这一核心人物作为各种人事景物的相互关联点。玛尔塔是个神秘的人物,每年冬天都会像动物一样在太阳照不到皮耶特诺的时候冬眠,在苏醒的日子里她基本不睡眠。她长年穿着一件纽扣洞被抻大了的灰色毛衣。小说中提到的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出现的鬼魂、神话、传说,几乎跟玛尔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是小说各种人物产生交集的纽带,是主要人物马雷克·马雷克、如此这般、博博尔父子、埃戈·苏姆、克雷霞、弗兰茨·弗罗斯特以及女主人公“我”的邻居,也是新鲁达城里外号叫“狮子”的占卜师的旧相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鲁达,是这里一切人事景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关心一切,通晓一切。她知道“我”和R居住的房子是德国人盖的。她指引“我”注意教堂库梅尔尼斯的画像,她引导“我”追问“是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她知道各种动、植物名称,吃过所有的蘑菇却毒不死。她也是各种神奇现象的解释者,她说“如此这般”能看见马雷克的鬼魂是因为他看不到真正的自己,她说在黑森林的洞穴里住着远古的瞎眼的远古生物——不死的白色蜥蜴,她说上帝在造物时忘记了造一种夜里坐在十字路口动作迟缓的大动物。女主人公“我”梦见玛尔塔“背上长出一对膜状翅膀”,足可见其通晓万物的神秘之处。
因此,玛尔塔在整部小说中起着犹如定海神针的作用,文中几次写到玛尔塔家厨房不可思议的整洁程度,意在寓言:只要有玛尔塔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会整整齐齐地、有条不紊地摆放在相应的位置上。这也恰好是这部作品星丛式结构的内在连接线,玛尔塔就是一架流动的“摄影机”,她见证和记忆了所有的一切,也连接了一切。
(三)星丛式小说在内容的相似性基础上串联各种不同的事件
本雅明指出:“正是相似性让人与事物建立起一种原初而又自然的存在关系。世界以星丛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相似性表征。”[10]而托卡尔丘克也曾直言:宇宙万物在宏观与微观的尺度下显示出无穷的系统相似性[2]。星丛式小说正是这样,通过事件性质的相似性将众人的碎片化故事融为一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讲述的关于弗拉茨·弗罗斯特、苏戈·埃姆、他和她等人的生活片段故事,这些事件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悲剧是有相似性的,是战争的阴霾让这些人焦虑恐惧,痛不欲生。如战前的弗拉茨·弗罗斯特在儿子刚出生的那天就不祥地梦见:他的妻子用大大的平底锅炒有毒的红色毒蝇菌并给孩子吃,孩子被毒死了,他非常悲痛地把它埋在了苹果树下。这个可怕的梦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使他心烦意乱,神情恍惚。他因此焦虑不安,后来战争爆发了,他也被打死了,而那个可怕的梦也变成了现实,他的妻子果然误把毒蝇菌喂给孩子吃而导致孩子被毒死。而苏戈·埃姆的悲剧根源也是因为战争,埃戈·苏姆因被俘而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不幸遭遇罕见大雪,同行五人被搁置在荒野小站,在即将饿死的时候吃了一个冻死的同伴的尸体和内脏,后来侥幸活命,辗转来到新鲁达,在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生活还算安稳。但几年后他读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句话:凡是尝过人的内脏的人一定会变成狼[9]266,埃戈·苏姆的噩梦就此展开,时常害怕自己会变成狼,并产生幻觉,痛苦不堪,最后来到皮耶特诺乡村给小博博尔当免费长工,改名换姓,通过艰苦的劳动和献大量的血而获得了短暂的内心平静。小说中同他俩一样饱受战争之苦的还有《他和她》里原本相亲相爱的一对年轻夫妻,由于接待了来自集中营的莉莉姐妹,之后的生活就变得异常古怪,夫妻俩各自爱上了一个好似双性同体的名叫阿格尼的情人,阿格尼忽男忽女,行踪诡异,他们总是适时出现在夫妻短暂分离的空档里,分别和夫妻俩错时恋爱生活,犹如梦幻一样,后来他又突然神秘失踪,致使夫妻俩各怀心事,此后在思念各自的阿格尼的煎熬中度过了余生。以上人物的痛苦经历看似各不相关,但使他们痛苦的原因却是相同的,是战争给他们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正是这种原因的相似性让不同的故事有了内在连接,成了有机的整体。
与此同时,托卡尔丘克还将事件中出现的意象的相似性作为连接整体的纽带。如苏戈·埃姆梦见自己变成了狼,而另一篇《大麻做的糕点》中,那个把彼得·迪泰尔的尸体挪到捷克那一边的边防士兵最后在小博博尔家附近离奇地被狼吃了,但这个边防士兵一生只在动物园里见过狼。这就让两个独立事件有了因果联系。同理,在紧随其后的《网络中的梦》这一单元中,不知名的人梦见自己死了,而梦见的内容又跟边防士兵临死前的遭遇无比相似。由此可见,正是这种意象的相似性让这些不同的事件连接在一起,让小说以实幻不分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各个人物的客观生活遭遇和主观精神世界,这些人物虽身处不同境遇和时代,但现实身份和梦的内容却互相缠绕,彼此关联,使整篇小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之,托卡尔丘克的星丛式小说就是通过如上结构安排方式,展现了多元复杂的碎片化的世界图景,让小说跨越了时间界限、物种界限,将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人类与万物有机熔为一炉,让多重现实共存一处成为可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星丛式小说的结构形式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方面,其表层结构形式通过目录的缺失和各单元内容的独立自由使小说失去了文本秩序,又打乱了小说的线形连接线索,消解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及多维视点等多种方法,使得整部小说多元混杂又晦涩难懂,仿佛进入迷宫一样。其深层结构则是通过设立集中的场景、功能性的人物及相似性的内容等方式来让整部小说成为逻辑严密、充满内聚力的有机整体,通过表层结构形式和深层结构形式的双重配合,使得星丛式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具有了无以伦比的包容力。
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有效扩大了小说文体的表现范围,实现了小说文本承载内容的最大化,内涵意义的丰富化。这种小说形式顺应了当代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迎合了当代人的阅读趣味,使小说这一文体再次焕发新生。由于当代人随时随地都置身于网络环境,遭受各种信息技术的挤压,让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尤其是小说面临绝境,托卡尔丘克对此认识得相当清楚:“大多数人从来都不读书。文学一直都是精英们的功课。文学的参与者在人口中总是比例很小。”[11]信息科技的进步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面对新的时代命题,托卡尔丘克在自己的小说中自觉触及了一个近年来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话题,我们该如何叙述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托卡尔丘克大胆尝试使用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流动变化的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语言文字的魅力,进一步扩大了小说文体表现的范围,让小说文体通过不断地转换写作方式去应对危机,以便绝处逢生,这也是托卡尔丘克有关小说理论和实践的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
正是凭借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的巨大包容力,《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神奇地将神话、历史、童话、民间传说熔于一炉,把现实、魔幻及怪诞糅合为一体,展现了多重时代与多个人物的故事。与此同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同样实现了多元杂糅,《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将随笔、叙事体、自传体、史诗风格及议论文体等多种文体杂交,将讽刺、象征、隐喻等传统手法与互文、拼贴、元叙事等后现代艺术手法恰到好处地转换,由此形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多元开放的世界,让读者可以酣畅淋漓地亲历一场奇妙变换的精神漫游。
总之,《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星丛式小说,它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此小说的成功从形式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即星丛式结构形式,也说明了新的小说结构方式的诞生和被读者认可,为当代小说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可供借鉴的实例。因此,星丛式小说也已成为西方最受欢迎、最前卫的小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