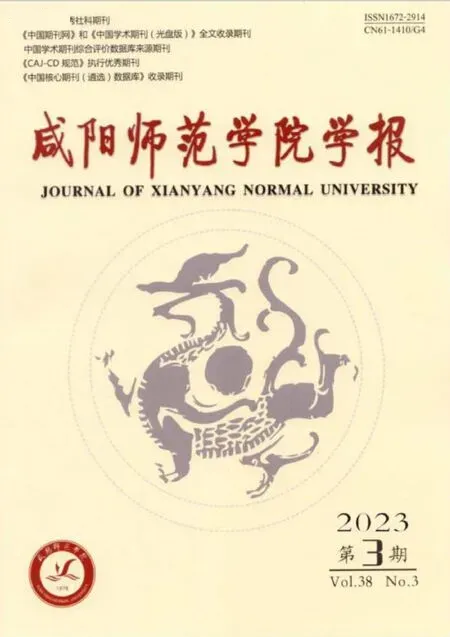自由与束缚:街头空间规划中的文化逻辑
王 姮
(天津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天津 300141)
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街头文化”的指称较为明确,往往指的是与底层民众自发的娱乐活动相关的文化行为。然而,对其中“街头”的界定,似乎并不十分明确。相较而言,“街道”通常指两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街头”一词的出现则往往伴随着“文化”“政治”“空间”等概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表征。街头更像是“地理位置和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空间,与其说它指的是一个个具体地理位置,毋宁说它指向的是一种特定生活方式里的‘空间观念’或‘位置感’”[1]。由此出发,从作为实地的街头、小说中的街头、电影中的街头出发,可以看出空间规划所形成的别样生活经验,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一 街头概念的厘清
街头,不仅仅指街道,也包括胡同里弄、茶馆酒肆、地坛庙会等场所,“街头作为公共空间,是民间文化发生、汇聚和表达的‘场所’”[2]。因此,街头文化指发生在传统民间、地方政治城市街头出现的各种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的谋生手段,甚至是街头权力的争夺。此外,街头文化又指可以在街头展现的任何艺术形式,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从欧美地区流行开来的街头时尚,如街头音乐、街头舞蹈、滑板族、滑旱冰,以及随之出现的街头服饰、涂鸦等。此种街头文化迅速兴起,并逐渐代替“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街头文化”内涵,以打破传统、造型夸张、张扬个性的特点迅速获得年轻人喜爱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我们无法对“街头”进行清楚的限定,使其成为界限分明的地理空间,但是对它的定义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层面:(1)街头一词通常指城市或城镇生活中不同建筑物之间的夹道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室外空间,以区别于个人生活场所。(2)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街头一方面履行着公共空间的职责,为进入其中的人们提供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另一方面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摒弃了室内或室外空间的规约性,将市民的流动囊括其中,这就使得街头成为可以考察公共空间、民众生活、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关系的开放性空间。
在对街头景观的考察中,许多学者从“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式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3]3入手,借助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的方式,梳理了某一特定地区街头文化的变迁,以及形成这些变化的各种政治力量作用。可见,街头空间可以成为考察政治权力变迁和时代变化的窗口,街头的含义也远远超出具体的位置和空间限制,而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上。
二 中国现代街头的诞生:以天津五大道为例
在传统社会,街头主要指的是建筑物之间的通道,为底层民众自由开展公共生活提供公共空间,某些街头成为“江湖艺人、杂耍、卖打药、诈骗术士等的聚集地,也成为下层民众的娱乐中心”[3]55。工业文明之后,伴随着城市街头的有序规划,街头则成为彰显工业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张力的特殊空间:通过对人行道、车行道、绿化带的严格区分,人们可以按照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彰显了对工业文明的倾慕和改造自然的雄心。以天津五大道为例,可以一览现代工业文明对城市街头的规划与改造。
如果说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的改造是伴随着国家内部政权更迭来逐渐完成的,那么天津的城市规划则伴随着老旧封建国家衰落的血泪而被卷入现代文明浪潮的。天津可谓是近代中国的缩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天津被迫成为通商口岸。1860年,大沽失陷,英法联军占领天津,自此,租界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城市的规划和使用不再属于本国当权者或底层民众,而成为西方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强行实践“文明化”的一种方式。今天的解放北路,昔日的中街,这条宽阔的中央大道与其他纵横交错的街道将英法租界划分为35块建筑用地。这种城市规划理念完全来自欧洲,与天津老城区四四方方的格局完全不同。具体看来,五大道的生成是现代技术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强行规划的产物。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负责当时整个英租界的规划,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街道上做标记,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1890年,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租界工部局斥资32 000 两白银,建造起租界区通商口岸的第一座市政大厅——“戈登堂”,城堡式的尖顶耸立云霄,带有了鲜明的西式建筑特色。自此,强有力的城市规划手段为更好地改造城市空间带来了实践创新:功能区的划分,使得住宅、商业、工业区分隔开来,既能有效地保护租界用地的安全,又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实现高效配置和产能优化。
土地划块,通过拍卖来获取收益。为了把有限的土地卖出更高的价格,租界地规划者开始注意街道的规整和街边绿化,水泥、鹅卵石等混合材料将原来的沙土路铺平,方便行走。同时,由于租界区的划分无法忽视毗邻的他国租界,交界处的道路衔接便有了偏差。设计师将墙面设计成弧形,道路也随之弯曲,一改传统中国城市中横平竖直的道路建构。弧形道路设计方便了车轮转动,便捷的交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街道的沟通功能大大增强。
租界地新型建筑的外观、颜色、样式逐渐增多,精巧的外观与老城区低矮的旧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人们观看的欲望。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定”[4]361。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城市景象。
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说,天津是晚清中国奋发图强、日益进取的代表,也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改革的中心。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短短40 年间,天津这座城市出现了九国租界,共占地22 600 多亩,比天津老县城的面积还要大八倍。与中国大连、台湾等地区单一的一国殖民不同,天津当时的殖民活动“涉及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微妙关系”[5]2。直到20 世纪20 年代,直皖、直奉军阀战争中,双方所使用的武器也多是从德国、日本、英国购来,在天津租界里成交[6]。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频繁的对外商贸在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打开了观望世界的窗口。教育、文化、社会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亦开始影响天津的社会生活。天津的特殊性,更加彰显了街头之于城市的特殊意义。可以说,通过综合性的技术改进手段,街头蕴含了城市文明所携带的超越人类生存空间限制的欲望。如果说这种自由发展的欲望在工业文明发挥作用之初是通过掠夺和改造的方式来实现的,那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超越开始以街头观看模式的转变来实现。
五大道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街头的诞生方式。一方面,它既有长久以来民众生活方式的凝结,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也彰显出现代街头的建构就像是一个边做边修改规则并最终成型的游戏。正如有学者所言,“巨大的城市机器,正是因为街道而变成了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活力和生命的有机体……城市借助于街道,既展开了它的理性逻辑,也展开了它的神秘想象”。[7]由此,人在街头的观看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在街道上既表达它清晰的世俗生活,也表达它暧昧的时尚生活。”[7]
三 街头观看模式的改变:以小说中的街头形象为例
古代社会中,街道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中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而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市民阶层日常生活、交通、刑法、庆典活动的展开场所,如布罗代尔所说,“小街小巷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即使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遗留的物质文明仍诉说着过去”[8]。由此,街头可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之地。
(一)鲁迅《示众》中的街头(1925)
1925 年,鲁迅在小说《示众》中描写了中国传统农村的旧式街景:“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9]206文中“首善之区”是虚构之地,且带有鲜明的反讽意味,这片街头被笼罩在一片炽热憋闷之中,潮湿闷热的空间环境隐喻着20世纪初新旧交替之时整个社会令人难以喘息的生存境况。就小说本体来看,它最大限度地淡化了传统叙事中以时间流程和因果逻辑推动情节发展的模式,以不同人物的行为片段在空间关系上的连缀和并置为主要推动力,使得叙事空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将小说放入具体的时代语境中可以看出,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的街头,视觉模式主要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看/被看”的模式,每个人既是“看”的主体,又是“被看”的客体。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针对街头人群“看”的模式进行反思,不断质询着“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看”“谁让我们这样看”等问题,试着找出掌控这一行为的主导力量,审视那些我们自古以来便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些甚至深入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规训的层面。街头观察者的视线由人转移到人们生活其中的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及现实社会现状中,关注点的变化引发了新的思考。
(二)刘呐鸥《都市风景线》中的街头(1930)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集中之地,街头成为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都试图争夺的空间。传统城市的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逐渐被更加现代化的城市面貌所取代,从高楼林立到广场辉煌,从商场、酒楼到超大银幕广告牌,白天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灯红酒绿。朴素的社区社会在遭遇了现代街头文化的冲击之后,很快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1930年,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在小说《都市风景线》中描写了作为大都市的上海街头:“近处一条灯光辉煌的街道,像一条大动脉一样,贯串着这大都市的中央,无限地直伸上那黑暗的空中去……那面交错的光线里所照出来的一簇蚂蚁似的生物,大约是刚从戏园滚出来的人们吧!”[10]12-13他从都市的建筑、交通、灯光、服饰等电光声色的直观文化层面入手,表现都市的力量、速度、声音与色彩。在这里,现代都市街头不再是人物展开活动的背景,更成为隐含着能动力量的客体。街道仿佛成为城市这头巨兽身上跳动的脉搏,在明明灭灭的光线中悄然蠕动,蕴含着令人难以琢磨的神秘力量。相比之下,人们像蚂蚁一样“滚出”,渺小的肉身被放置于充斥着现代技术的城市中,一种危险又迷人的街头体验便油然而生。
生机勃勃的街头既是繁华的象征,也是这繁华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城市成为“按照人的盲目欲望而建造的怪物;而且这种怪物越来越膨胀。它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和不可思议,因而不能不给人带来一种内心的惊恐与焦虑”[11]68。不断带来新鲜感和震惊体验的城市街头,不仅仅是沟通一系列新型建筑的道路集合,也超越了旧时街边琳琅散乱的简单交易活动,它引诱着无数居民从家中走出,在街上观看、享受新生活。传统的“看/被看”模式在新型的街头空间又一次发生变化:在旧式街头,因为街边的风景枯燥无味,人成为看的对象,每个人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看,同时也向四面八方投射出自己的视线,由此,人的行为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日渐发达的城市,不仅出现了辉煌的建筑,也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开放的街头公共空间,置身其中的人将视线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物的身上,人群成为蝼蚁一般的存在,不再是观看的中心,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新月异的街景所带来的波澜起伏的体验。
(三)木心《街头三女人》中的街头(1983)
街头观看模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体验,也构成了新型文化想象的基础。街头游荡漫步者以艺术化的方式寄托着自身的浪漫想象,行色匆匆、被卷入资本生产链的人将街头视作通往名利双收金殿堂之路。然而,当地点的沟通不承担实际需求的时候,关于街头的种种自由式的文化想象才会真正得以激活。这种文化想象往往并不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而是更多地接受着艺术作品的文化暗示。
就其位置绘图来看,街头原初的功能定位为个体空间与群体空间的通道,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意义的空白便为文学艺术的萌发提供了空间,激发着创作主体的无限想象。1983年,木心在《街头三女人》中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充斥着各种消费符号的外国城市街景:“据说第二次大战后,像纽约这样的都市,根本不见沿路设摊或推车叫卖的人。近几年却到处有撑起篷伞卖三明治、热狗的,有摆摊子卖T恤、裙、裤、腰带的,更有卖陶瓶、瓷盘、耳朵上脖子上的装饰品、现榨的橘子汁、当场刻的木雕、手绘的衬衫。花生米、榛子、腰果、核桃仁,都上了人行道。”[12]47读者的视觉跟随叙述者的讲述从各色日常物品中滑过,整个街景也随之成为故事的讲述背景,形成全景式的观照。置身其中的人(“我”)隐藏在物品和人群中,可以自由移动自己的视线和脚步,选择想看的人、想接的物,现实生活境况和历史时代语境被抛掷其后,脱离一切束缚的主体能动性便油然而生。
在文学家笔下,街头成为观照城市变迁的窗口,带有了展现时代特色的写实特征。如果说文学作品中的街头形象带有的是表征人在特殊时代变化中的思维方式变更,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那么电影中的街头景象则从全景式记录的角度,借助于灯红酒绿、琳琅满目的街景完美地呈现发展的盛景,为身处其中的人们编织着美好生活的愿景。
四 自由神话的塑造:以电影中的街头形象为例
街头漫步者以浪漫主义想象满足于街道对自由的塑造,而工薪阶层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快节奏、高效率方式建构这自由的幻境,在行色匆匆中得到一种身份的认同。2006 年美国导演大卫·弗兰科尔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多次出现街景,手里拎满大包小包的职业女性踩着高跟鞋,在充斥着汽笛声、叫卖声、电话声的纷乱街头健步如飞。我们很难看到女白领从通过一条完整的街道,从一个场所过渡到另外一个场所的完整性图景,恰恰相反,精致而破碎的街景为整个街头增添了一种超凡的力量,仿佛唯有步履稳健地通过它,姿色平庸、能力普通的小职员才可以被纳入“英雄叙事”的框架之中。街头仿佛成为重生的宣告,从踏上它的那一刻开始便寓意着告别过往,崭新的人生道路就此打开,自由、自信的新女性便可以站立其中。
在这里,街头成为一种实现生活理想化的空间媒介,它以自然的开放状态将人群纳入其中,仿佛可以召唤出强烈主体意识,将人们内心深处封闭着的、被世俗生活禁锢着的自我释放出来。走上街头意味着对平淡生活、平庸人生的反抗,意味着自我内心深处欲望与潜力的主动释放。由此,自我便不再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者,而成为有勇气超越自我、实现梦想的“超我”。一边是在颇具浪漫情思的散文、歌词中书写的身外物无的生命体验,一边则是各大银幕所展现的灯红酒绿、光影流转的发达资本现状,无论方式如何,街头都被看作一个可以达成愿望的理想空间。在与街头有关的文化想象中总是连接着追逐自由、超越自我等意义,走上街头意味着从自我空间脱离出来,告别舒适安逸的庸常生活,投入更加广阔的社会怀抱,以掌控更加丰富的人生。
可以说,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自由的品质乃是街头空间的主要文化想象。电影中的街头由直线、直角和斜向辐散的数条小路组成,连接着不同的街道、桥梁、广场、商场,以放射状的姿态对人群完全敞开。面对这样一种城市姿态,人们不再是随意走过,而是有目的地前去寻找乐趣。快速行走的人群和游客,其步调也和城市的步调一致,倾听着街道和城市的脉搏,观看着城市物质和文化的积累,对城市的未来也怀有更高的期待。街头成为步履匆匆的城市的象征性存在,不再是联通城市建筑、科技、文化、奢侈品的纽带,更寄托着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中,人们可以共享土地、共享城市功能、地位平等地共享财富,创造更加完美的城市的心愿。
然而,自由状态的开启往往与城市空间的遮蔽性相勾连。当街头以开放姿态提供便利的同时,它也在暗处对人进行区隔和分类。与诸如商场、公园等城市符号一样,街头因其功能性而保有颇具亲和力的一面,同时也毫不客气地在物质层面彰显不同的身份特质。发达的商业区背后不乏贫困简陋的街道,繁华的地方往往犯罪率也较高。街区标识着大部分居住者的经济能力,还暗示居住者的社会身份,却又在无形中忽视了一部分人的存在。换句话说,在街头激活的自由想象中,只有那些掌控城市发展前景的人才能够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机会,这无疑暗含着对于空间占有的崇拜。而街头则成为一个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社会中的典型象征,其文化想象深植于当代资本社会的话语体系中。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街头所激活的对自由的文化想象,反映了在资本至上观念主宰下,人的主体意义日益匮乏的趋势。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占用空间,通过空间的高效率使用获得利益,进而继续进行空间的争夺和使用,在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日常庸俗的生活经验麻痹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地位,人作为“人”的能动意义被遮蔽,代之而起的则是持续的占有空间、抽离意义、再赋予意义的机械的生产过程,人的价值无法直接实现,而不得不借助于其他客体。在此过程中的焦虑、疲惫、怀疑,则可以通过身体的自由移动来弥补,人们在街头行走、观看、体验、忙碌,所有的过程都指向一个目的,即如何为被剥夺了主体意识赋予新的、看似自由而美好的经验和意义。
对于身陷于街头自由愿望之下的普通个体而言,自由的神话带有吊诡的色彩。一边是试图超越固定空间束缚的美好愿望,另一边则是愿望背后隐含的空间占有合法性辩护,隐含着对资本权力的崇拜,即只有通过占有城市空间,包括占有固定商业区、住宅区、公共场所和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街头,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自由,获得主体身份的指认,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一种自由的神话便显得充满悖论:一方面是企图超越现实社会固定空间的幻想,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自由幻境中隐含着对空间占有的崇拜,由此,街头空间所携带的自由想象也就成为当代主体生存境遇的一种症候式寓言。
五 结语
通过分析可知,现代城市街头的规划从一开始便是占据话语主导权的阶层自上而下的制造行为,始终指向进步的、与现代城市所相关的内容。然而,在实际的使用中,街头空间却带有了鲜明的多义性。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看客,还是刘呐鸥体验到的震惊,抑或是木心观察到的琳琅满目,人们的不同体验共同表征了在时间的长河中城市生活经验的真实性存在。电影中的街头则更加带有强烈的戏剧性,仿佛早已背离了设计者制造一个现代城市的简单初衷,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了更多寻找和幻想生活意义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街头所带有的交流性色彩,展现出柄谷行人意义上建筑空间的本质,即并不仅仅提供公共空间本身,更提供了一种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13]10,这也正是街头空间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