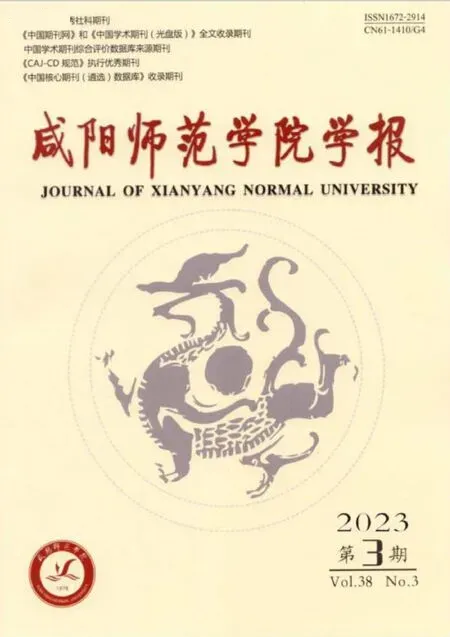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梁玉田,李红岩
(西安工业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礼书》与《乐书》是《史记》八书的第一、二篇,重要性不言而喻。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1]3304-3305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作《礼书》的目的是表述“礼”近人情、通王道,顺应古今之变;作《乐书》的目的是讲述“乐”的兴衰。观今存的《礼书》和《乐书》,《礼书》在主要论述“礼”的基本原则、《乐书》在系统介绍了音乐的基本理论的同时,还对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层阐释。由此观之,今存《礼书》《乐书》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原意。为此,众学者对两书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但仍存在争议。本文在梳理学界对《礼书》《乐书》来源相关看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认为司马迁在世时创作的《礼书》《乐书》全本已经消亡;现存两书的篇前序文是司马迁原文之序;两书佚失后,后世某位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佚名者,根据残存的序文以及司马迁经手的文献补写了《礼》《乐》两书,使得《礼书》《乐书》以成书的方式留存至今。
一 关于《礼书》《乐书》来源的三种观点
(一)认为《礼书》《乐书》有录无书,对补书人的问题并未高度关注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史记》中有十篇早已无书,只存其录,他们将关注点主要放在《礼书》与《乐书》是否处于“有录无书”的十篇之列,对现存文本的补作者并未作更深入的探讨。最早提出“有录无书”观点的是东汉的班彪,“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2]1325,其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3]2723-2724而对于缺失的十篇,班彪父子并没有详细说明。唐人颜师古引用了三国时人张晏的说法,他在《汉书》中注解道:“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3]2724可见,张晏认为“有录无书”的十篇中就包括《礼书》和《乐书》。随后张晏提出其中三篇是褚少孙补作,但并没有说明是何人补作了《礼书》与《乐书》。张晏列举的《史记》亡佚十篇的篇目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南朝宋人裴骃所著《史记集解》以及唐代司马贞所著《史记索引》都有对张晏观点的引述。南宋陈振孙认为十篇全亡,其《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曰:“而其余六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誊荀子《礼论》、河间王《乐记》,《傅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4]96陈振孙认为《礼书》《乐书》是后人誊抄的,但对于补作者并未提及。近人崔适在其《史记探源·序证·补缺》中更是鲜明地指出“八书皆赝鼎”[5]18。支持张晏说的还有余嘉锡,他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说:“凡考古书,当征之前人之书,不可臆见说也,《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著于《七略》,载于本传,而张晏复胪举其篇目,其事至为明白,无可疑者。”[6]6梁启超也认同此观点,认为《史记》所缺的十篇全是经后人之手编造出来的,他在《新学伪经考》中列举了班彪、张晏的注解,并指出所缺的十篇“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7]261。这些学者大部分都只关注《史记》亡佚的十篇是哪十篇,至于《礼书》与《乐书》是否属于“有录无书”之列,两书出自何人之手,又是何人将其引入《史记》之中等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
(二)认为《礼书》《乐书》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所补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礼书》和《乐书》的序文都出自司马迁原笔,而序文之后的内容为后人补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写道:“史公《礼书》惟存一序,此下皆后人因其缺而取《荀子》续之。”[8]757梁玉绳认为,“礼由人起”之前的文字是司马迁原文之序,余下的内容是后人所补。孙同元《史记阙篇补篇考》认为:“盖十篇中《景纪》《兵书》《傅靳传》三篇全具,并无阙文;《礼书》《乐书》《将相表》《龟策传》四篇,其上半篇尚仍史公之旧。”[9]254孙同元的结论是根据司马迁的行文风格得出的,“《乐书》自‘太史公曰’至‘当族’,文笔古雅,且其中并有‘今上即位’之文,其为史公原文无疑”[9]111-112。张大可的观点与孙同元相似,他在《〈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中写道:“《礼书》《乐书》篇前之序有‘太史公曰’,当是补亡者搜求的史公遗文,可以说这两篇是书亡序存。”[10]而后张大可指出,《乐书》序文中以“世多有,故不论”作为段落的结尾,正是司马迁的笔法。
对于后世何人补作《礼》《乐》两书,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两书皆为褚少孙所补。此观点主要受到张晏观点的影响。张晏最早提出褚少孙对《史记》进行了补写,“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1]3321。虽然张晏并没有说清楚《礼书》和《乐书》是否也为褚少孙所补,但后世诸学者仍以张晏的见解为依据,认为其他所缺篇章也是褚少孙所补。唐人张守节认为包括《礼书》《乐书》在内的《史记》所缺十篇都是褚少孙所补,其注解《礼书》道:“此书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1]1174清代史学家赵翼与张守节的看法相同:“《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11]7。明代杨慎在《史记题评》中写道“褚先生升降之也”[12]12,认为《乐书》从正文到篇末都是褚少孙取《乐记》之文有所“升降”而成。钟惺认为《礼书》《乐书》等篇“所称‘太史公曰’云云,多褚先生辈以意假托,肤窘牵率,试取后四书读之,真伪自见。《礼》取荀卿,《乐》取《乐记》,尤属无谓,断宜去之”[13]881。
二是认为《礼书》和《乐书》乃是后世不知名的好事者所作。清人梁玉绳认为,《乐书》全篇皆是后人所补,“附案:《乐书》全缺,此乃后人所补,托之太史公也”[8]758。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对《礼书》有考证:“愚按‘礼由人起’以下,后人妄增,但未可必定为褚少孙。”[14]1612对《乐书》论云:“‘凡音之起’以下后人取《礼记·乐记》《韩非子·十过》等书妄增。”[14]1616
(三)认为《礼书》《乐书》皆是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礼书》和《乐书》是司马迁还没来得及写完的文章。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唐代刘知幾,他认为:“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15]377刘知幾所认为的“有录而已”与班固注解的“有录无书”有所不同,刘知幾强调的是《史记》亡佚十篇是司马迁还没有写完的,司马迁只写了名录或是只写了序文而已,而不是成书之后才亡佚的。清代郭嵩焘《史记札记》载:“按《礼书》前叙啴缓无节奏,而其意美矣,疑太史公草创之文,未据以为定本也。其取荀子《礼论》以为《礼书》,《乐论》以为《乐书》,盖谓三代典礼无可征,惟能征其义而已;秦、汉以下并其义失之,不足与于礼乐之事也,是以阙而不书。史公于此,有深意焉,其文则不免于疏率矣,故知非史公之完书也;以为褚少孙补,则非也。”[16]120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首先引用了杨慎“褚少孙补明矣”的说法,接着进行了反驳,指出杨慎以及杨慎所引用的《索隐》与《正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礼书》与《乐书》皆是司马迁草创之文。司马迁参考荀子《礼论》以及《乐论》来编写《礼书》与《乐书》自有其深意,但是司马迁没来得及完成两书并且修缮之,因此才使得《礼书》与《乐书》显得如此粗略草率。
二 《礼书》《乐书》来源考辨
(一)两书皆是书亡序存
最早关注到《礼书》序文的是梁玉绳,他认为:“史公《礼书》惟存一序,此下皆后人因其缺而取《荀子》续之。”[8]757但对于《乐书》,梁玉绳却认为:“《乐书》全缺,此乃后人所补,托之太史公也。”[8]758观现存的《礼书》与《乐书》,不难发现,两书的情况十分相似,皆为“十篇有录无书”之列,也同样为誊抄古书拼凑而成。梁玉绳称《礼书》存序而《乐书》全佚,且没有具体解释,不免有前后矛盾之隙。笔者认为,《礼书》与《乐书》的序文皆为司马迁原笔。
首先,《礼书》与《乐书》原应为全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3319能够写出具体的篇数与字数,表明司马迁当时已经完成了《史记》全书,若非全本,司马迁为何要统计出具体的字数并记载下来?另外,《汉书·司马迁传》也有对《史记》篇数与字数的记录,说明司马迁在自序中记录的篇数与字数为班固所认可,也由此证明了其数据具有很大的真实性。由此看来,包括《礼书》与《乐书》在内的《史记》一百三十篇文章,司马迁在世时应当已经全部完成。
其次,序文的内容与笔法符合司马迁的文风以及作文原意。笔者认为,在《礼书》中,序文应是从开头的“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至“垂之于后云”,其后皆是誊抄的内容。观其序文,先是太史公发表自己对“礼”的见解,然后自周代开始,“自子夏”“至秦”“至于高祖”“孝文即位”“孝景时”,到“今上即位”,论述各代的礼制变化,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的作书目的相符合。在《乐书》中,序文的范围应是从开头的“太史公曰”至“世多有,故不论”,“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一段经多位学者考证,存在年代窜乱的情况,应当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从“凡音之起”始皆为誊抄的内容。细观《乐书》之序文,其笔法及结构其实与《礼书》相同:先是太史公发表自己对“乐”的见解,然后自郑卫之音开始,到秦二世,到高祖等,最后“至今上即位”,论述古今音乐的变化,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所写的“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的描述相符,也与“比《乐书》以述来古”的作书目的相符。汪继培《史记阙篇补篇考》曰:“《礼书》《乐书》《龟策列传》皆有‘今上即位’之文,使非出自迁手,何以并年岁而袭之?”[17]255-256结合两书序文之中的关键字词,以及古朴文雅的文风与一气呵成的文笔,我们认为《礼书》与《乐书》的序是司马迁之原文。
最后,《礼书》与《乐书》除序文之外的内容确已亡佚。《汉书·艺文志》曰:“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注:“十篇有录无书。”[3]1714《汉书·司马迁传》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3]2724但是这里并没有注明亡佚的篇目与时间等其他信息。值得思考的是,班固父子所称的“有录无书”,其“录”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注“有录无书”的只有两处,同在春秋类著录中,其中一处是对“太史公百三十篇”的注解,另一处是对“夹氏传十一卷”的注解。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云:“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18]20“目录”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叙传》中,“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3]4244。《艺文志》载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1701。余嘉锡认为:“旨意,即谓叙中所言一书之大意,故必有目有叙乃得谓之录。录既兼包叙目,则举录可以该目。”[18]20因此,刘向时所称的“录”应该是“书录”,也就是刘向对其所整理书籍相关内容的记录与抄录,可能是书籍的主要内容或是能概括文章旨意的篇前序文。等到刘向去世之后,刘歆子承父业,“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方技略》”,其《七略》应当是在继承刘向对书籍“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整理方式的基础上“记录、抄录群书书名而成的‘目录’”。刘向《别录》重在为每一书籍撰写叙录,刘歆《七略》则聚焦于分类,因此,刘歆的《七略》是在刘向“书录”的基础上整理的“目录”。
再至班固,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3]1701,删除了《七略》中每一书的“指要”,仅留下“记录、抄录群书书名而成的‘目录’”。基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班固所注的“录”应当是指刘歆《七略》的“目录”。但是刘歆整理的“目录”是由刘向整理的“书录”而来,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称的“有录无书”表面上是指刘歆的“目录”,实际上指的是刘向的“书录”。如“夹氏传十一卷”中班固注云“有录无书”中的“录”只能指刘向“书录”,而不是“书录”中的篇名部分,因为二刘著录的时候此书是存在的,据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隋志》:‘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此固先有其书,故二刘著录,至班氏乃绝耳。”[19]57因此,班固的注解仅仅是为了说明其书之不存。那么,同在春秋类著录中,班固对“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注解中的“有录”,也应当是指《史记》中缺失的十篇在刘向时期是完整无缺的,且刘向已为其抄记了书录,只是到了班固时期,成书已经丢失亡佚,只存留其“录”,此“录”即刘向对成书内容的记录与抄录,有可能是文章的序文内容。
由此可以推知,尽管刘向整理的“书录”经刘歆整理后成为了“目录”,但班固时期已经“无书”的《史记》十篇,在刘向时代确实是“有录”的,那么班氏父子以及后世司马贞、刘知幾等人所称的“有录无书”的“录”,即指刘向的“书录”,也就是《史记》每篇之前的一段小序。由此来看,古代诸位学者认为《礼书》与《乐书》有目或者有序存在是有道理的。
(二)两书皆非褚少孙所补
自张晏提出褚少孙对《史记》篇目进行补写的观点之后,便有很多人认为《礼书》《乐书》皆是褚先生所补。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褚先生补写《史记》的方式进行考察。在《史记》中,有“褚先生曰”的共计九篇(除卷十四至卷二十二所记年表外)。另《张丞相列传》结尾出现了两段“太史公曰”,据张大可考证,“孝武时丞相甚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这里起应该是“褚少孙他篇所述续史之意,当为褚少孙所补。篇首因脱‘褚少孙曰’,好事者误以为司马迁文而在篇末窜加‘太史公曰’”[10]。由此可知,褚少孙在其所续的内容前都会加“褚先生曰”字样,并且,褚先生所补的《史记》诸篇,皆文辞可观,并不像张晏所言的“言辞鄙陋,非迁本意”。褚少孙作为元、成之间的博士,其在续补时是非常尊重司马迁的,这一点可以从《三王世家》“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1]387看出,褚少孙所补内容是非常得体的,而且在体例上与太史公保持一致。反观《礼书》与《乐书》,两书皆取成书割取拼凑誊抄而成。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对《史记》注本《集解》《索隐》中皆谓《孝武本纪》为褚少孙所补提出过质疑:“褚先生当时大儒,以文学经术为郎,虽不善著书,亦何至于此?且其所补缀附益,皆自称‘褚先生曰’,以别于太史公原书,往往自言其作意及其事之所以得者。”[6]28此说对于《礼书》与《乐书》同样适用,以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张照亦云:《礼书》“割裁《礼论》之文,横加‘太史公曰’四字,作《礼书》赞,则谬戾已甚,恐褚先生不至是。”[20]16由上,笔者认为《礼书》与《乐书》都不是褚少孙补写的。
(三)两书皆为同一人所补
关于《礼书》与《乐书》的真正作者,学界并没有定论,通常称其为“补史者”或“好事者”云云。尽管笔者也无法确考真正的补写者是谁,但补写《礼书》《乐书》的乃是同一个人当可确定。
从文章结构来看,两书的行文结构非常相似。《礼书》与《乐书》都是以“太史公曰”四字开篇,序文之后,《礼书》自“礼由人起”以下割取了荀子《礼论》以及《议兵篇》之文,而《乐书》自“凡音之起”以下割取了《乐记》之文,并且两书结尾都假借了“太史公曰”一段作篇后之序,《礼书》篇后之序与今本荀子《礼论》是相同的,而《乐书》篇后之序被认为是今存《乐记》之外的遗失文段。杨合林认为两书的正文以及篇后之序都是“从现存文稿中抄撮而出,补亡者将其冠以‘太史公曰’,当是误认它为司马迁所亲撰”[21]。
从文章内容来看,正文的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残稿资料摘抄的。上文已经论述,两书的开头序文是司马迁原笔,《礼书》中“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1]1158出自荀子《礼论》,原文为:“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22]157这说明,司马迁在写《礼书》的时候,接受了荀子的大部分思想,或许搜集了荀子的相关著述,因此在为《礼书》写序文时,能够将《荀子》中的语句融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同样的,司马迁在写《乐书》的序文时,亦引用了《乐记》的内容。《乐书》中“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1]1175出自《礼记·乐记》,原文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23]1091补缺者在补写两书的时候,参考了司马迁的序文,从《荀子》中誊抄拼凑文字形成了《礼书》,从《乐记》中誊抄内容形成了《乐书》。杨合林认为,除了开头的序文,其余文字内容都出自司马迁的遗稿,但笔者认为出自司马迁为撰写两书所整理的文献资料的残稿可能性更大。若是出自司马迁的残稿,那么补缺后的文章必定是依循司马迁原意的,然而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云述“礼”“乐”之写作目的,便可知道今本《礼书》与《乐书》序文后的内容是偏离了司马迁的原意的。因此,两书序文之后的内容,更有可能是补缺者誊抄司马迁为撰写两书所整理的先秦旧文资料残稿而来。
总之,两书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都非常相似,当为同一人所补写。
(四)补书人为任职于皇家藏书阁的人员
对《礼书》与《乐书》进行补写的,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首先,司马迁《史记》成书的其中一份以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整理的文献资料,极有可能入藏汉廷秘室之府,即天禄阁或石渠阁。据记载,石渠阁与天禄阁不仅是汉代的国家藏书阁,还是士大夫整理经文、研究文献的处所。班固的《西都赋》云:“天禄石渠,典籍之府。”[2]1341《三辅黄图》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24]398《隋书·经籍志》序曰:“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25]25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3320陈直认为“藏之名山”应当是“藏之于家”:“太史公自序说,当时有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存在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褚少孙、刘向、冯商、扬雄等所续,即是根据副本,副本在当时已又录副本,太史公亲手写的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26]但是有学者不认同此观点,认为“将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的‘名山’解释为‘藏之于家’,不明所据。杨氏(杨恽)家中的《太史公书》应当是传本,也就是‘副在京师’本。而‘藏之名山’的正本是秘而不宣的”[27]。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将其放置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目的是“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所以两处的藏书应当是一样的。根据《史记索隐》:“《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所谓‘藏之名山’是也。’”[1]3321可知“藏之名山”一词是由《穆天子传》中“群玉之山”的典故而来,那么《史记》很有可能被司马迁藏在了石渠阁或天禄阁。此外,司马迁父子作为太史公,主要负责记载史事与掌管国家典籍,是能够进入天禄阁与石渠阁等汉廷秘室之府进行资料阅读与整理的。“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也表明司马迁曾在皇家藏书阁整理文献资料,那么他是极有可能将其为编写《史记》而整理的文献资料保存于汉代的中央档案库或皇家藏书阁的。
其次,只有任职于皇家藏书阁的人员才有可能接触到汉廷秘室之府的秘藏书籍,才有可能通过司马迁遗留的文献资料对《礼书》与《乐书》进行补写。一方面,西汉秘室之府的藏书是严禁外传的。《汉书·叙传》曰:“时书不布。”扬雄《答刘歆书》曰:“有诏令尚书给笔墨,得观书于石室。”余嘉锡据此曰:“然则中秘之藏,人臣非受诏不得观矣。”[28]231又《北史》有载:“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这表明《史记》藏于国家藏书阁之中,寻常人等是不能阅读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史记》“副在京师”的另外一册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否则东平王也不会向皇帝求书,褚少孙也不会“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往来长安中”,求书访篇,仍所得无多。至于宣帝时杨恽所持“副在京师”的《史记》,并没有整本对外公布,也没有公开传阅。到了宣帝五凤四年(前54),杨恽获罪而死,《史记》遂下落不明,极有可能是被没入国家书库。如此,《史记》都藏入了国家藏书阁,只有零碎的文字片段传于民间。另一方面,从史书中所记载的对《史记》进行过校对以及续补的人,如刘向父子、班固父子、冯商、扬雄、刘恂等来看,他们都是任职于汉廷秘室之府,可以接触到秘藏书籍的人,那么这位能够接触到司马迁整理的资料残稿,并对《礼书》和《乐书》进行补写的人,亦极有可能任职于皇家藏书阁。
三 结语
综上,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创作的《礼书》《乐书》早已不存,但两书在司马迁离世前应当已经是成书,两书的篇前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因为二文与司马迁创作两书的目的相一致。两书佚失后,后世某位暂不知名姓的人,根据残存的司马迁序文以及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补写了《礼》《乐》两书,使得《礼书》与《乐书》以成书的方式留存至今。这位不知名姓的补作者,很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