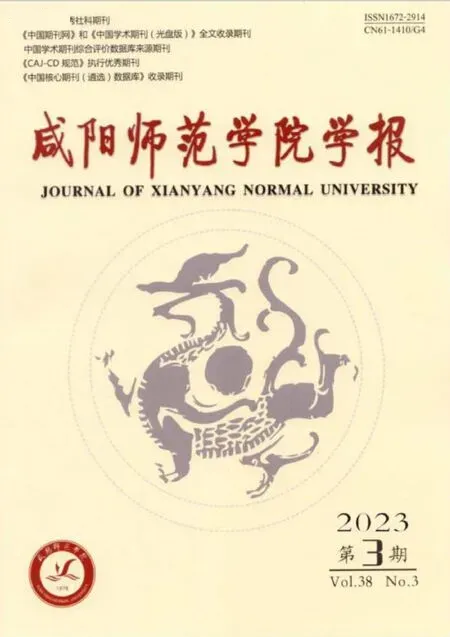与秦始皇相伴终生的迷藏游戏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心理学家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时的记忆往往像扎根沃土的种子,当环境适宜时就会生长出来,对人格的塑造及人性的发展产生不可摆脱的影响。正如萨特所说:“人生只有童年,他的所有按键在童年时期都已按下。”①见理查德·埃尔曼《弗洛伊德与文学传记》,转引自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89页。秦始皇自出生之日起,就陷入了一场不能自拔的迷藏游戏。这场游戏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他的一生都纠结其中,始终扮演着游戏中的角色。迷藏游戏中的心理与场景不仅影响了秦始皇的一生,也影响着秦朝的政治和命运。
对于秦始皇心理的研究,学术界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里对童年时期秦始皇的身体状况与心理特征进行了剖析。1985 年张文立在《未定稿》中发表《秦始皇的性格》,对秦始皇的心理与性格及其对秦朝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林剑鸣《秦始皇的恚恨》、施琪嘉《中国始皇帝——嬴政的心理动力学分析》,较多利用了心理学理论对秦始皇进行研究。赵良在其《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专门设置“情感紊乱的抑郁人格者——嬴政”一章,分析秦始皇的心理特征。笔者在《秦朝兴亡的文化探讨》一书中也曾设置专门的篇章“秦始皇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特点”讨论秦始皇的心理特点。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秦始皇童年生活的场景出发,利用游戏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童年经历对秦始皇及其一生的影响。
一 童年时期:黑暗中才最安全的躲藏者
伴随着一场政治交易和权力游戏,嬴政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降生在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在嬴政出生的前一年,秦赵之间发生了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残酷战争——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大败赵军,“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1]2335,接着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企图一举灭掉赵国。作为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嬴政的父亲及嬴政母子无疑成为了整个赵国最为仇视的人。嬴政出生的第三年,大将王龁率领秦军包围了邯郸,赵人欲杀嬴政的父亲子楚,商人政治家吕不韦不愿意自己的巨额投资化为泡影,“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1]2509。子楚逃脱,赵国把追杀对象转为嬴政母子,“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1]2509。
在秦赵关系最为紧张、赵国最为痛恨秦人的时候,嬴政降生在赵国首都,嬴政和他的家人面对的无疑是周围憎恨、仇视、厌恶的目光。而3岁的嬴政刚刚牙牙学语,步履蹒跚,有了最初的记忆,父亲便无情地抛弃了他们,自己回到了秦国。赵国举国上下都在追杀嬴政母子,嬴政母子只好尽可能躲在隐秘的角落。这样的生活,伴随着嬴政的童年时光,延续了6年之久。
可以想象,嬴政的整个童年,像是在一场迷藏游戏中度过的。可惜的是,在这场游戏中,嬴政母子只能扮演一种角色,那就是躲藏者。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游戏并不好玩,一旦被人发现,暴露了自己,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和死亡。嬴政母子战战兢兢地充当着躲藏者,他们恐慌、焦虑,不敢与人正常往来,任何知道他们行踪的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以致剥夺他们的生命。对于任何人都要怀有警惕,这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模式。因此,在嬴政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敏感、猜忌的种子和对随时可能被发现、被杀戮的恐惧。任何公开场合、任何一次与人接触,都潜藏着被出卖的危险。与此同时,嬴政也渴望着角色的转换,由躲藏者变成寻找者,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由躲在黑暗中的待宰羔羊变成发号施令的游戏主宰。然而,秦赵紧张的关系、身在敌国的处境,使他难以摆脱躲藏者的身份。在这样的场景中,嬴政感到紧张、恐惧、压抑。他烦躁、愤怒,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在幻想中渴望光明,渴望转换,渴望胜利。这样的迷藏游戏持续了6 年,一直到嬴政9 岁,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1]2509。
可以说,嬴政的童年始终是在“躲猫猫”中度过的,这样的经历,在嬴政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像梦魇一样伴随着他,挥之不去,并时时重现。童年的经历对人生的影响至为重要,现代心理学认为:“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这种‘生命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在努力估量他自己的力量及其在周围生活中的分量。到五岁末的时候,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方式,在处理问题和完成任务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对世界和自己的期许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此以后,他会用一套既定的模式来审视世间一切:接收经验之前对其进行诠释,这种诠释总会响应他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2]11-12在持续嬴政童年时光的迷藏游戏中,隐藏得越深,保险系数越大;越是躲在黑暗中,就越有安全感。在与对手的周旋中,有恐惧,有伤害,嬴政感受到了生命的难以把握和神秘,甚至时常产生刺激与快感。
二 青少年时期:迷藏游戏的旁观者与思考者
嬴政9岁时同母亲一起回到秦国,祖父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就去世了,父亲子楚即秦王之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在位3 年去世,13 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秦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蚕食六国,嬴政作为秦国的国王,按理说应该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但是,这时的嬴政不仅没有成为舞台的主角,反而受到了相当的冷落与忽视。
回到秦国的嬴政尽管处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被追杀对象一跃成为了秦国的王位继承者和年幼的秦王,然而,在精神上,嬴政反而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孩童。在赵国期间,嬴政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度时艰,得到了母亲全力的庇护和爱怜。回到秦国后,母亲完全被权力所诱惑,被奢华的生活所吸引,还与已经成为相国的吕不韦旧情复燃,几乎顾不上对儿子应有的关怀与照顾了。父亲庄襄王抛弃嬴政母子在前,又忙于处理秦国政务,对嬴政的冷漠也可以想见。尽管身处高位,但仅十几岁,尚是一个孩童的嬴政,却难以从父母那里得到应有的关爱。
庄襄王去世后,嬴政成为新的秦王。按照秦国的祖制,国王22岁才能亲政,在此之前,国家政务要交给权臣或贵戚代理。嬴政9岁前的生活在躲藏中度过,回国后需要熟悉环境,适应新的生活,他本人尚缺乏应有的政治历练。应该说,18岁之前的嬴政,并不具备掌控秦国复杂政治的能力。这时秦国的政治舞台上,迷藏游戏仍在进行,主角却是吕不韦和赵太后。
赵太后与吕不韦私通,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吕不韦因运作庄襄王王位之功,又得赵太后之助,自是风光无限。“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1]2509-2510或许觉得政治的聚光灯太过耀眼,或许有物极必反的忧虑,或许感受到了嬴政从旁窥视的带着怒火、恨意的眼睛,再加上年老体衰,吕不韦决定适度隐藏自己。“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1]2511吕不韦用李代桃僵之计,将年轻力壮的嫪毐假冒宦官送给赵太后,以便自己抽身。嫪毐成为太后新宠,“太后私与通,绝爱之”[1]2511。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嫪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1]227。嫪毐小人得志,极为猖狂,他不仅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还想除掉嬴政,“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1]2512。
吕不韦本想让嫪毐代替自己成为太后的面首,而利欲熏心的嫪毐却成为了吕不韦权力的强大竞争者,两人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攻防大战,一度掩盖了秦王嬴政的光辉。《战国策·魏策》记载,秦国进攻魏国,有人给魏王出主意:“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3]957这段史料说明,不仅在秦国国内,六国也都知道在秦政坛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吕不韦集团和嫪毐、赵太后集团,而秦王嬴政无关大局。由于嫪毐、赵太后集团过分谋求一己之私,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秦国政治和统一不利,所以才有人建议魏王通过嫪毐割地给秦,支持嫪毐成为秦国主宰者,从而帮助魏国延缓灭亡的命运。
这时的秦王嬴政,似乎成为了政治上的看客,没有人重视他的地位,甚至时常漠视他的存在。“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4]427也就在此时,嬴政利用难得的时机,观察、思考、学习、历练,为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做着准备。
嬴政回顾家人围绕政治权力而发生的变化,首先思考的当是政治权力的巨大魔力。吕不韦为了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将身为落难公子的父亲子楚经营成秦国国君,他自己也成了秦国的相国;父亲子楚由赵国的人质变成了秦国的国君,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增长难以想象;母亲和自己因为父亲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在赵国由被追杀的对象变成了被礼送回国的上宾;母亲回国后,因参与分享政治权利的盛宴,顾不上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嫪毐因通过母亲分享了政治权力,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政治权力如此魔力无限,令人迷狂,也使嬴政认识到:只有充分掌握政治权力,才能主宰一切,改变一切。夺取权力、张大权力、垄断权力、专享权力,成为嬴政的终身奋斗目标。
同时,嬴政也在暗中观察、学习。他利用自己的孩童身份作掩护,忍辱负重、不露声色,一方面学习治国理政的知识和理念,另一方面观察政治舞台上的人们如何表演,如何运用权力,分析着不同政治势力间的关系、矛盾,历练着自己的才干,等待着跨向政治舞台、充当核心角色的时机。
三 成年时期:由躲藏者到追逐者的角色转换
登上秦王王位的第9 年,22 岁的嬴政到了亲政的年龄,经过几年的学习、准备、忍耐、积累和历练,他一举粉碎了嫪毐的政变,接着,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将整个秦国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新的迷藏游戏中,他不仅不再需要隐匿、躲藏,还要快意地出击、报复。
嬴政明白,要想强化自己在新一轮迷藏游戏中追逐者的地位,核心在于掌控权力、扩张权力、巩固权力。剪除了嫪毐、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后,秦国国内已没有人能挑战和撼动嬴政权力核心者的地位了,他继续把扩张权力的触角伸向国外,加速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步伐。为了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嬴政接受李斯的建议,取消了逐客令。尽管尉缭指责嬴政“少恩而虎狼心”[1]230,但他的计策有利于秦灭六国,不仅被嬴政采纳,其本人也被任命为国尉。嬴政对母亲淫乱及与嫪毐一起策划叛乱之事恨之入骨,将母亲流放到了雍地,但是当茅焦指出“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1]227,嬴政立即将母亲接回甘泉宫。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权力扩张,不能影响统一大业。嬴政带领秦国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用了10年时间灭掉六国,他自己也由秦国的国王变成了秦朝的皇帝。统一天下后,通过推行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秦始皇成了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大权在握的秦始皇,实现了角色的彻底翻转,他不再是躲藏者、旁观者,而是迷藏游戏的追逐者和主宰者。他要揪出一切与自己为敌的躲藏者,挫败之,打击之,报复之,以此抚平童年时期的内心创伤,缓解长期积累的心理压力。
对于参与叛乱的嫪毐集团的骨干成员,嬴政以“枭首”处置;对于嫪毐本人,下令“车裂以徇,灭其宗”[1]227;对于嫪毐集团的其他成员,则给予剥夺爵位、判刑、流放的处罚。吕不韦进献嫪毐,对少年嬴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嬴政把他免职后,又将他流放蜀地,逼其自杀。燕太子丹谋划荆轲刺秦,嬴政派大军连续攻击燕国,直到取来太子丹的首级,并最终灭掉了燕国。在总结统一六国的原因时,嬴政还愤愤说道:“燕王混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1]235-236秦军攻破邯郸后,秦始皇由咸阳赶到自己的出生地,“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1]233。儿时的记忆如此深刻,报复的心理如此强烈,也说明了童年时期“躲猫猫”的经历对秦始皇造成了巨大伤害。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有一则《秦始皇禁伐湘山树木诏》:“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臣敢请。’制曰:‘可。’”[5]57-58对于这段史料,学者多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行郡县,在湘山渡长江时遭遇大风大浪,怒伐湘山树木的记载相对应,认为是简牍史料与文献史料对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孙家洲则认为,这是一次文献史料失载的嬴政出巡记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不战而胜,攻破强大的敌手齐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嬴政趁机到新征服的荆楚之地进行巡视。“此时,作为征服者的秦始皇,携统一天下之威南下荆楚,纵情享受统一战争的成果,也向曾经拼死抵抗的荆楚遗民炫耀武力,在秦始皇的内心深处,应该有此必要。”[6]初并天下,秦始皇一扫长期所受压抑,意气风发,遂安排一次短暂出巡,表达志得意满之心情。来到湘山,看到树木葱茏,产生审美情结。当他想到这里曾发生过反抗秦国统一的激烈战争,现在却变成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1]245时,不由心情愉悦,下令保护周边树木,“皆禁勿伐”。秦始皇的举动与这一时期的心态是对应一致的。
从22岁亲政到统一初期的近20年时间,是秦始皇人生的黄金阶段。他由隐而显,由被动而主动,除政敌、坑仇怨、灭六国、当皇帝、行郡县、巡天下、封泰山、击匈奴、修道路、筑长城,真可谓“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1]258。但是,在一场游戏里,如果一个人固定扮演某个角色,则难免乏味。角色的转换,有时出于游戏规则,有时出于游戏者自觉不自觉的个人选择,晚年的秦始皇,又在人生的迷藏游戏中回归到了躲藏者的角色。
四 人生后期:游戏躲藏者的角色回归
心理学上有两个相联系的概念,叫作“固结”和“回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人口迁徙作比喻,将人的发展比作人们穿过新地域的行进。在阻力最大和冲突最剧烈的那些地点,人们将把最强的分队留下来,然后再前进。如果继续前进的人们因力量的削弱而遭受失败,或碰到较强的敌人,他们就会退却到先前停留的地点,在那里取得支援。弗洛伊德说:‘但是,他们在迁徙中留下的人数越多,则失败的危险也就越大。’因此,早期的固结越强,日后回归的要求就越大:‘固结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越强,活动就越容易避开外部困难,回归到固结,因而发展活动也就越加不能在其进程中克服外部障碍。’正像弗洛伊德在其迁徙比喻中说的那样,已通过发展成熟阶段的个人遇到持续的重大挫折时,对付痛苦和不满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心理机制的较高发展阶段回归到较早时期的活动模式。将后退(或回归)到留有弱点的性心理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过程具有未能解决的冲突和未能消除的焦虑。”[7]在秦始皇的一生中,对他心灵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童年时期的遭遇。长期被追杀的经历和只有躲在黑暗中才能获取一点安全感的压抑,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固结。晚年时期,秦始皇又遇到了无法释解的难题和焦虑,在无力克服的挫败感面前,回归孩童时代迷藏游戏躲藏者的角色,在游走和与世隔绝中寻求安全,成为了秦始皇的唯一出路和选择。
那么,作为至高无上、权倾天下的皇帝,晚年的秦始皇遇到了什么难题,让他无法释怀,无力解决,也无法躲避,以致只能回归躲藏者的角色才能感到一丝安全呢?那就是死亡的威胁与对死亡的恐惧。
可能与出生时的处境和孩童时期的经历有关,秦始皇的身体并不健康,或许还与多种疾病相伴。对于秦始皇的身体状况,他的同时代人尉缭有一段经典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易轻食人。”[1]230郭沫若年轻时学习医学,他认为:“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病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枝炎是经常并发的。”[4]427软骨病和气管炎作为并发的慢性病,在年轻身体强壮时尚能承受,但年老体弱时对人体的侵害会逐渐加重。受社会条件和医疗水平的限制,战国秦汉时人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40岁。统一后的秦始皇已经开始步入老年,疾病的困扰日趋严重。在疾病发作时,秦始皇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多病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秦始皇,为了独揽大权和治国安邦,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258。每天以120斤的标准处理文书,其操劳程度非同一般。再加上骄奢淫逸,纵欲享乐,进一步加速了身体的衰老。“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的消耗,秦始皇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的问题。”[8]
死亡的威胁不仅来自身体的衰弱和疾病的折磨,还有六国旧贵族的暗杀活动。见于记载的著名刺秦行动有四次: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险些要了始皇的性命。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也就是秦统一之年,高渐离将铅灌注在乐器筑中,“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1]2537。一次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张良收买大力士以铁椎击打秦皇车驾,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侥幸逃生。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秦始皇与四个武士夜晚在咸阳城微服巡行,结果在兰池被刺客包围,“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1]251。每一次刺杀都险象环生,令秦始皇心惊胆寒。
与此同时,关于秦始皇死亡的预言也不断出现,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有一颗流星坠落东郡,落地为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1]259。这年秋天,“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1]259。
这些暗杀活动与死亡预言,给秦始皇带来了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荆轲的刺杀,“秦王不怿者良久”[1]2535;高渐离的筑击,使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1]2537;张良的博浪沙椎击,导致“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1]2034。对于陨石刻字,“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1]259。越来越激烈的反应,表明秦始皇对连续出现的暗杀活动的震惊以及面对新的死亡威胁的痛苦、暴躁、狂怒和无助[9]。
梦有时最能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潜在心理,“如果我们被某个问题所困,我们的梦境会受到同样的困扰”[2]98。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1]263。海神是阻止秦始皇寻求不死之药的恶神,是死亡之神。心理学家认为:“只有在不确定问题能否解决时,只有在现实仍旧向我们施压,并且在梦中也制造困扰的时候,我们才会做梦。这便是梦的任务——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2]98-99死亡压迫着秦始皇的神经,令他难以释怀,也无法摆脱。秦始皇梦中与之奋战、搏斗,表明死亡如影随形,时刻相伴,步步紧逼,无法剔除。秦始皇烦恼至极,恐惧至极。为了抵御对死亡的恐惧,摆脱死亡的威胁,晚年的秦始皇无可奈何地回归到了童年时代。
在童年时期躲迷藏的游戏中,秦始皇感受到些许安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摆脱死亡威胁的方法:不断变换藏身地点,居住之地不被外人掌握;隐藏在黑暗之中,除了母亲及近身僮仆,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幻想找到一种不死之术,彻底摆脱死亡威胁。
统一后秦始皇的生活与不断迁徙巡游密切相连。统一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巡游活动,在以后的10 年里,先后5 次巡游天下,并最终死在了巡游路上。实际上,晚年的秦始皇体衰多病,本应该在咸阳处理公务,安神养身,之所以违背常规不辞劳苦地游走天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无疑是在死亡的威胁下,力图回归到童年时期不断变换藏身地点以躲避死亡威胁的场景中。在游走中才能感觉到安全、才能些许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也被他身边之人所知晓。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为了破解死亡预言,“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1]259。深谙秦始皇心理的占卜者,迎合他的愿望,把他引向了为躲避死亡却走向死亡的人生最后一次巡游。
除了不停巡游,秦始皇还尽力让自己的居住地点隐秘而令人不可窥测。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为秦始皇寻求不死之药的卢生建议:“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1]257这是劝谏秦始皇要安静恬淡、清心寡欲,不能过度游徙、操劳,才符合祛病强身的养生之道。对于这个建议,秦始皇的应对措施是:“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1]257把咸阳周围200 里范围内的270 多所宫殿楼观,用复道甬道连为一体。复道是在空中架起的连接楼宇的道路,甬道是地上带夹墙或遮蔽物的道路,行走在这样的道路中,很难被别人发现。这样,秦始皇在享受骄奢淫逸生活的同时,又把自己隐身起来,似乎回到了躲藏起来才有安全感的童年场景。
晚年的秦始皇,热衷于用各种复杂的道路连接宫殿。修筑阿房宫时,“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1]256。秦始皇游走于各个宫殿之中,不允许任何人泄露自己的行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1]257可以想象,高大深邃、阴森寂寥、曲径通幽、环环相连的众多宫殿,犹如秦始皇幼年时期幻想的迷宫,在那里既可以尽情嬉戏游乐,又不被追杀者所知晓。
躲避死亡的最佳途径就是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这是童年时期就有的幻想,也成了晚年秦始皇的迫切追求。为了寻求仙药,他被方士牵着鼻子走,演出了一场场闹剧,却最终死在了求仙路上,这时的秦始皇才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彻底回归[8]。
五 后秦始皇时代:迷藏游戏的余波与震荡
为了躲避死亡和寻找仙药,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又一次踏上了巡游之路,最终死在了沙丘平台。按照秦始皇的安排,死后要由长子扶苏主持丧礼,并即皇帝之位。但在赵高的策划,李斯、二世的参与配合下,秦始皇的安排化为了泡影。
赵高祖籍赵国,父母均被秦国治为罪犯,他自己也出生在罪犯劳动的隐宫之中。出身卑微、对秦政权充满仇恨的他,靠自己的才华、奋斗以及对秦始皇心理的把握与迎合,爬上了中车府令之位,替皇帝掌管车马印玺。他深知,按照始皇的遗嘱,如果扶苏顺利即位,秦政权可能度过危机,自己的位置或将难保,搞垮秦政权的企图将成为泡影。于是,赵高勾结秦二世,策反丞相李斯,隐瞒秦始皇死讯,改换皇帝遗诏,逼长子扶苏自杀,拥胡亥为二世皇帝,成功发动了沙丘政变,改写了秦朝的历史走向。
沙丘政变充满了偶然与阴谋[10],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始皇在炎热的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1]264。巡行队伍载着皇帝尸体行走了一月有余,甚至尸体发出了臭味,竟然很少有人知道皇帝的死讯。在这期间,赵高等人仍以皇帝的名义,赐扶苏自杀,夺蒙恬军权,完成了政变的一系列步骤。看似无比的离奇与荒诞,却是赵高利用秦始皇晚年深陷迷藏游戏制造的一场闹剧。晚年的秦始皇,竭力把自己隐藏起来,几乎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秘莫测,若有若无,人们习惯于接受他身边人发号施令,把他们当作皇帝的化身。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才能让赵高从容谋划,精心布局。
赵高本人的出身及经历,让他熟知迷藏游戏中躲藏者的心理。策划沙丘政变,更使他体会到了把他人引入迷藏游戏场景,自己加以操控的奇妙魔力。政变成功后,赵高故技重施,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把秦二世导入迷藏游戏躲藏者的角色,这样,才能让秦二世与众臣隔绝,便于他操纵与控制。
秦二世是通过沙丘政变登上皇位的,再加上身为幼子,在秦国统一过程中并无尺寸之功,自然深怀恐惧自卑心理,担心政变阴谋泄露,功臣不服,宗室夺权。赵高掌握了他的这一心理,诱导秦二世诛杀功臣,铲除兄弟姐妹。“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1]268通过制造恐怖氛围,赵高将秦二世与可能亲近、影响他的人疏远,使他听不到真话忠言,从而将二世隔离起来。
赵高利用秦二世的自卑心理,通过恐吓、诱导,进一步将他引入迷藏游戏的躲藏者角色。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1]271为了让二世皇帝安于躲藏者的角色,赵高又诱导他纵情享乐,在温柔乡中醉生梦死,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浑然不觉。这样,秦二世完全变成了孤家寡人,秦朝的权柄则为赵高所掌控,“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1]2558。
指鹿为马和李斯被害事件充分说明,一个人不与外界接触,就会失去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秦二世完全被赵高玩弄于掌股之间,成为了赵高操纵的傀儡。赵高借二世之手将秦朝带向了灭亡之路,实现了自己报复秦朝、毁灭秦朝的目标。玩火者必自焚,子婴取代二世被扶持为秦君后,设计诛杀了赵高,赵高也未能摆脱秦亡殉葬者的命运。
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1]393童年的经历如同一场迷藏游戏,它伴随了秦始皇的一生,也影响了秦朝的政治乃至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