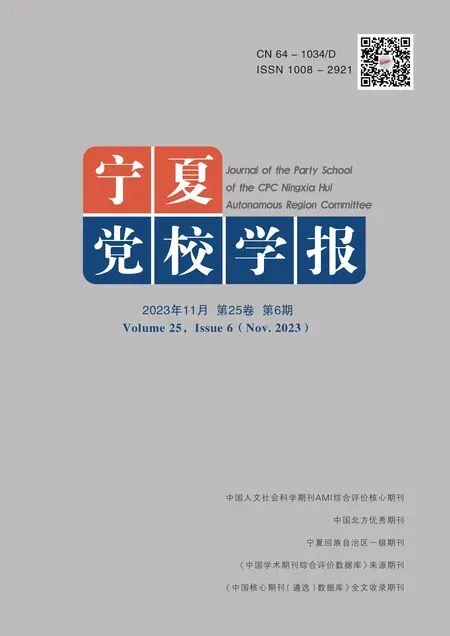实现劳动的自由:马克思与阿玛蒂亚·森劳动能力概念的辨析
张 瑶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阿玛蒂亚·森在借鉴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为核心概念的能力路径(capabilities approach)。森提倡“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的可行能力而使他们获得实现自身所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其中,劳动能力作为个体可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相关。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重要且集中地体现在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就包括劳动能力。然而森和马克思对现实社会成员劳动能力的不同考察方法,使得劳动能力概念在他们各自的劳动能力观中具有不同内涵。
一、劳动能力:个体实现劳动的自由
如何比较森和马克思“劳动能力”概念的具体内涵,罗尔斯关于正义概念和正义观的区分为我们提供借鉴,“把正义概念(the concept of justice)看作有别于各种不同的正义观(conceptions of justice),看作由这些不同的原则、不同的观念所共有的作用所指定的,看来就是很自然的了”[1]。可见,作为一般概念,它可以由包含各种不同内容和原则的观念的共同性所规定,因此,为了辨析森和马克思的劳动能力概念,我们可以从最为抽象和简单的“劳动能力”概念出发,将其分别置于森和马克思的劳动能力观中,揭示出劳动能力这个一般性概念在两者不同观念中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反过来获得一个较为具体和丰富的劳动能力概念。
基于此,我们可以首先界定出共同适用于森和马克思劳动能力观的“劳动能力”这个一般性概念,我将这种一般的劳动能力概括为“个体实现劳动的自由”。在森的能力路径中,个体的“功能性活动”是指个体认为值得去做的行动(doing)或是想要获得的生活状态(being),而劳动便构成个体的功能性活动之一,而各种可以选择和实现的功能性活动所组成的集合便构成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可见,功能性活动反映了个体实际获得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则反映了个体在不同成就中进行选择,并实现这种成就的机会和自由。因此,个体的可行能力便与其实质自由关联起来,这种自由就是个体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即个体有理由珍视的不同成就和生活方式的机会。“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实际达到的成就,可行能力则反映此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可供这个人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组合。”[2]63基于此,当我们将个体的劳动视为一种功能性活动时,个体的劳动能力便是指个体实现各种自身有理由珍视的劳动的自由。
在森那里,个体的劳动能力首先包含着个体的内在因素,例如与个体劳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些内在因素类似于努斯鲍姆所言的内在能力,“一个人的特质(品性特点、智商情商、身体健全与健康状况、内在学识、感知和运动的技巧)都和其混合能力是高度相关的,但此处仍有必要将这些特质与混合能力区别开来,它们仅构成混合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将这些个人状态称为内在能力”[3]。森将这种栖息于个人体内的劳动特质和能力视为现代社会成员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源禀赋,成员可以凭借这种资源禀赋获得对收入和商品的权益,“资源禀赋,即对于生产性资源和具有市场价格的财富的所有权,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仅有的、能发挥显著作用的资源禀赋是其劳动力”[2]163。可见,在这里,森将个体劳动能力中所蕴含的内在因素视为与土地、商品相同的、能够与其他资源和财富进行交换的个人资产,个体可以凭借劳动建立起对收入和商品的所有权并对其进行支配。
马克思首先将“实践”视为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因此,就个体活动之意而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森的功能性活动概念具有类似含义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相比于森的功能性活动概念具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更应该被视为理解现实世界包括社会历史的逻辑出发点以及解释原则。,然而,相较于森将个体的劳动视为与免除疾病和死亡、获得教育、参与政治等活动相同地位的一般功能性活动,在马克思那里,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是个体最为基本的实践形式,其构成了个体存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一方面,人是自身劳动的历史结果,人通过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完成自我的生成、发展和确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4]同时,个体的劳动方式决定了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表现形式,个体在劳动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关系,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的现实性本质;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劳动与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形成共生关系,在生成自身的同时也创造着社会和历史,个体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础上也进行着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正是这些多重的生产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发展出整个人类社会活生生的历史。
在现实中,个体劳动所运用和发挥的本质力量构成了个体的劳动能力,“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195。一般而言,个体的能力是一种蕴含于人生命之中的本质力量,具有发挥和实现的可能性,个体只有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将这些潜在力量发挥出来并作用于现实的客观对象,才能将这些力量现实化。我们将这种蕴含于人体内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从潜在走向现实的过程称为能力的外化。就劳动能力而言,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个体首先将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的对象,通过劳动将自身的劳动能力作用于生产资料,通过改变劳动对象的外在形式从而将这种潜在的能力实现出来,因此,劳动的过程便是劳动能力外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个体的任何潜在能力包括劳动能力必须合理和充分地现实化,并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这种潜能的实现和完善直接根植于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性之中。“既然任何特定事物都要依据其内在能力和本质属性所决定的那种存在过程来理解,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我实现的过程要求特定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的,或者至少某些对抗性的条件不存在。”[6]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能力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实现自身的规范性意义,而这种劳动能力实现的受阻被马克思视为一种道德浪费,是一种理应批判和超越的状态。并且,在马克思那里,个体的劳动过程便是个体劳动能力发挥和实现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劳动能力概念同样理解为个体实现自身劳动的自由。总之,通过对森和马克思劳动能力概念的直接考察,我们可以界定出共同适用于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劳动能力概念,即个体实现有理由珍视的劳动的实质自由和机会。
二、森劳动能力观中的“劳动能力”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森和马克思都将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个体实现劳动的自由。然而,由于森和马克思基于不同的方法对社会成员现实的劳动能力进行考察,因此,在他们各自的劳动能力观中,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显现为不同的过程,因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森的劳动能力观中,个体劳动能力首先包含着与个体劳动相关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必须通过教育、训练而获得培育和提升,国家对此负有责任;同时,个体的劳动能力必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条件相结合而转化为一种实际的功能性活动,以此创造出各种实质性的自由和机会以实现个体所追求的成就和生活方式。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个体内在能力转化为实际功能性活动的过程类似于马克思所言的劳动能力的外化,但是,与马克思强调劳动的对象性不同,森从资本主义市场出发,将这种社会的转化因素集中于自由和充足的就业机会,其必须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获得保障。
森指明自由市场机制是个体内在因素转化为实际劳动这一功能性活动以实现个体劳动能力的重要社会因素。一方面,市场均衡在增进个体可行性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鉴于这些标准假定,竞争性市场均衡在能力和商品持有的机会和自由方面具有弱效率。”[7]就劳动能力而言,自由的市场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以及相应的就业机会,使成员能够自由进入劳动市场以获得这些潜在的就业机会,并且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机制,凭借自身的劳动而获取收入和商品。森在其能力路径中强调了五种工具性自由②这五种工具性自由分别是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其中,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2]32。森将个体的劳动能力视为其获得经济权益所拥有和可运用的资源,而自由市场机制便为这种资源的运用提供了机会。可见,自由市场是个体劳动能力实现的重要经济条件,对提升社会成员的福利和生活质量以实现其实质自由具有工具性意义。
另一方面,森指明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体最终获得实现自身所珍视的生活的自由,同时也要关注实现这种自由的过程,从而获得一个整全性结果。“我们可以广义地定义机会,我相信这更为可信,从取得‘全面结果’的角度来定义,即注意到实现最终结果的方法(例如,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还是受其他人的命令)。”[8]基于此,劳动能力的实现并非仅仅体现为社会成员能够自由进入劳动市场而获得特定工作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个体能够避免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自主选择各种职位。“重要的是使社会成员自由选择其工作或活动,而不是使他们重返劳动市场而无论工作的质量如何,以及所有与专业和社会融合相关的政策和集体框架应该以这种方式提高成员的能力。”[9]在这里,森同样指明了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决策和控制的杠杆掌握在各自的手中,在没有特定类型的‘外部性’(关于对决定的控制)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地行使它们。”[7]基于自由的劳动市场,个体可以在不同类型、工资、质量、工作环境的岗位中进行自主选择,甚至是退出劳动市场,而免受他人的干涉。在森看来,一方面,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功能性活动,“真正选择的存在实际上可能会影响所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的性质和意义”[10]。因此,自由市场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多种就业选择本身可以提升成员的福利。同时,市场的自由交换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不需要通过个体获得收入和增加福利而获得解释,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在森看来,对自由市场的破坏本身就是对个体和社会自由的剥夺。
从森的视角来看,雇佣劳动制度事实上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因为这种制度将社会成员从原始共同体狭隘的人身依附和地域限制中摆脱出来,使其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劳动市场上自主订立契约以出售自身的劳动能力,并通过自由的商品交换而获得实现自身所珍视的生活的物质资料。可见,森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出发,将劳动能力视为个体获得和选择自身有理由珍视的劳动,并凭借这些劳动获得收入和商品权益的自由和机会,基于此,实现劳动的自由在森那里便具体体现为劳动的自由(freedom of labor),以及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freedom through labor)。森主张通过市场本身具有的自由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势,为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和自由的就业机会,以确保个体能够获得自身所珍视的工作,个体劳动能力的剥夺便体现为不自由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成员的强制性劳动或失业。基于此,社会公共政策便集中于保障劳动和商品市场的自由运行,并通过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改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成员间劳动能力不平等的分配。
三、马克思劳动能力观中的“劳动能力”概念
不同于森将资本主义市场作为考察个体劳动能力的出发点,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指明,个体现实的生存处境及其能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对现实个体劳动能力的考察绝非仅停留于社会的流通和交换领域,而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能力观中,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体现为一个更为完整的过程。
首先,与森一样,马克思强调个体劳动能力的内在因素,即个体劳动所运用和发挥的本质力量,这些本质力量一方面作为个体劳动的基础不断外化于现实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活动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出来。“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1]487也就是说,个体在运用和发挥劳动能力的过程中也在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出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劳动技能和其他才能。其次,劳动能力实现的前提在于对劳动能力本身的占有,即个体能够自由支配自身的劳动能力。再次,劳动能力的实现是一个将蕴含于个体自身的内在潜能通过劳动不断显现于对象的过程,因此,其必然包含着劳动能力的外化。最后,劳动能力的实现还包含着对劳动能力的确证,这体现为对自身劳动能力外化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占有和享受,劳动者通过对产品的占有和享受,使自身的生命获得独特的表现形式,个性获得显现和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占有和享受既包括个体对自身劳动产品的直接占有和享受,同时,当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在享受我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以满足需求时,我的劳动能力以及独特个性也获得了间接确证。“非异化的劳动和交往,这种劳动和交往在为其他成员提供必需品的过程(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满足。”[12]总而言之,马克思将个体的劳动能力置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进行考察,基于此,劳动能力的实现便体现为个体劳动能力获得培育、占有、外化和确证的总体过程。
基于此,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劳动能力的实现首先在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存在,因此,只有确保个体生命的存在,才能使蕴含于生命中的劳动能力获得外化的可能,这就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将自身的劳动能力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劳动能力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对自身劳动能力的占有和支配为前提,这就要求社会成员以独立、自由的个体身份获得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所有权,在拥有和占有自身劳动能力的基础上自主地使用和支配它;能力的外化必须以客观对象的存在为条件,就劳动能力而言,劳动能力的外化必须具有劳动对象即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个体的劳动能力不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培育,个体还必须在劳动过程以外从事各种自由活动以发展丰富、全面的能力,这以充足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为前提。
可见,与森一样,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能力作为个体实现劳动的自由也体现为“劳动的自由”和“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一方面,劳动的自由即个体作为独立个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能够占有和自由支配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及实现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其中就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劳动的自由还体现为社会成员在超越过去自发性和强制性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潜能和个性从事科学性和社会性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体现为个体通过生产活动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更体现为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将过去支配人的自在和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置于自身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支配之下,在确立人在历史中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个体自身的自由。同时,通过劳动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协作与交往,社会成员在实现自身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丰富和全面的能力,为个体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基础。
然而,在马克思的劳动能力观中,劳动能力的实现不仅仅体现为“劳动的自由”以及“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其中还包括“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freedom at labor),也就是说,人的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必须体现人的自主性特征,具体而言,劳动条件是自我支配的,劳动的目的是自我选择的,劳动过程是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的;劳动结果的占有和享受是自我决定的,它们都必须出于社会成员的自主而免除他人的干涉,只有这样的劳动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同时,在马克思看来,个体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所实现的自由,仅仅是处于必然王国的自由,这种自由依旧受到自然的必然性制约,只有到了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自由王国,人们才能摆脱劳动的外在强制性,而直接将自我才能的实现作为目的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自我实现是个体权力和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实现和外化”[13]。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实现劳动的自由还体现为个体“摆脱劳动强制性的自由”(freedom from labor)。总而言之,马克思对成员劳动能力的考察,不仅集中于社会的流通和交换领域,而且进入了社会的生产领域甚至是生产领域的“彼岸”。基于此,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是一个包含着劳动能力培育、占有、外化和确证的总体性过程,甚至还包括从劳动的强制性中摆脱出来,从事自由活动而发展以自我为目的的能力的过程,实现劳动的自由在马克思那里便具体体现为劳动的自由、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以及摆脱劳动强制性的自由。
四、对森“劳动能力”概念的批判与重构
通过与马克思劳动能力概念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森对社会成员劳动能力的考察仅仅停留于资本的交换和流通领域而未能抓住资本的实质,因而未能揭示社会成员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存在状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在于资本的增殖,它分为三个环节,“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11]383。第一个环节,资本同劳动能力交换以保存自身价值的过程,即工人将自身的劳动能力作为与市场上其他产品一样的商品与资本家出让的一定数额的交换价值即工资相交换;第二个环节,工人运用和发挥劳动能力即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以使资本价值增加;第三个环节,资本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货币,以实现资本价值。这三个环节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同时也是不同性质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同资本的交换作为资本运行的第一个环节仅仅属于简单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只有进入到资本运行的第二个环节即商品的生产环节,劳动能力才能显现出其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即这种商品能够生产出超过自身交换价值的价值从而使资本增殖,才能显现出劳动能力同资本的交换与其他简单商品交换不同的性质,即工人劳动能力生产出的超过自身交换价值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劳动能力与资本的交换并非同其他商品交换一样属于等价交换。
然而,森对个体劳动能力的考察仅仅局限于资本运行的第一个环节,即集中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劳动能力自然也就仅仅被视为个体凭借其能够获得收入和商品权益的资源禀赋。在这里,森将个体的活的劳动能力与土地以及其他资产等同起来而一道视为一般的生产要素。这事实上就陷入了斯密和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错误中,其结果便是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质被抽象掉而沦为劳动一般,资本剥削劳动的本性被掩盖。可见,森基于商品市场的考察并没有揭示出资本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揭示出社会成员劳动能力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也正是如此,森将个体劳动能力遭受剥夺的外部缘由排他性地归结于不自由的劳动市场,这就必然掩盖了社会成员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能力遭受制度性和结构性剥夺的现实,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并非导致个体劳动能力遭受剥夺的唯一原因,即便保障了自由的雇佣劳动市场而使社会成员获得就业机会以进入劳动过程,然而他们的劳动能力在劳动过程中以及劳动过程后依旧遭受剥夺。
从马克思的劳动能力概念出发,将个体的劳动能力置于社会总体性的生产过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个体的劳动能力在培育、占有、外化和确证过程中的每一步受阻都会导致个体劳动能力遭受剥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能力的剥夺首先体现为私有制所导致的个体劳动能力同实现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工人由于无法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丧失了劳动能力外化的对象,自然也就无法直接占有和享受将自身劳动能力外化于其中的产品即生活资料。“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5]659基于此,工人必须将自身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以此进入生产过程而获得劳动对象,只有这样,工人才能将自身的劳动能力对象化于其中从而生产出劳动产品,同时凭借劳动换取的工资获得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使得工人的劳动能力不再作为生产的客观物质条件而被他人直接占有,劳动能力摆脱了原始的依附关系而获得自由;但同时,雇佣劳动制度也剥夺了工人劳动能力实现的客观物质条件,使他们自由的一无所有而只能被迫出卖自身的劳动能力。
在劳动过程中,由于工人让渡了自身劳动能力的使用权因而丧失了自由支配自身劳动能力的条件,工人劳动能力的运用和发挥必须服从于资本家的意志以及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不再是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自主过程;同时,一旦交换价值成为商品的首要规定,获取交换价值就成为工人劳动能力发挥的首要目的,基于此,工人劳动能力的实现也必然受外在经济必然性的支配,受异己的物的关系的统治。“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1]107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能力的实现并非指向人的自由个性,而直接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劳动能力的发挥和实现失去了自主性和自我目的性而遭受剥夺。在劳动过程之后,商品的普遍交换使得个体劳动能力的确证并非表现为对劳动产品直接的占有和享受,其必须以交换价值为中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劳动能力的确证不得不服从于外在偶然性,一旦商品无法在市场上顺利转化为交换价值,那么对象化于商品中的工人的劳动能力便无法获得实现和确证而只能沦为一种剩余,自然也遭受剥夺。此外,社会成员劳动能力的剥夺也体现在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通过剩余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从这些物质条件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以发展各种才能,因此,资本家丰富、全面才能的培育和发展是以工人劳动能力在大工业体系下的畸形化和片面化发展,以及其他才能的牺牲为代价的,这直接造成了社会成员劳动能力以及其他才能的不平衡发展。
可见,一旦我们扩展森的劳动能力概念,将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视为一个更加全面的总体性过程时,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就自然从一种道德的辩护转向一种批判和超越的视角,在森看来,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和自由就业机会的雇佣劳动制度,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直接造成社会成员劳动能力遭受剥夺的物质根源。森认为,在劳动市场,工人通过与资本家自由订立契约而获得就业机会,然而,劳动成为一种雇佣劳动而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其前提在于劳动与其劳动对象的分离,工人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劳动的客观条件,因而也就被剥夺了劳动能力发挥和外化的现实性,总而言之,一旦劳动能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就意味着个体劳动能力遭受剥夺。同时,基于森的劳动能力概念,个体凭借劳动获得收入和商品的权益从而实现自身所珍视的生活。然而,即便这样,个体也没有获得其所生产的所有报酬和商品,因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仅仅是其必要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和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和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对马克思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剥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劳动能力也遭到剥夺。
马克思指出,必须要认识到工人劳动能力同其实现条件、实现成果的分离本身就是对个体劳动能力的剥夺,这是一种不公平并理应超越的状态,“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11]455。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马克思考察个体劳动能力存在和发展状况的起点,同时也是其必须超越以实现个体能力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工人想要实现自身的劳动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其他才能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重获自身劳动能力实现的客观条件并占有自身劳动能力对象化的产品,并利用自由可支配时间从事各种活动而发展出更为丰富和全面的才能。
总之,森将个体的劳动能力与其实质自由关联起来,提出实现社会成员劳动能力的公共措施,这对提升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实质自由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重要意义可能会由于森对劳动能力较为狭窄的概念界定而被削弱。因此,森必须扩展其劳动能力的概念,将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视为一个包括劳动能力占有、培育、外化、确证以及摆脱劳动强制性的总体性过程,不仅关注社会成员“劳动的自由”以及“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自由”,还要关注其“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以及“摆脱劳动强制性的自由”。只有这样,森对当代社会成员劳动能力的考察,才能从一种对劳动和商品市场的考察进入到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性背景的考察,也只有这样,森才能真正获得关于当代成员劳动能力存在和发展状况的整全性结果,才能实质性地提升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以实现他们自身所珍视的成就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