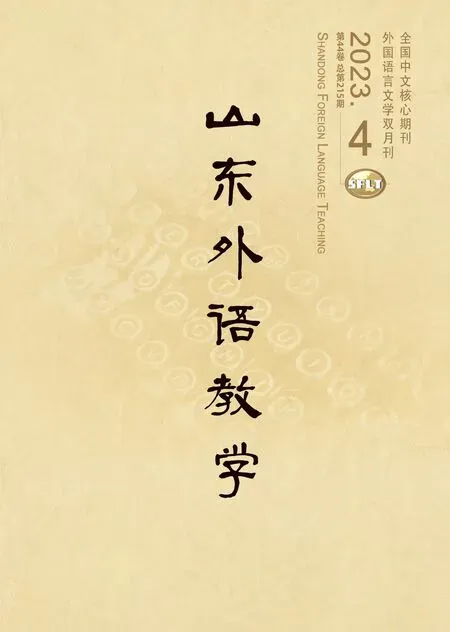《河流,黑暗的灵》的生命意识与民族认同
胡碧媛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1.引言
鲁道夫·安纳亚(Rudolfo Anaya, 1937-2020)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奇卡诺文化运动崛起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奇卡诺文学之父”。他出生并成长于美国西南的乡村,长期定居新墨西哥州,在创作中以个人生长的地域环境与文化生活为主要素材,彰显浓郁的地方特色。美国西南部主要指毗邻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及加州南部一线,边界化的区域位置和西班牙殖民、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背景,赋予这一地区独特的族裔杂糅文化模式。作为奇卡诺文学的代表人物,安纳亚在2016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勋章,时任总统奥巴马评价他的创作是“美西南的先锋故事”,生动再现了美西南乃至拉美地区的族裔社会现实。
学界认为,安纳亚以小说这一文类的地方叙事为核心,展现多元文化融合及世界主义的价值理念,他本人也多次重申,“我视自己为兼收并蓄的人,愿意吸纳各种传统”(Sharma, 1994:178)。在他看来,印第安文化是墨裔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也接受欧洲文化、英裔美式主流文化的融入与影响,这种杂糅特征充分表现于新墨西哥的地域想象与区域化书写中。他关注现代流变中族裔性的内涵、文化传统的转型与延续、历史记忆的价值传承、族裔群体的维系等认同主题,对他而言,“奇卡诺意味着将命运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994:177),“我的身份与奇卡诺身份紧密联系”(1994:180)。他将文学创作作为实践场所,采用英语与西班牙语结合的双语体系书写墨裔身份、历史、传统与价值。
安纳亚的第一部小说《河流,黑暗的灵》(BlessMe,Ultima, 1972)①是其文学风格的综合体现。小说讲述了一位墨裔男孩安东尼的成长故事,核心主题聚焦族裔个体与群体认同。对于饱受西班牙及美国殖民影响的美西南族裔群体而言,文化认同是有关生命政治与族群存亡的根本问题,群体意识与个体身份的关系、乃至自我与群体的双向建构广受族裔作家的关注。评论界对安纳亚文学创作的评价集中于其文化多元性的再现,无论是“世界视野”(Clark, 1995:41)或是“新世界人物”(解友广,2015:310)的论断,或是认为其跨文化的世界观将奇卡诺文学融于更广阔的当代文化景观之中(Pérez-Torres, 1991:248),都强调的是文化融合而缺乏对个性,或者确切而言,族性的阐释。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安那亚提倡的“兼收并蓄”是一种欧裔、或是英裔、或是西班牙裔文化中心意识还是奇卡诺文化的延续?是族裔文化的转型或是被同化?“兼收并蓄”的内涵究竟为何?亦有学者指出,“奇卡诺文学最基本的元素正是为自我或是祖先记忆追寻的身份之谜,是不为压迫者所知,捍卫文化独特性的秘密”(Taylor, 1997:251)。安纳亚的创作再现的是“集体无意识”,“为保留族裔的集体意识,将他自己的景观经验转化为生命支撑的神话体系”(Taylor, 1997:252)。据此,我们可以借用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民族认同观,考察《黑暗的灵》的族群认同表征以探索作家的族性书写。
2.祖地:家园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史密斯的研究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这一现象展开历史性的考察,深入剖析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文化演变和模型机制。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中型公共文化,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2018:55)。与此同时,他归纳出族裔共同体的六个特质:具体的群体名称、共享的神话原型、历史集体记忆、共有的文化元素、祖地的栖居和族群的凝聚力(2018:30)。史密斯认为在个人与集体的认同中,“地方性、区域性的认同同样是普遍存在的”(2018:9)。作为族群生存繁衍的地理基础,史密斯将祖地定义为共同体建立的“一块安全的、可识别的、紧实的领土”(2018:80),族群世代繁衍的原生态的自然地理区域,在族群的发展中逐渐凝聚历史内涵,内在驱动族群文化模式的塑形与重构。
《黑暗的灵》中安东尼及其族群生活的祖地,为美西南新墨西哥州东部与德克萨斯州西北部交界的荒原地带。夏季来临时,“‘亚诺荒原’的美丽正在我面前展现,河流唱着潺潺的歌,伴随翻滚的大地的低吟。童年的神奇时光静止不动,大地鲜活的脉动让我感受到它的奥秘而血液沸腾”(安纳亚,2015:1)②。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人文理论界的身体转向中,身体与情感关系建构成为最显著的重点。身体作为情感发生最紧密的空间尺度,使情感在身体具象化研究中得到重视,众多地理学家将关注点聚焦于身体经验的情感内涵。如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感性经验(experientiality)这一概念,阐释了身体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与心理认同以及情感依附的关系。如前所述小说的开篇文字,即通过五官的各种感性经验反映对生活祖地的热烈情感。安东尼的视觉映射着亚诺草原生命现实的“翠绿”与神秘魔幻的“蓝色”,耳畔聆听者河流的“歌”和大地的“低吟”,双脚感觉着“大地的颤动”,身体整体的感知进而激发兴奋的“颤抖”。 “空间意味着自由”(段义孚,2017:1),身体的空间性带给个体外在空间的感知并为此获得时间的隐喻性,草原的广阔所呈现的广度与纵深的延展性,代表着向未来延续的永恒,将祖地景观进行了去时间化的处理,安东尼的“时光静止不动”表达了一种非时间性的永恒感所带来的精神满足(胡碧媛,2016:96),使感性经验的个体与自然及祖地产生精神与情感的同一性。段义孚指出“对于故乡的深深依恋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现象”(2017:126),而这种故乡的所指总是一种基本的地理概念和特定的区域,这种依恋感也同时寄托于生活在共同祖地的共同人群。
地缘与血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理论也将血缘与地缘作为共同体建构相辅相成的要素。《黑暗的灵》的文本叙事体现非常典型的血缘共同体意识,文本中反复提及安东尼父亲家族“玛雷兹家的血液”及母亲家族“鲁纳家的血液”对于维系家族的重要作用,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享有共同生活劳作与经济方式,占有维持基本生存的生产资料。血缘共同体往往居住在同一处地域,与土地建立的种种联系也维系着共同体内部的团结,进而发展成更为持久深沉的亲密情感与精神要素。“鲁纳家的血液让他们安静……才能了解耕种所必需的土地的秘密……玛雷兹家的血液就是要疯狂……像后来成为他们家乡的辽阔亚诺一样”(41)。
扎根祖地表现稳定的家园坚守,这对于族裔群体包括安东尼族群而言是自然而然的,而段义孚对于具有迁徙习惯的美国大平原本土裔族群的研究表明,游牧的狩猎民族对故乡依然有着“最为炽烈的情感”,因为“她拥有赋予生命的力量”,个体在迁徙过程中也时时置身于自然景观之中,“以便能够接近哺育他们成长的力量”(2017:129)。与此类似的是,安纳亚在《黑暗的灵》的叙事中,并未执着于书写地域性的家园坚守,转而提及流动性对共同体的冲击。安东尼的父亲感叹三个儿子二战服役结束回到家乡,不安于现状又意欲前往他乡谋生,“我早该知道他们身体里流的玛雷兹的血液会让他们无法安宁。就是这同样的血液让我在年轻时四处流浪啊!”(121)在这里,现代流动冲击着美西南的区域文化模式,将地域坚守改写为跨域的表现和理想追求。在安纳亚笔下,地域认同与血缘认同的结合已上升为族裔群体的价值理念,不再执着固守地域以强化共同体的稳定性,而是依靠血缘家族始终保持精神的同一性。“唯有血缘的亲近和混血,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统一,因而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人的共同意志的可能性”(滕尼斯,1999:73)。
另一方面,家族成员都深知,“我们必须团结到父亲身边”,父亲的“目光也始终朝向西方”,“他的梦想是骑着马往西边去,寻找新的冒险”(25)。作为家庭血缘共同体、乃至族群共同体的老一代个体,父亲始终在践行开拓求索的西部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深植于美国历史的文化传统,更体现多元族裔融合的民族历程,所以美西南的地域文化和区域特质在安纳亚笔下,既反映墨裔文化模式的地方性建构,同时将现代流变与美国民族历史产生关联,使得族裔文化认同从具象的地域家园延伸为普遍化的跨域性民族归属。安东尼家族的墨裔家园既是亚诺荒原,也是美西南乃至整个西部,尽管父亲渴望举家前往加州,但是接受三个大儿子、安东尼的三个哥哥选择前往不同的他乡,“玛雷兹的血液把他们带离家园跟父母”(71),个体的空间分离却始终由家园、族群、地域及民族的精神纽带联结。
3.暴力:族群分裂的信仰焦虑
自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开始,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部族的生存状况就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从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殖民者不断侵略印第安人土地,掠夺资源威胁其基本生活,且变本加厉大肆杀戮印第安人。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对印第安部族进行野蛮迫害与屠杀。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人以远征的方式穿越东亚利桑那开始进入美西南地区,并且持续向今天的新墨西哥州及科罗拉多州挺进,开始长达近300年的入侵与征服。直到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1848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政府获得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大部的控制权。欧洲殖民者对于美洲族裔群体及西南区域的殖民历史,以强权及暴力的方式改变着区域化的文化塑形。
《黑暗的灵》的文本叙事叙述了墨裔族群的诸多暴力事件。小说开篇的警长被杀事件在安东尼的族群引起极大的恐惧:警长查维兹巡逻完毕在咖啡馆小憩时,被杀人嫌疑犯路比托莫名爆头,“完全没有警告的,朝他的脑袋开枪”(16)。这一恶性事件继而引发更大的混乱,查维兹的家人、安东尼的父亲等一干人加入了对路比托的追捕,直至追到河边路比托走投无路。路比托“苦涩扭曲的狞笑”,“一头野蛮困兽的眼睛”(17),“一个饱受折磨男人的哭喊出现在我神秘而祥和的绿色河流上”(18),以为自己被日本兵追击,因而大声求救。路比托的非理性行为引起族群的极大反弹,在族人“一命抵一命”的叫嚣中,来自“古老家族”的族人纳西索坚持以同情与共情之心劝说大家,并且为失去理智的路比托做心理辅导,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混乱中的擦枪走火,路比托丧生于族人乱枪之下的悲剧命运。
安东尼的三个哥哥参加二战得以幸存,回到久违的家乡,每日的生活状态“就像浮肿的动物,呆板重复的过日子”(64),“他们都因为战争而生了病,正在努力遗忘战争”(65)。路比托在绝望之际大喊“日本兵!日本兵!我受伤了。救我”(18),也足以说明战争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作为定居于美西南的古老族群,历史殖民以及现代战争都为族群的生存带来极大危机。与众多美西南的文学家一样,安纳亚并未回避战争的“创伤性冲击”,而是在文本叙事中积极再现暴力的表征。
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从三个方面研究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暴力行为:主观暴力、客观暴力和语言暴力。齐泽克认为,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被体验为一种将非暴力的零层面(zero level)当作其对立面的纯粹暴力,被视为“对事物‘正常’和平状态的扰乱”,是一种显性层面的非理性行为。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则是内在于事物正常状态里的暴力,它是无形的,因为它支撑着“用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标准”(2012:2),是指的社会系统结构性问题。语言暴力则是语言表征系统呈现的表述性符号形式。作为被战争直接侵害的族群个体,安纳亚反映的是遭受战争主观性暴力的个体化表征,但是族群的客观暴力机制却直接导致个体主观暴力的差异性。安纳亚在文本叙事中隐晦地呈现客观暴力的存在,即殖民权力对于族群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和控制,其表现方式迥异于非裔作家批判式的态度,转而描绘族裔群体及个体的自我选择,即主观行为的模式。显然,路比托所遭受的主观与客观暴力的双重压迫,反映了西南殖民史所导致的个体与族群的分裂及认同危机。然而,客观暴力所指涉的族群系统性问题,更多是源于文化殖民的操控与影响。
男性孩童成长的重要仪式是暴力游戏,与所有男性儿童成长类似的是,安东尼与同伴的游戏中包含着打斗与语言粗野的暴力现象,这种模仿性的游戏在培养孔武有力男性气质的同时,训练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从族裔儿童成长的文化基础来看,无疑具有原始主义以及殖民历史的影响痕迹。这种暴力表征的驱动力则是客观暴力的内涵,安东尼的玩伴佛罗伦斯因不信上帝的存在而被认为犯有亵渎之罪,遭伙伴排挤并被施以语言暴力,他发出这样的诘问,“我从来没有要求被生下来。但是他让我生下来,给我一个灵魂,然后让我受到这种惩罚。为什么?”“那他为什么不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或邪恶存在?为什么他不让我们所有人都互相好好对待?他可以让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夏天”(196)。在安纳亚笔下,欧裔信仰的文化暴力是墨裔族群认同焦虑的根源。
安东尼的路卡舅舅被女巫下诅咒久病缠身,起源于路卡舅舅误入族人德纳瑞尔三个女巫女儿的秘密仪式场所而受到报复。安东尼舅舅家无奈求助于家族灵魂人物乌蒂玛,她用草药与黏土混合的药汁催吐,使路卡吐出被施魔法的一团头发。原本简单的拯救事件演变为愈演愈烈的族群极端冲突:德纳瑞尔的女儿莫名丧生,德纳瑞尔归咎于乌蒂玛的巫术,在不断寻仇的过程中与族人纳西索产生激烈冲突,导致纳西索惨死枪下。德纳瑞尔继续一意孤行向乌蒂玛寻仇,乌蒂玛不幸丧生,德纳瑞尔也为恶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系列的情节从表层来看是一连串的族群内部矛盾、报复、仇杀,而其中的深层原因却是信仰与认同的价值冲突。安东尼族群一致认为德纳瑞尔三个女儿操纵的巫术是邪恶的力量,亦有许多族人谴责乌蒂玛的黑暗魔法。原始巫术仪式是人类最早最普遍的宗教仪式,被视为一种准宗教现象, 是原始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巫术与原始主义的关联性,表明的是在前现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欲望。从本质上来说,巫术代表的是一种信仰和人类的精神需求,因为原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极为有限,才形成了具有幻想性质的信仰崇拜,同时在巫术仪式上以一种恐惧化的模仿制造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虚幻假象。巫术仪式往往具有暴力性色彩,包括主观暴力和语言暴力形式,在《黑暗的灵》中,巫术的邪恶性极大地破坏了族群的凝聚力,导致族群的分裂和生命的毁灭。
此外,《黑暗的灵》使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欧裔殖民为墨裔族群施加的信仰同化。以安东尼母亲为代表的普通人虔诚信仰基督教:严格遵循礼拜日的仪式,尊重崇拜神职人员,日常祈祷自律信奉原罪观等等。在经历所有暴力之后,安纳亚的书写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态度,揭示基督教对人类精神的麻醉作用,无力给予个体安慰与精神支持。安东尼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对基督教信仰的各种疑问,“我想让上帝到我的身体里,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纳西索会被杀?为什么坏人不会受到惩罚?为什么他容许邪恶的存在?”(190)。欧裔殖民所植入的信仰观念与安东尼的墨裔族群产生剧烈冲突,安纳亚表面温和的书写方式在深层展现对于文化殖民批判的态度,其价值核心有着明确的指向。
4.神话:自然崇拜与生命认同
安纳亚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他对于历史与神话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创作中也有着充分的借鉴。“我喜欢神话,我喜欢我的族人的口述传统并利用为小说素材,以此反映本土裔经验的重要性”(Sharma, 1994:180)。史密斯认为,“共享的历史记忆”的现象往往由神话的形式来体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而非事实(通常很难厘清)。对族裔认同来说,重要的是虚构的血统和想象的祖先”(2018:31)。学界对于安纳亚小说创作中的神话原型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如海克(An Van Hecke)曾分析了包括安纳亚在内的众多墨裔作家在创作中频繁借鉴的三个墨西哥神话原型:羽蛇神(Quetzalcóatl)、哭泣的女人尤罗娜(la Llorona)和瓜达卢佩的圣母(la Virgen de Guadalup)(2014:61)。羽蛇神是中美洲文明普遍信奉的神祗,据说是长满羽毛的蛇的形象。哭泣的女人尤罗娜源自一个墨西哥传说:一位墨西哥妇女与一个西班牙男子生下三个孩子,这个男子拒绝结婚并转而另娶。墨西哥妇女伤心欲绝,将孩子溺死于河流之中后自杀身亡,河流也因此被赋予神秘、阴暗、含混与复杂的内涵。瓜达卢佩的圣母是有关天主教圣母在印第安青年面前多次显灵的故事。在海克看来,安纳亚将这些神话素材糅合进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再创造式的改写与重构,以赋予古老的神话新的内涵从而展现其历史传承的中心作用。
本文使用的小说译名《河流,黑暗的灵》是基于传统译文《保佑我吧,乌蒂玛》的地域化演绎,尤其明确指向该小说的核心神话意象以及生命支持系统。一方面,河流作为包括亚诺荒原在内的祖地生生不息的源泉,在哭泣的女人尤罗娜的原型中隐喻为创伤记忆和殖民与父权的暴力,在安纳亚的叙事中成为小说人物路比托等的族群个体葬身之地,这种毁灭性的意象终其根源指向殖民暴力的毁灭力量。另一方面,小说呈现了与河流意象相关的另一个神话故事:金鲤鱼的传说。印第安族人在神的恩赐之下来到物产丰美的美西南生活,他们可以享受自然馈赠的一切却唯独被禁止捕杀河流里的鲤鱼。某年族人遇到大旱饥荒,吃光了所有可食之物,不得已将河流里的鲤鱼捕获为食,为此面临天谴。众神之中有一位慈悲的神怜悯印第安族人的境遇,替他们求情从而将惩罚改为把族人变为鲤鱼守护美西南的河流,而这位神则化身为金鲤鱼守护美西南的土地与时代定居的人民。
金鲤鱼的传说在安纳亚的书写中至少具有如下意义。其一,金鲤鱼解释的是奇卡诺族群神秘的创始历史,而奇卡诺族群的墨裔文化作为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一支,其创始文化溯源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兹特克文明的羽蛇神,美西南正是阿兹特克文明所在地。金鲤鱼实际上是安纳亚的文本改写,这种改写无疑更为适应美西南的地域特征,特别是喻指这一干旱区域作为生命维持力量的水意象的重要性。其二,金鲤鱼中的选择、福地、神的惩罚、水的洗礼与救赎等元素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的元素,安纳亚将对西方宗教信仰的质疑和解构,改写为将其融合于本族群的文化传承体系中,凸显其对生命支持的功能,从而达到延续族裔传统和强化族性的写作意图。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通过对古希腊神话及古希腊哲学体系的考察,发展出认识论的基础即诗性智慧。在他看来,神话所反映出的早期人类基于想象力对于人类世界的认知,构建出高于理性思维的具有逻辑化的哲学观。想象力是人类创造力与实践智慧之源,“神话就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这类寓言故事必然就是各种诗性语言的词源”(2006:237),“诗的语言,由于它所运用的诗性人物性格,可以对古代历史产生许多重要的发明”(2006:243)。可见,在维柯的认识论建构之中将神话叙事的诗学效果认同为历史书写。史密斯认为神话体系是联结家族与民族的纽带,作为“族性的这项特质会不断产生向心力”,这种世袭神话最终以回归原生态的方式,解决族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2018:31)。
重要的是,无论是金鲤鱼的传说,或是河流的意象,亦或是羽蛇神的原始崇拜,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意象的自然化特征。安纳亚自称或是学界界定的“兼收并蓄”,实则是以自然化的生存认同原则建构包括生物、土地、人类以及自然万物的命运共同体,抵抗殖民体系对于生命的摧残与毁灭。小说的生命共同体书写不仅在于重构神话传说,更在于魔幻人物的塑造,即安东尼家族的灵魂人物乌蒂玛。乌蒂玛是一位能以草药与魔法治病的巫医,是安东尼族群备受尊敬的“长者”。印第安族群中巫医与药师这类人物,其内涵往往含有“智者之意”,类似于我们现代意义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在现代世界中发掘集体认同的历史根源与族裔独特性的深层含义”(史密斯,2018:116),致力于推动族群个体发现“内在自我”。乌蒂玛加入安东尼家族的时候正是亚诺荒原最为生命蓬勃的时期,安东尼的认知将乌蒂玛与自然景观建立一种对等关系。“她的眼神扫过周围的山丘,而透过它们,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山丘野性的美以及那条绿色河流的魔力。我的鼻孔颤动,感觉知更鸟的歌声和蚱蜢的嗡嗡声跟泥土的脉动融合在一起。亚诺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向我汇聚而来,白色的阳光照在我的灵魂上。我脚底的沙子微粒,与我头顶的太阳和天空仿佛都融合成一个奇特的、完整的存在”(11)。
乌蒂玛经常带领安东尼走遍这片祖地的山川田野,识别各种花草树木,体验大自然的气息,培养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亲密感性。同时以自然的审美体验来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感受自然带给个体的存在感和现实意识,从而获得个人的成长与和生命意识。乌蒂玛还有一个与之寸步不离的守护动物——猫头鹰,她担当着乌蒂玛的信使与守护神,为乌蒂玛执行各种任务。乌蒂玛的生命安危与猫头鹰息息相关,猫头鹰代表乌蒂玛生命与灵魂的寄托,德纳瑞尔最后击中的是猫头鹰,但是却意味着乌蒂玛生命的终结,她留给安东尼的遗言是,“热爱生命,如果绝望进入你的心,记得在风温柔地吹着、猫头鹰在山里歌唱的傍晚寻找我。我会与你同在”(260)。乌蒂玛这样的族群智者具有史密斯所说的“拣选神话”权力,“宗教神话的族群占据了专业人士阶层,他们的地位与视野都与拣选神话的成功和影响力密不可分”(2018:48)。乌蒂玛的一生诠释的是人与自然的同质与一体,自然既代表人类本真的物质生存方式,也是人性本源的体现。美西南的地域特征赋予墨裔文化等本土族裔文化基于自然的生命理解,在应对殖民权力压迫时体现包容性的和解,这即是安纳亚文学创作中对于族性区域化建构的想象,也反映区域书写所揭示的生命认同的本质属性。
5.结语
《黑暗的灵》因当中反对天主教信仰的内容,在美国出版后一度被列为禁书。作为人文奖章颁奖词的补充说明,奥巴马却认为安纳亚的小说及诗歌作品“讴歌了奇卡诺文化经验,揭示人类生活的普遍现实”(Romeo, 2020)。作为奇卡诺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安纳亚扎根于墨裔的族性,再现他所经历并为之强烈认同的族裔经验,但对于安纳亚而言,族性从来不是单一化的存在,“有时我为世界写作,有时我为奇卡诺族群写作”,“我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写作”(Sharman,1994:181),可见他执着于将墨裔的族性与人类群体的本真人性建立同质化联系,体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是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张叉,2018:11)。同时,他的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浓郁地域性,重在表现美西南这个饱受忧患之地的生命气息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彰显文学特殊的审美内涵,并且以对个人、族群、文化的具体关注反过来界定先在的地域。从更为宏观的政治意涵而言,美西南区域性与美国民族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安纳亚族裔书写的区域化想象,能够以见微知著的视野勾勒美国民族叙事,反映文学再现的现实性功能,丰富民族与国家在地性、地域性和跨域性的理解。
注释:
① 本文研究的小说英文标题为BlessMe,Ultima,通常译为《保佑我吧,乌蒂玛》。本文使用的译文出自译著《河流,黑暗的灵》(2015),下文统一简称为《黑暗的灵》。
② 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