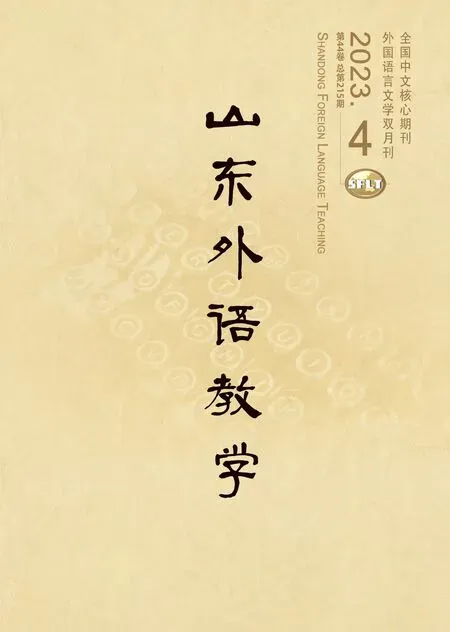中国儿童文学在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英国汉学家汪海岚访谈录
董海雅 汪海岚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83;2. 大英博物馆 币章部,伦敦 WC1B 3DG)
董海雅(以下简称董):汪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与您探讨儿童文学翻译。您以前翻译过余华、张承志等作家的作品,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儿童文学翻译之路的?
汪海岚(以下简称汪):十八岁那年,我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汉语。快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很喜欢翻译,于是毕业后为英国一家很小的独立出版社(Wellsweep Press)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包括张承志的《天道立秋》和余华的《现实一种》。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文学英译作品,是约翰·凯利(John Cayley)开的,他和当时任教于亚非学院的赵毅衡教授共同编辑了两部中国文学集。我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帮他做一些翻译工作。那个年代,翻译作品在英国很难出版,而且出版费用昂贵。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英国译者并不多,参与翻译这两部文学集的译者包括刚毕业的几名大学生。当时中国作家并不富有,参与的译者没有翻译费,如果这两部文学集出版后盈利,收益都归中国作家,而不是给译者,这种运作方式很好,意味着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机会在英国出版。但同时,译者又难以真正靠翻译谋生。我得找份工作,赚钱养家。所以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动笔翻译。
孩子们渐渐长大后,我便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机缘巧合,我与从事汉英文学翻译的韩斌(Nicky Harman)结识。我们经常见面、聊天,共同发起了“中国小说读书会”(China Fiction Book Club),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小说。在一次读书会活动中,韩斌提起艾阁萌(Egmont)英国分公司正在为两部中国童书寻找译者。我很感兴趣,就联系了编辑,得知一部是动物小说,另一部是公主类题材①。我更愿意翻译动物小说,便参加了试译。出版社请六位申请者试译大约一章的篇幅,并支付报酬。我最终被选中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翻译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译作出版后,感觉特别自豪,又激动又开心。可没想到生活一如既往,仿佛波浪汹涌之后,大海又归于平静。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郝玉青(Anna Holmwood)跟我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青铜葵花》。就这样,我开始与曹文轩的作品结缘。
董:您刚才提到的动物小说就是沈石溪的《红豺》吧。据我所知,其他译者要根据您的英文版翻译成俄语、德语、波兰语、瑞典语等七种语言。当时会不会感到压力很大?
汪:这本书之所以要先翻译成英文,再译成其他七种语言,是因为中国是2012年伦敦书展的主宾国,艾阁萌出版集团计划在书展上同步上市《红豺》八个语种的版本。我受出版社委托翻译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约定日期前交稿,因为其他语种的译者都要参照我的译本。老实说,当时我还是个新手,唯一担心的是怎么才能按时完稿。后来,我才意识到沉甸甸的责任。当你在某个领域是新手时,就像小孩子一样,不一定会考虑任务多么重大或有多少风险。
董:您长期从事古钱币研究,学术成果丰厚。很多考古界同行可能对您的儿童文学译者身份并不了解。乍听起来,考古研究与儿童文学翻译似乎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学术文章正式严谨,而儿童文学的语言生动活泼,充满童趣。我很好奇,您的考古研究对于您翻译儿童文学有哪些帮助?
汪:没错,考古文献和儿童文学这两种文体确实风格迥异。我在博物馆从事钱币研究。我们观察钱币时,要非常细致,就像法医一样,必须要对研究对象做出合理解释,还得精确,每一步都必须科学严谨地核实。在博物馆里,通常能近距离地观察展品,观察其大小、外观以及光泽。其实翻译也是如此,必须充分理解翻译过程的每一步,才能驾驭翻译素材。有时需要用心思考,巧妙用词,考虑稳妥才行。如果翻译时随心所欲,就会有远离原文的风险,那不是真正的翻译。这样看来,两者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我觉得主要表现在对素材的驾驭上。对我来说,不论是撰写工作中涉及的非虚构文本,还是翻译小说,这个过程均涉及阅读和写作。不了解语言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就无法翻译文中的文化因素。
董:我听说,您在孩子们小的时候经常给他们读故事,还口头翻译了一些中国故事。请问您翻译时如何把握孩童的语言?您认为儿童文学译者是否要经常接触儿童,或阅读本国的童书,从而保持语言的鲜活?
汪:我觉得有这样的意识很好。不过我在翻译儿童文学时,会比较谨慎,不会刻意阅读与原作题材相近的英文作品,因为我担心自己的风格会不知不觉受影响。至于如何把握儿童语言,我只能尽力而为。译好之后,再重读一遍,如果感觉某个词不对劲,听起来陈旧过时,就换用其他词。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一般来说,童书的编辑熟悉儿童语言,了解市场,也熟悉目标读者。他们偶尔会介入,做出调整。但大多数时候,出版社对我的选词或语言风格还是比较满意的。偶尔,我会就某些词询问女儿的意见,听听20多岁年轻人的想法,这很有意思。不过我基本能自己把握。
实际上,童书也会探讨非常成人化的话题,有的非常深刻、前卫。我翻译时尽量选用恰当的词语,避免用幼稚的语言,因为幼稚的语言有局限性,小孩子可能有一阵子喜欢,慢慢长大了,就不愿意再读了。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语言来翻译,关键在于译者要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要尊重儿童。如果是图画书,也要尊重成年人,因为往往是成年人读给孩子听,否则一本书读上几百遍,会令人厌倦。
董:我们来谈谈您翻译的曹文轩作品吧。继《青铜葵花》之后,2021年您又翻译了《蜻蜓眼》,也是由知名的沃克出版社(Walker Books)出版。两部小说都有一些悲剧元素,透过苦难写人性的光辉和亲情。时隔几年再次翻译曹文轩的长篇小说,您对他的写作风格应该更为熟悉了吧,翻译时觉得更加得心应手吗?
汪:熟悉他的语言并不一定意味着翻译起来会容易,因为两本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青铜葵花》的语言富有诗意,文学色彩浓厚,而《蜻蜓眼》的语言更直截了当,较为平实,非常适合这本书的风格。
董:在《青铜葵花》英译本中,您对叙事风格做了一些调整,删除了一些重复性的描写,而这是原作的美学特征之一。在翻译儿童文学时,您会优先考虑哪些因素?让故事更具可读性,还是忠实于原作的美学特征?
汪:回答这些问题前,我想还是先谈谈《红豺》。如果我把《红豺》的开头直译后拿给英国小朋友看,他们可能不愿意再往下读了。于是我想稍做改动,至少让他们愿意读下去。我翻译第一页第一段时,并没有逐字逐句翻译。艾阁萌的编辑说,他们很喜欢我讲述故事的方式。我当时还是新手,没有深思熟虑,就按自己的想法翻译,因为出版社已经接受了我的试译稿,他们也是读过其他几份译稿后才决定让我来翻译的。不过,后来我着手翻译《青铜葵花》时,却多了几分胆怯,不知道怎样翻译最好。我突然意识到《红豺》译得比较自由,或许不该那样。于是,我向沃克出版社的编辑提议,我先直译《青铜葵花》第一章,让她看看整体效果。待她润色后,我再按照编辑后的风格翻译第二章,向她的风格靠拢。双方对此都感到满意,她就放手让我独立翻译了。这便是我们的合作模式。这样挺好,有助于我了解编辑怎样润色,删减或保留哪些部分,希望意译的程度如何。
从那时起,每次翻译新书之前,我都会询问编辑对译作有何期望,是希望我紧扣原文直译,还是希望译文较为灵活,可读性更强一些。出版社会把要求告诉我,然后我再询问具体的编辑过程。这是因为,如果出版社将对译文进行大量修改和润色,我就先提交更偏重于直译的版本,然后我们再共同商讨打磨。如果他们想要的是精雕细琢、接近定稿的译文,我就会花更多的时间润色。但我尽量遵照出版社的要求来翻译。我会非常谨慎,避免过于直译或意译。我现在的习惯是,先翻译一个非常粗略的初稿,有时会译得比较自由,然后再重译一遍,把自己拉回来,尽可能地紧扣原文。当然,中间还会多次修改。
董:除了这两本书之外,您翻译其他儿童文学作品时,编辑模式也是类似吗?
汪:每本书的编辑模式都不一样,这完全取决于出版社和编辑习惯采用的编辑过程。一般来说,为中国出版社翻译,还是为英国出版社翻译,两者差异很大。中国出版社往往对原作和译作进行详细比对;而英国一些出版社通常没有懂中文的专业人员,收到英译稿后,一般不会再对照中文版查看英文版。我们签翻译合同时,我得保证不会加入任何非法内容,不会让出版社陷入麻烦,或引起任何法律纠纷,保证译文忠实原文。我译完《青铜葵花》后,沃克出版社请人对照了我的英译稿和法语版。其实我翻译之前就知道有法语版,但刻意不去看,因为出版社委托我做中译英,而不是法译英,那我就不该参考法语版。后来出版社经过对照,发现这两个版本有几处不一致,请我再核实。现在具体细节记不清了,不过这是当时出版社把关译文准确性的唯一途径。
编辑过程的快慢也不一样。比如,《蜻蜓眼》英文版的编辑过程很长。2017年我就提交了初稿,这本书直到2021年初才正式出版。翻译时,我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后来,我私下请一个英文极好的中国朋友帮忙看了一遍,看哪里译得不恰当或译错了。我从自己的翻译费中支付一些给她,这纯属私人间的安排。
董:在《蜻蜓眼》英文版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又很特别的现象,您不仅直接用拼音翻译了亲属称谓,如Dagu、Xiaogu、Yeye,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大姑”“小姑”等汉字。而这种“汉语拼音+汉字+英文解释”的翻译方式在《青铜葵花》中葵花教青铜写字那一章里也出现过,您怎么会想到这样处理的?
汪:《青铜葵花》里有个场景,青铜和爸爸去草滩割茅草,偶遇一个叫“青狗”的男孩,他们在泥土上写各自的名字,涉及一个文字游戏,我觉得处理起来很棘手。后来我就琢磨,能不能把汉字放进去?这是一部儿童小说,儿童读者很容易看出汉字的间架结构,即使不认识汉字,也能看出笔画的构成,可以看出两个“青”是同一个字。如果学汉语的英国孩子碰巧看到一个汉字,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会有一种很美妙的感觉,“我认识那个字,我也会写”。于是,我询问编辑,是否可以在英文版中保留原来的汉字。她欣然同意,说只要确保用词准确就行。
中国人的名字尤其难翻。名字通常蕴含一定的意义,有时比较复杂,翻译时如果直接用拼音表示,会让人感觉冷冰冰,了无生气,除非英国读者学过拼音,或碰巧知道拼音是什么,否则不明白名字的含义。这很棘手。当你面对的是一种多维度的语言时,单用拼音远远不够。能在英文版中保留汉字,感觉特别好!把拼音和汉字一起呈现,有助于读者看到汉字的结构和多维度的美,感觉更亲近一些。
董:这样的视觉呈现方式我也很喜欢,可以帮助英国读者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蜻蜓眼》以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时间跨度为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70时代,这段历史对英国青少年读者来说,应该很陌生吧。您翻译时如何处理原文的历史叙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汪:编辑希望我在书的末尾加一个“后记”,简短解释故事中的历史背景。对我来说,写起来其实非常困难,怎么可能仅用1—2页就把长达几十年的历史说清楚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至于如何消除读者对历史背景的陌生感,我并没有采用特殊的方法,就是跟随着故事的发展脉络来翻译。《蜻蜓眼》英文版的目标读者不是很小的孩子,而是大一点的孩子。他们感兴趣的话,会看后记。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就会查找更多资料。我所能做的,只是在翻译涉及中国历史背景的具体术语时,尽可能采用标准英文译名,便于读者日后上网查找更多资料。
董:记得2016年您接受“纸托邦”联合创始人陶建(Eric Abrahamsen)的访谈时曾表达过一个观点,“译者的角色是用英语讲述故事。如果故事暗含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等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应该向编辑提出。”②我在对比了《红豺》的中英文版本之后,发现英文版存在不同程度的删减或改写。请问您的改动是基于个人的判断吗? 还是与编辑协商后做出的决定?
汪:刚才我也提到,我翻译《红豺》时还是新手,经验不足。坦白地说,这本书快翻完时,我才意识到,也许我应该告诉编辑我的改动,我删除了一些我认为翻译后会明显带有对性别或残疾人歧视的语句。因为这些话如果照搬到英文中,歧视感过于强烈。我不确定在中文语境下是否带有歧视意味。我想,如果原作者不是有意为之,我就不该让这些话在英文版中表现得那么强烈。现在离翻译《红豺》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依然记得原文有几处,大致说雌性总是弱于雄性。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原封不动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对当今的儿童读者来说,这很不合适。一次或两次“弱于”也许还行,但并非总是如此。我就改成雌性有的时候不如雄性强壮,或者直接删除。回头想想,假如当时能和中国译者合译这本书,我们肯定会展开精彩的讨论。
董:除了开头一段的改动外,我注意到其实结尾的改动也很大。与原作悲情的结尾相比,英文版结尾塑造的母豺形象明显不同,身体残缺的母豺显得更加坚韧,她下定决心保护女儿,而不是将女儿生存的希望寄托于雄性救星大公狼。请问您的改动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汪:对《红豺》结尾改动,主要还是因为字里行间强烈的歧视感。原作中有两个场景让我深感不安。一个是母豺不断试探未来的郎君公豺,这显然会两败俱伤。那些情节有悖常理,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另一个场景就是结尾。交稿时,我对编辑说,我不认同原作的结尾,问他能否帮我处理这部分。我给他讲了原来的结尾,于是他重新改写了最后两句,改得很好。如果我当时经验更丰富一些,译文可能会稍有不同。不过话说回来,不论翻译什么,下次的译文总会和这次有所不同。
董: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儿童文学翻译与成人文学翻译的明显差异?儿童文学的译者和编辑无疑会考虑译作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考虑对儿童读者的影响。
汪:没错,不仅要考虑儿童读者,还要考虑购买童书的学校、老师和家长等等。他们是守门人(gatekeepers),他们要是反对书中某些内容,就不会给孩子买书,自然会影响出版社的销售。如果一本书含有非常棘手的内容或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就不会有出路。也就意味着不会为出版社带来商业价值,而英国大多数出版社都是商业出版社,需要考虑利润。
董:据我所知,翻译之余,您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介中国儿童文学。2016年,您与瑞典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的馆员陈敏捷共同创办了“华语童书”英文博客网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使英语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童书资讯。我经常关注更新的内容。例如,2021年11月13日“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榜单发布的当晚,您就用英文做了详细报道。请问创建这样一个英文博客的初衷是什么?
汪:在此之前,我已经参与了其他几个网站,其中之一就是“纸托邦”,介绍中国文学相关内容。我很想做一个儿童文学的网站,但我不想独自创办,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与其他人合作会有更多乐趣。我有幸邀请到陈安娜和陈敏捷共同创办。
当时巨大的困境是,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这些作家在中国很有名气。同样,英国人对中国的插画家、童书主题和奖项也鲜有耳闻。如果我给英国出版社推荐一本童书,说这是某位作家或插画家的作品,他们就会问:“这人是谁?”我说这本书获过某某奖项,都是在中国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他们会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就像是未开发的荒原之地。没关系,我想,那我们就把一些相关信息放在网站上,一旦形成文字,就会对别人有帮助。不仅供我参考,还能供别人参考。这样就能打开局面。
我们经常刊登对作家、插画家和出版界人士的访谈,通常问五六个问题,让被采访人先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简单介绍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让他/她回忆自己童年读过的书。这是我最爱问的问题,我和其他读者借此能了解更多。我很感激很多人不吝惜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
董:其实我也从那些访谈中受到不少启发,尤其是对儿童文学译者的访谈。你们为网站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报酬。是什么支撑你们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汪:很高兴你能从中受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我们自愿去做,不愿意的话,就很难做成。最耗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把中文书名、作家和插画家等信息与英文相匹配,这个过程很辛苦。
董:感谢您在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和传播方面的辛苦付出。2017年您喜获中英两国颁发的两个大奖,我很想知道,获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汪: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英国的“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翻译界对我的认可。2017 年该奖项首次颁给从事汉英翻译的译者,这也是最后一届。此后,马什基金会不再设立翻译奖。2017年底,我在上海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能在中国得到认可,我倍感荣幸。我决定用这两个奖的奖金进一步探索儿童文学领域。我在儿童文学或翻译方面都未经过专门的训练,主要靠自学,所以我所了解的知识并不系统。我去希腊参加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大会,去瑞典参加了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的会议,还参与了其他活动,遇到很多业内人士,了解儿童文学领域的运作模式。
董:获奖是否也意味着您有更多机会向英国出版社推荐中国童书?
汪:推荐是推荐,但是否出版最终取决于出版社。不过获奖之后,出版社和编辑确实对我的翻译质量更有信心了。在英国,一般来说,外国童书的影响并不大,不像在中国,有大量引进并翻译的作品。这一点很遗憾。
董:近年来被译介到英语国家的中国儿童小说和图画书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您觉得这主要由哪些因素促成?是否与中国出版社的主动推广以及英国中小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有关?
汪:现在英国出版的中国童书确实有小幅增长。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对中国或中国事物越来越熟悉。学校有“汉语卓越项目”(Mandarin Excellence Program),许多英国人身边都有去过中国或在中国工作的亲朋好友。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项目对翻译的支持。因为英国出版社通常需要得到一笔资助才可能出版翻译作品。现在,有些国家会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富含本国文化的书籍在海外翻译、出版,中国也不例外。有时,英国出版社购买版权后自己安排译者。有时,中方译好之后才卖版权和译文,便于日后使用。美国有些出版社,如雷克拉夫特出版社(Reycraft Books), 直接从中国出版社手中购买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童书,他们稍做调整之后,就直接放入小学购书的系统里。
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衷心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优质童书能被译介到英国,受到读者的喜爱。
汪:我也希望如此。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童书译成英文,我很高兴。用母语阅读另一个国家的故事,感觉很美妙。但与此同时,译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注释:
① 此处指伍美珍的作品《小公主与矮爸爸》。
② 参见E. Abrahamsen. Interview with Helen Wang, Translator of Cao Wenxuan[EB/OL], 2016. https://paper-republic.org/pers/eric-abrahamsen/interview-with-helen-wang-translator-of-cao-wenxuan/. [2023-01-10]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