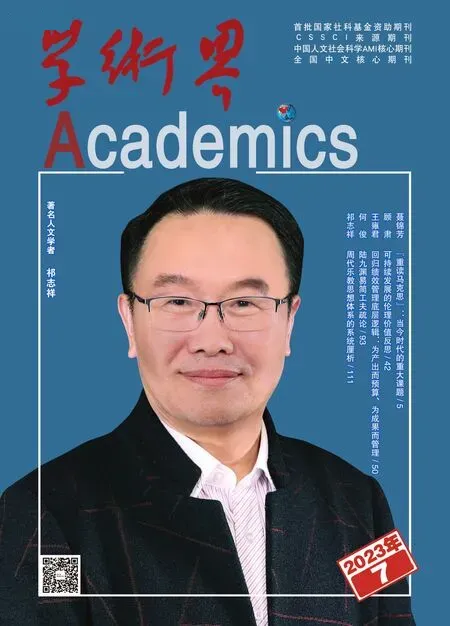宗白华美学思想中“信”与“爱”的悖论〔*〕
刘建平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抗战前后的这一时期,中国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在美学研究上成绩斐然,丰子恺、朱自清以及现代新儒家的方东美、唐君毅等也著述频出,可谓进入了中国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睁眼看世界”、备受凌辱和摧残,而在文化上、价值上始终屹立不倒的信心和勇气。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也大致形成于这一时期,他在1932年所写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一文,标志着其生命哲学和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已经基本成型。宗白华的美学思考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他最重要的美学论文大多写于这一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造成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1〕王国维所言的“最大之烦闷”,曾留学德国的宗白华也感同身受。宗白华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应是富有生命精神的、雄丽的、能对时代精神起到振衰起敝作用的,这是“可信”的一面;然而,宗白华通过他所创作的诗歌向我们呈现的审美理想,却是忧郁恬静、闲和静穆的,这是“可爱”的一面。一边是“舞”的生命精神,一边是“静寂”的审美意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理想“悖论式”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充满了紧张、矛盾与张力。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这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二者又是如何“逆反”地融合在一起的呢?从“可信”与“可爱”的视角出发去探究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及其悖论,能够克服传统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中片面化、简单化、肤浅化的问题,进而揭示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维度。
一、时代危机:宗白华美学思想的起点
宗白华以“流云小诗”“散步美学”闻名于世,其文大多优美典雅、高超脱俗,一般不涉及对现实和时代危机的评论,但在《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2〕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美学思想萌生的时代背景。日寇的野蛮侵略导致了我们民族的贫穷、愚昧、粗鄙、落后,也激发出宗白华对中华民族美丽精神找寻的文化使命,“在唐代却不然了,初唐诗人的壮志,都具有并吞四海之志,投笔从戎,立功塞外,他们都在做着这样悲壮之梦,他们的意志是坚决的,他们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诗人才可称为‘真正的民众喇叭手’!中唐诗人的慷慨激烈,亦大有拔剑起舞之概!他们都祈祷祝颂战争的胜利,虽也有几个非战诗人哀吟痛悼,诅咒战争的残忍;但他们诅咒战争,乃是国内的战乱,惋惜无辜的死亡,他们对于与别个民族争雄,却都存着同仇敌忾之志。如素被称为非战诗人的杜少陵,也有‘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看吧!唐代的诗人怎样的具着‘民族自信力’,一致地鼓吹民族精神!和现在自命为‘唯我派诗人?’‘象征派诗人?’只知道‘蔷薇呀!’‘玫瑰呀!’‘我的爱呀!’坐在‘象牙之塔’里,咀嚼着‘轻烟般的烦恼’的人们比较起来,真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呢!”〔3〕这是我们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时不能忽视的一个出发点。
首先,“救亡图存”的时代危机深深地影响着宗白华,使他对中国美学精神的建构充满时代的忧患意识。早在1917年8月,日军侵占了中国山东青岛,使年轻的宗白华倍感屈辱,他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在家自学了德国文学、哲学,仔细阅读歌德、席勒、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著作和荷尔德林的诗歌,这是宗白华一生哲学、美学思考的开始。1922年,宗白华谈到文学改革的方向时就指出:“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所以我极私心祈祷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呢!”〔4〕他希望艺术家们通过创造出乐观的、雄壮的艺术作品,以唤起我们民族的生命力。1935年,宗白华又在《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中引用邵元冲的话,盛赞文艺作品对民族精神盛衰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在危险困难的时候,如果失了民族自信力,失了为民族求生存的勇气和努力,这个民族就失了生存的能力,一定得到悲惨不幸的结果。反之,一个民族处在重大压迫危殆的环境中,如果仍能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来充实自己,来纠正自己,来勉励自己,大家很坚强刻苦的努力,在伟大的牺牲与代价之下,一定可以得到很光荣的成功。”〔5〕1938年宗白华在主编《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时,也曾深情地写道:“在19年前,‘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灯》应了那时代的三种精神而兴起:(一)抗日救国的精神……今天的《学灯》,仍愿为这未尝过去的时代精神而努力,《学灯》愿擎起时代的火炬,参加这抗战建国文化复兴的大业。”1941年4月宗白华自信地写道:“我们设若要从中国过去一个同样混乱、同样黑暗的时代中,了解人们如何追求光明,追寻美,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化苦闷而为创造,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请读完编者这篇小文。”〔6〕宗白华通过参观敦煌艺术展览,高度赞扬敦煌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热情而灿烂的创造精神,我们今天应该将这种创造精神传承下来,以唤醒抗日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信心。
其次,宗白华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通过对中国美学精神的建构回应西方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冲击,因此,宗白华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鲜明的“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特色,同时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问题,与“五四”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片面地强调“全盘西化”不同,对西方文化有深切体验和研究的宗白华采取的方式是融合、创新,也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收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7〕宗白华在1930年代开始以“艺术意境”为核心,围绕着中国美学精神来展开多维度的研究,这是他利用在德国留学时受到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冲击来解决和分析当代中国美学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1946年,宗白华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一文中激情地呼唤恢复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8〕为了找到中国文化的这种美丽的艺术精神,宗白华对各种艺术门类的特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书法、绘画以其“线条”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原型和风格特征。值得留意的是,宗白华探究中国美学精神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不是孤立地去分析一门艺术,而是重视把各种艺术门类联系起来作整体地观照和共通性地分析,也就是在方法论上有一种“艺术通观”的意识,〔9〕注重联系艺术哲学、审美体验、艺术意境、艺术风格、艺术价值等问题对中国美学精神作一整体的、融合性的考察,多维度推进中国美学精神的研究。
最后,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还包含着对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合法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现代中国传统艺术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汇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大潮、成为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源呢?还是只能成为博物馆里面一件缅怀历史的收藏品?由此问题而延伸到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精神该如何建构的问题。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的合法性问题,其实是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维度。宗白华关注人性问题由来已久,他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至上、精神生命堕落的现状忧心忡忡,这也迫使其在遍览西方社会和文化艺术之后,重新潜入中国传统文艺资源之中,希望能在“诗”与“美”中恢复现代人的感性维度,消弭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移情’就是移易情感,改造精神,在整个人格的改造基础上才能完成艺术的造就。”〔10〕他在发表于1944年1月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中指出:“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显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11〕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阐释和重新建构,就是要以此方式来应对现代社会科技过度发展造成的人性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等现代性的问题,从而使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成为现代人类精神品格重建的重要资源。
二、“舞”:时代精神凋敝的对治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生命哲学思潮,顺应了当时贫穷积弱的中国社会奋发图强的时代潮流,从而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宗白华美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柏格森认为世界的唯一实在是一种向上的、创造的“生命冲动”,生命是一种超越空间、永不停息、无始无终的宇宙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限交合变化中衍化出生命的发展进程,生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源泉和基础。生命哲学思潮暗合了中国人当时求进化的意志,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识有相通之处,因而迅速成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宗白华认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12〕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鲁迅、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朱光潜、方东美等都先后受到生命哲学的实质性影响,甚至借鉴某些生命哲学的基本范畴和原则建构出自己的体系。
宗白华是从创造的视角来看生命的本质,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创造的。每天总要创造一点东西来,才算过了一天,否则就违抗大宇宙的创造力,我们就要归于天演淘汰了。所以,我请你们天天创造,先替我们月刊创造几篇文字,再替北京创造点光明,最后,奋力创造少年中国。我们的将来是创造来的,不是静候来的。现在若不着手创造,还要等到几时呢?”〔13〕创造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本质,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生机、生意的根源,正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赋予万物以精神、活力,“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后所深藏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宇宙活力……所表现。这个自然的活力凭借着物质,表现出花,表现出光,表现出云树山水,以至于鸢飞鱼跃、美人英雄。”〔14〕如果说在西方生命美学传入中国之初,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对西方生命美学持一种“拿来主义”态度的话(如王国维、鲁迅),那么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命美学之间的相契、相合不断被发现和彰显,整合中西方生命思想以创造新的汉语美学的冲动便逐渐占据上风,其结果就是以宗白华、方东美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美学思想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通过对康德哲学、尼采哲学以及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分析,发现东方文化中所说的“生命”精神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生命哲学,“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艺术则给与西洋美学以‘生命表现’和‘情感流露’等问题。而中国艺术的中心——绘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暗’等问题。”〔15〕在这里,他发现“生命表现”和“气韵生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自然观,东方文化把整个自然看作是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因而他们以和平之心来爱护、美化之,并在静观寂照中以自己心灵的节奏契合于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16〕这与西方文化在主客两分、“心”与“境”对立的基础上对自然征服、利用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宗白华不仅反省中国美学因“轻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而导致“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的悲剧,同时也对西方美学持一种辩证的、批判性的态度,“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最近如原子能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撕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精神又要往哪里?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17〕正是通过对中西不同的生命思想的分析,宗白华意识到在我们文化的伟大传统中蕴藏着真正的生命精神,他耗费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魏晋人士简约玄澹的哲学的美,“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18〕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崇拜转而对中国传统艺术生命精神的发掘,这是他美学思想上的一个深刻转向。
作为艺术精神的“舞”直接展示了生命活力,舞蹈所具有的节奏和中断、转折和停顿、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生命精神的具体呈现。在宗白华看来,所有宇宙的生命都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节奏,宇宙的生命可以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灵节奏相契合,宇宙生命的精神最好的呈现形式并不是自然灾难、战争或改朝换代,而是音乐、舞蹈,“音乐不只是数的形式构造,也同时深深地表现了人类心灵最深最秘处的情调与律动……音乐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一镜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19〕舞蹈是整个宇宙生命力量的再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某种神秘的、抽象的哲学概念的象征,苏珊·朗格指出,“一个舞蹈表现的是一种概念(conception),是标示情感、情绪和其它主观经验的产生和消失过程的概念,是标示主观情感产生和发展的概念,是再现我们内心生活的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的概念。”〔20〕艺术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感性的形式把这种不可言说的最高存在或生命的节奏呈现出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文化,都欲在实用生活之余裕,或在社会的重要典礼,以庄严的建筑、崇高的音乐、闳丽的舞蹈,表达这生命的高潮、一代精神的最深节奏……音乐的节律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式,乃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21〕因而从根本上讲,“舞”就是“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艺术家通过创造的艺术作品将这种生命精神呈现出来,欣赏者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也似乎分享了自然变幻无常的生命精神,为生命的力量而欢欣鼓舞。
在1944年《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中,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为“舞”,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22〕“舞”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美学中被称为“生命的节奏”“自然的旋律”,它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也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的体现,艺术作品中舞蹈的身姿、飞动的线条、传神的笔墨、跳跃性的意象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空间意识和生命精神的体现,“在实践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天机活泼,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这就是‘美’与‘美术’。所以美与美术的特点在‘形式’、在‘节奏’,而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23〕通过欣赏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宇宙律动的节奏,进而窥见生命的奥秘,“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24〕林语堂曾把中国书法艺术的这种“舞”的精神称之为“势”,他说:“单纯的平衡匀称之美,绝不是美的最高形式。中国书法的原则之一,即方块字绝不应该是真正的方块,而应是一面高一面低,两个对称部分的大小和位置也不应该绝对相同。这条原则叫作‘势’,代表着一种冲力的美。”〔25〕李泽厚则把“舞”的艺术精神称之为“主观情感的运动形式”。〔26〕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的“舞”“势”以及“主观情感的运动形式”等把生命不可说、不可捉摸的奥秘以这种富有韵律的形式充分显现了出来,人类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最自由最充沛的生命精神,都需要空间供它活动,于是“舞”成为最直接、最具体、最富有感染力的呈现。
“舞”也是中国艺术由“景”入“境”的重要媒介。但“舞”的艺术精神的呈现方式却不拘一格,它是生命力动态的呈现,这尤其体现在花鸟画、动物画中,例如中国历代画家中有不少画马的高手,唐代的韩干、近代的徐悲鸿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善于画出马的奔驰、飞动的舞蹈姿势,“马是被当作运动的速度和运动的美的象征而受到赞美的;它常常被画成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草原上、为自己的力量和敏捷而欢欣鼓舞的形象。”〔27〕与马的形象相类似的还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这是一个行动敏捷、永远飞舞的精灵,是中国艺术通过速度和力量来展示生命之舞的活力的一个典范。在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中国艺术对“舞”这一生命精神的爱好如此的热烈,“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它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28〕以至于中国艺术家们试图把世间所有的艺术形象都描绘成翩翩欲飞的形象。
三、“静寂”:生命精神“逆反”地呈现
宗白华一生追求艺术境界,是典型的诗人型的美学家,他不仅有丰富的审美体验和理论思考,也有《流云小诗》这样优美的诗歌创作。他曾说道:“诗文虽不同体,其实当是相通的。一为理论的探讨,一为实践之体验。”〔29〕然而,我们从宗白华所创作诗歌的艺术风格和他在文艺理论中所追求的审美意境来看,发现两者之间不免存在着“手不应心”“可信”与“可爱”的矛盾冲突。正如前述所论,宗白华在美学上的思考与现实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刚健乐观、生意弥漫的美学观,他将中国美学精神的本质界定为“舞”的生命精神。然而,我们从宗白华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却发现这些诗歌中弥漫的却是另一种别样情调,以《流云——读冰心女士〈繁星〉诗》为例,第二节出现了四个“幽凉”——“心中无限的幽凉”“月的幽凉”“心的幽凉”“宇宙的幽凉”,表达了一种幽清冷寂的情怀;第三节“白雪已消了,弦歌已绝了。余音袅袅,绕入梦里晴天。”以及第六节“城市的声,渐渐歇了。湖上的光,远远黑了。灯儿熄了,心儿寂了。”等也是饱含寂寞抑郁的色彩。在《流云——〈夜〉与〈晨〉》中,第一节“黑夜深,万籁息,桌上钟声俱寂。寂静!寂静!微缈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尽。”第二节“夜将去,晓色来,清冷的蓝光,进披椅席。剩残的庭影,遁居墙阴。现实展开了,空间呈现了……森罗的世界,又笼罩了脆弱的孤心!”类似这样的“幽思”“寂静”“孤心”“清梦”“悲吟”“微光”“微颤”等忧伤的情绪的语词比比皆是,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窥探到宗白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真实的性情。宗白华在谈到这些小诗的创作时曾回忆:“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在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在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30〕宗白华一方面用诗歌创作抒发着孤寂的清凉幽思之美,另一方面又用美学理论书写着他对“光明”“美”和“力”的热爱,这里体现出了宗白华美学思想中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在宗白华的审美理想中,“舞”与“静寂”这两种艺术精神始终奇特、和谐而“逆反”地融合在一起。所谓“逆反”,也就是要体现“舞”,呈现给你的往往是非“舞”的静寂;要呈现空灵,呈现给你的却是“充实”的实在。因而,“舞”的艺术精神另一个特征往往不是通过激烈的动态、挣扎、战争等呈现出来的,而往往呈现为一派优美祥和的“静”的世界,“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法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31〕为了表现这种“生意盎然”的精神,画家常常使用虚实相生这一表现手段,“生动之气笼罩万物,而空灵无迹;故在画中为空虚与流动。中国画最重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且空而后能简,简而练,则理趣横溢,而脱略形迹。”〔32〕唯道集虚,抟虚成实,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代表着中国人于虚空中创现生命流行、氤氲的气韵。中国的山水画看起来是虚静的,但是却又是富有活力和生命的激情的;艺术家通过宁静的自然山水并不是引导我们去寻求逃避世俗烦恼的避难所,而是渴望与那种变化不息的宇宙精神合而为一。“舞”的精神直抵生命节奏的内核,深入发掘人类心灵的律动与深度,呈现为一种说尽人间苦乐、发人之不能言、抒人之不能抒的幽深情怀。宗白华把“舞”的意境称为灵境,“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这种有灵气、有生命的“灵境”,也就是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的生气流行的境界,需要通过“妙悟”才能领会和把握。宗白华对“舞”的艺术精神的发掘不仅契合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也是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现代阐释的重要尝试,他也因此被看作是20世纪继王国维、蔡元培之后第二代美学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这种“悖论”呢?从根本上言之,宗白华喜爱那种恬静、清幽、富有东方情调的美,然而现实中的颠沛流离、政治上的运动冲击、学术上的科学主义思潮等,使得他富有诗情、充满灵性的美学研究很难继续下去,这里仅举两例:1941年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发表之后,介子写了《晋人的颓废》一文对宗白华崇尚个性主义和恬淡自然的美学观念进行批评,“晋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有意无意的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并给后来中国人的萎靡颓废的生活,奠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即就艺术而论,真正的美,也是汉唐的刚健雄伟,生力弥漫,而不是晋朝人的萎靡颓废,矫揉造作。”〔33〕宗白华不得不又写《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34〕进行回应,通过对儒家道德观与礼法观的重释,指出抗战时期最大的危机来自“支配着中国精神和文坛两千年”的“乡愿主义”,从个性自觉、精神解放的诠释进路转向了人性改造、救亡图存,此乃时代精神使然。1936年,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所表现出的时空意识特点的分析,独具慧眼地指出中国艺术“以大观小”的空间意识,不能用西方的科学透视法来审视和解释。1962年,俞剑华批判道:“以大观小之论,实不足信,而其恶劣之影响,则固甚大,以其合于国人夸大之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35〕“论以大观小,颇陷于唯心主义,故加以批判。”〔36〕宗白华本可借机对民族绘画独特的心理机制展开明确而清晰的学理阐述,为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迫于时势,宗白华并未直接回应,只是在1963年写就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轻描淡写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中国和欧洲绘画在空间观点上有这样大的不同。值得我们注意。谁是谁非?”〔37〕这里的“谁是谁非”十分突兀,显然有所指,很值得我们玩味。对宗白华而言,学术上可信者不合时宜,而可爱者又不可信,他不愿卷入时代的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只好以“散步”的美学姿态对抗时代的变乱和残酷,在这貌似洒脱的身影背后,我们除了感受到宗白华未被时代污染的艺术趣味和纯净心性外,还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沉重和遗憾。
四、结 语
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中,宗白华说道:“生命是要发扬,前进,但也要收缩,循轨。一部生命的历史就是生活形式的创造与破坏。生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所以一切无常,一切无住,我们的心,我们的情,也息息生灭,逝同流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这是人生真正的悲剧,这悲剧的源泉就是这追求不已的自心。”〔38〕歌德生活也是充满矛盾的,他对流动不居的生命与圆满谐和的形式有同样强烈的情感,在向外的扩张和向内的收缩上都作了尽可能的探索之后,歌德“以大宇宙中永恒谐和的秩序整理内心的秩序,化冲动的私欲为清明合理的意志”,〔39〕因而,在歌德身上,体现了一个伟大而活跃的生命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宗白华高度赞美歌德积极奋进、不断创造的人生态度,认为他的生命在极端的静中仍潜藏着一个鸢飞鱼跃的世界,“每一次逃走,他新生一次,他开辟了生活的新领域,他对人生有了新创造新启示。他重新发现了自己,而他在‘迷途’中的经历已丰富了深化了自己……他能在紧要关头逃走退回他自己的中心。这是歌德一生生活的最大的秘密。”〔40〕歌德的生命精神就是不断地丰富自我,开发自我,创造新的自我,“浸沉于理性精神之下层的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这里的“理性精神”就肯定了歌德的生命并不是非理性的情感倾泄,在这“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中又包含有秩序、规律和原则,活跃的生命和理性的克制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创造。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之间的这种富有张力的矛盾和紧张也许可以从歌德的生命历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他对中国艺术的“舞”与“静寂”、“空灵”与“充实”等截然不同的艺术精神进行“逆反”式的融合创新,正是其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理解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一把钥匙。一边是“静寂”的审美趣味,一边是“舞”的生命精神;由“静寂”而有神韵气象,静观美感之“空灵”,“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后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它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由“舞”而深厚有力,得真力弥漫之“充实”,二者共同呈现了中国艺术精神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如此,宗白华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艺术一直存在着“初发芙蓉”和“错采镂金”两种不同的美的理想,“鲍照比较谢灵运的诗和颜延之的诗,谓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则是‘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诗品》: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这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41〕这两种美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济有功”的,二者“悖论式”地融合于中国艺术审美理想之中。
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在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时曾大惑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他终于明白:“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42〕宗白华无疑也具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特质”,他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特殊时代,在一个科学主义思潮泛化到艺术理论、思想理论的时代,高举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大旗,坚守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性论,开创了中国古典绘画空间理论研究路向,体现了他试图调和坚持文化主体性的“信”和救亡图存、顺应时代的“爱”之间矛盾的文化自觉。王岳川指出,“宗白华先生是在社会动乱的年代中、在思想压抑的年代赞美这种自由解放的晋人的美,是在战争频繁、世道无情之时呼吁人间深情和激荡出大无畏的精神,是在文化衰堕时期锻造真性情和真血性,这已不仅是颂‘晋人之美了’,而是夫子自道了。”〔43〕宗白华思想“可爱”与“可信”的悖论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特殊时代难能可贵的反省精神和文化主体意识,这也是宗白华美学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注释:
〔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11页。
〔2〕关于《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的作者,学界存在一些争议。台湾学者秦贤次认为《唐》文作者可能是冯白桦,时宏宇认为《唐》文作者是张默君,参见秦贤次:《朱湘·鲁迅·宗白华——30年代中国文坛钩沉》,《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时宏宇:《〈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的作者为张默君——兼与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商榷》,《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本文认同学界普遍的看法,即《唐》文为宗白华所写,《唐》文也编入了林同华编选的《美学散步》和《宗白华全集》。
〔3〕〔5〕〔10〕〔14〕〔16〕〔31〕〔4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48-249、247、174、228-231、59、123、28-29页。
〔4〕宗白华:《恋爱诗的问题》,《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2页。
〔6〕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编辑后语》,《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7〕〔1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102、79页。
〔8〕〔17〕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402-403、403页。
〔9〕参见汪裕雄、桑农:《艺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臆解》,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5-242页。
〔1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356-357页。
〔13〕宗白华:《致康白情等书》,《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41页。
〔15〕〔19〕〔21〕〔22〕〔23〕〔24〕〔30〕〔32〕〔38〕〔39〕〔40〕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43、54、99、366、98、366、155、51、9、7、5页。
〔18〕宗白华:《自德见寄书》,《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36页。
〔20〕〔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页。
〔25〕参见邹宗淼:《中国书法——林语堂灵魂深处的文化情结》,《中国书法报》2016年1月26日。
〔26〕李泽厚认为:“线的形式中充满了大量的社会历史的原始内容和丰富含义。同时,线条不只是诉诸感觉,不只是对比较固定的客观事物的直观再现,而且常常可以象征着代表着主观情感的运动形式。正如音乐的旋律一样,对线的感受不只是一串空间对象,而且更是一个时间过程。”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27〕〔英〕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28〕李泽厚:《美的历程》,第43页。
〔29〕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23页。
〔33〕介子:《晋人的颓废》,《三民主义周刊》1941年第22期。
〔34〕参见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80-284页。这篇文章原题为《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发表于1941年1月19日的《星期评论》(第10期)。受到介子批评后,宗白华将“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补入文中,改名为“《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增订稿)”,分别于1941年4月28日和5月5日发表于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第126、127期)。
〔35〕俞剑华:《画论罪言二十一则》,周积寅、耿剑主编:《俞剑华美术史论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36〕俞剑华:《中国画论选读》,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3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第三卷,第470页。
〔42〕〔美〕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3页。
〔43〕王岳川:《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