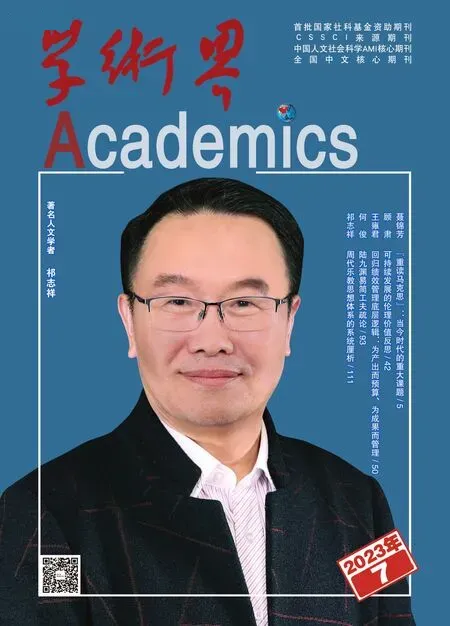生态正义理论的四重建构〔*〕
贾可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生态正义最初来源于环境正义一词,1988年彼得·温茨的《环境正义》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生态正义领域的开创性著作。随着现代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差别逐渐显现出来。所谓“环境”,有环绕在主体周围并为之服务的从属性涵义。环境正义预设了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二分,凸显人类的中心地位,强调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而如何利用自然环境。与之不同,生态正义摒弃了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以自然生态的整体系统为最高关怀,处理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生态要素之间利益和负担的合理安排问题。“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一词是由尼古拉斯·洛和布伦丹·格里森在1998年的《正义、社会与自然》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们指出:“由环境政治所塑造的正义斗争……有两个相关的方面:在人民之间分配环境的正义,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正义。我们把正义的这两个方面称为: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1〕
生态正义研究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尚欠缺系统性的理论著述。截至目前,不少学者仍倾向于将生态正义区分为人际正义、代际正义、国际正义、种际正义等。其实,前三者只是作为社会益品之一的生态资源益品在不同人群主体间的分配,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分配,属于社会正义而非生态正义的范畴。从根本上看,人类社会分配的基本益品往往与自然资源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态性。若将人与人之间有关生态资源的分配看作生态正义范畴,就无法与以人类社会内部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正义相区分。这无限扩大了生态正义概念的内涵,导致其丧失明晰性。社会正义不必然意味着生态正义,因为人类主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可能以合谋侵害自然为基础。社会不正义也不必然意味着生态不正义,因为人类主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并不都与自然生态相关联。因此,应当明确:社会正义研究人类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和负担的分配问题,即人际正义(包括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而生态正义则研究不同生态主体特别是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种际正义。
一、生态正义的动因建构
环境正义以及生态正义思想的出现,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副产物相伴生的。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展示在公众面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显然与现代工业化道路以及社会制度体系密切相关。无论是先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对生态福祉和美好生活的诉求,促使人们检讨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范围的绿色生态运动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持续高涨,推动了生态正义理论的形成和完善。
(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
现代人类文明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上,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一方面奠定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与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生态破坏及其对人类自身的伤害,是生态正义理论产生的根本动因。
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是“控制自然”这一思想意识的结果。西方文明在经历过天人混沌的古代神话时期后,逐渐确立起人与自然主客相分的思维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疾病、洪涝、干旱等自然灾难产生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4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虔诚的宗教信徒同样无法幸免。这令欧洲人觉得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依靠自然或神灵的力量。16世纪的培根“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2〕17世纪笛卡尔关于人与自然的绝对二元论被当作现代科学和现代性的前提。此后,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作为人类力量的表现,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有助于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也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滥用自然造成各式各样的生态灾难。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也往往首先选择消除贫困,维护人们生存的尊严。
技术决定论者以为,科学技术终将能够解决困扰人类的所有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比如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单位GDP的消耗将会下降,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会无限地减少。但“杰文斯悖论”表明,技术改进和管理优化往往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大幅提高,不仅不能实现生产的非物质化,还会使环境进一步恶化。詹姆斯·奥康纳也指出,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并没有将人类从自然的盲目力量的强制下解放出来,相反“它使自然退化并使人类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3〕比如,过量矿物燃料、核武器和核能源、有毒化学制品、生物工程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危险技术的应用,都在威胁着这个星球的生存。
(二)经济关系与利润动机
生态危机及生态正义理论的产生不但与生产力发展有关,而且与社会生产所依赖的经济关系有关,具体表现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都有可能对自然生态造成侵害,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冲突的。资本主义企业关注的不是生产与自然的平衡,而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詹姆斯·奥康纳在大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4〕第一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这一双重矛盾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资本主义重视财富积累而忽视对自然生态所丧失物质能量的弥补,因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断裂,即马克思引用李比希所言“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5〕
消费是经济关系的重要环节。在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影响下,生产厂商宣传诱导消费者过量消费、不当消费,成为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无法在生产领域获得自由,于是便渴望从消费领域获得自由的补偿。在这种思路的驱使下,人们盲目追求消费以发泄对劳动压力的不满,甚至把消费活动置于日常生活的中心。然而,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不会使人真正快乐,因为这种异化消费和人的客观需要相背离,扭曲了需要、商品和幸福的关系。异化消费造成的市场繁荣假象还会导致生产盲目扩张,进一步加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从而成为生态正义的一个引发点。
从分配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加剧生态环境灾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形式平等的竞争机制,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必不可少。但是,自由市场经济以不平等的天赋能力和机遇为前提,在公共产品和外部性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由于资本主义对市场机制导致的贫富差异缺乏根本有效的矫正,社会群体的阶层分化只会愈演愈烈。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往往能享受更好的生态环境,也更容易通过产业转移、居所搬迁等方式规避恶劣生态,而弱势群体通常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的恶果。不同阶层在生态利益问题上存在的冲突,是生态正义话语产生的重要社会根基。
(三)全球化与生态帝国主义
由于人类生存的地球的唯一性以及自然界的一体性,生态环境问题天然具有跨国界特点和全球性质,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体的人都无法逃脱地球生态的影响。生态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全球现象,它不能满足于被限制在特定的国家内”。〔6〕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特征表现得更明显、更直接了。
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扩展,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全球化扩展。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和环境,往往凭借自身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把污染严重的工厂搬迁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贫穷国家变成有毒废弃物的抛放地,将生态成本转嫁给第三世界人民。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有害垃圾中,约有90%都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发表题为《让他们吃下污染》的文章,认为从经济收入和污染成本的角度来看,欠发达国家的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生命价值要比发达国家低,同时欠发达国家对污染的承受力更强。因而,应当允许和鼓励将污染转移到第三世界。这种公开支持生态帝国主义的言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批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本国需求,还不断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当中“居住着全球大约25%的人口,但却消费75%的全球资源”。〔7〕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由于自然资源的毁灭而崩溃,或被迫依附于生态帝国主义国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衰竭、可再生性资源的减少以及对全球民众生存权利的掠夺”。〔8〕约翰·福斯特批评资本主义“将新陈代谢断裂扩大到全球层面,产生了各种全球不平等和生态矛盾”。〔9〕生态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全球北方欠全球南方一笔巨大的“生态债务”。生态帝国主义造成生态破坏和全球分裂,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强烈反对,全球性的生态正义也随之提上日程。
二、生态正义的主体建构
对于何者构成生态正义的主体,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环境伦理学大致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蕴含着生态正义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在此基础上,温茨提出了“同心圆”式的环境正义理论。按这一理论,人们优先考虑那些离自己较近的人(如家庭成员),而后考虑那些离自己较远的人(如外国人或其他物种)。“我们与某人或某物的关系越亲近,我们在此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数量就越多,并且/或者我们在其中所承担的义务就越重。亲密性与义务的数量以及程度明确相关”。〔10〕就生态正义而言,假如将生态主体比作同心圆,那么,居于同心圆中心的是我们人类,居于同心圆外围的是非人类生命及非生命自然,此外还有作为同心圆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
(一)核心主体:人类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被看作唯一的生态主体和价值主体。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作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11〕自然对于人类只有工具价值,人类对于自然之物不负有道德义务,这种人类中心论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其依据主要有:一,灵魂优越论。如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朽是人优越于动物的标志,上帝赋予人类以大自然的管理者的特权。二,理性优越论。如康德认为具有理性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罗尔斯也认为自然界的非人动物缺乏理性合作能力而无法成为正义共同体的成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自然除了为我们所用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12〕20世纪70年代以后,鉴于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重,古典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向现代“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美国学者布莱恩·诺顿认为应对人的需要进行合理性审查,只有经过审慎思考的需要也就是理性偏好才是值得肯定的。
无论是“强”或“弱”的人类中心主义,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一切以人为中心,否认自然界其他主体的内在价值,把自然界看作供人索取的仓库。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促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同时也可能导向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造成生态破坏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困境。有人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乃是基于人类的无比强大。然而,强大未必意味着中心地位的合理性。假如智慧和能力超过人类的外星生物莅临地球,我们是否会按这一逻辑,将更强大的外星生物视为中心,心甘情愿为其所囚禁和奴役呢?恐怕多数人不会认同这一点。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是:人类无论如何不可能摆脱自身视角,不可能真正为了自然界的利益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而保护生态。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人类不能摆脱自身视角不等于以人类为中心。比如父母是以自身视角来照顾婴儿,但不能说这种照顾是以父母为中心。一个深陷爱河的人是从自身视角看待恋人,但完全可能以恋人而非自己为中心。因此,生态正义在主体建构过程中,首先是从居于核心地位的人类物种出发,因为人类毕竟是生态系统“最精致的作品”。〔13〕但同时必须打破人类中心论的局限,向更广阔的主体范围推进。否则,我们就很难关照那些远离人类圈子中心的人或物并为其主张正义。
(二)外围主体:非人类生命
约翰·罗尔斯认为,人类对有知觉物种具有同情的责任而非正义的责任。不过,在罗尔斯的理论设置中,那些有知觉但不完全具有道德能力的人——例如智障人士或婴幼儿——同样被包容进正义体系。按此逻辑,我们也应为与之有相似知觉能力的其他生物保留空间。也就是说,非人类物种可能缺乏善观念和正义感,但这不是非人类物种成为生态正义主体的障碍。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人类与大多数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人类与灵长类动物具有共同血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其他动物的道德地位。〔14〕其次,现代的一些科学发现证明:非人类生命具有某些形式的感知能力和自我意识,即便是植物也并非被动的对象,而是存在与外界的互动关系和感知、反应行为。这些特征为它们的道德地位奠定了基础。人类本身其实就是宿主与微生物共生的复杂生态系统,人体中的微生物细胞数量是人体自身细胞的10倍之多。此外,如布莱恩·巴克斯特指出的,是否成为生态正义主体不一定要基于特定的善和正义观念,而可以基于候选者是否在其中拥有特定利益,有利益则有权利。以智障人士为例,虽然他们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但无端致其死亡无疑是对其利益的损害。如果这种“利益—权利”论是有道理的,那么将这种伤害的非正义性归于同样缺乏知觉的非人类生命也是有道理的。非人类物种“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或回报道德关切,不能成为他们被排除在正义之外的理由,就像排除处于类似情况的‘不善言辞’的人类一样”。〔15〕戴维·施洛斯伯格认为:“正义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可以只是正义的接受者,而不必同时是正义的接受者和实施正义的主体。”〔16〕正义共同体概念的这种延伸是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
虽然人类和非人类生命都可以成为生态正义主体,但他们之间不是完全平等的。由彼得·辛格、汤姆·雷根、阿尔贝特·施韦泽等一些生态学家敬畏生命的思想出发,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生命平等主义。在特定情况下,各生态主体有可能相互依存而结成平等的利益共生体。但更多例子表明,不同物种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一些生物将其他生物作为生存资源。例如,草是羚羊的营养来源,羚羊又是狮子的营养来源。一种生命形式的实现可能会破坏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实现,因而生命平等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道德立场。如果按照极端的生命平等主义的逻辑,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价值而不受侵犯,则地球上的大多数生物都将因失去食物来源而死亡。在自然界中,“食物链是一个使能量向上层运动的活的通道,死亡和衰败则使它又回到土壤。……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环路”,〔17〕物种的每一个层级都依赖于下一层级为其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按此,人类作为理性能力最强的地球物种,可以在必要的条件约束下,利用、改造自然和其他生命体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三)系统主体:自然生态
生命中心论者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生命,奥尔多·利奥波德、阿伦·奈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等生态中心论者则进一步将其扩展至整个自然界。罗尔斯顿指出,“在大自然中,生态系统有规则地自发地产生着秩序;在丰富、美丽、完整和动态平衡方面,这种秩序要比该系统任一组成部分的秩序高出一筹”。〔18〕马克思亦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19〕强调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0〕如果承认自然作为生态主体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并尝试理解它。自然不会像人类和某些生物一样“说话”,但正如人类除语言之外还依靠身体和表情的交流,自然界也可以通过很多信号而非直接话语来表达意思,特别是一些负面表达如地震、酸雨、沙尘暴等。如约翰·戴泽克所说:“通过聆听来自大自然的信号并与之交流,人们将不但成为社会人而且成为生态公民。”〔21〕
生命体与无生命的生态主体没有截然的界线,刻意加以区分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例如落叶虽已非生物,但通过堆肥发酵以及与其他有机物质的互动,能够产生新鲜肥沃的土壤以及附着于其中的各种微小生物。自然界的一片土地、一条河流并非只是物理学、化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与许许多多肉眼不可见的生物融为一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土地、河流等自然物实质上是能量的源泉,这能量在土壤、植物和动物之中循环流动,维持着生物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生物群落的完整。2017年,新西兰宣布旺格努伊河为生物实体——这是世界上第一条享有人类权利的河流,印度亦宣布恒河及其支流亚穆纳河为享有人类权利的生物实体。同是在2017年,一个名叫索菲娅(Sophia)的机器人成为世界上首位被授予合法公民身份的机器人。这些新现象的出现,预示着作为生态主体的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边界日趋模糊。
有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而不是人置于中心地位,把自然视作人类的主人,有可能导致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人类,如戴维·佩珀批评生态中心论可能导致一种“反人类主义”。〔22〕马迪·尼尔称之为“极权主义”,埃里克·凯兹认为它破坏了对个体的尊重,汤姆·雷根甚至将利奥波德的理论称为“环境法西斯主义”。〔23〕然而,这些观点是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误解。生态中心主义并不枉然牺牲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而只是在物种或个体利益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作出的选择。为减少歧义,可将“生态中心主义”改称为“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习近平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4〕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分立相争而是内在一体的共生关系。
三、 生态正义的价值建构
完整的生态正义体系应以一定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原则。当然,这种价值建构仅是针对具有高度理性而成为“地球管家”的人类而言的,其他生态主体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执行价值理念的要求。立足于“只有一个地球”的现实,生态正义应当促成人类行为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符合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永续发展。内在价值原则、生态平衡原则、永续发展原则构成了交叉、递进的价值体系。
(一)内在价值原则
价值通常是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范畴。这里的主体和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生态主体;可以是相异的,也可以是合一的。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整体主义承认并尊重一切生命体、非生命体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价值。系统价值在所有价值中居于最高地位,因为“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25〕“创生万物的生态系统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现象,尽管人类是这个系统最有价值的作品”。〔26〕在生态系统中,“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它的价值也不可能高过整体的价值。客体性的生态系统过程是某种压倒一切的价值”。〔27〕自然产生了具有价值的主体,就表明了自然的价值所在。非人类自然即便是无生命的存在物,就其孕育和进化出生命而言,也不能说是无价值的。一条河流能够满足一些鱼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是河流相对于鱼类的价值。“牛奶或者一头鹿具有某些种类的价值——工具价值、审美价值,或是一些其他类型的价值——而不管人类存在与否。”〔28〕此外,某一生态主体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对其他生态主体的意义和效用,而且其自身生命的完满和延续就是一种内在价值的展现——此时的价值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从自然生态的演变进程来看,某一生态主体的价值也并非依赖于人类。“大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good)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各就其位。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承载者。”〔29〕如果人类只是居于整个生态进化过程中的一小段,那么人类就没有资格以自身为界划定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边界。随着生态系统的进化,即便人类灭绝,也可能孕育出新的高级生命,这些新生命的价值观当然也不可能以人类的价值观为据。总之,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内在价值不依赖人类等生态主体的主观需要和感觉而存在,具有不以他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的理性是事物之价值被“发现”的依据,而不是价值“存在”的依据。作为主体的人是价值的“翻译者”,但不能认为“价值的呈现必须以翻译者的存在为前提”。〔30〕
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价值是某一生态主体在道德上应受尊重的依据,因而也是权利的基础。所有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主体都有相应的生态权利以维护其价值的实现。有人以为人类之外的生态主体无法履行责任因而不应拥有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新生儿不可能有责任意识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由于不同主体的生态权利存在矛盾和冲突,也就有了生态正义存在的必要。根据权利的能动性和丧失后所可能导致的伤害程度,可以认为:生态系统整体的权利优先于生态个体的权利,生命体的权利优先于非生命存在者的权利,具有较高知觉能力的生命体的权利优先于较低知觉生命体的权利。按照这种序列,人类在生态系统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也享有更多的权利。
(二)生态平衡原则
生态平衡是以整体生态系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调和人类以及非人类生态主体的价值与权利,实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如前所述,不同生态主体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不是平等的,生物个体和个别物种有时可以被消除——比如蚊虫和某些病毒,但总体生态系统应当保持平衡和运转的能力。如利奥波德对土地伦理的表述:“当一件事倾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31〕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描述的则是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恶果:在一个能被许多牧民共同使用的公共牧场,想增收的人可以随意扩大他们的羊群和牛群。随着公共牧场上的动物越来越多,牧场内的植被会因为过度放牧而彻底消失。结果所有人赖以维生的牧场这一公共资源以毁坏告终。“很多环境资源就像哈丁故事中的牧场一样。海洋、空气和臭氧层对我们而言就像牧场对牧民一样重要,但没有人可以拥有它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利用或掠夺这些自然资源,但从长远来看,每个人最终将受到伤害。”〔32〕
维持生态平衡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积极的方式需要人类创造条件来支持生态主体特别是某些动植物的繁荣,例如帮助那些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动物找到新的栖息地。这对人类的工作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这种积极的维护方式会遇到一个问题,即不同生态主体的需求可能互相矛盾,无法同时予以满足。而消极的方式只需要人类不抑制繁荣即可,即履行不伤害其他主体的消极义务,不干扰野生动植物的生活,不破坏它们的栖息地。也即“不增加痛苦”,而非“减少痛苦”。〔33〕对消极意义的生态正义的把握,有助于避免一些对待个体动物的深层冲突,比如所谓“猎物—捕食者”的问题。〔34〕按此,当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捕食羚羊时,没有必要人为干涉或制止。综合起来看,维持生态平衡应以消极方式为主,积极方式为辅。如果生态平衡已遭到破坏并出现生态退化,则需要采取生态补偿的积极措施尽量予以恢复,比如中国在西北地区持续多年的退沙还林工程。
(三)永续发展原则
生态正义的内在价值原则和系统平衡原则可以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实现,比如原始社会。而永续发展原则是一项更为积极、更具开拓性的原则,它允许人类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为了生产力发展而消除个别生态主体或打破原有平衡,比如捕杀野兔、开垦土地等。当然,最终必须能够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重建新的平衡,否则永续发展就无法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伴随着“生态平衡—打破平衡—重建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谨记恩格斯的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5〕这种报复往往表现为事与愿违和前功尽弃。因此,在暂时打破平衡时必须谨记重建平衡的目标。永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大致相同,差异主要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可能是最低标准的,而永续发展的持续意味更强,对生态保护的要求更高。永续发展原则蕴含着代际的生态正义要求。如罗尔斯所说,原初状态中的人们“作为家长,……希望推进他们的至少直接的后裔的福利。……希望所有的前世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将成功地从合理的条件派生出对其他世代的义务”。〔36〕
永续发展包括生物多样性状态的维持和发展。尽管在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规律作用下,多样性生物的构成会发生变化。这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永续发展是相互助益、不可分割的。如彼得·温茨指出:“基因多样性使某个物种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回应。如果物种成员间在很多方面彼此各不相同,那么新环境出现时,可能某些成员的适应性会很强。适应性强的成员继续茁壮成长,确保了物种的延续。然而,如果基因多样性降低,而且同一物种成员间差异很小,那么,对某些成员致命的新环境也会给全体成员带来毁灭。……这将成为一个灾难。”〔37〕在约翰·福斯特看来,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还将使人们“失去为我们提供新食品、新抗癌药品以及其他产品的基因库”。〔38〕鉴于其重要性,“尊重地球和生命的多样性”已经被《地球宪章》(即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
四、生态正义的路径建构
当代生态危机既直接体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也间接涉及人与人的矛盾;既有生产力的问题,又有经济关系的问题;既与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相关,又与社会制度设计有关。由于生态问题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外部性,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因此,消除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正义,必须从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变革入手,谋求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相结合。生态正义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建构生态正义的主体只能是具有高度理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必须从作为“地球管家”的人类的视角出发,确定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制度方案。
(一)代理式生态民主
作为程序正义的生态民主是建构生态正义的基本路径。所谓生态民主,主要是指由生态系统的各个主体通过民主商谈的方式,确定相互间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显然,除了有理性的人类之外,其他物种是无法参加到这一进程中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民主走不通。生态民主如同社会民主,未必一定是直接的参与式民主,而可以是代议制或代理式民主。正如不善言辞的人需要代表一样,不能言辞的非人类主体也可以通过代理的方式解决。“通过掌握关于非人类主体利益的知识,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产生代表的合法性”。〔39〕也就是说,对那些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生态主体,可以由具有理性、愿意维护非人类自然的人代替其发表主张,表达利益诉求。至于这种主张和诉求的内容,可以通过经验和实验对其他物种加以了解而发现。对自然的破坏体现在大量生态信号中,例如鸣禽更早返回,动物向北迁徙,冰川融化,某些地区雨量增加、其他地区更加干旱等,所有这些“警告”加起来就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化。〔40〕这样,自然就可以通过“人类代理”而成为民主进程的一方,进而实现其利益诉求。这种“实现非人类自然代表权的机制与将非人类自然的内在权利写入法规相辅相成——即自然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承认”。〔41〕这种虚拟的代理民主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例如,美国许多州要求在有生态争议的设施获得许可时,在当地成立咨询委员会以使公众彻底和真实地参与这些过程。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成立了一个“有毒物质委员会”,包括来自环保界和工业界的代表,在监督有毒物质管理和向公众发布信息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42〕
现实中各种保护生态和为自然争取权利的运动也是生态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在理论上可以作出区分,但在实际运动中经常相互重合。与理论家相比,实践活动者往往采取实用的态度和多元化的理论指导。比如大卫·施洛斯伯格提到,在使用回收废水在本地印第安部落的神山修建滑雪场的案例中,很容易看到基于分配(印第安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环境损害)、承认(缺乏对部落文化的认可)、参与(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和缺乏部落语言材料)和能力(对部落保留文化和教义的能力的影响)的环境正义观念。还可以看到基于分配(水从一个流域转移到另一个流域)、承认(自然过程被忽视)、参与(没有受影响物种或社区的利益的代理人)和能力(掺有药物的水会对当地动植物的繁殖产生影响)的生态正义观念。所有这些都同时存在于一个造雪方案中。〔43〕吸取生态民主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其理论多元化策略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人们包容他者,推动生态正义理论的发展。
(二)革命性生态制度
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革命性的制度变革。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找到出路。如马可·毛里齐所说:“应该把反对物种主义同反对资本主义统一起来,这两方面其实是同一种斗争”,〔44〕即反抗压迫的斗争。马克思亦曾对未来社会作出展望:“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5〕
这种革命性制度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生态产权关系的认定。一个生态正义的地球是所有生命群落的共同家园,不为任何物种所私有。“人类对地球不拥有任何(全部或部分)原始所有权”,〔46〕这是生态正义的理论前提。人类的出现晚于生态系统的出现,并且晚于很多其他物种的出现,怎么能够说一个在人类之前就存在、产生了人类,而且很可能在人类消亡后仍然存在的事物归人类所有呢?更准确的说法是自然拥有人类,而非人类拥有自然。当然,终极所有权的无主性(或生态系统的自有性)不代表占有权和使用权也没有主人。马克思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47〕由此可以认为,人们常说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指占有权和使用权(可合称为占用权)。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和条件的社会化,其实是指对于生产资料和条件的占用权的社会化。在生产资料占用权社会化的基础上,采取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可以遏制资本的过度逐利,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社会生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标,人与自然的矛盾有望得以化解。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要求。高兹认为“只有当民主决策优先于追求利润和经济权力时,经济才会对生态和社会负责”。〔48〕奥康纳提出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实现工人参与管理,“将某种生态的、积极的实质内容灌输到自由民主的外壳中去。”〔49〕奥康纳还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主化程度不够:其一,劳动阶级没有就某种环境问题自主组织和讨论的自由,导致了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和冷淡情绪。其二,缺乏对污染水平的公共信息披露机制,“消极的外在性”或“社会成本”常常得不到恰当的确认。此外,社会主义“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的强制规定削弱了通过组织技术革新来节约劳动的积极性”,〔50〕因而也就安于以较高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现状。若工人以适当方式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将会极大地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劳动而非消费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经济民主的要求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生态问题的解决均具重要意义,是生态正义的制度化建构所应认真考虑的。
(三)绿色化生态劳动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要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经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同时将产生的废料向自然排放,实现新陈代谢的循环。在这种劳动的过程中,人类既可能维持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也能导致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破裂而引发生态危机。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要实现生态平衡和永续发展,都必须以劳动的生态化作为中介,借助生产劳动的绿色转型,减少和化解人对自然的破坏。所谓生态劳动是指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循环作为衡量标准,在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三个方面实现绿色化、生态化。劳动者的生态化主要是指作为劳动者的人树立生态共同体观念,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自然生态,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损害自然生态系统。劳动对象的生态化是指自然生态不仅是人类加工改造的自然物,而且具有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身价值,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劳动对象生态化的要求。劳动工具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中介,具有放大劳动者力量的作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它的生态化变革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重大影响。
科学技术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实现科学技术绿色转型并对劳动过程赋能,有助于促进劳动者生态科技能力的提升,促进劳动对象范围扩大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工具的清洁化、高效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产品能耗,有效保护生态。与之相比,一些绿色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化手段如碳排放权交易等,并不能对解决生态问题起到根本作用,因为它们只是改变了污染排放的主体,污染本身并不会减少或停止。
(四)差异性生态责任
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生态问题天然具有公共性和无界性特征。生态问题的成因和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因而其治理也必将是全球性的。当前,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以全球环境问题为重点的国际框架公约和议定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在组织机构方面,除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官方机构外,还有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许多非政府环保组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原则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成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的一项普遍原则。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即所谓“共同责任”。一方面,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排放总量不同、人均排放量不同、污染治理能力差异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的大小是不同的,即所谓“有区别的责任”。应将第三世界的“生存性排放”和发达国家的“奢侈性排放”区别开来,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并向第三世界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最主要的就是消除清洁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障碍,解决技术转让成本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对大自然进行肆意破坏。一些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另一些国家却无视自身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于国家责任的规定具有不确定性,这可以成为调和不同国家冲突的润滑剂,也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推脱责任的理由。尽管国际集体行动困难重重,但各国通过谈判分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然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
2015年《巴黎协定》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值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争取1.5摄氏度之内),世界各国尽快实现碳达峰并于21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和。巴黎大会之后,一些法学界人士起草《世界环境公约》,旨在确立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巩固全球环境治理的框架。如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将成为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第三个综合性的世界公约,进而为环境权(生态权)的确立奠定基础。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有人提议在联合国建立一个具有与世界贸易组织同等权力的世界环境组织,比如国际环境法院。但这还远远不够。鉴于全球和平、发展以及生态等问题盘根错节,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一个具有法定强制力的世界政府。 “在一个体现人权和非人类世界权利的宪法下的世界政府最终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为人类文化和自然生态的最大多样性的繁荣提供一个公正的框架”。〔51〕面对生态危机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统一的世界性政府的诉求或终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注释:
〔1〕〔31〕〔51〕Nicholas Low,Brendan Gleeson,“Justice,Society and Nature: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Routledge,1998,pp.2,139,192.
〔2〕〔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3〕〔4〕〔8〕〔49〕〔50〕〔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藏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0-321、275、13、401、4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页。
〔6〕〔15〕Brian Baxter,“A Theory of Ecological Justice”,Routledge,2005,pp.156,119.
〔7〕〔美〕约翰·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刘仁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1页。
〔9〕Brett Clark,John Foster,“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2009,pp.3-4.
〔10〕〔28〕〔32〕〔37〕〔美〕彼得·温茨:《环境正义论》,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2、172、12、34页。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1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13〕〔18〕〔25〕〔26〕〔27〕〔29〕〔30〕〔3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9、235、268-269、306、259、4、159、80页。
〔14〕Brian Baxter,A Darwinian Worldview:Sociobiology,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Work of Edward O.Wils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141.
〔16〕〔21〕〔40〕〔42〕〔43〕David Schlosberg,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Theories,Movements,and N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8-119,191,192,208,172.
〔17〕〔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19〕〔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185页。
〔20〕〔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559-560页。
〔22〕〔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北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23〕〔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杨官明、林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
〔34〕〔46〕Anna Wienhues,Ecological Justice and the Extinction Crisis,Bristol University Press,2020,pp.65,174.
〔3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38〕John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25.
〔39〕〔41〕J.Gray and P.Curry,“Ecodemocracy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Non-human Nature”,in Helen Kopnina,Haydn Washington ed.,Conservation: Integrat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Springer,2020,pp.158,164.
〔44〕Marco Maurizi,Beyond Nature:Animal Liberation,Marxism,and Critical Theory,Brill,2021,p.1.
〔47〕〔美〕约翰·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48〕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Verso Press,1994,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