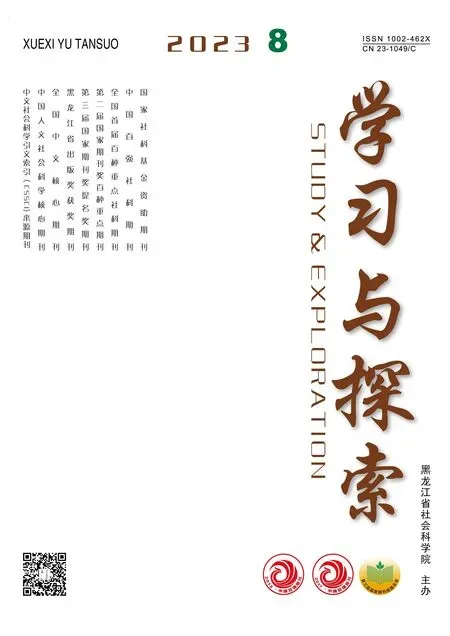德性政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权力合法性的再造
郭 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巴龙(Hans Baron)、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西方权威学者都认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共和主义自由”。然而,哈佛大学著名学者韩金斯教授(James Hankins)在其最新著作中提出,“共和主义自由”是一个次要的主题,并且人文主义者已经摆脱了共和、寡头等政体思想的羁绊。较之于优良政体的具体类型,人文主义者认为统治不善的症结不在于政体的类型,而在于统治者缺失“德性”,不仅在道德与政治论著中,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德性”的身影,因此人文主义的政治说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政治”[1]xxi。本文在认同韩金斯教授这一总体性论断的基础上,以人文主义者审视权力的视角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关于德性的论述,从彼时的德性与高贵之辨、德性与法律的关系、德性与荣誉的塑造三个方面剖析德性之于人文主义者的重要意义及其内在的政治逻辑。
一、开辟合法统治的新路径
自古典时代起,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有多重来源,诸如民众认可、世袭特权、君权神授,以及承袭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各种思想传统。然而,在14—15世纪,意大利政治局势的转变使得权力合法性的传统源头趋于枯竭。一方面,随着罗马教廷权威的日渐式微,“君权神授”愈发遭受质疑;另一方面,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出身卑微,彼时的“新君主”为了确立合法统治而努力做着各种尝试,他们操纵公社选举,拉拢大行会,通过政治联姻获取贵族身份,编造具有世袭高贵血统的族谱,甚至不惜直接充当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这些策略无法从根本上让人民自愿地接受其统治,欣欣向荣的和谐城邦更是无从谈起。于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再度浮现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舞台,成为在各国宫廷效力的人文主义者关注之焦点。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权力合法性的新源头。醉心于搜罗古典著作的人文主义者很快便将目光锁定在古罗马人身上,古罗马的历史为人文主义者重新诠释统治权力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尽管在14—16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中,除了威尼斯之外,几乎没有哪个能够像古罗马那样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维系长治久安,但这丝毫不影响人文主义者以古罗马为榜样。即便当西罗马帝国覆灭近千年后,但丁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依然主张“罗马人生而治人”[2]43。在但丁看来,罗马人拥有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具备的高贵德性,这是一种渗入基因的决定性优势。
然而,人文主义者发现他们无法把罗马人合法统治的标签直接贴到意大利各城邦的统治者身上,而必须针对当下的状况有所变通。此时的君主、城主或寡头统治者鲜有良好的出身或高贵的血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僭主”,因而人文主义者根本不可能以“生而治人”的基因论为他们的统治寻找依据。比如,米兰的维斯孔蒂和斯福尔扎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乌尔比诺的蒙特菲尔特罗家族等最初都是从戎军人,作为雇佣兵队长厮杀征战才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可想而知,人文主义者想要证明他们的统治像古罗马皇帝那样正当,或许唯一能够被接受的说法就是,这些人的统治恰恰是为了复兴古罗马的传统,但他们绝非古罗马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换言之,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新君主”的权力不是源自对古罗马人统治权的接续,而是历经断裂之后的重拾。
那么,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古罗马的历史,为当时带有头衔缺陷的“新君主”提供合法统治的新依据呢?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方案是,合法性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正当地施行权力。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僭政与所谓的“合法”统治在法律层面上的差异无足轻重,将两者彻底区分开来的关键在于施行权力的方式,哪怕是君主国,只要统治者道德不端,同样也该下台,“最具德性的统治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危害性最小的统治者,一定是懂得如何正当施行权力的人”[3]180。
另一位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蒙特马尼诺(Buonacorso da Montemagno)在论及高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时同样指出:在良好的共和国里,个人拥有的荣耀和地位不会根据其家世宗族的高贵来论定,哪怕他的祖辈居功至伟,唯有自身博学多才、充满智慧和德性之人才配得上统治的权力[4]40-52。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尔多(Leonardo of Chios)关于高贵的论调则更加直白,他将传统世袭的高贵视为虚假的高贵,真正的高贵只源于自身的德性。高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浮于表面的、一般为世人公认的高贵,这种高贵通常与财富、古老的血统、世袭权力如影随形;另一种则是更为纯粹的高贵,它不惧世俗目光的评判,它不因贫穷而卑微,这种高贵的每一寸都因充满德性而熠熠生辉……任何拥有这般高贵的人等于被赋予了智慧和美德,这样的人更加适合治国理政[5]118-119。
显然,人文主义者提倡的统治合法性与高贵、德性密不可分,能够正当行使统治权力的人必须具有“真正高贵”。财富与门第无法推衍出合法的权力,唯有当权力与德性相伴时才能拥有真正的高贵;哪怕是皇族出身,也需同时具备理智与道德才算合法,只有这样才能让被统治者心悦诚服。人文主义者所谓的“真正高贵”意指基于德性之上的统治技艺,由此赋予了政治观念以伦理道德的意味。在早期人文主义者那里,权力就这样自然巧妙地与德性挂上了钩。那些有钱有势、出身名门的人,只有当他们自己也具备德性时,才能合法地行使统治权力。彼特拉克及其之后的许多人文主义者甚至激进地认为,即便是出身卑贱的人,只要他获得了德性,同样也能跻身于统治阶层[6]223。薄伽丘坚持说,真正的高贵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从显赫富人到农夫、工匠、武士[7]4。薄伽丘枚举了大量古罗马人物,尽管这些人出身卑微,但他们后来个个都是杰出的政要将领,乃至古罗马皇帝。换言之,社会各个等级皆有成为真正高贵之人的可能。著名的人文主义国务秘书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尤其鄙视那些倚仗财富和血统而自视高贵的贵族,称他们整日只知道沉溺于狩猎、打斗、游戏、骑马,追求财富与纵欲享乐,极少有贵族出身的人懂得德性的重要性[8]73-74。萨卢塔蒂的弟子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更是指出:德性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愿意拥抱德性,那么成为有德之人便易如反掌;与之相反,恰恰是那些自恃高贵,只知道寄生于祖辈荣耀之下的贵胄反倒很难具备德性[9]88-89。
韩金斯认为,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平等观念模式,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获得德性的能力,韩金斯称之为“德性平等主义”[1]40。这种对德性能力平等的认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中潜藏的基督教人类学观念。普拉蒂纳(Bartolomeo Platina)解释道:高贵的人懂得遵从正义、恪守尽职、克制欲望、遏制贪婪。只要能够做到这些,即便他有可能出身底层,但同样是拥有德性的高贵之人。不用顾忌家世、权柄和财富,只要考虑到理性道德的能力,那么人人生来平等[5]282。波焦·布拉乔利尼同样认为,高贵是“德性散发出的光芒……它通过意志和力量属于每个人,没有人能违背他人意志夺走德性”[9]84。
但在笔者看来,同所有前现代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人文主义者也认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等级制,认为这是自然的且必要的。在一个政治体系当中,精英永远必不可少,无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制。人文主义者的德性政治说到底强调的是“德性”在政治统治中的核心地位,牵涉到德性与权力之间的对等关系。简言之,就是有德者称王。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者主张精英群体必须保持开放,允许所有具有智慧和德性的人参与其中,不论其是何种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在如何获取德性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也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古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获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仅需要后天的道德实践和哲学沉思,同时还要辅以世袭血统、教育环境以及优秀朋友的引导。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人文主义者的方案则直接得多,他们将人文主义教育(studia humanitatis)作为获取德性的一站式途径,主张德性具有自给自足性。这是15世纪人文主义教育家在研究古典文化时提出的一个全新有力的说法。他们认为古典文化灌输的都是高尚的道德观念和实践智慧,这些都是优秀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品质。道德哲学和历史、格言警句和典范广泛散布在古代诗人、演说家那高贵丰富的语言里,不仅能够让统治者学会如何施以德政,而且还能让他们掌握优秀统治者所需的雄辩术。
人文主义者深信通过向精英阶层灌输人文教育,德性便会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使得人民从统治者的才德中获益,由此施行温和派政治改革。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写道:“在国家中担任统治角色的人,一旦具备了正义、善良、审慎和节制,便能与所有人分享这些德性所带来的‘果实’,将德性的力量传播给每个人。当个体沉思于哲学研究时并不能带来实用的功效,因为它仅能对从事哲学研究的单独个体产生影响……古代圣贤完全有理由赞赏那些驯化君王的教育家,他们通过提升统治者个人的德性,藉此影响许多被统治者的行为习惯。如伯利克里的老师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迪翁(Dion)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与意大利的君主们、阿忒努德鲁斯(Athenodorus)与伽图、帕奈提乌斯(Panaetius)与西庇阿(Scipio),即便在我们的时代,克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10]263-264总之,人文主义者希望通过人文教育使统治者在智慧和德性两方面有所受益,继而使他们成为人民争相效仿的道德典范。
二、德性与法律的权重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推崇德性政治,直接原因是帮助他们所效力的对象确立合法统治。不仅如此,人文主义者还将“德性政治”作为治国济民的良方,提出要从根源上,即从统治者自身出发,用人民的信任取代欺诈和暴力,唯此才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只有当人民对统治者的忠诚发自于内心,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才指日可待。人文主义者认为,具有德性的统治者会心系于民,始终以共善为目标,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关爱百姓;相反,失德的统治者则一心谋求私利,他们不可能赢得民心,城邦亦不会长治久安。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看来,世风日下与政体形式无关,统治者个人能力的不足和德性的缺失是导致腐败和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不是“国家”,而是统治国家的个体,统治者的德性要比特定的政体类型远为重要,这种政治关怀的倾向凸显出“德性政治”的功能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文主义者政治观念中的“统治者”范畴与统治人数的多寡没有必然联系,他们既可以接受君主制和贵族制,也可以接受多数人参与统治的民主政体。其二,“德性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治人,以德服人,人文主义者希望并鼓励统治者凭借美德、智慧和能力,为被统治者树立榜样,倡导道德教化要比武力压制更加有效,因为被迫的顺从不会持久。例如,一个皮球,越是重力拍打,它越反弹得厉害,政治统治同样适用此理。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违背民意,无论政体形式如何,这种倒行逆施的统治方式势必会引发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顺乎民意,用德性代替武力,缓和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要么在革命的浪潮中推翻现有的统治势力,让真正高贵的有德者成为新领袖。
自古典时代以来,任何类型的政治共同体里都出现过滥施权力或行僭政的现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也不例外。对此,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像法学家巴尔托卢斯(Bartolus)等人那样,在法律框架下界定何为僭主或暴政。相较于如何定义“暴君”“专制”等概念,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回到西塞罗、李维、塔西佗、萨卢斯特等古代作家的著述中去理解政治腐败背后的原因。在面对如何解决统治者滥权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同样也不会诉诸法学理论中民众同意、合法抵制等手段。在人文主义者看来,首先,不可以通过民众暴动来代替腐朽的统治阶级,让乡村野夫通过暴力革命来掌控政权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其次,也不可以通过推举强人来解决政治问题。一些雇佣军队长在社会秩序混乱时会动用武力维持和平,这种方式在14—15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出现危机时常采用,但是武力压迫无法改造人性,即它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人文主义者从西塞罗《论义务》(De officiis)这本关于政治道德的权威著作中了解到,社会是不可能通过蛮力凝聚在一起。于此,人文主义者相信,只有君王以及簇拥在君王身边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卡斯蒂廖内(Baldassar Castiglione)《廷臣论》教的就是这个道理。廷臣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做“君王的磨刀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剔除滥权的“毒瘤”。廷臣要让君王明白,统治者必须依靠人民的信任才能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秩序。
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城邦试图通过颁布更多的法律,或成立司法机构来解决国家腐败和僭政现象,不过人文主义者非常清楚这么做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深谙塔西佗之意:“国家过去虽由于恶习而遭受灾难,目前却由于法律而大遭其殃。”(1)拉丁语原文为“corruptissima respublica plurimae leges”,直译为“国家越是腐败,法律越是复杂”。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三卷),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0页。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奈何不了权势者,对此,波焦·布拉乔利亚早就借对话者之口说过:“城市中只有下层阶级和弱势群体才会受制于法律,有权有势的公民首领毫不忌惮法律的威力。”[1]50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将法律喻为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它专门捕食弱者,却极易被强者撕毁。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那些无依无靠、势单力薄的人才会需要法律,认为法律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强者欺凌。庄重、审慎、有头脑的人并不需要法律,因为他们自己就能规划出一套正确的生活法则。这些人要么天生便拥有良好的美德,要么是接受了人文教育熏陶后所得;城邦中的权势者唾弃、践踏法律,认为法律只适合那些弱者、雇佣兵、工匠等社会底层的贫穷者,较之于法律的权威,暴力与恐惧的威慑更有助于统治。”[1]50米兰斯福尔扎家族、阿拉戈纳的君主们、威尼斯共和国和后来查理五世的代理人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谋杀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采用这种手段[11]490。
显然,在人文主义者眼里,法律的强制力对于权势者并不管用,他们要么因为自身已经品德出众,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法律;要么就蔑视法律,视之为专门用来束缚弱者的武器。不过不能就此夸大地认为,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的法律文化皆嗤之以鼻。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仍崇尚罗马法,并将罗马法视为古典智慧的宝库。他们也相信自然法和神法,只不过他们觉得当下的司法实践充斥着腐败堕落:法令条文繁缛,混淆是非曲直,暗地钱权私通,欺上罔下抹杀共善,正义被禁锢在复杂且无用的司法程序里。连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人也毫不避讳地感慨道:“我们轻视外部法律,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不是正统合法的,而他们的法官和官吏都是坏人。”[11]469法律在那时几乎成为模糊真相的帮凶,司法实践早已背离了揭示和捍卫真相的初衷。
简言之,人文主义者对法律规制的烦琐以及实践程序上设置的重重障碍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由此羁绊了道德自由,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同时,人文主义者也不相信法令法规能够彻底保障行为的正当性。人文主义者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认可明智善良的人才是最好的法官,他会在实际判断中审慎运用法律。罗马人曾说“社会应当施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这句格言有待商榷,社会确实需要法,但同时也依赖执法之人。
由于法律和制度并不足以抵御腐败的侵袭,唯一能够与滥权较量的砝码就压在了统治阶级身上。人文主义者身兼劝导统治者举止良善之重任,通过向他们灌输古典文化来养成高贵品德。不过人文主义运动的勃勃雄心远不止于培育未来的君王,他们更希冀改善当时的政治生态,最终目标是形成一股广泛崇德立德的社会风气,人人都能明明德,鄙夷无德之人。
在以培育、提升德性为目标的君主驯化过程中,雄辩术扮演了重要角色。要让君主接受人文教育的熏陶并做出改变,人文主义者必须掌握一套说服的技艺,通过言辞说教让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道德约束和自我监督。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雄辩术是吹响德性的号角。人文主义者擅长雄辩,并且在他们的雄辩术中夹杂着修辞的技巧,他们会用最生动形象的言辞来颂扬善行,用最严酷犀利的训斥去苛责恶行。
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在1390—1430年间,公共演说在意大利各城邦逐渐流行起来,至15世纪末,公共演说俨然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仪式传统,雄辩的口才则是一份重要的政治资产[12]330。演说者以人文主义者为主,他们在公众及私人场合用拉丁语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举行演说仪式的场合包罗万象,比如显贵家族办理婚丧、政府要员的就职典礼、大学新课程的第一次开讲,以及来访使节的会晤等。1415年在佛罗伦萨的某次政府就职仪式上,一位外来的新任法官就以“正义”为主旨进行了公开演说。这一时期的演说内容因为涵盖了古代经典和圣经权威而变得丰满且具有说服力。佛罗伦萨政府卷宗《建议与咨议》(ConsulteePratiche)进一步证明了修辞学(演说)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演说者们大多秉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高度赞扬美德并呼吁统治者重视德性,在统治过程中发挥道德的感召力量。
这类演说的最终目标是唤起人们对德性的普遍关注,尤其是要向所有在任的政府官员以及对即将上任的新官传递一种道德期望,督促他们恪守职责,履行人民公仆应尽之义务。这种道德问责制具有无穷的威力,虽然不像司法惩戒手段那般令人望而生畏,但它会让任何低于道德期望标准的统治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背负心理压力,在遭受人言唾弃或史书载录中遗臭万年。
总之,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在思考德性与法律的关系时得出的结论是,道德名誉上的蒙羞要比鞭笞肉体所带来的痛苦更为深刻且持久,因为不仅是道德败坏者本人,其家族都会因此遭受牵连。鉴于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擅长的雄辩术并非只是空洞的修辞或华丽的缀饰,人文主义者希望借助雄辩术建立起一套道德行为规范机制,他们努力宣扬惨遭漠视的道德价值,通过雄辩的言辞强调德性的重要意义及其内在的政治逻辑。
三、建构新古典主义的荣辱观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擅长的雄辩术堪比现代流行的社交技能,借助社会舆论影响和民众心理导向(而非暴力强制手段)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通俗点的说法就是“人言可畏”,以公共演说的方式宣扬德性的力量,批判不良的行为。若借用德裔美籍思想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看,人文主义者的目标是想通过激发一种新的激情来抵消腐化的激情和欲望。前一种激情来自对政治共同体荣誉的敬仰与渴望,后一种激情是指对个人利益得失的算计与报复。人文主义者希望在这两种激情碰撞的过程中构建起新古典主义荣辱观。
首先,统治者的荣耀来自人民的信任与爱戴,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是获取人民拥戴的前提。当下及未来的统治领袖始终应当沉浸在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的熏陶中,因为只有在道德为先的社会里,最高的赞誉是送给公仆的。毋庸置疑,这种新古典主义荣辱观受到了被理想化的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启发,人文主义者试图用之来取代先前以封建思想和骑士精神为源泉的贵族阶级认同感。对此,但丁援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话指出:在腐朽的政体之下,好人也会变成恶棍;而在良善的政体之下,好人与好公民合而为一[13]112-117。“公民不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为他们的国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为公民而存在,国王也是为百姓而存在的。正如建立社会秩序不是为了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则是为了建立社会秩序,同样,人们遵守法令,不是为了立法者,而是立法者为了人民……从施政方面来看,虽然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目的而言,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2]19。人文主义者相信,古典文化中蕴含的崇高美德在任何时代、任何政体下都不会过时,只要统治者与人民同心同德,重振古罗马雄风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其次,人文主义者希望统治阶层乃至社会所有成员皆能浸透于萨卢斯特式德性竞争的氛围中。萨卢斯特指出,我们应当“以我们内在的资源,而非身体的力量来追求荣耀……财富和美貌带来的荣耀是流动的、脆弱的,而德性则被认为是光荣的、永恒的”[14]1。人文主义者明白,这种新古典主义化的德性依赖于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自我发掘和为国奉献,个人在共同体里的尊严与荣耀取决于他是否愿意为共同体服务,而不是出于私利的行动。荣耀必须与德性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荣耀[15]73。人文主义者希望人们能以批判性眼光辨析真正的高贵与荣耀,从而在整个共同体内达成共识,使有德性的人得到地位与尊重,德性缺失的人蒙受耻辱和贬职。显然,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人文主义者试图培育将政治义务与公民道德两相结合的公民政治精神,并以此唤醒人们对美德的重视与对荣耀的渴求,借此打破血统、门第、财富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让德性成为真正高贵的本源。
为了更好地建构新古典主义荣辱观,人文主义者不仅在演说和著述中枚举了大量值得称颂的古典美德,他们更是巧妙地运用壁画、雕塑以及建筑等形式,不断强化人们对道德讯息的感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让统治精英在思想和情感两方面都浸透在崇德弃恶的环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俨然超越了文化艺术的范畴,它已升华为一场旨在复兴古典美德的道德政治运动。我们可以想象,当漫步在新古典式庭院里,看着小径两旁伫立的古罗马伟人雕像,一股效仿古人的欲望便油然而生[16]251。无论是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国的议事大厅里,四壁和天顶上刻满了古人的碑文铭言,瞬间会让那些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人回想起曾读过的古人伟绩,督促他们牢记职责所在,时刻要明智行事。那些取材于古典时代的雕像、碑文、壁画既是为了纪念与唤醒公民美德,更是为了教导人们汲取政治教训。譬如,在当时许多政府议事大厅的墙上都刻着一句广受欢迎的萨卢斯特格言:睦则小而兴,携则大而坼[16]258。
甚至音乐也被用来营造仿古、崇古的氛围。尽管人文主义者在音乐领域所做的贡献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关联不大,但人文主义者确实创作出一种新的音乐批判风格。他们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最后一卷中发现了音乐与德性之间的联系,坚信音乐具有促进道德行为的功能。此外,人文主义者还提倡复兴一种现已失传了的音乐文化——古典说唱,他们从对古典文化的理解中重构了这种音乐唱法。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早期,以著名歌唱家布朗多利尼(Raffaele Brandolini)为首的许多音乐家都在实践人文主义音乐艺术,用七弦琴弹奏改良后的拉丁诗歌。这种新的音乐方式既与之前歌唱爱情的小丑剧、哑剧不同,也无需狩猎音乐中的大鼓、钹、小号、号角等器乐[17]1401-1402。人文主义者想要发展的是一种能够取代世俗音乐的新风格,使得上层阶级在闲暇时也能感受古典美德的熏陶[18]231-262。正如美国学者布鲁克尔所言,那些开始时是个人手法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种倾向、一场运动、一个新的风格[12]354。
四、结语
透过德性的焦点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力图勾勒出一幅崭新的理想国画卷:上至君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道德的评判,继而营造出德性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德性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让美德的行为广受嘉奖,让有德的个体加官晋爵。
那么,人文主义者德性政治传统对于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到底贡献何在?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概括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要素:政府、法治、民主问责制,并区分出三类政府体制:职能最优的现代政府、前现代政府、失败的政府。第一个要素即现代政府属于非人格化的政治秩序,它代替了前现代社会中的部落和世袭的政治秩序。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国家既有暴力方式的垄断,又有完美定义的权益,还有国家公仆和官僚机构,这些人假公济私,表面看是为了社会集体利益,实际上却中饱私囊,扶持家族亲信或朋友。福山称之为“传统世袭制主义”(patrimonialism)和“庇护主义”(clientelism)。第二个要素即法治是逼迫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遵从成文法,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法律有时也会成为酌情决定权的障碍。第三个要素即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要求统治者对国会以及其他代表民意的政治机构负责,他们的统治权受制于广泛的民意,选举即是如此。
显然,人文主义者德性政治对现代国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德治”上,它同时挑战了宗法世袭和裙带关系的权力形式。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扮演着文人、律师、政治家、外交家和宣传家的角色,他们更是驯化君主,提倡以德治国、以德服人的教育家;他们主张个人荣耀源于为国服务,将古典美德与公民义务两相结合;他们呼吁社会各阶层重视道德教化,将高贵品德作为衡量权力与地位的新标杆。
然而,人文主义者的德性政治观对现代法治的贡献则相对模糊不清。虽然像比昂多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赞扬罗马共和国能够让最具权势、最受敬仰的罗马公民也臣服于法律统治,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具有智慧和德性的统治者可以在法度之外酌情自由裁量,甚至还有极个别者主张国家可以背离法律。依笔者之见,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事实上,他们恰恰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人文主义者们非常清楚当下司法体系漏洞百出,政府功能失调,官员偏袒舞弊,他们惧怕权势者操纵垄断司法程序,在法律名义下耍弄骗人的把戏。因此,人文主义者才会希望法律能够听从德性和智慧的号召,毕竟如果失去了德性的驾驭,哪怕再公平正义的法律条文也不过是一纸空文[19]98。
纵观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状况可知,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观最终没能得以延续,一方面是因为人文主义者以德性为中心的改革理念过于理想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法有效地适应近代国家的运行机理和政治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继人文主义者之后的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政治去道德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德性政治。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现实迫使思想家把目光从德性政治转向了国家理性,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而非单一地凭借提升执政者的德性)才是近代国家政治治理的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德性政治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应对彼时政治现实需求之产物,亦是人文主义者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与思想启示。
身处21世纪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今人,同样需要重视年轻一代的道德培育,需要教化成年人多为公共利益考虑。治国理政不能仅凭调节利益机制,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