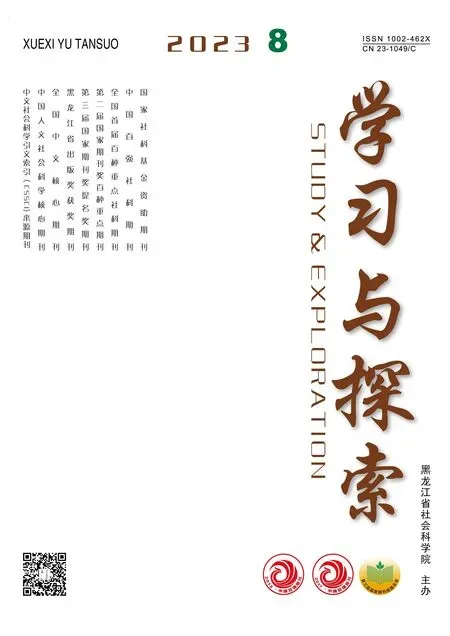鲁迅戏剧创作旨趣与俄国文学渊源的一种考察
——以《过客》《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为中心
于 溟 跃
(1.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12;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鲁迅长期保持着对戏剧艺术敏锐的洞见和深入的思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审美意识、价值取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创作一直秉持的旨在启蒙性灵、探寻反抗超越的精神,亦内化于对戏剧的态度和实践,后者充分见证了前者的深化与发展。《过客》(1925年)是鲁迅难得的一部戏剧体作品,鲁迅选择以独幕剧的形式抒写自己对时局的思考、对反抗精神的坚守,成就了其彼时在戏剧领域的创作尝试与新探。
众所周知并得到鲁迅本人承认的是,鲁迅受俄国戏剧家、小说家安德列耶夫(鲁迅译作“安特莱夫”“安特来夫”“安得烈夫”等)的影响颇深,而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1903年,以下简称《一生》)被视为作家象征主义转向的代表作,且其中也有一个遭受苦难、惶惑窘迫,又时刻以信仰激励自己与绝望抗争,直至信仰之路走向坍塌,生命之路走到尽头的男主人公形象。《一生》与《过客》在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上具有高度的趋同性——皆于诗意中书写对绝望的反抗,两位主人公的动作、心理乃至命运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通过对二者的解读,我们可以探寻到以反抗精神为理路的鲁迅戏剧创作旨趣与安德列耶夫、与俄国文学的一种渊源。
一、鲁迅的戏剧及俄国文学之缘:以反抗精神为核心
鲁迅一生与戏剧颇有缘分,从儿时在戏曲文化中的浸润,到后来对传统戏曲的批判和对西方戏剧文化精神的汲取,鲁迅的文学与生活中大量充斥着戏剧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迅与戏剧的关系、对中西方戏剧的关注角度,以及他的戏剧观念演变与创作过程不仅透射着他的人生经历,还反映出他的生命哲学与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以批判现实、不断探索超越为核心内涵的反抗精神是或隐或现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
(一)对中西之“戏”的态度及演变
看戏是少年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戏曲构成了其成长环境的基调之一,《社戏》《无常》等文中均有文字证实。在鲁迅辞世前夕创作的《女吊》中,他对自己四十年前看戏的时间细节、仪式氛围等仍保有清晰的记忆,印证了其少时对绍兴地方戏熟悉与感兴趣的程度之深。然而,中青年鲁迅对传统戏曲的态度大转,他说:“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尔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1]561“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1]561鲁迅一边认为中国戏“自有他的风致”,一边在精神上与之划清“天之南地之北”的界限,他对传统戏曲的感受和评论变得矛盾复杂,甚至颇有“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80之感。但总的来说,质疑和批判是鲁迅后来对“旧戏”的整体态度。鲁迅态度的转变是与时俱进的,这既是基于他对旧戏的现实把握而进行的民族性、心理性自省,又是顺应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大潮和时代使命的反抗精神的自觉产物。
鲁迅在日本留学前后逐渐成长为译介外国戏剧作品的先行者,“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3]161。鲁迅接受并推荐外国戏剧的初衷是“拿来主义”,借助外来的思想力量而更好地实现唤醒被压迫束缚同胞的理想,更快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贡献智慧,“增长新文学阵营的势力,扩大读者的眼光,以更快地打倒旧文学;同时为新的创作界多提供一些范本,添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学的泥土,以资助中国新的革命的文学的成长”[4]44,“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5]40。
如果说传统戏曲更多的是丰富了鲁迅文学作品的传统文化氛围和风格意趣,外国戏剧元素则为鲁迅的思想性和其作品的精神厚度打开了新的视野,平添了许多资源,提供了可观的精神滋养。鲁迅的一生中,戏剧始终在场,他对中西之“戏”的态度是紧紧伴随着他的哲思演变的,二者相辅相成、交织融合,前者折射出鲁迅刻在骨子里的反抗精神的持续滋长,后者决定了鲁迅对待戏剧的观念与实践的不断变化。这一现象还说明,鲁迅心中一直存在着“新”与“旧”的冲突交战与扬弃思考,他的思想有着浓厚思辨性的生机与魅力。
(二)与俄国文学及安德列耶夫的渊源
自留学期间接触并关注俄国文学起,俄国文学便与鲁迅的文学活动相生相济、相伴始终。他曾由衷地说道:“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6]6731920年4月至11月间,鲁迅经常“往午门”,参与审阅整理“德华总会”藏书中的德文、俄文书籍[7]401。鲁迅对俄国文学戏剧作品的译介是值得关注的,据统计,他一生翻译、编校的俄苏文学作品、理论著作达160多万字[8](其全部著作量约为600万字),经他翻译、评述的俄国作家多达37人。他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引为“同调”,心中的反抗精神也从这片“伟大肥沃的‘黑土’”[6]475中获得了许多养料:“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9]511冯雪峰评价鲁迅为“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4]39。其中,鲁迅与安德列耶夫的渊源不容忽视,鲁迅是中国译介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人,他不但翻译校订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戏剧作品,还亲口表示受其影响很大——“(托尔斯泰、高尔基)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10]15,甚至有时会效仿借鉴安德列耶夫的写作情绪、艺术手法等创作要素。曾有学者发现:“我们在阅读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谩》、《默》(1909年3月)这两篇文章时,核心就是要体验鲁迅内心受到的‘西洋的冲击’。”[11]
安德列耶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文笔深刻,怀有人道主义精神,多以冷峻幽深的笔触描写俄国穷苦大众的生活和命运,代替他们抨击黑暗,表达对剥削压迫者的抗议。他常常使笔下人物与苦难的生活和异化的现实勇敢抗争,在“毫无胜利之望的斗争”[12]46之下仍不屈于命运的安排;他一边向底层民众的痛苦绝望表达怜悯关切,一边又为他们安排寻求解放反抗到底的悲壮结局。这正与鲁迅的审美相契合,他时常惊叹于俄国文学所蕴含的博大深沉的爱和“异常的慈悲性”[13]193。鲁迅认为,安德列耶夫“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14]159。观照鲁迅对安德列耶夫其人其文的推荐与赞扬,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反抗精神在呈现更加深刻坚定的走向。
鲁迅曾言,自己“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15]5。除安德列耶夫外,鲁迅还提及尼采,尼采也是影响鲁迅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一点也反映在《过客》中,有学者认为,《过客》的“反抗绝望”主题和不断行走超越的主人公“过客”都显示了与尼采超人哲学的密切关系[16]。而安德列耶夫也一度迷恋尼采的学说,曾整夜整夜地阅读其作品;《一生》的主人公瓦西里,同样是一个狂热坚持信仰、不停向前“奔跑”的“超人”。鲁迅与安德列耶夫的“灵魂相遇”以及深层次的渊源也许正在于此,在相近的审美旨趣与反抗精神作用下,安德列耶夫对鲁迅的天然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二、“过客”与瓦西里的人物动作心理分析
《过客》《一生》两个文本的故事背景不同,两位主人公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精神信仰也迥然相异——一位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的乞丐“过客”,一位是生活平淡中带着无常、但终究有家可归的神父瓦西里,然而,二者之间却具有相似性。他们或许是鲁迅和安德列耶夫不约而同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实践与致敬,但可供我们探索的是,《过客》的创作过程中是否暗含着鲁迅的安德列耶夫式体验?从人物角度出发,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契合?
(一)相同的人物动作:“走”
曹禺曾说:“一切戏剧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理和行为。”[17]427一切艺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戏剧是人的戏剧,人物动作是戏剧艺术的关键元素之一。作为独幕剧的主角,鲁迅赋予“过客”一个标志性动作——走,并且是贯穿整出戏剧与过客整个人生的“走”。“走”字在文本中出现了37次,表明鲁迅对这一动作及其所喻示的反抗意涵的强调和重视。“我们感到:鲁迅赋予了这‘走’以不寻常的重大意义,在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这个问题一定也占有中心地位。”[18]
过客的出场是未见其人先见其动作的,从小女孩的台词“(向东望着),有谁走来了,看一看罢”[19]188-194可知。随后,“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的过客“踉跄走出”,“慢慢地走近老翁去”,并说“我走得渴极了”,这里传达出过客在身体极度不适、缺乏行走条件的情况下仍在坚持行走。据他自己交代,“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他还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与其说这是鲁迅在向自己的潜在读者/观众多次表达主人公的行为,不如说“走”的动作就是这个人物的灵魂,其已在无意识层面反复确认了自己的使命。后文中,“我只得走”又被过客述说了三次,“我还是走的好”在三个人物的对话间一共出现了6次;此外还有对过客“(准备走路。)”的专门动作描写。在短短的文本中,“走”的动作及其效果已被鲁迅发挥到了极致。
在这里,“走”是一个无限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行为,而《过客》既然是独幕剧作品,自有其剧场性存在,在空间时间高度集中的有限的一幕以及可被搬上的舞台中,文本所构造的有限的时空与无限的“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是鲁迅有意无意地为自身创作的戏剧性所在而孕育的氛围感和冲突性,融会充盈着他对戏剧艺术的独到见解和大胆实践,更展现了鲁迅文学所蕴藉的珍贵的现代性内涵。
对应地看《一生》的文本,每当瓦西里遭遇严酷的无常而怀疑人生时,他同样会选择“走”出门。当儿子不幸夭折,妻子从此变得疯癫,瓦西里一瞬间不堪命运的重创而“跑到田野里去了”[20],“在麦田中间的一条小路上走了很久”;多年后,妻子仍未走出丧子之痛,他难以面对越发疯狂的妻子,深夜里“连衣服也不添,就穿着那件破旧的黄色土布做的长袍,向旷野走去”。小说结尾,妻子意外去世,女儿寄养到别人家,瓦西里孤身一人带着新生的“痴儿”,又在教堂生活中充分感受到人们的苦难和生命的脆弱后,他的信仰真正崩塌了——他“向门口冲去”,“每次摔倒后,他总是爬起来又跑”,最终“伏倒在路上,瘦骨嶙峋的脸埋在被车轮碾成粉末、被人畜踩成粉末的灰蒙蒙的尘埃里。他的姿势仍保留着撒腿狂奔的样子”,“仿佛他虽然死了,人却还在奔跑”。“走”“奔跑”的前进之动作伴随了主人公的一生,“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亦是在前行中不断重塑精神支柱、以期与生活和命运所带来的苦难绝望相抗衡而反反复复、跌跌撞撞“爬起来又跑”的一生。
“走”是鲁迅与安德列耶夫共同强调的人物核心动作,也是两位主人公面对不堪现实和悲苦命运的一种释放方式,是支撑他们坚持前行的“不屈的意志”的直接反映。虽然两个人物信仰不同,但他们“走”的动作都寄寓着作家的反抗精神——以一己之力反抗绝望,暗喻着“尼采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精神境界”[16]。“《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21]442,鲁迅之所以将笔下的角色也即他自己当时的精神肖像定名为“过客”,便是因为过客所到之处终是路过,他从不停留;反抗绝望的精神不断引领激励着他,他孑然一身,却超越自身。
(二)相通的人物心理:“声音”
两位主人公各自不同的信仰在文本中表现为同一种元素——人物心理,也即他们心中反抗绝望的“声音”。《过客》中,“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揭示了过客心中“声音”的恒久存在。并且在老翁年轻时,也听见过一样的声音——“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然而,当过客追问“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老翁却记不清楚了,因为他“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这是鲁迅利用声音元素对过客和老翁所代表的两种人的巧妙划分,前者被声音所吸引,坚定不移、上下求索,执着孤独地踉跄前行;而后者对“声音”视而不见,对人生亦是半途而废,退缩妥协,放弃追求。
《一生》对“声音”的描写更加细致丰富、形象生动,是主观与客观并行的,是全面而呈现互文性的。瓦西里不仅在心里守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条无形的嗓子在黑暗中发出了声音”,还多次朝天大喊:“瓦西里神父举目望着苍天,把两只手按在心口,想向苍天吁求什么。……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响亮而又清晰地对天喊道:‘我——信仰你。’……接着,他像是在驳斥什么人,狂热地说服什么人,警告什么人似的,又一次哀号说:‘我——信仰你’”,“这条嗓子所吐出的话语,却清晰得像天火一样。‘我——信仰你。’”最后,在生命终结前夕,他又“放开喉咙吼叫道:‘上帝啊,我信仰你!信仰你!’”这多次重复的相同声音是主人公在已经明显对信仰产生质疑的境况下依然所做的自我催眠,他想使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来对抗令人绝望的现实;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冷冰冰的跳跃不已的火焰,青筋嶙嶙的身子充满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作家蕴含着强烈对比的词句间满溢着最深的绝望,瓦西里最终悲剧地被他心里的“声音”吞噬了。
另外,《一生》中还有一个数次出现、与人物心理相呼应的背景声音——钟声。小说中段写道:“小教堂那口喑哑的钟单调地敲响了起来……这钟声怯生生地打钟楼上跳入雾霭沉沉的空中,堕落到地下,就消亡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响应小教堂所发出的畏葸的,然而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迫切的召唤声。”这显然构成了对瓦西里心里“声音”的补充,作家在通过对客观环境的描绘,说明瓦西里遭遇的信仰危机——信仰已是喑哑的、怯生生的且很快消亡的存在,即便瓦西里固执迫切地去巩固它;而他作为神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等到备受生活煎熬的人们前来教堂忏悔了。后来,“大斋节的钟声依然那么单调、凄切地发出召唤”,人们“被某种东西连接在一起地朝着同一个看不见的目的地,忧心忡忡地鱼贯而去”。此刻,信仰仍是瓦西里心中的灯塔,他与人们一样,被钟声所代表着的东西召唤着,朝着虚无的前方踉跄行进。
当瓦西里内心的信仰与残酷现实相碰撞而达到小说情节的矛盾高潮时,钟声变得“声音嘶哑、凝滞,而且支离破碎,狂风转眼之间就灌满了钟巨大的嘴巴,呛得钟喘不过气来,哼哼唧唧地呻吟着”;“夜在拿钟逗乐。它一把揪住肥头胖耳的低沉的钟声,发出咝咝声和唿哨声,把钟声团团围住,将它撕成碎片,掷向四方,要不就用力把钟声往旷野上滚去,把它埋在雪堆里……当响起另一下钟声的时候,不知疲倦的、凶狠的、像恶魔那么狡狯的夜,又扑上前去把它截住”,“教堂的钟在召唤着迷途的人,但是它那衰老的声音却在为自己的孱弱而哭泣”。安德列耶夫以此象征和影射了社会现实以及虚无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教会对人们的残害,无法通过信仰挽救的悲惨境遇加速了瓦西里们心里“声音”的消亡,衰老孱弱的钟声也已近发不出声音。当死神降临时,瓦西里“还想起了暴风雪。钟声和风雪声”,至此,他虽还能想起钟声,但钟声与他内心的“声音”已全然不会再响起,留给主人公的只剩下“失神的眼睛”和“死亡的气息”。
然而,皆有“声音”指引的同时,两位主人公也遇到了或多或少的信仰与信念的动摇危机。如前所述,瓦西里始终走在重塑信仰的路上,但他是迷失的,当最后阶段“声音”消逝,他想再次还原自己“走”“奔跑”的动作而癫狂拼命地重建信仰时,他却“向门口冲去,却找不到门……不知谁的两只索索发抖的手用力搂住他,不放他出去”,他的世界最终天塌地陷。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过客是截然相反的。过客虽然也多次感到难以行走,并重复他的对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的好”,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但他心里的“声音”是不能后退、不可沉沦、不忘理想的战斗精神,是宝贵的、向生的、积极探索国民出路的奋斗精神,更是鲁迅历久弥新久久为功的觉醒信念和反抗哲学所在。如果说过客和老翁二者代表的是鲁迅“内心两种声音的交战”[22]151,是鲁迅作为知识分子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取向输入与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之下,对民族前路命运的思考,那么胜出的一方必定是也最终证明是过客,反抗绝望、探索超越的人们走向光明和希望,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三、象征与意象在文本间的交相辉映
安德列耶夫是一位很有才华并且勇于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家,翻阅《一生》的文本,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洋溢着的作者的才情,用来象征隐喻社会现实与人物心境的自然景物及氛围比比皆是,且能够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巧妙地织在一起。据周作人记载:“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来夫……这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23]184-185安德列耶夫的创作艺术风格也给鲁迅带来了深刻启发:“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24]185止庵就曾评价道:“就连《野草》也说得上是‘安德列耶夫式的’。”[25]
《过客》是一部诗剧,凸显了鲁迅结合传统的民族的诗情,并吸收西方象征主义手法的营养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有益实验。《过客》篇幅不长,却含有大量的象征、隐喻、暗示手法,具有饱满的象征意义,鲁迅还利用种种意象帮助自己吐露心声、抒发感情,在激烈的反抗主题之外,给予我们诗意的真实和诗化的哲思。李欧梵对《过客》做出过这样的研究:“《过客》则是用的浓重的象征剧的形式,在剧中,三个人物进行了一长串富有哲理性的对话”[26],“从诗篇开始时所写的简单的‘舞台说明’看,很容易误认为一幕荒诞剧的舞台”[18]。比较考察两个文本,鲁迅和安德列耶夫都着重选择了以自然环境象征暗示社会环境与人物心理环境,并以“路”的意象隐喻两位主人公秉持各自信念信仰而踏上的精神道路,实现了跨越民族文化的诗意书写上的遥相契合。
(一)以萧瑟破败的自然环境象征现实与人物心境
鲁迅为自己戏剧发生所“量身打造”的环境和场景十分集中明确,正值“太阳要下去了”的时分,过客向西行,前方是荒凉破败的丛葬,他自己从杂树间走出,走到一处门侧有一段枯树根的土屋前停下,独幕剧由此上演。鲁迅写就这部作品时,正值二七大罢工、五卅惨案等反帝反军阀的重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的时期,那是富于才华、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们难以委身和接受的苦闷黑暗的环境,他们是一定会求新求变的。在鲁迅笔下,“黄昏”“杂树”“瓦砾”“丛葬”“土屋”“枯树根”等共同展示了一幅幽暗凄凉、破败萧索的图景。这种直接交代故事环境而省去渲染描写的简洁性和指向性是戏剧体作品所特有的优势,既象征了过客处境的艰难绝望,又烘托出其精神意志的坚定决绝;既赤裸裸地展示了鲁迅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沉重不堪,又直白地勾勒出他自身精神肖像的彷徨孤独与失望痛苦。鲁迅悲观而不无讽刺地说道——“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后文中又直接给出了对过客来路环境的形容:“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
前方等待着过客的环境又是什么呢?过客“西顾,仿佛微笑”,对于前方如何,他似乎知道一半:“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在前方,已知的是长着野百合、野蔷薇的坟地,未知的是坟地的再前方。它们共同营造了一种死寂的氛围,象征着过客所坚定走向的也是鲁迅预料到和必须面对的前方——已被确定的坟地和未知的坟地之后不仅可能是依然不变的残酷阴暗的社会现实,而且可能会使前行的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绝望虚无。然而,鲁迅又“仿佛微笑”地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希冀——野百合和野蔷薇,二者都象征着生命力,有着极强的适应环境的顽强和勇敢,以及与命运抗争到底的精神。这种处在灰色空间中的一抹色彩和处在极强对比之下的坚贞不屈的美无疑令读者动容,鲁迅用两种存在巨大反差的意境告诉我们,哪怕前路未知且可能无功而返,哪怕走下去会与黑暗共沉沦,秉着坚韧意志、肯于反抗绝望、敢于执着探索的人都总会见到勃勃生机。这一点又与其《故乡》的结尾高度互释:“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7]485
《一生》中多处可见对于主人公身处的周围环境的描写,如瓦西里第一次出走时:“黑麦已经长得很高……在他左右前后,长在纤细的麦秆上的沉甸甸的麦穗,如波浪起伏般地向四面八方涌去,一直涌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他头顶上,则是无涯无际的、热得发白了的天空,此外就空无一物了,没有树木,没有房舍,也没有人影。”密密层层的麦子如同黑色的高墙一般包围住瓦西里,象征着人物在生活重压之下处境的艰难逼仄;广漠无垠的天空同时暗示着他的迷茫和无助。瓦西里的妻子遇难时,“温暖柔和的夏夜闯进了洞开的窗户……好些飞蛾由窗里飞进屋来,不声不响地绕着油灯打转,虽然跌落了下去,却重又歪着负伤的身子向灯火猛扑过去,一会儿消失在黑暗中,一会儿又像飞舞的雪花,闪出白光”,室外和谐温暖的良夜从反面喻示了瓦西里家绝望死寂的氛围,一只只扑火的飞蛾也象征着他在心里对妻子死亡事实的一次次确认。
在小说最后的场景中,作家直接点明“那天一开始就有不祥的异象,仿佛自然界也在以其沉重的无形的混乱来回答人间的混乱”,“一扇扇窗户中的呈现出凶兆的红铜色的天空”,“此刻所有的人都看到教堂里越来越暗了,一个个扭过头去望着窗外。槭树后边的天空一团漆黑,宽阔的槭树叶已不再是绿油油的了,而变得惨白如纸,吓得不敢动弹”,诸多关于环境的描写有力地渲染了瓦西里们信仰瓦解、走向死亡的悲剧氛围。纵观全篇,作家以概念化的象征手法每每在悲剧情节处暗示其笔下人物所正在经历的情感和困局,使《一生》成为既长于现代派表现技巧,又富有戏剧化批判色彩的象征主义转型力作。安德列耶夫和鲁迅都喜用天空、晨昏、植物等自然元素营造低沉压抑的环境氛围,象征与揭示人物波澜起伏的心境,这一点无论是呈现为象征剧还是象征主义小说,带给读者的都是视觉和知觉上的诗意飨宴。
(二)相通的意象:“路”
《过客》与《一生》繁复的意象中,尤为重要而相通的是“路”,这既指两个主人公所切实走在的实体之路,又喻指他们的精神信仰之路,更暗含着作家形而上思考的哲学意蕴之路。但两个文本中的“路”具有相异的形态特点,其所通向的结局也全然不同。
《过客》对“路”只有一句描述:“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结合过客“踉跄”的走路姿势,及其“脚早已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来看,这条路的面貌是崎岖恶劣的,并且有着“似路非路”的暧昧性和模糊性——正因过客的行走,它才成了路,这也与《故乡》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遥相呼应。《过客》中路两旁的环境也是荒凉死寂的,除了杂树、瓦砾便是丛葬,这样一条狭窄曲折毫无生机的路,是不适合人去行走的。这也恰好显示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主旨,在路上,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过客的,亦是他自身写照的孤独的反抗者的背影。巧合的是,《过客》写作的同年,鲁迅翻译了日本诗人伊东干夫的《我独自行走》:“暗也罢,/险也罢,/总归是非走不可的路呵。/我行走着,/现今也还在行走着。”[28]134-135
《一生》中“路”出现了多次,或是田野间的小路,或是宽阔平坦的大道。瓦西里迷茫之时所踏上的麦田间的小路,“有的地方留着很深的鞋后跟印子和不知什么人的光脚丫的脚印,那些圆圆的脚印清晰得跟真脚一般无二”,此处作家对路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感知到,在瓦西里之前仿佛刚刚有人走过同一条路,就连脚印的纹理都还清晰地留在地上;这也象征着俄国底层民众遭受苦难煎熬的普遍现实。最后时刻,瓦西里“跑出寨门,来到了一条平坦的大道上”,“倒毙在离兹纳缅斯克乡三俄里远的一条又宽又平坦的大路中央”,道路宽而平坦,不由得反衬出瓦西里的信仰之路和人生之路却在越来越窄,暗示着他的反抗精神即将烟消云散——“全部死尽死绝了!”成了瓦西里一生的最后一个念头。
《过客》中的“路”虽困顿难行,却是启蒙性的出路,是怀着光明信念和反抗精神的路,指向希望;而《一生》中的路从田间小路到平坦大道,越来越宽的同时却表现出毁灭性,是信仰崩塌之路。同样是运用“路”的意象,鲁迅显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要更胜一筹。并且,鲁迅以“似路非路”的混沌暧昧性,含糊地表现了自己头脑中“新”与“旧”、“进”与“退”的取向纠结和前进方向的不确定性,这反而使其反抗精神得到了更加伟大的升华。同时,这也从侧面向我们展示,那个年代相互碰撞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有难以弥合的裂隙。
结 语
交互探寻《过客》《一生》两个文本,在文字魅力的冲击和精神思想的震撼之下,在主题意蕴和创作手法的趋同性之外,二者还存在诸多不同。其一是文体不同,二者分别作为戏剧和小说,《过客》以简洁而独具冲突感的短剧体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性和理性,但毕竟篇幅有限;《一生》则富有更多的对情节、细节的刻画,以体量较大的小说体包含了更多有血有肉的感性书写。其二是时空范围不同,《过客》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严格遵循剧情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也仅集中在“一日的黄昏”;《一生》的时间跨度则较长,几乎等同于小说题目,所写的就是主人公的一生,文本中的地点景色也是纷繁复杂的,带给人们的是更为丰富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其三是写实性程度不同,在这方面,《一生》更具有故事发生的现实根基,也显然有着更加充盈丰满的内容,作品中出现了多个人物且性格各异,人性的不同侧面和他们的不同结局共同构成了人间百态;而《过客》的故事场景和人物个性表现为高度的抽象性和凝练感,要向人们着重展示的是它的精神内涵。由此,在将象征主义与写实性相结合的领域,安德列耶夫的文采和成就是应该被充分看到的,他的创作之所以能受到鲁迅的青睐,与他所拥有的大师般的才华和哲思不可分割。
要言之,《过客》《一生》以不同的文体择取、时空跨度与创作情怀实现了宝贵的殊途同归,给予后人探析其个性差异之上的共性,乃至探寻鲁迅戏剧创作与俄国文学渊源的可能。瓦西里以悲壮的方式死去了,而过客还将继续走在他的路上。明知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明知前方等待他的终点是“坟”,他也还要在无人为伴的孤寂中坚持踽踽独行,这是一种极度的苍凉,有着“向死而生”的哲学意味。“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9]92鲁迅就像过客一样一直在路上,直到今天,他的锐利、正义和担当仍在启示人们走上追求生命真义之路:战胜绝望和虚无,一路探索与前行。正如卢卡奇所说:“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30]452优秀作家的思想总是不会过期,而常常具有永恒魅力。
鲁迅曾说,安德列耶夫“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24]185——或许《一生》便是其中的一部,激发鲁迅以诗意书写赋能戏剧实践的灵感,滋养鲁迅探索戏剧创作的精神旨趣,帮助承载着厚重反抗精神的独幕剧《过客》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也或许两个文本之间的趋同性存在巧合,但内蕴于其中的动人艺术表达、丰厚写作经验、雄浑文化气度、深沉民族情感,以及洞穿世事后的自我超越和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诗性沉思已跨越民族文化而同频共振,并作为经典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