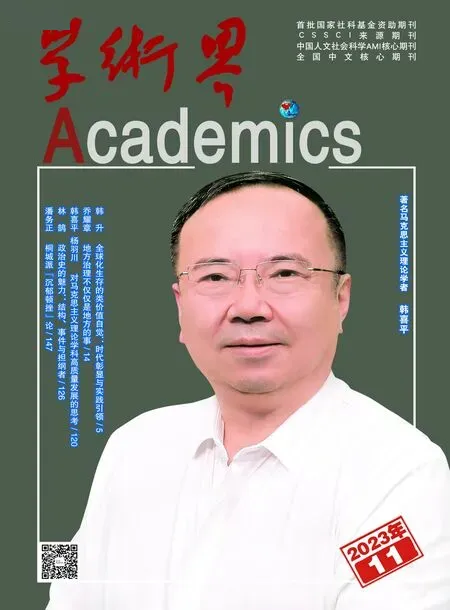贫农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柱石〔*〕
李永芳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我国农会组织肇始于清朝末年,“1907年7月(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我国近代直接由清廷颁发关防图记式样、享有社团‘法人’社会地位的农会组织首先在直隶诞生”。〔1〕但无论是清廷饬令建立的农会抑或是随后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均是一种以绅商和地主为主体、依附于政府的旨在农业改良的社会团体。而真正旨在解决农民阶级切身利益、属于农民自己的农会组织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1年9月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1922年10月成立的广东海丰赤山农会以及1923年9月成立的湖南衡山岳北农会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批新型农会组织。尤其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农会组织呈蓬勃发展之势。据武汉政府农民部1927年6月底的统计,当时全国农会组织遍及19个省份,会员达940余万人之多。〔2〕而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农会组织曾在国民党的摧残下一度逐渐消退。但是,随着苏维埃区域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贫农团”为主体形式的农会组织又旋即建立,并且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3〕其在巩固政权、战争动员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研究却相当薄弱,专门论述苏区时期贫农团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笔者曾在拙著《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和《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对贫农团有所阐述,但言未尽意,仍感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故本文力求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宽加深,对苏维埃政权时期贫农团作一较为系统性的历史考察。
一、贫农团的由来与背景
贫农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愿性群众组织,亦是大革命时期农会组织的承续和发展,其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建立贫农团是纯洁革命队伍、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需要。1929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工农兵苏维埃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政权机关,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工人农民兵士及其他贫民利益去决定”,〔4〕可见党在建立苏维埃之初即已申明该政权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根本目标是确保劳苦民众的利益。但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际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不少地方的小地主和富农分子“混入各级机关,操纵把持苏维埃”,“秘书专权专事,也所在多有”。〔5〕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也曾发表通告,针对苏维埃中“地主富农当选”的情况,要求同那些代表地主富农思想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6〕1933年10月,作为川陕苏区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在《苏维埃》第11期发表的《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一文中列举了该地区地主富农混进苏维埃的几种办法后,特别强调“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是最重要的任务”。〔7〕
1932年,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在3月2日第6版、5月25日第8版先后发表了《反对浪费严惩贪污》《反对散漫与腐化的苏维埃政府》等文章,揭露和批判了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种种官僚作风问题,并且披露了在川陕地区甚至出现了苏维埃主席由富农担任的情况。〔8〕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建立贫农团这一苏区群众组织便被中共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其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柱石,“加强政府工作能力”。〔9〕
其次,建立贫农团是反抗国民党对于农会组织进行摧残、造成斗争新气势的形势需要。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先期创建的农会组织曾给予认同和扶助,譬如国共合作举办农民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分子,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分赴各地以发展农民协会等。但由于国民党内存在的左右两派对扶助农工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因此在农会政策的制定上呈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矛盾性,即一方面认可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农会组织,另一方面又不认同其实行的革命路线;一方面“借助于共产党在组织民众运动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对其“心存疑虑直至最终走向清算”。〔10〕而在1926年4月国民党二大上通过的《肃清共产分子案》,则标志其对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会组织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从心存疑虑变为公开“声明共产分子假借本党活动”。〔11〕随后伴随其清党运动的开展,对农会组织和农民运动进行了全面清算,在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进行疯狂报复”。〔12〕如在江西,1927年6月5日反动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出动。吉水劣绅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劣绅拘捕农协执行委员;铜鼓农会以及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更大肆残杀农协职员。又如在湖北,夏斗寅、杨森等相继叛变革命后,每到一处便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农会会员被杀者分别为天门20余人、沔阳20余人、嘉鱼30余人、咸宁50余人、武昌50余人、罗田60余人、黄安100余人、钟祥200余人、枣阳500余人、麻城500余人、随县1000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圻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施行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等残酷刑罚”。〔13〕据全国农协1926年6月初步统计,“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14〕同时,1928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开始了重建农会工作,企图以此避免农民运动“更蹈”大革命时期那种“完全让共产党给包办”之“覆辙”,巩固其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统治。〔15〕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反抗国民党对于农会组织的血腥摧残,同时也是为了有别于国民党重建的农民协会的名称,贫农团这一新型的农会组织应运而生。
最后,建立贫农团既是共产国际最高指示的结果,也是中共中央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贫农团”的名称最早来源于1930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其中明确指示,苏维埃土地革命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贫农团……使苏维埃机关底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16〕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亦强调指出:“雇农苦力以及其他乡村的工人都应当参加贫农会”。〔17〕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关于建立“贫农团”的这些最高指示,无疑促进了贫农团等农会组织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的步伐。193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进一步要求苏区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贫农团,并且再次强调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18〕翌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苏维埃区红五月运动工作决议案中要求各苏区“必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成立起来”。〔19〕随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以及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贫农团这一新事物便在各个苏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
二、贫农团的发展过程
纵观土地革命时期贫农团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初步建立、广泛兴起和逐步消退三个阶段。
(一)初步建立(1930年6月—1932年6月)
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直接领导的农会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摧残,其组织活动基本停止,革命高潮时曾经发展到915万人的农会队伍“现在大部被打散”。〔20〕但是,随着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各地武装起义的爆发和井冈山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重新恢复和大力发展农会组织又被重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27年1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并强调指出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组织”和“暴动的组织”。〔21〕随后,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22〕尤其是如前所述1930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以及10月中共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下发后,贫农团这一新型农会组织在苏区开始初步建立。不过,从整个苏区来看,其成立范围不大,数量不多,“贫农团亦只在赣西XX地方建立了,大多数都是没有”。〔23〕而且此期各苏区建立的则是名称不一的农会组织,或“贫农团”或“农民协会”或“贫农会”或“农民委员会”等。“尽管名称不同,其组织形态则无有大异,当均属于农会组织的范畴。”〔24〕
(二)广泛兴起(1932年6月—1934年6月)
1932年以后,随着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逐渐展开,贫农团组织的发展呈迅猛之势,尤其是在1933年,仅中央苏区8县贫农团成员即有149000余人;〔25〕湘赣11县先后组织起了87个贫农团,其会员达到25783人。其中吉安白区贫农团有7个,会员323人;分宜县贫农团20个,成员3389人;枚县贫农团7个,会员178人;莲花县贫农团会员2632人;萍乡县贫农团会员195人;安福县贫农团成员10123人。〔26〕
(三)逐步消退(1934年6月—1937年7月)
从1934年上半年开始,尤其是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后,由于广大苏区陷入敌手,因此各地贫农团组织逐渐走向消退。而随着查田运动的结束,贫农团的活动也就由“日趋减少”最终走向了“停止”。〔27〕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被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归于国民政府领导,于是作为各级苏维埃政权基础的贫农团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时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在抗日根据地“须要组织”建立起来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联合会”等农会组织,成为“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28〕
三、贫农团的组织结构
为了指导和规范贫农团的活动,中央和各苏区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主要有1931年8月28日和11月16日先后制定的《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贫农团问题的决议》,以及1933年7月15日制定的《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等,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厘清贫农团的组织构成。
(一)会员资格
贫农团对其成员资格要求比较严格,主要由贫农和雇农组成。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曾规定贫农团的会员资格主要为:(1)“耕种田地不够养活家庭还须出卖劳动力的贫农及其家属”;(2)“专门出卖劳动力做长工或短工的雇农苦力及其家属”;(3)“直接对老板或对包工头出卖劳动力的手工工人”;(4)“最积极勇敢的游击战士”。〔29〕在两天之后8月30日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案》中,明确规定贫农团组织成分“系雇农、贫农、苦力、手工业工人”,“无条件的洗刷富农,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30〕在随后11月16日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贫农团问题的决议》中亦明确规定:贫农团“在反富农的斗争中应分析清白”;不允许中农加入贫农团组织,但“中农参加贫农团会议或旁听是可以的”。〔31〕
综合以上三个文件不难看出,贫农团的主要成员是贫农和雇农,地主和富农被绝对地禁止加入,甚至中农也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加强无产阶级在群众中的领导权”等有关。〔32〕
(二)入会程序
贫农团在成立初期,其入会程序较为简单,无需个人写申请报告,也无需他人介绍或者审查。譬如1931年1月8日的《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即曾规定:贫农团“都是由雇农发起或贫农同志发起,先由少数人组织,以后由贫农自动加入”。〔33〕但此后不久,贫农团的入会程序便有了较大变化,逐步严格了加入程序及其审查制度。例如在1931年8月28日的《湘鄂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凡自愿加入贫农团,有一人之介绍,经过审查者,都可为贫农团会员”;〔34〕1933年7月15日,在由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等联合署名发布的《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中强调:“加入贫农团是以自愿为原则,一切男女老少的工人贫农,均可报名加入”,但要“保障贫农团不被地主富农混入”。〔35〕
(三)组织构成
贫农团的组织结构较为简单,没有完整而严密的全国—省—县—乡—村等垂直层级组织系统以及组织章程,最高设至乡(区)一级,乡之下分为小组,一般以一个村庄为一个小组。由于“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故“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的组织,只是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36〕而“赣东北苏区甚至只设村一级组织”。〔37〕
干事会是贫农团的重要议事机构,负责处理全乡贫农团大会闭幕后的一切事务。其讨论范围包括怎样反对富农以及讨论上级通告决议案与实施方法,如何依法解决土地问题和生产工具、种子、肥料,以及计划耕种收获与合作社食粮储藏调查等各种问题。〔38〕
(四)组织运作
1.选举制度。从有关具体的史料来看,苏区各地贫农团均实行了严格而民主的选举制度。譬如,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就明确规定:“贫农团委员会委员由贫农小组推举或者全团大会选举产生”,介绍或开除团员应“由单个或少数贫农提出,在小组会通过,经委员会半数通过”。〔39〕又如在《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亦曾规定,贫农团根据乡的大小和会员的多少,由大会选举3—5人“组织委员会,由委员会推定主任一人,主持全盘工作”。〔40〕
2.会议制度。大量史料显示,苏区各地贫农团的会议制度亦较为规范。如在《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中明确规定,“凡遇到重要问题,即召集全体会员开会讨论”,“只有平常的问题,才单由革委会讨论,或由委员会召集小组组长参加讨论”。〔41〕又如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干事会每七天一次,小组会每十天一次,组长联席会、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由干事会临时决定召集之”。〔42〕
3.组织经费
对于贫农团的办公经费及会员会费,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以及《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贫农团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中,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即贫农团“不需要如工会一样的严密的组织形式,不需一定的章程,也不需要缴纳会费”。〔43〕其办公费“可向富裕的人募得或由苏维埃帮助,会员不要入会金也不要月费”。〔44〕
四、贫农团的主要活动
据笔者所搜集到的史料来看,苏维埃政权时期贫农团开展的实际活动内容相当广泛,兹就其荦荦大端者略述如下:
一是领导分田、查田运动。据史料记载,在苏区土地分配的实际工作中,各地贫农团坚持“经常参与讨论苏区土地分配问题”,“决定整理和重新分配的办法和进行工作的方式”。〔45〕正是在贫农团的组织推动下,一场“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46〕的土地分配运动在各个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二是组织扩红、拥红运动。自从1930年以后,为补充兵源不足问题,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其中贫农团发挥了突出作用。1930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兵士补充工作中“农会更可以群众大会议决某区某村派选多少农民加入红军”。〔47〕1932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号召,“要运用一切组织上(如工会、贫农团等)的会议来进行经常的扩大红军工作”。〔48〕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贫农团的带领下,苏区的拥红和优红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例如,“湘赣全省三个月就扩大了6740名红军”。〔49〕
三是进行苏区经济建设。为了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保障军需民用,贫农团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采取各种措施,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例如“由贫农团等组织发起组织农业生产竞赛委员会,发动群众加紧耕种和开荒”。〔50〕又如广泛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领农民建立生产、消费、农具、种粮、犁牛等各种合作社,建立劳动互助组、模范耕田队等,以及“兴水利,开荒田,修道路等”。〔51〕苏区开展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活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军需粮食的供给,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是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例如在改善交通方面,各级苏区贫农团积极带领群众参加修路运动,据史料记载,闽西苏区到1932年底,修路500余里;江西仅兴国县到1933年底就修路520里。〔52〕又如在改善衣食方面,赣南贫苦农民的衣着比革命前改良了一倍,“过去能做1元钱的衣服,现在可做2元的了”;兴国县长冈乡雇农“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农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苏区农村的建设和稳定,同时“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53〕
五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苏区教育在以国家办学为主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以及私办学校。1934年4月,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列宁小学生组织大纲》中,要求各地小学与贫农团等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依靠这些群众团体资助办学经费,并请他们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苏区贫农团以及其他群众团体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为了提高苏区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还发动群众捐钱给教师发奖金”。〔54〕正是在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苏区的教育事业呈蓬勃发展之势。据1933年赣、闽、粤三省文教事业发展不完全统计,在三省共计2931个乡中,分别拥有3052所列宁小学,89710名学生;6462所补习夜校,94517名学生;32888个识字组,155371名组员;1565个俱乐部,49668名工作人员。〔55〕
六是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在苏区广大农村,受千百年的传统影响,村民卫生意识非常薄弱,卫生环境极差。诸如弃死婴于河内、死猪死禽随地乱扔、生病卜卦叫魂等,恶俗陋习比比皆是。而国民党对苏区的屡屡进犯,致使这种状况更为加剧,各种烈性传染疾病发生频仍,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危害。据此,1933年苏区政府及时颁发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群众团体带领全体群众一起“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斗争”。〔56〕随后,贫农团等群众团体雷厉风行,保证了苏区卫生防疫运动的顺利进行,且成效显著。
五、贫农团的组织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苏区贫农团所开展的诸项活动,表明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贫农团的组织性质
在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对贫农团的性质曾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贫农团是用以进行反富农斗争而团结中农在其周围的。贫农团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起,它是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它的组织成分应包含贫农雇农苦力及乡村中其他工人”。〔57〕在1933年7月颁布的《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中亦明确规定道:“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在苏维埃管辖区域内的广大贫农群众的组织”,“贫农团的作用是赞助政府实现政府的一切法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关系于工人贫农的利益与权利的各种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58〕据此,对于贫农团的性质我们不妨概括为以下几点加以理解:首先,贫农团把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贫雇农组织了起来,故其是代表贫雇农利益的群众性组织;其次,贫农团组织农民开展的分田和查田运动、拥红和扩红运动以及进行苏区经济建设、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等,充分显示其在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文化动员中的职能作用,故其是一种社会动员组织;再次,贫农团机构简单,只有乡、村两级,故其是最基层的群众组织;最后,贫农团既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建立并开展工作的、又有监督苏维埃政府工作以及提出自己的候补名单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基本权利,故其是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基层群众组织。
(二)贫农团的历史地位
从中共中央和各苏区政府制定的有关文件以及各地贫农团制定的组织章程,尤其是贫农团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来看,苏区贫农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整合了乡村社会一切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譬如贫农团所开展的扩红、拥红运动,大大促进了苏区青年农民的参军高潮,壮大了红军队伍,从而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贫农团所进行的组织动员群众慰问红军以及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侦探队、向导队等一系列活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前线的武装斗争;贫农团所开展的生产竞赛活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农业的丰收,保证了革命战争和建设的需要;贫农团所开展的文化动员,则培养了大量的革命人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其次,推动了乡村的土地改革,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苏区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分田和查田运动中,贫农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依靠广大的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其带领人民群众,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没收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拥有土地的梦想。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使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做了社会的主人,而且使他们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彻底的翻身,从而激发了他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宣传贯彻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树立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地位。贫农团一再强调申明:“贫农团应受乡村苏维埃政府的指导”。〔59〕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才能正确的实现他的一切任务,不致受富农的影响,不致受一落后区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贫农团的工作,在于随时能注意到工人贫农以及中农的利益,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而斗争。”〔60〕正是基于对组织自身职能的这一明确定位,贫农团在组织和带领群众参与苏区建设工作中,分别采取了编印画报、壁报、传单、小册子等多种方式,宣传贯彻了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用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及生产积极性,从而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辉煌战绩,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树立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带领群众开展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活动,发挥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作用。如前所述,贫农团领导苏区人民所开展的分田查田、扩红拥红、农业互助合作、卫生防疫等运动以及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等举措,充分表明贫农团已逐步树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已经成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和教育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斗争的战斗组织”。〔61〕对于贫农团所发挥的作用,各地党组织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在1931年6月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政治报告》中,称“贫农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巩固的骨干”;在同年8月14日的赣东北《曾洪易向中央的报告》中,称“贫农团一般的说来,在斗争中的确是勇敢积极的”;在19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四个月工作总结报告》中,称“贫农团在诸项经济政治斗争中的确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同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称“贫农团的组织能够吸引群众,推动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已经是各种组织所不及的事实”;等等。〔62〕
注释:
〔1〕李永芳:《清末农会述论》,《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24〕〔51〕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3、513、520-521页。
〔3〕〔18〕〔57〕《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430、454、454页。
〔4〕《苏维埃组织法》(1929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5〕《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页。
〔6〕《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三号》(1930年6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6页。
〔7〕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30日),原载《苏维埃》第11期,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2-1543页。
〔8〕《苏维埃主席是富农,就乱没收中农,拴打工作人员》,原载《苏维埃》第8期(1933年10月3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8页。
〔9〕《赣西南工作综合报告》(1931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1988年内部版,第263-264页。
〔10〕〔13〕李永芳:《扶助 疑虑 清算: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农会政策》,《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11〕《肃清共产分子案》(1926年4月4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19页。
〔12〕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14〕《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1927年6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53页。
〔15〕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农民运动方案》(1930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85页。
〔16〕《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17〕《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193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5页。
〔19〕《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1831年3月21日),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20〕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1-42页。
〔21〕《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3页。
〔2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四、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0-211页。
〔23〕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5页。
〔25〕《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全会上讲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2-603页。
〔26〕〔6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6、90页。
〔27〕〔54〕〔56〕余伯流、凌布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8,71、783,860页。
〔28〕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3页。
〔29〕〔39〕〔42〕〔59〕《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88、90、90、57页。
〔30〕《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案》(1931年8月30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31〕《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贫农团问题的决议》(1931年11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档案馆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2页。
〔3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7页。
〔33〕《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1年1月8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34〕〔44〕《湘鄂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88、90页。
〔35〕〔36〕〔38〕〔40〕〔41〕〔43〕〔49〕〔58〕〔60〕《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1933年7月1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67、67、68、67、67、67、63、67、67-68页。
〔37〕〔62〕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36、139页。
〔45〕〔50〕湖南、湖北、江西档案馆等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0、136页。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47〕《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
〔48〕《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1932年9月),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52〕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71-172页。
〔53〕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6-248、309-312、321-329页。
〔55〕《赣、闽、粤三个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统计》(一九三三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辑》第四册(1931.9-1937.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