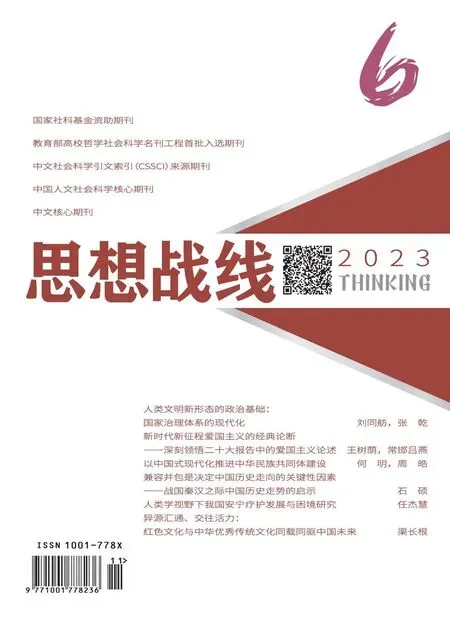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的田野工作与人类学研究
段 颖
随着科技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非人世界的重要连接,甚至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存在状态。人类学关注网络现象已有时日,研究焦点从最初的复杂连接、互联互通、网络文化逐渐转向虚拟世界、人机互构、数码革命、网络原住民乃至后工业时代人类状况的探讨,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络人类学(cyber anthropology)、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甚至延伸至赛博世界中数字、信息、系统、政治、技术、生物纠缠共生的探讨。(1)Escobar,A.,Hess,D.,Licha,I.,Sibley,W.,Strathern,M.,&Sutz,J,“Welcome to Cyberia: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Current Anthropology,vol.35,no.3,1994,pp.211~231.(2)Downey G L,Dumit J,Williams S,“Cyborg Anthropology”,Cultural Anthropology,vol.10,no.2,1995,pp.264~269.(3)参见Palfrey,John&Urs Gasser,Born Digital:Understand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Digital N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2008.(4)参见Sanjek,Roger and Susan W.Tratner eds,eFieldnotes: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in the Digital Worl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5)参见Hjorth,Larissa Heather Horst,Anne Galloway,and Genevieve Bell 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Erhn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6)参见Haidy Geismar and Hannah Knox eds.,Digit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2021.(7)参见Haraway,Donna J,Staying with the Trouble:th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而与之相关的田野工作,也从特定时空下相对稳定的地方、社群与文化,转向由方寸键盘所连接的弹性、变动、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和转折,从最初作为快捷通信技术的电子邮件,到BBS等网络社区(8)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的出现,再到QQ、微信等虚拟社交网络的推出,再到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生活平台的流行,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所促成的新一轮城乡关系(9)姬广绪:《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社会流动(10)Qian,Linliang,“The‘Inferior’Talk Back:Suzhi(Human Quality),Social Mobility,and E-Commerce Economy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7(114),2018,pp.887~901.、数字劳动(11)钱霖亮:《低度包装与本真性展示——中小带货主播的阶层化数字劳动》,《浙江学刊》2021年第3期。与信息时代新工人阶级的形成。(12)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线上线下的互动,虚实之间的多方合力,共同塑造着网络生态,以及人们与所在世界的关联。而人们逐渐“习以为常”的大数据与平台经济,所呈现的不单是人机结合的赛博空间,更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驯化与社会治理。(13)Sun Ping,“Programming Practices of Chinese Code Farmers:Articulations,Technology,and the Alternative,China Perspective.2018(4),pp.19~27.而学者对虚拟世界与网络社会的关注,也逐渐从网络人类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的介绍、探讨,(14)刘华芹:《网络人类学:网络空间与人类学的互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15)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和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转向少数民族微信群(16)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数字平台的时间性劳动(17)Chen,Yujie,Sun Ping.“Temporal Arbitrage,the Fragmented Rush,and Opportunism:The labor politics of time in the platform economy”,New Media and Society,2020.4(1),12~27.等更为深入的案例研究,以及将进入日常生活的网络信息技术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实践加以讨论和反思,(18)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19)孙信茹,王东林:《作为“文化实践”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进而探索信息、科学、技术对更具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可能带来的研究范式转型。
由上可见,由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衍生的各种新生现象均对人类学之田野工作与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无疑,人类学研究需要面对时时处于虚拟与现实之间,人机混融状态之下的具体的人,如何呈现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广泛影响,如何对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社会文化现象产生即时回应,又如何拓展人类学网络研究的进路,同时与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相关联,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加以审视,相对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虚拟民族志与数码人类学的时代性与反思性又是如何,凡此种种探索与追问,亦即本文论述之缘起。
一、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的崛起
事实上,关于万物互联的讨论,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的提出及其对电子媒介文化图景的勾勒(20)参见[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即可视为全球连接、时空压缩以及信息时代的前奏。而对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更见于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21)即《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卡斯特从技术革命、网络社交以及信息社会化等角度切入,着力探讨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并重新审视信息时代下结构与权力之间的新型关系,由此探讨信息时代的人如何自处,又如何与世界相联。
网络社会的崛起有其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后工业时代生产关系的变革、资本的弹性积累、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福利国家的式微,以及与这一系列的结构性变迁相伴的以公民权利、女性主义、环境保护、文化自主等议题为焦点的文化社会运动。而信息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特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国家、社会、民族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个体连接甚至重构社会提供了新的平台及可能。
那什么是网络社会?显然,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不同,网络社会是由一个个没有中心的节点连接而成,具有灵活性、开放性、暂时性和可拓展性的一种活态的网络链接与信息流,网络社会随时处于由“网络之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所推演的“网络化(networking)”状态当中。虽然是通过亿万台电脑与通信设备完成的连接,但网络社会却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使用,极大地体现出终端的个体化与流动性,既体现出信息技术的全球消费与政治经济过程,又切实改变着人们沟通、交流以及获得信息的方式、移动的能力以及与世界相联的可能性(22)Horst,Heather,“The Anthropology of Mobile Phones”,in Haidy Geismar and Hannah Knox eds,Digit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2021,pp.65~84.,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经常讲,在信息时代,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网络。
卡斯特进一步解释了网络社会的文化,强调并不是在网络社会里建立新的文化价值观,而是突出共享的通信价值,亦即,在网络沟通与共享中,过程甚于内容。在此过程中,人们在共享资源的同时,也共享着交流的权利,“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文化意义网络,各种文化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能在交流的基础上彼此交互并互相改变(23)[英]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以信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及其所拓展的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基础——时间和空间。在此之前,我们所在的空间都是以具身体验来感知的,即,现实的在场(real presence),并与地域性、方位感以及与具体的地方(place)为基础所延伸出的功能、意义与实践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空间变得虚拟起来,所谓“地方”,也逐渐成为一个个所属网络的节点——以事件、议题为基础的信息流的汇聚地,以及身处节点中的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之呈现,即,“虚拟在场”(virtual presence)。由此,空间不再固定,从“静止”转向“流动”,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也日渐松动、模糊。
而对于时间的感知也变得更加动态、多元、复杂,既包括农业时代以来依照四时节气运作的自然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时还有工业时代之后被广为接受的标准化时钟时间,其建立的基础源于契约、分工与社会合作;再加上信息时代之后,一种无时间感(timelessness)的序列时间逐渐涌现。人们可以利用互联互通,更加有效地克服时差,实现更为快捷、有效的信息共享,比如各类公开课程以及跨时区的商业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自然时间、工业时间与序列时间并不构成递进或替代关系,而更体现为一种多重时间观的叠加状态。
二、网络世界的变化与趋向
以时间与空间为基础的经验世界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人的存在境况,从生产、消费,到沟通、交流,再到亲密关系、生死爱欲,无所不及。而今,嵌入式的互联网生活已成日常,如我们经常谈到的“宅男腐女”现象,事实上,他们身虽不动,但心却无时无刻经由网络与外界相连,即所谓的“精神沉浸,肉身疏离”,个体通过网络中的信息交换与互动,完成对世界的远距离接触与想象,自由与依赖并存。而当我们的生活进入到这样的嵌入式状态以后,网络就不仅是最初互联互通的交流工具,不同的行为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在网络世界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自己,完成着自我塑造(self making)。
此外,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境遇与状态不大相同,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活动会留下很多印记,虽说在现实语境中“凡走过,必留印迹”同样存在,但其承载、传递形式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与常态的叙事、情感、记忆、联想不同,在线痕迹成为我们理解“网民”所思所想,乃至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重要依据。凭借日趋成熟的数字技术与大数据系统,我们可从智能手机的使用状况直接或间接地追踪、记录、呈现出人们的日常行程、消费习惯、甚至情绪、偏好,并通过大数据计算,结合人的饮食、休闲、工作、旅行、朋友圈、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亲密关系等生活细节,确定人们的需求和喜好,甚至推演出人的择偶倾向,模拟从恋爱到婚姻的类型选择、成功率及可能性。
当然,关于人类的欲望、情感是否能“标准地”转化为大数据演算仍存在不少争议与质疑,但大数据支持之下的技术行为和社会实践的互构却已悄然渗入人们的生活。比如,大家会通过手机或电脑经常关注体育赛事、娱乐节目或时政新闻,大数据便会依此形成基于个体偏好的推演计算,然后在个体使用媒介平台时在首页或者在选择相关议题时弹出依照个体偏好“自动”挑选出来的信息,久而久之,这些信息无形中影响着个体对世界的认知,这就回到了鲍德里亚所言的拟像世界,(24)Baudrillard,Jean,Simulacra and Simulation,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数字化世界所建构的并非图景,而是现实本身,只不过在网络时代,镜像之现实变得更加个体化而已。换言之,人们生活在网络当中,对世界的认知更多以镜像化的状态呈现出来,而作为非人的行动者,网络反过来也在追踪人类的行为,在想象与现实的相互形塑和融合中,完成真实与虚拟之间的互构。
除了以上提到的在线痕迹之外,以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世界,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留存和记录过去的信息。这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感知与理解,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人们有可能重塑记忆和记忆模式。比如,在人机结合的环境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处理选择性记忆与结构性失忆之间的关系。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逝者建立联系,虽然斯人已逝,但是他曾经登录的页面、使用的公号、博客或者Twitter、Facebook还在,除非他的继承人或者后继者授权清空(而逝者存留信息的主权归属,也是网络社会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所以,技术变革之下,我们还可用这样的形式找到跟逝者的联系,唤起往昔记忆与共情,让人明了,即使逝去,生命意义仍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这也是信息时代时间逃逸的又一体现。
再者,大数据的运用自然会涉及关于算法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多少都生活在算法控制之下,但必须留意算法背后存在的深层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与现实世界发生着非常深远的交互作用,算法并非不能简单视为“科学”的程序和计算,更是一个需要被问责的社会技术系统。(25)Nick,Seaver,“Algorithms as Culture:Some Tactics for the Ethnography of Algorithmic Systems”,Big Data &Society,vol.4,no.2,2017.pp.1~16.如数据或信息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某些信息和数据并非全民共享,因此,如何获取,获取之后如何使用,使用过程中,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会不会生成新的知识,都成为亟需思考的议题。此外,可及性也需要突破“习以为常”,比如搜索引擎,总体而言,搜索引擎相对公平、快捷地为人们提供所需信息,但引擎本身也有逐渐商业化的趋势,比如第一时间弹出广告。而一旦考虑到搜索引擎的设计者依旧是人,那么,当我们输入某些关键词时,其联想和关联到底指向何处,是点击率、数据源选择,还是程序员偏好,网络中的任何行动者都有可能影响搜索结果。又如,我们平常会使用各种网络平台,涉及购物、出行、交友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平台本身也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输出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塑造着参与者体验、文化表达与自我认同。
当然,当人们看似在网络世界自由驰骋时,还需注意到网络依旧与现实社会相连,也是一个潜在的政治经济场域,网络的基础在于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是需要有数以千计的服务器相互支撑,这就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网络基础设施。如果从全球数码环境而言,世界范围内的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典各占1个,所以,基于通信协议所建立的互联互通,一旦发生意外或者遭遇战争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则不能排除根服务器中断或者被局部控制的可能。因此,网络世界并非一马平川,信息时代的不平等参与,依然不时地将人们从理想拽回现实。
另外就是技术潜力、资源配置和知识局限的问题。在当今中国,随着社会发展,村村通网络正在逐步实现,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全球互联互通,就会发觉网络的通达依旧逃离不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比较差异与中心边缘格局,在笔者做调查的泰国、缅甸,还是有大量地区网络无法覆盖。而即便网络基础设施便捷,使用网络的人群的知识差异,如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的不适,数字城市建设中对可及人群考虑不周等,都涉及网络世界之外的隐形权利关系。
就此,倘若再论可及性,网络世界中,谁在看、听、用,如何看、听、用?值得进一步延伸、探索。首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很顺利通畅地通过网络连接世界;其次,每一个人连接网络的目的不同,网络当中信息源提供者的潜在目的不同;第三,网络既然同时与现实社会相连,自然也会与国家治理或社会舆论连在一起,比如各种网络屏蔽现象,还有网络当中因算法逻辑在无形中被过滤掉的信息,其后的运作逻辑值得深思。最后,也是最为显见的,如果网络世界被资本控制而逐步商业化,那么,开放的网络依然会被重新置入一个密码保护的封闭世界(26)Lievrouw,Leah A,“The Next Decade in Internet Time:Ways Ahead for New Media Studie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vol.15,no.5,2012,pp.616~638.。现在很多信息平台开始实行收费会员制,这实际上消解了网络社会构建之初的互联互通以及开源共享的生态环境。
三、田野工作、虚拟民族志与反思人类学
那么,在网络时代,如何开展与之相关的人类学调查与民族志研究?众所周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基本保持三段式的进路,无论成果如何,人类学者总是需要去到调查地,进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再返回其生活之地,根据田野中的观察、体验与思考,撰写民族志。总体而言,传统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跟身体位移有很大关系,涉及人类学者本身的时间、空间、注意力、兴趣偏好和有限的在场。因此,传统的民族志写作自然会面临预设时空边界和写作延时的问题,从去到回,再到民族志呈现,人类学者可能甚至必然会“冻结”历史或是现场的人,我们只能写到某个时间段,等到民族志或相关学术著作出版,离我们的现场参与和观察,至少已时隔三五年,换言之,当人类学者撰写民族志的时候,民族志本身成为“在场”的终结,人类学者虽说研究“当下”,但实际上书写的是一种已成历史的状态,我们很难借由频繁、及时、即时的信息沟通呈现、回应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变化,这就与网络研究与虚拟民族志形成了巨大反差。
就此而言,网络时代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身处网络之中,时空逃逸可以使我们以开放、非线性的方式收集信息,通过网络,我们可以随时与我们在泰国或缅甸的朋友联系,随时连线到远方的田野,知道当下他们的状况,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田野的时空限度。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田野,因为信息载体和记录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某种意义的可逆性,通过在线痕迹,依托文本叙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回到”原有的田野状态当中去。人类学者可以通过文本阅读,分析、思考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文和互动,借由不断地重新编辑和多重解读获取信息,进而重组经验与知识序列,为避免在单一模式下描绘世界提供新的可能。
在此情景下,虚拟民族志就不仅仅是传统民族志的拓展,而成为人类学探索世界的新路径,同时又因其自身的特色以及关注焦点的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27)Beaulieu,Anne,“Vectors for Fieldwork: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New Modes of Ethnography”,in Larissa Hjorth,Heather Horst,Anne Galloway,and Genevieve Bell 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Erhn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pp.29~40.
首先是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主要聚焦与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人的认知、情感与实践,(28)参见Hine,Christine,Virtual Ethnography,London:Sage,2000.如线上线下互动,网络世界的信息流又如何回馈到现实生活之中。在实际田野里面产生的田野感和在信息模式当中所产生的话语流如何相互参照,网络环境中,民族志研究的潜力何在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其次是媒介民族志(Mediated Ethnography),更多关注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共享材料,沟通形式如何,在媒介的互动交流以及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当中有没有权威性存在,这与传统的民族志写作不同,人类学者去到田野点,在那里长期生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获之共享经验,加之理论的积累,即可支撑后期的民族志写作和人类学知识生产,但网络的状况与此不同,我们需重新思考,基于网络共享的资源与文本分析,所谓的“田野感”何在,虚拟民族志写作是否与传统民族志一样,具备某种意义上的权威性。(29)Horst,Heather,“Being in Fieldwork:Collaboration,Digital Media and Ethnographic Practice.”In Roger Sanjek and Susan Tratner eds,eFieldnotes: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in a Digital Worl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pp.153~168.
再者为计算民族志(Computational Ethnography),计算民族志强调网络世界不是当然存在,而是与互联网设置、大数据运算逻辑、数字化信息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这就涉及人与非人的世界如何相联,比如,代码作为语言的一种工具形式,在信息技术变革中,计算变得更加突出,那么,人在其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同时,算法的交互作用、计算及其生成潜力,也成为该领域关注的议题,而其潜在的目的,就是把技术重新拉回人的世界。(30)Wellman,Barry,“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Science,vol.293,no.5537,2001,pp.2031~2034.
那么,在网络世界中,何处是田野,又如何做田野?于此,从事网络研究的人类学者已有不少探讨。(31)参见Sanjek,Roger and Susan W.Tratner eds,eFieldnotes: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in the Digital Worl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32)参见[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伟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首先,网络作为媒介载体以及信息集散地,其连接的各端其实就是天然的信息源,网络研究的田野素材可以来自于博客、播客、公众号、短视频、网络游戏、多媒体期刊,以及线上线下的互动,非常多元、丰富。其次,我们需重新思考在网络世界里如何建立融洽关系。研究者可能会产生长时段和沉浸式的体验,比如参与网络游戏小组,如果研究者喜欢游戏,那本身就可能是长时间的参与者,或者身处某一粉丝团中,共同喜欢某一偶像,参与观察线上线下的互粉活动,并在融入与抽离之间,考察与他们的共情与差异。
当然,在建立网络关系时,也需要承认网络嵌入的即时性、碎片化、短暂性与模糊性,这实际上是网络情景与网络关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们漫游网络,并没有太强的目的,而处于一种无意义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怎样处理随性的聊天、即兴的互动以及顺意刷短视频时所产生的相对放松的情感体验,或者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网民能够产生所谓精神式的沉浸抑或冲动,又如何捕捉意想不到的信息,都需重新考虑,毕竟跟现实世界的田野中寻找关键报道人大不相同。
第三,注重互文性的考察,在网络世界的即时空间中,会产生多元多样的文本,一个主体文本出现以后,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评论,赞成、反对、客观评述、情绪表达同时存在。需要留意文本的互文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尤其是由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信息流,注意聚焦观众、表达意见、对话细节以及聊天日志中所呈现的参与者的性格特征与表达方式,并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文本分析,于此,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话语分析对于网络研究而言至为重要。
第四,设计在线调查。尽管不能面对面接触和访谈,但仍需注意线上访问时可能涉及人际关系、兴趣、习惯的细节信息,同时,重视随机的情景分析,即时出现的状况,可能会连带出预想不到的结果。此外,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共享,营造网络独特的互动氛围,在网络中,参与者可能期待看到结果分析,这也是数码技术可见性的体现,实际上为调查者创造出更多元的讨论空间,比如,我们用APP制作问卷,因为网络的即时性与开放性,参与者能够及时或较快地看到结果,甚至产生回应和互动,这样也会促使问卷设计者重新考虑的调查研究的效用与公共性,而非局限于专业的学术分析。反过来说,如果网络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通达民众的路径,这自然也会提升网络研究的参与感、真实性与社会影响力。
第五,信息留存。与传统田野调查不同,网络本身作为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库,我们的网络活动,以及我们在网上说过的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将所记录下来的文字视为一种场合,非常重要,这其实就是文本或者文本所涉及的情景,对于网络人类学而言,这就是网络世界中的田野点,在这里,文字内容、表达形式、具体语境同时留存下来,可供研究者不断复盘、利用和分析。
第六,在线痕迹分析。在信息时代,无论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消费倾向,还是一天的运动指数、生活轨迹,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以痕迹追踪的方式在网络中呈现和保留下来。现在很多人开始用APP来控制饮食,保持健康,或依托不同类型的APP计算每日步数,测量心率体脂,这些日常操作无形当中都会被大数据系统所记录,关键在于数据是否会被公开,或者会否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分析和解读。
网络世界的特殊性质推动人类学者更新思维,以更加贴近网络情境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创造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而在网络研究中拓展出来的方法,并不是对传统人类学田野与民族志方法的取代,反而会形成有益的参照与补充,尤其是对细节的把握、文本的分析、话语的阐释,以及相关语境的考量,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于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中的具体的人,并由此思考信息、技术的变革对人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今,网络可谓无处不在,但人却不能,也不可能时时生活于网络之中。
四、数码人类学的特征、原则与实践
因此,数字技术乃至网络社会对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仅存于虚拟世界,更多表现为真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的结合、互构与连动。数码记录不可能完全反映我们所在的世界,重返现实也是生活之必然。所以,对网络世界的关注,同时需要与线下的现实生活相互配合,当我们把线上线下视作前台和后台时,彼此之间如何相互转换,比如,很多短视频播主,线上展演与线下生活究竟如何,差异在哪,他们又如何面对在真实与虚拟之间不断变换的双面生活。
再者,线上线下的关系,也可能反映出流动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笔者曾经关注过一个约饭APP,顾名思义,就是城市饕餮的饭局社交平台,生活在同一城市互不相识的人们在此分享美食信息,相约餐聚,饭局主题是美食,间或吐槽各自的工作、感情和生活,正因彼此不熟识,反而无拘无束,吃完饭后就各回各家,也许再见,也许不再相见。这样的网络社交,也包括诸如宠物爱好者、同人小说迷以及二次元cosplay群等等,映射出现代都市陌生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从传统社会关系脱嵌之后又通过网络重新构建的松散连接,他们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结伴”,但又不想彼此承担责任,过多牵连。
而今,还有很多网络互嵌式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紧密相连,如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逐渐成为年轻人的生活空间,在与更为广泛的世界相联的同时,身心的疏离却导致了现实世界中附近的消失,人们即便坐在一起,却依然沉迷于各自的社交媒体。当然,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完全不同的面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手作艺人利用短视频呈现手艺的世界与手艺人的日常,虽是虚拟世界中的表达,但却关乎他们的生计发展与现实生活。再如,由政府推动的数字化农业,通过网络将消费者、企业与农民整合起来,创造城乡之间的新型连接,试图弥补由城镇化发展所造成的悬浮与断裂。可见,网络以及社交平台,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与集散地,而是集媒介、生产、消费、价值、观念为一体,成为人们的生活之境。
这就引出了关于数码世界的人类学研究,一个超越网络本身,连接虚拟与现实,反思技术与社会,理解数码文化与人的存在,探索人类可见未来的新领域。于此,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可谓数码人类学的开创者与领军人物,米勒长年致力于探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交生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早在十余年前,米勒就与霍斯特合著《数码人类学》,(33)[英]丹尼尔·米勒,[英]希瑟·A.霍斯特:《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在2021年新版中,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数码人类学的基本原则,(34)Miller,Daniel and Heather A.Horst,“Six Principles for a Digital Anthropology”,in Haidy Geismar and Hannah Knox eds,Digit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2021,pp.21~43.结合案例研究,探讨在网络社会与信息时代,什么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与新实践,而什么又保持不变。
首先,Miller强调,数码本身事实上强化了文化的辩证本质,无论数码世界多么丰富多样、碎片杂糅或变动不居,但数字技术的深层逻辑恰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基础状况,以数码世界最多谈及的代码制为例,计算机语言的二进制通过0和1来完成编码,而又从0和1编码序列与组合中延伸出无限的可能,以此为基础,经过不同层次的转换生成,可以增值扩散出异常丰富多样的差异性,这与一般意义的人类学中论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人类并没有受到数字技术兴起的绝对影响,无论数码世界的研究怎样丰富多样,其底色依然通向现实世界与人的本质,以及与人相关的基本命题。在信息时代,人们可能生活在依照不同行为框架所构成的领域,并通过不同的方式相连,但即便在数码世界,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行为依旧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层面,就此而言,数码人类学的关注焦点从另一层面强化了人类学传统议题。
第三,网络世界内外结合的整体论原则。整体论乃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具体到网络研究,我们不能只集中观察线上的沉浸式表达,还要回归到生活世界,而今,没有人会完全的生活在网络世界,也很少有人完全不受网络世界的影响。因此,需要把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以及网络世界内外的情况结合起来,将之视作信息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来进行整体研究。
第四,数码接触、连接的全球性与文化相对主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依凭通信协议完成的全球互联互通,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不同地方的人在接触和使用网络时所呈现出的丰富多样的地方性。2019年,笔者在西双版纳布朗山作田野调查时,就发现村民虽生活在山地,但他们非常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刷抖音,玩快手。可稍作留意就可发觉,布朗山民并没有一味地通过智能手机这样一个数字技术之物来体现他们对城市生活乃至外面世界的向往,在他们的手机中,更多呈现的反而是他们的山野生活、宗教仪式与岁时庆典,以及以布朗话为交流方式的微信群,一个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网络世界。
第五,数码文化的模糊性。数码世界中开放性和封闭性同时存在,这与更为广泛的权力、资本和社会运作相关,假如人们接收的信息并不完整,那么,谁在筛选,如何过滤,真相是否存在,又是什么。此外,数码世界同样要面资本运作的影响,嵌入式广告无处不在,看似便捷有效的搜索引擎也可能被某种算法逻辑控制,如此一来,人们可能一直处于被误导的“真实”之中。在后真相时代,而谁在控制网络社区乃至网路舆情,网民的文化主权又如何维护,值得深思。
第六,数码世界的物质性和规范性。在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中,事物之间的秩序、关联和能动性,物的价值、意义及其再生产一直为人类学者关注。从过去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乃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反思,(35)[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等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都将之视为探讨的核心。回到网络世界或数码人类学,可以看到,支撑数码技术的基础设施、数码内容、数码传播的环境,相互之间呈现出互为主体的状态。几者之间都可能成为非人的行动者,并在网络行动、连接、转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最后,数码人类学的实践则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灵活性与可拓展性相关,并关乎人类学在信息时代的公共性与社会影响力。简言之,就是人类学如何参与数码世界中的开放访问与资源共享。其实,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很早以前就有过开源软件运动,目的是为了公开信息、知识共享,反对网络社会中的技术霸权,如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的垄断,因其受控于资本运营,过度服务于商业利益,这也包括最近对于知网的争议,事实上,知识的开源是否,也直接涉及网络主权与民主,之前开源主要关注网络世界中的知识与技术能否平民化,能否让更多的人用低价甚至免费获取资源。在新技术和新的文化协议之下,数据容量在不断扩容,数据共享也被屡屡提及,最近美国人类学协会也在讨论是否将与协会相关联的期刊开放共享。这就涉及之前讨论的可及性问题,但往往又与政治、经济以及网络文化环境相关。
事实上,就人类学领域而言,借助开源运动的力量,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各高校及科研机构,重新激活民族志与历史档案,比如目前已在运作的数字喜马拉雅、数字敦煌以及数字大藏经项目,使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获取更为丰富的动态资源,更为便捷地拓展相关研究。若能更进一步,则是推动对开放与合作的民族志计划,将民族志资料/数据作为集体资源而非个体化的存在呈现出来,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途径接触到基本素材,进而展开更加多元的分析。
结 语
无疑,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时空压缩、流动加速、数码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工程以及由此衍生的后人类状况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数码现象无论作为社会运作机制,还是连接世界的想象,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远弗届,不问西东。网络作为非人类的行动者,已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信息与科技的介入,而是在相互交织、纠缠中创造出新的生境,无形中型塑着人类的自我认同、社会交往、亲密关系、生产消费、生活方式、具身体验乃至存在状态。
我们会怎么样?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虚拟世界中日趋频繁、日常的行为实践。信息时代新的沟通与表征系统正在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向度,对时间与空间的再度界定,使人类经验跨越线性序列与地理边界,多媒体抑或网络社会的文化,以多样的形态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表达,真实的虚拟文化的产生,则映射出镜像世界中的混融状态,既然现实总是通过符号、象征甚至代码表征出来,那么媒介即是现实。
再度回到虚拟民族志与数码人类学,我们或许可以延续格尔兹式的经典追问,我们是在研究网络,还是在网络中做研究?此即关乎人类学在认知论与方法论层面的转向。在多维时间叠加,地方与空间微妙转化的背景下,通过思考以信息为核心的技术变革如何重塑人与人,人与物的关联与互动,理解身处其中的具体的人。
总体而言,数码人类学的基本原则与逻辑在于力图建立穿梭虚拟与现实的连接,明晰万物互联的背后,依旧存在知识、权力、资源的复杂关系,连接与断裂并存,同时通过剖析数码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进而揭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双向形塑,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时俱进地回应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即信息时代的社会构成以及后人类状况之下的文化图景,并在人与非人世界的物我关联和交融中,重新思考人的存在状况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