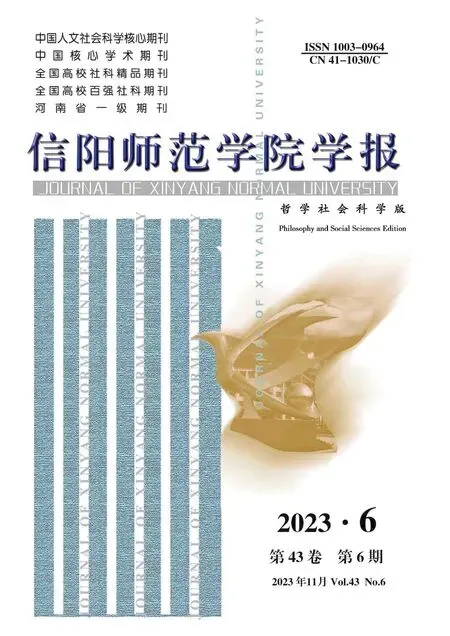论《金瓶梅》的历史书写
梅东伟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金瓶梅》流传之初,其中的历史书写便受到关注。沈德符认为它借此“指斥时事”,以蔡京映射严嵩,以林灵素映射陶仲文,以朱勔映射陆炳[1]2584,点出《金瓶梅》“以宋写明”的叙事意图。现代以来,吴晗、郑振铎等探讨了《金瓶梅》所表现的明代历史,并由此推断小说的作者与创作年代①。近年来,此论域大体形成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对《金瓶梅》提及的宋代人物、事件进行索隐,产出大量成果②,而索隐研究的过度解释,也引发了学界批评③;二是与索隐式研究不同,另有研究者注意到《金瓶梅》历史书写的艺术手法、叙事价值和所包含的政治隐喻④。已有研究有利于理解《金瓶梅》历史书写的丰富内涵和文学意义。不过,《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日常生活”是小说家的叙述重心,历史如何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其间的历史又有怎样的文化特质,尤其,当历史融入日常生活叙事时,日常生活实际上也成为小说家思索历史的一种视角,如何体现小说家的历史观与文化思考。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尚缺乏深入的探讨。
一、碎片化:《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生活化
较之历史演义,《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篇幅微不足道,但对历史的表现自有特点,它以编年时间的月、日化,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谈资化、条目化,散漫分布于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成为小说家所构建的世俗生活故事世界的一部分。
《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碎片化”首先表现为编年时间碎片化并散漫于日常生活。《金瓶梅》以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却并未舍弃编年时间,它在历史时间放在由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到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的脉络中,排列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编年是史书叙事的基本方式,张竹坡说:“《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2]76魏子云根据故事情节撰著了《〈金瓶梅〉编年纪事》一书,可见编年的文本构成意义。不过,《金瓶梅》的编年突出月、日尤其是“日”,而非“年”。尽管小说家在叙事进程中也会以政和、宣和、重和、靖康等年号,提醒读者小说故事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但小说家更注重以“月”尤其是以“日”为单位展开故事,故此“宣和×年”“重和×年”之类时间标识在小说中并不多见,而“一日”或“×日”之类以“日”为单位的模糊性时间标识大量出现,这正是历史时间的碎片化。如第98回叙及张叔夜征剿并招安梁山泊宋江等贼寇,及蔡京、朱勔和高俅等人的倒台,是为北宋宣和、靖康年间事,却并未以“宣和×年”或“靖康×年”标识时间,而只是不断以“日”为单位提醒读者时间的变化和故事的进展,诸如“话说一日”“晚夕”“一日”“迟不上两日”和“过了一日,到第三日”之类词语。由此,宣和等年号所代表的历史时间实际上也被一个接一个的“一日”所分解并碎片化,进而被那些充斥其间的日常生活内容——家长里短、饮宴交欢、嫖娼偷情之类所淹没、吞噬。在此重“日”轻“年”的叙事倾向下,“年号”的历史标识价值已削弱,尤其“年号”与小说世界的主要人物及其活动也没有历史性联系,因为这些人物(如西门庆和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是小说虚构的结果。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中的历史时间已经“道具化”,“在历史的那些时段本不存在小说所叙述的某家某家,因此,真实的历史朝代纪年实际上在小说中发生了转义。就好比舞台上的器物,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器物,但却变成了道具”[3]。这种说法很形象,有其道理。然而,编年时间在日常生活层面叙事功能的淡化,却不意味着它在思想意义层面也沦为道具,更不意味着它叙事价值的淡化;相反,它是表达文本内涵的重要修辞手段,正是借助于历史编年时间,《金瓶梅》才获取了浓厚的历史感。《金瓶梅词话》将故事的起点定格于“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崇信着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4]4,终于靖康之变和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政权的建立,其间表现了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透露出历史的变迁和家国的兴亡之感。这正是《金瓶梅》“编年时间”的巨大价值所在。
《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碎片化”还表现在历史事件的谈资化,成为小说人物日常信息交流的一部分。在《金瓶梅》中,历史人物或事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常常发生于官员的社会交往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第六十四回中,薛、刘两太监祭奠李瓶儿,叙礼之后,西门庆、应伯爵等陪坐听戏、吃酒,期间薛、刘谈及当时朝廷事务:
刘哥,你不知道……昨日大金遣使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掣童掌事的兵马,交都御史谭稹、黄安十大使节制;三边兵马又不肯,还交多官计议。……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4]1028
这节谈话包含丰富的历史讯息,如谈话所涉及的童贯封王事宜,《宋史·童贯传》载:“宣和七年,诏用神宗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广阳郡王。”[5]13661不过,从读者角度,薛太监给出的“信息”又是不完整的,且与不相关联的史实相联系、杂糅,如所谓的“割内地三镇”事发生于靖康元年,此时无论蔡京、童贯,均已被朝廷免职、罢黜,这里却被刻意的编织起来。有时,亲友间的日常交往,也会谈及历史,如第78回中,吴大舅向西门庆和吴月娘谈“屯田法”:“太祖旧例,练兵卫因田养兵,省转输之劳,才立下这屯田。那时只是上纳屯田秋粮,又不问民地。后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这夏税[4]1344。”作为“谈资”的历史是一种社会信息,也是人际交往的话题。但由于当事人对历史情境的熟悉,谈资化的历史往往是片段化的,在日常生活流中转瞬即逝。同时,谈话者的情感倾向,也使这类历史书写带有明显的立场,如上述薛太监对童贯的偏袒。
《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碎片化还表现在“条目化”的罗列人物姓名。《金瓶梅》没有大篇幅的历史书写内容,也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但所透露的历史讯息却十分丰富。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提到的北宋历史人物多于《水浒传》,其中《宋史》有传者35人,出现于其他宋代史籍或附载于《宋史》他人传记中的人物有17人,还有其他可能因误刊而确认的宋代人物4人,合计56人;《明史》有传者4人,见于明代其他史籍者9人[6]。这些历史人物的职官、姓名都承载一定的历史信息。小说家对姓名的列举不厌其烦,如第65回中的叙述:
良久,人马过尽,太尉下轿,进来。后面抚按率领大小官员,一拥而入,到于厅上。……为首就是山东巡都御史抚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参见,太尉还依礼答之。其次就是山东左布政龚共、左参政何其高、右布政陈四箴、右参政季侃、左参议冯廷鹄、右参议汪伯彦、廉访使赵讷、采访使韩文光、提学副使陈正汇、兵备副使雷启元等两司官参见,太尉稍加优礼。及至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师文、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莱州府叶迁等八府官行厅参之礼,太尉答以长揖而已……[4]1045-1046
这些人物大多史籍有载。小说家对他们官职、姓名的罗列,除了凸显出地方官员对朝廷高官的逢迎,表现小说家对官场风气的批判意图之外,也简洁而集中地传递了历史信息,否则,小说家完全可以对这些姓名进行虚构,或者一笔带过。不过借助姓名罗列的方式传递信息,实际上也使人物自身物化,蜕变为历史信息的载体。
此外,“奏章”和“邸报”也是《金瓶梅》展开历史书写的重要载体,但需注意的是,《金瓶梅》中提及的奏章、邸报内容,是小说人物从官府中抄写而来,它们出现于日常生活,而非公务场合,只是人们日常生活流中的片段而已,而奏议或邸报信息的影响也主要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这些抄来的信息也常常是“条目式”的,它也是小说历史书写“碎片化”的表现。如第48回中,来保从东京给西门庆抄回了朝廷准允蔡京奏议的邸报,主要内容为“条陈七件事”,小说将它们从1到7分条罗列,其中让西门庆感兴趣的是“更盐钞法”,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发大财的门道。但奏议内容施行后的社会政治影响却丝毫没有提及,可见小说家历史书写的着眼点。同样,第77回中,西门庆从巡按衙门抄来的有关宋乔年巡按山东官员奏本旨意的邸报内容,同样以“条目化”的形式评骘所涉官员的劳绩、品行,但小说也仍未交代宋乔年奏本的社会政治影响,而是正面描写了荆都监和吴大舅升职后来拜访、感谢西门庆的情景,从而将奏本的影响落脚于官员的私利和日常生活。
不过,《金瓶梅》历史书写的“碎片化”虽使历史信息淹没于日常生活,却无法淹没小说历史书写的意义。实际上,小说家正是借助烦琐生活内容的描写,构建了观察和描述历史人物、事件的日常生活视角,并借助虚构的日常生活场域,淡化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挣脱实录观念的束缚,从而糅杂宋、明,使《金瓶梅》的历史书写带有了丰富的寓言特质和现实批判色彩。
二、日常生活视角与寓言化:《金瓶梅》历史书写的叙事特质
西门庆及其妻妾的日常生活是《金瓶梅》的叙述重心,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小说家又明确设定了故事发生的历史时间:北宋政和二年(1122年)至建炎元年(1127年),并不时在此虚构世界中穿插历史人物、事件,从而使真实存在的人走入虚构世界,虚、实之间已无法以虚实参半或者三七之分的比例衡量。在此虚实糅合的故事世界中,虚构的市井之徒与历史人物频频往来,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家书写历史的主要视角;而在表现宋代历史的过程中,小说家又常常植入明代历史人物的姓名或典章制度,突出小说的现实指向,从而强化了《金瓶梅》历史书写的寓言意味。
日常生活的领域是“私”的领域,充斥着人们吃、喝、拉、撒、睡之类私生活内容,《金瓶梅》的着眼点便在于此,包含对历史人物日常生活的描述。如第55回中,为蔡京祝寿的西门庆,在翟管家的带领下来到蔡府,切身感受了当朝宰辅的饮食生活:
(西门庆)隐隐听见鼓乐之声,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门庆又问道:“这里民居隔绝,哪里来的鼓乐喧嚷?”翟管家道:“这是老爷教的女乐。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晓得天魔舞、霓裳舞、观音舞,凡老爷早膳、中饭、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门庆听言未了,又鼻子里觉得异香馥馥,乐声一发近了。……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师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红蟒衣的,是太师了。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宫样妆束,执巾执扇,捧拥着他。[4]846
且不论相关史籍中蔡京的事迹、形象,这里对他日常饮食生活奢华的描摹,也能让读者想象他在其他方面的穷奢极欲。尽管其中包含着诸多的想象、虚构,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但并非不合情理。
然而,这类直接着眼于历史人物日常生活的情节,在明代通俗小说中并非鲜见,《金瓶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通过市井日常生活叙事引入历史人物、事件,也即小说家首先通过市井人物日常生活烦恼问题解决方式的描述,将日常生活叙事的触角延伸至传统演义小说的领地,从而在整体上构建起从日常生活观察历史人物及其政治生活的视角。第10回中,武松因杀李外传被清河县判为死刑,东平府知府陈文昭认为清河县判案不公,要捉拿西门庆、潘金莲等人重审;西门庆却通过亲家陈洪联络到蔡京,蔡京写信给陈文昭,事情很快解决。这是《金瓶梅》中历史人物蔡京第一次现身活动。然而,蔡京所解决的不过是一起因“偷情”而引发的民事诉讼。《金瓶梅》中,历史人物、北宋徽宗朝宰相的第一次现身便与市井之徒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开启了小说从日常生活视角书写历史人物的进程。很快,第14回中,花子虚因兄弟争产,被告到京城开封府,李瓶儿请西门庆找门路搭救花子虚,西门庆再次找到了蔡京,蔡京一纸“简帖”,开封府尹杨时便很快了结此事,释放花子虚。这是小说中蔡京又一次介入市井生活,表面上看是兄弟争产事宜,实际上也与市井之徒的偷情相关联。这里的蔡京,较之正史中左右时局、败坏朝纲的蔡京,颇具讽刺意味。
同时,小说家也描述了重大历史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冲击与影响,这类故事在明代通俗小说中亦多见,“三言”中的不少篇目便写到“靖康之变”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金瓶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极少从正面着笔表现历史人物的政治遭遇,而始终从人物日常生活角度映衬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影响。如第17回中,沉醉温柔乡中,筹划迎娶李瓶儿的西门庆突然叫停婚娶事宜,正与宋、辽的战争中严重失利有关,宇文虚中弹劾蔡京、王黼、童贯和杨戬等,致使杨戬倒台、下狱,波及亲党,惊恐之余的西门庆急忙着人赴东京打点,惶惶不可终日,“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下人无事亦不敢往外去,随分人叫着不许开。西门庆只在房里动弹,走出来,又走进去,忧上加忧,闷上添闷,如热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在九霄云外去了”[4]232-233。西门庆的日常生活状态,折射着政局危机的严重性和政治斗争的激烈。然而,很快经过一番疏通,西门庆的生活回归正常。此后,通过频繁的贿赂,尤其丰厚的寿诞礼物,西门庆密切了与蔡京的关系,并开始了自己的“官作生涯”,这一虚构人物也与历史人物有了更为频繁的联络,并更深入地融入到了历史世界中,而小说的寓言特质也凸显出来。
借助于叙事“杂糅”,《金瓶梅》表现出了丰富的寓言性。随着“官作生涯”的开启,西门庆越过了市井生活的局限,开始进入并活跃于官员士大夫圈层,并得到广泛认可,第70回中的兵部邸报称赞他:“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4]240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官员)开始出现于西门庆的宅院和他的社会活动中,小说家借此呈现的历史信息,亦愈加丰富,小说的虚构世界进一步与历史书写联系起来,这一虚、实杂糅的故事世界使《金瓶梅》表现出了丰富的寓言性,“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并不是他表面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7]103张竹坡将《金瓶梅》视为寓言,并从谐音修辞角度解读人名的深层寓意,而未关注人名背后的历史讯息,如他对“宋乔年”“安忱”的解读:“安沈(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寓意也”[8]62。这种解读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意蕴,却忽视了小说家借历史人物表达的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如宋乔年此人,《宋史》卷三百五十六有传,是宋皇祐宰相宋庠之孙,也是蔡京的姻亲;安忱则是徽宗朝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安惇的哥哥,《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载:“忱,惇兄也。”[9]248若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宋乔年作为蔡京的姻亲,与蔡京的“干生子”频繁交往,包庇其收受贿赂、胡乱断案的行为便显得合情合理了;而对安忱,小说家说:“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4]531对照史籍,这里的记述张冠李戴,并不准确,“三月,亲试举人,赐霍端友以下五百余人及第有差。……阶,深之子而陈瓘甥也。时特奏名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阶魁,南官多士,无以示天下,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第”[9]248。历史上的安忱参奏他人,使之不得为“魁多士”,而小说中,却以同样的理由被他人参奏,不能做状元,得到报应,其间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也隐喻着宋、明两朝的激烈党争。
其实,如“安忱”之类历史人物,在《金瓶梅》中还有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对他们所任官职,甚至事迹的叙述往往有误,甚至淆乱宋、明,这种情形在相关历史地名、时间和事件的描述中同样存在。有学者提出:“《词话》中的人名、官名、地名、时间、事件等,往往是宋明杂糅。这是分析《词话》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假虚实,错综混杂,‘水乳交融’,难以分辨。”[10]17如第65回中,参与宴请六黄太尉的20位两司八府官员中,侯蒙、宋乔年、龚共(应为龚夬)、何其高、汪伯彦、赵讷、陈正汇、胡师文、张叔夜和黄甲等为宋代官员,而凌云翼和韩邦奇却是明代官员[11]323-325。其余的8人,陈四箴、季侃、冯廷鹄、韩文光、雷启元、徐崧、王士奇和叶迁,学界尚未发现明确的史籍记载,应为虚构人物。这种宋明杂糅、虚实杂糅的复杂情形,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它使小说叙事包含了丰富的寓意指向。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北宋末的官场风气和政治生态,也可以视之为明代社会的政治寓言,如黄霖先生对“陈四箴”“何其高”的解读,“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庭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12]174-175。而诸如此类的叙事杂糅,无论虚、实杂糅,还是宋明史实的杂糅,在《词话》中大量出现,是通俗小说历史书写的新的形态,也丰富、强化着小说的寓言性。
不可否认,《金瓶梅》的历史书写错讹百出、不伦不类,但它与虚构日常生活故事的杂糅,虽显怪诞却又合情合理,谢肇淛誉之曰:“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13]172从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的历史书写,使《金瓶梅》带有了新的艺术特质和丰富的寓言价值,有学者说:“兰陵笑笑生的大手笔就在于,写跟女人玩乐的鸡毛蒜皮同时,写了西门庆如何通过金银重礼跟当朝宰相成了‘关系户’,进而进入官场并靠官场发大财。作者如此对题材广泛拓展的结果,使一部可能的‘黑幕小说’或‘情色小说’升级为世界名著。”[14]163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然而,离开相应的历史书写,《金瓶梅》恐怕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不过,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小说家何以选择从日常生活视角展开历史书写,并在鸡零狗碎的反复演绎中描述家国、朝代覆灭,这种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体现着小说家怎样的历史观。
三、历史观与兴亡思索:《金瓶梅》历史书写的背后
《水浒传》以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死亡为线索使小说家摆脱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烦琐,走向广阔的江湖世界,从而营构出了以英雄聚义、征伐平乱为主要内容、宗旨的宏大叙事,体现出“乱自上生”的兴亡观念。而《金瓶梅》则复活了西门庆、潘金莲,重新走入欲望横流、烦复琐屑的日常生活,并建立起与宏大历史的关联,小说家同样表现了历史治乱的思考,却折射着不同的历史观。
《金瓶梅》的社会历史认知明显不同于《水浒传》。《金瓶梅》的开篇取自《水浒传》“武十回”的开头部分,不过,面对同样因奸情引发的命案,《金瓶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水浒传》中,武松杀掉王婆、潘金莲,打死西门庆,自动投案,府尹陈文昭“哀怜”武松仗义,不仅将他的罪行改轻,还派心腹到东京“替他干办”[15]518,武松得以“逃出生天”。从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正义的存在与弘扬,尤其官员对道德正义的秉持。而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从知县到知府再到当朝宰辅的通同联手,保下了杀人犯和奸夫淫妇,其中陈文昭仅有的一点正义感,也因“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4]130-131不得不“糊涂”放下,委曲求全。对命案的处理方式表现出小说家对历史社会的不同认知。在施耐庵看来,道德良知是存在的,既在基层官员身上,也在民间百姓身上,尤其作为民间社会象征的“水泊梁山”更是忠义的所在,而国家之所以内忧外患、纷乱不息,是因为朝中奸佞扰乱朝纲、蒙蔽圣聪,因而“乱自上生”。兰陵笑笑生则不同,他显然是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正义已不复存在,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维护邪恶而放逐正义;社会治乱的根源在君主,而朝廷中奸佞、权臣则是乱的帮凶和邪恶的维持者、维护者,《金瓶梅》展现的是一个污秽不堪、不见希望的世界,它所突出的,是人性的放纵和伦理道德的崩塌。
《金瓶梅》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正是基于人性理解的儒家道德史观展开的。从日常生活叙事角度,《金瓶梅》将个体的欲望放纵乃至纵欲而亡的生活故事与北宋王朝的覆亡相结合。在小说史上,“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价值,其中包含着小说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儒家道德史观的体认。《礼记》是集中讨论典章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典,其中明确记述了儒家基于人性理解的道德史观: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16]471-472
儒家学者认为,“大乱”源于人们沉溺“物欲”,泯灭天性中的善良本质,从而产生叛逆诈伪之心,恃强凌弱,以众凌寡,以至老幼孤独不得其所,这最终会导致社会大乱。《金瓶梅》所营造的正是充满诱惑的物欲世界。它是美色诱惑的空间。故事的发生地清河县城,是个繁华的小城镇,妓院和美貌的妓女众多,它们构建起了清河市井社会的情色空间,以至西门庆流连忘返,自幼便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4]39。这个物欲世界还是“品物”繁盛和时尚诱人的世界,如饮食之美,小说家不厌其烦地罗列各类筵席上的美食,还会介绍各种美食的做法与口感,如第61回中对腌螃蟹的描述:“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剃剥净了的,里边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煠、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吃。”[4]960如服饰之时尚,产自苏杭、扬州的绸绢衣服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如西门庆为众妻妾裁制的衣服“贴里一色都是杭州娟儿”。然而,美色萦绕与“品物”丰盛并未给西门庆带来身心的满足感,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欲望追求,他勾搭有夫之妇王六儿,与独身的贵妇林太太偷情,同时还觊觎“干儿子”王三官的妻子,以及同僚何官人的妻子蓝太太,还梦想着苗青送他的美女楚云……“物至而人化物”,对“物欲”的沉溺所造成的不仅是伦理主体自省能力的丧失,还有道德沦丧和人性的迷失[17]。西门大院内的家反宅乱、伦常失序,西门庆在官场中行贿受贿、糊涂断案,都昭示沉溺“物欲”所带来的社会乱象。
与西门庆这位家中“皇帝”相映照,宋王朝的皇帝同样沉迷于物即“花石”之好中。《宋史纪事本末·花石纲之役》记述了宋徽宗的这种“物欲”带给民众的灾难:“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而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荑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18]506徽宗好物、玩物的危害可见一斑。《水浒传》曾叙及杨志押运花石纲在黄河“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15]233,丢失官职,并以此为起点逐步走上流落江湖、对抗官府的道路。从英雄失路、官逼民反角度表现了“花石纲”的社会危害。《金瓶梅》则写出了官员们对“花石纲”的切身感受,第65回中黄主事代宋乔年拜访西门庆,希望他做东宴请迎取“花石”的钦差六黄太尉,他说:
先生还不知,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宋道长督率州县,事事皆亲身经历,案牍如山,昼夜劳苦,通不得闲。[4]1034-1035
现场的县官则私下对西门庆抱怨迎送钦差之苦:“钦差若来,凡一应祇迎、廪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4]1036这类日常生活场域或私人场合下官员们的牢骚、抱怨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徽宗“花石”之好所造成的乱象。在《金瓶梅》中,如果说西门庆对情色欲望的沉溺导致丧身败家,那么宋徽宗的“花石”之好则导致北宋的败亡。
《金瓶梅》注重日常生活故事的叙写,并借日常生活场域书写历史,探询家国兴亡之理的创作思路,透露出小说家历史价值观的变化。不少学者都注意到,《金瓶梅》包含着修、齐、治、平的内在逻辑,只不过是从反面展开的[19]。由“修身”到“平天下”的儒家政治伦理,构建起了个人与国家天下密切关联的逻辑进路,它建基于“格物”,所谓“格物”,即“格去物欲之蔽”[16]801。“物欲”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由此,《金瓶梅》从日常生活叙事出发,将历史书写置于日常生活场域以探讨家国兴亡的思路便也自然而然了。不过,这种思路的形成也与明中后期社会风尚相联系,当时纵欲之风的盛行毋庸赘言,还值得注意的是此际文人士大夫“恋物”“玩物”的社会风尚,“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20]19,甚至在明清之际的文化反思中,“玩物丧志”构成了士大夫言论中的重要话题[21]。“物”存在于日常生活,沉迷“物欲”就意味着伦理主体日常道德践履的失败。阳明学派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践履,王阳明说:“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22]108然而现实情景却是日常生活中的物欲横流,基于此,有学者视《金瓶梅》为“阳明学得以产生的‘现象学’注脚”[23]91。不过,对阳明学者而言,注重“日用之间,见闻酬酢”中一言一行,旨在提醒和告诫儒家学者要时时注重道德修养,而《金瓶梅》注重日常生活故事的表现,并借此书写历史,探讨家国兴亡之“理”,则体现着小说家文学视野的转变,它的背后是历史价值观的变化。
总之,与历史演义借助军国大事展现历史风貌的书写方式不同,《金瓶梅》将历史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开辟了历史书写的一种新的方式,虽然其中历史书写的篇幅微不足道,却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其间的宋、明(历史)杂糅,虚、实杂糅,又使《金瓶梅》的历史书写带有了浓厚的寓言特质。《金瓶梅》的历史书写,不同于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它从日常生活视角展开北宋覆亡的社会历史情景,从中探询家国兴亡之理的创作思路,是基于儒家人性理解的道德史观,也透露出小说家历史价值观的变化。从小说史的角度,《金瓶梅》将历史融入日常生活的历史书写方式,不仅丰富了历史表现的方式,也为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开辟了一种新的方式,也即注重现实性、寓言性而淡化实录色彩,这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小说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它们突出小说寓言性质的同时,进一步淡化小说历史书写的时代标识,而通过人物故事和相关文化背景的描述,增强小说的历史感。
注释:
① 参见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和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相关论著,如马征《〈金瓶梅〉历史人物本事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美)胡令毅 《“六黄太尉”是“黄太尉”吗? ——兼答“集体”“陋儒”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1期;霍现俊《〈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如杨彬《“六黄太尉”是六个太尉吗?——兼论〈金瓶梅〉作者非徐渭或“大名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美)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④ 如黄霖《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霍现俊《〈金瓶梅词话〉的主旨及其表达的特殊方式》《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王进驹、杜治伟《〈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及其小说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