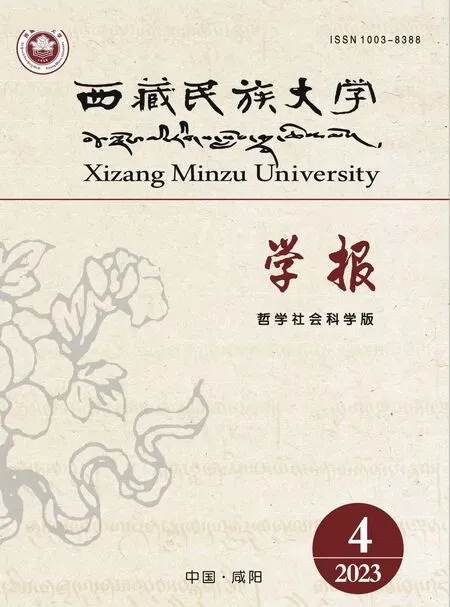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唐蕃和亲影响
杨 娅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唐朝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原王朝,如何巩固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封建经济,与其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秉承“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1](P6215-6216)的宽待优容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唐朝的安边政策中,面对“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2](P5345)的选择时,多数情况下,和亲羁縻手段成为唐朝处理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四海一家、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下,各民族互通有无,往来频繁,共创共融,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时期。
一、唐蕃和亲背景
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下,国力逐渐由复苏走向强盛。居于青藏高原的雅隆悉补野部落首领松赞干布于公元629 年继位,逐渐统一邻近诸邦,改变了高原长期部族分散、不相统属的局面,建立起吐蕃王朝,开启了延续千年的藏汉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作为新兴政权,为巩固其统治,松赞干布希望与强盛的唐朝建立联系,贞观八年(634),吐蕃踏上遣使前往唐朝朝贡之路。来而不往非礼也,吐蕃遣使来唐后,冯德遐被唐太宗派遣前往吐蕃回访抚慰。吐蕃“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2](P5221)松赞干布听取了使者返回后的汇报,认为其求婚不成的主要原因是吐谷浑从中离间,为与唐朝成功联姻,吐蕃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2](P5221)。与此同时,“逐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2](P5221)吐谷浑兵败后,吐蕃大掠其人畜物产,随后又破党项及白兰诸羌部落,率20 余万部众兵临唐朝松州城下,言之:“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2](P5221)为求娶成功,吐蕃引发了唐蕃间第一次以战争形式的军事交流。最终,松州战役,唐朝以5万步骑军击败吐蕃军队。“弄赞(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2](P5221)历经曲折的请婚终于在于贞观十五年(641)变成现实,“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2](P5221)
唐蕃首次和亲后,双方人员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融洽。唐蕃和亲缔结者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相继去世后,禄东赞的儿子论钦陵兄弟把控朝政,年幼的赞普权力几近架空,“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2](P5225)。此时的吐蕃,政治主张与诉求发生变化,屡次进患唐朝边境,唐蕃关系再度紧张。后来,赞普器弩悉弄(赤都松赞)年岁渐长,与亲信大臣秘图,把握时机亲自挂帅带兵讨伐钦陵,钦陵兵败自杀。器弩悉弄遣使入唐请和,朝贡并请婚。武则天许之,唐蕃关系较之前有了新的改善。
器弩悉弄亲征南诏,卒于军中。“嫡庶争立,将相争权,自相屑灭”[2](P3042),其后,“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缩赞为赞普,时年七岁。”[2](P5226)中宗神龙元年(705),执掌朝政的赞普祖母可敦没禄氏遣大臣悉薰热前往唐朝进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2](P5226)吐蕃与唐朝再次恢复了频繁的岁贡往来。景龙三年(709),吐蕃“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2](P5226),唐蕃双方代表在长安苑内球场举行马球比赛。景龙四年(710)正月二十七日,唐中宗“亲送于郊外”[3](P205)以左卫大将军杨矩为使护送,“金城公主既至吐蕃,别筑一城以居之。”[2](P5228)从而完成唐蕃间的第二次联姻,进一步扩大了双方交往交流交融的维度。
二、唐蕃和亲影响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和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联姻,其背后蕴含联合、给予、互助、和平、文化认同等多种因素交织的隐性内涵,以及因“和亲”所衍生出的一系列你来我往的互动,有助于和亲主体唐蕃双方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增强彼此的政治互信、经济发展,促进生活习俗、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融。
(一)增强唐蕃间政治互信
完成部落统一后的吐蕃政权,为巩固其统治,用和亲联姻的形式与强盛的唐朝建立了关系,以“大国子婿”的身份“在政治上可取得李唐的认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4](P224),进而使周边其他部落更尊服之。如松赞干布所言:“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2](P5221-5222)对唐朝统治者而言,和亲有利于边境安宁,是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非武力选择,对巩固王朝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唐蕃和亲,始于双方政治需要,并在和亲后的姻亲关系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增强了政治互信。
文成公主前往吐蕃,松赞干布于河源亲迎之,执子婿之礼恭候和接待作为主婚和护送公主入蕃的江夏王李道宗。得知唐太宗伐辽东凯旋长安,松赞干布遣禄东赞入长安致贺,上疏奉以“臣”自称,表曰:
“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於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纔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壻,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2](P5222)
除了自表“臣”之身份,松赞干布恭敬接受唐朝授予的各种封号。唐高宗继位后,松赞干布被授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后继续得到唐高宗嘉奖,进封其为“賨王”。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松赞干布遣员“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2](P5222)。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逝世,“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侯将军鲜于臣济持节赍玺书吊祭。”[2](P5222)和亲后频繁互动的唐蕃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关系。
军事互助是政治互信的直接表现形式。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一行出使西域,路途中“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2](P5222)此为唐蕃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吐蕃对唐朝提供战争援助的最早史料例证。贞观二十三年(649),唐高宗继位之初,松赞干布致书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2](P5222)。可见吐蕃珍视唐蕃间已有的政治互信关系。建中四年(783),唐德宗在位期间“泾原兵变”(奉天之难),朱泚带兵攻陷长安,“朱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浑瑊用论莽罗兵破泚将韩旻于武亭川。”[5](P6094)吐蕃此次请助讨伐叛军,尽管不排除其从唐政权谋取利益的初衷,但在唐政权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出兵相助,不失为唐蕃政治互信、履行盟友职责的行动。
后来,应金城公主请求,开元二十一年(733),唐蕃在赤岭立碑分界,相约“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5](P6085)。又于建中四年(783)的“清水会盟”明确表态:“唐有天下……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礼,甥舅之国,将二百年……蕃国展礼,同兹叶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2](P5247)将双方政权主体融入到“甥舅”的亲属伦理范畴中,会盟前后约七八年间几无大战,该会盟拟定的边界,基本保持到了吐蕃王朝崩溃。
基于机会约束混合整数规划的风火协调滚动调度//马燕峰,陈磊,李鑫,赵书强,刘金山,甘嘉田//(5):127
(二)助推唐蕃社会经济发展
唐蕃和亲,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蕃,每次“嫁女”,唐朝统治者都赏赐了大量财物,派出大量随行人员。唐蕃首次和亲,唐太宗既以“八狮子鸟织锦垫,并绣枝叶宝篆文,赐女能使王惊奇……工巧技艺制造术,高超能令人称羡,如此工艺六十法,以此赏赐我娇女。一世温暖锦绫罗,具满各色作服饰,凡二万匹赐与汝。身材妙曼可意儿,善承人意诸女伴,二十五名作侍女。”[6](P68)西藏本土历史典籍载之:“上赐公主嫁奁极丰,不可计量……复赐负运此珍宝、绫罗、衣服、饰品与及当时所需资具之马骡骆驼等甚众。”[6](P69)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中原珍宝使吐蕃上层人士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金城公主入蕃和亲时,弃隶缩赞尚年幼,唐中宗“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悉从。”[5](P6081)这些因和亲从中原汉地至吐蕃的“公主的嫁奁有万匹绫,及诸种工艺,凡至王前所需之具,皆有携备。”[7]这些汉地的能工巧匠随和亲公主在吐蕃扎根,将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吐蕃,助推吐蕃生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汉书·艺文志》有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於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歌谣系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之,贴近群众生活,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民思想感情及意志愿望。[8](P59)藏族世代颂扬文成公主为民族情谊的象征,其被称作“阿姐甲莎”(汉族阿姐),并非偶然。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近四十年,视边陲他乡为故乡,始终致力于改善吐蕃较原始的生产方式,对吐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评介:“她为进一步发展唐蕃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且树立了有利于吐蕃社会生活、文化的深厚风尚。在藏族民间流传着文成公主发展农业生产、建立水磨、纺织氆氇的动人故事。”[9](P100)世居高原的吐蕃后代通过故事或歌谣传唱的形式,表达了西藏群众对文成公主和亲入蕃后,在吐蕃生活几十年给吐蕃人民社会经济带来诸多变化的感激之情。“大地肥来土地美,肥田沃土要数白归雄;种下公主带来各种粮,共有三千八百种。”[10](P85)以及“王后文成公主,带来畜种五千;给西藏乳酪的丰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10](P84)文成公主带领来自中原的随行人员向吐蕃民众传授汉地先进耕作法,使吐蕃的农牧业产量不断提升。唐高宗嗣位,吐蕃又向唐朝“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2](P5222),高宗并许焉。这些汉地能工巧匠在青藏高原积极传授推广中原的科学技术及手工技艺,提高吐蕃家庭手工艺和手工业技术水平,助推了吐蕃经济社会发展。在吐蕃流传着被传唱了千年的《公主带来手工艺五千》的歌谣:“王后文成公主,带来手工艺五千;给西藏地区的工艺,打开了繁荣的大门。”[10](P84)“龙纹瓷杯啊,是公主带来西藏;看见杯子呵,就想起了公主的模样。”[10](P84)这些脍炙人口又饱含真挚情感的民间歌谣,形象地刻画了文成公主在藏地造福人民,给吐蕃人民带去幸福生活火种的场景。在文成公主的随行人员或其从唐朝请拨的汉人工匠技师帮助下,吐蕃逐渐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手工技艺,集市逐渐出现了琳琅满目、品质上乘的商品,社会经济日益发展。
时至今日,西藏山南市杰德秀镇仍流传着文成公主为藏族妇女传授氆氇制作技术的故事,以及山南的农民一直视二牛抬杠的犁由文成公主从汉地传至西藏,甚至日喀则的铜匠都奉文成公主为“祖师”[11]等现象也直接反映了因唐蕃和亲,汉地农耕先进生产技术及传统手工技艺传入吐蕃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三)促进唐蕃生活习俗变化
伴随两位和亲公主一起入蕃的数量庞大的侍者、工匠艺人群体在与吐蕃民众长期的交往交融中,对唐蕃双方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具有双边效应的影响。
吐蕃原俗是“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麨为椀,实以羹酪,并而食之。”[2](P5220)因和亲公主入蕃,唐太宗为文成公主赏赐了诸种金玉器具,造食器皿、食谱、玉辔藏鞍,诸种花缎、绫罗绸缎等不计其数的丰厚妆奁。“诸种府库财帛藏,众多宝物虽难舍,仍以赐赏我娇女。诸种食物烹调法,与及饮料配制方,玉片鞍翼黄金鞍,以此赏赐我娇女。”[6](P116)将上等绫罗绸缎、中原服饰、汉地生活用具乃至烹饪方法等汉地日常生活习俗传入吐蕃。文成公主初抵逻些,对吐蕃这种“男女皆辫髪毡裘,以赭涂面”[12](P9229)的妆容很不适应。因“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2](P5222),松赞干布下令禁止,改变了吐蕃民众的妆容打扮。领略到绫罗绸缎的柔软舒适后,原来以毡裘而衣的吐蕃人,从其赞普松赞干布起,带头“自亦释毡裘,袭纨绮”[2](P5222),身边近臣、贵族等跟随效仿,逐渐推广,吐蕃开始“渐慕华风。”[2](P5222)
唐蕃和亲后,人、财、物等频繁密切往来,对唐蕃双边生活习俗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致使吐蕃赞普能如数家珍的指认出各种汉地茶的特点:“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㴩湖者。’”[13](P175)至五代,“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14](P918)直到现代,藏族的很多生活方式仍能窥探到唐代汉人的习俗轮廓。唐蕃群众交往交流逐渐深入,相互学习借鉴进而彼此融入,出现了“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15](P3812)的盛况。
在丧葬习俗方面,“吐蕃过去对死去的大臣们,没有祭奠的习惯。”[16](P4)“人死,杀牛马以徇,取牛马头周垒於墓上。其墓正方,垒石为之,状若平头屋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於脚下刺血出尽及死,便以殉葬。又有亲信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17](P1729)以及“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2](P5220)等方式。面对吐蕃此等以人殉葬的丧葬习俗,“金城公主说道:‘我们汉地佛法弘扬,对死者有七日祭的习惯。吐蕃佛法不昌盛,人死后得不到祭奠,实在可悲可怜!’以后,便倡兴七日祭。从此,人死后,立即向成千的人天施焰食,摆设供养,以为祭奠和悼念。这就是所传的‘吐蕃七日祭’(或‘祭七’)的由来。”[16](P4)由此可推测,西藏一直延续至今的“七日祭”丧葬习俗,应是吐蕃时期由金城公主和亲入蕃从汉地传至藏地。吐蕃对中原丧葬礼仪文化的认同也体现在其吊唁皇帝时的周全礼仪,“中宗崩,既除丧,吐蕃来吊,深衣练冠待于庙。或曰:‘今定陵自有寝庙,若择宗室最长者,素服受礼于彼,其可乎?’举朝称善而从之。”[18](P43)
当然,这种因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所产生的生活习俗变化具有双边效应,在更开放包容的环境下逐渐形成对彼此文化的相互认同。“赭面妆”传入汉地后,成为汉地女性妆容的新趋势之一,甚至出现了吟诵至今的《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15](P2151-2152)“元和妆”乃女子将头发梳成髻堆,在脸部或点或涂红褐色护肤品的一种妆容。吐蕃女子的赭面、髻堆以及佩戴念珠璎珞等装束与中原女子的装扮迥然不同。“元和妆”在汉地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妆容,说明唐朝中原民众在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审美情趣受到吐蕃的影响。
无独有偶,由吐蕃传入长安的马球在中原尤其风靡,在唐朝统治者和军队中备受推崇。乃至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大臣尚赞吐等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时,“中宗宴之於苑内毬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舆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观之”[2](P5226)的盛况。这场球赛,唐蕃对抗十分激烈,“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19](P53)由此可见,在唐蕃密切的双边交往交流中,运动习俗也渐次融合。
(四)推动唐蕃互市贸易兴盛发展
“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20](P102)文成公主入蕃和亲,吐蕃执“甥舅之礼”身份与唐朝互派使者,朝贡往来是维持唐蕃双方关系的关键环节。唐朝每有重大仪式,吐蕃皆前来觐见朝贡。每次出使可获得唐朝统治者给予的丰厚赏赐与馈赠。唐朝统治者对吐蕃的大量赏赐,史书多有记载,如开元七年(719)六月,“吐蕃遣使请和……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采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廷,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一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21](P2511)又,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命工部尚书李暠使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疋,私觌二千疋,皆杂以五采,遣之。”[21](P2512)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命内使窦元礼使於吐蕃”[21](P2512),此类双边使者往来,促使大宗物资流动之事例,不胜枚举,史不绝书。统计相关史料典籍记载,唐蕃和亲后双方使节往来的频繁程度:自贞观八年(634)到会昌二年(842)的209 年中,平均一年零四个月双方有使节往来一次。这其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天宝十三年(754)、贞元三年(787)、长庆二年(822),一年之内唐使入蕃2 次,而建中四年(783)则达3 次之多。贞观二十三年(649)、万岁通天元年(696)、开元八年(720)、大历九年(774)、贞元二十年(804)、宝应元年(762)、长庆四年(824),皆一年之内吐蕃遣使入唐3 次,长庆元年(821)则达4次之多。因唐朝赏赐和馈赠数量庞大,乃至出现使团前后不绝的情景。吐蕃境内建立了“百里一驿”[5](P6072)完备的驿站制度,驿站更设有“置顿官”,便利了唐蕃使者往来交通。唐朝使臣前往清水,“吐蕃舍人郭至崇来迎”[20](P2802),蕃帅对唐使更是“接待殷勤,供亿丰厚”[20](P2802)。直接反映了唐蕃和亲后的双边互动给吐蕃带来的巨大经济动力。
金城公主入蕃后,鉴于唐蕃边境互市贸易和人员交流不断扩大,开元十八年(730),“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5](P6085),宰相裴光庭谏言甘松岭位置重要,且中原人马前去不便,建议定为赤岭。唐终“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5](P6085)赤岭互市的合法化,不失为唐蕃经济交往、物资交流的一大盛事。中原汉地以吐蕃所需的丝绸、茶叶、日用工具等交换吐蕃的马、牛、羊等牲畜及金、银等珍贵物品,随着双边关系的缓和,物资交流数额愈加庞大,吐蕃民众能较便利的购买到内地货物,互市贸易和人员往来的繁荣景象如独孤及《勅与吐蕃赞普书》所述:“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20](P1727)享受到因互市贸易带来切身惠利的吐蕃百姓世代传唱:“从西藏到内地,自古往来人烟稀;好心的商人结成队,赶着骡马常来去;上等的砖茶和绸缎,源源不断送到藏民手里。”[10](P73)可见,和亲互市,对唐蕃的经贸交往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加强唐蕃思想文化与艺术交融
唐蕃以和亲为媒介,搭建起思想文化与艺术交流的桥梁,双方在互动交流中不断汲取对方的思想文化精髓并渐次融于一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蕃首次和亲,唐朝统治者唐太宗以“经史典籍三百六,以此赏赐我娇女……汉地告则经三百,能示休咎命运镜……四百又四医方药,四方、五诊、四论医典,六医器械皆赐汝”[6](P68)等数量繁多的经史、医典、器械等赏赐给文成公主,随其入蕃。对刚建立统一政权仅十余年、尚无浓厚文化积淀,又缺乏完药医学体系、百事待举的吐蕃政权而言,这一批随文成公主入蕃的经史典籍、医学巨著及先进医疗器械,对吐蕃文明和藏医药体系的建立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批汉地医学典籍到达逻些后,松赞干布立即组织专人将其译成藏文,译后成稿被命名为《医学大成》(藏名《门杰钦木》)。受惠于这些医典医方及医疗器械的吐蕃民众,一代一代地流传着《公主带来的门巴①》:“求神打卦多年,病痛总不离身;公主带来门巴,治好了我的病根。”[10](P86)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和亲入蕃,也给吐蕃带去大量医学巨著。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索玛热咱》)即为金城公主组织的吐蕃和汉地学者在汉地医学典籍的基础上,又汲取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写成。这部《月王药诊》比由宇妥·云丹贡布编著的藏医典籍《居悉》(《四部医典》的简称)早将近一个世纪。五世达赖的第师桑吉嘉措认为《居悉》在吐蕃本土具体情况基础上,参考了内地传来的《月王药诊》的精华。[22]
除了医学典籍,汉地经史典籍也为吐蕃打开了一扇学习先进文化的窗口。吐蕃统治者领略到随文成公主入蕃的汉地经典之磅礴内容和深邃思想后,表现出振奋和欣喜。此后,吐蕃掀起一股学习汉地先进思想文化的热潮,“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2](P5222)出现了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在唐朝“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17](P966)开元十九年(731),吐蕃遣使以金城公主之名向唐“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2](P5232)此举在唐朝廷引起激烈争论,以于休烈为代表的人强烈反对,“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典有恆制,不可以假人……吐蕃,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任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2](P5232)其认为,若吐蕃应请得到唐朝国之经典,从中“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1](P6794),给唐边境安定带来无穷后患。以宰相裴光庭为代表的人,则认为“吐蕃聋昧顽嚣,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1](P6794)最后,唐玄宗听从了裴光庭等人的建议,同意了吐蕃使者的请求,“制令秘书省写与之”[2](P5232),逐如数与之。《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地典籍很快被译成藏文在吐蕃统治者及文化圈内传阅参读。学而优则用。不久后,吐蕃王朝也逐步建立了修史制度。
金城公主和亲时,唐中宗赏赐了“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5](P6081)随金城公主入蕃。从此,龟兹乐在青藏高原渐行开来。长庆二年(822),唐使刘元鼎前往吐蕃都城逻些会盟,赞普设宴款待,“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涼州、胡渭、録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5](P6103)。此时距金城公主入蕃已百年有余,仍能在吐蕃大毡帐中听到百伎熟练演奏《秦王破阵乐》等汉地乐曲,可见汉唐音乐艺术在吐蕃经久不衰的流行程度。在高频的互动交往中,一方面,高原边寒的吐蕃出现了“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15](P951)的现象。另一方面,居于中原的汉地也迎来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15](P2107)的景象。经过百年的交往交流,一度出现了“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5](P1524)描绘的正是唐蕃群众在互学互鉴中逐渐融合的景象。
结 语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23](P7)。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在你来我往中进行物质和文化上的交往、交流进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政治交往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交流、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和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不止于政治的界限。唐蕃和亲促使双方在政治、社会经济、经济贸易和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有频繁且深入的交往与交流,在对彼此文化的吸纳和融汇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产生出一种更新的、更高层次的复合性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唐蕃和亲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影响深远,对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 释]
①门巴:为藏语音译,即医生。
——西北民族大学于洪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