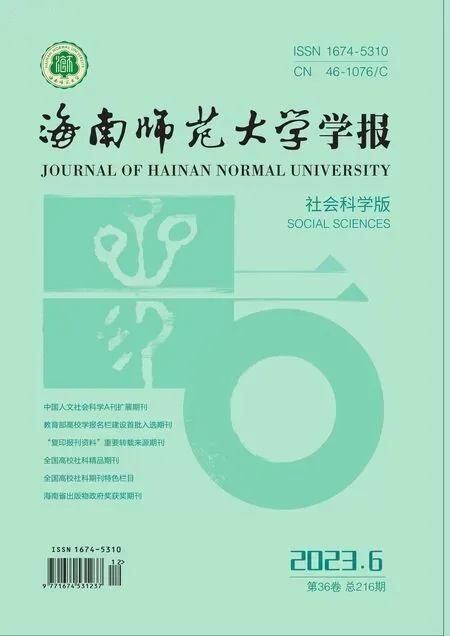作为“正信”的阿Q“精神胜利法”
孙 伟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启蒙和革命是解读鲁迅《阿Q 正传》的两个重要视角,前者侧重观念觉醒,后者强调制度落实,以1990 年代中后期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西为法,或向英美学习人文观念,将阿Q 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进行批判;或向苏俄学习阶级斗争,将阿Q 看作落后农民加以改造;另一派则是从中国本位出发,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野,将阿Q 视为半殖民地社会中被压迫的结果。后一阶段是以中观西,即中国在完成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等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在文化领域发出自己和而不同的声音,《阿Q 正传》开始被频繁视作不同意义上的“寓言”。首先,被视为由本能和直觉引起的反抗,进而导向20 世纪具有独特性的革命寓言①;其次,被看作历史转型期中国文明整体系统失序的寓言②;再次,被看作以农民为主体的开展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寓言③;最后,被视为建立在阿Q 劳动能力基础上塑造的历史主体而展开的继续革命的寓言④。前一阶段以西为法的一派,无论把阿Q 看作农民还是全体国民,都意在通过“个体改造”造就“新人”,进而追赶西方,其思想资源是以个体为旨归的人文主义思想和霍布斯奠基的由自然权利而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而以中国为本位的一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资源。在后一阶段,将阿Q 看作别具意味的“寓言”,意在彰显其所在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特征,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特别价值,思想资源是后殖民理论和文明冲突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仅要完成生存竞争意义上的自立自强,也要实现文化价值层面的自洽自信,对《阿Q 正传》的阐释恰体现了这点。
将阿Q 置于横向的共时段与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比较固然重要,但对纵向的历时段本土文化历史的考察同样不可或缺。阿Q 在“而立之年”被杀于辛亥革命后不久,《阿Q 正传》是一个在清朝最后三十年的人的传记。鲁迅为一个在传统中没有资格入史的人做传,作为旧时代的阿Q,在以“正信”为文化根基的理学传统中有着怎样的前现代面目?他的既有精神状态和思维特征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又会发生怎样的耦合?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首提“正信”①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王士菁解释为“信仰”②王士菁将《摩罗诗力说》中“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赓响矣”一句,解释为“当他们流离异地时,虽然仍怀念祖国,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哀歌》以后,就没有继起的声音了”。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赵瑞蕻亦持此说③参见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页。。“正信”指的是与“信仰”相类的德行品质,西方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宗教,而在中国则是士大夫代表的儒家经义。黄进兴指出,程颐“所谓的‘儒者之学’,便是后世所称的‘理学’或‘义理之学’。而‘义理’即是‘德行’”④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页。,承担着滋养人心、凝聚社会、评判得失的系统功能。传统的史传文学以经衡史,观人物得失,匡正世道人心,朝代虽有更迭,经义一脉相承。以“正信”观照阿Q 的“精神胜利法”,不纠结于具体代表哪个阶层,抑或全体国民,而是对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士”“民”“鬼”三个群体分别考察,以“言行一致、名实相符”的标准对其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进行挖掘,进而分析在过渡阶段中国人对外来思想的接受基础是什么?而这些又共同指向以“新人再造”为目标的新文化建设。
一、“理”的破产:“士”对义理实利的名实错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等旧乡绅和赵秀才、假洋鬼子等新士绅形成了中国在基层社会的统治力量。问题在于,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北伐,都没有将中国各阶层联结为一体,尤其是没有得到农民支持。近现代的“士民分离”如何从传统社会的“士”为四民之首的结构中演化而来,需要对有清一代“士”的处境进行考察。
在《阿Q 正传》中,理学是衡量未庄人能否入史的标准,也是确立未庄的权力秩序的法理,同时还是日常生活的规范。但在阿Q 生活的清末三十年中,理学已经有名无实,代表理学的士阶层也名不符实,⑤参见张全之:《〈阿Q正传〉:“文不对题”与“名实之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反倒是被教化为理学已成为其主观无意识的最底层的农民阿Q 以圣经贤传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赵家因为有秀才而被人尊重,却没有真正地遵奉理学。阿Q 因“恋爱的悲剧”而赔偿给秀才家的香和红烛,并不用来祭祀祖先,而是“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⑥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以下文中所引《阿Q正传》皆出于此版本,引用处标注页码,不再另注。;阿Q 调戏吴妈,给府上带来了不吉利,“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第528 页)。佛、道登堂入室,理学徒有其表,而这些都是装饰,赵家真正奉行的是权势至上。以理学建构起来的未庄的社会文化秩序已经名存实亡,沦为《破恶声论》中被批判的“以强凌弱”和“以众陵寡”的末世。道统坍塌,使得评价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就是权势和暴力,顶端是“太爷”,底端是“虫豸”。阿Q 试图以宗族血缘接近赵家,获得的却是赵太爷的耳光。他虽然和赵太爷一样以暴力欺辱弱小,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严格的理学道统遵行者,并以此要求自己和衡量未庄的一切人和事。这也是阿Q 虽然处处落败,但内心却能处于精神道德高地的原因。阿Q 偷盗不是因为其品行败坏,恰是其努力遵行理学而不可得,进而导致基本生存发生危机,“不能生存而又不得不生存,那么他就不能不接受给定的生存前提及其文化设计,并且不能不以人格的健全为代价,去换来最低的生存条件和安全感”⑦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阿Q 在未庄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正是理学道统在乡村逐渐失落的表征。
阿Q 遵从的理学道统为什么在未庄有名无实?赵太爷代表的士阶层为什么以暴力和金钱取代了理学的地位?这需要对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宋初,由于对唐朝依五经正义取士僵化思想状况的反动,王安石、范仲淹等人重新倡导儒学的经世致用,以恢复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在后续的发展中,朱熹主张以《四书》取代《五经》,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理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经过宋明六百年的演化,理学逐渐僵化式微,特别是明末王学末流泛滥,心学与现实脱离。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提出复古,通过回到三代、孔子和孟子的源头,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文本,从而恢复思想与现实的联系。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没能发展壮大起来。从康熙开始,统治阶层大力推举朱熹理学。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士人言行分离、名实错置。像阎若璩、毛西河等努力致仕的士人,才华高超,考证精密,但做学问的主要目的,已不在经世致用方面。雍正朝的清流领袖李绂将时间、精力倾注考据,不发议论。这也是乾嘉学派兴起的历史原因。之后的戴震、王念孙等人倾尽心力对理学原典进行疏证,试图借道汉学重新恢复经学原义,进而批判宋明理学。①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41-310、331-404页。章太炎在东京教鲁迅等《说文解字》也在这一脉络的延长线上。鲁迅对此感慨:“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②鲁迅:《花边文学·算帐》,《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2页。
《祝福》里的鲁四老爷读的并不是儒家原典,甚至也不是程朱的书,而是理学入门的工具书《四书衬》。书房的对联出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论语》“季氏”的注。上联“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学诗的注;缺失的下联“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则是学礼的注。③参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居然只关注“能言”的诗,而对“能立”的“礼”弃而不顾,这是对有清一代士人德行的讽刺。在现实中,这幅对联恰刻在绍兴周家老台门客厅的柱子上,其中意味不言而喻。④参见无名:《鲁迅的家世》,《文艺阵地》1939年第4卷第1期;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绍兴市文物局编:《稽山红遍:绍兴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图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21年,第16页。士人德行败坏也体现在《阿Q正传》中,“等到阿Q 从城里凯旋回到未庄,向未庄的居民廉价推销他的赃物时,赵太爷未始不知道这批东西的来源不大清白,可是他的势利而贪小便宜的劣根性在作祟,逼使他去做阿Q 的顾客之一”⑤蒋星煜:《论阿Q周围的人物》,《新文艺》创刊号,1946年6月1日。。曹聚仁将阿Q 精神归结于士大夫,“这样一位精神胜利的大人物,的确是出于名门华族”⑥曹聚仁:《阿Q的父亲》,《申报》1935年9月26日。。
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因此,阿Q 的灵魂不仅活在清朝,而且一直持续到民国。《阿Q正传》的写作是鲁迅对当时士人精神状态的一次精准白描。在小说开始,作者即煞有介事地对阿Q 的生平进行考证,“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第514 页),以此嘲讽清朝士人专注考据而忽略思想;“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第515 页)。这是讽刺胡适对青年提倡“整理国故”⑦参见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虽然假以“科学实证”的外衣,但如果不关心时事,就会缺少思考和参与现实的能力。清末适逢西学东渐,从“正信”角度完成中国知识阶层的名实统一,再造既具现代眼光又能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精神界之战士”⑧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是鲁迅一直致力的任务。从《新生》时期对“志士”和“伪士”的批判,到《新青年》时期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再到后期对“帮忙”和“帮闲”文人的批判,一以贯之。
未庄理学的颓败和“士”的名实错置,一方面缘于清朝统治者采取的思想文化措施所导致的异化,另一方面也有着宋明理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阳明心学后期已经呈现出空谈心性义理,远离经世致用的缺陷。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有警示:“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⑨[明]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集》(上),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2页。晚清以来,对新人的呼唤不绝如缕,这里的“新”首先指向的是“士”。中国进入现代是被动和后发的,王富仁用“逆向性”进行概括。①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新”进入中国后,要想落地生根,需要找到内在的历史文化结构并与之化合。当时的中国是从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士民”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里,“民”并不具备直接接受“新”的基础,而是以“士”为楷模建立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种观念要想获得民众的认同,需要先获得士阶层的接受,然后再由士及民。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融入汉朝经学,到宋初应对佛学冲击建立理学,这种“先觉觉后觉”的传播方式一以贯之。西学在士阶层完成转化,一方面需要与既有传统对接,另一方面要能够完成现实历史任务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知识观念的生成,更要造就新的知识阶层。士影响民,并不单靠语言文字,更有赖于道德修养和人格操守。民是否接受士的观念,关键是士能否“言行合一,名实相符”。
以“正信”衡量近现代以来的“新人”,旧民主主义时代的维新者、改良者和革命者与传统“士”的关系密切,还没有形成新的历史主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者提出了新观念,但没有找到与现实结合的基础。1920 年代末,出现了一大批寻找理想革命者的作品,如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茅盾的《蚀》和《虹》、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在时代的革命浪潮中,努力寻找观念与行为相一致、个体与时代相融合的恰切路径。
二、礼的沉潜:“民”对乡土秩序的执着坚守
阿Q 的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着巨大落差,他执着地“以名统实”。当两者间的裂隙过大,阿Q就不得不借助“精神胜利法”强行弥补。他不认同权势凌驾道统,更反对“志士”和“伪士”的“名实分离”。阿Q 在名实、生死、华夷、家族、男女、避讳等方面,“几乎是一个‘完人’了”(第516 页)。尤其在名实方面,小说一开始就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第512 页),在孔子那里,“正名因而确实是为政的出发点和第一要求”②伍晓明:《文本之“间”:从孔子到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页。。为什么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士名实错置、言行不符,而身在未庄最底层的阿Q 严格以圣经贤传规范言行?
《阿Q 正传》在发表后,阿Q 这一形象被阐释为国民性的代表,之后沿两个路向分化,即被理解为农民和士大夫,分别由钱杏邨和茅盾开启。钱杏邨在1928 年指出,阿Q 所在的时代是“科举时代的事件,辛亥革命时代的事件”③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三月号,1928年3月1日。,其是旧中国农民的集中概括,新兴的农民阶级已经摆脱了他的缺点,获得了新的历史主体性。燕生针锋相对地指出:“阿Q 的时代虽已过去,阿Q 时代中所留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遗产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④燕生:《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长夜》(半月刊)第3期,1928年5月1日。在民国语境中,评论者在批判阿Q 的同时多寄予同情,“《阿Q 正传》的笔法自始至终是幽默的,忠厚的,而非是刻薄的,尖酸的”⑤林兵:《评两个〈阿Q正传〉戏》,《中国文艺》第3卷第5期,1941年1月1日。;“在未庄里阿Q 却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⑥仲密(茅盾):《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作为农民的阿Q 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其优点为什么得不到重视?
1922 年,茅盾指出:“阿Q 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⑦雁冰(茅盾):《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他在1933 年进一步解释道:“‘阿Q 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⑧玄(茅盾):《“阿Q相”》,《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日。废名延续了这一思路,明确指出,“未庄的环境农村其名而县城其实”⑨废名:《“阿Q正传”》,王风编:《废名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1页。;“主要是讽刺士人,即作者本阶级”⑩废名:《“阿Q正传”》,王风编:《废名集》第5卷,第2382页。。阿Q 在小说中明明是农民,为什么可以代表士大夫?士大夫的观念是如何沉淀到农民身上的?沉淀到农民身上的士大夫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士大夫观念有什么不同?这需要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分析。从“隋废乡官”开始,地方官实行“异地做官”,与当地士族的联系大为削弱,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如何重建朝廷对乡村的控制系统,朱熹等人试图以《家礼》和乡约等将理学推行到乡村,明朝建立起了一整套包括里甲、祭祀、乡约等相对完整的制度。清承明制,“清代沿袭了乡约制度,地方政府利用这个制度,强化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和行政控制。每个地方都要求建立乡约,定期宣讲‘圣谕’”①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02页。。为了巩固统治,清在赋税系统的里甲之外,又增加了治安系统的保甲,还特别规定保长不能由士绅兼任,《阿Q 正传》中的地保就是这种角色。保甲系统多品行败坏之人,对乡村公序良俗产生着消极影响。
作为联结朝廷与乡村的中间环节,士对乡村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采取了很多共同的措施,比如都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元朝统治者对汉族士阶层的态度与清大为不同,元朝按族群划分社会等级,汉族处于社会底层。“蒙古统治者不信任南人,限制其进入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机构,做学官是江南儒士不得已的选择。这既限制了江南儒士政治才能的发挥,也给元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带来不利的影响。”②申万里:《教育、士人、社会:元史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5页。“重视实际利益的元朝统治者虽然实行科举,但录取进士的门路狭窄,一般官吏都将胥吏的资历晋升视为正道,于是产生了胥吏官员化、士大夫胥吏化等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流品思想的一大变革,其结果可能引发吏治的颓废。”③[日]宫崎市定:《科举史》,马云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年,第30页。在元朝,科举对士人的吸引力大为下降。
对于程朱理学,元朝在推进理学北传和推广科举、祭祀、学校等制度层面做出了贡献,但始终没有实际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清朝则利用理学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有效整合,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自身的操守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集儒士、官僚、乡绅于一体的士以儒家经典作为统合士农工商的道德依据,自身依赖修齐治平的方法,实现着内心观念和外在行为的统一,但这种内外合一的模式在清朝发生着断裂,使士在朝廷和民众之间、道义和权势之间都处于两难选择境地。
与“士”的分裂形成对比的是“民”对理学观念的严格遵守,这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朱熹开始的以理学规约乡土社会的努力,到清朝时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制度。“在乡村地区,明清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存续数百年的行政管控体系。其中包括人丁、田产、赋税、商贸、文化、伦理教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中央政权对乡村治理的细化与改进,一方面加大了中央王朝对村的有效力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推进了村落共同体的形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村落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④胡彬彬:《中国村落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573-574页。此外,清政府官方推行的程朱理学和士阶层对古礼的研读考证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乡村,使得“民”真正地在言行身心等各个方面全方位遵行礼法。“礼教主义的奉行者企图通过强化宗族观念来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水平并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进而重新确立起士绅阶层在基层社会所应据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无论是在知识层面、道德层面,还是在对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层面,都应居于这样一种领导地位。”⑤[美]周启荣:《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家经典和宗族为切入点的考察》,毛立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针对清朝时期“士”的言行分离和“民”的言行一致,《儒林外史》将其归纳为“二元礼”和“苦行礼”。商伟指出,“二元礼”取代了“苦行礼”,恰是底层人成为“苦行礼”的真正践行者,“儒礼现在需要身居鄙位的局外人来确保它的诚实性”。⑥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严蓓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9页。鲁迅承《儒林外史》余绪,阿Q 颠覆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⑦《论语·里仁》,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4页。的传统,身为农民却严格按照经义修身、行事和立德。如果以“正信”为标准,对鲁迅笔下的人物超越传统的新旧之分,可以划为“有正信”和“无正信”两类:狂人、孔乙己、阿Q、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爱姑等属于前者;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四铭、高老夫子、赵七爷、慰老爷、洋少年等属于后者。前者的困境在于无法处理基本生存需求和坚守内心信念间的矛盾,但应看到其努力弥合二者的道德努力,以及失败后的愧疚自省。后者没有前者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即使行为违背信念也毫无道德压力和精神负担,反而能以高超的言语技巧将名实的分离巧妙融合,重获道德高地。这种民、士分裂的情况自晚清以来又遭遇到外来的冲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
三、“洋”的冲击:“鬼”对进化侵略的吹波扬尘
丸尾常喜认为,鲁迅笔下的“鬼”是与“真的人”相对立的落后的传统思想,“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所给予他的旧教养与感觉,现实生活使他背负的精神创伤和罪与耻的意识”①[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汪晖指出:“‘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汇聚。‘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即我们自身。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②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56页。伊藤虎丸认为,“鬼”指向反思启蒙构架,与“伪士”相对,与底层民众的“迷信”相一致的古民神思,在此可以“寻求民族生命力再生”。③[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42页。以上观点都指向一种新旧交杂的生命存在方式,而留学生最能够诠释这种时代角色。对于假洋鬼子,王富仁指出:“他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新变种,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时世的新变化在中国地主阶级这块腐木上催生的一颗毒蕈,是已微新其形而未新其思想的封建阶级的直系后裔。历史注定了他与他的同类们将成为封建阶级末代政治统治的代理人”④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页。。在这里,“鬼”的含义与伊藤虎丸的正向肯定相反,但又与丸尾常喜指向传统的消极因素不同,指向的是海外留学归来后未经本土消化检验而盲目照搬外来知识经验的一种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文中的“鬼”,指的是“假洋鬼子”代表的 “伪士”。
洋字、洋话、洋衣、洋炮、假洋鬼子、洋钱、洋纱衫,以及由“洋”带来的“恋爱”和“革命”,渗透进未庄的话语表述系统、权力秩序结构、日常社会生活,乃至于个体的情欲和意志理想追求等各个方面。问题是,“洋”的全面进入会给在“经”已破产的未庄带来什么改变?是革故鼎新,抛弃缺点,发扬优势,开创新的局面,还是加剧形势恶化,堕向更加不可解的深渊?洋字侵入,国人难以用旧有话语表述自我,落入被描述的命运。阿Q 已经不知道姓什么,只能采用一个没有任何辩识特征的“阿”字,在社会组织和价值归属层面陷入迷失。名字无从查考,其“行状”无法记录,“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第514 页);“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第515 页)。这里充满了失语的无奈,Q 并不能直接对应“桂”或“贵”,只能是一个没有内涵的空洞的能指。阿Q 最讨厌“洋”,却只能以洋字命名。这里面寄予了包括鲁迅在内的留学生,乃至整个华人群体在海外的屈辱处境。周作人解释说:“作者因为字样子好玩,好像有一条小辫,所以定为阿Q。”⑤周作人:《关于阿Q》,《周作人自编文集·秉烛后谈》,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清朝时,国人到了海外,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拖着一条长辫子,受到很多歧视。最早到北美打工的广东、福建人由于口音,“清国人”被误听且蔑称为“青虫”。鲁迅在仙台留学时,因为成绩和幻灯片事件深感屈辱,对清国留学生成群结队将辫子盘在头上逛公园的观感甚差。由辫子而受辱,在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中也多有出现。“阿Q”这个名字,表征着国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失语的无奈。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最早面对“洋”的冲击的是“鬼”和“Q”。两者有很多相似,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游走浮浪于城乡的漂荡者,都以外面的新世界作为炫耀资本,都对原来的乡土持鄙视态度,都希望在动乱年代获得新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荃麟认为,阿Q 是“现代中国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奴隶思想的结晶”。⑥荃麟:《也谈阿Q》,《文化杂志》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端木蕻良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出发,认为阿Q 是农业中国被卷入资产阶级体系的集中表现,阿Q 性最集中体现在两类人群,“既是从农村游离的劳动群,又是从宗法社会下挤出的子弟群”。①端木蕻良:《阿Q 论拾遗》(原载《学生杂志》第21 卷第2 号,1941 年2 月15 日),《端木蕻良文集》第5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但“鬼”和“Q”两者也有很大不同。“鬼”从旧士绅过渡而来,不仅承继了其资源和地位,而且还有道德伦理品质。“鬼”学习了一套西方话语,但和士阶层对待理学的态度一样,只是把西方话语当作了获取功名利禄的资本,而没有内在的认同。“Q”承继的是民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品质,严格以圣经贤传规范言行。“鬼”重权势利益,对理学和新学都不信仰,只以此作为幌子和招牌,“他也许对一切事物有过一种模糊的‘洋化’或者‘革新’的憧憬,甚至愿望,但是回到未庄的封建社会以后,他内心所蕴藏的封建思想又滋长发育起来,而把那些也许有过的憧憬和愿望完全腐蚀了,他个人和整个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彼此之间的全面协调是很可能的”②蒋星煜:《论阿Q周围的人物》,《新文艺》创刊号,1946年6月1日。。阿Q 崇信理学,其困境在于基本生存和生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而不得不做出与圣经贤传相悖的行为,但仍有羞耻之心和愧疚之心,而此困境则缘于未庄的等级压迫结构,“鬼”的介入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强化了这一结构。
阿Q 心向“革命”的原因是他在未庄处于无法生存的状态。汪晖认为,阿Q 的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发生断裂的六个瞬间,构成了觉醒的重要时刻。③参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罗岗提出“向下超越”,认为应当从阿Q 最基本的物质生存层面出发,分析反抗未庄秩序的现实可操作性。张天翼在1940 年代也提出过类似观点,“赵太爷们及其手下纵然都不把你当‘人’看,并把你教养得使你自己也忘了你是一个‘人’。但一个‘人’的欲求——你还是有的”④张天翼:《论〈阿Q正传〉》,《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这些构成了阿Q 反抗压迫的动因,但也不应忽视思想观念的价值,后者在对革命愿景的想象方面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阿Q 的反抗思想,潜藏在其所遵奉的理学道统与未庄依赖权势建立秩序的矛盾中,不应仅看作生存危机的产物,更应从有清一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分析。王夫之对“存天理,灭人欲”置疑,提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⑤[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13页。,“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则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⑥[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第641页。。颜元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在具体日常事务中践行,“辟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辩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知礼者斯至矣”⑦[清]颜元:《颜元集·四书正误》,王星贤、张芥塵、郭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9页。。戴震反对理欲二分,更反对将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理需求置之不顾,“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⑧[宋]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8页。。以此理观之,阿Q 对于食和性的需求都是正常的。“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存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⑨[宋]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8页。嘉庆、道光年间,作为对乾嘉学派专研考据的反动,注重义理阐发的公羊学派产生。这种以复古之名对新思想的寻求,延续到今文经学。康有为加入了西学视野,缺点是以西为尊,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弃而不纳,甚至为了论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对既有成果肆意窜改。这开启了弃置传统而将西方思想强行移置的不良习气。⑩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05-789页。
晚清时,魏源、龚自珍等对士人品行的无耻和世风世俗的败坏进行激烈批判,他们才华甚高而不得志,表现出“狂”的特征,一方面过分突出个体之“欲”以反抗“理”,而对“经”的合理性弃而不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个体的“意”,而对社会整体的良性有序发展置之度外。这般选择在历史环境中自有合理之处,但后人在着眼于新文化建设时,应当有批判地接受。面对西学冲击,应当在尊重学界既有成果和承继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我为主,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思想,不能像阿Q 那样借助外来名词,张扬的恰是既有思想中的“偏激”部分。
阿Q 对“恋爱”和“革命”的理解,承继了有清一代对“欲”的强调和“狂”的推崇,“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第539 页)。阿Q 对“革命”的幻想,与鲁迅批判的“兽性爱国者”一样,“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鲁迅对西方文化考察分析后指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应“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②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改革者往往只注重西方强盛表面的物质兵事,再与传统中“本尚物质而疾天才”③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8页。的缺点结合,“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④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8页。。康有为也有此论,“然而欧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也,而中国数千年圣哲贤豪之美化,则已涤荡扫除而无所留矣。且假令去中国之化,而真能受欧美之化,犹未可也;以施之于中国之历史习俗,未之宜也。况两化俱无,则为暴戾恣睢,纵欲横行而已”⑤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康有为全集》第10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对此路径,鲁迅称之为“缪而失正”⑥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何谓正路?希望在“鬼”和“Q”的哪一方?如前所述,革命前,阿Q 以赵太爷为榜样;革命后,以假洋鬼子为楷模。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皆为“无正信”之人,后者对待西学的态度和前者对待理学一样,都是以西学或理学为名获得权势,内心并不真正遵行。鲁迅感慨道:“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⑦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从城乡结构来看,是少数畸形繁荣的城市与广大被剥削、日益贫困的农村的对立,茅盾等人的“丰灾”小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从阶级情况而言,是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从新旧观念来看,是“西学”与“理学”的对立。鲁迅解释阿Q 的创作起因:“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⑧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这样的对立,成为底层反抗的持续动力所在。阿Q 是“受压迫者”,同时也包含了“革命者”,即在合适条件下的反抗。面对“洋”的冲击,希望所在恰不是唯洋是从、挟洋自重的假洋鬼子,而是顽固坚守礼法的阿Q,也只有在其身上才能寻找到吸纳新文化的根基。伊藤虎丸指出:“中国革命除此之外(自我变革以外)再没有可作为其承担者的‘国粹’的主体,而在这个意义上阿Q 也便是个‘积极人物’。鲁迅后来作为小说家的不断努力,体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在民众(国粹)当中,而不是在正人君子当中,去摸索这种能以自己的‘国粹’来托生欧洲近代之‘人’的变革主体。”⑨[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59页。
四、“人”的再造:“信”对道德品行的重新建构
通过新人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是新文化建设的一贯主题。新人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再造,一是知识观念的更新,一是道德品行的重构,前者只有建基于后者,“先觉觉后觉”的思想传播路径才能在民众中发生作用。诸多前贤已充分注意到“德”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严复从民力、民智、民德等三个方面讨论国家富强的办法,“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⑩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页。。康有为说:“夫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敝,无一可行也。”⑪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130页。梁启超说:“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帅。”⑫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卷,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45页。“德”的建设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面对“洋”的冲击,传统道德是应被完全摒弃,还是对新文化建设有可资借鉴之处,甚至不可或缺?黄进兴指出,梁启超早期批判中国有“私德”而无“公德”,但之后,“他坚持:‘若夫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①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第116页。鲁迅像梁启超一样思考着社会转型期“德”的承续问题,刚到日本时提出从“诚与爱”的角度思考国民性。《新生》时期从建设道德的根基处提出“正信”,以之为沟通传统的“诚”与未来现代社会的“信任”间的桥梁。“由仁、礼、中庸构成的整个儒学框架,又是建立在‘诚’这个基础之上的。‘诚’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为真实;作为道德范畴,是为诚实。而内心之‘诚’体现为对人尽心时则谓之‘忠’;‘诚’之外在表现则是取信于人的‘信’。”②《中庸·前言》,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87页。
朱熹对强调以诚修身的《大学》格外看重,“《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66页。。“诚”作为传统士人践行“道”的根本品质,指向的是自身与道的关系,而信是个体在践行诚时的具体体现。“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王星贤点校,第113页。朱熹对相关概念进一步区别道:“诚、忠、孚、信: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存于中之谓孚,见于事之谓信。”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王星贤点校,第110页。“诚”是人与道保持一致的客观实有关系,无善无恶,中道而行,只有圣人可以做到。普通人加入了个体的“私”来努力致于道,具体表现为“忠”“孚”和“信”,“忠”处理的是自我与道的关系,“孚”处理的是内心与外在表现的关系,“信”处理的是自我与具体行动的关系。阳明心学只是将本体由外在的“理”转向内在的“心”,但对“诚”的强调一以贯之,“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⑥[明]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集》上,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页。;“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⑦[明]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集》上,第23页。。
传统社会以“诚”作为道德根基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起点,是将个体、社会、宇宙联结在一起的思想基础。“洋”的冲击,带来了现代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建基于现代工业生产之上的个体意识,传统的认知系统和价值系统都面临巨大挑战。“诚”作为认识世界和道德品质的共同基础开始分裂,鲁迅放弃“诚与爱”的思路,转而提倡“正信”,对传统的“诚”建构的个体、社会和宇宙的一元联系有所松动,但仍强调内在信念对外在行为的指导作用。他对建基于“正信”基础上的内面主体的呼喊,以及对“心声”“内曜”的发扬,保持着对现代社会中以个体为行为单位的新的道德价值建构开放的可能。
“正信”是在社会转型期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约束观念和行为的粘合剂,并保持社会是一个可以互相沟通运转的有机体。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只有上帝施恩于人的过程中,同时人们感受到这一过程的时候,选民才能与上帝形成共同体,并且感觉到这一共同体的存在。换言之,他们的行为都源自对上帝恩典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反过来通过他们行为的品质来肯定自己。”⑧[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在从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的法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体从相对固定的时空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生命自主权,“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⑨[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信任是在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生产和生活中的德行基石,也是现代工业社会必需的基本品质,“信任最抽象的对象是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或政权制度(regime)的总体品质”⑩[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0页。。“信任”奠定人伦规则,沟通古今中西不同观念,是建设新文化的基石,它就像货币一样,是超越具体时空限制而形成的信用体系,不同的具象都有赖于通过与它进行交流,从而避免了很多沟通成本。在建立现代“信任”的过程中,“正信”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沿“正信”而行,可以从新旧冲突中脱离,提倡新并不必然遭到旧的反对,而没有“正信”的新,很难获得本土生命力;旧也并非全无是处,它遭到底层的抛弃源于失去“正信”。《阿Q 正传》中旧的统治阶层的文化体系已经崩塌,但作为底层的阿Q,观念世界依旧顽强地执着于宋明理学建构的世界。阿Q 通过“精神胜利法”,以内在精神固执地对抗不合礼法的周围世界,在虚幻的胜利中获得精神满足。如果从“正信”角度来看,这是通过抵抗以求精神世界完整,那么这个抵抗的过程就成为观察、思考中国转型期底层民众文化心理的重要契机,也潜藏着“新的主体”诞生的关键要素。对阿Q 的批判,还是多囿于观念对错和现实成败,而忽略了最为宝贵的“正信”品质和“抵抗”姿态。
新人再造,一向重知识更新,轻德行建构。这缘于对现代主体性的迷思,即通过建构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理性人”,以完成现代化宏图。在这种路径设计中,中国文化传统便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亟须断裂的历史负担;另外,现实也处于需要被改造的落后状态。但这种方案难以在中国落地生根,更不可能实现其设定目标。在《阿Q 正传》中,“洋”给未庄带来的变化是表面,甚至是负面的。“洋”必须在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特征和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为积极建构的力量融入。如果置有清一代的士民关系于不顾,不能重建未庄的“正信”,那么“恋爱”就会变成放纵,“革命”就变成造反。
进入现代转型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国人对工业、城市、个体、科学等过于迷信,完全以城市为导向,导致对传统农业文明中的优秀遗产选择性忽视,阿Q 也沦为负面典型,成为自证缺点和自我吞噬的症候。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农业、农民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真实的内在思想和情感却在价值评判系统中处于失语和被否定状态。这对城市的发展构成了牵绊,不利于那些像阿Q一样的“城乡浮浪者”的精神文明建构。城市吸取了他们的青春和劳动力,但社会价值体系认同和精神归属等任务,却由农村承担。这样的分裂,也使得城市日益繁盛而乡村日渐凋敝。当下,在重提“乡村建设”声音中,有学者提出“回嵌乡土”①参见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就格外有意义和眼光。
阿Q 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底层的代表,以“圣经贤传”为人生法则,并内化为自觉的道德。由于连基本生存都不能维持,这套法则呈现出种种的不合时宜,阿Q 只得以“精神胜利法”求得心灵安慰,但他并不像“志士”和“伪士”那样言行不一,而是努力使行状圆满,至死不忘。阿Q 所秉持的理学观念在新时代落伍,但其所呈现出来的努力保持德行的纯洁和品行的合一,恰是最为可取的。观念可以改变,但对观念的忠实品质需要保留,这也构成了连接新旧过渡时期最为重要的桥梁。
五、结 语
经历百年思想启蒙和革命斗争的洗礼,在完成了新的政治主体再造后,需要一种可以整合世道人心的道德品性的建构。回顾既往,经过充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站在新的时代起点,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寻找出两者可以连接的共通部分,充分挖掘文化传统中可资利用的成分,建构一套新的“正信”价值体系;对于未来而言,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市场大潮,人心浮动,需要一套稳定的价值系统,以应对资本力量对伦理品质的腐蚀和破坏,为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提供精神层面的定海神器。充分尊重以“正信”为根基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为基础,有效提炼、承继其中正面的活力部分,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有效接纳、化合外来文明,从而建设积极正向的新文化,既有利于自身发展,也能有效地贡献于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