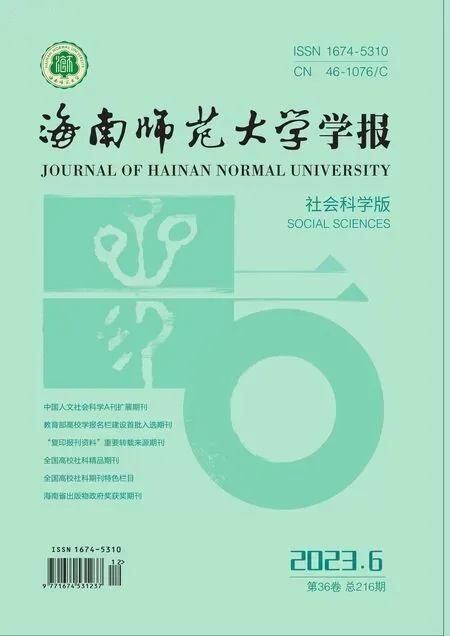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李 松,成文奎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引 言
近年来,海外学界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例如梅维恒(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①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omepage, 2001.、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②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 ,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张英进主编的布莱克威尔版《现代中国文学指南》③Edited by Yingjin Zhang,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2015.、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指南》④Edited by Kirk A. Denton,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魏朴和(Wiebke Denecke)、李惠仪(Wai-yee Li)和田晓菲等编撰的《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⑤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Xiaofei Ti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等,这些文学史著作不仅提供了新的知识与观点,更突出展现了生成新知识的思想与方法。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编的《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⑥Edited by David Der-wei W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该书中文版译作是《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繁体版由中国台湾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出版,简体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以下简称《文学史》),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思想基础,以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为叙史形态,无论观念还是体例都令人耳目一新。目前,学界关于海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不少,视角多元,各擅胜场。余来明①余来明:《我们应该怎样写文学史——王德威主编〈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之思》,《写作》2018年第7期。从“现代”“中国”“历史”“文学”等四个关键词出发,论述了该书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超越”,启发笔者探究文学史书写的方法论。季进②季进:《无限弥散与增益的文学史空间》,《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和陆丽霞③陆丽霞:《弥散的话语空间与多维的历史图景——论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对文学史空间的阐释,体现了研究者对书写空间及其转换的关注。总之,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亟需回答的问题,也为笔者考察该书思路与方法背后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即历史观念提供了启示。本文试图以“福柯”(即福柯的历史哲学与书写实践)作为方法(method),探讨该书作为文学史基础理念的历史观,同时指出这种历史观的合理性
一、《文学史》的书写理念
如果说1961 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成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正式取得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2017 年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世,则意味着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发现与突破性认识。这两本书既是学术史的承传与对话,也是文学史观念在不同时代与环境中的革命性突破。《文学史》“新”在何处?王德威说明了该书的编撰宗旨:“归根结底,该书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通过重点题材的配置和弹性风格的处理,我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棋罗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④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页。除了从解构主义意义提供颠覆性、挑战性的“新知”,其书写方法本身也在内容与体例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这样一种新的书写方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生成于西方人文学术丰富的理论土壤。王德威在多个文本中所述的西学理论,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星座图”(constellation)、“拱廊计划”(Arcade Project),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genealogy),或德勒兹(Gills Deleuze)的“组合论”(assemblage)、“皱褶”(fold)论等,构成了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脉络,这些西学理念都在《文学史》的编纂中留下了理论痕迹。⑤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14页。这些理论资源以现代性作为批判对象,成为本书超越历史理性化的思想依托。
该书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新编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系列的第四本,也遵循了该系列挑战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方法:“一反以往文学史那种以大师、经典和历史事件来贯穿的线性书写,代之以看似武断的时间点和条目,由此编织成散点辐射式脉络”⑥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19页。。同时,该书面临如何解决以下文学史问题的困难:“过去的”中国与西方影响下“现代的”中国,如何书写编纂者“不在场”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史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学话语自身有着深厚而绵长的生成史。近代以来,由于古今中外各种复杂因素的聚合、裂变,研究者需要调整“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中国看中国”的视角,尝试“从世界看中国”的可能性,既有从世界视野重新理解诸如“文学”“中国”“现代”“历史”等议题,也有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思考的“何时现代”“何为现代”“何为文学”“何为‘文学史’”,以及如何“讲述中国”等问题。《文学史》与前三部《德国文学史》(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法国文学史》(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美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不同的是,其所要表达的“中国”是一个极为丰富而异质的概念:“作为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重层历史积淀,一个文化和知识传承与流变的过程,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想象共同体’”⑦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17页。。以上追问,最终指向的是回答“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⑧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6页。。
王德威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他认为,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在过去也是一个很标准的学术研究的课题,用一个新的观念套进去,自然产生不同的意义维度。探讨《文学史》书写中的理论互动是理解其书写方法的关键,而这需要依循一定的线索与路径来追踪。如上所述,王德威在该书的《导论》中交代了文学史编纂中形形色色的理论幽灵,如福柯的谱系学等①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14页。,福柯理论的魅影处处显现。第一,福柯之于王德威的直接影响。作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的第一位中文译者②参见[法]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中国台北:麦田出版,1993年。,以及作为中国大陆学界所熟知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式命题的提出者,王德威的理论支撑显然难以缺少福柯。因此,就王德威的知识结构和文学史观来看,福柯的理论即使不能说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第二,编撰者与福柯思想立场的契合。福柯是一位思想边缘的行者,是其时代的“反对者”,他不满、对抗,甚而是叛逆,或带着某种“影响的焦虑”。从福柯与《文学史》的主编王德威两者跨国、跨文化的边缘身份及思想位置来看,他们的历史观念与思考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在某种程度上应节合拍。以“中心—边缘”范式来观照福柯,与之对照的是,该书往往立足于边缘立场,秉持一种批判传统、突破陈规的思想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就《文学史》主编来说,其书写初衷并非是为某种理论作注脚;就参与者的书写实践来说,并非完全遵照或演绎、套用某一理论,毕竟各人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素养、人生经历、学术训练。本文以福柯理论作为方法,并不认为可以将其平面化、简单化、工具化理解,而是尝试探析在《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中,王德威、福柯理论、《文学史》文本这三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文学史》的知识考古学
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上,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后,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Archaeology)方法强调历史的偶然性。知识考古学是指:“重构和考察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的条件的知识”③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4页。,它是反形而上学的知识考古,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事先了解的全貌,只是通过考古发掘,一点一点地探寻未知的世界,而所得到的发现也是偶然的、片断的、不成系统的东西,所以,也就无所谓规律与大写历史。简言之,知识考古学是将“话语”作为“实体”来分析。④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可以认为是“话语的自我体系”,这其中的“话语”是指“人类社会中,所有知识讯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现象”。⑤[法]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第29页。因而,面对“文学史”,知识考古学的处理方式是,将其“话语”乃至其本身作为“实体”进行探析。“话语”一旦不作为“实体”的表征,而是被视为“实体”,它就失去了连续与绵延,而遍布“罅隙”。在“罅隙”中,“话语”如“化石”般没有主体性、自在自存。空间层面没有总体性,凌乱碎裂;时间层面,没有连续性,褶曲断裂。“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的特殊性可暂时不管)的学科,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⑥[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历史深处的断层与裂隙成为意义生产新的可能。
李杨曾经探讨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视阈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这为本文探索《文学史》书写理论的福柯之维提供了参照性的启示。⑦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文学史》对“诸如‘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以及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⑧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6页。等经典命题进行重新探讨,体现了知识考古学“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意涵。因此,本文将话语作为文学史知识的考古对象。当然,“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这三者并非一种直线式或金字塔式的关系,它们同样“互缘共构”,缺一不可,互相生发。消解“主体”,意在避免主体通过翳蔽离散和多元以维持一种总体和连续的假象。打破“总体”,意在释放诸多所谓的“主体”——从而消解自身。在缺乏“总体”的图景里,破碎的“星空”各有各的时间与运动,在纷繁中消解对于“连续”的叙事和想象。斩断“连续”,则是抽掉“主体”和“总体”的基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①[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第13页。。相较于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史理论,王德威和其他参与者更乐于在书史的过程中发掘边缘知识的真相,而这种对“知识”“真相”的追寻,必须打破为“想象”民族国家或其他目的而建构的总体性的“文学史”,即重新书写一部“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文学史,实现对“现代”“文学”“文学史”等主导话语的重新探讨。
(一)反主体
知识考古学方法阻却了“主体”出场的可能性,主体“已近于一个被抽空的概念”②郭洪雷:《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已经指出了它的虚构性,因而对那种想象性的奠基性的主体就可以置之不理。”③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对话语的分析不是去发掘和描摹话语的主体,而仅是探究“话语”本身的实践。“反主体”的最终形态就是“人之死”。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人”是近世的产物,“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两个世纪的角色,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④[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0页。,而在此之前,“人”在话语实践中并不存在。在福柯这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⑤[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第392页。,他“始终怀疑和敌视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主体”⑥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479页。。《文学史》碎片化的历史观对“主体”抱持怀疑,并以多种方式表示其“反主体”的立场。
《文学史》通过书写者的多元来消解单一“主体”的褊狭可能。文学书写空间里充斥着无数可能的主体,这样的图景使得《文学史》缺乏一个“整体性”的主体,某种意义上成为各种话语的独自言说。以往在民族国家基底上的文学史书写,不管是独著或合编,将书写者隐匿在一个整体叙事中,书写者是某个“主体”发声器的不同侧面,经过“合体”书写使之显现,在教育或阅读机制中为读者所接受。典型的做法,例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着强烈的“文学演进”意识,“民族中国”这个“主体”在时间层面沉浮,以一种类“人”化的存在主导文学史的书写。但在《文学史》中,“主体”存在的唯一“迹象”就是“编年”,将不同的话语按序排布到时间的绵延之中,“主体”的意志难以明显被发掘。而“编年”体例,某种意义上是由人类语言的秩序性组合本质所决定的,但是这一线性形式的排布展现的是话语的非线性内涵。
《文学史》以作家为“自己”或其血缘上的“后代”写作来“反主体”。在文学史中,由“谁”来书写,本身就是对“主体”的追问。王安忆对“茹志鹃”、朱天心对“朱西甯”、莫言对“莫言”、余华对“余华”的文学史书写都表征对传统书写主体的背反。中国大陆现有的多部经典文学史著作中,鲜见这样的写作主体,即文学史书写“对象”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体”即书写者,这无疑是对“主体”本身概念的“破坏”——“主体—对象”二分的结构不再存在。该书中,作家莫言的文章与其说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不如说是对自身书写的捍卫以及在文学史论域中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作家余华讲述1980 年代的先锋写作,也似乎以这一文学史事件给出自身的文学史定位。
《文学史》“反主体”有着多重动因。第一,知识考古学试图通过“反主体”保持一种“中立性”⑦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页。。该书的编纂缘起是为英文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研究者应该回到海外的学术语境与预设的读者对象来理解其理念,以免在语境错位的基础上形成强制阐释。个体书写者的意识形态选择比较单一,但一百多位书写者众声喧哗使得“主体”的倾向性不复存在,或者说这种判断交由读者去完成。①王德威、苗绿:《重写中国文学史——王德威教授访谈之一》,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王德威曾经在访谈中认为:“我们现在多了后现代的包袱,没有一个是超然的、透明的伟大叙事,它是众声喧哗。”②王德威、苗绿:《重写中国文学史——王德威教授访谈之一》,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第120页。第二,《文学史》在“异托邦”空间的书写,本身就充满各种可能的主体安排,而这些可能的主体如何安排呢?主编的处理方式是以“反主体”的姿态使其各自言说。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以往文学史书写主体过于强大的决定性意志。传统文学史总是存在着一个强烈鲜明的“主体”,这种“主体”掌握着某种文学话语能否进入文学史的权力。《文学史》则力图重新发掘历史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对掌握“总体性”的传统文学史“主体”进行拆解。另外,“反主体”意在回应王德威及诸多书写者“不在场”的问题。“反主体”意味着“摆脱自我”与“另类思考”。③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越界、褶曲与布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1页。在“反主体”中,“我摆脱自我成为他者”,也就是说,无论是处于文学发生主体场域的中国大陆书写者,还是处于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场域的其他书写者,抑或本来就是以“他者”身份观照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在此刻的书写身份是一致的,即以某种“他者”身份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另类思考”。
(二)反总体
启蒙历史观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每个人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力量,因而,历史学者的工作是从中追问“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形而上意义, 掌握普遍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价值。主体的消解也意味着总体的破坏,在《文学史》中,充斥着各种破坏“总体性”生成的书写。“一切解体,成为流动的、散点透视的状态。”④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0页。该书打破了大众对文学史基本范畴的总体性认知。从“文学”看,“文学史的写作,蕴涵着文学观念的变革”⑤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页。。在王德威看来,“文学无他,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取消、彰显和遮蔽的艺术”⑥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39页。。而作为核心话语的“文”,王德威则认为:“‘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模拟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映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呈现的经验集合”⑦王德威:《中文版序》,《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iii页。。返观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相比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等,《文学史》除了容纳大众惯常理解的文字作品,还有“画报”“木刻”“电影”“食物”“档案”“打字机”“摇滚”等作品和物件。这些边缘话语破坏了“文学”纯粹的文学性,仿佛任何材料都可以归入讨论,不再将“文学”的领域封闭起来,而是敞开固定的自律性边界,对文学史书写内容进行无远弗届的扩容。《文学史》不仅以“文化”来容纳语义射程极其宏阔的“文学”观念,而且打破了读者对“文学”的习惯性认知,刺破各类文学史著作为“文学”构造的总体性泡影。
按照读者惯常的看法,作家及其作品通常是“文学史”所要书写的“对象”,这样才可以获致某种客观性,但是在《文学史》中,余华围绕《收获》杂志1987 年第5 期的出版,通过写作《制造“先锋”》一文,谈论自己的“先锋”小说写作,结篇部分写道:“20 多年后的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不会在夜深时紧锁大门,可以24 小时进出。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现在也成了我们的文学传统。”余华在这里以华东师范大学1980 年代紧锁的铁栅栏门与如今可24 小时进出的校园来隐喻“先锋”文学在中国的结局,以隐喻的文学手法来重新书写已经为文学史所包纳的“文学事件”。⑧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张治等译,第1011页。由此可见,文学史书写这一行为已经不再有其“同一性”,本身成为一个“复数”和“杂陈”的“反总体”物。对照目前传统或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书写者,基本为典型的学者,鲜见其他身份,尤其是由“作家”本人或其后代来书写这个“作家”的文学史。王德威期望或想象的文学史,就是文化意义的文学的历史,而非“跟经济史、社会史、地理史放在一起,只是文学有那些事儿,把它做成资料而已”①余雅琴:《专访王德威:此汉学非彼汉学,小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原载《南方周末》2022年9月22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35243?source=131.。更重要的是,在元文学史的视域中,去“叩问‘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一种论述、一套文史互动的法则,本身是如何生成的”②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石静远(Jing Tsu)撰写的《林语堂与“明快”打字机》将这种“反总体”的考古学书写展现得极为精彩。在通常的认识中,“打字机”与“文学”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而只是在文学的物质书写这个层面有着间接联系。但是在对“文学”的反总体性认知和定义中,发明打字机作为文学史事件被书写,则并不欠缺正当性。从科学发明的艰难历程来透视汉字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该文细腻地关注到打字机所表征的“汉字书写的媒介问题”,这一问题牵涉文学现代性的几个重要关键词,那就是“现代”“世界”“德先生(科学)”。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其遭际是“对中文这一充满文化意蕴的象征所做的一项科学演绎”③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张治等译,第738页。,更是对中文如何赶上并融入现代化进程这一命运的微观折射。
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未定意义的可能性。福柯认为:“我们竭力在面具下确保和聚合的同一性,本身不过是个可笑的模仿,它本身是复数的,内部有无数的灵魂争吵不休,各种体系杂陈交错,相互倾轧。”④杜小真编选:《福柯集》,第163页。总之,在“反总体”的映射下,可以发现,《文学史》挑战传统惯例对文学史书写范畴的制约,将其“再问题化”,以实现对文学的开放式认知、想象与书写。
(三)反连续
文学史的连续性叙事体现了线性历史观的规范,“亦即文学的发展必然是按照线性指标,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⑤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启蒙时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前后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与现代性历史从源头推导发展历程的方法相反,福柯的“系谱学”(Genealogy)方法则从当下溯源过去,摒弃预设的“中心化”与“精英化”立场。
王晓明曾经反问:“我们为什么要死死抱住那个线性进化的文学史模式不放呢?”⑥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文学史》对这一文学史模式进行反拨,致力于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该书的连续性固然体现在其按时间“编年”的161 篇文章之中。不过,在后现代主义史家的眼里,“编年”并非一种有意义的历史书写形式。⑦[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张文杰:《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某种意义上,“编年”从反面昭示《文学史》的断裂与差异——除话语不得已的线性时间生成外,也呼唤更多具有阐释价值的时间节点的出现。陈晓明认为,“文学史”在20 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⑧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而《文学史》则反对线性进步观,各篇之间不存在一个递进的、起伏的关系,反倒是“并置”的,将文学史中的每个时刻视为与其他时刻没有二致的独立界标。或许可以将这样的抽象论述放置在这样一个隐喻图景中:线性进步观的文学史是“一道手电筒发出的光线”,有其清晰的原点,也有绵延的光轨;“反连续”的《文学史》则是并置于天空的“星光”——无论这些“星光”是从几万年前发出,还是几分钟前发出,在此刻的天空并无二致。简言之,“反连续”的知识考古学将历时层面的“时间”规范置换为共时层面的“空间”意象。线性时间观某种程度上意在推导出“进步”与“必然”,但在福柯看来,这“其实是传统思想家杜撰的一个神话”⑨王治河:《福柯》,第90页。。“历史的本质乃是断裂、不相连贯。”⑩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文学史》拒斥“线性”的连续,也拒斥一种“文学”不断演变进步的观念。⑪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32页。扩而言之,考察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不存在一厢情愿的连续性,反而存在着无数的“空档或深渊”。①[法]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第35页。例如,关于“1935 年”这一时间节点,王德威接受访谈时说:“那一年,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受欢迎;电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杀,成为媒体的焦点;而河北定县的农民首次演出《过渡》《龙王渠》等实验戏剧。文学史的时间包容了考古学式的后见之明”②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这样的时间并置是《文学史》的有意布置,将文学史话语的碎片并陈,期待读者读出其中隐微的文学性巧思与文字所未阐发的文学史知识。
《文学史》的“反连续”还体现在,书写者减少对大作家、大作品、大事件的关注,增加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作品、小事件的研究。在主流的文学史著述中,大叙事往往确立文学史线性连续的坐标,而且自身的历史书写谱系也极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连续性。反过来,小人物、小作品、小事件则被排除至边缘,至少就文学论域而言,它们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之外。例如,古柏聚焦“1650 年7 月22日荷兰报刊报道的明朝覆灭”,根据明王朝覆灭写就的《鞑靼战纪》(About the Tartar War)在欧洲市场颇受欢迎,而这是主流文学史很少关注的“边角”事件。③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49页。再如,汪晖在《鲁迅与墓碑》中讨论“1925 年6 月17 日”鲁迅编撰《坟》,“墓碑”“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表征的挖掘,与鲁迅的文学书写联系起来,发掘作为墓碑的“文学”与作为文学的“墓碑”。④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383页。这些论述脱离了对“连续”的追求,曾经被线性进步观主动忽视或被动舍弃的文学现象、文学事件浮出历史地表。《文学史》通过发掘中国现代文学的“罅隙”,以尽可能地探索文学史历史节点的“方向”与“可能”,使得曾经受制于连续线性书写而被翳蔽的文学话语得以重回文学史,丰富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阐发和理解。《文学史》借助知识考古学,一反读者以往对文学史巨细靡遗、面面俱到的期待,不是对“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也并非“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⑤[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第151页。在“反主体”“反总体”与“反连续”的操作中,解构主义的文学史理论呈现出历史的罅隙,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邀请“读者参与,持续填充现实,更新观念,证成感知开放的状态”⑥王德威主编:《中文版序》,《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iii页。。
三、《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学
福柯的知识系谱学方法意味着显示年代概念,一代代人物的排列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也没有高潮,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考古学与系谱学是福柯哲学不可分离的方法。”⑦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越界、褶曲与布置》,第3页。两者都是对传统“话语”的“重新评估”,都否定传统史学和人文科学的形而上基础,从而“相互呼应”。⑧[法]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第39页。考古学与谱系学存在着接替和深化的关系:“以权力为中心的谱系学开始接替以话语和知识为中心的考古学。谱系学和考古学相区分,但同时又是它的深化补充,它不是同考古学的原则一刀两断,而是采纳了考古学的要义,同时,又将权力注入考古学中,将社会制度、实践的楔子钉入考古学中。”⑨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161页。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知识谱系学方法成为了一种基本的研究范式。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这一传统文学史书写无法绕过的问题,王德威从“福柯谱系学的角度以果寻因,追本溯源”⑩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24页。,在谱系学视阈下回答这一问题。然而,知识谱系学“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作有关价值、道德、禁欲主义和认知的谱系研究,决不是把历史插曲当作不可把握的东西忽略掉,决不是径直去追寻它们的‘起源’。……历史有它的强盛、衰弱,也有神秘的迷狂和晕厥般的激动,它是生成变化的肉体。只有形而上学家才到遥远的起源的观念性中为自己寻找灵魂”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第146-150页。。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并非回答问题,而是将问题对象化,对“问题”本身进行研究——“其实是个问号”①朱又可:《“原来中国文学是这样有意思!”王德威谈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原载《南方周末》2017 年8 月24 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27302?source=131.。利用这一小“问号”,“将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这些古老话题再次问题化”②王德威:《文学史也要讲好文学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24日第18版。。因此,不能在传统文学史“起源”这一思维范式下认识和理解《文学史》所界定的“1635 年”这一书写起点。承接知识考古学的“反连续”,就谱系学而言,“谱系学导向的历史不是寻找我们同一性的根源,相反要尽力消解它,不是确定我们源出的唯一策源地、那个形而上学家预言我们必将回归的最初决定,而是致力于昭显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非连续性”③杜小真编选:《福柯集》,第167页。。因此,如果从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接续的视阈来看待,那么“1635 年”也不是《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起源”问题的传统回答。谱系学“研究来源和出现”④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166页。,它“重视事物曲折、颠簸的‘由来’(descent,Herkunft),而非一路无碍的‘源起’(origin,Ursprung)”⑤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34页。。来源与起源不同,至少在存在数量上,来源是复数,而起源是单数;在“夜空的星光—手电筒灯光”隐喻认知下,来源就是“繁星点点”,而起源就是手电筒灯光最初发出的位置。起源是线性历史观的端点,而来源反对“线性”,它是“散点”。也可以认为,《文学史》是在“来源”而非“起源”的意义上界分出“1635 年”这个书写起点。“1635 年”的设定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福柯式的典型做法:“按传统史学首重起源,顺时而下,而福柯却把源起设于‘当前’,倒果为因,逆行而上。”⑥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22页。在《文学史》第一篇文章中,李奭学讨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首先,他将“中国文学面貌的契机”追溯至改宗天主教的儒家官员杨廷筠的宗教小册子《代疑续编》,《文学史》中“文学”的定义相当于英语词汇“literature”,指称的是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其次,李奭学论述了1932 年周作人发表的现代文学起源的演说(即稍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认为其“在晚明发现的是有关五四人文主义自由派话语的源头”;再次,李奭学讨论了1934 年嵇文甫的《左派王学》,认为该书追溯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至晚明,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标志”。对此两例,李奭学认为,“两人都以有意的以今搏古,对历史进行一种现代意味的介入”,而就“1635 年”这一时间点来看,李奭学本人的界定也是“倒果为因,逆行而上”的福柯做法。不过,他相比于周作人和嵇文甫更进一步,认为“关于‘现代’中国文学‘源起’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结局的叙事”,“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有如满天星斗,闪烁万端’”。⑦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42-46页。这样的做法以及对“源起”问题本身的看法,都不自觉地暗合福柯的“谱系学”理论。
王德威曾经指出:“中国文学它永远是不必定为一尊的,中国文学的缘起永远是可以再给它一个新的源头。而这样的一种作法,恰恰符合了什么是我们现代性、当下性的一个对‘现代’的敏锐思考和感受。”⑧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长江学术》2012年第4期。他不再寻求一个单数的“起源”,也就是不再对“起源”作传统的线性思考,而是借助谱系学尽力挖掘“来源”——不会归结为“一”的“来源”。究其根底在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不可能在某一时点突然齐备,它的各个侧面、各种因素在不同的时点酝酿。因此,“要紧的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任何断言式的起源论述,都是掌握或意图掌握“权力”的“主体”试图在“总体”和“连续”中“想象”自己的“手段”。“所谓传统不能再被视为是时空切割的对立面;相反的,传统是时空绵延涌动的过程,总已包含无数创新、反创新和不创新的现象及其结果。”⑩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27页。《文学史》中隐含不少的“历史引爆点”可催生被称为“现代”的中国文学:“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从另一角度来说,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⑪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8页。
在知识考古学视阈下,《文学史》拒斥对“起源”做断定的书写。《文学史》尽管上溯至晚明,但这并非起源,而是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某个来源,正如题名所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①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41页。这样写就的文学史无法从“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相”出发对其作出评价,因为“谱系学从不宣称自己对于历史的观察是客观、公允、全面和不偏不倚的”②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167页。。发现并复原历史原貌,发掘历史科学真相,“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中被质疑与动摇。因而,谱系学视阈下对“来源”的探索,解放了文学史书写的桎梏。正如学界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的热烈讨论,《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晚明”开始写起,如果引起传统文学史书写者巨大的“震撼”与“批判”的话,并不意外。
四、《文学史》的实践价值
《文学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传授知识的教科书,而是力图针对海外读者围绕“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些基本概念进行解构式的重新书写。这是一部跨越中西文化、隐含比较意识的、“关于可能性”的文学史著述。正如唐小兵所说:“一部文学史书,也只是叙述者的一家之见,绝不是真的就是历史。”③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6页。《文学史》依然需要接受韦勒克的诘问,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④[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52页。
成书于1989 年的哈佛版《新编法国文学史》⑤Edited by Denis Hollier,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下,展现了彻底的解构姿态。⑥Edited by Denis Hollier,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p.xxv.作为哈佛版“新编文学史”系列的第一部,这本书为该系列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书写姿态——解构。《文学史》则延续这一传统,基本保持了同样的书写姿态⑦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以“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突破了主流文学史的严谨体系与规整构架,从而寻找历史的罅隙与碎片,以期发现“文学”话语的现代生成,即“中国”何以“现代”。哈佛版“新编文学史”系列在第一部出版多年以后,才出版了第二部,即《新编德国文学史》⑧Edited by David E. Wellbery, Judith Ryan,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其对第一部保持了一种反思性的接续,“有‘进’有‘退’”⑨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新编德国文学史》的主编大卫∙E. 韦尔贝里(David E. Wellbery) 与朱迪思∙瑞恩(Judith Ryan)并不满意纯粹的解构,而是追求一种解构之后的重构。200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国别体“新文学史”系列出版了《新美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和沃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共同主编。该书秉持文化视野的文学观。文学内涵大大扩容,模糊了文学与文化的边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去分化的理念,主张文学史的建构观,拆解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强调历史横断面的小叙事,重视文学接受的考察。⑩李松:《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文学史》也接受了这样的书写思路,同时试图尝试在“解构”与“问题化”之后,尝试“重构”文学史,可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反思的平衡”。
回顾以往的文学史书写实践,基本上是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学反映。⑪参见[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53页。“通常称之为文学史的东西,同文学便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⑫[比]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不过,自从“文学史”这一现代装置被发明以来,对于书写“文学”的文学史,不乏这样的书写自觉。王德威认为:“文学史自有它的历史脉络,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发明。”⑬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第6页。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文学史》精心制定了追求“文”的文学史这一学术理想,从书写技艺与文学观、历史观这两个层面生成文学性①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力求实践“文学性”这样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②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4页。王德威借用中国“诗史”传统和钱锺书的“管锥”方法,强调文学史的“文学性”表达,鼓励书写者尤其是极富想象力的作家们“选择最得心应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历史‘感’。”③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16页。《文学史》以碎片式的书写来生成自由的“文学性”。
文学史的撰写是西方近代历史理性的产物,《文学史》则是对历史理性“合理化”的现代性道路一定程度的抵制。笔者明确认为,《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思想革命和体例实验意义的重要成果,其思路与方法对本质主义的文学史叙事进行了拆解,拒绝文学历史成为某种抽象的逻辑框架统摄的程序,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开拓活动。从对立角度而言,《文学史》宣告了文学史书写的终结。作为本质主义的历史理性预设了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构建了一系列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概念模式对文学史的言说方式进行规范,导致的结果是书写者不得不遵循这套话语方式对鲜活的文学作品、现象、事件、作家、读者等问题进行非个人化的裁剪。例如,以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作为普适性话语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那么不符合这种规范的作家和作品则被淘汰出局。以历史理性对文学史事件的整合,通过文学史理论预设的理性力量,使文学史中的偶然事件在思维中统一为一个历时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的过程,原先零散的历史碎片被整合成一个一维连续体,并被人的认识能力所理解。现代性本身的缺陷造成了它自身的对立面,从而引发学者们对现代性负面价值进行批判和反思。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思的策略,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反思、重新调整或矫枉过正。经过后现代主义者的反思和批判,重建社会、历史、文学的可通约性和共识。没有一种文学史模式是万能的,毕竟文学的历史比任何一种简明的逻辑都要丰富和复杂。
五、“福柯”作为方法的省思
《文学史》出版之后,在国内学界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其中商榷与批评的看法值得注意。张隆溪说:“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其实变成了一个模式。例如我们看到,前不久王德威编了一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非常典型的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这本书请了很多人来写,不是一个人写的,王德威是主编,但是有很多人写。其中有些篇章是由很好的学者写的,是值得看的,但是就文学史而言,在我看来,大部分内容都不值得看。为什么?因为这些内容跟文学史没什么关系,都讲得非常零碎,可以用‘乱麻’来形容。”④张隆溪等:《世界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及其对话》,《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张隆溪的批评主要针对《文学史》内容的五花八门与文学史无关而言,认为其应有自己的审美价值,文学史书写应该关注的是重要的、经典的作品,并以文学批评的标准作出价值判断。张隆溪在主编《文学的世界史》⑤David Damrosch and Gunilla Lindberg-Wada. Literature:A World History, Hoboken, NJ : Wiley, 2022.第三卷的基础上撰写了英文版《中国文学史》⑥Zhang Longxi.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该书试图向国外展示中国文学传统的悠久和深厚,使中国文学的经典能够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叙述,而绝对不是那种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乱麻。我非常强调我写的是文学的历史,不是社会史,不是政治史。”⑦张隆溪等:《世界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及其对话》,《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他认为,《文学史》这本书的卖点是因为“哈佛”这个品牌,而不在于其本身价值,“如果由一个中国学者,譬如说像陈引驰教授,来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然后召集一批人,让大家随便写,例如写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天的市场情形如何等等,这样一本文学史,你拿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说不定不会出版,但是为什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出版?这本书的卖点就是四个字——哈佛新编。就这么回事。因为是哈佛新编,所以一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像文学史这种书,不能看见‘哈佛’两个字就觉得一定好,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本《哈佛新编文学史》并没有太大的价值。”①张隆溪等:《世界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及其对话》,《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文学史观念的争议,其背后实际上是如何界定文学、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如何讲述中国的问题。争议的交锋有利于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形成,也是学术生态自由开放的体现。
(一)文学与历史的辩证
在引述以上否定性批判的前提之下,笔者试图提出如下值得反思的问题:如何书写“文学”的“历史”。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最后一章《文学史》中提出:“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末是社会史,要末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末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②[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52页。他们提出的问题意味着文学史著述既是“文学”的历史,又是文学的“历史”。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历史即文学”,“时至今日,历史越来越被大家当作文学来阅读”。③[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如果说在黑格尔美学观念的引导下,文学史是“文学”在时间序列发展显现并与自身取得和谐的历史,那么福柯则造就了独特的文学史观念,即不再连续发展趋向和谐。④郑鹏:《话语、考古学、谱系学——福柯话语理论的迁转与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福柯被控诉正在弄死历史。⑤[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43页。那么,以“福柯”作为方法写就的《文学史》,能否经得住韦勒克提出的问题——“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文学史》以“福柯”作为方法“关注‘文学’遭遇历史时,所彰显或遮蔽、想象或记录的独特能量”⑥王德威主编:《中文版序》,《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治等译,第i页。,是否可以考掘出一堆零散的“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⑦[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第224页。,是否能够“仅凭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的材料支撑起一座历史的大厦?”⑧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页。当文学作为历史形式编纂时,“文学性”的生成似乎是以“历史性”的牺牲为代价,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就是文学,“文学史”成为了“文学”或至少是“类文学”的存在。因此,文学史就“好比一场假面舞会,文学戴上假面,频繁与人对话,不断更换舞伴,致使它嗓音变异,面目全非”⑨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正如德曼所言:“阐明文学现代性及其历史性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⑩[比]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第189页。“文学史”失去了“历史”的依托,于是“真正的文学历史,依然不见踪影”。⑪[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渺、汪捷宇译,2011年,第210页。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有的理论家们简单地否认文学有其历史。例如,克尔争辩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文学史,因为文学史的对象总是现存的,是‘永恒的’,因此根本不会有恰当的文学史。艾略特也否认一部艺术作品会成为‘过去’。……有人可能和叔本华(A.Schopenhauer)争辩,认为艺术总是达到了它自己的目标。它永远不会有所改进,也不能被取代或重复。在艺术中,我们不需要象兰克(L.Ranke)给编史工作所定的目标那样去寻找‘过去究竟怎么样’,因为我们能完全直接地在艺术中体验到事情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文学史并不是恰当的历史,因为它是关于现存的、无所不在的和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⑫参见[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54-255页。简言之,上述观点认为“文学”没有“历史”,但是如果“文学”没有“历史”,那么“文学史”又何以重构,那些非“文学”的“文学史”,是否是对这一点无奈的彰明。当然,这只是后现代理论映射的回答,不过至少从“元文学史”视角观之,可以认为“文学史”已成为“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检验装置。如果试图重构“文学史”,那么必须回答“文学”有“历史”,而这一命题的证成,则仰赖于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重新认识与解释。总之,在后现代主义思想视野中,一方面,“历史就是文学”意味着作为书写文学历史的“文学史”似乎成了同义反复,成为悖论性的书写“文学的文学”,失去了历史的依托;另一方面,当文学被认为是共时性的存在时,无所谓线性,无所谓进化,处于文本的永恒之中,“文学史”则要书写“没有历史的文学”,失去了历史本身。而以此观之,以“福柯”作为方法的《文学史》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与“没有历史的文学”,作为现代发明的“文学史”则并未被重构出来。文学与历史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王德威意欲发扬“诗史”传统,榫接“文学”与“历史”,抛弃线性叙事,转时间演进为空间并置的做法,是对文学并未“过去”而是与时代并存的强烈表征。
(二)文学史著述作为话语的博弈场域
笔者提出以上的反思,一方面是对文学与历史辩证关系的重新估量,另一方面则想指出,如果认为福柯理论是解读《文学史》的唯一主线的话,实际上有片面褊狭之嫌。《文学史》主编在年代的选取、作者的遴选、内容的主题等方面,实际上有预先充分的考虑,在碎片式的编年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主编对于线性历史线索的追踪,并非“召集一批人,让大家随便写”。可以说,《文学史》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调和、博弈、冲突的话语场域,而不能理解为某种历史观念一以贯之的结果,更不是关于某个问题的盖棺定论。
理论是女妖塞壬的歌声,充满诱惑,但也极具危险。刘禾曾经指出:“现代和当代某些批评实践常把文本当作哲学、心理学或其他理论的注脚或例证来处理。从问题的提出到术语的使用,乃至做出的结论,都往往着眼于某种理论的统一性,并受其制约。文学批评要找到新的语言,起码应对这样的批评实践做出反省。”①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15页。关于文学史书写与理论的互动,有必要进一步了解王德威的深刻反思,从而对他的历史理念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在一次访谈中,王德威坦承:“国外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客观研究,即所谓的材料部分,我们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才更多地注重与理论的互动”,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海外学者并不能挟洋自重:“对一些唯理论是尚的同事,我不太能够认同。我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你们都知道齐人有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些理论是我们学来的,并不是自己发明的,其实是‘嗟来之食’。在西方吃得快快乐乐,然后回到国内,很是骄傲,也接受了很多的掌声,这也许都无可厚非。可是,我觉得不能对理论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骄傲,回来之后这个‘理论的身段’一定要放下来”。②季进:《海外汉学:另一种声音——王德威访谈录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这些论述提醒身处书写场域中心的研究者,面对舶来的理论,既要有消化的过程,也要有清醒的辨析与转化的能力。《文学史》的历史观深受福柯理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简单套用,也不应该在理论和文本之间粗暴地强制阐释。王德威在关于该书的学术对话中说:“具体到《文学史》的编纂而言,前期我的确介入较多,不够‘民主’。为什么?因为我并不以为编纂一部符合后现代标准的解构主义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的使命,我甚至认为那不是一种正确的对待历史——至少是对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态度,而更像是虚无主义的把戏。解构主义背后的理念先行与意识形态的主导色彩可能远比它希望解构的对象还要重。我相信认真的读者可以发现,尽管没有挑明,即不像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那样一目了然,《文学史》中其实也是贯穿了几条主线的。这些主线便是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核心理解。而在这一阶段‘独裁’一些,坚持我的立场,我想还是必要的。”③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对于各种文学史观念的反思,如果得出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孰优孰劣的结论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抽离文本历史语境的悬空化解释。现代性的本质主义一元论、决定论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呈现了现代社会知识学的张力形态,不如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它之于现代性是一种反拨、互补的建设性立场。
结 语
本文关于《文学史》理论渊源的考察,有可能陷于为理论的自洽而任意剪裁的危险之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本意既非纯粹的“福柯”理论研究,也非简单地拆解《文学史》,更非有意将二者强行附会,而是试图在诸多线索与证据的牵引下,在解读的过程中参照福柯理论,进而分析该书的思想探索,从而发现、揭示《文学史》多个叙事线索的由头。《文学史》中,有些篇目的书写与论证也并非完美。笔者期望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中,能够更好地促进对这部《文学史》的探讨;在“鱼渔之喻”的文化认知中,更期望能够收获“渔”的思想启示。而获得“渔”的意义是,为突破中国文学史的重写窘境提供方法论的反思,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