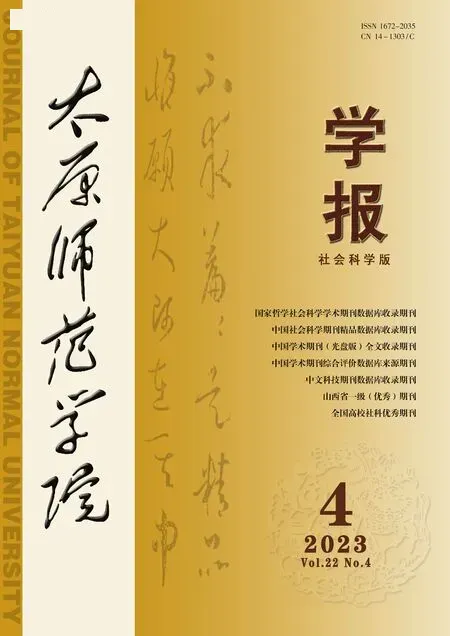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传统叙事与地域文化实践
闫咚婉
(长治学院 中文系, 山西 长治 046011)
上古帝王传说是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饶有趣味的话题。学界以往关于帝王传说中人物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从古史考辨的角度来探讨人物关系。例如顾颉刚先生早期曾指出鲧禹并非父子关系。[1]126童书业先生认为大禹与启建立关系也是后起之事,启或许原来只是一个乐神,二者建立关系是传说人物分化的结果。[2]198-220其二,在故事类型学、母题学等理论指导下的传说人物分类研究,多在对某一帝王的家庭传说单元内部相关人物作介绍时简要讨论。例如张晨霞的帝尧传说研究,在“传说叙事类型”帝尧家世传说中对相关人物进行了介绍。[3]159其三,针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帝王与帝女、帝子关系的研究。例如陈泳超先生对尧舜与娥皇、女英的研究,指出二女是作为尧舜传说中“政治试验工具”[4]315存在的形象本质。再如吴玟瑾等对丹朱、商均等古史传说中不肖子等“配角”[5]身份的研究等。整体而言,目前对帝王传说内部的人物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且对正史文本以外的地方传说内容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结合典籍文献与地方传说两种叙事资源,兼顾传统与当代两种语境,对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进行再审视。关于父与子关系的讨论,就叙事而言不涉及较深的叙事学理论探讨,仅就与父子关系相关的帝王传说叙事资源展开讨论,不涉及上古史的考辨。
一、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经典模式
在中国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表述集中于两种模式:一种是基于先秦时期族群整合需求的世系关系描述,形成了一父与多子之间血缘系统的大整合,以帝俊、炎黄等上古帝王传说为代表;另一种是为宣扬禅让制而出现的父与子之间的非和谐关系,父与子的关系暂时让渡于君主与继承者的关系,尤以古帝王尧舜禹禅让传说为代表。
(一)一父与多子:族群整合与父子关系的谱系化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最典型的模式是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世系。血缘关系本应是科学的、生理性的基因关系表述,但是在上古传说中,血缘关系的表述杂糅了空间、政治等因素。因此,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呈现出的谱系化形式浸染了复杂的时代特征、社会特征。
基于权力意识觉醒形成的空间观念是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建立的依据与早期表现形式。尽管人是自然界的高等生物,但原始人类的空间占有行为与动物界通过圈割地盘所表现的领地意识具有相似性,空间成为权力形成、牢固的依据。作为古帝王世系较早的记录文献《山海经》,其世系描述方式就表现出突出的空间叙事特征,这是父与子关系最原始的表征。例如《山海经》中的帝俊一系,其世系描述中表现的空间特征尤为集中:“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6]344、“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6]346、“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6]347、“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6]348、“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6]371。《山海经》的叙事模式隐含着空间权力的秩序性,诸如帝俊一系父与子关系呈现的“‘有 A 国’+‘某生 A’”的空间叙事模式在《山海经》中极为典型,[7]将一父与多子的谱系关系通过“一种作为权力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8]建构出来,反映了原始社会族群统一的客观发展需求以及早期的空间秩序确立行为。
《山海经》中早期帝王谱系的空间特征描述,与春秋时期以实现族群统一、巩固王权为目的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土地分封为标志的政权模式相呼应,血缘、空间、权力三者成为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系。尤其是周朝建构的以黄帝为祖先的世系,即春秋时期黄帝“共祖”的现象,充分证明了黄帝以一身统摄当时多族群的传说内容,在世系建构、政权巩固中发挥的作用。刘晓曾对春秋时期黄帝“共祖”地位的形成过程作过系统的分析,例如姬周世系对黄帝本支与旁支的整合、异性诸侯对姬周世系的融合等,[9]详细论证了当时各族群出于政治秩序考虑而进行的族源附会行为。
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较为原始的族群空间记忆相比,基于政治文明演化、空间权力进一步整合衍生的帝王世系建构不断复杂化,父与子的关系建立也更加显性。例如《国语·晋语四》中所记:
……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10]333-337
其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黄帝之子与得姓者的数字差额隐含了权力的分配机制,此十二姓或为周初姬姓政权为巩固王权建立的有选择性的血缘政治体系。通过这种体系,他们与周王朝获得了政治权力上的双赢,十二姓成为各诸侯国“身份”确立的合法标签[9]104。对于周王室进行的黄帝世系确立行为,有学者指出,“诸如此类的族源追溯方式,正是为其‘大一统’的目的而悬拟的”[11]224。基于血缘关系的父与子式的族源追溯,对族群整合、政权统一产生的积极意义为后世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那些“通过血缘借地缘发展的诸侯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血缘被稀释,造成分宗立氏的高潮……氏族林立,纷乱如麻”[12]70,形成了诸侯国纷纷借世系的窜入与确立来争夺权力、保障利益的局面,反映了彼时“世系危机”的现象。[12]70空间占有行为的强化与逐渐无序,从侧面刺激了黄帝“共祖”行为的延续。以黄帝姬姓为核心,各诸侯国通过多种手段的附会逐渐纳入到黄帝谱系中,进而谋求新环境中的正统地位。例如炎帝一族,通过与黄帝同出少典的早期族源追溯方式,最终与黄帝并称“炎黄”。
黄帝由二十五子之父到夏商周之祖,最后到华夏民族初祖的地位演进传说,是上古帝王一父与多子父子关系衍生的重要产物,为彼时政治权力的稳固、族群的统一提供了理论逻辑。先秦是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谱系化发展的重要形成期。出于大一统政治的需求,秦汉时期上古帝系被不断建构,各种文献如《世本》《五帝德》《帝系》《史记》等不断充盈着帝王谱系。在此后的王朝更迭中,尤其是志在认祖归宗、力求融合统一的少数民族,都积极通过追认黄帝或炎帝为祖先的做法,加入万世一系的政治认同活动中,充分展现了一体对多元的统摄。
(二)子不肖:禅让制与父子关系的非和谐性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谱系化与先秦时期族群统一的需求紧密契合,因谱系化叙事重在强调父与子即纵向的关系建立,忽视了横向的关系演化,缺少具体事件支撑父与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黄帝与其二十五子传说中,仅有关于少数几子的封地传说,并没有黄帝与其子之间详细的叙事活动记载。发展到战国时期,关于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事件性叙事逐渐产生。可以说,上古传说中尧舜禹之前的帝王几乎没有此类传说内容。发展到尧舜禹时期,父与子关系的非和谐性叙事典型且极其规律。这种叙事变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相匹配,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大致对应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此时部族力量发展迅速,资源与环境的变化为部族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一时期的部族形态变化预示着古中原政权力量正在向更高级的阶段演进。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之间非和谐性叙事以“子不肖”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它打破了父位子承的秩序,“丑化”了帝子的形象,并且引发了子与父之间的矛盾。客观来说,“子不肖”的人物特征是儒家推崇禅让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传说叙事中的反映。禅让制的出现是为了打破血缘政治的传承模式,目的是将父子关系让渡于君臣关系。禅让制与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长河中君主继位的两种不同形式。就禅让制而言,不论是先秦诸子学说还是今人学术研究,仅仅是对某一时段政治历史发展进程在学理上的概括。历史现实与历史记载、历史研究是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因此,从传说叙事研究这一视角来看,尧舜禹禅让情节的出现,使得上古帝王父与子传说中出现了“非和谐”的因素,起到了丰富叙事的作用。故而,在上古帝王传说叙事的讨论范畴中,我们不过分关注禅让制的本质或真假问题,仅仅关注禅让制与“子不肖”的关系。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尧舜禹“三圣传授”之说,即“尧、舜、禹先后交替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13]91。禅让制只是对其“交替担任”形式的一种制度化诠释。如果我们将禅让制的出现与“子不肖”的文献视为本文讨论传说叙事的背景,那么,不妨将禅让制作如下理解:禅让制是势力相当的政权组成的同一联盟体中产生领袖的方式[14],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事件,其中平等式联盟是其发生的社会基础[15]。也就是说,尧舜禹三者在这样的联盟中曾一度地位平等,直到大禹通过治水之功提升了地位,打破了和谐的部族联盟力量并逐渐形成、确立了世袭制。因此,尧舜禹的禅让活动尽管有不和谐的插曲,但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点从先秦诸子文献中记载的几次规模较大的上古战争都发生在炎黄时期而非尧舜禹时期可以得到印证。
“尧、舜、禹先后交替担任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先后交替无外乎两种模式:和平与战争(或者仅是局部暴乱)。儒家提倡仁政,孔孟虽然没有完全反对战争,但是对待战争之事一贯是谨慎保守的,《论语·述而》中讲“子之所慎:‘齐、战、疾’”,《孟子·离娄上》中明确指出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战国时期诸侯频繁征战的现实,儒家的仁政思想显得格格不入,法家思想一度成为最实用的学说。那么,彼时儒家推崇的尧舜禹和平禅让制就明显带有了“鼓吹”的性质,叶舒宪先生曾以陶寺遗址等出土文物为例证,指出华夏文明起源中的暴力成分,以此考证儒家禅让神话背后遮掩的血腥历史。[16]先秦时期如“舜囚尧、舜逼尧、禹逼舜”等文献记载似乎也力证了这种说法,但这些文本经常被学者视为“异说”,原因在于诸家默认了儒家禅让说的“正统性”。可见,禅让说已经成为儒家历代神话中的核心意涵。暂且不论上述文献的真伪,仅从叙事角度来说,儒家为了使禅让制这一事件显得真切而有说服力,需要极力完善传说叙事活动中人物的性格与行动。那么,禅让制和平施行的前提必须是有利于继承权力交接给外部力量的条件,即儒家大力宣扬的传位者之子“不肖”。如果说彼时的禅让制是自然而然、十分公平的权力继承模式,那么“子不肖”的程式化人物形象就是传说中毫无意义的因素。因此,只能说明禅让制在传说中的出现,必须通过“子不肖”的人物形象进一步衍生出父与子之间非和谐性的人物关系,才会使事件发展显得自然合理。
上古帝王传说中不肖子的形象众多。例如《国语·楚语》:“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10]483-484相较而言,大禹之子启则是另类,打破了叙事中“子不肖”的循环,因为彼时世袭制的建立时机已经成熟,“子不肖”在叙事中已经成为了阻碍因素。“子贤”背景下的启,成为民众归顺的一方,使得大禹禅位的伯益成为了反派。一方面是力量的悬殊,另一方面是民心所向,故《史记·夏本纪》记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17]75“帝禹之子”一语重在强调帝子继位的合法性。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之间典型的非和谐性叙事,起因是由“子不肖”形象引发的新的帝位继承关系,其不和谐根源在于外部的继承者导致的被动非和谐性。此外,尚有一种由武力冲突导致的父与子内部的本质矛盾,如黄帝与蚩尤父子间的非和谐关系。在清华大学收藏的“清华简”中,战国竹书《五纪》中记载:“黄帝又(有)子曰寺蚘(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18]此处记载黄帝与蚩尤是父子关系,虽然与传统典籍的记载不同,但也并非无稽之谈。《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中曾载田千秋上书言“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17]980,尽管太史公并未以此事入《五帝本纪》,但其或可与战国竹本《五纪》内容进行对读互证。黄帝与蚩尤的父子关系,与其他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不同在于,蚩尤叛父并且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后果,与儒家内隐的传说风格背道而驰,大胆正视了“子不肖”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古部族中新的继承者对于上一任首领血腥的取代方式。通过《五纪》记载的黄帝对“畔父”蚩尤的严厉惩戒或可推知,“舜囚尧”、尧时后稷征伐丹朱的文献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二、父与子关系中典型的功能性人物
基于上述两种传说中典型的父与子关系的形成,在传说叙事中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人物角色逐渐增多。这些人物除了在传说中承载并稳定上述父与子关系之外,很少有具体的角色刻画。叙述学的人物观理论认为,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分为“心理性人物”和“功能性人物”两种,其中“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19]51,即功能性的人物从属于行动,是为行动服务的,因此不断产生出“以事件为中心的程式化的作品”[19]69。相较于“子不肖”的父子关系,“一与多”的父子关系的建立在传说叙事中更强调人物间纵向的联系,较少关联周围群体,并引发相应的叙事活动。同时,在发展中,其与追溯真实的“祖先历史”息息相关,客观而言,在“一与多”的父子关系中,功能性人物在叙事中发挥的空间较小,乃因历史信息制约而导致叙事受限,所以本文集中讨论“子不肖”父子关系中典型的功能性人物(1)吴玟瑾等在《礼俗互动视野下古史传说中配角的留存机制——以不肖子丹朱为例》一文中将这类人物视为“配角”,并且将同类型人物称为“同类理念人物”。。
“子不肖”父子关系中典型的功能性人物围绕“不授其子而授贤”的事件展开。程式化的人物关系与形象特征为:上一任帝王(贤)—其子(不肖)—下一任帝王(贤),核心的功能性人物为“不肖子”。与“不肖子”同时存在、在作用上平行但意义截然不同的人物还有“拒位者”[20]40,或称为“逃亡者”[4]315。“任何一个角色在故事格局中都被相对地定位,它只能在这个格局中按照格局的规则运行,拒绝或者破坏这个规则就意味着失去角色和资格。故事结构中的每个角色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要完成特定的任务。”[21]41因此,“子不肖”父子关系中典型的功能性人物“不肖子”“拒位者”形象一旦被固化,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叙事使命,按照既定的角色规则完成叙事任务。“不肖子”一方面要衬托其父,即上一任帝王举贤的作为;另一方面要以自己的“无能”反衬下一任帝王之贤。而“拒位者”的出现,一方面是要加强“让位”行为的真实性,烘托上一任帝王的无私公正;另一方面是要以自己的逃避反衬继位者的“无义”。这些人物都具有双重使命。
上古帝王传说中丹朱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兼具“继位者”与“不肖子”身份的程式化角色开始形成。故而,担负同样叙事使命的舜子商均之“不肖”是必然的,因为他身上也天然携带着继位者的标签。同时,帝子商均牺牲形象的必然性,也侧面强化了禅让制的合理性。此外,为了使核心的功能性人物更具真实性或典型性,更多的量化形成的功能性人物相继出现。例如:
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22]258
舜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22]263
禹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22]276
(尊) 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椲□氏、垆□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22]250
如果说丹朱、商均真如史书所载不贤不肖,那么尧尚有其他八子(2)另一种说法为“尧有十子”,《吕氏春秋》中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的记载。、舜尚有六子可考察,何以全部否定?历代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八子”“七子”性格品行的具体描述,这样的“漏洞”显示出叙事的刻意性与目的性,但同时又很好地诠释了父与子典型关系中一父与多子的传统模式。这样的模式甚至逐渐延伸到炎黄之前更加缥缈的古帝王(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等传说中,借此反证尧舜禹时期传说的真实性。将上古众多“有天下”的远祖搬出来,构拟出诸子皆不肖转而授贤的“神话”,如此泛化的、集中的群体行为描述,更可见其“造势”端倪,恰恰透露出文本不真实的一面。
因继位者的让天下行为,使得他们也成为了与“不肖子”同类的功能性人物,例如尧舜时期出现的许由、子州支父、巢父、善卷、北人无择等。这些人物多出于《庄子》中,是一类人的个体化形象展现,究其内里,均为程式化的形象塑造。陈泳超先生指出,这些逃亡高士群体就是另一路反对尧舜禅让的队伍。[4]187艾兰女士认为,“对提供的权位,圣人们加以拒绝,这暗示了‘义’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利’”[20]42。对舜这样接受权位的人来说,就相当于接受了“利”,而这些“让王”的、真正的圣人们用逃亡的行为来反对“利”的获取,可见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旨在攻击禅让制。
由此可知,“不肖子”与“拒位者”两类人物,在不同叙事目的的支配下,呈现出相反的功能。同时,为达到强化特定人物形象的目的,尚有其他的辅助性功能人物存在,例如衍生出主角周围人群群体性的形象特征。为了凸显继位者虞舜的贤能,则产生了舜帝家庭成员群体性的负面性格特征——父顽、母嚣、弟傲,并且有“皆欲杀舜”的行为。为了成全舜帝一人的美名,尚可牺牲家庭成员整体的声誉,那么在帝尧传说中牺牲丹朱一人的声望,似乎也并不突兀。
三、父与子关系的地域文化实践——山西长子县的“丹朱文化”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长子县是丹朱传说的重要流传地,但并非唯一传承地。历代典籍中涉及的与丹朱封地有关的“丹水”“丹渊”等地名指涉多样,且历来聚讼。本文仅就长子县作为帝尧、丹朱传说重要流传地的前提作讨论(3)丹朱传说在山西的临汾、长子以及河南、山东等地均有流传。关于丹朱封于长子以及长子作为帝尧故里的地域考证已经卓有成效,以长子帝尧与丹朱传说研究为基础形成的《上党帝尧》(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收录了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太原师范学院李蹊教授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观点以及诸多地方文化精英的考证。。2017年,长子县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千年古县”称号,意在保护、传承悠久的“长子”地名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关于“长子”县名的沿革,《山西通志》中记载:“长子县,周太史辛甲所封。春秋晋长子邑。汉长子县为上党郡治。”[23]1573由此可见,长子乃周文王分封辛甲之地,历史久远。关于长子县之“长”的读音确定,与长子县是否可与尧封长子丹朱事件建立密切、清晰的关系息息相关。《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颜师古注曰:“长读曰长短之长,今俗为长幼之长,非也。”[24]1252此观点认为尧封长子之事与长子邑之间毫无关联。《今本竹书纪年》记载“……郑取屯留、尚子、涅”[25]134,言及战国时屯留、尚子等归属问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指出“尚子即长子之异名也”[26]163,且唐代陆德明在《周礼注疏·卷三十三·职方氏》中注“长子,丁丈反。长子,县名,属上党”[27]875,似乎又为长子县“长”之读音正名。当代学者李蹊认为,古人在赞叹一件事或者一种见解时的最高地位时常说“尚矣”“至矣”,故尚子当为长子。[28]2此解释力证了《水经注》所言。除去文献考辨、训诂释义外,结合长子地方的语言习惯,长子本地人皆言“长”为长幼之长,这是一种地方文化记忆的体现,是民众集体认同的文化产物。因此,综合而言,长子读长幼之长合乎情理。
唐代《十道图》载:“丹朱城,尧长子丹朱所筑。丹朱,尧之长子,因名,亦名丹朱城。”[29]81此应是最早将长子县与丹朱直接联系起来的文献。尽管唐代以前文献,如《汉书·律历志第一下》“(唐帝)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24]871、《史记正义》“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17]306等都提到了丹地——丹水、丹渊等相关地名,但是并没有言明丹地即今天的长子县域。由此可推知,至晚在唐时,今上党长子县已经与帝尧长子丹朱的叙事建立了密切关系。长子县作为尧封长子之地,流传于此的丹朱传说具有如下特点:
(一)“无尧不丹朱”
“无尧不丹朱”的叙事逻辑在于“长子丹朱传说在长子县的流传”这一研究预设,即将长子丹朱作为故事逻辑上的主人公,因为单纯从“长子”之名来说,长子显然是作为名词存在,意指丹朱。那么,当地流传的传说,我们自然会认为应以尧的大儿子丹朱叙事为主,但在长子县丹朱传说的真实流传情况却并非如此。长子县作为尧封长子之地,因帝尧、丹朱父与子之间的事迹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名。地名的意义基于帝尧与丹朱的父子关系,以及帝尧作为帝王与父的双重角色分封丹朱的事件而形成。因此,在父子关系与分封事件这两个纽带中,帝尧占居了血缘、政治伦理下“帝与父”的强势地位,所以在长子县流传的丹朱故事就呈现出“无尧不丹朱”的特征,即帝尧承担了丹朱叙事“起兴”的作用,有关丹朱的故事情节必与帝尧发生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长子县被当地民众视为尧王的出生地,即民间所说的帝尧“发迹”前的老家,这里有大量与帝尧相关的文化遗迹群;另一方面,从情感认知来说,相比于典籍记载中多有“污点”的丹朱,帝尧的品格则更加高洁。
因此,就“无尧不丹朱”这一特点,尧王封长子丹朱于长子县事件的核心,重在强调尧王与长子县的故地情缘背景,具体表现为,在长子县无论是人物传说还是遗迹传说,从数量上看,帝尧都占绝对优势,关于长子丹朱的故事可以说屈指可数。帝尧将丹朱分封于此,某种程度上是延续帝尧与长子县关系的一种代际传承方式。此外,长子地区曾有多座祭祀尧王的庙宇,例如韩坊村尧王庙、潜山尧王庙、陶唐村三圣庙等,这正与丹朱被封于此地的说法相印证。“朱子谓尧庙当立于丹朱之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30]34因此,在丹朱封地兴建尧庙祭祀帝尧,又体现出子承父地、父祀于子封地的特殊性。
(二)丹朱人设之“辩”与惑
丹朱在历代典籍中褒贬不一,对其贬低的文献占主流,这与儒家强大的叙事传统有关。那么长子县作为尧封丹朱、以丹朱得名的地域空间,在丹朱人设的问题上,有没有为丹朱进行过辩护呢?此疑问的提出,起于山西临汾尧陵出现的一通明代碑刻,名为《祀朱辩》,撰者为明代临汾知县临潼赵统,碑文言:
……夫人之情槩若是耳,朱之隐德谁复知之,诚如《书》言朱也,以其启明之才而济之以嚣讼之资,方其尧宾于天,舜避于山,以天子之子取天下名正势顺。舜非阴有以制其短长之命也,夫恶得而禁之,舜之有天下也,而朱无闻言不贤而能。如是乎,夫朱苟有天下,非如桀烈之荼毒,舜与天下必不忍弃之,夫自知其德之不如舜而阴逊之,以成舜以免生民于荼毒,其贤乎?人也远矣,故舜之有天下也,与之者尧而成之者朱也……(4)碑刻资料。该碑刻镶嵌于山西临汾尧陵献殿右侧墙壁上,嘉靖十八年岁次己亥仲秋立,青石质,碑刻规格为长115cm、宽101cm。碑文中“诚如《书》言朱也,以其启明之才而济之以嚣讼之资”,引用了《尚书》之言:“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 帝曰:‘吁!嚣讼可乎?’”
通过碑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书写者对于帝舜继位一事的态度:因丹朱明事理晓大义故自动隐退,且辅助舜称帝。尧崩之后,丹朱本可以天子之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但是他自知贤能不及舜,于是让位。碑文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假设,即让丹朱继位也未必就会像暴君一样使百姓遭难,强调了丹朱治理天下就算能力不及舜,但也未尝不可一试的客观性,侧面反衬出丹朱让舜的高洁情怀,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为丹朱辩护,替丹朱翻案”的态度。该内容与民间传说中盛行的丹朱不成器,因嫉妒舜继位而举兵反尧的故事大相径庭。但这正是碑文撰刻者“适闻子大夫辩朱可谓贤矣乎,闻之乡曲愚父老诮朱者辞殊不经,请我大夫倡此以为朱释诬,遂镌词于石”的目的。因正史记载的影响,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接受尧因丹朱不肖而禅让于舜一事,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使得为丹朱的辩护也显得意义重大。
那么在山西临汾这样一个以帝尧为主角、流传着大量丹朱不肖事迹的传说圈中,为何会出现为丹朱辩护的碑刻?一方面或与知县陕西临潼人赵统初来此地,在闻“子大夫辩朱”之贤后,闻“乡曲愚父老诮朱”的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作为新一任地方官或许别有深意。此处我们摘取一则在临汾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贬低丹朱的传说:
据说他的相貌奇丑无比,脸像人,嘴像鸟儿,又尖又长,背上长着翅膀可不会飞,有时他把嘴伸到河里,像个钓鱼的杆子,能钓上鱼来……丹朱比起尧王爷来,从天上差到地下,地下还得打个井,井里还得挖个十万八千里深的大疙窝。尧王爷坐天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子,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粗米淡饭,喝的是野菜汤,用的是土碗、土罐罐。可他的儿子丹朱,住的是高屋大厦,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大鱼大肉,而且整日游手好闲,游山玩水。(5)内部资料,详见临汾市民间故事集成编委会编《尧都故事》,1989年印,第48-50页,引用时有删减。河北省魏县有关于“丹朱夜游台”的传说,丹朱强征民夫连夜堆土垒台,建成高数十丈的圆形高台以满足自己饮酒放歌、尽情享乐的欲望。正与临汾地区传说中丹朱游山玩水的形象符合。
由此可见,临汾虽然出现了“祀朱辩”,但是民间认为丹朱不肖的传说流传仍然很广泛。临汾帝尧传说的核心在于赞颂帝尧,且这样的话语强势而独立,在临汾地区帝尧与丹朱更多体现的是两个独立的形象,并未像长子县那样过多关注“父与子”关系,并且传说中出现的帝尧与丹朱的对比,也仅是为了表明丹朱不如其父。所以,在这样的叙事环境中,贬低丹朱只会起到加强、巩固帝尧正面形象的作用。但是长子县不同,长子一名以父与子的伦理关系将帝尧与丹朱紧紧联系在一起,有父才有子,有子必有父,强调二者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可推测临汾地区出自统治阶层笔下的“祀朱辩”,或是为完善帝尧美名,恐其子玷污其父美名,旨在全面促成临汾帝尧的佳话,而非真正为丹朱辩解,从另一层面上发挥了丹朱人物的辅助功能。相较于民间的“主流”声音,客观来说,其辩解的作用微乎其微。
临汾有“丹朱辩”,那么,长子县历史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丹朱之辩?依据现存的各种版本《长子县志》中“艺文志”部分,笔者所查阅到的历代古诗文资料中,文人吟诵上党神话人物帝尧、炎帝、精卫的诗作非常丰富,但是对丹朱几乎绝口不提,仅仅提到“尧封”“封丹朱”等事件,以及“丹岭”等地理遗迹,并未提及丹朱具体的个人形象。同时,笔者比照临汾县令撰写“祀朱辩”碑刻的事件找寻,仍是无功而返。长子县至今发现的历代碑文中,多为记录帝尧个人事迹的内容,涉及丹朱的也很少,仅可从三处县志的序言、跋中发现一些端倪,可作为长子有无“丹朱辩”的参考。
其一,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版《长子县志》序中,作为前任潞安知府的陈庭学写道:“虽古典有不详焉,可也,况本有以疑传疑之法乎?且如漳水之有清有浊,吾诚不知何以云也;丹朱之为城为岭,吾诚不知何以解也。然而,极水之深不如升斗之活于民也,穷山之高不如尺寸之补于事也。不然,莫幻于精卫之填海。是可以为真乎?”[29]1529
其二,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版《长子县志》跋中,时为廉山书院山长的冯文止写道:“典籍散佚,经传残缺,讆言谚说,皆得起而乱之。虽极博通之士,无从考而原焉。信之则愚,削之则妄,苟求有据而传闻又异辞矣。《虞书》曰:‘允子朱启明’。孟子曰:‘丹朱之不肖’。或曰:‘尧长子监明早死,其嗣封于刘朱。’ 或曰:‘长子,尧伯明封国。’明之后,妘姓。以孟子则朱其名也。以二说则明其名也,朱其国也……自史遇不敢更定,诸说并存,诚不知其孰是也?”[29]1530-1531
其三,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版《长子县志》序中,时任礼部侍郎、山西学使的陈嵩庆言:“按《志》:‘长子县之得名,相传为丹朱封地。’否德弗嗣说本无稽……民俗俭勤,犹有陶唐氏之遗意焉。”[29]1531
综合上述三种说法,前两者重在“疑”,无论是以精卫填海莫幻之说类比丹朱筑城之事,还是“吾诚不知何以解”“传闻异辞”“不知孰是”的困惑,皆表达出对丹朱之说的怀疑与不屑,或者说不去正视被正史贬低而又闻名于地方的这一矛盾性人物。嘉庆年间县志序言,对于《尚书》所记内容持“否德弗嗣说本无稽”的观点,似乎有了丹朱之辩的意味,但是更多的是以帝尧遗风反证长子县民风淳朴,旨在维护长子一县风俗,并非为丹朱个体辩护。尽管以三则县志内容无法断定长子县有无为丹朱辩护一事,但可窥见时人对丹朱事迹的大致态度,即其惑大于辩。
可以说,在长子地区,虽然依托尧封长子的传说极力宣扬长子县得名由来,并且长子以尧之栖息地而久负盛名,但是并未发现较多的为典籍中丹朱负面形象正名的有利文献。
(三)丹朱之变
明代奇书《千百年眼》中“帝尧善爱其子”一条言:“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窃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其所以贻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为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之于子,亦若是则已矣。”[31]3与传统儒家传说不同,该书喜从新颖视角立论,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帝尧让位之举,其爱子之意胜过让天下大义,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就宣扬长子文化的长子县来说,帝尧正是出于对傲虐子丹朱的长远规划,希望丹朱得以安宁,所以将其分封在自己的老家。此举使得帝尧君与父的角色都得以圆满。虽然在长子县难寻有利的“丹朱之辩”,但仍可见“丹朱之变”,并产生出继“子不肖”之后父与子关系的转变。
在长子地区,关于“子”丹朱的人物传说中极少有讲述其不肖的故事情节,并且发生了丹朱的人设之变。长子县并没有刻意规避文献记载中丹朱不肖的品行,因为在强势的儒家主流文献影响下,长子县域的“辩解”似乎于事无补。欲以长子丹朱为长子县正名,就需要“生变”。“生变”即意味着对典籍中丹朱较为负面的人物形象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来自民间的叙事策略十分明智,通过在地化的丹朱故事讲述,合理地将丹朱的形象予以“纠正”:其一,通过人物的改邪归正行为延续史籍中的话语,通过“接着讲”这一方式使原有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在新的故事环境、在后续的叙事发展中自然迎来转机,达到扭转丹朱固有形象的目的;其二,通过长子的地域风俗固化并宣扬当地民众对丹朱的情感偏爱,重塑地域文化精神。
据当地传说,尧知丹朱任性难以继承大统,故考察虞舜才能以禅让。“看到尧王让贤于舜,对朱的震动很大……于是虚心向舜请教,处处学习尧舜的高尚品德和治国方法”[28]164,并且在听说尧王故乡受灾时,“为了避嫌,主动交出兵权,并且请求回到故乡丹地重建家园”[28]164。同时,在丹朱的带领下,“人们安居乐业,无不称颂丹朱的政绩”[28]164。可见,在长子县的丹朱传说中,丹朱不仅受尧舜启发改邪归正,同时颇有政绩,似乎“落实”了临汾尧庙《祀朱辩》中丹朱积极的行为。不仅如此,丹朱与帝尧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丹朱十分怀念父亲尧王,常常站在丹河边的土岭上向西眺望(意指眺望尧都临汾),并且临死前叮嘱人们把他埋在这里,后来此岭被称为丹朱岭。”[28]164丹朱改邪归正、造福于民、父子相敬成为了长子丹朱传说的核心情节。在另一则传说“丹城”中,尧王在见到儿子筑造丹朱城的成果后喜泪盈眶,倍感欣慰,并且放心地将丹地交给儿子治理,[28]156传说中俨然一幅慈父爱子的画面。
长子县当代文人创作的诗歌《北高庙·熨斗台》中云:“帝子初封到此来,正遭大难万民衰。淘淘洪水塌天祸,逼出城池熨斗台。丹朱筑起盛民城,黎庶欢歌唱大功。胜迹尧封天下最,春秋几度报繁荣。”[29]1468其中“逼出城池”一句,似乎在点明帝子丹朱本不肖,封于长子后才改头换面被尧“逼出”盛大功绩之事。对于长子县的地标建筑熨斗台,俗传即为丹朱建造。乾隆十五年(1750)《重修熨斗台庙碑记》(6)此碑文中出现的丹朱筑造熨斗台一事,是长子地方碑刻中较为罕见提及的丹朱正面事迹。中记载:“相传尧胤子就封兹土,筑熨斗台,即祀神农氏于上。”[32]538此即言丹朱筑造熨斗台祭祀神农之事,亦可见丹朱并非顽劣不肖之徒,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丹朱因在上党感神农事功之伟,故筑台以纪念,后此台被帝尧封为“天下第一景”,足可见尧对丹朱行为的认可。
宋代《路史·后纪十一》中记载:“(丹朱)骜狠媢克,兄弟为阋。嚣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使出就丹。”[33]187该文本讲述了帝尧为使丹朱改变发明围棋的故事,已经出现了“丹朱之变”的情节。民间传说与典籍文献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互动,一方面民间传说的讲述需要借鉴典籍文献的权威为己说验证,另一方面典籍文献又需从民间传说中取材,并以文字形式将民间传说保存流传。因此,上述长子县关于丹朱“改邪归正”的传说,并非单纯出于地域情感的“维护”之举。丹朱之变与帝尧的教导密切相关,无形中又一次展现出丹朱对帝尧人物塑造的辅助功能。
此外,长子县以家族长子的独特身份为尧之长子丹朱正名,强调了长子正面形象与长子县得名的关系。在长子当地有“兄弟分居长子住堂房” 的说法,即老百姓在分家的时候长子优先居住阳光充足的堂房。据说这是尧王父子流传下来的,以此来象征丹朱坐镇长子正堂的权威,而长子辈辈相传也说明了帝尧和丹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28]190此外,“长子不出门”的习俗也源于尧王父子,即家族中的长子必须留在家乡守住家业。刘毓庆先生在调查中发现,在长子以及周围地区的县市,凡是名字叫“守业”“守家”“继祖”的,肯定是老大。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了长子守家的民俗。《通志·氏族略四》中有“尧氏,帝尧之后,支孙以为氏,望出河间、上党”[34]128,也可证明长子县域周围帝尧后裔的分布。“长子不出门”的民间习俗,一方面解释了丹朱缘何被分封于长子,另一方面以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传承了陶唐遗风。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父权制封建家庭模式,长子在家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广东省三水市曾有记载称在明代“律有长子不出门”(7)内部资料,详见1982年政协三水县委员会文史组、三水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合编的《三水文史》第169页。,青海的土家族家庭组织结构中也有“长子不出门”的习俗[35]206,著名山西籍作家马烽在其作品《忆童年》中也提到了山西孝义的乡俗“长子不出门”,可见该习俗在中国多地都有传承,但长子县的习俗似乎因尧封长子之事具有了生动的故事性与可释性。
上述长子县为丹朱正名的传说文本,严格来说仅是长子地区当代传承的民间传说,且传说的讲述主体多为地方文化精英,普通民众讲述的丹朱民间传说资源较为匮乏。笔者在长子县陶唐村、韩坊村、丹朱岭等地调查时,受访者中能够讲出丹朱传说的仅是诸如陶唐村村支书、丹朱岭退休教师等这样“有文化”的精英群体,普通民众对这样一段故事多数处于“失语和失忆”状态,这种当代丹朱传说的传承与改写现状,更值得我们思考。作为长子县“丹朱之变”的主要推手,地方文化精英在丹朱“文化重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说讲述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具有对文化敏锐的感知力、专业的书写力和传承的主动性,比普通民众更能及时地洞察到时代对地方传说重塑的需求。尽管这样一种精英主导或引领、民众追从的重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文化精英群体对地方知识“垄断”的现象,但是放置于民间传说客观流变的时代背景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传说自身演变规律在实践中引发的创造性发展。客观而言,“丹朱之变”对于重塑长子县地域文化风貌、传承陶唐遗风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仅凭一腔地域文化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史料文献、民俗资源去支撑、印证,并且最终形成“精英之说”与“民众之说”互动结合的良性局面。
此外,对长子县丹朱文化的整体传承现状,我们同样需要理性正视。自2022年5月起施行的《地名管理条例》明确指出,该条例的制定是“为了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国际交往的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长子县作为千年古县,借尧封长子事件而扬名,但是从目前长子县的丹朱文化传承现状来看,仅强调了地名“长子”之来历,并没有深入地结合地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对长子文化、丹朱文化进行系统挖掘。虽然在长子县不乏依托丹朱之名进行的地名文化资源运用案例(8)例如长子县城中的学校、街道、商铺、小区、公司等命名,“丹朱一中”“丹朱西街”“丹朱粮行”“丹福饭店”“丹朱花苑”“晋丹嘉园”“丹旭商贸”“丹康公司”等新兴的空间名称,与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村落名,如“尧神沟村”“尧长村”“西尧村”“尧山村”“尧科村”等,在新与旧的文化交错中相辉映,足见当地丰富的历史地名文化。,但是如何跳脱出表面的发展而深入内里弘扬长子文化,如何留住“陶唐遗风”,如何与临汾帝尧文化形成互补互促的共生环境,如何将地名文化资源真正运用于地域文化资源的发展中,是摆在长子县丹朱文化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长子县帝尧与丹朱父与子关系的展现,以“一与多”父子关系中尧王九子的长子地位为基础,进一步衍生出逐渐被修正的“子不肖”关系,兼具了两种典型父与子关系的地方文化诠释。与长子县的丹朱之变类同,在河南商丘虞城,即舜子商均的封地,也有着类似的不鸣之平。对于丹朱与商均的当代正名,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古籍记载是否真实科学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在地域文化自省的敦促下为当地文化发展寻求新的契机。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建立新的生存秩序,传统的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重在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而“求变”的地方传说讲述中父与子关系更加注重满足地方民众的审美需求与新的时代语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说故事人物与情节的发展走向。为丹朱正名传说文本的出现,正是在当代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乡土记忆被唤醒,地方文化荣辱感急剧增强,乡村开始自觉地从自身寻找内生性动力。在这样一种传说改写中,无论是帝尧作为父对于子丹朱的计深远,还是子丹朱对于父帝尧的尊崇,都透露出长子县对传统家庭美德文化的弘扬,这是一场因长子县对地名文化资源的重视以及长子人民自觉、自主的“趋善向上”而引发的“丹朱之变”。这种由内部文化重塑与自省引发的道德传承,一种寻根式的情感回归,更容易让当地民众接受并且践行。当地域情感成为传说叙事的前提,最终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自然会符合地方民众积极的心理期待。与典型的“一与多”“子不肖”父子关系的建构类同,其背后都夹杂着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动机,并且在时代的客观需求中不断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