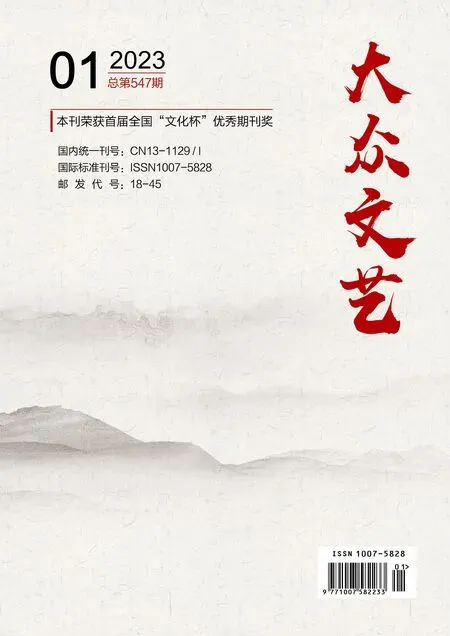论《刀锋》中拉里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史红利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00)
《刀锋》是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晚期最知名的小说。他自1915年发表代表作《人性的枷锁》,当时已活跃于英美文坛三十余年,以许多具有异国风采的短篇故事与脍炙人口的剧作闻名于英语世界。“刀锋”一词出自印度教圣典《迦托·奥义书》:“悟道之途艰辛,如同跨越刀锋,越过刀锋实属不易,因而智者常言救赎之道艰辛”[1]。毛姆自己也从不讳言他小说中的人物是从真实生活取材的,《刀锋》可以说是一幅两次大战之间的现实主义画卷。细读《刀锋》可以发现,这本长篇小说倾注了毛姆晚年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伦理思考。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毛姆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月亮与六便士》《面纱》《人性的枷锁》和其短篇小说上,对《刀锋》的先行研究相对较少。总的来看,对《刀锋》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主人公拉里的精神危机及其自我救赎和疗愈、毛姆作品与东方宗教(尤其是印度宗教)的对话、《刀锋》独特的写作手法和技巧和《刀锋》中的女性形象等等。但鲜少有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对《刀锋》进行解读和评析。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主张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其立场和最终目的是发现文学的伦理价值。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鉴,《刀锋》中关键人物拉里在小说特定伦理环境下产生的伦理困惑及其作出的不同伦理选择,为探求毛姆笔下的伦理机制与伦理诉求、挖掘《刀锋》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拉里面临的伦理困境及成因
伦理困境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术语之一,是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①[2]。并且,一般来说“伦理两难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之一。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2]。《刀锋》中几个主要人物,包括拉里、伊莎贝尔、索菲和艾略特等等,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伦理困境。进一步探讨这些伦理困境的成因则需要回归当时的伦理环境。聂珍钊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到属于它的伦理环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2]。毛姆在《刀锋》中刻画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看似经常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拉里”[3]尤为让人印象深刻。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拉里作为《刀锋》的主人公,一直面临着某种伦理困境。
毛姆作为一战的亲历者,对战争的残酷及其带来的创伤有着深刻的感悟。晚年的毛姆对战争、对人性、对整个西方文明都加以了深刻的反思,并诉诸笔端,写成了《刀锋》这部长篇小说。毛姆通过对拉里这一人物的刻画巧妙地在《刀锋》中展现了创伤人物的心理困惑,以表达自己对“人性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4]。拉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维持世俗生活和进行精神探索的伦理困境。现代化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战争带来的痛苦、悲伤、无助也引发了“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体验”[4]。经历一战后,拉里拒绝了马图林先生提供的稳定高薪的工作、丢下了未婚妻,一心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邪恶,人生的终极意义又是为何。拉里对伊莎贝尔是这样解释的:“你知道,我有个看法,觉得我这一生还可以做许多事情,这比卖股票有意义得多”②[5]。在拉里眼中,追逐名利的世俗生活是一种枷锁,一种精神的枷锁,人生的意义应该在于不懈的精神追求和满足。后来,拉里又对未婚妻伊莎贝尔坦白:“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存在着邪恶,我想要知道人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人死后一切就没有了”。可以说,维持世俗生活和进行精神探索的伦理困境始终贯穿于这部长篇小说看似混乱的叙事主线,同时也成为主人公拉里生存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回归《刀锋》的伦理环境进一步探讨拉里面临的伦理困境的成因,可以发现其实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导致了这种伦理两难。一方面,拉里在一战中目睹爱尔兰好友牺牲的个人经历促进了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他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又到底意义何在,人生是否就是一出盲目的、糊里糊涂的、由命运造就的悲剧?”。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关乎人生终极意义的发问首先揭示了主人公拉里内在自我的精神觉醒。拉里对人类生存状态及意义的终极思考引发了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他在此刻意识到了人生归于荒诞和虚无的可能性,这与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谋而合。这种伦理困境同时又作为一种催化剂,裹挟着主人公拉里不断进行自我和精神的探求,从而不断成长,最终走向洒脱和自由。另一方面,毛姆笔下的《刀锋》所处的时期,也就是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经济迅速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传统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靡一时。这一点毛姆在书中多次提及,在刻画马图林一家的富有时更是大肆渲染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格雷才二十五岁,每年已经能进账五万美元,而且这只是开始。美国真是个遍地财富的国家。这不是短期利益,而是一个伟大国家蓬勃兴起的必然势头”。一战后美国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使得拥有一份稳定且高薪的工作成为评判一个青年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拉里的好友格雷要拜托父亲给拉里安排一份好工作,而伊莎贝尔迫切地希望拉里接受的原因。然而,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会促使拉里更加关注自我,开始思索人生。这就使得拉里一开始处于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的伦理两难之中。
二、拉里的伦理选择及伦理教诲
伦理选择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聂珍钊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在作出第一次生物性选择即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还经历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人是通过伦理选择才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伦理选择才能把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而“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毛姆笔下的拉里在面临上述伦理困境时作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
毛姆在《刀锋》中创造了一个近似乌托邦式的人物——拉里。小说中拉里身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此时的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正处于一个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内实用主义盛行一时,金钱至上蔚然成风。而拉里在面对物质诱惑和精神追求的伦理两难时一直执着于对精神的探索和追寻。《刀锋》中其他人物也为拉里的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提供了有力参照。伊莎贝尔虽然爱着拉里,却最终出于拉里的游手好闲而和他解除婚约,嫁给了多金的格雷,从此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格雷破产后,伊莎贝尔又来到巴黎投奔其舅父艾略特,继续这种物质的享受;书中的艾略特更是一个贪慕虚荣、趋炎附势的势利鬼;作者本人扮演的“我”更是坦陈对金钱的追捧——“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里对外在物质的轻视和对内在精神的不懈追求。拉里一直试图在对精神的探求中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基于此,更有学者认为《刀锋》是“毛姆竭力探索灵魂(Atman)的产物,是关于神秘思想的论文”[6]。值得注意的是,拉里的精神探求所面临的伦理选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拉里刚经历过一战的创伤,面对物质主义带来的冲击,拉里选择沉入知识的海洋,希望能从知识中找到人生的答案。这一时期,他主要求助于深奥的心理学和哲学著作,后来逐渐扩展到所有书籍和知识,包括各种语言。小说前半部分有这样一个情节:拉里和伊莎贝尔等人在酒吧度过一夜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选择回去补觉,而是早早地到阅览室,渴望在书籍中解答内心的迷惘,寻求人生的答案。毛姆是这样描述在阅览室的拉里的:“我看了看,原来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部名著,在心理学史上很重要,而且书写得极其流畅……我绝没有想到他手里会有这样一本书”。而拉里自述:“我的知识太浅了”。毛姆笔下的拉里从小就是个藏书家,在伊莎贝尔和其他孩子去参加聚会寻欢作乐的时候,拉里和索菲则常常在家里读诗。在拉里看来,书籍是几代人智慧和知识的结晶,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巨大创伤后,拉里的第一选择是转向书籍,而书籍也确实是他的一剂良药,尽管没有彻底解决他面临的精神困境,这些书籍也深化了他对那些关乎人生的哲学问题的思考。遗憾的是,哲学、文学和艺术都无法最终解决他心中对人类生存的困惑,更无法满足他对精神和灵魂的探索。
拉里在伊莎贝尔决定和格雷结婚后,决定从书籍中解放出来,去法国北部的一个煤矿从事体力劳动,这是拉里伦理选择的第二个阶段。拉里是这样解释他的这一行为的:“我认为从事几个月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这会使我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静下来”。可见,在拉里眼中,从事体力劳动和之前阅读书籍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进行精神的探索,都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满足。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然而拉里的确在这场体力劳动中收获颇丰。他在法国煤矿的这一段生活不仅让他以一种国际视角更深切地体验和见证了这个世界,而且遇到了来自形形色色的来自不同阶级的独特个体,并意识到生命对每个人都是苦难重重。采矿时,他和科斯蒂——一个被驱逐出祖国的波兰人同住一个房间。科斯蒂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准备隐瞒自己的学识;他博览群书,但总是对知识嗤之以鼻;他身上总是笼罩着某种神秘色彩。这个波兰人给拉里带来了很大的精神震撼,他在激发拉里对一系列宗教问题的好奇心的同时,也深化了他对宗教本身意义的认识,从而极大促进了拉里的精神成长。与第一阶段类似,这一转向同样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拉里的伦理困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一转向促成了拉里下一阶段的精神追寻。
在经历农场事故后,拉里前往德国波恩,并由此开始了他以宗教为名的第三段精神探索:“他是在寻求一种哲学,也可能是一种宗教,一种可以使他身心都获得安宁的人生准则”。拉里是一位不断被罪恶问题困扰的新教徒。然而德国当地的神父却告诉拉里:“你与信仰之间的距离不会比一张香烟纸的厚度大”。这个时候拉里面临的伦理困境更像是一种信仰危机。拉里对基督教教义仍有怀疑,他不明白为什么无所不能的上帝要创造这样一个不完美、散布着邪恶的世界。此后,他先后前往西班牙和塞尔维亚,并最终在东方印度宗教里找到了答案,寻得了内心的平和。值得一提的是,拉里并没有转向传统的宗教教条,而是一直在寻找真正能为心灵提供指导、重视个体心灵体验的宗教。拉里作为毛姆笔下的人物,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拉里面临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的伦理困境作出了他自己的伦理选择,并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心灵上恒定的平和。之后,拉里更是毅然决然地把自己仅有的财产分给了亲友,回到纽约当起了出租车司机。对拉里来说,工作只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工具,过多的财产只会成为精神的枷锁,成为沉溺物质享受的诱惑,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探索。
拉里作出的伦理选择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人的精神和灵魂获得拯救的三个重要条件——知、行和信仰。这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甚至现代社会无疑是一种映射和讽刺。20世纪上半叶是欧洲文明大动荡的时期,一方面,从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后,欧洲社会物欲横流;另一方面,战争的惨无人道也迫使欧洲人“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与福利社会的美梦中醒来”[7],重新审视西方文明。最初的拉里在经历一战的残酷后也不免感到困顿和迷惘,但他没有放纵自己沉溺于当时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而是试图为自己、也为所有人的精神荒原寻找出路和生机。毛姆笔下的拉里对外在物质的轻视和对内在精神的重视一方面契合了一战带来人心灵上的迷惘与失落的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精神危机敲响了警钟。幸福并不取决于物质,对精神世界的忽视终将导致自我毁灭,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生活的富足才能带来人生真正的满足感。可以说,拉里在那个时代的伦理困境下作出的伦理选择具有一定的伦理教诲,能够激发当今时代批判性和启发性的精神探寻。
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探求毛姆长篇小说《刀锋》中关键人物拉里在那个时代下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作出的伦理选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借鉴。毛姆的一生处于一个“西方文明的弊病显露无遗、精神世界荒芜和信仰失落的时代”[7]。他笔下的青年主人公拉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善恶的包容无形中敦促了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为缓解现代精神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只有通过知识和实践不断完善自己,坚定自己的信仰,填补精神的空虚,才不会在挫折或困难中迷失自我,走向邪恶和堕落,甚至自我毁灭。诚然,聚焦于主人公拉里一个角色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作出的伦理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刀锋》中伊莎贝尔、索菲和艾略特等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也值得探讨,届时也会有一个对比的视角,对这部作品伦理价值的解读也会更加全面。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刀锋》,探求毛姆笔下的伦理机制与伦理诉求,挖掘其文本背后蕴藏的伦理价值,为深入解读这部经典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应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提供借鉴和参考。
注释:
①后文中出自聂珍钊学者的引文出处同此,不再另外标注。
②后文中出自毛姆《刀锋》原文的引用皆为此出处,不再另外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