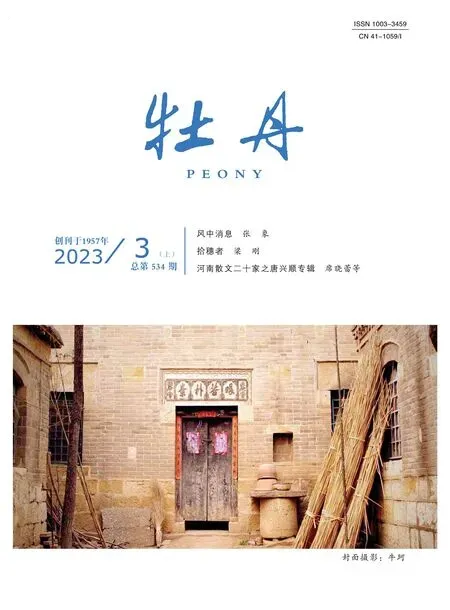黄金之吻
唐荣尧
一把攥着光明的手,掀开罩在城市上空的帘布,随着一束束光破窗而入,千万家平房、楼房的玻璃窗亮堂了起来。办公室的同事尤其女同事,像一支支绷紧在弦上的箭向门口射去。我等好大一会儿,才见他们带着一脸的幸福感回来,就像沙漠里渴久了的行者,足足地喝了一肚子水。这样的一幕,在我工作的那个城市时,老是被复制着,时间久了,我才知道答案:这座城市像个怀着心事的老妇,常年阴着脸,太阳一出来,同事们着急回家取出被褥要晒。阳光,在那座城市如此金贵,狗看到天上出太阳,都会朝天狂吠。
我写的这个地方是成都。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我在成都的一家报社工作。夏天,同事们在出太阳时飞奔回家晒被褥衣服;冬天,同事们纷纷向领导请年假,几天后归来,脸上像一个个即将成熟的苹果被放进秋天的时光之缸里浸泡足了似的:他们坐着绿皮火车,去川南的攀枝花晒太阳去了!
攀枝花,以一朵花命名的城市。第一次听见这个城市的名字,让我展开想象:那里该有多大的一朵花,绽放出的魅力,像甩向成都的一个个鱼钩,让天府之城的人,请假、买票,挤上一列列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穿山越岭地在蜀地中熬过20 多个小时,竟然就是为了去700公里外的小城晒太阳。
有时候,免费的东西更珍贵,比如空气、真情、信任和阳光。没想到,攀枝花的太阳,却需要花费时间、金钱才能去享用。后来,我虽然离开了成都,但同事冬天去攀枝花晒太阳的事,种子般落在了脑海里,我一直纳闷:那些掏钱去晒太阳的人,坐或车、越群山、穿林地去攀枝花,他们究竟在攀枝花的哪片花瓣上和阳光对话?
一
“米易”,这个词汇进入大脑时,我立即将这个地方理解成“易米”的倒装,想象中那个地方一定盛产米,吸引周围各地的人赶集似的前往那里,以物换米,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衢勾连、四通八达的陆地码头。然而,如果选择乘坐飞机前往这个攀枝花市下属的小县,也得在攀枝花或西昌机场落降,米易和这两个机场之间,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如果选择乘坐火车,只有那条有40 年路龄、560 多公里的成昆铁路可供选择,前往米易的火车,三天才有一趟,隧洞有近400 个,火车钻进一个个黑色暗道,让你能让足足感受到蜀道之难。
米易,是成昆铁路上124 座车站中的一个。
走近米易,时间之手伸过来,矫正着我对一个地名的望文断义:这里并不盛产米,它有个叫“迷旸”的乳名,直白点说就是迷水之阳,是指太阳照在迷水之北的地方,迷水就是金沙江。也就说,米易得名于它是金沙江北边的一片阳光灿烂的地方。
古人对一个地方的取名是有讲究的,有的蕴含着哲理,有的荡漾着诗意,有的寄托着良愿。很多古老而有文化内涵的地名,走向现代语境且被简化的过程,就是丢失其文化底蕴与浪漫气息的过程。
旸,本意是指旭日初升,引申义为晴天。迷旸,就是一个让阳光迷恋的地方。了解了迷旸的地名渊源,我的脑海里立即涌出了一个带着太阳迁徙的人,他从《史记》中走出,带领一群追随者,身披阳光,像一寸一寸阳光积累的岛屿,一步一步地从黄河流域移到金沙江边。
我们总习惯忽略光环遮蔽下的人与事,尤其对那些历史人物。高中时读《史记》,看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叙述,觉得三皇五帝时期的中国历史,就是三皇五帝这八个主角书写的。后人关注最多的还是三皇,甚至连黄帝的儿子昌意都懒得去留意。《史记》简单地告诉我:昌意被分配到若水,娶了蜀山的女子昌仆,生下了五帝中的颛顼,司马迁给颛顼也只是给了一个模糊的蜀地血统。
四川是一片诗意之地,地处川南的米易人,嫌想象中一寸一寸由北至南移动的颛顼速度太慢,干脆让颛顼坐在想象的翅膀上,在阳光下连个模糊的背影都没留下,从4000 多年时光的隧道中,蹦地一下从中原直接到了川滇交界处,落地于雅砻江和安宁河之间的山地间。
历史往往很功利,让后人记住的多是成功者。颛顼继承帝位后,引得炎帝后裔共工的不满,共工联合其他天神反对颛顼。共工的结局是在反抗失败后,带着绝望朝不周山一头撞去,导致天穹失去撑持而向下倾斜,天与地分开了。神话总是美丽而浪漫,这样一个举动,竟引得后人无比赞赏,共工被供奉为水神,他的儿子后土也被人们奉为土地神。
三十多年前,我看过《史记》后,一个少年的好奇,像一道辐射里程有限的老雷达,不停在书中扫来扫去,终未穿透历史的迷雾,而探究颛顼和共工的目光,像一束瘦小的手电筒光,在司马迁不知所终的记述中消失。
在米易,看到“中国颛顼文化之乡”的宣传招牌时,我内心里涌出了阵阵排斥的浪潮:先入为主地认定,这是当地为了迎合旅游时代而杜撰的一篇蹩脚的文章。
按照19世纪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领域第一个最大的学派——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的说法,太阳神是人类最早塑造的神,人类最早的崇拜是太阳神崇拜。
中国百姓的神位里,日神是谁?共工怒触不周山后,将天和地分开了;颛顼称帝后,甘愿放弃神位,成为三皇五帝中第一个为人的,这不仅将人和人分开,也代表着日神的消失,让后来的中国人仰视白昼天空时的眼光,逐渐转向商周以后兴起的天神、地神甚至鬼神系统的信仰中了。
这不仅是日神的消失,也是标明崇拜太阳和光明的“华族”的消失。
米易人把颛顼“请”到南方,重新祭起了中国的日神。
二
米易,连接滇川的万山崇岭中的几条山沟串起的骨架,雅砻江和安宁河两条银腰带束围着的地方,这隔着4000 多年的时光安置日神的牌坊。傍晚,我和县文联主席李雅斌在安宁河边散步,他指着路边那些有关颛顼传说的石碑,给我阐释“中国颛顼文化之乡”。
我像个知道答案却故意惹老师生气的学生:“这不都是些传说么?没史料和事实支撑,反而让你们像一位篡位后不合法的皇帝给自己加冕!”
他着急了:“怎么不合法,中国颛顼文化之乡是我们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的。”
我笑了笑,继续惹他:“那你说说,4000多年前的交通条件,颛顼怎么从中原到达这里的?有具体路线吗?即便是颛顼带着他的追随者飞到这里,也该有一座可供降落的机场吧。”
其实,我的内心里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颛顼在哪里出生不重要,颛顼怎么到这里来的不重要——他带着跟随者,沿着费孝通说的“藏羌彝大走廊”,还是法国学者石泰安说的“甘川青藏走廊”也不重要。那时的交通条件,他们即便没遇到途经地区部落的拦截或袭击,即便是天天赶路,走到得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只能想象,颛顼是飞过来的:被米易人唱着混合有汉、彝、傈僳等民族的迎神曲,敬献着从落差3447 米到980 米的山地上生产的五谷和水果,从2000 多年前的《史记》里,把颛顼恭请到了米易!他们从遥远的北方、从神话里、从国人记忆的死角中,请来了一尊中国的日神,复活了中国人关于日神的记忆。
听到我将颛顼奉为中国日神时,李雅斌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我明白他的惊讶既包含着一种期待,又有着一种替米易受宠若惊的心理。按照古人的说法,羲和、炎帝、神农、日主、东王公和太阳星君才是中国的日神,颛顼怎么能算作日神呢?
我继续替颛顼辩护,也李雅斌揭开谜底:我们现在以正月初一日作为一年节气的计算起点,是从颛顼而来的,这种历法被秦朝统一六国后,向全国推行,历法的名字就叫《颛顼历》,这种历法延续到汉代,成了中国历法的“正统”。
中国是个农耕大国,几千年来一直重视历法。每一部历法的研制,能离得开太阳吗?颛顼将造反的共工赶到山穷水尽时,后者一怒触山,导致天地分开,河山变形,并被后人奉为水神,而颛顼却自觉地从神的位置上走到人间,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大谦虚。颛顼带人耕种田地,开启了农耕生活;颛顼确定婚嫁制度,稳固了男女关系,开启了中国人的婚姻模式。
和印度、埃及、希腊和南美的印加文化一样,中国也是太阳神最早崇拜之地,其他文化圈内的太阳崇拜的延续性怎样,我无法知道,但在中国却有着一个奇特现象:如果太阳是一粒种子,它起初是被刻在石头上的。岩画的创作者,把太阳崇拜留在石头上,在农耕时代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古代的彩陶上,太阳神像变成了泥和水合制出的日用品,最终被埋在了地下,即便有了后来的考古发掘,也只是从地下走进冰凉的博物馆里;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古人将太阳铸造在青铜树上,或许希望它能开花;也有些地方,会保留一点太阳祭祀的内容,但让太多表演遮盖了原本的底色与光芒。这些,都无法让太阳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
米易人隔空取物般地将颛顼迎接到阳光迷恋之地,算是给日神重新安了个新家,是对日神崇拜给予一次新的回归,将太阳的种子播在了城乡的角落、生活的日常和细节中。
米易县有五个乡,其中彝族乡就有三个。彝族人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十月太阳历。这种历法指引出了离太阳最近的生活:蜻蜓的翅膀和雄鹰的鸣叫是金黄的,玉米的额骨和麦粒的舞蹈是金黄的,连“彝人制造”在《看见了》歌词里也唱道:“看见那红红太阳温暖着大地,看见那闪烁星星点缀着夜色。”米易县有一个傈僳族乡,傈僳人有“追赶太阳的民族”之称,他们才是真正的太阳粉丝:衣帽上绣着太阳的图案;太阳落山后会燃起熊熊的大火并围火而舞;为亡者送葬的人中,点着火把的人仅排在撒买路钱的后面,寓意为亡者点起阳光般的光明,送其回归太阳的怀抱;傈僳死者的坟墓上也刻着太阳图案。
在新山傈僳族乡的傈僳族博物馆里,我看到这个民族的迁徙之路,其实就是一条追寻太阳的路,他们目前定居在半山上,在云端保持着和太阳对话的姿态。
我有幸见到一次傈僳人欢迎嘉宾的仪式,男性村民吹奏着涂抹了一层层太阳色的葫芦笙,发出迎宾时的真诚;常年在日光下劳作,男人的脸上仿佛戴上了被太阳锻造的青铜面具,傈僳族姑娘头饰上的黄金线条,仿佛太阳笑起来露出的小褶皱。
在傈僳族人集中居住的撒里海,看着对面山坡上高处的核桃林,村民告诉我,核桃已经下树,剥去绿色的外衣,亮出黄金铠甲般的硬壳,这是米易县境内生长海拔最高的植物,也是最接近太阳的植物;寨子四周,是金黄的梯田,北方的梯田因为干旱缺水而种点耐旱的糜子、谷子、荞麦之类的小杂粮,体现出了北方农民们对环境的无奈和惋惜,而傈僳族的梯田里装的却是金黄的水稻和喜悦。这个民族呀,把水果栽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把梯田修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把庄稼种到了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把对生命的赞歌唱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约会总有着其私密性,这导致人类借助月光、星空来为这种私密性披上一件美丽而神秘的外衣,让约会成了两个人的夜晚狂欢。然而,傈僳族农历三月十二至十八的“约德节”,这是男女青年约会的节日,完全是在阳光下进行的,让阳光和亲人一起见证年轻人甜蜜的爱情。
告别撒里海,顺着山路往回走,其实就是一次赏阅当地立体农业的过程。吊在枝杈间的一颗颗枇杷,像是涂抹了一层黄金粉末,让枇杷成为金黄水果,和水稻、杧果、玉米一样,是一厘米一厘米的阳光照射和一毫米一毫米的汗水通过一道道看不见的管道浸泡出的,地球上最美的色彩,有着和太阳对话、媲美的植物之色。农民怕飞鸟啄叨枇杷,在枇杷快成熟时,用各种不同色彩的纸将枇杷包了起来,看上去好像是穿了彩色外套。就像数量再多,草原上的牧民也能数清自家的牛羊,枇杷再多,经过这一个个纸包给婴孩穿衣般的清点,每一株树上每一颗枇杷,果农都记在心里。
三
一天晚饭时,我看到餐桌上有一张精致菜单,每份菜、水果、小吃和饮品的后面,都标注着诸如安宁河畔、老高山基地、核桃坪村、益满达农庄等食材产地。菜单上出现的牛肉、野参、寿菇、红苕、荞麦粑、枇杷等名字,仿佛闪耀着一道道阳光。吃的是黄金般颜色的核桃、菇片、煮玉米、烤红苕、荞麦粑,喝的是枇杷汁、玉米汁,这里的人,把最接近太阳颜色的作物都能酿成黄金液体。
人类对太阳的崇拜有着多样性的表现,印度人修建太阳神庙,埃及人过“太阳节”,印加人自喻为“太阳之子”。在中国同样如此,北方游牧民族将太阳神像刻在石头上,古蜀人将太阳神鸟铸在青铜树枝上,日照人天台山中凿刻太阳神石和修建太阳神陵,等等。米易人则把生活过成了太阳般明媚的诗意,整座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蓄电池:当地人喜欢把白天在阳光下积蓄的热情和能量,散发在夜晚。瓦蓝的天空被安置成远景,黑黢黢的鸡冠山和鸡罩山像两片微张的嘴唇,上下唇之间轻含着整座县城,街灯和路边的各种灯饰,犹如镶嵌了两排黄金牙齿,轻轻咬着柏油路面;静静流淌的安宁河面上,被两岸的灯光铺上了一层细细的金粉,仿佛向白天借来的缕缕阳光舍不得用,在月光下偷偷地自我欣赏。
希波克拉底说过:人类最好的医生就是空气、阳光和运动。米易,就是一位好医生。
在尼采的笔下,日神代表着一个梦幻世界,她的美丽形象只在梦中出现于人们灵魂面前。夜晚的县城,散发着日光般神韵的气息,透露着日光被借用到夜晚般的梦境之美。让我觉得仿佛是日神不经意间迷路了,推开黄昏的小门,悄然走进了米易的夜晚。
巴黎有拿破仑,纽约有自由女神,呼和浩特有成吉思汗,很多地方都有扮演当地形象代言者的名人塑像。米易将自己所在的这片地方奉认为“中国颛顼文化之乡”,我试图在这里找寻颛顼的塑像,却没找到。智利当代诗人贡萨罗·罗哈斯有一首诗歌,名字叫《太阳的唯一的种子》,这名字多好。颛顼试图把太阳种在历法中,古代亚洲北部的游牧者想把它种在岩石里,彝族人想把它揉进金黄的玉米酒里,米易人把这粒种子抟造成一个古代伟人的形象,却并没具象地展现在红男绿女、车来船去的地方,而是将一粒粒颛顼的种子,播种在水之阳,山之巅和民之心,让这信仰的庄稼,一茬又一茬地在民众心里茂盛长久。
离开米易时,我巴不得将那清澈得能洗肺的空气压缩成包,交付快递邮递回自己的家乡;我巴不得让照往米易的阳光中途转弯,照向我的家乡。
选择坐汽车的方式,告别米易,前往攀枝花市。一路行过,方明白一株株攀枝花的每个枝条都沿着一个个看不见的梯子,努力向太阳攀登,让一座城市以此花命名,这该是多大的一朵花,“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宋代诗人刘克庄说的木棉花,就是攀枝花,那被染得如夕阳般红彤彤的花色,是幸福生活的脸庞,米易是攀枝花这朵花中,献给太阳神低调而尊贵的黄金之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