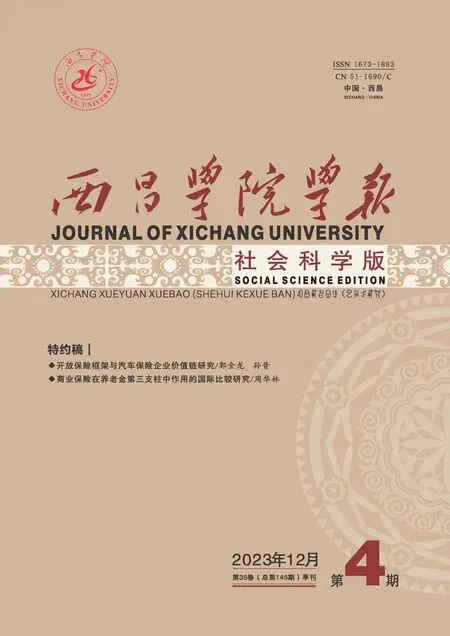儒学教化
——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曹群勇,刘 星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入:彝族地区在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地位
明王朝称彝族“罗罗”,亦称“鹿卢”,即唐宋时期的“乌蛮”“东爨”。《太祖实录》载:“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1]2889学界认为,明时彝族除了“罗罗”这个共同的最常见的族称之外,还因地区、方言、自称、习俗的不同而有摩察、罗婺、鲁屋、聂素、撒摩都、朴刺、母鸡、阿倮、孟乌、葛倮、阿度和阿戛、阿细、阿者、车苏、喇鲁、利米等20 余种族称[2],这些多种族称,或出于其族自称的翻译,抑或出于不同支系、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部落名称。
明王朝彝族地区主要包括乌撒、乌蒙、芒部、霑益、东川、永宁、马湖、凉山、建昌、越巂、盐井、会川、黎州、水西、安顺、普定、普安、毕节、曲靖、越州、禄丰、罗平、罗雄、武定、寻甸、姚安等地,即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以及四川南部的广大地区。除滇池周围,贵阳附近及建昌(西昌)等地有较大的汉彝杂居区外,其他集居区以彝族为主,还包括僰、苗、仡佬、仲(布依族)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分别纳入彝族土司的统治之下。可见,明朝时期,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与云南毗连的广袤地区,这一地区对于明王朝巩固与开拓西南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彝族地区的西南与西面是现在的云南省迤西与迤南的广大地区,这里有漫长的国境线与中南半岛诸国相连,在这广大区域与国境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容易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另外,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攻取南宋,采取绕道大理,迂回包抄中原的战略。明太祖深谙这一位置的微妙。彝族地区的南面是现今贵州和广西的一部分,这里又是明王朝的南部边界。朱元璋曾对贵州水西等彝族土司的“诏谕”指出:“如霭湖广、四川与巩固边戍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其从征军士有疾病疲弱者,每卫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还。”[1]2225可见安定彝族地区对于明王朝控制云南和巩固国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初期对彝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一)和平争取策略
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对彝族地区武力征服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政治招抚,即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彝族土司势力的归附。长期以来,彝族首领一向认为自己就是境内最大的“兹莫”,不愿意头上顶一个管辖、调遣自己,并要为之承担赋役的封建王朝。政治、军事经验丰富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认识到,要使彝族首领服从就范,必须经过军事力量的较量。元代在彝区的统治崩溃后,明王朝正是通过军事行动的铁腕手段重新确立巩固彝区统治秩序。
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军队在四川剿平明升的反抗之后,云南还存在元宗室梁王的残余势力。当时,明朝已基本上统一全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为了恢复元末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明朝廷在对云南梁王采用争取和平归附的方针的同时,也加紧对彝区土司的笼络安抚工作。从洪武四年十二月起,陆续有马湖、贵州(水西)、建昌、永宁(叙永)、黎州(汉源)等地彝族土司来朝,明王朝对彝族土官的和平争取策略初显成效。对于这些彝族土官,明朝廷一般予以原官授职,给予优厚赏赐,有的并予以升迁。如“洪武六年八月戊寅“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1]1449,“升四川永宁长官司为永宁宣抚司,以土酋禄照为宣抚使”[1]1649。而对彝区的内部矛盾,明朝廷不偏袒其中一方,以免卷入纠纷,造成不利。洪武五年八月(1372),“贵州宣慰使霭翠上言部落有垅居者,连结仡佬,负险阻兵,以拒官府,乞讨除之……上以垅居交侧不从命,由于霭翠所激,谓大都督府臣,曰:蛮夷多诈,不足信也。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1]1389。朱元璋认为垅居“连结仡佬,负险阻兵,以拒官府”是霭翠所激,并以国之大器不作报怨之具为辞,拒绝出兵。“诸夷诸酋长,洗心涤虑,效顺中国,朕当一视同仁,岂有间乎”[1]2228,尽管明王朝做了较细致的和平争取工作,但彝区首领并不愿意真心归附。在明朝廷数次争取梁王失败的背景之下,彝族土官借故迟迟不和明朝廷建立联系,已取得联系的土官也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很明显,明王朝要在云南及广大的彝族完成统一大业,必须经过军事实力的较量,这是回避不了的。在对云南梁王和平争取完全失败之后,朱元璋决定对西南用兵。
(二)征南大军的用兵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号称三十万的征南大军在颍川侯傅友德率领下,分两路进入彝区。最初,明军进攻的主要目的是捕捉梁王的主力。同年十二月,在曲靖地区与梁王十余万主力部队进行决战,取得胜利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深入云南省城至迤西大理,一路由傅友德“自率众数万,捣乌撒(威宁)”[1]2212,在赤水河畔与彝族部队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取得初步胜利。赤水河之战并没有消耗彝族军事主力。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朱元璋令征南部队,在乌撒、乌蒙(昭通)、东川(会泽)、芒部(镇雄)、建昌等彝区,“约束其酋长,留兵守御,禁其民,毋挟兵刃”[1]2225,并要求诸夷诸酋长“洗心涤虑”,恭顺王朝,否则“即加兵讨之”[1]2228,令傅友德把彝族土官“悉送入朝”[1]2234。朱元璋在系统总结汉唐时期西南诸夷反复起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熟察其详情”“宽猛适宜”“详慎处置”,“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的谨慎方针[1]2236-2237。虽然明朝廷为安抚争取做了较多努力,但彝族首领仍坚持在战场上继续决一雌雄。同年四月,乌撒一带的彝族又起来反抗。随后,普定(安顺)发生“西堡蛮”暴乱,乌蒙、东川、芒部、盘江、关索岭等地的彝族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一场反明高潮。明王朝从大理抽回征南主力部队,七月在乌撒地区对彝族部队发动重点进攻,取得“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计”[1]2295的重大胜利。经过半年左右的持续斗争,于1383 年正月取得全面胜利。同年二月,“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部土酋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1]2387。这标志明王朝与彝族统治者之间大规模军事斗争的暂时结束[3]。1383 年至1384 年,彝族土官络绎赴南京朝贡。朱元璋命令沐英率部镇守云南,1384 年3 月,傅友德大军班师回朝。
(三)反抗的余波
彝族土官的入朝不是反明斗争的终结,只是赢得1384 到1388 年约五年短期的平静。1388 年三月,随着云南西部麓川(今陇川、瑞丽及其南部)傣族土官思伦发起兵反明,彝区的局势再起波澜。同年六月,“东川、越州、罗雄、把哲诸夷,悍鸷未服”[1]2879,“东川诸蛮,据乌山路结寨而叛,其地重关复岭,崖壁峭险,上下三百余里人迹阻绝,请讨之”[1]2882。明朝廷再动兵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率军入彝区。同年九月,越州土官阿资与罗雄州“营长”发来起兵反明。彝区形成两大反明中心,一为东川乌山路,一为越州(今曲靖东南)。由于明王朝积累了对彝族部队作战经验,采取分化瓦解,团结争取的双重策略,反明斗争没有扩大。明朝廷采取各个击破战术,成功化解彝区的反抗。1388 年取得对东川的胜利,同年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阿资无奈投降。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乌撒、乌蒙彝族土司恢复朝贡。阿资与明朝廷有杀父深仇,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二月起又屡次兴兵。在此期间,明王朝于1392年正月平定“毕节罗罗诸蛮”的反抗,同年十一月平定建昌地区月鲁帖木儿的反抗。1395年正月对阿资的平定[1]3443-3457,标志着明初对彝族地区较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基本结束。1397 至1398 年,在普安、水西等地发生一些较小规模的反抗,明朝廷动用贵州地方卫所兵力即能解决。军事行动的胜利为明王朝彝区治理及儒学教化奠定了基础,随后,明王朝在彝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就这样,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三、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一)制度安排:彝族地区的儒学教化
儒家经过西汉董仲舒的重构与阐扬,最终确立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儒学教化的核心是倡导以德施政,推行教化,以礼施治。儒家教化传统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兴国安邦的坚实理论基础和施政理念。明王朝作为汉文化的继承者,符合逻辑地大力推行儒家教化。“四海之滨,莫非王土”,彝族地方虽系偏僻闭塞,与外界隔阂之区,但儒学教化亦概莫能外。
教乃政之本。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丙午,太祖诏谕广西左、右两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1]667在他看来,“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4]1686。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推翻元朝统治需要武力,治理大明王朝,则离不开文治教化。地方治安官员严格贯彻执行王朝的“为治之始,莫先学校”[5]的治国方略。儒学是汉文化教化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体现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推行教化,实行仁政,离不开儒学。平叛安边,聚拢民心,仅凭武力征伐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武功文治并进,威德并施,军事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齐抓并举”[6]305,成为明王朝治理西南彝族地区的政策基调。
明王朝继承唐宋以来的建学之制,中央设太学(国学、国子学),地方设儒学。洪武初,在南京建国学,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统治地区,亦俱设儒学。洪武十五年(1382)岁末,征南大军既平云南,朱元璋诏谕:“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7]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上疏,请于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设学,教授土官子弟。朱元璋旨谕:“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3475-3476明王朝在西南彝区推行儒学教化的同时,亦在中央大学——国子学吸纳彝区土官子弟,对他们因材施教,并给予诸多优渥。据《明太祖实录》卷203、卷204 记载,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戊申,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请入国子学读书,各赐钞锭。同年九月辛卯,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驹请人国子学读书,赐以衣钞。土官子弟入朝求学的事例在《明实录》中不胜枚举,赐给他们袭衣、钞锭、靴靺者更是随处可见,土司后裔不入学不准承袭土司职位。
明王朝西南彝族地区以儒学推行教化,教化的具体内容框架如何呢?儒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强调国家统一,天下治平。就彝族地区而言,就是要通过推广儒家意识形态,从文化软实力的路径维护边疆稳定和中央王朝的文化认同及政治认同。当然,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儒家教化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以下三个维度:其一,化民成俗,劝善去恶;其二,明伦常,道德守礼;其三,造士育才,报效王朝。童轩《重修曲靖府儒学记》云:“自古王者建国,军民靡不以养士为先。”[8]学校是按照统治阶级意志培养和造就人才的教育机构。因此,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儒学,不仅仅是为了使彝区民众臣服,还有借机培养符合王朝意志的国家治理人才,从而进一步按照内圣外王的要求,修齐治平,报效国家。
除了上述三层意蕴之外,吸纳西南彝族地区土官子弟入国子学,还有一层不太好言说的政治用意,即帝王的“驭人之术”——以土官子弟为人质,用亲情关系防范土官反叛。《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洪武十五年,车里蛮长刀坎来降,改置车里军民府,任命刀坎为知府。永乐元年,土官刀暹答令其部下剽掠威远知州刀算党及民人以归。朱棣敕谕刀氏如不归降,西平侯沐晟将发兵征伐。刀暹答被迫就范,并遣使入贡谢罪。永乐四年,“遣子刀典入国学,实阴自纳质。帝知其隐,赐衣币慰谕遣还,以道里辽远,命三年一贡,著为令”[4]8156。
(二)彝区的响应:流官办学与土官兴学
现存记录明王朝彝族地区儒学发展的诸多碑刻较全面记录了有明一代彝区各府、州、县学创建、改迁、修复、扩建的历史。明王朝派遣的流官在西南彝族地区崇儒教化、尊孔兴儒、建学立庙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文治教化,推行文化软实力安边的国策。
最早在云南推行儒学教化的明代政府官员当属以沐英为首的沐氏家族。黔国公沐英平定云南之初,“开学校以教民子弟,诸酋长亦遣子入第,王时嘉奖掖。民知习礼义,稍稍如内郡县矣”[9]。沐英次子,定远王沐晟“建学立师以教导其人,使归于善,尤孳孳不倦”[10]。沐英曾孙沐璘“自幼颖敏,读书习礼”,担任云南总兵官期间,“凡百废坠,莫不修举,而城堡兵器,学宫使馆焕然一新,汰冗剔蠹,简僚修政,严祀抚夷,德化大行”[11]。应该看到,“沐氏镇滇期间,承担着诸如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平服叛乱,稳定边防,修明政治,统领三军等众多政务。在如此繁重的镇守任务之中,特别是在平滇之初,政局尚未稳定之时,沐英及其后嗣时刻不忘尊孔兴儒,建学立庙。沐氏在滇崇儒施化是为了落实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广施教化的国策”[6]307。实际上,沐氏家族只不过是西南边疆彝族地区兴学施教众多流官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兴学之举在明代西南边疆有开先河之功。但也不可因此忽视或泯消其他官员借儒学推行教化,化导世风的壮举。更多的修建儒学碑刻史料表明,在西南彝族地区的总兵官、三司、知府、州府、知县、卫所将帅、巡按总督、巡抚等众多官员都曾参与办学教化工程,如水西土司兴办儒学,遵义龙坑牌坊所记捐资办学之事。《楚雄府儒学会讲亭记》《曲靖府儒学记》诸碑记明确记录了兴学的用工出资情况。兴学所需赀钱财出自官、民自愿捐助,未因兴学使民众承受重负。
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儒学教化体系的制度安排,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就是彝族地区当地的土官。以云南元江为例。那氏彝族土司源自罗婺部落,是彝族六祖徳布德施的后裔,朱元璋赐姓为那,任元江军民府土知府。元江那氏土司在洪武初年平滇之时归附王朝。西平侯沐英曾上疏褒赞那氏忠顺,后改元江路为元江府,令那氏世袭镇守。元江府学始建于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七年重修,庙庑、门堂、学宫、斋舍规制具备。嘉靖四十年,迁府治北。万历二十五年,土舍那天祐重修。又据张绎《元江府文庙圣贤铜像记》,正德十六年,土官知府那端曾改迁学地,宏阔庙学,出资铸造圣贤铜像[12]。可见那氏家族重儒兴学是代代相传的。
梳理史料可知,土官向学与土官抵制儒学在彝族地区发展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学界认为,“在更大程度上土官抵制的情况更多一些。这当与土官担心教化形态的改变,进而动摇自身的统治基础有直接关系”[6]313。
四、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儒学教化的评价
明王朝彝族地区推行儒学教化的治理方略既有对元代的继承,又有在前代基础上的创新,继承性巩固了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既有成效,确保彝族地区治理方略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明代彝族地区推行儒学教化的治理方略彰显出彝族地区与内地和边疆区域单元的一致性。换言之,和其他地方一样,明代的彝族地区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其政治政策、经济发展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化诸方面已经基本趋同。彝族地区已经逐步步入明代国家治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发展的快车道。
明王朝在彝族地区的儒学教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与明朝在彝族地区的统治相始终。从王朝对彝族地区的儒学教化推行的成效来评价,以崇儒施化的教化政策确实发挥了其应用的作用,基本达到了王朝以文化软实力巩固西南彝族地方的统治目的。儒学学校遍布彝族地区大小府、州、县,基本覆盖彝区全境。当然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各地儒学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分布密度不一致的特点。但相比元朝而言,明代彝区儒学建设已经发生质的飞跃。儒学已经在彝区落户生根,众多府州县儒学废坏后屡经重建的历史表明,儒学已经成为明王朝彝族地区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众多百姓参与兴学的历史反映儒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他们已经不是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教,而是开始心悦诚服地接纳并按照儒家的思想意识积极参与王朝政治文化生活。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