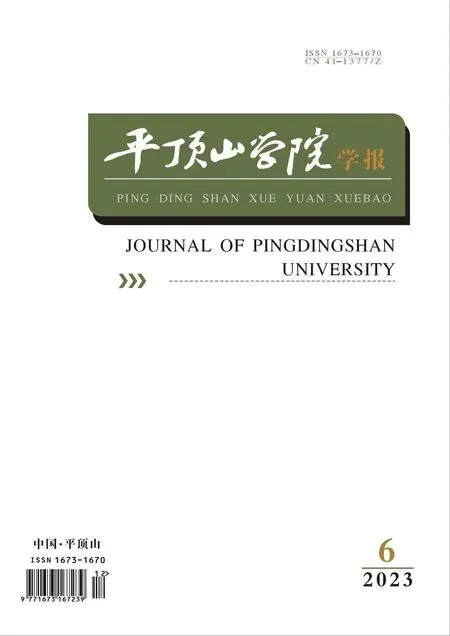也谈苏轼为何葬在郏县
——兼以体察苏轼内心世界
庞晓畅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10)
苏轼生在四川眉山,身后葬于河南郏县。对于苏轼为何选葬郏县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所谓“练汝说”,即苏轼是因为在汝州做团练副使,看到当地山水形胜,故选此作身后葬地。而汝州团练副使一职苏轼实际上并未到任,他从黄州量移汝州途中两次上书,乞居常州,皇帝同意后他掉头就往常州去了,所以此说难以成立,并且早已被证伪。其他诸如“形胜说”“家境不济说”“表恋阙之微诚说”“祭祀方便说”等,都被学界认为虽有一定道理,但依事理推测,缺乏直接证据,无法令人信服。
近年来,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对于三苏研究的不断关注,这一问题渐趋明朗,代表性的新成果有:乔建功《苏轼葬郏探因》,提出苏轼“最终归葬郏县实为兄弟情义高于一切”,“苏辙慢说选择郏县葬地,即使选择其他任何地方,兄长也会义无反顾地前往相随”[1]。 王维玉《苏轼葬郏之选: 事件、观念与哲学意蕴》,认为“苏轼葬郏之选客观上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等情势所迫,主观上是由其政治、历史等观念所致,并有其深层的情本论哲学意蕴”[2]。 刘清泉《郏县苏轼符号——谈苏轼的丧葬观》,提出苏轼葬郏是“不循流俗、顺应天命、临时随宜的自然丧葬观”的表现[3]。上述三文没有像过去许多文章那样单就事件本身进行考据,而是更多结合了苏轼本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以及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更多地探究苏轼内心。这种方法和思路是可贵且可取的。
本文也吸收借鉴这种考察思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苏轼选葬郏县的原因,简单来说,一是“情”——主要是与苏辙的兄弟情,也包含巴蜀故乡情、宦海浮沉中的故人情;二是“义”——嵩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含义契合了苏轼匡世济民、报效有为的内心价值追求;三是“便”——苏辙在嵩山南麓购有田地,选葬郏县属随缘求便、省力避害之举。换言之,苏轼之所以选葬郏县,是因为主观有愿望,客观又允许。这里的“愿望”不是非葬郏县不可的愿望,而是和弟弟苏辙同葬一处的愿望,若非此愿,未必要葬嵩山,更几无可能选葬郏县。若有此愿,但地方不理想或不方便,也未必一定能实现。
苏轼尽管儒释道集于一身,但儒是内核,因此,他有放得下的东西,也有放不下的东西。放得下的是世俗所谓的生死、贫贱、得失、进退等观念,放不下的是骨肉故乡之情和匡世济民的理想追求,“情”“义”“便”三者正与此对应。当代学者叶嘉莹评价苏轼是“人而仙者”,以区别于李白的“仙而人者”,也是对他这种放下、放不下的内在精神的概括[4]。
一、归颍昌:真“情”难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即位,苏轼被赦,度岭北归。五月行至真州时写下《与子由弟十首(八)》(以下简称第八简) :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四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兄万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讬师是致此书。[5]
这封信历来被看作苏轼选葬郏县最重要的直接证据之一,其中处处透露出对骨肉团聚的渴盼。这种渴盼一是生前(相见前夕,形势变化,团聚不成,因而“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二是死后(纵使生前“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死后一定同葬一处,实现团聚,决心已定,无需商量)。此时苏轼六十有六,一生宦海浮沉,老年被赦的他决心过一番平静生活。写信时他身体尚好,还未得病,能够平心静气思考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余生和后事安排,可以想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当时苏辙虽奉召回京,但朝廷是蔡京当权,久在仕途的他避之不及,遂生退意,又因在颍昌府有田,故请求致仕归隐许昌,而后写信苦劝苏轼去许昌与他同住。苏轼原本答应,却为了避开政治乱局与官场争斗,未能如愿。此信书后两月,苏轼瘴毒大作,暴病不起,卒于常州孙宅。据《春渚纪闻》记载,苏轼临死前一直念念不忘:“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6]
兄弟之情作为古代五伦之一,历来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人所看重。罗大经《鹤林玉露》曾写道:“然余尝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会聚,久速固难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继而生,自竹马游嬉,以至鲐背鹤发,其相与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7]兄弟情谊之深,可见一斑。而苏氏兄弟之情更是久被称道。据不完全统计,二苏往来诗词多达200多首。同时期其他文人兄弟,如程颐、程颢兄弟,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兄弟,都有文集传世,但鲜见兄弟唱和之作。而在苏轼的诗集中,仅以“子由”直接为题的诗,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有104首之多[8]。
二苏年龄仅差两岁,两人一同长大,共同学习生活。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里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9]1099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皆才华横溢,年少成名,在嘉祐二年同中进士。然而自中第入仕后,二人仕途都不顺遂,苏轼更是一再被贬。此后两兄弟常是天各一方,唯有为父母丁忧的六年和当京官时能在一起,可谓聚少离多。苏辙在《逍遥堂会宿》引言中追忆:“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10]这便是二苏“夜雨对床”这一约定的由来。风雨交加中,至亲之人相伴相守、对床而眠,个中欣喜快慰战胜了外部恶劣的自然条件,这当然也引起了渴盼相聚的苏氏兄弟的强烈共鸣。此后二人对此诗、此约念念不忘。苏轼有诗云:“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是大苏在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时写给弟弟的“诀别诗”,诗中他不以生死为意,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兑现“夜雨对床”之约,于是从对面写来,想象弟弟在自己故去后独自“黯然伤神”[11]。此诗此情,让人动容。苏轼去世后,苏辙也果然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追忆从前,凄然感怀:“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9]1101可见,聚少离多的二人生时便心心念念相聚,哪怕只是在风雨中对床而眠,就已觉得弥足珍贵,那么死后葬于一处,于黄泉下相伴,对弥留之际的苏轼与挂牵兄长的苏辙来说都是心之所愿。
除了“兄弟情”,“故乡情”与“故人情”也是影响苏轼归葬郏县的因素。苏轼自少时出川,多次表达还乡之念,如“婉娩有时来入梦,温柔何日听还乡”(《次韵李邦直感旧》)、“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与杨济甫十首(七)》)、“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等。在贬谪黄州时期,他更是渴望“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临江仙》)。归乡之日遥遥无期,此时苏轼唯一的直系亲人是苏辙,最关怀、思念、牵挂他的也是苏辙,以至暮年的苏轼既知归乡希望渺茫,那么和兄弟在一起也算是重续故园记忆,弟弟在的地方便成了半个家。
除了苏辙的因素,范镇墓落在许昌,也是让苏轼感到慰藉的重要原因。范镇是北宋一代名臣,又是成都华阳人,与苏洵是故交,比苏氏兄弟大二十多岁,亲如叔侄。他的两个孙女分别嫁给了苏过(苏轼子)与苏远(苏辙子)。苏、范两家不但是老乡加姻亲,而且“政治倾向又相一致,关系非同一般”,乔建功引用《栾城集》和《苏辙年谱》中的记载,说“苏氏、范氏,同出昆维,蜀公告休,居颍之湄,我老去国,归亦从之”,“苏辙谋居与定居颍,与范氏有联系,镇及妻葬于汝州(临汝)之襄城,苏辙兄弟葬于郏城,属汝州,皆在汝州之东南,相距甚近”[1]。
熙宁九年(1079),苏轼入狱,范镇因与苏轼书信往来频繁,又上书欲救苏轼,因此受到牵连,被罚后归隐许昌。范镇甚至曾写信给苏轼,“约之同居许昌,不得,范镇深感遗憾”[12]。六年后,范镇去世,葬于襄城。因为范镇墓的存在,归葬郏城对苏氏兄弟来说又多了一层意义。故人在此,生时未能同住,身后相伴也不寂寞。
如今走进三苏墓园,人们会首先看到一副对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这是明代学者王尚絅在浩瀚的苏学海洋中为之选择的。这句诗配以横额“青山玉瘞”在墓园刻石立坊,以“夜雨对床”昭示苏轼葬郏的兄弟情思。乔建功先生评价说,从这来看,苍谷(王尚絅的号)先生是读懂苏轼葬郏原因的第一人[1]。单就苏轼主观来讲,笔者也深以为然。
二、选嵩山:大“义”难舍
除了前文提到的第八简,苏轼选葬郏县的另一份证据,是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10]1410
这寥寥数字蕴含了很多信息:“公始病”,根据史料,苏轼是六月初三的午夜突然猛泻起来,这场病极凶极疾,不足两个月就带走了他的生命。他在此期间“以书属辙曰”,这封“书”现已散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临终前交代后事的书信,其言必体现其决心,表露其真情。而这封信里最重要的就是“即死,葬我嵩山下”。他知道苏辙在嵩山之麓有地,原本是要作为八郎妇(苏辙的儿媳)的墓地,但第八简因为还说了“葬地,弟请一面果决”,所以葬地不变则罢,假如有变,不要脱离嵩山。由此可见,苏轼明确想与苏辙归葬一处,且此地就是嵩山。
对于苏轼青睐嵩山的原因,前人也给出了多种说法。有学者说嵩山土厚水深,景色秀美,还有学者说这里有山状似苏轼家乡峨眉。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把这些外在因素当作苏轼抉择身后事的主因,就有“循俗”之嫌,况且风景旖旎的名山大川远不仅嵩山一处。真正的原因应当是嵩山在苏轼心中有特殊象征意义,切合了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也符合他一生不变的价值追求,这在他的诗歌里是能寻得证据的。
苏轼在《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中有句“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归”有回家的意味,嵩邙则承载了思乡梦回的心绪,可见嵩邙在他心里是精神的故乡。《和陶拟古九首其一》有句“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以贬谪之身处海南天涯之地,一想到自己可能会终老于此,谁不唏嘘?然而望着黎母峰,他宽慰自己,这里与嵩山和邙山有何差别呢?千山万岭中他独选嵩邙来自我开解,也正因为嵩邙就代表着故土、代表着精神家园。第八简里写“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这里的“近地”即近嵩邙之地,而“老境”一词也说明作者对这里的熟悉,是亲近亲切的家园故地。
显然,在苏轼心中,嵩邙代表京畿,也代表“归”的梦想、“家”的滋味。如果把四川看作他自然生命的故乡,那么嵩邙所代表的“近地”“老境”就是他的精神家园。
苏洵曾在诗中对比家乡与中原:
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
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
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
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13]
在苏洵眼中,家乡四川固然山水美好,物产丰富,“居之富者众”,但“我独厌倦思移居”,即嫌其闭塞,“恐我后世”因脱离现实主流世界而“鄙且愚”。天下之大,嵩岳最好,遂欲买地以居妻孥。
后来,苏轼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中对前诗做了回应: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徬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14]
许多人以这首诗为例证明苏轼葬郏是因为喜爱嵩洛风景,笔者以为不然。该诗作于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途中,在筠州与苏辙告别之时。他并不想去汝州,两次上书乞居常州,皇命未允。在与弟分别之际只好良言互勉:父亲当年就想移居嵩洛,现在你我有望实现他的夙愿,“茅轩照水”,“两翁相对”。然而苏洵移居嵩洛,是想远离闭塞,“恐我后世鄙且愚”,是入世之言;而苏轼却赞美其自然风光,向往闲适惬意,反而成出世之语。显然,这是一种正话反说,表面的旷达反衬的是贬谪之人心中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
在苏轼诗文中,有些字词和句式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比如“应”:“不应有恨”“多情应笑我”“纵使相逢应不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等。比如“何”:“何似在人间”“何事长向别时圆”“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何妨吟啸且徐行”“天涯何处无芳草”等。比如“恨”:“长恨此身非我有”“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不应有恨”等。
这些都可以看作一种反话,就是外在之“我”对内心之“我”的劝慰解脱:内心的“我”有恨,外在的“我”则宽慰道不应有恨。所以,苏轼虽是豪放词人的代表,但其豪放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正是一种外在和内心的矛盾。他渴望“羽扇纶巾”“横槊赋诗”,想要施展才干,匡世济民,但现实中却屡屡受挫。无奈之下,只好寻求自我宽解之法,归于佛道,为“有恨”的心灵寻找解脱的出路。
所以,苏轼虽看似集儒释道于一身,但其根本与内核是儒,他一切行动轨迹的圆心也是儒。他可以放下外在的世俗之见,却无法将圆心化掉。这个圆心就是关心民瘼、匡世济民的儒家理想,就是苏洵所言“鄙且愚”的反面。哪怕是失意被贬海南期间,他都不忘修订儒学经典,希望能够“知千载之微言,发圣人之秘旨,明上古之绝学”[15]。临终前,由于常州久旱无雨,病中的苏轼还让家人把黄筌画的龙挂在中堂,每夜亲自上香祷雨。纵观他的一生,无论境遇如何,为国为民之心无改,这就是他心中不变的儒的“核”与“圆心”。这个“圆心”在自然外物中外化为嵩邙——一片厚重的、养育黎民苍生的土地。选嵩岳作归地,是选自然的嵩岳,更是选精神的嵩岳,嵩岳的精神,是选他的内心。所谓“是处青山可埋骨”“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只是一种表面的潇洒,用于掩盖当时当下的心酸无奈。他何尝不想魂归故里,与家人故乡为伴,何尝不想自主选择葬地,不必考虑花销,但一切无法如愿,故以外在之“我”劝慰内在之“我”凡事看开,不必有恨。
可以说,在归葬祖坟“势不可从”之后,魂兮归来,他内心一定是归于嵩邙。一生之中,他的内心时常被佛道烟云弥漫笼罩,但临终还是显出其儒家士大夫念恩报国、匡世济民之义,这个“义”化成了一句“葬我嵩山下”。
三、定郏县:“便”利为要
如果说苏轼与嵩山的联结围绕一个“义”字,那么苏轼与郏县的渊源则简单很多,因为他们本就无甚联系。
苏辙在《卜居赋并引》中说,绍圣元年“予初守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颍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一子居焉,曰:‘姑糊口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10]1523苏辙当初被贬到汝州,四月到任,六月又被贬至袁州,后改筠州。此时的苏辙为免后顾之忧,在许昌西买田二顷,留一子住在这里种田糊口。后来他果然越贬越远,直至徽宗即位,赦免前臣,他才有机会回河南。三苏坟所在地郏城上瑞里处的田地,据考证当属他许昌西二顷田的附属部分。此地东距许昌近一百公里,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一段很远的距离,因此不便管理。且此地位于嵩山脚下,山岗薄地,不宜耕种,但土厚水深,适合作葬地。第一个被规划葬在这里的是苏辙的三儿媳黄氏(即八郎妇)。在此前的流放生涯中,黄氏一直陪伴服侍在苏辙夫妇左右,尽心竭力照料一家的饮食起居,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在苏辙到达循州的第二年,黄氏身染瘴毒不治而亡。苏辙深感悲痛,专为其撰写《祭八新妇黄氏文》,期望“灾厄有尽,天造有复,全柩北返,归安故土”[10]1386。如今真有机会北返,苏辙一定要首先安葬已故去两年的黄氏,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于是他很自然想到把郏城上瑞里处的田地作为葬地。
但这与苏轼无关。苏轼一生未在郏县一带做官,有人考证他在出川途中曾路过郏县,这有可能,但他对这里的了解并不多,只对汝州(郏县当时归汝州)的粗脖子病印象颇深。“粗脖子病”即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是汝州贫穷落后的象征。在从黄州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时,他不愿前往,行前写《别黄州》感叹: “长腰尚载撑肠米,阔领先裁盖瘿衣。”意思是人还未动,大领衣服已经备好。同年八月,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说:“勾漏丹沙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朋友去广南得到传说中勾漏山的仙丹,“我”到汝州去只可能甲状腺肿大,脖子粗如瓮盎。当初要去汝州上任时,他勉强出发,一路迤逦而行,拖延了近一年才到商丘,然而听说自己回常州的请求被准,马上调头南下,路上时间不到一个月,欢喜满足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写诗以自乐——“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归宜兴留题竹西寺》)。所以,苏轼葬郏并不因为自己与这里的联结,而完全是苏辙在此、嵩山在此,同时又要求便,不愿让弟弟因循俗而破费,才最终定下郏县。正如他在第八简中所说,“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苏轼心里虽然有放不下的情意与义理,但在生活里并不过分拘泥苛求,随缘求便“不循俗”,不为琐事而累,这便是苏轼心中的“放得下”。
在被贬海南期间写下的《试笔自书》中,苏轼说:“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16]在《记游松风亭》中,他写:“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17]人生如逆旅,他不再刻意苛求,也放下了人为设置的种种标准、要求、条框,还自由自在身,既然如此,世间何处不得歇?贬至黄州,便是黄州人,贬至天涯海角,便是海南人,生前如此,死后更不应拘泥。
在苏轼去世前,据李一冰《苏东坡传》记载,他听觉先失,然而神明丝毫不乱,维琳在他耳边大喊:“端明勿忘西方!”他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在旁,也大声说:“至此更须着力。”苏轼答曰:“着力即差。”[18]这“着力不得”与“着力即差”正是他凡事自然而为、不刻意强求的体现。无论是往生还是今世,苏轼把这些所谓“规矩”都看破看淡了。“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生命里“故意求之”的部分淡化了,随缘而动,随遇而安。既为游子,何处不可歇,何处不可葬?
也正因为凡事求“便”,他的生活与弟弟相比少了一些人为的规划安排。比如同样是一贬再贬,苏辙在还未彻底离开政治中心前购置土地房产,并派儿子在此看管,心细务实,考虑周全,可见一斑。而苏轼不同,虽然也曾因喜欢常州而在那里买地,但不知何故,那里没能成为他自海南回来的落脚点。或许经过漫长的七年,那边的房产无人看管,早已卖掉或倒塌。总之,在自己老迈有病之时,他只能借住孙家,最终也病死在他人房中。
苏氏兄弟二人性格不同,做事风格自然也不同,苏轼有高蹈英迈之气,为文闳肆,行事相对随性潇洒,苏辙则静厚寡言,为文简严精确,做事更加务实周全。但反过来说,考虑到苏轼当时“无家可归”的情况,他对于死后墓地的考虑确实是综合考量了各种因素和条件的,苏轼借住他人家里,没有安居之处,拜托唯一可以仰仗的弟弟替自己料理后事,当然希望省力求便。而弟弟考虑再三,遵从兄长之愿,将他葬于自己身边,也确实是最方便合适的选择。
四、结语
笔者最后想要指出的是对同一历史事件后人和时人的不同态度。据文献记载,探讨苏轼葬郏之因,始于元至顺元年(1330)郏县教谕孙友仁为“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撰写碑阴记,此时距苏轼仙逝,已过去229年[19]。从那以后,探讨者不断,直到今天。后人觉得反常,把这种探讨视作解谜,但与苏轼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却并没有提出疑问。可见,岁月的风尘淹没了苏轼葬郏一事的中间细节,只留下了故事的两头——四川眉山之苏轼,葬在河南郏县,后人因而感到困惑,历数百年讨论不休。其实,拂去历史烟尘,我们能看到的是苏轼实实在在的情义,与现实中的诸多无奈。苏辙在嵩山有地,苏辙、嵩山、有地——三个条件分别代表“情”“义”“便”,综合来看就解决了问题。
当然,这数百年来的不停追问与探索也反映出人们对苏轼不变的重视与喜爱。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人们都渴望还原他的真实想法,对其生平经历和内心世界多些了解。而本文通过对“葬郏”原因的分析,希望能够借此展开他丰富形象的一角:他能放下的是世俗之见,凡事随缘求便,不拘泥于外在条框细节,但放不下的是世间真情,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报效有为之义。纵观他的一生,“放下”与“放不下”之间的矛盾与挣扎贯穿始终,直至选葬郏县,即他人生中做出的最后一次的选择。而正是这种矛盾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苏轼,更构成了人们千百年来崇敬苏轼、喜爱苏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