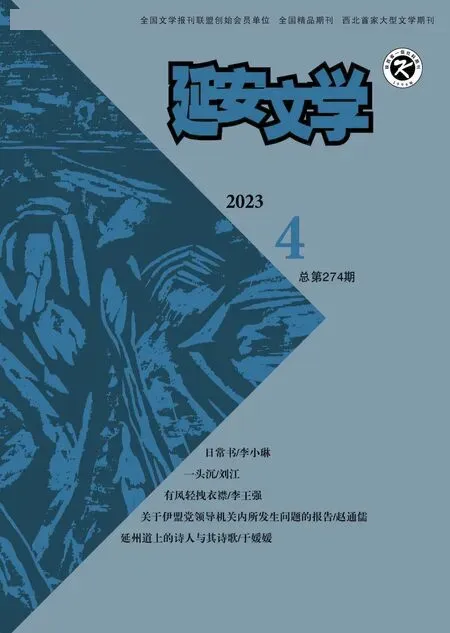拉票
王 佳
一
“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次列车。本次列车是G4321 次列车,由B市开往X 市……”伴随温柔的女声,高铁缓慢驶出站台。高大的穹顶渐行渐远,拐了个弯,消失不见。桥下的树木迈进加速度,连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线。
那个男人,一直在看她。源于女人的直觉,她敏锐捕捉。男人坐在她的右边,靠窗的位置。那时,她手提皮箱,站在座椅上,卖力地把箱子塞进行李架。她的实际身高多少?一米五几吧?她自己也忘记了,每次测量都不一样,索性就不管。反正肯定不够一米六,虽然简历上欲盖弥彰,写着一个虚伪的数字。本科毕业去找工作时,面试官目光苛刻,似乎她是一匹待价而沽的小马。她胆战心惊,等待真相的揭露。面试官终于对她表示了怀疑,随即从身高推演到了人品,慷慨激昂:你到底有没有一米六?她说,我就是一米六。你肯定没有,你为什么要骗人,你人品有问题。她垂着头,似乎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行李架暴露了她的真实身高,她站在座椅上,踮起脚扬起手,箱子在指尖晃晃悠悠。男人站起来,帮她把箱子放进去,像是抛掷一个轻巧的篮球。她报以习惯的微笑,说了无数个感谢,内心窜过了一行字——“随着社会的进步,男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有素质。”这是一个不错的论文开头,也是一段常见的汉译英试题。她早就习惯把一切都以学术性的话语代替,或许这叫做“学术体”?
二
她坐的是二等座。按照她的职称、级别,只能报销二等座,只能选择二等座。是最最普通的蓝色,这世上一切朴素大方的事物,都用蓝色作为包装或者衬托,比如蓝色工作服,蓝色窗帘。就连会场发的文件袋,也是蓝色。
她紧捏手机,焦急万分。
男人的注视,无暇顾及。
前天,她坐在从X 市前往B 市的高铁上,学院教学秘书发来一条链接,配上留言:“林老师,恭喜您入围决赛,需要网上投票,快快拉票吧。”她点开链接,从“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开始投票啦”中找到自己。一张全身照,配上五天前自撰的推荐语:“在课堂上,循循善诱,将晦涩的专业理论化为引人入胜的精神给养;在科研中,启人心智,为学生们在风雨兼程的科研路上保驾护航;在生活里,春风化雨,坚定地秉承着‘恭宽信敏惠’的德行与修养。”面对自我表扬和屏幕上严重失真的美颜,她有些恍惚,不由得捂住了手机。
四处转发在所难免。一想到要祈求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熟悉或不熟悉,平素有过节或无过节的人给自己投上宝贵的一票,她的脸禁不住红到了耳根。可是又能怎样呢?这些年学校职称评审改革,倒是不仅仅“唯论文”,要“唯”的可就更多了。从电影里提取一句话,叫做一个都不能少。非要把原来的偏科变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硬逼着人人都成为全才,木桶的每一块板子整整齐齐,像章丘大葱一样挺拔好看。三十五岁的大龄讲师林宝珠无法选择,再羞再臊都得把拉票进行到底。
勉勉强强博士毕业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科研毫无天分,只是凭着一股子心劲勉力坚持。当然,这里的普通,并不是广义的普通,而是高校圈狭义的普通,她只是学术这个菜园子里一枚小小青椒,广阔科研天地中一只弱弱菜鸟。好不容易读到博士研究生,学历上的终点,漫长学海的尽头,仅仅两篇小论文,就耗尽了她所有的心血和精力,终于毕业,终于成为战士中的圣斗士,终于如释重负。自那以后,她突然沧桑起来,年轻时候的不甘示弱轰轰烈烈,变成了风轻云淡低吟浅唱。这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得不到的时候,总想得到;得到的时候,又不过尔尔。
坐在高铁靠窗的位置,她回忆和梳理自己挥手告别的三十五年。飞驰的楼房树木庄稼良田,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撞向她,又像一枚枚邮票飞快地离她而去。关于过去的回忆也在脑海中斑驳闪现。在会场,她度过了自己身份证上三十五岁的生日,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于是悄悄咪咪,躲躲藏藏,自己都不敢面对。同样都是三字头,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四,尚且可以自欺欺人地四舍五入,退回三十。而三十五,任你如何掩耳盗铃,都改变不了迅速走向衰老奔赴四十的事实。青年项目以三十五岁为界,高龄产妇以三十五岁来划分,高校教职招聘也都卡在三十五岁……种种都在警告你,这个数字是你求职生育评职称最后的优待,过了这个村,你就再也享受不了任何年龄上的便利。二十多岁的时候,谁都体会不到这种焦虑和无助,一切离自己还那么遥远,该玩儿就玩儿,该恋爱就恋爱,还有大把试错和浪费的机会。回过头再看,其实并不遥远啊,稍微放纵和姑息一下,岁月就撑着时间的小船,呼啦啦划走了。当年怎么就荒废那么多时光走那么多的弯路呢?比如说读博,为什么就那么不开窍,那篇重要的论文,拖了一年半才发出来,大论文得了一个C,又延期了一年。比如说结婚,怎么就要一意孤行,非要赌气显示自己的坚强独立,不追随师兄出国呢?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选择,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决定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社会地位。唉,有些人天生就厚脸皮,比如刘美阳,什么货色,居然趁虚而入,抢走师兄。她这边还在等待师兄回心转意,那边早就莺歌燕舞,最后还作为家属,解决工作进了那个南方985,两口子双宿双飞。一想到这事,她就咬牙切齿,再想到是刘美阳捡了这个大便宜,更加悲痛欲绝。那么不思进取的一个人,本科毕业就辗转各个公司,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人家就是通过她这条线认识了博士师兄,暗度陈仓,牢牢抱住了师兄的大腿,如今也是多少学生仰望的“师母”了啊。
越想越气,这世界总有那么多不公平。就拿时间来说吧,你说它公平吧,当然公平,对任何人都铁面无私,绝不多走或者少走一分一秒。你说它不公平吧,它当然不公平,有的人就能按期博士毕业,有的人就要拖个十年八年,灰溜溜地把自己耗成大龄青年,哦不,中年。时间对于女人尤其残酷,从25 岁毕业到35 岁,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时光,要完成毕业恋爱结婚生育求职评职称,每一个词语说出来都是铿锵有力,力穿纸背,重若泰山,都代表了一定的难度和无可奈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她早会用学术的眼光评价总结——这是理论工作者最基本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她早就说过,有些事情注定是无法靠一己之力完成的,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是最难的。很不幸,她曾经和现在面对的毕业恋爱结婚生育求职评职称,包括投票,都是这种类型。
求人办事,总是不好意思,不知道竞争对手的票数是多少,不知道需要的票数是多少,总得几百上千吧。这就意味着需要央求几百上千号人去点击。早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求人办事的一天,必然未雨绸缪,提前谋篇布局。她为自己曾经的短视而悲伤。平日里,她在朋友圈和各种群里看到别人的拉票,总是不屑一顾。多么厚脸皮的人才会讨要一个点击一张票啊,真能拉下脸。她从来不去点击别人的拉票链接,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或者说秉持着某种原则和底线。她并不愿意为了虚假的人情去奉献自己的一票,破坏内心的评判准则。就像为了一块钱的红包去写一条好评,哪怕的确好。因为祈求和讨好本身就代表了不自信,红包就是贿赂。但是,任何遥远都是相对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总有那么一天,它就会真真切切砸到自己头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轮到她去低三下四去求人。
为了生计,不得不抛弃知识分子的矜持,转发朋友圈的时候,她有某种悲壮和屈辱。纵然如此,她仍然心存不甘,就想不露声色又含蓄内敛地达到目的。她静悄悄地转发,配上三个玫瑰图案,不再多写一个字。她想,看到朋友圈的人,会猜到我的内心吧,会投票吧?
点赞慢慢汇集,可仅仅是点赞。大多数的人,只是看一下标题,点个赞就走,丝毫不在意链接里面的乾坤。你要评奖,你要评职称,你心中着急焦虑彻夜难眠,你满脸爆痘内分泌失调,别人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在你没有央求对方的情况下,别人没有义务为你投票为你转发为你摇旗呐喊。怎么都预料不到,自己也会变成一个苦苦企盼网络虚拟投票的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之前多给别人投几次票,也不至于遭遇今日之窘迫。转念,她又痛恨起学院的比赛规则来。“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老师”,本科生欢迎就行了呗,管朋友圈微信群广大人民群众什么事?这分明就是人缘的比拼,是作弊。她愤愤不已。
如今的学术会议,会期只有三天。第一天前往目的地,去酒店报到;第二天是正式会议,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第三天返程回家。主办方节约了经费,参会者省下了时间,两者一拍即合,意见高度统一。茶歇和自助,是大型网友聚会现场。同一个学科领域,研究者寥寥数人,彼此都读过对方的论文和专著,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无论嫉妒还是钦佩,无论在网上刀光剑影“商榷”多少次,见面都热情洋溢,露出八颗大牙,亲切而夸张地握手,像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寒暄最近的成果,抱怨本校的待遇。一场学术会议中,最受追捧的是期刊主编,一呼百应,走到哪里都跟着一帮虔诚的作者,生怕错过有可能改变一篇论文命运的每一分钟。突如其来的投票,令她心不在焉起来,连主编都无心追随。会议的第二天,她又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次的措辞显然直白了一些,恳请大家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请投6 号。末尾仍然是一朵玫瑰。这一次,投票终于增加,缓慢而持续地攀升至三位数。
远远不够。她叹了一口气。差额投票,候选人有十五名,三分之二的入选比例,乍一听名额不少,其实竞争激烈。其他十四个,都是熟人,都是和她一样出于各种目的,需要这个教学奖的刚需,个个优秀,年轻有为,出类拔萃,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张老师是归国海龟,打扮时尚洋气,深受学生喜爱,拥有庞大的粉丝团,跟她比拉票,自己没有优势;李老师是学院出了名的教学能手,讲课声情并茂,侃侃而谈,把他挤下去,于心不忍。她代入了一下,如果自己是普罗大众,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不依靠红包和人情的贿赂,将怎样对眼前的十五人进行投票。反正不管怎么投,那么平平无奇的自己,没有过人之处和必须要给她投票的使命感。那么,结局显而易见,她淘汰出局。而后果呢,缺少这个奖,起码还要等一年,若是明年职称评定办法变了,还将继续等待下去。唉,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追赶永远跑不过改变。学院里那位陈老师,48 岁的老讲师,不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耗下去,好不容易凑够论文时,偏就需要项目,凑够项目时又需要经费,凑够经费时又要卡学历,逼得陈老师年近五十,还跟一帮90后00 后一起读博。第一天开学,保安拦下陈老师,不好意思,疫情影响,家长不能入内。陈老师在院办讲起的时候,众人哈哈大笑,她却有些酸楚,折磨人呢真是。总之,不会让你轻轻松松达成目标,非要变着花样搅腾你一下。什么叫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就是一个时间点没跟上就再也跟不上,你将面对彻头彻尾的落后。让你始终需要跳跃奔跑追那个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月亮,直到把自己从意气风发耗到沉默寡言。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工资、待遇,还关乎尊严,让你欲罢不能让你骑虎难下,西西弗斯一般永无止境。这样想着,她顿时觉得眼前黯淡无光,前途也那么渺茫,会场的一切像一个巨大的穹顶向她挤压下来。她闭上嘴巴,法令纹深重,本来就悲壮的脸又老了几岁。
不知道怎样结束的会议,她的心思完全被投票占领。坐在从B 市返程X 市的高铁上,四个小时,她可以仔细思考和认真谋划,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女王。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今天最后一天,拉票到了关键时刻。女王手下并没有将军和士兵,她必须俯下身子,低头求助,照例在朋友圈分享:各位亲,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多多投票,请投6 号哦。
唉,他们能听懂吗?他们会投吗?她捏着手机,手心在屏幕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汗渍。
三
她顾不得打量男人的长相。只是模糊有个印象,灰色夹克,这就够了,足以让她在从洗手间返回的路上,以这件衣服为坐标,寻找自己的座位。她揉了揉眼睛,既是养神又是思索。窥视的目光悉悉索索,像是蚂蚁爬过。她把座椅倾斜,微微左侧,侧过脸,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
高铁运行平稳,她的心却跌宕起伏。那些久远的记忆迈着小碎步纷至沓来。曾经,有没有人给她私聊,发送拉票信息呢?她在心里细数,从脑海里捕捉,好像是有吧?这类人肯定跟她不一样,起码并不排斥拉票。那么是谁呢?她挖掘大脑里的每一个褶皱。哦,周小芳,她本科室友,当年毕业后,回老家县中学当数学老师,生了两个孩儿,跟刘美阳完全不同的类型,憨厚质朴,洋溢着泥土的芬芳。隔三差五,她收到周小芳发来的链接,无非是拼多多砍一刀,又或者是积赞送礼品,再或者是孩子参加比赛,无一不体现出一个主妇的斤斤计较和数学老师的精打细算。就那么突兀地把链接发过来,从不多说一句话,大概是群发吧,属于有枣没枣打一杆的范畴,始终保持历经千帆,宠辱不惊,在拉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淡定和从容。那么就从周小芳开始吧。她斜斜地躺着,揉了揉眼睛,找出周小芳的微信,把链接投放过去。
数学老师可能没课,反应迅速,回答已投,为了证明自己,还附上手机截图。她打开投票窗口,果然多出了一票。她内心充满感激,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给周小芳真诚投票,不管是砍一刀还是积赞送卫生纸,无论是买火车票加速还是兴趣班免学费,她决心为周小芳家庭省下的每一分钱、争取到的每一点便利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对战友最诚挚的报答。
良好的开端令她信心百倍。这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呀。她又懊悔起来,以前怎么就那么害羞那么矜持那么腼腆呢?且不说错过多少免费的卫生纸卫生巾,就拿优秀教师来说,整整两天啊,就那么浪费了,难怪别人的票数飞长,肯定都是这样一张一张求来的,每一票都来之不易而又唾手可得,只需要厚着脸皮,请别人动动手,多么简单。她再一次为自己沮丧。痛定思痛,她决定趁热打铁,弥补前两天的损失。划亮手机,手指飞舞,天女散花般把链接播撒出去。微信响声四起,像是胜利的号角,全世界各地传来捷报,撒出去的种子硕果累累。她为自己的机智而自鸣得意。
女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需要稍事休息,随后再战。她合上手机,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四处张望。噢,原来男人特征明显,不仅仅是一件灰夹克。脑门又油又亮,像是蒙了一层保鲜膜。很多男人都是这样,无法逃脱谢顶的命运,只能“地方包围中央”,用周围仅存的几缕在头顶若有若无地徘徊,欲盖弥彰,徒增笑柄。男人把手支在座椅扶手上,强行霸占属于他俩的公共空间。她略微不爽,只好揉了揉眼睛,往左倾斜。
男人殷勤搭讪:“美女,你去哪儿啊?”
这是惯常的招数,这样一个油腻的男人,文化程度高不到哪里去,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伎俩了。出于对男人刚才热心帮忙的回报,她老实回答:“哦,我回X 市啊。”
“好巧啊,我也去X 市。”
她在内心就呵呵了。这趟车的终点就是X 市,这算什么“巧”?看她没有接话,男人继续发问。
“美女,你是老师吗?”
“啊,你怎么知道?”
“气质啊,你一看就是老师。”男人眉飞色舞,为自己正确的猜测而自得。似乎怕她溜走,男人继续追问:“你是教小学还是中学啊?”
她反问男人:“你看我像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
“呃……中学吧?看起来更有学问一些。”
“都不是啊,我是大学老师。”
“呀……呀,呀,呀。”男人表情诧异,不知道是故作姿态还是真情流露,发出歌剧中的咏叹调,“真是看不出来,你这么小小的,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男人用手比划了一下,“你竟然是大学老师。那你是博士吧?哎呀,我最崇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
她享受着男人的恭维。谁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骗人的鬼话。什么知性、学识、气质,在美貌面前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不然师兄怎么就转而与刘美阳孔雀东南飞了呢?其实,她对自己的长相不太自信,没人的时候她对着镜子孤芳自赏,鼻子吧有点塌,配着一张稍微宽厚的嘴,实在是平淡乏味。大约出于弥补吧,老天爷送给她一头茂密蓬松发量充裕的头发,不是黑色瀑布似的浓厚乌黑,而是钢丝球一样炸开,像蘑菇一样绽放的沙性发质。她还有一个小秘密,从小她的外号是爱因斯坦。这个外号的初衷是嘲讽她那伟大科学家一般的乱发,后来却成了她的动力——当一个姑娘不具备外表上的优势时,那就从知识武装自己吧。除了美貌,也只有知识才能让女人有一些底气,找回一点心理安慰。伴随年龄增长,这一头炸毛的乱发倒是优势凸显,当同门都为脱发秃顶烦恼的时候,她则毫无压力。自然,这是后话了。
她做出一副矜持的姿态:“哦,是的。”
“呀,呀,呀,呀。”男人再一次用咏叹调抒发内心。他瞪大眼睛,无数个问题顺着眼睛和嘴巴飘出来。无非是,在哪个大学,学什么的,教什么专业,诸如此类。
她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回答。男人的问题没完没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教环境啊。哎呀,这太有必要了,咱们国家,现在就是环境太糟糕了,你看看这……”男人指着窗外,一排排白杨树呼啸而过,“你看看啊,我们小时候,河水多干净啊,我们随便跳进去游泳。现在呢,谁敢啊?”男人捶胸顿足的模样。
“哦,是啊。”
“你一月工资多少?”
“啊?呃,那个,大概七八千吧。”她有些慌乱,不知道应该说出真话还是假话,于是选了一个折中的数字。
“呀!”男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感叹词。“呀!”男人又是惊叹:“我还以为你一个月一两万呢,怎么这么少。哎呀,读那么多年书,交那么多学费,挣这点,真是不划算呢。”
她有点窘迫。实际上,她的收入不仅仅这些。学校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科研奖励,教学工资,时不时出去做个讲座,这些零零碎碎的钱,加在一起,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她凭什么要把自己真实收入告诉这个陌生人呢?
她突然有些恼怒,这人太不礼貌了,难道不知道这些都是个人隐私吗?就算你再怎么好奇,再怎么惊讶,都应该保持基本的社交距离啊。她顿时把男人列入讨厌的阵营,决心敷衍对待,于是低头划开手机。
无数条信息弹出来,有的简短干脆,只回答“已投票”,这是最令人放心的一类,绝不多说一句话,彰显出经常拉票经常给人投票的熟练。有的故作惊讶,哇,原来你已经毕业,去工大工作啦,这是八辈子没有联系的老同学,甚至没有多余的聊天记录,这倒好,顺便告诉了他们最新动向。有的摇旗呐喊,犹如啦啦队一样发无数个“加油”,这是平时联系比较多的亲友团。还有的是不知道什么场合加的奇奇怪怪的人,大约是微商或者房产中介吧,轻车熟路,一口一个“收到,姐”,这是渴望“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一类。迫不及待点开链接,一人一票,倒也不少。
她抬起头,往后仰,再一次佯装休息。男人却像猎犬一样捕捉了她的动静,不放过她的每一分钟闲暇。
“你平时上班累吗?”男人问。
她快要被男人烦死了,哪有那么多问题。她装作没听见。
“美女老师,你平时上班累吗?”男人抬高了音调。
她确定,如果她不回答,男人将会锲而不舍地问下去。她安慰自己,很正常,在这个世界上,女博士本来就属于第三类人,大概是很罕见吧,你要理解别人的好奇。
“噢,还行吧。”
“你是不是觉得脖子不舒服?我看你一直揉眼睛,小心颈椎啊。”
“啊,是的,我们这一行确实要注意颈椎问题,这是职业病吧。”
“那你可得注意啊。我给你说啊,我就有颈椎病……”男人坐起来,向她展示自己的后颈,“你看啊,我这儿,就是这儿。”男人低下头,用手指着颈椎那块凸起。
“我这儿,医生说,原本颈椎是弯的,往前凸。”男人用手比划,“我去拍片儿,颈椎变直了,可把我痛苦的,那几年啊,经常犯困,不停揉眼睛,那其实就是头晕。”男人用手指着她,“喏,跟你一样,你以为那是犯困,其实是颈椎病导致的。”
她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后颈,试一试那里的弯度。
“我给你说,你可要注意了。颈椎病,很难受的。”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男人滔滔不绝,讲起了他与颈椎曲度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出于最基本的礼貌,她侧耳倾听。不得不承认,男人的讲述很意思,既有个人体验,又有医学知识,还有实践操作。这些年,男人像个小白鼠一样,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从不良坐姿讲到充足睡眠,从针灸治疗讲到中波短波微波照射。她相信,如果男人来参加学院的教学比赛,绝对名列前茅。
“喏,你试试。”男人不由分说,从胸前的包里掏出一串项链,挂到她脖子上,“能量珠,怎么样,是不是脖子有热热的感觉?看,你戴着正好,既能装饰,还能养生。美女老师,要不,这条你就拿走?”
四
她把钱转给男人,还有些发懵。手里的能量珠,有着明媚的光泽,显示出廉价的品质和不明的来历,突然就让她清醒过来。她有些后悔,怎么就那么愚蠢,一看就是打着高科技的旗号,交纳智商税的玩意儿,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她想和男人大闹一场,索回自己的财产,可又实在拉不下脸。钱是你自愿给的,价是你自己谈的,没有人强迫你讹诈你,就算闹翻天了,也无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反复复盘,明明是坐了次火车,怎么就变成了推销?很显然,这是处心积虑的靠近和推销,男人的殷勤和憨厚,大概是一个职业销售员的伪装,竟然那么真实和熨帖,让她无从防备,一头扎进了他密密编织的网,插翅难飞无处可逃。
男人得逞了,不再把她作为猎物,仰头闭目养神,颈椎呈现自然的曲度,不知道是原本就正常还是能量珠的功劳。她心里气鼓鼓的,想,起码应该骂男人一句,作为最后的赠言,反正萍水相逢,老死不相往来了,可是自己的形象呢?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她?如果她与男人发生争执,会不会有人录下视频?会不会一举成名?会不会成为社会热点成为新的流量密码?她任由自己的胸口起伏不定,竟然想不出一个骂人的理由和一句骂人的词语。
她一口一口嘘着长气,开始为自己开脱。淡定,淡定,这么多年,她一直在象牙塔度过,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与一个成熟的销售员明火执仗。尤其是她这张脸,一眼就能看出是涉世未深毫无城府,一副好骗的样子。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就单单冲她下手呢?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人生不就在于经历吗?人的成长,是需要交学费的,她只是补上了别人早就上过的一节课。她又给男人寻找借口,唉,谁都不容易,不然怎么会坐在火车上还惦记着推销,为了卖出一根珠子,处心积虑低三下四殷切服务,帮人搬行李,找人聊天,不累吗?两百块钱,也不贵,权当是给男人搬箱子的辛苦费,看那男人侃侃而谈,很专业的样子,说不定对颈椎还真的有点用,算了算了,就算买了个心理安慰吧。
她在内心进行最后的总结陈词,似乎在弥补学术会议上蹩脚的表现。如同给学生授课一样循序善诱:那么各位同学,这位推销员是靠什么成功的呢?
高铁即将到站,温柔的女声又一次播报:“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方,将要达到X 市……”她掏出手机,报复般点击:“各位亲,最后时刻了,请帮忙扩散,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和各种群,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记得,请投6 号哦!”
“到了,给我拿箱子。”她摇摇男人,命令道。
——基于全国246个村3447个农户的调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