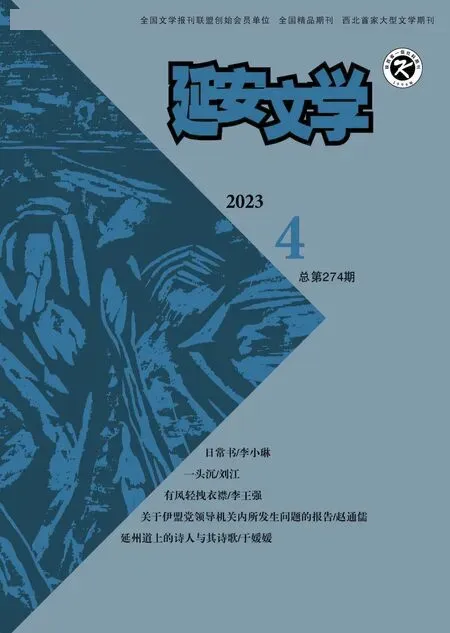几回魂梦绕高堂
席 军
父亲是个文化人
故乡有一口泉,清澈甘冽。它匆匆忙忙奔跑大约10 华里,汇入流经安塞县城的延河。
1948 年3 月,宜川战役结束后不久的一个下午,一位将领与他的卫士,骑马路过安塞县真武洞乡庙湾村,突然被一阵隐隐约约的诵书声所吸引。
这位首长侧耳细听,原来是有人大声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他颇觉惊奇,便循声觅去,几拐几弯看到泉边有个口中念念有词的少年。
其时,延安大批干部随全国解放走向各地,文化人奇缺。普通老百姓大多不识几个字,更别说能背诵《滕王阁序》了。他好奇地向少年走去,两人就攀谈起来。
通过聊天,首长知道少年虚岁十五,名叫席保儒,小学毕业本来应该到延安上中学,但因为战争,在家里休学一年多了。这位首长走后不久,乡长便来到了庙湾村,要让这位15 岁的少年到乡政府当文书。父亲席保儒当年就这样参加了工作。
两年后,父亲又被调到安塞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后来,上级给县委宣传部配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收音机如同现在的微波炉大小,能说能唱,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件。每天下午下班后,县委的干部们便聚集到父亲办公的窑洞里来听收音机。附近的群众知晓后,也跑来听。那时的安塞县委也就是几排窑洞,有围墙但没有门卫,群众可以随意进出。后来,当来听收音机的人在窑洞里挤不下的时候,父亲便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从窑洞里抱出来放在门外一张桌子上让大家听。从收音机里大家知道抗美援朝我们又打胜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人人都能吃上面包。有人听了收音机后还啧啧叹道:“收音机唱得比咱们县剧团唱得好多了!”
母亲后来曾回忆说:当年别人给她介绍对象,见面后得知男方是县委管收音机的干部,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啦。
那时候父亲被大家看作文化人。县委的好多材料,父亲都参与起草。当时的《延安报》上,也不时登载父亲写的关于安塞县的通讯报道。甚至过年时间,县委大门上的对联,也往往是由父亲来书写。
爷爷曾经拿着载有父亲文章的报纸,在乡亲们面前炫耀,村里大多数人当然是赞叹不已。但也有人说,现在公家人实行的是供给制,在县政府工作挣不了几个钱,那么一个大后生,还不如在家里种地收入多。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发生了争论:毛主席到底是住在北京还是住在中央?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我拿出一份《延安报》,指着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我爸写的。我爸说毛主席住在北京。于是大家全服了。
还有一次,晚饭后在院子里我拿着一本小人书给小伙伴们讲“普文公”的故事,在家里的父亲突然隔窗叫我回来一下。我回家后父亲笑着低声对我说:“应该是晋文公,而不是普文公。以后看到不认识的字要养成查字典的习惯。”父亲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但纠正了我的错误,同时也在小伙伴们面前保留了我的“面子”。
父亲也讲故事。那时家里只住一孔窑洞。晚上入睡前,当我们五个孩子上炕各自钻入被窝后,为了省油,家里早早地就熄灭了小油灯,然后父亲就开始讲起来:从父亲缓慢的语调中,我们知道了秦汉以来长安城里的许多故事,知道了范仲淹怎么镇守延州,知道了李自成怎么打进北京城,知道了许多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父亲酷爱读书,涉猎非常广泛。我在中学时,父亲曾经给我讲解过鲁迅的《阿Q 正传》、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父亲在学习上,非常注重向别人请教。工作之余,父亲经常到中学和老师们交流。有时他也像学生一样,拿个凳子坐到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他还曾经把自己写的文章,像学生一样抄进作文本里,送去请老师批改。
在延安工作时,父亲是延安大学图书馆的常客,不但去翻阅报纸杂志,而且常常借书阅读。时间长了,他和图书馆馆长牛振华成了好朋友。
我在大学时,父亲曾经写了一个“至善”的条幅送给我。父亲说:“这两个字出自《管子》,多数人理解为最崇高的善,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意思:‘至’是达到,‘善’是完善完美。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应当以追求完美为目标。”
我大学毕业后,父亲曾经和我一起聊过商鞅变法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记得父亲当时对我说:“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才30 岁,恩格斯只有28 岁。历史进程往往是由年轻人决定的。”
记得有一次和父亲讨论历史问题。父亲说,中国自秦以后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不应该称为封建社会;皇帝直接统治全国,应该是帝国社会(现在专家学者们也有“大秦帝国”“大唐帝国”的说法)。父亲说,学历史是为了知古鉴今。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应该是轮回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历史应该详细讨论商鞅变法及郡县制和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对中国两千年来政治体制的影响,应该详细分析汉朝盐铁专营、宋朝王安石变法和明代“一条鞭法”对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冲击,应该重点讲解中国“四大发明”及蒸汽机和电的发明等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父亲还举例说:“以前食盐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运输困难。胆大的人才敢组织马队驼队赶着牲口去宁夏盐池运盐,即使路上没有遇到打劫,来回也往往需要半个多月,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精力、财力?如今汽车一天跑一趟就能拉回几吨食盐,价格当然便宜了,而且副食公司半个月也卖不完。原因就是社会平安了,生产力发展了嘛!”父亲当年的这些说法,曾经让我耳目一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作为行政干部的父亲,尽管在1965 年就担任了县委财贸部部长,但此后职位一直在科级徘徊,直至退休。
一个人能做什么事,有时可能也是缘分。
盛世修志。上世纪80 年代,全国开始县级“地名志”编纂工作。延安市(现宝塔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到省里找了几位专家,人家都推说不了解延安的具体情况,婉言谢绝。到延安大学找了几位教授,人家以教学工作太忙为理由,礼貌推辞。三拖两拖,到了1985 年,《延安市地名志》的编纂工作还没有落实。
也不知是谁的推荐,有关部门找到了父亲,请他主持编纂《延安市地名志》。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推辞过,但我知道这项任务最终落在了他的肩上。
那时的父亲更忙碌了。开始是骑个自行车到处查资料,搞调查,往往是一大早出门到天黑才回来。进入撰写阶段后,父亲常常是彻夜不眠,伏案写作。
为了查清每一个地名的来历,为了弄清每一段历史沿革的细节,父亲不但大量查阅有关资料,还多次到西安请教有关学者专家。陕西省图书馆和考古研究所及陕师大历史系、地理系等单位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父亲的朋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父亲终于完成了初稿。拿到省里审查,书稿很快通过。得知消息后,父亲非常高兴。从不喝酒的父亲晚饭时举着酒杯对我说:“我终于给咱延安完成了一件大事!”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虽然几乎整天忙忙碌碌,但却不一定能干成几件大事。
父亲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我却认为父亲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学历不等于学识,文凭不等于文化。
如果不是家乡泉边的那次偶遇,父亲一辈子也许就是个农民。有时候,一次偶然的相遇,真的会决定人的一生啊!
我到深圳工作后,父亲曾经前来和我同住。有一次我们站在大海边,父亲望着漫无边际的大海感慨地说:“这大海里有家乡的泉水和延河的水呀!”父亲想家了!
父亲晚年回到了家乡。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家乡贫瘠的黄土山沟已经变成了青山绿水,家乡的泉水依然清澈甘冽。
于是,在我的梦里,父亲似乎依然时常坐在泉边的小院里和邻人拉话,走在泉边的小路上悠闲散步,伏在泉边的大石上写字读书,站在泉边的山峰上翘首远望……
陕北老太太
因为退休了,因为清闲了,因为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想念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于是,这位老太太告别了家里天天下蛋的老母鸡,告别了门前亭亭如盖的老槐树,告别了窗外情意绵绵的延河水,也告别了小区里恋恋不舍的老邻居们,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北京,也来到了我所居住的深圳。
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离大海边的深圳太遥远了,遥远会使人感到陌生。老太太初到深圳时,因为语言交流障碍,很少与人交往。老太太曾经感叹地说:我们陕北话毛主席都能听懂,广东人咋就解(hai)不开呢?
革命圣地延安在深圳人心目中太神圣了,神圣能使人产生亲近。陕北人又居住在延安,在许多深圳人心目中如同是北京人又居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一般。当人们知道这位老太太来自陕北延安后,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友好:早上取酸奶的队伍里会有人请她优先,傍晚散步的路上会有人向她问候;同时,有人操着生硬的广东普通话主动来与老太太聊天。由于不很熟悉,大家都称她“陕北老太太”。
与人聊天时,老太太很为自己的延安人身份而自豪:
“毛主席那时常常和我们延安的老百姓拉话呢……”
“毛主席在延安住过的地方离我们小区可近哩……”
这位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本来,母亲一贯为人低调,到老年后才有了这种近乎“自我炫耀”的表现,其实,这只是引以为傲的真情流露。实际上,母亲的一生,大多时光都是在平凡、艰难、愁苦中度过的。
因为“陕北老太太”这个称呼在小区太“知名”了,母亲的名字反而知者甚少。其实,母亲叫王义连,生于1936 年阴历九月十三日。1952 年与父亲结婚后,母亲先后生育三男二女。由于父亲工资很低,为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母亲那时的艰辛想起来就令人心酸……
在深圳,母亲常常与我们回忆起那难忘的过去:在上世纪60 年代困难时期,母亲曾经种过地,砍过柴,挖过野菜,吃过树皮。70 年代,为了解决家里的各种费用,母亲起早贪黑去当零工,给杨家岭的2 号工地挖过地基,给王家坪的革命纪念馆砌过砖墙。到了80 年代,家里先后有四个孩子上了大学,母亲又在延安地区医院病员灶当炊事员,并把做好的饭担到那座六层的住院大楼送给病人;那沉重的担子压在她的肩上,一日三餐,一餐几趟。如此楼上楼下,楼下楼上,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直到母亲退休……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家里太困难了!我刚上中学时,只有十二三岁,仍要在假期和哥哥到建筑工地提泥、抱砖、拉沙子、背石头……
在深圳,母亲与我聊天时,仿佛我还是个小孩,常常不忘给我叮咛“教育”。她所说的三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母亲说:“紧起鞋带往前爬。”这句话嘱咐我应该怎么工作。
母亲说:“人存好心福自来。”这句话教育我应该怎么处世。
母亲说:“让人一步自己宽。”这句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人。
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说:“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母亲没有上过学,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几乎再不认识多少字。我常想,如果母亲有点文化,也许会成为一名好老师,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的教授或学者。
在深圳,母亲一口地道的陕北话,与人交流往往很不方便。于是,母亲不但学习讲普通话,而且尽力学习当地语言。久而久之,经常与母亲接触的那些人,逐渐明白了“圪拉拉”(缝隙)、“圪崂崂”(角落)、“尔格”(现在)等话的含义,而母亲也能用“睇”(看)、“莫乖”(谢谢)等广东话与当地人交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应该算是一个陕北语言文化的传播者。
在深圳,母亲与当地人交往逐渐深入。一名姓樊的深圳籍香港退休法官回家乡,登山时被一条窜出的毒蛇咬了。他挣扎着刚走下山便昏了过去,恰好被母亲发现了。后来医生说,再迟一会就没命了。樊法官出院后宴请母亲和救治人员吃饭。当服务员给每人端上一只价值500 块的大鲍鱼时,母亲怎么也不吃,使得满桌人面面相觑。母亲说:“咱这一口下去吃的差不多是陕北农民几亩地的收入,是陕北小孩几年的学费……”后来,深圳帮延安建希望小学,樊法官知悉后,专程由香港赶回,捐出了数目不小的一笔。
在深圳,母亲的眼界大为开阔,也感受到了国家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当听说深圳原来也很穷,甚至有些家庭夫妻两人出门轮流穿一条裤子时,母亲说:“刚解放时干部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尔格早实现了。尔格的社会好!”母亲说:“以前的人怕年老了没人担水,怕遭饥荒。尔格自来水接进家,白面猪肉尽管吃。尔格的人享福了!”母亲甚至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毛主席让老百姓有吃有穿,邓小平让老百姓吃好穿好。”
在深圳,母亲也有不理解的。小区二巷住的小丽是搞舞蹈的,平时穿得极少。母亲好心地对小丽说:“肚脐眼子都露出来了,小心着凉!”六巷住的小马是炒股票的,天天在家上网。母亲疑惑地问我说:“也没见他上班,咋就那么多钱呢?”临街有个“策划公司”,母亲说:“想不到出个主意,说几句话也能挣钱赚钱。毛主席如果现在活着,他的话卖的钱不是几十辈子也吃不完吗?”……
在深圳,有位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的法国女专家,是法共党员。她曾找到母亲说,要听革命圣地延安当年的故事。然而,当年母亲还是小孩,并没有加入到那支生气勃勃的革命队伍中。母亲很遗憾,1948 年没有跟部队走。母亲对漂亮的法国女专家说,那年冬天,外爷随担架队走了,十三岁的她与十六岁的大姨和外婆没日没夜地给部队赶做棉鞋。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宜川大捷”的消息,再不久就收复解放了延安。母亲曾经认真而感慨地说:我如果那时那阵跟解放军走了,现在说不定也能“牛”得像个老干部!
母亲当年到底做了几双棉鞋我不知道,穿这些鞋的人到底后来成为将军还是烈士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当年几乎所有的陕北人都为革命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做几双军棉鞋是件小事,但这与战场驰骋流血具有同样的意义。记得毛主席1935 年10 月率领的那支一路缺乏给养的红军队伍刚到陕北时,部队衣衫褴褛。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没有棉鞋穿的毛主席的脚也冻肿了。刚刚出狱的刘志丹将军看到后,让夫人同桂荣立马给毛主席赶做了一双。毛主席穿上棉鞋后曾动情地说:“陕北地方好,人更好!”
陕北人好!陕北老太太好!——我的左邻右舍们在母亲回延安后经常这么说。
林肯当选总统后说道:“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慈爱的母亲!”我们虽然没有林肯那么大的成就,无法与林肯相比,但人类对母亲的感情是相通的。我想说: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
从一滴水珠可以认知一片大海,从一片绿叶能够发现一个春天。在我们古老的陕北黄土高原,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着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老太太。她们在这块土地上年轻过,风光过,忙碌过,操劳过,哭过笑过,爱过恨过。陕北的每一条小路,都有过她们的足迹;陕北的每一个村落,都有过她们的身影。陕北民歌没有她们不动听,陕北剪纸没有她们不生动,陕北的生活没有她们不动情,陕北的故事没有她们不感人。她们的酸甜苦辣,她们的喜怒哀乐,使得陕北这块土地更加雄浑,更加瑰丽,更加苍茫,更加壮美,更加迷人!陕北的历史是男人们风风火火的历史,也是女人们朴实勤劳生息繁衍的历史。
太阳总是默默地从陕北的山头走过,母亲啊!您老人家啥时再来深圳呢?
月亮也会静静地在陕北的小河隐现,母亲啊!您老人家能给我托个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