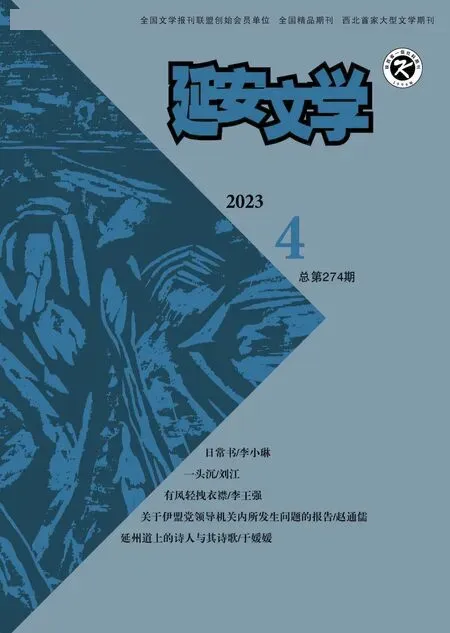我们村的北京知青
旷 野
我们村叫十甲村,座落于陕北延川县青平川。
2009 年,一大批北京知青组团回到了这里,以此纪念他们插队四十周年。
瞧吧,陆征、孙秋来、戴允林、周萱、曾伟、胡群海、杨西、乔淑秀、姜向阳、吕树恒、刘德森……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当年意气风发战天斗地的青年们,在岁月的洗礼下,现在都已变成了老人。但是他们的身子骨依旧像这里的大山一样坚挺,浑浊的眼神虽然已不那么清澈明亮,但依旧坚毅。
拂去岁月的面纱,他们也认出了村里的老社员:张信、张明、刘玉信、王树业……当得知村民们为了欢迎他们,在公路两边伫立了两个多小时后,知青们热泪盈眶,他们和老社员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重走村里的条条巷道,重登周围的山山峁峁,从深井中打一桶井水,用半个葫芦做的瓢舀一瓢甘泉狠狠地喝几口,仿佛婴儿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重温着母亲甘甜的乳汁。
1969 年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学生“心儿”(延川方言,意为孩子)。
大队社员赶着驴拉车,从八九公里之外的关庄公社接回来一批北京学生,共32人,分配到我们大队的4 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8 名知青。从此,这些首都青年,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记得我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位讲“洋话”的阿姨来到我家,拿出一套领子上带红领章的小军装,与我妈妈一起给我穿上,还给了我一把牛奶糖。我把奶糖放进嘴里,吧嗒着嘴,美滋滋地嚼起来。阿姨把我抱起来,亲了一口,夸奖我穿上小军装像个小解放军。妈妈说这套小军装是走了远路的,是曾伟阿姨回北京探亲时买的。曾阿姨是北京学生,比我妈妈小两三岁吧,她们关系特别好。由于我爸在关庄供销社工作,平时不在家,曾阿姨就经常来我家给妈妈作伴。
我们村名气最大的知青要数北大校长陆平的儿子陆征,他是四队的,是我们村的知青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一批知青,提了一桶汽油,登上娘娘山,一把火将娘娘庙给烧了,引起了轰动。当时“破四旧”运动风起云涌,这座庙自然成了封建迷信的象征。不过,现在娘娘庙早已修葺一新,每年的庙会成了远近乡邻朝拜的地方。
陆征和二队的姜向阳学历最高,是高中生,其余都是初中生。
姜向阳在知青里“受苦”(陕北人把干农活叫受苦)最能行,干农活丝毫不比社员们差,深得社员们的喜爱和肯定。
二队的李玉纯是著名的长跑健将,每天都要从我们村和邻村之间跑个往返,风雨无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成为乡村公路上一道别致的风景。
二队的戴允林是女知青,很能吃苦,担粪、开拖拉机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竟然还学会了很多男知青都学不会的牛犁地。犁地翻起的土疙瘩得打碎才能播种。戴允林个子高,一般的打粪拐子(一种T形木制农具)手把太短,根本用不成,总要把腰弯得很低很低。村里木匠给她特制了一个长把的,用起来才得心应手。她打起土疙瘩来,真是“只见黄尘不见人”,经常赶着前面犁地的人一路小跑。
四队的胡群山、胡群海是亲兄弟。兄弟俩最擅长挑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挑着沉重的麦捆行走,时间不长就把肩膀压烂了,兄弟俩咬着牙,坚持挑,直到烂了的皮肉长好,这让整天受苦的村人们自叹不如,竖起大拇指夸赞:“两个灰汉娃娃!”。
河里的低哨盖是个冲积而成的深水潭,两岸全是巨型青石,可以站在青石上跳水,是我们村的天然游泳池兼澡堂子,但只是男人们的天堂,与女人无关。每到夏天中午,劳累的男人们很多都泡在低哨盖里,有的戏水,有的洗澡。男知青们自然成了主角,三队的王虎、李树恒潜水谁也比不了,他俩在少年游泳队学过几年,每次潜水都要争个高下。
从1972 年开始,知青们陆陆续续通过招工、招干、升学、返城等途径离开了我们村。
经过几年战天斗地的农民生活,知青们认识了农村,认识了生活的艰辛,认识到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学会了耕作、播种和收获农作物,从初来乍到的韭麦不分到后来的行家里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收获。
陆征招工到宝鸡电力机车车辆段,做了机修电工,技术非常好。如果对口调动的话,通过父亲的关系回北京肯定不成问题。可他父亲说,他在铁路系统8 年,从没有给自己办过任何私事,现在也不能这么办。最后,陆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工作需要,先调到石家庄电机段工作了3 年,最后又找了个对调的机会,才回到北京。
曾伟先是招工到延长油矿供电车间,后来才回到了北京。戴允林和周萱是走得最晚的两个女知青。
周萱当时是我们大队的小学教师。我上二年级时,周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让我们跟她学普通话,要求读课文一定要用普通话。我们这些“心儿”从7 岁上学起,就按照周老师的要求刷牙了,这在偏远的陕北农村真是不敢想象。
村里很多家庭隔一段时间就会请老师吃顿饭,我们家也请过几次。记得有一次要请老师吃午饭,去周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请她时,她正躺在放在炕上的床上午休。我当时想,好好的炕不睡,非要把床放到炕上睡,怎么这么怪呢。长大后慢慢理解了,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她们,可能确实睡不惯陕北的土炕。
我们村每年正月都要唱戏,那可是周老师最拿手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导演、主演的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吸引来周围好几个大队的社员来看热闹。那真是人山人海,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小孩子个子低,大人们索性把我们架在脖子上。周老师扮演的是柯湘,男教师刘成员扮演雷刚,在永坪中学读书的我二爸张永海则扮演国民党军官。那时候我们小孩子最想看我二爸,穿一套军官服,拿着道具手枪。我们经常抢过他的军官帽歪戴着,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手枪举得高高的,拿腔拿调地学他说的台词:“团座有令,带共党!”
有时候晚上也演戏,由于那时还没有拉上电灯,社员们发明了一种晚上照明的方法,就是在戏台的两端分别栽根粗木桩,拴上粗铁丝,做三五个棉花团,按照一定间隔挂在铁丝上,蘸上柴油,开始演戏的时候,把几个棉花灯点上,顿时灯火通明。等柴油快燃烧完的时候,负责蘸柴油的社员端起盛有柴油的脸盆让棉花团完全浸泡进来,浸泡好了,端着脸盆离开戏台,不一会棉花团就又燃烧得很旺,恢复了明亮。
这就是我们村知青时代的春节晚会,周萱老师俨然成为我们青平川远近闻名的“杨春霞”,在社员们心目中,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明星大腕。她后来回忆当年大搞文艺活动时说:“除了爱好,也还是有点私心的。那时每晚都学大寨修梯田,我搞文艺,就不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1975 年,周老师也返城了,不过返的不是魂牵梦萦的北京城,而是另外一座城市——飞机城阎良,成了飞机制造厂的一名职工,直至退休。
戴允林则于1976 年直接返回北京,在某科研单位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她在长达七年的插队生涯中,与我们村学校的冯校长结下了很深的姐妹情,至今仍然保持联系。
男知青走得最迟的是刘德森。我们都上三年级了,他还总在我们学校里出现,因为他住在学校旁边的窑洞里。直到1977年,他才招了工,成了铜川矿务局的一名工人。
知青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同时也吸收了这片土地的养分。他们把陕北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尽力帮助着故乡的亲人,尤其是孙秋来,帮助的人最多。
孙秋来先是招工到子长县邮电局,后来回了北京,办了一个养殖场,靠养鸭子致了富。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的亲人们,资助很多村里的孩子上了大学。他还吸收村里十几个后生到他的养殖基地工作,不仅让这些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泥腿子到北京见了世面,同时还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孙秋来还帮扶了村里创业的村民。他得知村民刘罗罗正在为办养猪场缺资金而发愁时,二话没说,立马汇来6万元。到目前为止,他前前后后资助给我们村的资金接近20 万元。2017 年,孙秋来担任执行董事的集团投资6000 万元,在十甲村建起了鸭子现代化养殖、加工基地,建成了陕北第一座北京烤鸭炉。他说:“我只想低调地做点有意义的事,只想在晚年为养了我们八年,手把手教会我们生活,教会我们做人的陕北人民做点事……”
这次重回故地十甲村,知青们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回延安、回延川、回十甲,四十年漫长的岁月,山没变,水没变,乡音没变,乡情更没变。
几天的再聚很快结束了,当知青们再一次离别时,是那样地依依不舍。有人说:“咱们每人带一袋泥土回去放在花盆养花吧,这样就能天天和故乡在一起了。”这个提议多好啊,大家不由分说找来袋子,装了泥土。
知青们载着浓浓的乡情和满袋的泥土告别了,乡亲们和欢迎他们回来时一样,簇拥在公路上不停地挥手,依依不舍。知青们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请等待吧,这片深情的土地,这些深情的人们,我们还会再回来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故乡。